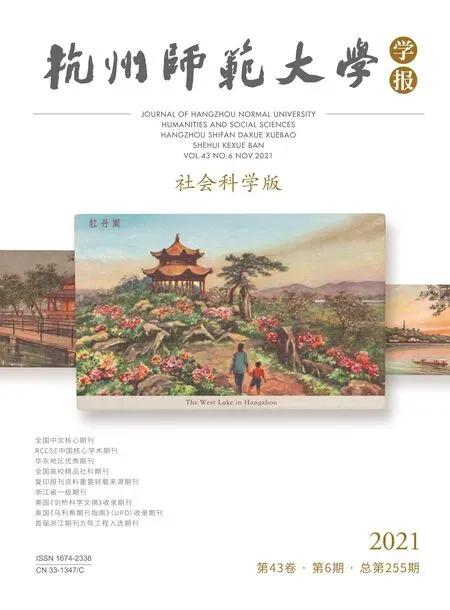王船山的家国情怀及其精湛智慧探论
2021-01-17王泽应陈佳文
王泽应,陈佳文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对家庭与国家的连带性认同以及将家与国有机结合起来的伦理情感与价值精神,展现的是不同于其他民族与文明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鲜明的共同体特质。家国情怀的生成基础在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与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以及“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情系家国、心忧天下,对家国情怀作出了全面深刻而又颇多独创之见的阐发与论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美德的伦理内涵,而且将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船山家国情怀中“家”对“国”的初始意义和拱立价值
船山的家国思想既肯定了家与国的不同之处,更揭示出家与国的连带之处,并对这种同异关系予以辩证的分析,由是对家国情怀作出了既继承前人又颇具自身独创性意义的价值论证。他借用“理一分殊”来对齐家与治国的本质内涵作出界定,指出:“齐家恃教而不恃法,故立教之本不假外求。治国推教而必有恒政,故既以“孝弟慈”为教本,而尤必通其意于法制,以旁行于理财用人之中,而纳民于清明公正之道。故教与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1](P.438)齐家主要凭借的是教育、教化和教养,立教之本是不需要倚重外在因素来建构的,重在启发启迪家庭成员的良知自觉和道德精神及其品质的培育、维护和讲求,治国则需要道德与法律等多种要素协同作用,不仅有以孝弟慈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而且要有对法治精神的认同和遵守,并使民众能够认同并遵循清明公正之道。整体上而论,教育和修养是可以兼成的,政治与教育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们应当将其结合起来加以统合式的考察。在船山看来,“治国之事,有政焉,有教焉。而自国而天下,则所推行者政也;自家而国,则所致一者教也。盖家之与国,政则有大小公私之殊,而教则一也”,“夫家国不同,而齐之治之者,同此身也,同此修身以齐治之也。其所以教家国者,同一理也,同一心也。”[2](P.76)齐家和治国的不同在于前者重视教育、教导和教养,后者除了政治的教育外还注重政治的治理和法制,而其联系则主要体现在“教”及与修身的关系上。无论是齐家抑或是治国都需要也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导。君子尽孝以事亲,“家之人皆知孝焉,则国之臣民所以竭其忠、尽其职而事君者,理在是已;尊之亲之,其道同也”[2](P.76)。不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够尽悌以事兄,那么“家之人皆知弟焉,则国之卑幼所以尊耆年、奉上吏而事长者,理在是已;敬之顺之,其道同也”;如果一个人在家中能够尽慈以恤幼,那么“家之人皆知慈焉,则国之长吏所以抚民之劳、勤民之事而使众者,理在是已;教之养之,其道同也”[2](PP.76-77)。由是可见,家与国在教养风化方面具有很多的相关性,这就决定了治国与齐家必然有一个相互依持和相互支撑的问题。虽然齐家与治国各有自己的“道”,但“喻之者同此理也,帅之者同此身也,定之者同此机也,兴之者同此心也。以吾孝弟慈之身,教之一家而仁让成,教之一国而事君事长使众之道在,故治国在齐其家,统之乎身而为立教之本也”[2](P.79)。船山的这一解释和论述体现了对家国内涵及关系的深刻思考,凸显了家对国的初始意义和拱立价值。
王船山的家国情怀思想在“小家”层面上主要集中展现在他对于家庭亲孝伦理的建设以及对“由孝及忠”“孝中含忠”等忠孝思想的阐发之中。家庭亲孝伦理的建设关系着“修齐治平”中修身、齐家的开展,是基于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家国情怀思想形成的本始要义。家国情怀的核心在于家以国为重、国以家为基的家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个人家庭之小集体与民族国家之大集体的有机结合,是己群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最佳整合。因此,对船山家国情怀的研究要牢牢把握住他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由此所彰显出来的道德智慧。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王船山忠孝节义家国情怀的基本要义。船山指出:“一字为万字之本,识得此字,六经总括在内。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万紫千红,迎风笑日;骀荡春光,累垂秋实,都从此发去。” [3](P.146)“孝”是儒家伦理的始基或本原,“培植德本”必须从培植孝心、弘扬孝道、践行孝德入手。孝德萌生于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亲子之间的自然天性之爱不仅是孝德的情感基础,更是孝道的理论基础,源于自然天性的亲亲之爱正是孝道孝德最为重要的内核,丧失亲亲之爱的孝道孝德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船山紧密联系孝的内核,以亲亲之爱作为孝道孝德的最本质、最核心的要义进行论述与阐发。在船山看来,亲亲之爱发自于“纯乎天性,无一丝毫之私欲遮蔽”的人心,即孝要从心中生发,发于纯然爱亲之心。“诚于心”就是尽孝之道,其中包含的是以亲亲之爱培植孝心、践行孝德的伦理要求。基于此,船山从孝应当纯粹的诚于心而非有所求的非功利性角度论述孝道孝德,认为“畏谴责而孝者,子之谊衰” [4](P.106),子女尽父母之孝道不是也不应该是害怕受到舆论的谴责,如果是因为害怕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对父母尽孝,那就意味着子女的孝义已经趋于衰落。船山还结合孔子的养亲和敬亲来加以论述,指出:“夫养者,子事也,非事亲之事也。以养为亲之事,则将以养为亲所待于我之事,是谓其亲以需养为心而以事之也。”[5](PP.387-388)如果子女仅以“养”待父母,就会使“孝”沦为物质层面的供养或赡养,从而缺失对父母精神层面由爱而生起的诚敬之心,这就丧失了“孝”的内在精神即孝敬,这种以物质性的养为“孝”是难以同“犬马之养”区别开来的。只有从心灵深处敬重自己的父母才能使孝道区别于动物。“君子事道,小人事养。故为人子者,苟以养为己之事,而不敢谓亲之我需。惟然,则亦恶敢以亲之身致之以报养乎?致其身以报养,抑将贸其身以求养。为人亲者,抑将贸其子以资养乎?”[5](P.388)船山认为,以“养”作为事亲之孝就会使孝沦落到功利主义的层面上,丧失其纯粹的“源于性,诚于心”的道的层面含义,缺失对父母由内而发的敬爱之心。由此可见,船山是从内在的诚敬之心而非外在的行为规范来对孝道孝德进行阐述与建构的,他所推崇的是非功利性的、纯粹敬爱之心的孝敬和诚孝。
船山认为,孝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与其他道德规范同源于天地之理的内在道德情感、道德品质和伦理准则。“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笼统。性即理也。”[1](P.655)这种源于性与理的孝既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自然天性蕴涵,更有在实践中养成和德化中培育的修为伦理指向。“孝友之德生于心者,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苟有其心,不能施之于行,则道不立而心亦渐向于衰矣。”[6](P.669)船山十分重视孝的行为实践的作用,把践行孝道放在学孝、知孝的前面,认为孝在知行上是行重于学,在孝的先后逻辑上是行先于学,不待先学孝而后行孝,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5](P.418)”一样,须落到实处切行实践。而学孝只是学习其中的礼节与精神,而不可乱其轻重与先后。船山批判先学而后行的孝道观,指出“‘学而后知父母之与我为一身’,非知孝者之言也。诚学而后知父母之与我为一身,终漠然其不相为一也。……故学者,学其节文而已”[5](PP.418-419),认为“世岂有孝弟而可谓之学耶?学也者,后觉效先觉之所为。孝弟却用此依样葫芦不得。虽所为尽道以事亲者,未尝无学,而但以辅其尽性之功,则辅而非主”[1](P.589)。船山指出先学而后知是不知孝,孝本是不学而知的。因为学是一种后觉效仿先觉的行为,孝发自天性之爱,诚于心中之爱即可,“非求合于舜”依样画葫芦去模仿而缺失其中的诚敬之心。船山也并不否定学孝的价值,认为学孝可以起到辅助“尽性”的功能,但尽孝更需诚于心、践于行,强调孝要于具体事亲活动中用心去感悟与践行,把孝道落到实处然后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形成美德意义上的孝德。
在践行孝道过程中,船山强调事亲尽孝要“诚于心”,认为“孝弟者,生于人之心而不可以言喻者也”[6](P.521) 。因此“孝子于亲,忠臣于君,孤致其心而不假于外”[7](P.257),“吾有父而吾孝之,非求合于大舜;吾有君而吾忠之,非求合于周公;求合者终不得合,用力易而尽心难也”[7](P.182)。孝存在于人的心中,尽孝只需“孤致其心”“诚于心”,求致于心中之孝,与心中之孝相合即可。而非假求于外,求合于大舜,流于外在表面的道德形式,而丧其内在的真义,失其“道”。“乃中心爱敬,即可自喻,而事亲之际,不但礼文之繁,即其恰得乎心而应乎理”[1](P.708),事亲要心中存敬爱之情,不被繁杂的礼文教条所束缚,自生诚敬之心,做到无微不至地温清定省。
船山基于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天性之爱对“孝”进行论证说明,直接地阐发了“孝”发自于道德主体内部“源于性,诚于心”的主体性,凸显的是孝子在孝这个伦理范畴之中作为行为的主体所应有的那种出于本身的意志认可并发自内心地主动去践行而不受其他外在意志干扰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这种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落实到具体的道德实践之中就具化成了“诚于心”的孝道、孝德和孝行。这种“源于性,诚于心”的孝是修身之基、齐家之本,是家庭生活幸福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保障。
在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与家国一体的价值构建的视域下,孝的要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在家尽孝”的“小家”的层面上,而应当从“小家”之孝中予以升华,上升到“大家”之忠,实现“小家”与“大家”的圆融相通。“小孝”为在家事亲尽孝,“大孝”则是为国尽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8](P.2)《孝经》认为孝不能仅仅停留于事亲,而要上升到事君,最后上达于立身行道之大业。而立身行道之大业则体现在事亲之孝与事君之忠之中,即应以事亲之孝为基,上升到大孝之事君和爱国之忠,于事君爱国之忠中实现立身行道之大业,从而真正实现孝的圆满贯通。船山虽然不赞同且批判《孝经》中“移孝作忠”的做法,认为事亲事君有着“全恩明义”的根本差异,二者“事之之道异”不可简单地照搬互通,但船山并不否认《孝经》中由孝到忠,再到立身行道成业进路中所蕴含的由“小家”到“大家”、由“小我”到“大我”的自我实现路径以及“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认为忠孝内部之间存在着道德情感的互通性,即孝作为为仁之本、诸德之始,孝德完备可以为忠德的践行提供情感的保障,忠的情感基础在于孝,因此“教家者教国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长、使众之本也”[1](P.431)。家庭之孝可以上达事君爱国之忠。
船山家国情怀中的忠孝观是基于道德情感“由孝及忠”推进式的,跟先儒基于政治目的“移孝作忠”等同式的忠孝观有着本质的区别。王船山赓续并发展了传统儒家的孝本思想,认为“孝为百行之源,孝道尽则人事咸顺。故曰‘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亦曰‘资以事君而敬同’”[1](P.604),指出了孝是立身行道的根本,是尽人事、明事理的前提保障。“孝弟慈者事君、事长、使众之本也。唯其不假强为,则同命于天,同率于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仅可通于家而不可行于国也。”[1](P.431)孝不仅只是“事亲”一义,而要从家庭之中延展进入到社会与国家层面“事君报国”“立身成业”。孝与忠虽为两种不同的道德伦理规范,但同源于“性”、归属于“天理”,具有形而上层面的一致性,而形而下层面的事君与事亲在道德情感上的相通性为“由孝及忠”打开了一条情感进路,使“小家”之孝上达“大家”之忠成为可能。
孝源于人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自然天性之爱、亲亲之情,孝为“为仁之本”“德之本”皆是基于人的自然天性之爱与亲亲之情,由天性之爱、亲亲之情由近及远、向外扩充至他人及物而形成人的系列德目,其中暗含的是孟子所提倡的“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进路。“亲亲而仁民”展现的是推孝之亲亲之情至陌生之他人,对陌生之他人施以亲亲之爱,实现由孝之情上达仁民之爱。同样仁民之中必含亲亲之情,不亲亲何以仁民,对父母不孝不爱何以关心、爱护他人,只有亲亲才能仁民、爱物。“唯孝子不忍其亲之心诚切充实,施及于老者,一以事父之道事之,故能然也。”“孝子亲没而思慕之心毕世不衰,见人之老,瞿然心动,自不容已于爱敬,况爱老敬长,人心之所同。”[6](P.701)只有亲亲之情、孝亲之心诚切充实,才能把爱由近及远扩充至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至孝之心及人而爱人,即可由孝达仁民、爱物。船山的孝并非仅仅停留在爱亲之孝上,而是由家庭亲孝伦常之“小孝”上升至国家层面的精忠报国之“大孝”,即“大孝至忠”,“大孝”应当上达“仁民、爱物”,践行“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天下”的公忠理想。
二、船山家国情怀中“国”对“家”的整合意义和保障价值
家国情怀必然是也应当是一种由家及国的伦理连带性认同和以国护家的价值确证性建构,要求“家”的伦理精神建构必须指向对“国”的建构性认同及其护卫,同时“国”的建构自然也理应凸显出对“千万家”的尊重与保障。家国情怀蕴含着既注重家庭建设又重视国家建设的关怀取向,充盈的是对家乡与祖国深深的爱恋之情和认同之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的认同即体现在为国尽忠、保家卫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上。
在王船山的家国情怀思想中,“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是辩证统一的,孝是忠的前提与保障,只有“在家尽孝”,于父母行孝道,才可能“为国尽忠”,做到真正的、纯粹的忠于国家。同样“为国尽忠”是对“在家尽孝”的升华,大孝至忠,忠是对孝道精神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实现。如果说“在家尽孝”之孝是家国情怀的起点与基础,那么“为国尽忠”之忠即是家国情怀的落脚点与价值归属。“为国尽忠”的忠德思想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忠,即忠于君主的“私忠”与忠于国家、忠于天下的“公忠”。忠于君主的“私忠”,在王船山看来并非是“以天下私一人”,因为船山认为君主的设立是天所要求的,是天之德与人之公的体现,“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9](P.67)。忠于君主并非只是忠于君主一人之私利,而是忠于君主这一身份所代表的国家与人民,即私忠之中蕴涵着公忠的指向。同时船山对于不分对错无条件服从君主的“愚忠”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事君之忠旨在“明义”,“无隐以明义,道之准也”[9](P.395)。船山指出“潜室套著说‘天下无不是底君’,则于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者之嚆矢;其根原差错则与墨氏二本同矣”[1](P.1014) 。对君主无条件服从的“天下无不是底君”之“愚忠”与墨家的“无父无母”之“兼爱”犯的错是相同的,都是不讲差别、绝对地看待问题,没有立足于现实,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故其流弊众多。船山反对“天下无不是底君”的观念,认为忠君并非愚忠,而是要心存大义是非分明,不能助纣为虐。“君之有不是处,谏之不听,且无言易位,即以去言之,亦自须皂白分明。故汤、武、伊、霍之事,概与子之事父天地悬隔,即在道合则从,不合则去,美则将顺,恶则匡救。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如何说道‘无不是底’去做得!”[1](P.1014)君有义则从,无义则匡,不改则去之。而“忠也者,发己自尽之谓。尽己之所可为,尽己之所宜为,尽己之所不为而弗为,而后可以其不欲者推于物而勿施”[9](P.779)。所谓“忠”其实是主体尽自己精神和能力于一目标、一人物、一事业的价值确证,包含着主体对理想的忠敬、对事业的忠心、对自己所认可的人物及共同体的忠诚。船山关于忠于君主的私忠的论述并非完全的只是忠于君主一人,而是要从忠于君主上达忠于江山社稷,忠于构成江山社稷的庶民百姓,忠于国家天下的大道大义。
王船山忠孝节义的家国情怀之“忠”包含着忠于君主的私忠与忠于国家、忠于天下的公忠。私忠为王船山家国情怀的表层含义,公忠理想才是王船山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王船山的公忠即忠于国家、忠于天下,在其思想体系之中具体展现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保类卫群”的爱国主义思想、“古今之通义”的至高价值理念。
(一)“天下为公,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王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将其上升到“大道”和“大德”的高度,从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的视域来阐述“天下为公,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赋予民本思想以政治伦理的建构性特质和政治文明的合理性特质,并以此来论说国家应具的国德,据此来判断历史上国家表现形态的“国运”。《读通鉴论》一书中,船山明确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9](P.1177)。天下之所以称为天下,是因为天地之间存在“大义”与“公理”,并且遵循“天下之公”,有着“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公义所在。以“天下为公”的天下在逻辑上否定了“私天下”的合理性,从公私的角度阐明了天下并非君王一家之物、一姓之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民众的天下,所以“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9](P.669) 。船山对公私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把“生民之生死”放在了大公的层面上,是高于并优于“一姓之兴亡”的价值的。船山有“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10](P.324)的断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天下私一人”的合理性,把君位看成是“可禅、可继、可革”的,只有民众的诉求和利益才是最根本的。船山从公私的层面肯定了“民本”的地位,把民众的根本利益看作是天地所遵循的大公所在,是否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成为了“一姓王朝”公私与否的标准。
船山在政治层面进一步论证“民为国之本”的合理性,把“民”这一政治范畴与代表“正当性与合法性”源泉的“天”相联系起来,给“民”国之本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天”的合法性色彩。船山指出:“惟古帝王,知国之所自立,民之生所由厚、德所由正也,克谨以事天,而奉天以养民。”[10](P.282)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重民和民为邦本的思想,强调“民之重,重以天也”,主张“即民以见天”。“言之无疵者,用之一时而业以崇,进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于天下,而上下、前后、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征天于民,用民以天,夫然后大公以协于均平,而持衡者慎也。”[10](P.327)天下大公是治理天下之大道,以天下之大公治理天下即是获得天下之大道,得道而治可以实现万世之伟业,使天下太平。而天下之大公在于民,民与天相通,民心代表着天意,听从民心即是遵循天的指示。以民为治国之本,听从民众之诉求、维护民众之根本利益,即是顺从天之道、践行天之公,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了进一步解释民与天的关系,船山提出“天视听自民视听,民视听自天视听”的观点,把民与天直接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意识”共同体,民意即是天意,认为民与天在道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民心代表着天道,民心之向背即是天道的选择,民之根本利益即是天之公的标准。因此民取代了君主成了天的代表,使民的国本地位的合法性有了“天”的保障。接着船山提出了“即民见天”“援民观天”的主张,表面上是要“见天、观天”揣测天意,但实际上船山的真正目的在于“民”身上,是在呼吁统治阶级要加大对民众生活状况的关注度,关心民众之疾苦,知民之安危冷暖,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用心解决好民众的民生问题,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以及治国方面要重视民情、尊重民意、得民心。
同时船山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还主张“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治国方针,认为“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9](P.309),要以“严以治吏”来保障和实现“宽以养民”,使民众摆脱基层官吏的剥削与迫害。在船山“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治国经纬之策中凸显的是忧民、爱民的仁政思想。船山的“天下为公,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把民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了“一姓王朝”的兴亡之上,十分重视和关切民众的利益诉求与日常生活,把“生民之生死”看成是天下之公义所在,无不展现着其爱民忧民之情与“民为邦本”的公忠理想。
(二)“保类卫群”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个人对祖国的深厚的依恋和热爱之情的凝练表达,是爱国心理、情感、行为和生命实践的有机统一,其中蕴含着浓厚的对自己民族文化认同与担当的家国情怀。王船山“保类卫群”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其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家国情怀的集中展现。在“保类卫群”之中饱含着船山为民族谋存亡、谋复兴的拳拳赤子之心,同时也充盈着船山极具民族特色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想,展现了船山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爱恋与对民族历史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强烈自爱、自尊、自信之情。
王船山身处于明清革鼎之际,亲眼见证了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引发的惨案,深感愤慨与痛心,骨子里生发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志,凝结成“保类卫群”“自畛其类”“夷夏之大防”等捍卫民族尊严与存亡的意识和价值理念。船山提出“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邱。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1](P.503)。把“保类卫群”当成天下之君长与圣人不可推辞的使命,天下君长与圣人之所以为之“长”,之所以为之“贵”,完全在于他们能够义无反顾地代表自己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拱卫与挺立民族伦理精神,使本民族不被其他民族所侵蚀,保障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保类卫群”的核心即是维护民族之独立性与文化之崇高性,捍卫华夏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因此在船山看来“保类卫群”是最有价值、最值得高扬的行为,是立国安邦之大本所在。“保类卫群”的一个重要精神是“自畛其类”,船山提出“奠三维”的论断,“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11](P.501)。所谓“畛”就是区别、界限,人之所以为人有其独特的规定性,得天地之精粹的人是与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要与物划清界限,不能与物混为一体,丧失其本质性从而沦为物。船山认为华夏民族同样应该如此,要意识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特质与道德伦理规范,保持并高扬自身内在的本质,避免沦为夷狄与禽兽。因此船山提出了“夷夏之大防”的主张,“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9](P.502),认为华夏与夷狄就如同君子与小人一样是需要谨防沦丧,要保持自身的伦理精神与道德特质,防止与其同流合污。船山对此进一步给出了分析,认为“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9](P.503) 。在船山看来夷狄一族是未经教化、缺乏道德礼俗、重利轻义的小人,“夷狄之唯利是趋,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9](P.924) 。“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9](P.169),并发出了“盗贼之与夷狄,亦何以异于人哉?志于利,而以动人者唯利也”[9](P.918)的论断,指出夷夏之分在本质上是表现为道德教化程度的差别,“夷夏之大防”防的就是本民族的道德的沦丧、精神文化的丧失以及民族的退步。船山虽强烈地抨击与贬低夷狄之民族的未开化以及落后,但并没有从血缘、族类等先天价值判断进行种族歧视,而是从礼仪、文化、环境等后天因素进行分析,把夷狄道德水平低下归咎于后天的生长、恶劣的自然环境、野蛮的文化与家庭社会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出船山所提倡的夷夏之分根本在于道德伦理以及文化程度的高低差距,即“文质分殊”,而不在于民族、人种之高低贵贱。“保类卫群”思想的背后隐含的是船山对本民族思想文化、伦理精神的高度认同和自信,以及想借此加强民族认同感、巩固民族共同体来为民族国家图存亡、谋复兴的宏大愿景。因此“夷夏之大防”不仅是政治军事上的斗争,更是道德伦理精神与文化上的捍卫,捍卫的是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家园。
船山之所以如此强调“保类卫群”“夷夏之防”,是因为船山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华夏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想要捍卫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特质,防止被夷狄所侵略而从本根上亡国灭族。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上下五千年而不断,就在于其民族所植根的文化精神特质的挺立与拱卫,即使异族入侵、朝代政权更迭也不会致使民族覆灭,也能迅速复兴走向繁荣富强。
(三)“古今之通义”的至高价值理念
明清易代所造就的天崩地坼的情势,给王船山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与价值撞击,让船山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求索践履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从而转身于民族复兴的哲学总结与伦理精神的阐扬之中,立足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提出了“古今之通义”的至高价值理念。“古今之通义”是王船山道义论伦理思想的重要命题与范畴,贯穿了古今的根本道义与至上价值,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是船山义理学说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古今之通义”展现的是船山跳出“一人之正义”的“狭隘”与“一时之大义”的“短视”,站在民族万世不朽之基业上做出有关民族兴亡的判断与选择,其中充盈的是船山想要捍卫民族与国家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以及贯穿华夏民族自古及今精神命脉的公忠理想。
船山指出需要明辨三种不同层次或质地的道义:“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9](P.535)这三种道义在公私轻重之上需要进行明确的区分与选择。“一人之正义”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正义,彰显了正义的价值,属于个人层面的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一时之大义”则是超脱出了个人的道义层面,着眼于某一时期的整体利益,符合集体正义与道德的行为,具体展现为代表某一时期的国家政权的利益与社会安稳。而“古今之通义”则是贯穿中华民族古今历史文化价值之中的道义,是民族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维系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和价值精神的命脉,是属于道统、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之类的最高正义、至上道义。[12]基于此种认识,船山进一步对这三种道义进行价值层级关系的阐发,认为“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9](P.535) ,明确地指出公义高于私义,不可因私而废公、因一时之义而废千古之义。在“古今之通义”面前,“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皆属于“私”的层面,都要服从并让位于“古今之通义”。“三义”能有机结合而不相冲突则是最完美的状态,否则就必须坚持去私立公的原则,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与指导,捍卫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
王船山“古今之通义”的道义观在价值指导与意义具化过程中,首先关注和应用的是涉及民族存亡的根本问题,即“保类卫群”“夷夏之大防”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题。王船山立足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着眼于民族的存亡与复兴,主张挺立与高扬民族自保与复兴的伦理精神,捍卫民族共同精神家园、防止民族伦理特质与道义精神的沦丧,提出了“保类卫群”“夷夏之大防”措施应对夷狄的入侵等问题,即是王船山依据“古今之通义”的道义精神所做出的判断与抉择。在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公天下”“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公”等公义思想则是“古今之通义”道义观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价值确证,展现的是“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的公义精神。
在船山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思想中无不贯穿着“古今之通义”的至高价值理念,展现出以天下为公、大公至正的公义思想与中华民族利益至上的道义思想。“古今之通义”价值理念既展现了船山对于华夏民族文化与伦理道义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与高度自信,同时也饱含着船山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精神的存废、文化的兴衰、文明的进退存亡的深挚关切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辩护与牵挂,无不体现着船山心系民族兴亡、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三、王船山家国情怀之家国关系论的精湛智慧与和合识见
船山家国情怀既重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圆融,亦重二者之间的价值层级和理性选择,有着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以国为上、以国为本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家国情怀以忠孝为基点,具体展现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内涵要求。船山指出:“立教之道,忠孝至矣……以言教者,进人子而戒之曰‘尔勿不孝’;进人臣而戒之曰‘尔勿不忠’;……奖忠孝而进之,抑不忠不孝而绝之,不纳叛人,不恤逆子……宜可以正于家、施于国、推于天下而消其悖逆矣。” [9](P.703)船山从亲孝伦常到孤忠爱国的思想阐发中展现了其仁爱有亲、忠贞为民、大公至正的道义价值追求,同时也充盈着船山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船山强调,“虚其国,疲其民,而以养其亲,仁者弗为也” [5](P.373)。真正有家国情怀的人能够深刻认识家与国二者之间的价值层级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会做出那种牺牲“大家”而保“小家”的行为。船山还说:“圣人之于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于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道敦厚。高明者,天之体也;敦厚者,地之用也。”[5](P.381)船山家国情怀有着以家庭亲孝伦常为基点,以国家兴亡为重,以天下古今之通义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建构性特质,同时又在置重国家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下始终不忘服务于千家万户的伦理性关怀,由此成就其“微而润如乳,宏而浩于穹”的伦理神韵,凸显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与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暗含的伦理特质与道义精神对于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家国情怀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古今之通义”的道义观是王船山家国情怀“宏而浩于穹”的伦理特质与“至高至大”的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义是捍卫国家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是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伦理精神最核心的要义与价值追求。以“古今之通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伦理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支撑中华民族衰而复兴、阙而复振,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开拓向前,在无数次苦难与灾祸面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且一直保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绵不断的伦理基因与精神命脉。“古今之通义”伦理精神核心的建构基础在于人民对于祖国与民族的高度认可与热爱之情,其中充盈的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家乡走向繁荣富强的美好期许以及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中华民族从19世纪濒临亡国灭种的惨怛处境到现在21世纪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将实现中国梦的富强之路,正是一批批仁人志士与一代代中华儿女秉持着“古今之通义”的伦理精神,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献身的结果。不管在任何时期,“古今之通义”的道义观都是不变的绝对法则,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精神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建立万世不朽之伟业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献身、以国为家的忠诚与付出,“古今之通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确证。大力挖掘与弘扬王船山“古今之通义”中的丰富内涵、挺立并传承其根本精神,有利于丰富中国梦的价值建构与道义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力量、汇集人心,同时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促进作用。
王船山家国情怀另一重要的伦理特质体现在“保类卫群”的思想之中。“保类卫群”的价值旨归在于“扶长中夏”的政治抱负与价值自觉,是船山面对异族入侵、国家危亡而产生的伦理自卫与价值重建,其中展现的是船山对中华民族道德文明与伦理精神的高度自信以及对异族入侵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的种种忧思。可以看出“保类卫群”是一种自卫、自保的健康民族主义,旨在通过高扬民族伦理精神,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提升民族意识,加强民族大团结,以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来抵御异族入侵与文化侵略,以及在民族重建过程中形成一股向心力助力民族复兴。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攻坚克难的时刻,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期,内外部各种风险与挑战接踵而至,此时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民族大团结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共同抵御各种风险、迎接各种挑战显得尤为重要。王船山“保类卫群”思想中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开掘船山“保类卫群”思想的价值精神对加强文化自信和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文化自信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皆源于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自信的加强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要从培养对民族与文化的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抓起。一方面要大力挖掘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精神,彰显民族特质、培养民族情感,在提升民族归属感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高扬中国精神,传承与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内心深处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形成一股向心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拧成一根绳,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船山家国情怀肯定“家之宜即为国之教,国之法必视其家之法”,“厚于家而后国之风俗不薄,本诸身而家国相因以治”[2](P.79),这是一种以家为基、以国为重,既重视家庭建设又重视国家建设的伦理情怀。在家国共同体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基层千万家的建设与发展,同样家的发展也必须依托于国的发展,要以促进国的繁荣来带动家的幸福,实现家与国双向联动、共同发展。王船山家国情怀以家为基、从家出发,注重家庭的建设,以孝作为情感基础,由孝及忠上达至国家层面的忠爱。在家的层面,建立孝道来维系家庭稳定和保障家庭幸福;在国的层面,倡导忠德来捍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古今之通义。再通过忠孝的联动,把忠的情感来源与忠的情感基础贯通起来,由孝及忠、实现忠孝的通达,从而构建家与国的双向连通和幸福圆融的家国无间的共同体。家国情怀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液之中的价值基因与伦理精神密码。代表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家国情怀,如黄钟大吕,似金声玉振,一遍又一遍地铸造着中国精神,又如春风化雨般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大力弘扬和培养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家国情怀是当今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以孝为基、止于公忠”的船山家国情怀对培养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家国情怀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培养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家国情怀,要从家庭之孝道抓起,由家庭之孝上升到国家之忠。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与培育新时代孝道观,去除以“能养”为孝的错误风气,树立以敬爱为情感基础的孝道观,以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来激发对国家的忠爱之情,培养家与国水乳交融的家国情怀。同时也要树立以捍卫国家民族最根本利益、去私立公为核心的家国意识,把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的层面,培育“以家为基、止于国、家国兼顾”的家国情怀。
王船山的家国情怀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族伦理精神特质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挖掘与弘扬船山的家国情怀思想有利于激发人民对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提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更好地培养爱国精神。船山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具体展现为通过“小家”上达“大家”,以“私”孝的“亲亲、仁民、爱物”的进路上升到“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天下”的“公”忠理想。
当代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变幻莫测的危机与转瞬即逝的机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信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迎接机遇与挑战。王船山家国情怀思想中展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担当精神,深度挖掘与弘扬船山家国情怀思想既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汇聚人心,也可以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提供一定的精神力量支撑,以更加自信的身姿站在世界民族大舞台之上迎接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