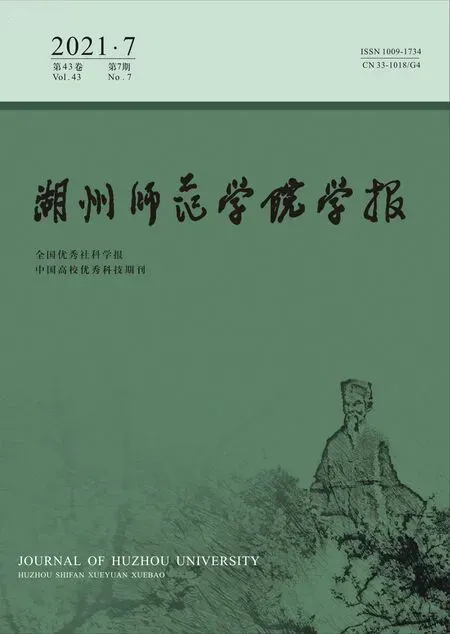矛盾与模拟*——恩古吉·瓦·提安哥长篇三部曲后殖民主义研究
2021-01-15曹霞
曹 霞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是出生于肯尼亚的黑人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是肯尼亚英语文学和吉库尤语小说的奠基人,是继阿契贝后非洲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因此,研究提安哥的反殖民思想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甚至非洲研究都具有较大的意义。提安哥从未忘记殖民主义时期留给殖民地人民的痛苦记忆,这些痛苦记忆必将作为一种文化表征不时地展现在他的后殖民写作中。他的长篇三部曲《孩子,别哭》(1964)、《大河两岸》(1965)和《一粒麦种》(1966)得到了多国文学界的好评,被公认为非洲文坛杰作,使他在世界文坛上赢得了卓越的反殖民主义小说家的称誉。在这三部曲中,他将深受剥削的肯尼亚穷苦人写进历史,再现了殖民时期肯尼亚人民的艰难生活状况,这意味着肯尼亚人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体现了提安哥对于民族自救之路的思考。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学术思潮,它深受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方法的影响,主要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问题、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全球化、文化身份等问题,以及阶级、种族、性别、文化等关系。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话语性理论,其主要任务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思和对抗。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其他各地的关系,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1]1-2。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出版为标志。萨义德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其后,最重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Spivak)、霍米巴巴(HomiBhabha)等。印度裔的美国学者斯皮瓦克的理论带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化批判色彩,她将女权主义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她认为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而具有英国国籍的印度后裔霍米巴巴的理论背景主要是后结构主义。霍米巴巴认为他的批评实践是一种将含混性和模拟糅为一体的独特话语方式和策略,其目的在于动摇和削弱关于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2]2-4。霍米巴巴作为一名出生于第三世界国家,受过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教育的知识分子,曾在他的著作《文化的定位》中,从后殖民理论角度提出新的概念——矛盾性、模拟和混杂性,并在该书中的《模拟与人:后殖民话语的含混性》一文中借用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模拟”(mimicry)与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带有差异的重复”(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的概念,将其用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上,其目的在于动摇和削弱关于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用霍米巴巴的话说,这其实是一种将含混性和模拟糅为一体的独特的话语策略。模拟实现的是一种差异的再现,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拒绝全盘接受的过程。不同于其他两位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华·萨义德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倾向于将殖民话语当作一种论战性的而非对抗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在于加强殖民权威,而是通过模拟而产生出一种相对于权威的杂体,其最终目的在于解构和削弱权威的力量。
香港学者罗永生认为,后殖民研究就是去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概念术语、想象结构等方面的遗毒,以透过形象、文本、政策和体制,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话语构成所主导的意象[3]153-154。这种后殖民文化批评方法可以被用来重新审视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本文正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的矛盾、模拟批评理论对提安哥的长篇三部曲进行作品细读,从而解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
二、长篇三部曲中的矛盾状态
霍米巴巴引用精神分析中的术语Ambivalence并将其用于后殖民理论中,用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关系中那种既吸引又排拒的复杂状态[2]100。在其看来,殖民者不是绝对的权威和强势,被殖民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模糊的矛盾状态,而通过不断的文化商讨和交流,总会产生某种对抗和抵制的可能性。
(一)对《圣经》的矛盾情感
宗教在非洲殖民地的传播是另一种隐形的殖民,它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殖民统治方式不同于枪炮,也不同于语言,而是直接作用于人民的精神世界,是人的精神鸦片,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人生价值观[4]192。以三部曲中的《一粒麦种》为例,对《圣经》的描述就贯穿始终。外来文化以一种温柔的、潜移默化的形式悄悄潜入被殖民地国家,并不断用自己的宗教信条为之洗脑,使之甘愿为之提供一切。《一粒麦种》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白人手捧圣书来到肯尼亚,那本书像变魔术般地说:那个白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甜言蜜语,态度谦恭,令人感动。接着,人们给陌生的白人一块硝过的皮革和一块地方,让他盖个暂时安身的屋子。盖好了屋子,那白人又在距离屋子几码以外的地方盖了一座建筑,他称它为“上帝的宫邸”。人们可以到那里去做礼拜和祭祀。最初,耶稣是大家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说,被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强势文化是对抗和抵制的。那个白人说,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爱,是人类的爱无法胜过的。有几人受到了感化。他们开始传播本国人难以接受的信仰。白人建起了永久居住的住房。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这一武器愚化、麻痹人民大众。殖民者先是用天国的谎言劝诱人民转信基督教,并想尽办法骗得他们祖传的土地。耶稣的教义让人民接受眼前的苦难,充满了不抵抗主义。小说描述的《圣经》是西方文明的象征,成为西方殖民者实现殖民主义的计划之一。《圣经》在殖民地被描述为一种能够给殖民地带来光明的文化符号,使得殖民者的罪恶行为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后来他们发现,这些白人笑脸的背后是一长串手上沾满鲜血的陌生人,这些人手执的不是《圣经》,而是剑。[5]14当被殖民地人民认识到殖民地国家的真实面目后,被殖民地人民纷纷拿起了武器。农民起义已经迫在眉睫了。[5]16而《圣经》正是被殖民地人民利用基督教教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争取自身权利的精神来源。《圣经》作为一种殖民权威文化的象征,霍米·巴巴将其称为“英语书”。殖民地人民在学习殖民者文化过程中,自觉地运用本土文化与殖民地文化进行对抗,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殖民文化的权威。
(二)对火车的矛盾情感
火车象征着殖民势力向殖民地内部的不断延伸,它激起了当地人对殖民者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一粒麦种》中的莫果说起过的那条钢铁长虫迅速向内罗毕延伸,以便在内地进行全面的盘剥。起来反抗的人们能把这条长虫搬走吗?它紧紧地贴在地上,嘲笑他们的痴心妄想[5]14。龙盖是全吉库尤人居住区的第一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许多享受不到铁路方便的村子却羡慕泰贝。连靠近麦赛人居住区边缘村子里的人,为了听听火车隆隆开动的喘息声,都专门前来观赏。龙盖是泰贝的骄傲。后来,铁路站台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5]88-89。这些描述说明肯尼亚人已渐渐习惯现代化帝国主义物品带来的便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入侵,但他们习焉不察。再后来,人们渐渐认识到殖民者的霸权统治,也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给他们带来的毒害,就像蒙碧所说:“我不愿见到自己的父老兄弟被火车活活轧死”。此时,火车已然充满了象征意义,它俨然成了西方文明霸权的化身。
三、长篇三部曲中的模拟
霍米巴巴将拉康关于模仿的理论运用于文化分析,认为殖民模拟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征形式,而且模拟自身也在不断地产生延异、差别和超越。一方面它是拒绝、不服从和摒弃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挪用”一切有益有用的东西来改革、调整和规范自身[6]86。“模拟”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当殖民者呼吁鼓励被殖民主体通过采纳殖民者的文化习俗、假设、建制和价值等去“模仿”殖民者时,结果从来就不是对那些特性安全复制或简单呈现,而往往是一份对殖民者“面目模糊的拷贝”,而根据巴巴的分析,对于殖民者而言,这种似是而非、似像非像的拷贝是很具威胁性的[2]106。王宁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中也指出,模拟是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是一种将矛盾态度和模仿糅为一体的独特策略[7]78-79。霍米巴巴认为这样做就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动摇了殖民权威,拒绝满足殖民者的要求、拒绝回应殖民者的凝视永远是一种有效的反抗之举[8]173。
(一)文化的模拟——教育
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所带来的现代化及其权威有一种本能的向往与崇拜,对自身的文明则因而滋生出自卑感甚至厌恶[2]103。《一粒麦种》中的基希卡刚识字,就买了一本《圣经》,一遍一遍地读摩西的故事,并给蒙碧和其他愿意听的人讲了这些故事。他相信祈祷,甚至天天读《圣经》,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孩子,你别哭》中的卡马乌也将领导黑人罢工的领袖称为“黑色摩西”——神的使者[9]56-57。《圣经》是恩约罗格最喜欢的一本书。他还非常喜欢《旧约全书》里的故事。他崇拜大卫那样的英雄人物,常常拿自己和他相比[9]63。由此可见,西方经典的《圣经》在被殖民地人民心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恩约罗格所受教育一直都是殖民统治区创办的学校,这简直就像做梦。他说:“如果我们能像贾科波的大儿子约翰那样到学校念书,那就更好了。人们总说,他已经在肯尼亚完成了学业,现在要远走高分到英国去了。”[9]5恩约罗格的哥哥鼓励弟弟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全家翻身的靠山。“父亲盼望着你有学问,能给我们全家带来希望。在肯尼亚有文化就有出息,这个道理约莫也曾经讲过。”[9]50由这些对话可知,宗主国文化被视为高人一等的,往往和财富相连。《圣经》作为一种殖民文化的文本,象征着殖民文化的权威。它作为先进文化的标志出现,被殖民地人民认为是可以照亮殖民地黑暗的一种奇迹。而宗主国传递给殖民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野蛮的低等人群,是没有文化没有制度规范的蛮夷,这个想法被深深植入殖民地人民心中。恩约罗格觉得自己虽然还小,但人们已开始赋予他一种难以言喻的使命。他心里明白,对他来说,有文化就能实现更崇高的目标和更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是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对他的希望,也是全村人对他的希望。这个目标使他精神焕发,信心百倍[9]51。即便土地被人强占,国家已经处于危亡之际,恩约罗格坚信上帝是公正的,灾难即将结束,前景是光明的[9]120。他对未来曾经满怀希望和幻想,遇到困难时,他常常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聊以自慰[9]152。这些都是殖民地霸权文化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烙印。
有别于殖民主义时期的军事占领和开展直接的殖民活动,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对非西方的控制和影响主要靠意识形态灌输和文化知识的优势。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法农指出:帝国主义长期实行同化政策。何为同化?就是让殖民地认同其政治利益、文化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模拟”体现了通过让被殖民文化拷贝或“重复”殖民者的文化来实现教化的使命[2]107。就像《孩子,你别哭》中,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恩约罗格,对上帝的公正深信不疑。直到他上了殖民地唯一一所高中后的某一天,他被抓走了,受到毒打,才发现现实世界和他信赖过的世界截然不同[9]153。在被释放后的夜里,他紧握拳头,径直朝酋长的家走去,他要为全家报仇。他流下了眼泪,但他并没有祷告[9]1154。从这个细节看出,恩约罗格再也不信任上帝,不信任统治阶级给他施加的文化教育和影响。
《大河两岸》中,查格带着儿子瓦伊亚吉来到山顶并对他讲述了多年前穆戈的预言:“用大刀砍不死那些穿花衣裳的蝴蝶,用长矛对付不了他们。除非你熟悉他们,了解他们的爱好和习惯,然后施以巧计才能将他们赶走。”[9]27此处,基库尤部族的先知已经预言了未来对付殖民者的方法便是要知己知彼,学习殖民者的文化,这样才能将其赶走。这种对宗主国文化的模仿也是对其文化权威的一种解构。为了实现这一预言,查格让儿子“去教会学校去,去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去了解白人的一切秘密,但是当心不要向白人学坏了”[10]27,并且嘱咐儿子“要忠于我们的人民,要记住我们部族的传统”[10]27。这种形式的殖民模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它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与殖民文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微妙的异同,从某种意义上解构了殖民地与被殖民地文化的差异性,颠覆了殖民地文化的权威性,实现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在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中实现了不断更新的可能。
(二)变异的模拟——颠覆
帝国主义利用文化霸权话语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同化、压制异质文化;同时,异质文化也在利用模拟、含混、杂糅等方式与策略渗透前者,使其内部发生滑动产生变异,最后达到对殖民话语的超越。石海峻在谈及模拟的变异性时提到,模拟是一种自愿而非强迫的行为,它表现的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是自我消亡的命运。模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造,是模仿者借助模仿对象而进行的自我改造,因此它常常变为被模仿者的变异体[11]19。因此,霍米巴巴提出,殖民模拟既是相似,同时也是威胁。
《一粒麦种》中的基希卡在对基督教研读后产生了自己的感悟:基库尤人的土地被被人抢夺去了,这些白人就是《圣经》里提到的以色列人的后代。黑人也是上帝的子孙,因而黑人在世界上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5]64。于是基希卡和自由战士们开始了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与殖民者进行激烈的斗争。最终,基希卡杀死了残暴的区专员罗伯逊。《孩子,你别哭》中恩戈索的儿子杀死了白人殖民者和依仗白人的殖民统治者贾科波。《大河两岸》结尾对西方文化和部族传统的商讨正是西方势力对殖民地文化折衷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霍米巴巴提出的这种模拟是具有颠覆性的,“几乎相同又不太一样”的特点与矛盾状态如出一辙,可以视为一种抵抗策略[2]106。这种“模拟”成为被殖民者模仿和嘲弄的对象并衍生出种种抵制模式。
革命英雄基希卡正是用《圣经》故事鼓舞热血青年投身革命:“拿起我的十字架——这是基督对他的人民所说的话。”不管是谁,如果为拯救自己,就会丧失生命;如果为我去死,他将获得生命。你们知道甘地为什么胜利了?因为他让他的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父母,去为他们共同的母亲——印度——服务。对我们来说,肯尼亚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至此,对殖民话语的模仿,其实与戏弄(mockery)也相差无几。于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优越与自卑、模仿与戏弄的矛盾状态中,形成一种既排斥又吸引的依存关系[2]103。
在《大河两岸》中,查格叮嘱儿子瓦伊亚吉:“你到教会学校去,去学会白人的一切。但要永远记住,救世主只能来自山里。”查格所言的“山里”就是指基库尤部落。在本族,“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人在人民需要时站出来解救他们,向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带领他们前进”[9]28。这种“模拟”策略在根本上摧毁了殖民文化的普适性价值,是对殖民权威发起的挑战,这使得这种“模拟”成为抵抗殖民权威的最佳手段。霍米巴巴运用“模拟”的策略,揭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状态。这种变异的模拟使得被殖民者拥有抵抗的能动性。这种模拟所带来的伤痛,一方面给本土文化带来痛楚,另一方面也对殖民者和殖民文化的权威根基产生破坏,为被殖民者带来生存的光明。《大河两岸》中以约苏亚为首一派依附白人殖民者,主张与部族传统文化决裂,用白人文化取而代之。以卡波尼为首的一派则竭力反对白人文化提倡维护部族纯洁,发扬部族的传统文化。两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基库尤部族传统的割礼上。约苏亚认为割礼是罪恶的行为,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而卡波尼派则认为这是维护部族纯洁性的具体表现,是联结基库尤人民的精神支柱[10]193-194。由此,两派以霍尼亚河为地理分界进行激烈的斗争。可以说,对割礼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表达的是学习西方与守护传统之间的矛盾。社会中的另外一部分力量是以瓦伊亚吉为首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主张教育救国,在两派斗争中采取折中态度,他们既反对白人文化专制统治,又对部族那些传统持保留态度,提倡有批判地吸收白人文化,以此达到将白人赶出去的最终目的。这部小说描述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手段是要批判地继承,既对殖民文化进行模拟,同时又不是完全的复制,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也体现出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矛盾和模拟策略。
模拟可以说是为霍米巴巴面对矛盾态度提供的一种方法。他的后殖民批评策略是以一种介于游戏性和模拟性之间的独特方式来削弱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即表面上是在模仿西方话语,实则通过这种戏拟削弱并破坏了西方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整体性和一致性[12]40。霍米巴巴通过对帝国话语的模拟来产生出一种相对于前者的权威的杂体,其最终目的在于解构和削弱权威的力量。殖民者使用模拟策略的目的是维持霸权,但它必然伴随这种矛盾状态,于是权利关系变得十分模糊[2]110。由于殖民关系都是矛盾的,这样它就为殖民国家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种子[2]104。
恩古吉·瓦·提安哥小说三部曲均以反殖民的“毛毛运动”为线,从不同人物的视角串起非洲人民反殖民的斗争。他敢于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展现了肯尼亚人民坚韧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颠覆了西方主流文化对肯尼亚的负面歪曲。通过三部曲中一个个人物典型事例的描写,以及矛盾和模拟策略的运用,重塑了肯尼亚人民的正面形象,解构了殖民权威,维护了民族尊严,帮助肯尼亚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们重新认识殖民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