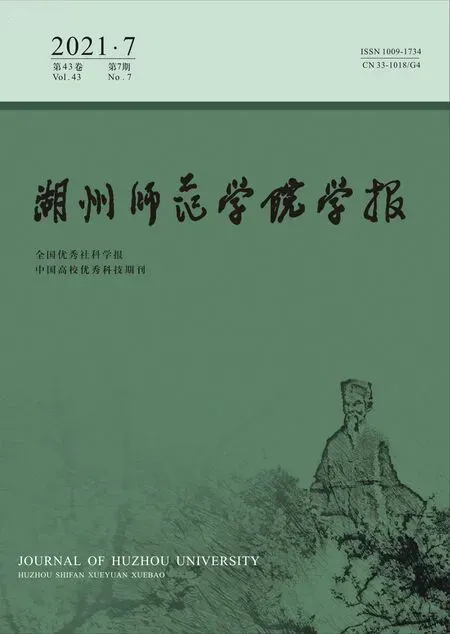全球能源互联网:突破“资源诅咒”困境的有效载体*
2021-01-15蔡聪裕
蔡聪裕
(1.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2.闽江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问题提出: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资源诅咒”困境
近十年来,以新能源为主线,国际能源形势大变局正在加速推进。如何突破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资源诅咒”困境,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是世界各国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努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将初步形成。2021年4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再次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省建设布局,科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积极促进清洁能源转型,助力对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突破。“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提出,他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没有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为一种制约因素”[1]241-243。从根本上说,“资源诅咒”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根据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现实结果却与理论背道而驰。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产业的过程中,不仅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而且还需担负自然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效应。
“资源诅咒”理论在现实中多次得到验证,资源丰裕国家陷入“资源优势发展”的困境,而资源匮乏国家却发展迅速。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产生?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理论性探讨。伊利斯赛斯·帕皮拉克斯(Elissaios Papyrakis)和雷伊·格拉夫(Reyer Gerlagh)通过“传输信道”机制验证了自然资源丰富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影响[2]181-193;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验证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负相关性[3]827-838;绍帅(Shao Shuai)等则运用概念模型和数理模型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4]632-642。二是影响因素探讨。叶森格里·奥斯肯巴耶夫(Yessengali Oskenbayev )等分析了资源依赖如何通过影响制度质量阻碍了经济增长[5]254-270。20世纪50年代,荷兰在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初期,出口顺差,但是后期却出现经济恶化,自然资源的发现带来的仅仅是不可持续的短暂繁荣。托拉森·哥理法森(Thorvaldur Gylfason)[6]204-225、杨莉莉[7]4-16、马里亚姆·莫拉德贝吉(Maryam Moradbeigi)[8]97-103等人认为荷兰病是“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胡援成、肖德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因素[9]15-23。
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环境等宏观维度对“资源诅咒”困境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而从微观视角对能源行为体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从能源行为体的“理念”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更是少见。本文认为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产生除了受上述人力资源、制度质量、“荷兰病效应”等因素影响外,还与能源行为体的理念紧密相关。因而,本文侧重从能源行为体的“理念”维度,即能源全球主义视角进行研究,分析全球能源互联网与能源全球主义的关系,并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实现逻辑。
二、能源功利主义与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强化
全球能源行为体涵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代表国家行使能源权力的石油公司等多个主体[10]2572-2584,其中既包含国家、国际组织等政府主体,也包含石油公司等市场主体。目前,全球能源行为体奉行的主流理念依然是能源功利主义。能源功利主义源于欧美国家对全球能源权力转移的担忧,他们试图通过贸易和投资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通过遏制发展中国家能源创新来维持自身在能源博弈中的垄断霸权地位[11]76-95。实践中,能源功利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目前体现为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参与国等主体在未能达成能源共识的前提下,他们以各自利益为中心,呈现区域性特征。这种能源功利主义不利于全球能源的优化配置。现实中,能源功利主义以传统能源观形式呈现,主要表现为资源枯竭观、资源战争观、资源争夺观三种类型。
第一,资源枯竭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支撑了人类近200年的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20世纪以来,世界能源和资源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长。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居高不下,化石能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触动了人们敏感和焦虑的神经。在这种形势下,能源是否濒临枯竭再次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能源崩溃、石油末日等词汇也频繁出现在各类国内外媒体和文献研究中。早在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出版了《煤炭问题》一书,认为英国即将进入能源短缺的时代,预言未来将出现能源短缺、工业崩溃、国家衰退,而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12]152。柳润墨《资源阴谋》一书指出,“就矿产资源来说,石油和天然气将在几十年内耗尽,乐观一点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0年。而根据现在的开采、消耗速度和全球已探明的储量,金矿将在15年内进入枯竭期,银矿会在20年内进入枯竭期,铜矿为30多年,镍矿为50年。除了铁矿外,支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会在21世纪内耗尽”[13]239-240。尽管国内外资源短缺或枯竭论者观点各异,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看,资源枯竭观强调的是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以及人类发展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理念把资源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要素,却忽略了环境等要素,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助推“资源诅咒”困境形成的影响理念。
第二,资源战争观。目前,从化石能源的布局来看,能源开发趋于向中东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源“霸权垄断”色彩浓厚,他们试图通过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创新来维护领导地位,而部分资源匮乏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依然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国家间的资源矛盾和争端不可避免,因资源引发国际战争的风险与日俱增,国际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导致这一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源偏离了正常市场商品的属性,并逐步演化为一种政治权力,如“石油政治”问题一直困扰世界各国,发达国家通过争夺石油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国内外关于能源战争、石油战争等主题的著作纷纷问世,如《新能源战争》《为石油而战》等。资源战争观暗含了当前石油等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带来战争风险增加的逻辑思路,不利于全球能源治理的和谐发展。其实,资源短缺并不必然助长或导致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促进合作是可以实现共赢局面的,资源短缺只是可能引发冲突的因素之一。资源战争观塑造了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助推了非洲等能源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衰退,不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是造成能源发展型国家“资源诅咒”困境的影响理念。
第三,资源争夺观。能源安全问题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趋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资源战争观强调国家间的能源博弈,而资源争夺观则从微观层面对能源公司等能源参与者进行博弈分析。当前,国际能源争夺本质上是“全球资源勘探开发及市场博弈”,其核心是各大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之间的争夺,而争夺的核心在于获取高额利润、增加国际市场占有率,而不是要控制资源。但是,目前一些国家仍试图通过主导国家能源公司的手段来实现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指出,当具有大量油矿的国家能够合作和协调政策的时候,如石油输出国1973年秋所做的那样,他们就能够对消费国施加压力,将政治条件强加于消费国。消费国如果拒绝,就会冒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危险[14]160-16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输出国可以利用能源手段实现其政治目标。因而,受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围绕能源生产、运输、市场等因素控制进行博弈,呈现出“现实主义与对抗性”的特征。但是,随着全球能源市场的日益完善,行为体和影响因素日益增多,控制能源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资源争夺观造成了能源行为体间协同力度的缺失,其是助推“资源诅咒”困境形成的影响理念。
能源行为体对全球能源的态度呈现多样化。通过分析资源枯竭观、资源战争观、资源争夺观可以发现:三者均有“以利为先、零和博弈”的能源霸权思维,均无法提供优化能源配置的可行路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能源的恐慌和担忧,是强化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本文试图在剖析能源功利主义基础上,更为理性地思考全球能源治理应有的理念,以实现“资源诅咒”困境的突破。
三、突破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理念:能源全球主义
如上所述,全球能源治理“资源诅咒”困境的产生与能源功利主义倾向有直接关系。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是“环境友好、结构合理、治理高效”。但从总体上看,全球能源治理现状距离这一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从全球能源分布上来看,各国家或各区域差异显著,大国仍主导传统能源的开采、生产、加工、运输、使用等环节。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主导了世界排名前20家大石油公司[15]1157-1162。从全球能源治理行为体来看,目前新兴的行为体参与度相对较低(如印度、中国等),很多国际能源机构参与门槛较高,他们通过会员制度等一系列审批手续将新兴治理行为体排除在外。如国际能源署(IEA)的正式成员仍是发达的能源消费国。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国动机多样,通常是基于军事、行政、外交、经济等因素的考虑,这就导致了全球能源治理效果不理想。目前,全球仍有20 亿人口处于能源贫困行列,仍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能源形势严峻,很多国家仍然不能公平获取并安全利用能源。作为能源治理主导者的发达国家,由于缺乏全局性、发展性的治理视野,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呈现“碎片化、功利化”特征[16]78-95。全球能源治理理念亟需向能源全球主义转化。
能源资源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呈现出不可分割性、渗透性和紧迫性的特点。丹尼尔·耶金(Daniel Jaykin)认为在能源问题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具有共同的利益[17]18。国内学者于宏源从能源合作、能源安全、能源主要推动者等维度探讨能源全球主义。他认为,“传统上讲,国家对其疆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当然的主权,一国的资源利用也应完全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每个国家都意识到他们在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相互依赖之中”[11]76-95。能源问题天生超越国家边界。主权国家无法垄断能源合作开发的谈判、签约、开采、争端的解决的全过程。能源问题应当放在全球能源体系的大背景中,采取跨界性、公共性、全球性(系统性)的方式和方法应对[11]76-95。能源全球主义是与能源功利主义相对而言的,其是实现全球能源治理目标的可行性理念。从总体上看,能源全球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能源生产从“有限”向“无限”的转化。世界能源发展经历了以煤炭代替薪柴和以石油替代煤炭的两次重大变革,化石能源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但是,由于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绝对储量有限性”的特点,因此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方式(如石油和煤炭的消耗)不可持续,不利于“碳中和”目标的达到,资源环境压力也会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能源的生产将逐渐由单一依赖向能源多样化、低碳化趋势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未来清洁能源可替代化石能源,有利于突破各国传统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类资源的“无限供应”,纾解“资源诅咒”困境中的资源不平衡问题。
第二,能源消费从“战场”向“市场”转化。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能源本身属于市场商品,这使得能源治理全球化具有相互依赖、分工合作的需求,以保证市场的优化配置。如电池生产行业,全球70%的锂矿来自澳大利亚,但全球多数生产地在中国,而市场却在欧美。石油欧佩克政策影响力的今非昔比,也可以有力地说明该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将通过市场贸易而不是战争或政治性干预来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市场力量将战胜能源价格的人为控制,推动能源利用方式从低效走向高效,从资源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从理论上讲,“能源全球主义”以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为工具,规避“战场”等政治干预对资源价格造成的扭曲,从而促进“资源诅咒”困境中的国家充分利用先天优势赶超其他国家。
第三,能源观念从“发展威胁”向“战略互动”转化。未来能源品种将呈现“分布式、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发展态势。如在丹麦和西班牙,普通民众可参股风力发电项目,北欧四国电网也已实现互联互通。全球能源贸易市场的完善,正不断恢复能源作为市场商品的属性。这也将改变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源威胁”能源观,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战略互动,促进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的民主化进程,建构更加开放和多元、参与性和互动性更强的能源经济体系。
第四,能源发展模式从“垂直垄断”向“扁平对话”转化。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民间组织等治理行为体数量的增多,能源发展模式主题将从“能源供应”向“能源发展”转化。与此同时,随着政府与民间组织在能源全球治理伙伴关系中逐渐发挥作用,原先垂直垄断的模式将发生变化,将逐步由“垂直垄断”向“扁平对话”机制转化。21世纪以来,以“能源治理”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和对话机制将逐渐打破 20世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国际能源署(IEA)的垄断地位。
四、实现能源全球主义的有效载体:全球能源互联网
“能源全球主义”理念的实现与否,关系到“资源诅咒”困境能否被突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认为,能源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蓝图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单元,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能源流与信息流实时流动,实现多种能源供应、传输网络及能源技术、信息技术高度耦合的新型能源利用体系[18]46-48。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通道),以清洁能源为主导,全球互联泛在的坚强智能电网。具体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将由跨国跨洲骨干网架和涵盖各国各电压等级电网(输电网、配电网)的国家泛在智能电网构成,连接“一极一道”和各洲大型能源基地,适应各种分布式电源接入需要,能够将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输送给各类用户,是服务范围广、配置能力强、安全可靠性高、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19]205。就技术层面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从价值维度分析,全球能源互联网要解决的是全球能源初次生产后的分配问题,是分配正义在全球资源领域的体现。21世纪以来,以新能源发展为主线的国际能源转型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正在引发国家间的新型竞争,重置全球能源秩序[20]62-70。结合全球能源治理转型的背景,笔者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如下特征: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对传统能源控制理念的摒弃,思维上从传统的控制、主导向分享转变,强调以共享、民主的方式进行资源开发,是一种“自下而上、从集中到分散、多主体民主参与”的发展思路,以实现参与各方的能源分配正义为目标,是实现能源全球主义的现实载体和有效途径。
具体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的特征和理念。在传统能源交易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效率差距。互联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平台逐渐打破这种效率差距,缩短或重构“传递价值”的商业逻辑[21]95-107。一方面,多元主体可以平等参与。与互联网类似,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家等全球能源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设备平等地连接到网络,进入市场。用户角色定位发生根本转变,这时用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另一方面,能源可以自由流动。在全球能源网络互联情景下,距离和资源限制将不再成为问题,清洁能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能源资源市场将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多元化综合服务平台的形成以及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助于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缓解化石能源供求,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消费,缓解化石能源的供求关系,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在国际能源署(IEA)的可持续发展情境下,与全球能源消耗相关的CO2排放量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急剧下降,实现与《巴黎协定》控制全球升温低于2℃的目标所需的发展轨迹相吻合[22]。
第二,实现资源“有效供应”,重塑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全球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降低能源的供应成本,通过开发潜力大、分布广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保障能源长期稳定供应。同时,依托全球能源互联网,取得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外送效益,能够有效降低电力供应成本。从现在开始预估,如果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年均增长12.4%,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80%[23]249。
第三,推动多方共识,解决能源争端。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使得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具有现实性和对抗性,表现为各国围绕能源生产、运输、市场的控制进行博弈,通过制定并执行能源战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如中东、中亚—里海和亚太地区能源地缘政治竞争激烈,均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伴随清洁能源大量生产,发达国家将逐步摆脱能源引起的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将加速经济发展速度。而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互联互通建设,将改变能源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大国能源垄断,推进能源治理民主化。
第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目前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地区尚有大规模未开发的清洁能源,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另外,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也有利于促进能源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如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将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智能配电网等技术实现突破和广泛应用。
五、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基本逻辑:从“权宜之计”的共通体到“全球共治”的共同体
全球能源互联网虽然可以从技术方面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但和其他技术一样,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否达到预期的治理成效,取决于全球能源行为体间的关系及全球能源治理理念是否达成共识。因而,全球能源各行为体如何达成理念共识,这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共识达成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过程,而是需要分阶段逐步完成的,笔者把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阶段性目标界定为全球能源治理“共通体”,并进一步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运行基本逻辑:从“权宜之计”的共通体到“全球共治”的共同体。
第一,“共通体”和“共同体”的概念区别。“共同体”强调一致性,即更注重消除差异性。这种模式强调形成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约束和权威,使资源分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并强调公共服务均质化、均等化。本质上看,“共同体”强调各方参与体聚合后形成新的主体,强调统一的规范。而“共通体”则更多体现的是协调性原则,即各方在协调与沟通的基础上,逐步克服差异性并寻求一致性。一般形成如下的资源分配模式:各方未形成有效的统一规范和权威,资源分配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协调基础上,强调协调后意见的同一性。从本质上看,“共通体”强调的是主体间的开放性结合,其特征是差异性的主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暂时形成一种团结的状态,具有不稳定性。
第二, 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阶段性目标是“共通体”。它是柔性实现共同体的阶段性状态,与罗尔斯提出的“权宜之计”具有类似效果。一个制度性秩序虽然无法达成道德共识,但参与方确实相信并支持它,它便是促进各自利益和价值观的一种明智方式,但这时的制度性秩序仅仅是“权宜之计”,它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妥协,每一个群体根据相对实力或优势来调和该群体价值和利益,各方经过议定达成一种平衡[24]37。“权宜之计”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处于权宜之中的参与方不一定会尊重另一方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倾向,而是优先保护和增强自己的权力,这个模式就成了“强权即有理”的榜样。“权宜之计”模式形成的制度秩序,是根据各个参与方的权力和他们所操纵的利益,通过谈判博弈后形成制度秩序的各个条款,因而这种方式下的协定条款不可能根据任何参与方的正义观寻得正义,无法达成“一致正义”的理想目标。目前,全球能源治理的现状还处在“权宜之计”的“共通体”阶段,需要建立包括原则、规则、规范、机制等在内的制度性约束,明确和强化规范,实现对国际事务和行为体行动的有效管控,这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目标。
第三,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别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的“共同体”,是“全球共治”的共同体。1971年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了“重叠共识”概念,合理地解答了如何达到理性的共识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如何达到长期稳定的问题。这对于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共识问题具有相同的适用性。罗尔斯把“重叠共识”定义为:从宗教、哲学、道德等诸多世界观推导出来或至少与它们相容,同时获得所有或大多数公民的非强迫的道德认同。在这样一种政治正义观上所达成的道德共识,罗尔斯称之为“重叠共识”[25]38-46。“权宜之计”并不是“重叠共识”,“重叠共识”寻求的是在多样化道德、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一个所有参与方都能在道德上认同的制度秩序。笔者认为罗尔斯所希望构筑的共同体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传统基础上的共同体。在构建共同体“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往往依赖于某种主导性的理念或传统,难免会带有霸权或意识形态的特征。
借鉴高奇琦教授关于共通体的定义[26]33-50,结合中国文化和语境,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共同体”理论框架,即“全球共治”的共同体。“全球共治”共同体具有如下特征:(1)其逻辑基础是“和谐共存”,强调全球能源治理参与体由冲突逻辑逐步向和谐逻辑转变。通过多次交往,判断参与体的品性和意图,逐步优化参与体,以长期和谐逻辑的方式进行交往。(2)其交流态度是“互助礼遇”,强调全球能源治理参与体需要从利益关系向朋友关系转变。参与主体可以在利益关系基础上着手构建真诚交往的朋友关系。朋友间互动的主要方式是互助与礼遇。(3)其行为模式是“权威协调”,即强调全球性能源治理的权威协调,推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能源署(IEA)、国际能源论坛(IEF)、能源宪章条约(ECT)的改革和发展。(4)其行为模式是协商民主。“全球共治”共同体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上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更多强调全球能源治理参与体间的包容、理解以及共识的达成。(5)其实现目标是“求同存异”。以“和而不同”为导向,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尊重差异的多元存在,反对用冲突和暴力的方式对待异见,在保持个性优势的基础上互相吸收彼此优点。简而言之,“全球共治”的共同体具有“和谐共存、权威协调、互助礼遇、多元协商、求同存异”的特征。
六、结论与讨论
能源市场日益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能源问题需要在全球或区域层面采取集体行动,而且只有能源各方行为体达成共识,才有可能突破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资源诅咒”困境。但是,受能源功利主义的影响,地缘政治经济斗争日趋激烈,传统热点地区矛盾冲突高涨,能源市场呈现“无共识的秩序”特征。从理念上,能源全球主义顺应全球能源有效治理的趋势,要求各方行为体放弃短期能源功利主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形成理念共识。从实践上,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实现能源全球主义的有效载体,能够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可行路径。目前,从技术层面,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设想具有可行性。但从价值层面,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否成为实现全球能源分配正义的平台,还需要各方行为体首先在理念上达成共识。结合中国本土情景和优秀传统文化,笔者创新性地提出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基本逻辑:从“权宜之计”的共通体到“全球共治”的共同体,以期实现多方行为体共识的达成。当然,本文只是从学理上抛砖引玉地提出“全球共治”的共同体理念,其构建和进展情况是与全球治理行为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体的话语权密切相关的。如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资源数据强国建设,完善能源市场机制,推进全球能源治理制度机制创新(如G20),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碳峰值和碳中和),加强全球能源治理的执行力,增加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技术的发展亦可能成为实现“全球共治”共同体的有效手段,比如是否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来推动能源共治平台的建构,这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