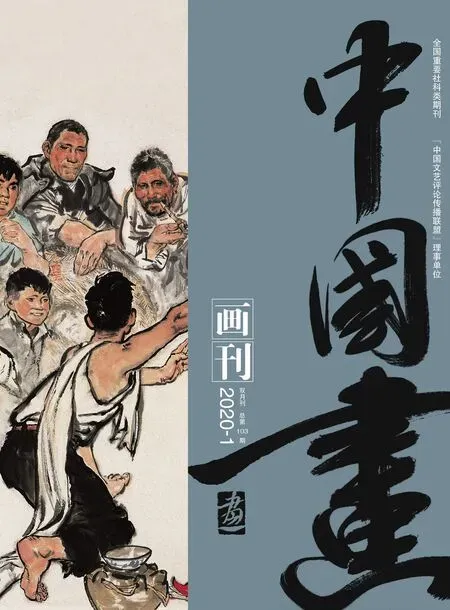论山水画中叙事性因素体现与运用
2021-01-14宋国超
文/宋国超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语言文学与绘画造型两种表现方式在对于内容的表达上各自具有其专长,先民在创作时总是试图将内容表达得更为清楚,绘画含义的清晰表达成为先民对于绘画效果的首要目的,并不以表现得更为优美为追求。大量早期画像砖以及壁画作品都包含着大量叙事情节,亦有众多图文并茂形式的作品如《山海经》《天问》等。《淮南子》载:“文王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皆著于明堂。”以上都证明,在一定时期中国绘画以叙事内容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表现完整的故事情节与表达的准确成为早期绘画的统一追求。
东晋顾恺之所作《洛神赋图》抒情、叙事相结合,山水部分将故事带入到浪漫梦幻的意境中。《九色鹿本生图》其中山林做间隔,对于不同时空的情节暗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连绵不绝的山石树木贯穿整个画面,在起到装饰画面的作用之外,又造成了对于故事情节的分割与连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于叙事空间的创造与建构,使情节有了内部发展的逻辑性。由此可以看出山水的产生,在一定成分上是作为有助于绘画叙事情节表达而出现,山水画在时空表现上都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山水画通过复杂的结体与笔墨变化可以产生一种空间转移与时间流逝的感觉,这也是叙事所需要的。热奈特曾对叙事与叙述进行过区分,他认为:“‘所指’或叙述内容称作故事,把‘能指’、陈述、话语或叙述文本称作本义的叙事,把生产行叙述行为,以及推而广之,把该行为所处的或真或假的总情境称作叙述。”山水本体创作对于“可居”“可游”的要求,也与叙事类题材的创作更容易达成一致。绘画作为空间艺术不同于时间艺术,在单幅画面中难以表现时间的流逝,但在山水画中却常常表现出时间性,“山静似太古”“荣落在四时之外”,对于空间更有一种“了然”而具有“广达”的“务虚”之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体现出山水独特的时空观,这既满足了对于叙事性的要求,同时又造成了独特的叙事形式。但在此问题上可以找到研究成果较少,希望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对叙事在山水中的丰富表现形成初步认识。绘画作为一种叙事载体,因为其艺术形式的特征难以回避自身的局限性,世间万象瞬息万变,寸毫尺素难以将时间洪流中的事件发展纤毫毕现,所以如何运用图像本身叙事,而不是作为文字内容的说明性叙事作品成为了探究绘画叙事的重要方面。本文希望通过对经典山水作品的深入分析,探究叙事类作品中如何巧妙运用叙事性因素,发挥山水在造境时空转换上的优势。
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哲学观,时空观,这都影响到山水画中叙事性的独特性。山水画善于一种特殊时空的营造,这在叙事类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叙事性作品需要时间与环境两个重要因素,山水画因素在绘画中的功用是多样的。如果以此推想,作为早期绘画中作为背景的山水画因素在叙事过程中应该具有环境因素所具有的同样功用,环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跟随着叙事进程的不断推进,叙事行为形成一个连续的活动体,因此以山水因素在早期绘画中所营造的环境不仅包括空间因素,同时也包括时间因素。当然山水画因素大部分属于自然环境,比如山川林木,云雾烟岚。又有人文环境,比如宫观舟车,庙宇楼台。但是山水画中构成因素是对于现实世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并不是“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粗糙模仿与再现,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即提到不同的环境类型“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这种总结归类是伴随山水画发展而逐渐成熟的,以期望达到通过有限的画面获得无限的意义,这当然有赖于山水画独立,因为山水画的独立是伴随着山水画因素不断担负的深厚的文化寄托以实现传情达意的功用。这当然是山水画“程式”的一种表现,所以山水画的叙事是指事会意的,是通过简练的语言与逻辑完成丰富的内涵表达。

萧翼赚兰亭 五代·巨然
山水画因素在早期绘画中一方面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同时又为画面提供了一种具有意味的空间环境,与情节人物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外在峰回路转,但当起伏的形势之下隐藏着一条绵延交错的线,这条线包含了绘画主题内在的叙事脉络。在叙事上,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可以起到引导与暗示的作用,将不同时间点的情节和谐在一个统一的画面中,又根据不同元素的分割串联形成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
例如戴文进(1388~1462,浙江钱塘人)有一幅作品名为《春游晚归图》。从名称上便有很强的叙事性特征,已经将时间与情节凸显出来。作品《春游晚归图》绘田野小径,农人荷锄返家,时天色已晚。右下角所绘的庭院前,有一位士人敲门,只见门内仆役提灯来应,提灯一举显示春游主人“晚归”的诗意。绘画技法笔墨清爽刚健,是戴进代表佳作。在作品的标题中我们可以明确获得作品主要希望表达的意图,一个是“游春归来”这样一件具体的叙事内容,另外还明确得知在时间上“晚”的具体内容。我们同样提到指事会意的叙事特征,作品在整体的气氛营造上并没有以再现的手法再现傍晚的自然景象,作品在叙事时间上采用了暗示与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来暗喻时间,第一,作品右下部分庭院里仆役提灯这一行为暗示当时天色已晚。第二,画面中描绘了田野小径,农人荷锄归家的意象,不由联想到“带月荷锄归”的诗意,同样印证了时间特征。此外,也印证了山水画与山水诗之间相互佐证,彼此生发的复杂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山水画中的时间是不会起到太大的限制性的,画家是不会完全执着于表现时间因素的,但是并不是在时间的表现上力不从心,这是山水画的智慧所在,放弃具体的局限的表现,而追求一种广义的叙事时间,笔者认为山水画的叙事是需要兼顾造境的体现,一幅山水画作品是可以存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时间点情节都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时间的体现上常常“抗心乎千秋之间”的超越之境。
山水画在叙事题材上也具有专题化与细致化的表现,出现了很多专题化的叙事题材。诸如,记游、雅集、送行、隐逸、渔夫等,又有对于时空四季朝暮阴晴雨晦的细致微妙的刻画,这也与山水文学互相引申,相互完善。在山水的表现技巧上,不同的叙事主题形成了相应的符号语汇与程式组合方式,不同叙事主题的表现均有各自不同的归纳、分析与组合。乔仲常的《赤壁图》是依托于文学内容为底本的记游山水的代表,表现了自己心象中的东坡赤壁,在笔墨气息上也暗合苏轼文辞间流畅开阔婉转幽深的意象。作为宋代文豪苏轼的记游诗文不断被画家用来发挥画意,《赤壁图》便成了经久不衰的山水记游题材,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典故。在笔墨技巧上与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有相类之处。以干笔为主,尤其注重毛笔的各种状态的运用与翻转的微妙变化。此卷以超越时空局限的手法,将不同场景在同一画卷上徐徐展开,同时配以诗文图文并貌。
以渔父图为情节内容的描绘也是诗画家极为喜爱的题材。从诗到画,历史上层出不穷,雅集送行也是一类重要的具有典型情节的山水题材,与记游山水类似,多以手卷形制表现。手卷应该算是善于叙事的一种绘画形制,让观者在展开的过程中已然具有了时间性艺术的特征,不断地舒展布景,长卷的情节构成开合起伏张弛有度。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雅集题材便是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记录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圆通大师等在主人王诜西园雅集的情形,据说此幅手卷即是他为此次雅集所做的客观描绘。在此之后,陆续有赵伯驹、马远、刘松年等人的摹本。尔后文征明、仇九洲、石涛也有同类题材的作品。叙事类山水画在叙事方式上比较具有优势的是长卷形制的选择,一种带有时间性质的形式,如上所述,《赤壁图》《西园雅集图》一类具有典型叙事情节的山水作品都有长卷形制的叙事方式,因为长卷善于情节的开合起伏变化。在《赤壁图》的叙事表达中求助于文字的解释,每一段都选取了相关的文字说明,这也是山水画与山水文学密切关联的佐证,也成为山水画叙事中一种“图文并貌”的独特叙事方式。
除“图文并貌”之外还有一种以标题点出叙事内容的叙事方式,此类作品往往具有两个特点:(1)叙事内容属于喜闻乐见的文学典故。(2)强化了山水内容的充分表现,使山水因素尽可能保持了独立的审美特征。此类作品如巨然的《萧翼赚兰亭》,除去题目,我们很难确定所绘内容具体所指,通过题目我们又在画面中隐约找到与故事情节相类的情节刻画。
恽南田评唐洁庵的画有言:“谛听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山水画的空间显然不是现实空间的再现,山水的创造性之一便是对于一种有意味的空间的营造,对于山水画而言,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独立审美价值。中国山水画的空间处理在流连万象之际颇有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超然与旷达之兴。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具有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识。既然叙事的感知使讲述事件“非现实化”,那么对于山水画的空间来讲,也必然是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如前所述,山水画的空间处理并非自然空间的再现,以一管窥之,山河大地,恐飞仙不能周旋,首先它以某种符号与象征与身处的大千世界形成对照,另外又在二维空间圆满自足,形成一个多种绘画因素相辅相成的精神空间。从而创造观古今于须臾的精神空间。当然山水画的空间处理在具有协调画面各种因素的合理之外同时具有独立的空间审美功能,古人概括出的“三远”法,以至于韩拙提出的后“三远”都是对于山水画空间提出的审美规范。,一个充满节奏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艺术家的魂灵,中国艺术家创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灵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