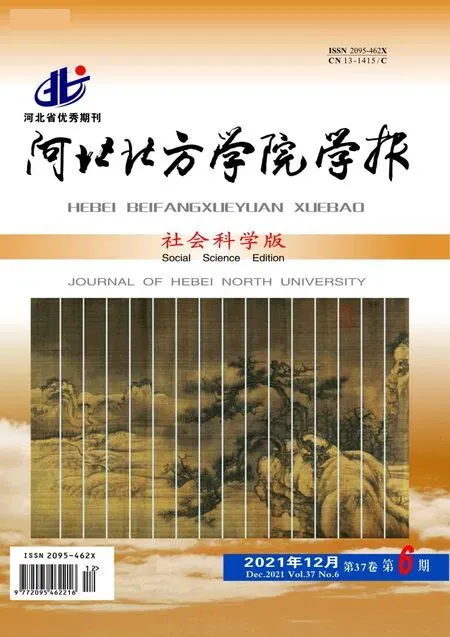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书写与身份建构
2021-01-12陈雨昕
陈 雨 昕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被中西学界列为文学经典。除了在叙事视角上的革命性创新之外,福楼拜对空间的细致书写与强调也顺应了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向,蕴藏丰富的意涵。但目前,国内外鲜有学者关注《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书写。文章将小说中以侯爵府和巴黎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异托邦空间和以婚后家宅为代表的乡镇生活空间联系起来,结合空间理论与身份认同学分析主人公爱玛身份迷失的社会成因,思考福楼拜在此刻画空间的深刻用意。
一、上流社会异托邦与爱玛的身份认知
异托邦是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且与日常处所相对立的他者空间,顺着他者的目光反观自身能让个体重新理解自身处境,形成自身定位。《包法利夫人》中,以侯爵府和巴黎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空间被长期生活在乡镇的爱玛视为异托邦。将富丽奢华的侯爵府异托邦与鄙视粗俗的乡镇空间相比,爱玛首次意识到村妇身份的局限性,发现了空间依凭社会等级划分,且广阔优越的空间只属于上层阶级的残酷现实。自此,她对乡镇生活的鄙弃也转向了对村妇身份的背离。此外,消费社会着力营造由消费景观构成的巴黎异托邦,并将奢侈消费打造成快捷实现阶级跨越的途径,这一空间幻象诱导爱玛追求贵族身份,最终形成错位的身份认知。
(一)侯爵府异托邦的差异致使背离村妇身份
福柯提出,异托邦在社会中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与日常处所运行秩序截然相反的空间,具有质疑与批判日常秩序合理性的功能。“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1]两者的区别在于乌托邦让人畅想美好未来,异托邦则指向当下,如同一面镜子让观者把目光投向现时的自我,在比照关联中重新理解自己的现实处境。《包法利夫人》中,奢华侯爵府代表的上流社会异托邦正是这面真实存在的镜子,让爱玛在比照中认清乡镇生活的鄙陋粗俗,并对自己的村妇身份心生厌弃。她在侯爵府舞会上望向窗外,听差砸碎玻璃的声音打断了她对侯爵府异托邦的观察与沉醉,将她拉回现实,爱玛回头突然看见窗外有许多向里张望的乡下人。屋内人品味高雅且生活奢华,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并谈论着异国旅行与赛马;屋外人则见识粗浅且庸俗鄙陋,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在他们身上爱玛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小说从爱玛的视角出发描绘侯爵府的生活场景,凸显出空间比照给她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波动。在乡镇,操持家务与照顾家人是女性约定俗成的义务,爱玛从小遵循这样的生活规范。而如今,真实存在的奢华侯爵府异托邦颠覆了她的认知,展现出女性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从富丽堂皇的侯爵府异托邦望向黑影笼罩的乡镇生活空间,爱玛开始质疑甚至鄙夷原有的生活,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与厌弃影响了她的一生。
侯爵府异托邦与乡镇生活空间的明显差异让爱玛认识到依凭身份等级划分的社会空间秩序,致使鄙夷乡镇生活的她作出背离村妇身份的举动。“空间用来表达社会阶层的距离”[2],宽敞的府邸属于“侯爵”“子爵”与“贵妇”,身份低微的乡下人被阻挡在外,上层阶级通过空间差异将自己与其他等级的人区分开。即使爱玛有幸受邀参加舞会,她仍旧体会到这种隔离感——身份相当的人聚在一起聊着她未曾听闻的地方,却没有人邀请她加入讨论。离开舞会后,她构想出这样一幅社会图景:“一种是外交家的社会,他们在四面全是镜子的客厅里……其次是公爵夫人的社会……夏天到巴登避暑……最后是餐厅的包间:一群文人和女演员……”[3]48自此,爱玛对乡镇生活空间的不满也转向对自己身份的不满,她强烈地意识到要摆脱平庸的乡镇环境就必须摆脱村妇的身份,于是她不再热心操持家务,故意表示见解特别,“别人称道的,她偏指摘……丈夫听了吃惊得睁大一双眼睛”[3]54。尤其是在庄主父亲结束拜访时,爱玛“把门一关,觉得松快”[3]54,她也在以空间区分的方式将原生的庸俗村妇身份排斥在外。至此,上层阶级确立的社会空间秩序在爱玛心中进一步内化并规训她日后的行为。侯爵府代表的上流社会异托邦是反观鄙陋现实的镜子,它激起了爱玛对贵族身份的向往。
(二)巴黎异托邦的幻象诱使追求贵族身份
异托邦具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4],这与乌托邦的作用相似,即人们可以在远方构建一个展现自己文化价值观的理想空间,为不完美的现实空间提供补偿。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多次描写巴黎,但从未让主人公走进巴黎。因此,巴黎实为爱玛在心中构建的一个遥远的理想空间,是一个象征权力与自由的上流社会异托邦。爱玛在幻象中逃避现实,体会贵族身份的优越。据《巴黎城市史》记载,19世纪30年代,随着老城改造工程的推进,市中心成为有钱人的生活区域,贫民被迫迁至城市边缘,巴黎不断提升作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展现出大都市的面貌[5]5。故而小说中爱玛猜想侯爵府的舞会结束后,子爵等人返回了巴黎,这个真实存在但远高于自己现实生活的上流社会空间。正如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指出,“上层身份能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时间,并且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一种受人关注、富有价值的感觉”[5]5。在爱玛的认知中,巴黎的贵妇拥有更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与选择权,她们可以乘坐马车游览一条条林荫大道,随心购置时装,甚至去近郊的森林举行聚会。而且贵妇的一切都受人瞩目,她们在舞厅和歌剧院是年轻绅士关注的焦点,她们的服装搭配与举止行为也被杂志报刊竞相报道。相比之下,乡镇里的女性只能整日待在屋子里操持家务,没有经济自主权,发展停滞的乡镇环境限制着她们的生活水平。巴黎意味着“更大的权力”“自由”以及“被关注与认可”,这都深深吸引着爱玛,使她愈发渴求贵族身份。无法去到巴黎的她通过阅读巴黎地图、沙龙杂志与流行小说汲取素材,在心中构建以巴黎为核心的上流社会异托邦,在投射理想中获得宽慰。爱玛在想象的空间里模拟贵妇身份的特权——乘坐敞篷车去时装店、剧院和赛马场,巴黎在她心中“比海洋还大”[3]48,象征着无限的可能。
然而,诱使爱玛在现实中坚信自己本该是一名贵妇,最终导致她的身份认知错位的原因极大程度上是消费社会营造由消费景观构成的上流社会异托邦,鼓吹个体追求奢侈消费以“实现”阶级跨越。爱玛幻想中的巴黎异托邦并非真实的巴黎,她了解到的有关巴黎的资讯是“七月王朝政府连同出版商和企业家共同参与的城市营销”[6]45。《Scenes Of Parisian Modernity: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谈道,早在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爱玛生活的年代,报刊杂志就开始着力宣传巴黎的“时装店”和“商业街”等景观,将此类消费场所同上流社会的品味相联系,将时尚视作度量阶级的重要标准,引导女性追逐时尚并消费[6]18。这种作法掩盖了阶级之间的真正差别,诱使人们相信消费是实现阶级跨越的快捷途径。爱玛在潜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异托邦即时尚之都巴黎的鼓吹与支持下,不断购买昂贵时髦的商品以向贵族身份靠齐,商人勒乐的恭维也一次次抬高了她对自己的定位,最终使她误以为自己与那些贵妇并无二致。小说多次提到爱玛感觉自己具有公爵夫人的身份:在永镇边的树林骑马散心,如同贵妇人去郊外森林散步的风尚;在按照巴黎建筑师图样建造的镇公所里与罗道耳弗眉目传情,仿佛回到了侯爵府的舞会上;在鲁昂的剧场包厢里欣赏前厅美少年,和贵妇在剧院与爱慕者对视的行为相似;不在乎银钱布置偷情的场所,与赖昂的关系更像是有钱贵妇与情人的关系。这些有意无意的拙劣模仿都是福楼拜对爱玛不自知的暗讽。但空间与权力和财富的联结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实现阶级跨越的过程充满了陷阱与限制,爱玛最终只是消费景观幻象下的牺牲品。
二、边界模糊的家宅与爱玛的身份僭越
福楼拜在对乡镇生活空间的描绘中详细介绍了爱玛婚后家宅的地理位置、房间布局与家居陈设,可见其有意突出婚后家宅对爱玛的重要影响,即婚后家宅规定了她的身份。在广阔奢华的异托邦的对比下,爱玛愈发厌恶平庸的婚后家宅及其指向的庸医妻子身份,向往家宅之外的世界。但家宅与外界的边界模糊,使爱玛很容易被闯入家宅的他者诱惑。走出家宅的空间越界行为表征着爱玛对妻子身份的僭越。
(一)他者闯入家宅诱使僭越身份
在广阔奢华与讲究时尚品味的上流社会异托邦的对照下,爱玛的现有生活环境显得更加鄙陋粗俗,她认为婚后家宅是其追寻贵族身份的最大束缚。家宅是表征身份与地位的空间,是存续家庭与婚姻关系的空间,也是男性圈限女性活动范围并彰显其对女性的控制与占有的空间。19世纪的法国,女性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实现空间的迁移与身份的改变——从父亲的家宅迁至丈夫的家宅,并冠以夫姓。侯爵府的舞会让爱玛意识到嫁给乡村医生使她丧失了前往大城市的可能,并止于庸医妻子的身份,这使她将对这段婚姻的无奈与厌恶都投射在对家宅的感受中——这个空间让她感到潮湿冰冷,难以忍受。爱玛常常望向窗外或走到后院及镇边树林散步,尽可能摆脱家宅的束缚,她也渴望出现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子带她逃离此地。家宅之外的世界对爱玛充满吸引力。因此,当家宅与外界边界出现模糊时,她很容易被闯入家宅的他者诱惑。
受到伦理道德的规约和现实的制约,爱玛并没有勇气和能力独自出离,闯入家宅诱惑爱玛的外界男性才是她僭越身份的直接推手。与外界边界模糊的家宅也为这些心存不轨的闯入者提供了机会与借口。造成爱玛婚后家宅边界模糊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乡镇邻里联系密切,串门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事。“就设计而言,没有哪种类型的建筑比19世纪的郊区房屋限制更少。”[7]乡镇的住宅规划有别于城市,沿街而建的城镇以及带有前院的低层联排式房屋为邻里间的来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且不同于进入贵族的住宅时需要层层审核,他人未经准许也能走进爱玛家中:勒乐擅自走进厅房推销商品,郝麦不顾女佣的阻拦在包法利夫妇上床后仍闯进他们的卧房。与贵族的住宅相比,爱玛的私人空间遭到更多的侵犯,她的处境也更为被动。第二,丈夫将开放的工作场所设在家中。在道特,诊所的隔壁就是厨房,“看病时候,隔墙透过来牛油融化的味道;人在厨房,同样听见病人在诊室咳嗽”[3]25;在永镇,进门的门厅就可充当急诊的场所,边上的厅房就是爱玛冬天的临时卧室。这样的空间布局使家中常有各种人员出现,使爱玛被迫受到更多人的注意,甚至成为他人的猎物。正是在厅房,陪同病人就诊的乡绅罗道尔弗发现貌美的爱玛并设计诱惑了她。穿着讲究且见多识广的罗道尔弗三番五次走进爱玛家中,无异于将异托邦的形象直接带到她的面前,爱玛不由自主地将他与自己的丈夫作比,就愈发想摆脱平庸医生妻子的身份,跟随他走出家宅。此外,罗道尔弗的关注与赞美于爱玛而言是身份更高者的追求与肯定,也进一步证明她值得拥有更好的归宿。“包法利太太!……哎!人人这样称呼您!……其实,这不是您的姓;这是别人的姓!”[3]132罗道尔弗的言语诱导让爱玛以为背叛丈夫就能获得更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从“妻子”到“情妇”身份的转换使她不过成了另一位男性的附庸。
(二)爱玛走出家宅表征僭越身份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成员相互的隐匿监视让人时刻处在规训的束缚中。爱玛注意到靠街道一侧常有“监视”目光——行人能透过窗户看见内部的活动。久而久之,社会对贤妻的规范也内化在爱玛心中,当外人走进家宅时,她总是表现出贤惠守德的一面:罗道尔弗看见爱玛能干地担任丈夫的临时助手,和丈夫一起救助患者;赖昂看见爱玛轻吻丈夫的额头,“十分端庄,亲近不得”[3]89。而转向家宅的后方,在较私密的后院她得以流露自己的欲望。小说中爱玛告别赖昂的一幕就突出地展现了这种区别:临街的窗户对赖昂紧闭,她偷偷打开面向花园的窗户望向赖昂出行的目的地。福楼拜有意通过空间的布局暗示爱玛的欲求:情人罗道尔弗的家位于爱玛家宅的后方,后方的草原和河流代表着不受社会规约的自然,源源不断的水流应和着她内心的情欲。
后院虽与后方的草原只有一墙之隔,但仍隶属家宅的领域,选择在这个家宅与外界空间的交界处与赖昂私会,表明爱玛对僭越妻子身份存在犹豫。受制于世俗的道德规训,当时的她还没有勇气背叛丈夫走出家宅,她只能在这个十分隐秘且看似合理的交往场所内进行身份的逾矩。但在成为罗道尔弗的情妇后,爱玛将偷情的地点定在家中,甚至故意在丈夫的诊室中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这都彰显出她对丈夫在工作与家庭领域权威的双重挑衅。对男性而言,私人领域同尊严及权力相关联,他者的闯入会损害他们的权威。“罗道尔弗坐在这里,如同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书架、书桌,总而言之,整个房间,在他看来,好笑异常,不由自己,就大开查理的玩笑。”[3]146爱玛擅自闯入丈夫的工作空间,让情人取代丈夫的位置,以占领这一空间——她甚至怂恿情人在丈夫进来时一枪击毙他。这样猖狂的空间越界表明爱玛在心中完成了对妻子身份的僭越,她借助另一个男性的权势体验征服丈夫的快感。而当爱玛心中的道德歉疚越来越少时,她直接当着丈夫的面生气地甩门离开,走出家宅。之后,她甚至和罗道尔弗在自家房间里偷情,“活像一个妓女等候一位大贵人”[3]160。从室内走到室外是爱玛对妻子身份的出逃,从室外回到室内则表明爱玛完全无视与丈夫的婚姻关系。
三、爱玛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追寻
异托邦空间与家宅空间隐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影响着爱玛,促使她通过改造、逃离以及构建空间的一系列实践来追寻理想身份。但在男权社会影响下,身份追寻的思想局限与空间实践的行动限制使她无法在家宅空间之外的地方构建自己的身份,这也是19世纪法国女性难以逃脱的身份藩篱。
(一)爱玛对空间实践的失败
空间与人相互作用且互为表征,这表现为爱玛受异托邦吸引向往贵族身份,却被家宅圈限在庸医妻子的身份中。她努力通过改造、逃离以及构建空间的一系列实践来追寻想要的身份,但均以失败告终,这3次失败印证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现实。首先,她轻信商人勒乐的言语,购置巴黎新出的饰物与家具,企图将自己的家宅改造成上流社会空间。其次,她渴望情夫罗道尔弗带她出逃到异国,去那些她在舞会上听到的贵族度假地点。最后,她和从巴黎归来的赖昂把鲁昂的旅馆房间称作“我们的房间”,不惜变卖嫁妆补足开销,坚持讲究幽会的排场,使赖昂成了她这位“贵妇”的“情夫”。但最终,罗道尔弗丢下爱玛,导致她走进异托邦的计划破灭;在高利贷的骗局下,法院要出卖爱玛家中的所有动产,没有了昂贵家具的家宅对追寻贵族身份的她而言是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地方;而赖昂的逃避也标志着热情衰退下勉强维系的“我们的房间”的幻灭。小说的结尾,爱玛为了借钱出入一个个富丽堂皇的男性住所——公证人家、税务员家和罗道尔弗家,却又失望离去。实际上,这些男性住所都是“无动于衷的庄园”[3]271,因为里面居住的都是对爱玛命运无动于衷的男性。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威胁与警示——外面的世界是男性的空间,充满着危险和陷阱,女性作出违背性别规约的空间实践只会遭到伤害。而女性之所以缺乏应对外界世界的能力,又是源于家宅空间的长期圈限,在这样的循环模式下,爱玛永无逃离家宅与走出乡镇的可能。最终,无处可去且不知所措的爱玛只好用自杀来逃避问题,她不知空间实践失败的原因,更未曾发觉自己孜孜追求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不自由的。
(二)爱玛对身份追寻的局限
爱玛的深层悲剧在于她追寻的理想身份仍是男权规训的结果,是一个他者的角色。这种规训体现在无论上流社会异托邦还是她所处的乡镇生活空间,都传达着女性是男性附庸的思想。爱玛从未质疑此点,她渴望的自由不过是自主选择伴侣并向心仪男性展现女性魅力的自由。19世纪的法国社会决定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身份认可只能在家宅空间中实现。因此,在福楼拜的笔下,爱玛不过是在一个个家宅空间中流转:从拜尔托田庄的女儿房间到道特和永镇的婚后家宅。即使与赖昂在鲁昂偷情,她也还是要按时回到家里。事实上,爱玛厌恶的不过是表征自己庸医妻子身份的家宅,因而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她所建构的并认为能满足自己意愿的“我们的房间”仍是一个新的家宅空间。直至1944年才被基本废止的《拿破仑法典》将妇女认定为终生的未成年者与无能力者,许可离婚的条件也十分苛刻。“法国婚姻制度如此贬低已婚女子的做法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罕见的。”[8]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框定已根深蒂固,限制着爱玛对身份的追寻,她只能是女儿、妻子、母亲或是永远无法私奔的婚外情人,难以脱离男性的掌控构建自己的身份。小说最后,吞食砒霜的爱玛又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躺在卧室的床上。奄奄一息时她摸摸丈夫的头,并想抱一抱女儿,临死时的这番举动隐射出她终究承认了自己的妻子与母亲身份。爱玛最终死在她无数次想逃离的卧室里,她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却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爱玛代表了19世纪法国所有受男权空间规训的女性,她们实践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始终无法走出家宅。
综上所述,《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书写可发现福楼拜较早地意识到空间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及空间与人的相互表征关系,这对重新理解这一经典文本的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细致书写以侯爵府和巴黎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异托邦和以婚后家宅为代表的的乡镇生活空间,真实还原了上层阶级确立的社会空间秩序与男权话语对一个19世纪法国女性的影响过程。这样的理解视角有助于对人物作出更客观的评判:爱玛出轨的背后是女性对权力与自由的向往,她意识到空间实践是改变身份和命运的重要方式,并积极行动。而在当下,女性想要建构独立的身份依旧离不开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或许是福楼拜在19世纪中叶破除道德伦理的规约,大胆写出女性不满现状、尝试追求更高等级的身份及进行空间实践的思想旨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