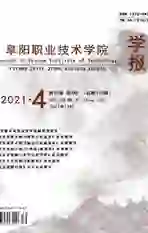两起“触摸”事件的不同结局
2021-01-11鲁学冬
鲁学冬
摘 要作為严歌苓又一部“文革”题材的力作,《芳华》虽然延续着“穗子”系列小说的叙事基调,但其怀旧感伤的情感更加浓郁,小说中的萧穗子已人到中年,经历过了青春成长的阵痛。严歌苓以自身生命体验为叙事基础,通过回忆、插叙、倒叙等多种叙述方式,着重讲述了刘峰的两起“触摸”事件所导致的不同结局(“触摸”林丁丁被集体背叛与抛弃;“触摸”何小曼唤起了他人对生活的希望),其试图超越原有对人性的认知,把对人性的思考引向更深邃的领域。
关键词严歌苓;《芳华》;人性书写;“文革”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1)04-0067-05
作为严歌苓“穗子”系列小说的延续,《芳华》一经发表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严歌苓曾称“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是其对少年时期文工团生活的追忆与想象。而《芳华》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穗子系列小说“文革”时空的界限,小说所讲述的时间,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主人公刘峰去世,40多年的历史跨度,那个曾经“少年的萧穗子”早已年近花甲。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一改之前“穗子”系列小说的叙事风格,展现出《芳华》独特的叙事特征。
《芳华》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重点围绕学习雷锋标兵刘峰因一次“触摸事件”而被文工团上下所“背叛”的故事,着重讲述了缺失亲情关爱的何小曼艰难的成长历程,书写了革命浪潮下的复杂人性。虽然“严歌苓通过这个形象(刘峰)谱写了一曲人性之歌”,以“误读的叙事形式来表现这个形象隐含的人性高贵内核。”但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的地方,比如小说内容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人物的年龄前后矛盾、有些故事情节难以自圆其说等。有人提出,“《芳华》在叙事方面的逻辑混乱,也显示出严歌苓驾驭故事能力的退化。”这主要是“严歌苓个人的‘讲述’欲望,要远远大于其讲‘故事’的欲望,因此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并不是她所关注的重心,让‘故事’无条件地去迎合她的‘讲述’欲望,才是构成小说《芳华》的意义所在。”
那么,是什么激起了严歌苓“讲述”的欲望,而把故事情节的合理性置之度外?在小说《芳华》中,严歌苓将“讲述”的欲望聚焦于小说人物的人性问题,淡化以往强调小说的叙事结构,思考两位主人公如何忍受着来自集体与时代的外界压力。按严歌苓自己的话来说,“我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其实我就想找到人性当中的迫害性。”[4]87
一
作为一名经历过“文革”的华人作家,严歌苓要比一般的作家对人性问题更加“痴迷”,“‘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在文学创作生涯中,严歌苓始终保持着对复杂人性问题探寻的趣味与热情。
小说《扶桑》中,在遭受众人残暴蹂躏时,扶桑却保持着出奇的冷静与淡定。她这种笃定的行为与躁动的暴徒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东方母性强大的隐忍与宽容力。
在《第九个寡妇》中,当众人都在参与社会革命运动时,主人公王葡萄试图坚持社会运动之前的生活方式。在政治思想学习会上,她依旧“纳着鞋底”;在全国上下大炼钢铁中,她依旧精心地照看她喂的猪。王葡萄对政治宣传毫无兴趣,与外界的社会运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王葡萄坚守着社会革命时期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基本人性准则,以至于不会在时代的漩涡中迷失自我。
反观小说里那位怀孕的女知青,当社会革命运动结束时,“她和所有知青一样,觉着让谁骗了,让谁占了便宜,让谁误了大好时光,让谁剥夺了他们命里该有的东西——上学、逛公园、夹个饭盒上工、骑个自行车下班、早上排队买油条、周末睡懒觉、晚上进电影院……他们原来本该有着那样的命,可被谁篡改了,剥夺了。”在大梦初醒中,人们回望自己在革命年代所做出的有违正常人性的行为,明白了无私地投身社会革命后,却是人与人之间隔膜所导致自我人性的虚妄。
这种对人性异化的书写,在严歌苓“穗子”系列的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灰舞鞋》中,一直被看似天正无邪的小穗子,早已情窦初开。“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正站在黑暗里想着‘爱’、‘私奔’之类的念头。我们对她的理解是一片空白,她在这片空白里忙着她的秘密感情生活,欲死欲生。”当小穗子与邵冬骏的“地下”恋爱被发现时,她一下子发现自己被战友孤立了,成为了异类,被集体所排斥。在特殊年代下,小穗子不仅要背负违规谈恋爱的罪名,还要受到来自战友的集体无意识的冷落。
在这一点上,《灰舞鞋》中的小穗子、《芳华》中的刘峰以及《爱犬颗韧》中的小周,他们都曾尝试着去触碰那个“浑身满心乱窜”的“爱”,但结果往往却遭受战友们的孤立与抛弃。当小周与赵蓓为爱而偷食禁果时,“我们都清楚他俩正做的事,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而不敢做的。只有让他俩把事做到这一步,我们才会像一群观看杀鸡的猴子,被吓破胆,从此安生。我们需要找出一对同伴来做刀下的鸡。我们需要被好好吓一吓,让青春在萌芽时死去。”在“穗子”系列小说中,我们会看到“‘群体’身份给个人带来的某种困境,抑或某种戕害的反思。”
通过对文工团中的青春爱情悲剧故事进行反复书写,严歌苓表现出对特殊年代的人性问题独到的见解。因为她“没有走描写人物命运多舛的‘伤痕’之路,也没有在历史废墟上作文化政治的反思,而是以自身的体验去关注‘文革’悖谬语境中人的表现与人性的变异。”
从《扶桑》到《芳华》,小说中无处不在展现人性的多个侧面,其中《芳华》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篇小说的历史跨度大,从“文革”中后期一直到21世纪,是严歌苓作品中鲜有的。在4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小说主要人物在性格、价值观等方面前后产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把对特殊年代的人性问题引向更深广的领域。
二
在《芳华》中,透过萧穗子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具有高尚美德的学习雷锋标兵刘峰,结识了被文工团和家庭所抛弃的何小曼,见识了特殊年代集体无意识对个体的迫害。在个体与集体间的相互反抗与妥协的交织中,小说折射出不同人性丰富的内蕴。
小说中,刘峰是一名学习雷锋的标兵,以非功利、无条件为做事原则,把人性中的“好”推向了极致。“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触摸事件”发生前,文工团里的其他人对刘峰这种非功利的助人行为产生怀疑,“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得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在那个全员学习雷锋的年代,人们熟练地掌握着表演学习雷锋的技巧,深刻地理解革命话语中所蕴含的缝隙。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一方面人们试图以实际行动来靠近学习雷锋标兵的标准,另一方面,人们对这套话语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一个人的革命思想无论有多么进步,也达不到圣人的地步。
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 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随后每年的3月5日,被确定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雷锋被视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标志。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原来鲜活的雷锋形象逐渐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这造成了文工团人对刘峰学习雷锋极致化的革命行为规范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被刘峰获得全军学习雷锋标兵的称号而打破。当刘峰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归来时,文工团上下鼓掌欢迎,依次走向刘峰与他握手,把刘峰由原来向雷锋的学习者,当成了文工团里的“活雷锋”。我们看到刘峰自身的认识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他逐渐相信自己的思想境界、人格魅力要比以往高于常人,并化身为一位具有极高道德情操的圣人来感化众人。如他向身负男女问题的萧穗子送去关爱和同情;帮助自己深爱着的林丁丁入党,鼓励她在思想和事业上取得进步;化解被集体和家庭所孤立的何小曼没有男舞伴的窘境……一系列的好人好事,让文工团所有人对刘峰的思想境界刮目相看,“一个其貌不扬的身躯里怎么容纳得了这么多的好?我们这个世界上,也许真有过一个叫雷锋的人,充满圣贤的好意和美德。”
“触摸事件”发生后,包括刘峰自己在内的文工团人,都对人性极致的好这套标准再度产生怀疑,也意味着由学习雷锋所构建起的“文革”美德标准体系彻底崩塌。在遭受文工团人无情的批判后,刘峰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性的伪善,认识到了学雷锋标兵惨痛的结果。“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的污染。”
有人提出,刘峰“触碰林丁丁源于他身体的欲望,触碰何小曼则是他人性中向善力的驱使。与之对应,两次触碰有着完全相反的效果:一次宣告了自己的毁灭,另一次却救赎了他人。”其实,触摸事件只是导致刘峰被下放连队的导火索,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刘峰从一开始无条件地接受与相信特殊年代的价值準则,并把这套行为准则作为自己人生追求和精神信仰,为之而虔诚的努力。而他殊不知自己逐渐被这套行为准则所异化,已成为集体眼中的异类,触摸事件中林丁丁那声大叫“救命”,就是最有力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触摸事件让刘峰顿然醒悟见识到了人性的卑劣,但他身上却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烙印,使其不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新时期市场化经济浪潮中,依然展现出被“文革”规训的优秀的道德品质。
在严歌苓看来,“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
如果说刘峰是文工团中的活雷锋,享受着来自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认可,那么何小曼却是一位处于民间与官方视野之外的边缘人。何小曼是文工团中的另一个极端,她是“人群里经受了屈辱,经受了各种各样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自身也是因为她的成长过程而成为这样一种‘小耗子’性格的一个人。”
在未取得“英雄”称号前,何小曼始终被家庭和文工团所忽视与冷落。在家庭里,何小曼是以“拖油瓶”的身份生活在继父的家庭中,基本上没什么地位可言,更极少会得到母亲的关爱。这种寄人篱下的境遇,让她养成像老鼠一样的吃东西和观察外界的习惯。“有时母亲给她夹一块红烧肉,她马上会将它杵到碗底,用米饭盖住,等大家吃完离开,她再把肉挖出来一点点地啃。”
初到文工团时,何小曼期盼着自己缺失的亲情会在集体生活中得到弥补,可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入伍刚开始,她就因为自己的头发比一般人要浓密粗壮得多,而被以异类来看待。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又因像老鼠吃饭的习惯和乳罩风波而受到众人的鄙视,再次回到边缘的位置。在一次排练中,何小曼陷入到了无人托举的窘境,其最终被刘峰所解决。这次“触摸”让何小曼感受到了人间的爱,唤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正是长期忍受着集体的冷漠,何小曼才会看不惯文工团上下随时怀疑刘峰非功利的做事行为。因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换句话说,一个常常处于边缘位置的人,要比群体能更加理性与客观鉴别人性的好与恶,也更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关爱。
在看穿了群体展现出多变的人性面目后,刘峰和何小曼这两个原本处于集体两极的人最终交织在了一起,他们彼此相互支撑先后忍受着来自革命时代的群体性压迫和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社会巨变。在一定程度上,从生存境遇来看,刘峰与何小曼要比文工团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其被两个时代所抛弃,成了时代浪潮中两枚弃子。虽然这里有主观和客观上的因素,但暴露了集体对个体戕害所产生的持久性。就如严歌苓所言,“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也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集体会发现一个另类,一个可以承受集体的各种各样负面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他们会把身心当中所有负面的东西发泄在他身上,把这个人变成这个集体的一个对立面和牺牲品。”
与刘峰和何小曼两个极端的个体相对立的“我们”,是小说中重要的一类群体,展现着人性的复杂与多变。这类人是没有具体的指向性的,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故事发展的进程与思想内核。因为“通过刘峰的‘触摸’事件而最终深刻地挖掘出包括叙述者萧穗子在内的我们整个民族某种难以见人的集体无意识来,正可以被看作是严歌苓《芳华》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之一。”
这种集体无意识给个体带来两个结果,要么归顺于集体,要么被集体抛弃。就如鲁迅笔下的看客,始终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找寻个体的弱点,满足自身的欢欣。小说中,以“我们”为代表的集体始终掌控着话语的主动权,也占据着社会的有利资源。在特殊时代,“我们”对参与社会阶级斗争活动驾轻就熟;在新时期,“我们”享受着市场经济所带来丰厚的物质基础。
可见,“我们”对不同时代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也表现出了人性的伪变。如林丁丁在“文革”时,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天真无邪、孩子气十足的独唱演员。新时期以后,曾经柔柔弱弱的林丁丁变得泼辣起来,将原有的天性展露出来,“放下了做首长儿媳妇的包袱,也破碎了做歌唱家的梦。”在社会市场化浪潮中,不只是林丁丁,像郝淑雯、萧穗子等人的性格和价值观也发生变化了,就如萧穗子所言,“这年头说谁好人,跟骂人一样。”这种“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人已经不再是知识的主体和对象,信息的生产、储存和控制决定了知识的内容和社会发展方向。”
作为“文革”遗产下的后现代人,刘峰与何小曼面对物欲化的社会浪潮要笃定得多。一方面刘峰与何小曼本身保持着极高的道德品质,如刘峰的逼娼为良。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他们难以像郝淑雯、林丁丁等人那样快速融入市场化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刘峰与何小平再一次沦为社会和集体的弃子,但彼此要淡然得多,或许经历过从被集体推崇到摒弃,再到见识过死亡的威胁的人更能感悟到人性的真谛。就如鲁迅所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三
一段时间以来,严歌苓对《芳华》这类题材的反复书写,表现出其对特定历史、特定群体有着深厚的审美趣味,也构筑一条别样的探寻人性的创作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芳华》的叙事方式上,严歌苓突破了以往类似题材小说的叙事框架,试图建构起独具个性化的叙事模式,为其思考人性的命题而服务。
首先,《芳华》是以第一人称“我”(萧穗子)作为叙述者,并穿插着集体化的“我们”、作者两个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这使得整部小说在叙事上更为多样,也展现出严歌苓叙事上的大胆尝试。正如她所言,“好像看起来是非常任性的一种写法,其实是结合了布莱希特的‘离间式’的,不断让读者看到严歌苓在说话,严歌苓在讲往事,实际上是一种离间的办法,但很快又让读者感受到这是‘萧穗子’在讲故事,是劇中人在叙述故事,所以我这次就把老师教的这些扔掉,来一次非常任性的、自我的,既主观又客观的写法。”
这种掺杂着主观与客观的“离间式”叙述方法,一方面改变了“萧穗子”全能型的上帝叙事视角,让其视野范围具有限度,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这种限制性叙事的态度,最容易凸显现场感、艺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拉开了集体性的“我们”与个体性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认知距离,让集体与个体产生人性间的隔膜。作为小说中叙述者,“我”(萧穗子)更多时候是为集体发声,其是以集体性视角来表述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的。
小说中,“我”获取刘峰和何小曼的主要信息渠道:一是亲身的历史经验与观察,二是与有关事件的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在现有故事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想象。可见,“我”对于刘峰与何小曼的认知是有限度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叙述方式会让刘峰与何小曼故事衍生出另一个版本,突出个体生命的张力。在小说的后半段,“触摸事件”的当事人刘峰几乎处于缺席的状态,萧穗子主要借助郝淑雯、何小曼等人的转述,来拼凑出刘峰后半生的生存状态,这让“我们”无法窥探到刘峰内心深处的真实世界。
其次,小说通过复调式叙述结构,展现出主人公看穿人性的精神顿悟。在叙述者、当事人、作者三个的叙述声中,“触摸事件”的前因后果逐步清晰,让刘峰与何小曼这两位主人公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刻的顿悟。如刘峰“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他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从那时候,他就看破了。还可能更早一点,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时候。”而何小曼是在刘峰,因为“触摸事件”被集体无情的抛弃而看透了,“我们”那个没有丝毫人情的群体。抑或是在,她因为一次帮扶受伤的战友而被官方话语大肆宣传下发疯之后,看透了所谓的“英雄”称号是如此缺乏真实性。因此,当市场经济浪潮助推着社会再度躁动时,刘峰和何小曼自觉地选择处于社会边缘的位置。
就如严歌苓所言,“前线的经历使我之前的英雄主义观念发生了颠覆,我发现,一个人的生命、青春可以在一刹那间全改变、甚至毁灭,一个健全的身体在一刹那间变成了残废。”正是对英雄主义产生怀疑,才促使其在小说的后半段对于刘峰因为“触摸事件”而导致一系列悲惨命运的反思。甚至将这种反思转化成为一种推力:试图冲破革命年代下对自由人性的束缚。
其三,小说以“文革”为基本叙事载体,形成今夕的时空叙事结构。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小说展现出人性的虚伪,人们戴着虚假的面具进行表演。就如小说中的“我”,“那时的我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也不难受。”人们带有功利化的表演方式向组织靠拢,“扫院子喂猪冲厕所,或者‘偷偷’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偷偷’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做足本分之外的事,你就别担心了,你会出现在组织的视野里。”
到了新时期,集体的“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为了追逐经济利益的弄潮儿,抛弃了革命的理想贪婪地吸取物质财富。可在角色的转化中,“我们”失去了青春芳华,成为了一个个感伤与怀旧的生命体,为自己年少时伤害过的人与事而叹息。
因为“人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会越来越诚实,对自己的反省和悔罪,都不怕了。”在对《芳华》这类题材的反复书写中,严歌苓试图超越原有的认知领域,让文工团的“我们”经历着成长的阵痛,把对人性缺点的思考引向更深邃的地方。
四
就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毕飞宇眼中的苏北平原一样,严歌苓也在构筑自己的文学版图:“文革”中的“我们文工团”,其《穗子物语》中的萧穗子几乎贯穿这一系列小说的始终。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严歌苓试图对原有的故事框架进行再突破、再想象,以窥探出特殊年代下人的多重维度的人性,这是当代文学少有的现象。
作为严歌苓时隔多年的又一部“文革”题材的力作,《芳华》虽然延续着“穗子”系列小说的故事基调,但其怀旧的成分更加浓郁。小说中的萧穗子已人到中年,经历过了青春成长的阵痛。严歌苓以自身生命体验为叙事基础,通过回忆、插叙、倒叙等多种叙述方式,重点讲述了刘峰的两起“触摸”事件所导致的不同结局(“触摸”林丁丁被集体背叛与抛弃;“触摸”何小曼唤起了他人对生活的希望),展现其对于人性深度的思考力。正如她所言,“对‘文革’,《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可在一定程度上,从《芳华》开始,那种“嘻嘻哈哈讲的”的青春书写基调消失了,对岁月的感伤情怀、人性思考、时代变革等方面的关注与反思增强了,这种反省力度超过了前期的“穗子”系列小说。
如果说《芳华》对人性的书写给当代文坛乃至文学史带来了什么,我们会在其文本中探寻到以往“文革”书写所触及不到的人与事,如极致的人性、身体的欲望等。当躁动的历史大幕落下,文工团的“我们”除了追忆青春往事,感伤年华已逝之外,还得虔诚的忏悔被集体所伤害过的个体生命:像刘峰和何小曼这样的人,在躁动的社会中选择笃定的生活,选择试图告别“文革”话语中的“英雄”神话。
————————
参考文献:
[1]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1.
[2]陈思和.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J].当代作家评论,2017(05):58.
[3]宋建华.青春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冲突:关于《芳华》[J].扬子江评论,2018(6).
[4]刘艳,严歌苓.多重况味的青春记忆:访谈录[J].小说评论,2020(04).
[5]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60-261.
[6]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10.
[7]严歌苓.穗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89.
[8]严歌苓.白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37.
[9]王小平.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论严歌苓的“穗子”书写[J].华文文学,2006(2):51.
[10]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90.
[11]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2]杨超高.论严歌苓《芳华》的身体书写[J].华文文学,2019(3):95.
[13]舒欣.嚴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14]王春林.个体经验与精神分析学深度:关于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J].扬子江评论,2018(1):72.
[15]赵敦华.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20.
[1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17]刘艳.军旅“芳华”的同题异构:严歌苓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与近作《芳华》比较研究[J].小说评论,2018(02):184.
[18]严歌苓,果尔.从故事、小说到电影:严歌苓访谈[J].电影艺术,2014(04):52.
[19]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J].华文文学,2005(0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