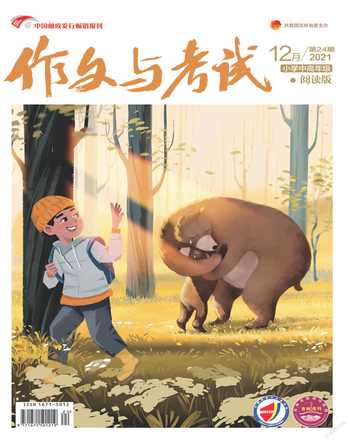“灯塔级”人物点亮了情节(续三)
2021-01-10三水
三水
给孩子们带来思想的影响,只是 “妈妈”这个“灯塔级”人物的一种表现。在《铁路边的孩子们》的有关情节之中,“妈妈”还把“言传”和“身教”结合起来,见缝插针地给予孩子更多点拨、教导、忠告。而这样的“逆耳忠言”,在孩子们成长的路上,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此形成的因果关系,因为有源头的“点染”,让孩子们的性格塑造更有说服力。
上文说过,孩子们离开伦敦的那一年,郊外的六月异常寒冷,雨水如矛,冻人彻骨。孩子们不能去上学,待在屋子里很冷,在户外游玩也好不到哪里,只好请“妈妈”同意,烧煤取暖,驱赶寒气。面对孩子们可怜的请求,“妈妈”是如何答复的呢?
其实,对于生活的急剧变化,“妈妈”早就“打了预防针”:“妈妈不止一次告诉他们,他们‘如今很穷了’,但这只像是说说罢了。大人,包括妈妈在内,常常说出一些似乎没有意思的话,不过就是随便说说。他们还是吃得饱饱的,还是穿原来那些好衣服”。在富足而优越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对于“穷”以及由“穷”带来的冻馁之忧,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在我国古代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了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能挖草根,甚至吃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报来,晋惠帝大为不解,居然询问群臣:“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没米饭充饥,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生活在富足里的人,是难懂穷困的难堪的。“妈妈”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在面对孩子们的生火请求时毫不回避:“不行,我的小宝贝。都六月了,我们不能再生火——煤太贵了。你们觉得冷,就到顶楼上去玩吧,玩玩会暖和起来的。”虽然孩子强调“生火只要一点儿煤”,可是妈妈毫不退缩,“那点钱我们也花不起,小宝贝” ,“妈妈”快活地说……对于家中真实的生存情况,“妈妈”不隐瞒,公布真实信息;时常挂在口边,给孩子的接受“预热”;在孩子受冻与请求取暖的时候,她权衡利弊,温柔制止。这样的处理,表面上看,似乎是在用苦难“打击”孩子,但其中却体现出了“妈妈”面对窘境的真诚,对孩子的尊重与信任,并借此最终凝聚起全家共渡难关的信心。“妈妈”对穷困生活有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打算,如此,对孩子的自立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孩子们的性格形成添加了底色。
所谓穷困的生活,就是自顾不暇,不断要忍受冻馁之苦。这个时候,如果家里再添一口人,增加一个人吃饭,岂不雪上加霜,更加窘迫?还是拒绝这样的人吧——但是,“妈妈”却有自己的做法。那一天,孩子们在车站“偶遇”“犯人”——一个来自俄国的作家。当他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钱包和车票都丢失了,身体虚弱,语言又不通,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幸好“妈妈”来了,用法语与“犯人”交谈,并认定他是俄国的一个著名作家,“妈妈”甚至还读过他的书。经过这一番了解,“妈妈”扶着他回家,并嘱咐孩子们马上生起火来,把屋子烧得暖暖的——不仅如此,自从这个俄国人来了之后,“妈妈”把爸爸的衣服找出来给他穿。平常,“妈妈”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写作,以便换取面包和小点心。可是,自从“犯人”进门,妈妈不仅要照顾他,甚至停下了写作,陪着“犯人”聊天,还自费投出大量信件,帮助这个俄国人寻找他的妻子、儿女。“妈妈”不惜自己家庭陷入窘迫,来接纳、照顾、帮助一个陌生人,这样的古道热肠,对孩子们的性格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孩子们在猎狗追兔子比赛的隧道里,救了一个腿骨折的男孩。可是男孩的家住得很远,他必须就近找一个住处。这时,伯比毫不犹豫地说:“噢,把他抬到我家吧,它就离铁路不远,我断定妈妈会说我们该这么办。”伯比之所以敢于这样答应下来,正是因为之前有“妈妈”接纳并照顾“犯人”的行为影响。如此,两个人物前后呼应,并形成情理兼具的因果关系,如此的笔法堪称点睛。
孩子们的好朋友珀克斯要过生日了,他们还听说,珀克斯都三十二岁了,还从未庆祝过自己的生日,于是,孩子们集思广益,开始筹备。他们自作主张地来到镇子里,挨家挨户询问在珀克斯过生日时,大家要有什么表示,并且代珀克斯把礼物收下,打算再转交给珀克斯。“妈妈”也为珀克斯准备了礼物,但是,“火眼金睛”的她却预感到这里有问题,提醒孩子们说:“不过要看你们怎么做。我只希望他不会生气,以为这是施舍。穷人是很有自尊心的,这点你们要知道。”可是,孩子们却以“我们爱他”为理由,并不听妈妈的忠告。尽管如此,“妈妈”却并不点破这个迷局,而任由事态继续发展。果然,珀克斯正如“妈妈”预料的那样,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大发雷霆,在孩子们的不斷解释中,才逐渐消除了火气,让关系“回暖”。这个“妈妈”充满智慧,她既有防微杜渐的提醒,又给孩子留有余地,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碰撞”,来消解相处的难题,在真实的沟通中成长。
不得不承认,“妈妈”这个形象所用的笔墨并不多,却因为每次出现,都是在孩子们遇到“难题”的关键时刻、性格发展的转折之点,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