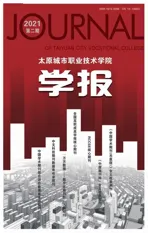《高加索灰阑记》的陌生化处理研究
2021-01-08■王斐
■王 斐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布莱希特作为20世纪伟大的戏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其最突出的成果在于通过陌生化理论而实践其叙事剧创作。身处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布莱希特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戏剧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特别是当他接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之后,更加意识到通过戏剧改革引起人们思想改变,进而达到社会改造的重要性。通过对熟悉题材的陌生化处理,让观众对想“当然”的事物获得全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解是陌生化的主要目的。因此,布莱希特选取了对于欧洲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灰阑断子”的故事来践行他的戏剧理念。
一、“灰阑断子”故事类型及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
“灰阑断子”的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国的文献中都有所记载。《旧约全书·列王记上》中记载了所罗门王采用劈开平分的方式判定孩子的归属,并最终将孩子判给了反对将孩子劈开的真正母亲的故事。通过对所罗门智慧的描绘,赞扬了耶和华的智慧和恩泽。《大正大藏经》第四卷《贤愚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也是通过生母的慈爱之心来判定孩子归属,认为“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绁挽”。中国本土也不乏类似故事,如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中丞相黄霸通过让两妇去抱孩子,并将孩子判给了不忍“急抱”的亲母。唐《意林》、唐《北堂书钞》、北宋《太平御览》、南宋《折狱龟鉴》、宋《棠阴比事》也都有类似故事[1]。
李行道的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主要写身为富翁的马均卿有妻胡氏,并娶妾海棠并生有一子。胡氏与其情夫赵令史合谋害死马均卿并诬陷给海棠。为了谋取家产,又称海棠的孩子为自己亲生。在第一次审判之中,海棠被判死罪。第二次审判由包拯主持,使用“灰阑断子”的办法判定海棠为孩子亲生母亲,并惩戒了正妻胡氏及其奸夫。
以上判案的根据都是真正的母亲在意孩子的生命安全这一人伦常情,也即亲情。其中决定亲情的根本原则便是血缘。其不同则在于《旧约全书》反映神智、神恩;《大正大藏经》反映佛智、佛恩;《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反映对清官、清明盛世的期盼[1]。而将这一故事类型进行大改造并赋予新的思想的则是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
布莱希特在关注社会活动同时也对中国戏曲艺术充满兴趣。他不仅喜爱中国文化艺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充满兴趣。他赞赏唐诗并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是描写语言明晰的高超的艺术,并且翻译了白居易、毛泽东的诗词;他研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同时,还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来分析戏剧艺术作品[2]。在戏剧创作内容方面,吸收张国宾所作元杂剧《合汗衫》中陈虎于雪中被张孝友所救,却反而夺其妻的故事框架创作了教育剧《例外与常规》;《四川好人》中的妓女沈黛则是部分借用了关汉卿《救风尘》的内容;《八路军的小米》则改编自抗日战争题材话剧《粮食》。
布莱希特从小就对《圣经》感兴趣,因此对于“灰阑断子”这一框架也十分熟悉。他一共进行过四次创作,分别是《男人就是男人》的幕间剧《小象》,创作于丹麦但未完成的《奥登西灰阑记》,创作于瑞典的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以及在美国期间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3]。
183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曾经翻译过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其情节来源的直接证据则是歌手介绍,“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当然,我们的演出在形式方面做了更动”[4]。而对于中国戏曲中,如楔子、自报家门、题目正名、演唱等的吸收则从形式上反映了布莱希特以“陌生化”,也即“间离效果”为内核的“叙事剧”。
二、陌生化的叙事剧与中国戏曲
陌生化理论源自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主要是对于形式的新鲜感受性。其代表人物施克洛夫斯基认为感受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的目的,因此需要使对象陌生。将形式变得困难就可以增加感受的难度,也就可以增加审美感受的时间,陌生的形式导致新的风格、文体和流派的产生。陌生化理论同时还强调艺术并不是对于外在世界的模仿而是指向自身,也因此展现出不同于日常的形态[5]。布莱希特在其戏剧实践中所使用的“间离效果”就是来源于陌生化理论。他的“间离效果”体现在戏剧作品的各个方面:故事结构、人物构成、台词风格、演员演技、背景技术等[6]。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悉的东西因为过于熟悉就会放弃对其理解,也就是放弃了“知其所以然”的兴趣。而陌生化效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当然”的事物打上“绝不当然”的印记,使其失去熟悉的表象而露出社会的本质。陌生化理论希望引起观众理性和冷静的思考,而不是沉醉于感情的享受中。通过对人物、时间和社会进程的观察,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并最终做出有益于社会改造的行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将作为剧本的客体和观众的接受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开,令主体意识到现实与虚构的距离,进而避免过度沉迷。这种有意扩大的距离不在于单纯的审美意图,而是与社会功能紧密相关。
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运用莫过于其叙事剧的创作。在他早期创作的《人就是人》《三角钱歌剧》等作品中就运用类似中国讲唱文学夹叙夹唱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也是对欧洲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突破。在中国讲唱文学中,叙述的部分由作为通俗阐释的“讲”来承担。而布莱希特戏剧中的“讲”则更强调叙述中鲜明的主观态度,在时刻提醒观众与艺术作品保持距离,引导观众对作品、世界、社会进行思考,进而改造社会。通过“间离法”忽视感情功名而达到理性思考的叙事剧,正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和实践的标志。
布莱希特曾于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在这之后他还写过不少关于中国戏曲的文章,如《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论中国人的传统戏剧》等。但是他不满于让观众陷入感情、丧失自我的传统戏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把握事物本质,进而达到社会的变革[7]。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思考方式是中国传统戏曲所没有的,并且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所创作的新的德国戏剧并未受到亚洲戏剧的影响。但是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中确实存在很多与中国戏剧相类似的用于表现陌生化的成分。比如“不存在的第四堵墙”,演员在表演时是“自我观察的艺术”,程式是“通过另一个人来表现一件事”,中国戏的表演可以随时“被打断”。虽然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作了新的解读,但是偏颇之处也不在少数。比如关于“自我观察”就有着欧洲表演流派中“表现派”的影子。对于习惯了“程式”的中国演员和观众,这种形式是否还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中国戏曲与其说是“被打断”,不如说是演员可以自由进出,布莱希特之所以会感觉陌生正是由于主客体对立与分析哲学的影响,对于极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欧洲戏剧而言,“物与神游”“天人合一”的中国戏曲自然感到陌生。与其说是中国戏曲影响了布莱希特,不如说布莱希特通过中国戏曲印证了自己的“叙事体戏剧”和“陌生化效果”理论,对于这种陌生化,布莱希特还是当作一种表现技巧来看待的。
三、《高加索灰阑记》形式上的陌生化
布莱希特通过叙述性的手段对《高加索灰阑记》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比如让演员担任叙述者的角色与观众直接交流,向观众讲述事情经过;歌手或者合唱队通过全知的叙述视角对情节进行评论;充分利用舞台道具和舞台设置,使场景独立并且跳跃;开场的楔子通过对剧情的预告来“间离”艺术与生活。
《高加索灰阑记》中戏剧结构的陌生化体现在其中三个独立的故事,第一个是楔子部分中两个村庄为了争夺山谷的归属权,而由楔子部分引起的戏中戏则又有两个独立的故事,一个是女仆格鲁雪保护并抚养焦尔吉总督的孩子米歇尔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因为无意中救了大公的村文书阿兹达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独特的结构,并由小剧构成完整的大剧。“戏中戏”起到了“间离”观众和艺术的作用。通过松散的、片段式的情节组合,突破了欧洲习惯的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激烈冲突的惯用模式从而形成陌生化。布莱希特通过歌手的唱词,将这些零散的片段连接在一起,这也是对于中国讲唱文学中“唱”的部分的应用。“唱”原本是让听众更好记忆的同时享受音乐美感的韵文,而布莱希特则把“唱”作为间断剧情速度、揭示人物命运的叙事手段,增加抒情性的同时冲淡了情节的冲突。《高加索灰阑记》还模仿中国戏曲中折的形式为每一场都分别设置了标题,分别为第一幕《贵子》,第二幕《逃奔北山》,第三幕《在本山中》,第四幕《法官的故事》以及第五幕《灰阑断案》。标题对剧情起到概括作用的同时减弱了故事的情节性,从而引发理性思考的愉悦。在叙事时间上也打破了时间的连续性[8]。比如揭示人物命运的预叙,在第一幕《贵子》中,歌手就已经概括揭示出总督的命运,他唱道“有一位总督,名叫焦尔吉·阿巴什维利。他非常富有,简直是个活财神......格鲁吉亚再没有另一位总督”[4]。第四幕《法官的故事》则通过歌手之口交代了格鲁雪和阿兹达克故事的平行关系,歌手唱道“就在大叛乱的复活节那一天,大公被推翻,他的总督阿巴什维利,我们这个孩子的父亲,脑袋被砍”[4]。在舞台演出方面,布莱希特通过让总督、总督夫人、铁甲兵等非主要人物戴上夸张的面具,进一步提示这些表现手法是艺术的荒诞和怪异,与现实生活无关,从而达到由陌生而达到“间离”。让观众意识到艺术只是激发理性思考途径才是布莱希特的主要目的。
陌生化的效果还体现在“第四堵墙”的破除,演员面对观众直接进行演唱,使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疏离感打破。演员不再是剧情里的主人公,他们是历史事件的表演者,戏剧的动作也不过是正在进行的表演。通过这种间离手段,演员与剧本也产生了距离,既不用被剧本所束缚也不必掌控观众,演员的作用不再是引起观众的共鸣,而是令观众辨别和思考。同时,布莱希特还大量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对复杂环境和人的心理进行了深刻刻画,这正是自然主义式的戏剧所无法做到的。比如当格鲁雪在听到胖侯爵要奖赏的同时,歌手通过演唱替不能发言的孩子呼唤,反映了格鲁雪内心的波动,他唱道“站在屋门和大门之间,她听见了……至少她听来是这样。‘女人,’他(米歇尔)说,‘救救我。’”还有如对深处环境演唱,“全城充满了大火与哀号”[4]。因此,叙述者的构建是区别于欧洲传统戏剧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歌手和乐队可以作为叙述者,演员自身也可以跳出剧情进行叙述。在第二幕《逃奔北山》中,关于出逃的格鲁雪,歌手唱道“格鲁雪·瓦赫纳采出了城,走上格鲁吉亚的乡间大路,前往北边的高山峻岭,她唱一支歌,买一点奶”[4]。而紧接着的乐队的演唱则是对歌手的重复和延伸,“有心肠人怎样能逃开没心肝禽兽,那些陷人精和噬血的豺狼?她逃往渺无人烟的高山峻岭,她走在格鲁吉亚的乡间大路上,她唱一支歌,买一点奶。”在歌手和乐队的演唱进行完之后紧接着的是格鲁雪的演唱,通过对出征伊朗的四个将军的蔑视和对索索·罗巴吉采的歌颂,为自己的前进之路鼓劲,她唱到“索索·罗巴吉采,出征到伊朗,硬仗不怕打,打了个大胜仗”[4]。从作为公开叙述者的歌手、乐队的第三视角营造了逃亡环境的艰难,而从演员自身的第一叙述视角展现了格鲁雪的心理活动,而这些正是欧洲传统戏剧难以表现的部分。布莱希特通过引入大量的演唱、朗诵的手段对环境、人物情感以及人物行动进行叙述的方式,正是其吸收讲唱文学之后所形成的“间离化”的叙事剧所具有的特点。
四、《高加索灰阑记》内容上的陌生化
李行道的元杂剧《灰阑记》中的开篇楔子部分首先是海棠母亲的陈述,海棠由于家道中落而沦为妓女,哥哥反对妹妹的决定而离家自己谋生,海棠则准备嫁给马员外为妾。之后的四折讲述了海棠为马员外生子,正妻胡氏与奸夫赵令史合谋害死马员外后诬陷给海棠,为了争夺财产把海棠的孩子留下了。海棠不服告官,却由于赵令史的从中作梗被定罪。在开封府中,包拯重新审理案件,将孩子置于石灰所画圈中,并让胡氏和海棠同时拉孩子,拉出者为孩子亲母。包拯从海棠两次都不忍心用力拉扯,判定海棠为孩子生母。元杂剧《灰阑记》与其余的“灰阑断子”系列一样,认为生母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人,血缘才是人伦之情的基础。
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楔子则是一个关于山谷之争的相对独立的故事。牧羊的加林斯克庄员在希特勒入侵结束后准备迁回山谷,而种植苹果的罗莎·卢森堡庄员认为山谷应该用来种植葡萄和苹果。在展开争论的过程中,牧羊庄员认为旧草好过新草。而苹果种植园的庄员从工具论的角度认为这片山谷不适合放牧,并说明了扩大种植面积和建设水利工程等计划。最终,牧羊庄基于实用的立场同意放弃山谷,而苹果种植园决定用“灰阑记”招待牧羊庄来表示感谢。这种对于效用的追求也正是布莱希特通过陌生化所想要实现的内容,所以戏中戏的《灰阑记》中,布莱希特摒弃以往“灰阑断子”系列中人伦之情来自血缘的传统模式,而是通过将孩子判给养母格鲁雪来强调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山谷之争中对于“灰阑记”的重述就在于为现实中人的关系提供间离式的理性思考。
《高加索灰阑记》的五场戏中,由于阿兹达克成为法官的过程穿插在格鲁雪与孩子关系的发展与灰阑断案之间,从内容角度来看连接松散、剧情间的逻辑性不够,但是这也正是内容上的陌生化的体现。因为在之前布莱希特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对于法官仅仅略施笔墨,“这位法官名叫伊格纳茨·多林格尔,以粗鲁和博学闻名整个施瓦本地区。”就是这样一位“会写拉丁文的粪土庄稼汉”却赢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他们“编了长长的歌谣称赞他、歌颂他”[9]。法官的性格特征得到了保留,但是扩展成一场的关于阿兹达克的故事间离了情节间的逻辑。而这种片段式的松散结构正是陌生化所追求的效果。
在人物塑造方面,女仆格鲁雪的善良纯真与癫狂混乱的法官阿兹达克形成了对照,孩子判定结果也是由将权威踩在脚下的出身下层的阿兹达克所决定的,加之以歌手、乐队的评论和叙事,通过喜剧化营造出了陌生化[10]。如当阿兹达克并非出于本意而救了大公之后,他骂自己道“我卑鄙,不仁不义,无耻!......因为我无意中收留过大公,那个大骗子”[4]。而当他去自首的时候却发现由于战争,社会秩序早已变得混乱,代表正义与公正的法官伊罗·欧贝利亚尼被织地毯工人绞死,警察局长、教长、总税务司长等人也已不在,旧的权利结构被解构,而阿兹达克则成了法官,进行正义的审判。这样的法官受到了底层人民的喜爱,而在“灰阑断子”中也正是他做出了合情但是不合理的决定。布莱希特将“灰阑断子”系列中象征绝对权威的神、佛、包拯改编为癫狂、胆小甚至有些无赖的阿兹达克,将庄严的法官形象解构的同时也造成了内容上的陌生化,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公正的判决不一定依靠神与圣人,可以共情之人皆公正。布莱希特并不是没有犹豫、怀疑、愤怒与失望,而是他在保持幽默,这种尖锐而明快的幽默正是对悲观失望的解毒剂[10]。布莱希特的创作不是为了观众短暂注意力的集中,而是强调将这种热情转换为认识的改变。正如因为收留逃亡大公而后悔不已跑去自首的阿兹达克一样,他的清醒与无秩序的环境造成的不和谐的陌生感令人觉得捧腹。因此正是基于陌生的形态,观众才得以对事物本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