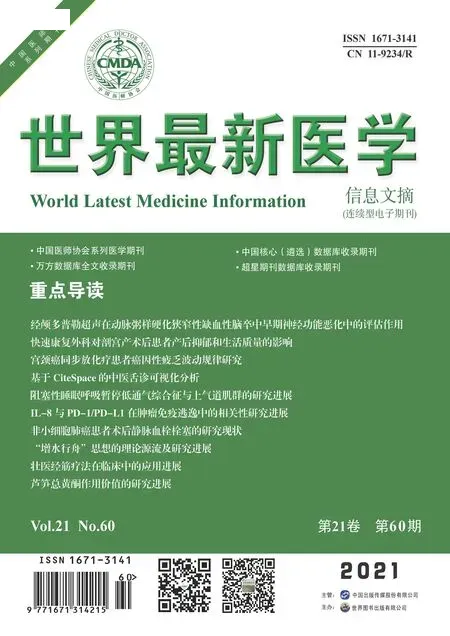PLR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2021-01-06李敏贾喜花
李敏,贾喜花
(承德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1 炎症与肿瘤的关系
早在十九世纪,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发现肿瘤通常发生于机体的慢性炎症部位,在肿瘤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由此推测肿瘤的发生与慢性炎症之间存在某种联系[4]。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慢性非可控性炎症会增加肿瘤的罹患风险,据统计全世界约有15%-20%恶性肿瘤的发生与感染、接触刺激物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引起的慢性炎症相关[5]。
慢性炎症反应可能早于肿瘤出现,这些致癌性炎症包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致胃癌和MALT淋巴瘤,炎症性肠病可致结直肠癌,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致肝癌等[6]。有研究表明[7-8],环境暴露也会诱发慢性炎症,吸入石棉和二氧化硅颗粒可影响炎症小体对促炎性细胞因子IL-1b的释放而引发慢性炎症,烟草烟雾等空气中的刺激性微粒物质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些炎症反应大大增加了肺癌的发病风险。
炎性介质的表达及炎性细胞的募集会重塑肿瘤微环境并促进肿瘤的生长,这种炎症被定义为肿瘤引起(或相关)炎症(TEI)。肿瘤微环境(TME)中免疫细胞释放的炎性物质,例如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可通过促进癌前细胞和癌细胞的增殖,以及增强这些细胞对死亡和应激的抵抗能力,直接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进展。此外,炎性信号可以通过树突状细胞、未成熟髓细胞和其他抑制因子诱导免疫抑制,增强TME中其他促肿瘤的辅助细胞(例如成纤维细胞,髓样细胞和新生血管内皮细胞)的募集、增殖,并改变TME对肿瘤代谢的调控作用[9]。肿瘤干细胞(CSCs)被认为是肿瘤生长和转移所必需的,但肿瘤中CSCs的数量和比例并不像正常组织中的干细胞那样是恒定的。相反,各种刺激,包括通过转录因子NF-kB和STAT3在肿瘤细胞中发出的炎症信号可以驱动它们的增殖,增加CSCs在肿瘤细胞群体中的比例,从而提高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10]。总而言之,肿瘤细胞和免疫元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直接促进肿瘤的发展,或导致肿瘤的免疫编辑,从而使肿瘤进入休眠状态或促进肿瘤免疫逃逸。
另一种重要的炎症类型是治疗诱导的炎症,它是在各种抗癌治疗手段,包括化疗、放疗、各种生物治疗以及免疫治疗所引起的免疫浸润反应下发展起来的。垂死的肿瘤细胞会释放具有免疫调节活性的损伤相关模式(DAMP)分子,如高迁移率蛋白1(HMG1)可以刺激IL-1a等免疫刺激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而这些肿瘤新抗原的增加可能诱导或维持抗肿瘤T细胞反应,或可能诱导免疫抑制[11]。
淋巴细胞、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可以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形式控制和塑造肿瘤微环境,并促进肿瘤生长。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作为新兴炎性标志物,可直接反应机体炎症反应程度,从而作为判断肿瘤预后的预测指标。
2 血小板与肿瘤性炎症的关系
血小板是由巨核细胞释放的无核细胞碎片,在机体内通过止血功能来保护血管的完整性。血小板除止血作用外,还可以促进血管内免疫反应的启动以及协调免疫反应的平衡。血小板持续监测血管的完整性,密切协调血管运输功能,帮助机体建立对感染和肿瘤的有效免疫反应[12]。血小板计数升高,或血小板增多症,最近被确定为恶性肿瘤的标志物。有研究表明[13]。血小板增多症的患者患肿瘤的风险增加,血小板计数增加也是隐匿性恶性肿瘤患者的肿瘤预测因子。
在感染或肿瘤患者体内,血小板与血管内皮细胞相互作用,通过促进血管生成、保护血管的完整性、调节血管通透性和血管张力、释放促转移因子,为肿瘤细胞的播散提供血管床,形成转移前的肿瘤微环境。粘附在肿瘤生长部位的血小板分泌原发性生长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前列腺素E2(PGE2)和溶血磷脂酸(LPA),可触发上皮-间质转化(EMT)并促进血管侵袭[13]。血小板是最早与血管内癌细胞相互作用的细胞之一,血小板几乎在进入血液后立即与循环肿瘤细胞(CTCs)结合并在其周围形成聚集体。血小板被膜可作为CTCs的机械保护屏障,血小板还可抑制自然杀伤性T细胞(NK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并逃避NK细胞的攻击。此外,血小板还可分泌促癌因子,并为肿瘤细胞提供粘附受体,促进肿瘤细胞的远处转移[14-15]。这些研究表明,肿瘤细胞能够通过“劫持”血小板,从而颠覆宿主对肿瘤的免疫反应。血小板与肿瘤细胞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肿瘤进展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因此将血小板作为靶点可能成为肿瘤的一种新的治疗方向,而血小板与CTCs的紧密结合使其可能成为靶向运送抗癌药物的理想运输系统[16]。
3 淋巴细胞与肿瘤性炎症的关系
淋巴细胞是人体免疫反应的主要细胞之一,它们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监测细胞变异、对抗感染,在肿瘤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是适应性免疫的主要力量,也是机体抗肿瘤机制的重要环节,其通过细胞毒性破坏作用和分泌效应因子来发挥抗肿瘤作用[17]。CD8+CTL能够以识别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MHC-I)的方式直接杀灭肿瘤细胞,目前大多数过继细胞疗法(ACT)以激发CD8+CTL介导的抗肿瘤反应为主要研究方向[18]。CD4+辅助性T细胞(Th)可为CD8+CTL应答提供“帮助”,防止CD8+CTL产生免疫耐受,促进效应性和记忆性CD8+T细胞的存活,从而增强CTL的抗肿瘤活性[19]。此外,CD4+T细胞产生IL-2可增强干扰素γ(IFNγ)介导的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20]。Foxp3+Tregs已被证明是肿瘤免疫耐受形成的重要因素,介导免疫抑制作用。在一个肺癌模型中,Tregs细胞被证明在肿瘤相关的三级淋巴结构中发挥作用,以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反应[21]。Tregs细胞可以通过直接的细胞毒作用介导CD8+T细胞的凋亡,而肿瘤衍生因子可以诱导Tregs细胞表达颗粒酶B,从而导致CD8+T细胞的杀伤和抗肿瘤免疫能力下降[22]。B细胞抗肿瘤免疫的潜在机制可能涉及肿瘤浸润的B细胞能够在肿瘤部位招募T细胞,从而促进和维持抑制肿瘤发展的T细胞反应。此外,肿瘤浸润性B细胞可能作为抗原呈递细胞来辅助抗肿瘤免疫[23]。因此,外周血淋巴细胞数与肿瘤免疫密切相关。一项荟萃分析表明,低淋巴细胞计数与多种实体肿瘤较短的OS和PFS有关,淋巴细胞减少患者的存活率明显低于淋巴细胞计数正常的患者[24]。
4 PLR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逐年上升,尽管肺癌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日益先进,但肺癌的预后仍然很差。因此,寻找更简单、有效的预测肺癌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尤其是血清生物标志物,有助于临床医生制定更有效的肺癌治疗策略。PLR作为外周血炎性标志物,在肺癌患者中具有潜在的预后作用。
肺癌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目前尚无明确的指标可作为肺癌发生的预测标志物。在一项对肺癌发病高危人群的随访中发现,PLR的年平均变化率与肺癌的发病相关,患肺癌组的PLR年平均变化量是对照组的11倍,而PLR每年增长值≥4%的人群的肺癌发病密度较对照组增高112%,因此年度PLR的评估可能作为肺癌的筛查指标[25]。
对于不能或不愿接受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是一种推荐的治疗方式,可以改善患者的局部控制率(LCR)和总体生存率(OS)。但在一项对SBRT治疗RTOGII期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虽然放疗对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很高,但仍约有20%的患者在3年内出现远处转移[26]。有研究表明[27],治疗前的PLR是SB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的预后指标,PLR升高的患者预后较差,而高PLR值(PLR≥250)患者在SBRT治疗后发生转移的风险更高。在早期肺癌患者中,SBRT治疗后的辅助治疗仍存在争议,PLR的水平对于患者后续全身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化疗和放疗是局部晚期或晚期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化疗耐药和局部复发或转移是治疗肺癌的主要障碍,慢性炎症在放化疗抵抗中起重要作用[28]。PLR作为全身炎症的反映指标,对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一项荟萃分析表明[29],在NSCLC患者中,PLR与OS独立相关,PLR值升高可显著预测NSCLC患者的不良预后,但在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中,PLR值与OS无关。另一项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的研究中发现[30],在接受同步放化疗的患者中,治疗前的PLR值与OS相关,较高的PLR(≥140.1)与较差的OS相关,而与无进展生存期(PFS)无关。有研究发现[31],治疗前PLR升高是Ⅳ期NSCLC合并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较差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PLR在NSCLC中有预测价值。一项对肺癌术后辅助化疗的研究发现[32],术前的高PLR是影响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PLR升高预示着术后辅助化疗的NSCLC患者预后不良。
随着分子医学和新的靶向药物的发展,肺癌的治疗已逐渐由以含铂方案为主的化疗发展到靶向治疗为主的个体化治疗。有研究发现[33],在ALK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中,较高的PLR与较低的PFS和OS相关,因此PLR变化趋势可作为判断ALK阳性NSCLC患者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病情进展情况的指标。另有研究发现[34],PLR可能是接受EGFR靶向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因素,治疗前高PLR组(PLR≥190)患者的PFS显著低于低PLR组(PLR<190)。
近年来,免疫治疗迅速发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格局。在免疫治疗时代,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的治疗中获得突破性进展,外周血炎性指标或可以作为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标志物。一项大型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表明[35],免疫检查点抑制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在二线及二线以上的晚期NSCLC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前的PLR值低于200时与较长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率(OS)、较高的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相关,治疗前PLR水平较高的NSCLC患者使用nivolumab的疗效可能较差。近期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36],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NSCLC患者中,治疗前PLR升高与较低的PFS和OS相关,而治疗后PLR与OS和PFS无明显相关性。一项对接受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治疗的NSCL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发现[37],治疗前的高NLR、低LMR和高PLR,与较短的PFS和OS显著相关。
5 结语
全身炎症反应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炎症反应了免疫系统抗肿瘤与促肿瘤功能之间的动态平衡。炎症主要表现为外周血细胞参数的改变,可以通过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血小板的比值来评估肿瘤患者的全身性炎症[38]。因此,PLR作为外周血炎性标志物,在肺癌患者中具有潜在的预后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证实PLR可作为肿瘤预后不良的标志物,但PLR对肿瘤的预后价值机制尚不清楚,尚需要对肺癌患者进行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以证实PLR在肺癌患者中的独立预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