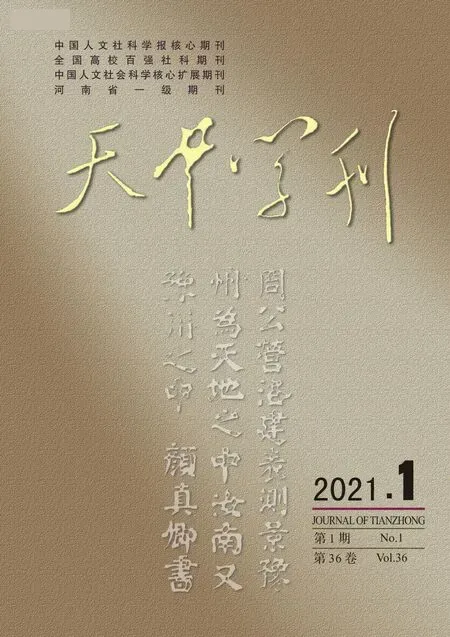唐代诗歌研究的新视域——评吴振华著《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
2021-01-06罗曼卢燕新
罗曼,卢燕新
唐代诗歌研究的新视域——评吴振华著《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
罗曼,卢燕新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吴振华新著《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是近期唐诗研究的新收获,该著以“诗”为本,以“序”为媒,联通文学与文化,考察文人创作诗歌的真实情境和写作心态,进一步探究唐代诗歌内涵以及社会生活的文化底蕴。著者一方面探索“诗序”一体的源流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文体的视角进行分类研究,既有整个先唐及唐代诗序的宏观考察,又以作家为纲,按照唐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揭示相关作家创作诗序取得的成就,并揭示诗序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文化意蕴。该著具有“穷源溯流,厘清理路”“自出机杼,另当别‘类’”“宏观把握,微观透视”等学术特点,思路清晰,结构新颖,见解深刻,为唐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诗歌;吴振华;《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新视域;新贡献
诗与序之间向来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序更是探幽诗之内涵的一个窗口,古人对《毛诗序》的看法便颇能说明序的牵引作用。宋代程颐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1]程大昌亦云:“古之序也者,其《诗》之喉襟也欤。”[2]马端临进一步阐明:“《诗》不可无《序》,而《序》有功于《诗》也。”[3]前贤所言均认为诗与序之间具有相得益彰、相互发明的重要关系。究其因由,诗与序作为同题之下的两种不同文体,互为补充,水乳交融,使作品整体呈现出辞约旨丰而又不至于晦涩难解的整体效果,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谈及诗与文的区别,认为“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4],道出诗歌艺术意象、意境具有想象性、朦胧性、暗示性的特征,而散文则相对明晰准确,故序之于诗,有着说明背景、揭示大义、补为解题等重要作用。
诗序经过先秦的萌芽期、两汉的生成期、两晋的成熟期、南北朝与隋朝的衰落期,及至唐代,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更加丰富多元,耐人寻味。唐人爱好诗且重写诗,诗性文化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且“诗序合一”是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以唐诗中的序作为切入点进行诗歌研究是唐诗研究的新视角。吴振华新著《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以下简称吴著)正是着眼于此,以“诗”为本,以“序”为媒,联通文学与文化,考察文人创作诗歌的真实情境和写作心态,进一步探究唐代诗歌内涵以及社会生活的文化底蕴。
一、穷源溯流,厘清理路
唐代诗序是著者聚焦的研究对象,那么对“序”这一文体进行穷源溯流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众所周知,一种文体的形成向来是漫长而复杂的,对序体进行追本溯源并非一件易事。关于“序”的源头学界说法纷纭且尚无定论,而其流变历程更是斑驳曲折,吴著锐意于此,沿波讨源,将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这团乱麻一点点理顺,并对其文学史意义进行深入论述,颇具拓荒之功。
吴著考索“序”之源头,不囿于文学的单一范畴,而能拓宽视野,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去寻找根源,并层层推演。
首先,著者从“序”的本义考索。“序”本指古代建筑物的组成部分,即东西墙,著者认为中国古人由于东西方位建立了时间有序交替的秩序观念,故古人十分重视东西方位,并将房屋最重要的东西墙命名为序。而后,随着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发展,进一步赋予“序”以秩序的含义。周代,序又有“学校”之意,学校设于王宫东、西郊,在于养国老,明人伦,推行礼制。可见,“序”的产生与古人生活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并因时而变,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其根本均与“秩序”“次序”之意相关。后“序”逐渐衍生出文体名称的含义,即介绍、评述作品内容的一种文体,这是因为“序”与“叙”“绪”音同义通,具有“端绪井然”“叙述次第有序”之意。著者认为“序”的含义显示了中国古人在重礼治的文化背景下,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秩序的形而上的理性追求,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文化内涵。
其次,关于文体的“序”产生的过程,著者则着眼于经典产生的先后,进一步分析“序”的产生和演变。著者认为《周易》作为最早形成的典籍,处处可见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是一部“原始要终”而“言之有序”的著作,《序卦传》含有排列卦序,指明各卦依次相承的意义,虽还未脱去“传”的胎壳,但已具有后代文体“序”的基本特征。而后司马迁作《太史公自序》解释《史记》也明显受到《序卦传》的影响,《太史公自序》可以看作“序”体正式确立的标志。随着历史的发展,文章体类越来越多,杂类个体文章的文集也随之衍生,文学作品由集体撰述向个体著述演变,西汉末期刘向校录群书,并为古籍撰写“叙录”,刘向所作的《新序》标志着文集序的诞生。而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考的单篇作品最早的序是贾谊《鵩鸟赋》前的一段文字,它与赋相互呼应,互为补充,并起到了范式作用。此后,汉赋并序相当普遍,而单篇诗“序”最早可考的则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并序》和《怨诗并序》。著者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最终考索出“序”体产生于整理编辑文献的过程中,书籍序远远早于单篇诗序,书籍序又衍生出文集序,而赋序又早于诗序,层次分明,轮廓清晰,让读者对“序”体的产生和流变一目了然。
再次,吴振华并不满足于勾画“序”体源流的轮廓,对其细节亦是探幽穷赜。如关于《诗序》正式产生的时间,学界说法较多:其一认为作于毛亨之前,即先秦时代;其二认为乃汉儒增补;其三认为是东汉卫宏所作;其四认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总体完成于西汉中期之前,东汉毛诗家亦有润益等,诸家皆有理有据,各执一词。面对这一“僵局”,著者转换思路从文体学的角度思考:“序”体的演化路径乃是经过“序卦”至“自序”,最终至单篇作品序的成型,如果《诗序》这样成熟而标准的“序”体产生于先秦,那么到张衡所处的东汉时期才出现第一篇“诗序”,则不合逻辑;而赋序的出现也是远远早于诗序的,经过著者的数据统计,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赋序有252篇,诗序有102篇,从数量看也符合这一规律,如果说先秦时期便产生305篇“诗序”,则显然不可思议,故著者认为《诗序》产生于东汉之前是比较合理的,符合“序”体的发展规律。著者对这一争议颇多问题的解答或有待学界继续商榷,但其从文体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无疑打开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也拓宽了古代“诗序”研究的范畴。
二、自出机杼,另当别“类”
在厘清序“体”的形成理路和先唐诗序的发展轨迹后,紧接着关键性的任务是对主要研究对象“唐代诗序”进行分类、演绎、总结和具体阐释。在这其中,分类看似容易,实则最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此前的“序”体研究,或是以体制为先,将其分为单篇序、集序和赠序三种;或是从表达方式上着眼,将其分为议论和叙事两种。著者认为这两种分类方法虽有其明确的分类依据,但过于含混和粗放,且唐代诗序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的统一体,难以明确区分。故吴振华自出机杼,按诗歌功能用途和创作情境来对诗序进行分类,将“唐代诗序”分为“赠序”“游宴序”“追忆之序”“独特经历之序”和“独特诗歌观念之序”5种,尽可能展示作品的真实背景、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心态。其中,“赠序”“追忆之序”“独特诗歌观念之序”的分类和具体阐释颇能显示出著者的匠心独运。
(一)“赠序”
“赠序”即送别友人或相互酬赠赋诗的小序。赠序是唐代诗序中最为流行,同时也是用途最广的诗序。中国古人素有“赠人以言”的文化传统,《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问礼于老子,辞去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5]“在友人离别之际相互劝勉、安慰、祝愿,成为人们表达和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符合古人‘有德者赠人以言’的寓意。”[6]57唐王朝疆域辽阔,经济军事强大,文化兼容并包,也涵养了唐人乐观自信、积极豁朗的性格,善交友,好远游,志在四方,故唐代的送别风气尤为兴盛,唐代的赠序也丰富多元,姿态万千。
著者将唐代赠序分为“帝王赐序”和“友人赠序”两大类。其中,“帝王赐序”是赠序的最高规格,如唐玄宗的《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序》,叙写对迟暮的贺知章辞官归道的理解和应允,进而命百官供帐青门,以宠行迈,对于受赠者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对于帝王而言,其目的在于“崇德尚齿”和“励俗劝人”,颇能显示出一种盛世情怀。“帝王赐序”是唐代送别风气浓厚背景下的一个文化现象,而“友人赠序”才是唐代赠序的重点和亮点。著者又将“友人赠序”按照赠别形式的不同,具体分为“赠别友人”“留别友人”和“酬赠友人”。
首先,“赠别友人”也分几种不同情形。送别从京城赴边塞、异域或外国者的赠序,多由朝廷的著名文人撰写,大都带着鲜明的政治特征,具有宣扬声威和怀远于边的政治用意。送别京城调往地方官的赠序,在中唐时期臻于高潮,这与中唐时期中央弱、地方强的总体形势密切相关,藩镇在广泛吸纳仕宦文人。此外,这类诗序的风格在唐代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初唐以文采昭著,盛唐以豪兴见胜,而中唐则以议论为主,总体趋于理性,追求敦厚中正。送别从地方入京为官、赴选或朝觐者的赠序,则通篇洋溢着对远行者前途的美好期待和祝福。送别入京应举或落第还乡的赠序,则以勉励和宽慰为主,用壮气来助行色等。正如江淹《别赋》中所言“别虽一绪,事乃万族”[7],不同的送别因由和场景调动的是人们不同的送别情感,但归根结底所表达的均是慰藉人心的真挚关怀。
其次,“留别诗序”一定属于“赠序”,但独特之处在于是离别之人所作,赠予饯送自己的友人,与赠别之作相比,情感更加真实浓厚,对送别者充满感激,往往以誓言来抒发感情。
再次,“酬赠诗序”是文人间相互酬唱、赠送的诗序,不同于“赠别诗序”的是,它的创作不囿于具体的送别时间和空间,凡兴之所至,均可酬唱和赠,创作的自由度更大,情感也更真实。著者认为酬赠成为原唱与和作产生的艺术触媒,是唐诗产生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方式。著者还敏锐地观察到中唐以后酬赠诗序远远多于赠别诗序,这一变化体现了群体行为向个体行为的转变,诗歌产生的情境空间逐渐缩小,当缩小到个人单独空间之后,于寂寞中独自品味心灵的诗歌就会大量产生。唐代诗序发展的一大特点便是赠序的大量出现,著者将赠序划归一类,并根据不同的创作情境对赠序层层细分并解释其背后具体的原因,详尽细致,令人豁然明朗。
(二)“追忆之序”
“追忆之序”,是著者另辟蹊径所单列的诗序门类。唐诗中存在一种重要的“追忆”现象,即诗人在某一场景的触动下,追怀往事,写出感慨深沉而沧桑的作品。尤其是在中晚唐,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大唐盛世轰然倒塌,诗人们追忆个人经历和历史成为普遍的现象,咏史、咏物诗大量涌现,许多诗序记载了这类诗歌产生的过程,诸多细节值得回味和探索。宇文所安曾在《追忆》中写道:“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8]追忆之序往往是诗人们带着感伤,噙着泪花,饱含缅怀之情写下的,因而其艺术感染力往往更加浓厚。例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并序》写杜甫晚年偶然在夔州古城看到熟悉的剑器舞,所舞之人是盛唐名家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这不禁令杜甫追忆六七岁时在郾城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的场景;当时公孙大娘动作迅疾奔放,节奏浏漓顿挫,获得满堂喝彩,杜甫抚今追昔,五十年沧海桑田,当初的梨园弟子如今四海飘零,那个舞乐繁荣的开元盛世已经永远地消逝了;杜甫通过对比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舞剑的舞姿、背景、场面、观众氛围以及各自的命运遭遇,抒发了物是人非、昔盛今衰的深沉感慨。另如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序虽篇幅不长却浓缩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被贬朗州司马,10年后被召回京师,因写作《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次被远贬连州刺史,又14年后,他再次回到京师,来到玄都观,“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9],刘禹锡通过昔是今非的场景道尽24年的命运无常、物是人非。著者注意到追忆类的诗歌和诗序主要出现在中晚唐,而这两个时期诗序特征也略有差异:“中唐时期比较多的作品集中在对往事追怀或故人的思念,而晚唐的作品则较多转向追怀更为遥远的故人或历史遗迹;中唐诗人,尤其是元和贬臣的诗歌情感更真切,因为是自己生命的独特经历凝结的感慨,而晚唐人则相对较弱,且往往带有传奇色彩。”[6]86
(三)“独特诗歌观念之序”
进入唐代之后,诗人更加自觉地在诗序中评诗论艺,追溯诗歌发展的历程,表达自己的创作价值趋向或憧憬的诗歌境界,传达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使唐代诗序具有文学史的批评意义。这不仅丰富了诗序的内容,更为文学批评史增加了斑斓的色彩。吴振华观察到这一现象,将之单列为“独特诗歌观念之序”进行论述。例如,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本是一首和诗,但因其序中包含了作者对创作理论的总结和其诗歌理念,提出的“风骨”“兴寄”理论适应了诗歌革新的趋势和潮流,带有鲜明的宣言性质。陈振鹏、章培恒认为“其长处也不在于阐述理论的说服力,而在贯注其中的高远的历史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未来诗歌的热情呼唤”[10],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诗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意义。另如白居易《新乐府并序》表达了他的新乐府观念:第一,注重新乐府诗干预社会生活的功能;第二,模仿《诗经》体制,首句标目,卒章显志,诗歌主题明晰,警醒人心;第三,题材真实可信,语言通俗质朴;第四,运用歌行体,追求节奏轻舒流走,有益于传播效果。该诗序言明确表达了作者“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不为文而作”[11]的诗歌观念,显示了作者重现实、轻文学的创作心理。白居易的主张符合中唐时期国家力图中兴的强烈心愿,也得到了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的广泛认同,在当时掀起了蓬勃的“新乐府运动”讽喻诗歌的高潮。再如韩愈在《荆潭唱和诗集序》中道:“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也。”[12]这篇诗序具有很大的诗学价值,与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则鸣”的诗学观念相互辉映。韩愈认为诗歌是落魄之士在羁旅他乡穷愁潦倒境地中的真情流露,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寄托,而王公贵人志得意满,除非出于天性钟爱文学,往往无暇亦不屑于创作诗歌,故诗歌仿佛总是与穷愁困顿结缘。这一观点从本质上总结了文学内部的创作规律。虽然到了宋代,尤其南宋,有一大批文人对这一观点有所异议,认为“鸣国家之盛”亦是“善鸣”,但“不平则鸣”论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也符合中国古代长期的文学批评传统,故而广为流传。总而言之,唐代诗序是表述诗歌理论的重要载体,唐人不像宋人那样有意识地专门着笔阐述诗歌理论、总结创作规律,唐人的诗学、文学思想往往伴随着兴之所往的创作一起产生,其诗论往往散见于其铺垫诗歌的诗序中,有的虽是短短几句,却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吉光片羽。故而,著者将“独特诗歌观念之序”单列一类,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诗序的研究本属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但从著者对唐代诗序的分类看,是不拘常规、自出机杼的,他能够根据唐代诗序具体发展的情形另当别“类”,以求最大限度挖掘诗序背后所蕴含的诗人真实的情感和观念,体现唐代不同时期的历史图景和文学思潮。
三、宏观把握,微观透视
吴著无论从架构安排,还是从行文分析,都充分体现了“宏观把握,微观透视”的特点。总体架构采用“总―分”的安排,先整体综述,再进行个案剖析,轮廓清晰,细节丰富,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往往能结合时代特点、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进行大背景的铺垫,继而精准对诗人、作品进行具体深入的阐释,点面映衬,相得益彰。
首先,就整体架构而言,吴著总共七章,前两章溯源“序”体的发展理路及先唐诗序的流变,重点关注唐代诗序不同阶段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高屋建瓴地把握“序”体的发展演变以及唐代诗序的总体特点。第三章至第七章则分时段进行个案研究,第三章将“唐代帝王诗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聚焦”探讨,四到七章则分时段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全面展开,选取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陶翰、李白、杜甫、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于邵、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等各时段代表诗人,对其诗序作品进行分析阐述,有条不紊,徐徐展开。
著者对唐代诗序的研究本着全面、细致、深入的态度,但又不想落于四平八稳的研究和论述模式,故而在整体构架上,以时间为轴纵线展开,以诗人为点横向对举,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著者在研究中能“因人制宜”“因作品制宜”,不断转换研究方法,对诗人及其作品进行最大程度的呈现。著者在进行个案分析中,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分析方法,而是因人制宜。对诗序作品数量不多或尚处于过渡期作品特点不甚明显的诗人,在分析其诗序特点时,著者按照诗序类型逐一分析,继而进行归纳总结,如对初唐四杰、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的分析。而对诗序作品丰富独特或对诗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著者则对其诗序特征直接进行归纳阐述,进而对其经典作品进行深入剖析,并分析其影响,如对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分析。此外,著者还将同一时期的诗人进行对举,如韩、柳,元、白,皮、陆等,将其诗序作品对比分析,既能呈现同一时期诗人诗序的整体面貌和气质特点,又能突显其独树一帜的地方。
其次,就个案分析而言,著者能将对诗人及作品的细致研究和时代大背景结合起来,既有宏阔丰富的视野,又有细致周密的分析,互为补足,相辅相成。著者在探讨盛唐诗序的问题特征时,将其与“盛唐气象”联系起来,如评析陶翰《送田八落第东归序》中“勿以三年未鸣、六翮小挫,则遂有清溪白云之意。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13]3382时,著者认为陶翰的诗序典型反映了唐人对待挫折的态度,“通脱而自信,自强而自尊,以铮铮之骨挺立于天地,这正是那个健康的时代赋予诗人们独特的诗性品质”[6]212。同时,著者认为陶翰诗序中的写景均展现了一种开放型的向外无限拓展的心境,如“云天极思,河山满目,菡萏春色,苍茫远空”[13]3381–3382、“征帆南岸,挑吴山而可见,值湖水之将碧。震泽千里,孤舟渺然”[13]3382、“杨花初飞,郊草先碧,自秦至洛,云山千里”[13]3380等,都写得气象阔大,境界奇丽,“不像初唐四杰那样剪翠雕红,拖沓繁复,而是简洁明快,将概貌特征与情感紧密交融,显得气象浑厚,情真意挚。诗序是短小精悍的抒情诗,与盛唐时代整体的雄壮浑厚文风是相融的”[6]213。著者认为,盛唐诗序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盛唐气象”,具体表现为:其一,从帝王到普通诗人,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时代都高度的自信;其二,诗人对自己的前途、品性和才能也充满自信,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其三,大唐全盛时期和平安详、繁荣昌盛的整体氛围,表现为诗人兴酣标举的精神状态,充满壮阔的想象、沸腾的情思;其四,“安史之乱”后,面对盛世的毁灭,诗人们无比怀念那个伟大的时代,企图通过改造文风影响士风,进而改革时代的弊病,重新回到盛唐时代。时代的氛围往往与士风、文风相互映衬,对时代风气的把握能更进一步了解诗人的创作心态和精神情怀,而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则会对当下的时代精神有更深层的体会认知。
再次,吴著在探讨中唐诗序的散文化特征时将其与“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著者认为,诗序在中唐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方面撰写诗序的作家和作品数量猛增;另一方面喜爱撰写诗序的以独孤及、于邵、梁肃、权德舆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掌握着主流文坛文柄,他们所创作的大量诗序也影响着主流文风的变化。中唐诗序的两大特点:一是更多地干预社会生活;二是散文化倾向,无疑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文运动以力图中兴、拯救时弊为己任,具体通过弘扬儒家忠君观念、大一统思想来改变藩镇割据下日益浇漓的世风,另外以流畅明白的散文体更大范围地传扬道德观念。中唐诗序所呈现的两大特点恰好与“古文运动”的宗旨相一致,故中唐诗序也承载了更多的历史内涵,成为议论时政方针的渠道、明道的工具、宣扬文学理论的载体等。总而言之,时代的需要是导致中唐诗序面貌转变的一大原因。另外,著者在第六章“中唐诗序研究”中反复强调,文体改革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代代人矢志不渝的努力,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等都用自身的实践创作避免诗序走向骈文的老路,不断将其推向散文化。著者认为文学史家习惯将在他们之后的韩愈散文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典型,是因为以韩柳为标志,“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故人们也习惯将文体改革的功劳“扣在”个人的头上,但实则从中唐诗序漫长的散文化过程来看,这一说法则并不精准。
最后,著者随文所附的两篇附论,亦以唐代的两篇“序”体名作为研究对象。附论一是以《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为中心论元稹的文学思想,附论二是对《津阳门诗并序》的深层解读,论析精彩,颇具新见。
其一,元稹的《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既是一篇精美的墓志铭序,又是一篇理论价值极高的诗论,其中既包含了元稹对杜甫诗歌的评价,也暗含了元稹自己的诗美理想。在这篇序中,元稹给杜甫的总体评价是“集大成诗人杜甫”,如若给杜甫贴上一个标签的话,则是“无诗体不擅长的多面手”。这是因为元稹认为杜甫熟知古今诗歌艺术题材的特点,擅长融会各人的独特专长,成为汇纳百川的大海。杜甫诗歌兼有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艺术风貌,既全面继承诗骚传统又具有当代品格。元稹之所以给杜甫如此高的评价,并提出了著名的“李杜优劣论”,认为杜优于李,主要是因为元稹对杜甫诗歌观念的推崇。首先,杜甫诗歌中包含大量以刺时事的谏诤内容,符合元稹的诗史观念,即主张诗歌要有干预生活的进谏功能。其次,杜甫继承了陈子昂以来肯定“建安风骨”的诗歌艺术风貌及诗学传统,这与元稹的复古诗学思想不谋而合,即要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真实的人生。此外,杜甫对诗歌格律尤为重视,晚年尤其致力于长篇排律,而元稹正是中唐时期的复古文学家中最重视格律诗的人,尤其喜爱长篇排律的创作,其与白居易酬唱所作的长篇排律成为一代诗人竞相效仿的诗体,即“元白体”,元稹对此有引领一代诗歌风向的自豪感。以上,正是元稹推崇杜甫的原因。
其二,《津阳门诗并序》被誉为“唐代七古第一长篇”,是一篇以盛唐时代李隆基与杨贵妃婚姻爱情为主线描写历史盛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规模宏大的史诗。其序文主要着眼于当下情境,交代诗歌背景是郑嵎读书赴考期间路过骊山,听一位年近花甲的老翁讲述玄宗时期华清宫的往事,并由此产生兴衰往替的感伤,因而作此诗。《津阳门诗并序》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史诗意义,史诗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历史意识”,即通过对古代或当代历史的书写,表达作者的史识。以李杨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最经典的莫过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比于《长恨歌》中以历史为背景,重点突出李、杨爱情的创作意图,《津阳门诗并序》则是以李、杨爱情为主线,重点在于全面深刻地展现整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另外,此诗中丰富的“自注”记录了大量的史实材料,表现了晚唐人对盛唐由盛转衰的冷静思考,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也充分符合著者在论述晚唐诗序时所言的“晚唐的诗歌和诗序往往具有感慨深沉的史诗性质”[6]377。
唐代诗序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了唐代文人士子的创作心态、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正如著者所言:“唐代诗序就成为一部鲜活的唐诗创造史,是一座诗人生活、情感、心境的活的资料库,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永恒的艺术价值。”[14]著者将唐代诗序视为独立的系统,以此来研究诗歌,回溯唐代社会的士风文风、历史风貌,视角新颖,新见迭出,论析深入,创获颇丰,为唐代诗序以及中国古代诗序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程颢,程颐.二程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46.
[2] 程大昌.考古编:诗论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3]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39.
[4] 刘熙载.艺概: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0.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09.
[6] 吴振华.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M].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36.
[8]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3.
[9]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03–704.
[10] 陈振鹏,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849.
[11] 白居易集[M].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52.
[12]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
[13]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吴振华.唐代诗序的文化意蕴[J].古典文学知识,2010(6):54–58.
I207.2
A
1006–5261(2021)01–0056–07
2019-12-22
罗曼(1994―),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卢燕新(1967―),男,陕西商洛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