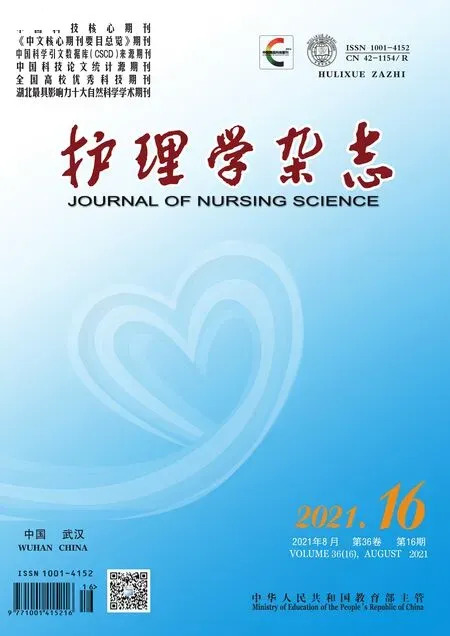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研究进展
2021-01-06肖美丽皇洒洒胡颖米春梅唐秋萍雷俊
肖美丽,皇洒洒,胡颖,米春梅,唐秋萍,雷俊
围生期抑郁(Perinatal Depression, PND)是指在妊娠期间或分娩后1年内轻微或严重的抑郁发作[1]。围生期抑郁严重危害母婴健康,严重者可出现自杀或杀婴行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2]。在发达国家,围生期抑郁发病率为11.4%,发展中国家为13.1%[3]。研究发现,围生期存在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孕产妇中,88.9%的孕产妇认为自己存在心理问题,83.0%的孕产妇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讨论过自己的情绪状态,69.0%的孕产妇认为可以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而实际上仅有33.0%的孕产妇在围生期预约过心理保健门诊[4]。围生期抑郁发生率高,危害大,就医率低,促进围生期抑郁女性主动寻求心理援助,有助于围生期抑郁防治。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是指存在抑郁症状的孕产妇为缓解或解除抑郁症状而寻求他人帮助的过程,包括向医务人员等专业人员求助和家人、朋友等非专业人员求助两种方式[5]。目前,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主要在发达国家开展,我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对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现状、求助对象和途径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我国开展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心理求助行为概念
求助行为(Help-seeking Behavior)指个体在面对问题或经历痛苦体验时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如支持、信息、建议、治疗)的行为,是个体在各种健康状况下延迟或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手段[6]。Nicola等[7]指出,以健康问题为导向的求助行为可定义为以健康问题为焦点,采取有计划的行动,并与求助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人际交往活动。而心理求助行为(Psychological Help-seeking Behaviors)是指存在心理痛苦或心理困扰的个体为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8]。围生期是女性的心理脆弱期,极易遭受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困扰[9],明确心理求助行为的定义,有助于对围生期抑郁女性开展心理求助行为研究。
2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现状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可发生在妊娠期及产后1年内,多与围生期产检时间或婴幼儿体检时间一致[10]。由于卫生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和社会环境等存在差异,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发生率有所差异。目前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9,11-15],发展中国家主要为非洲、印度、越南、希腊等[16-18],而我国相关研究数据暂未见报道。
2.1发达国家 总体上发达国家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发生率为13.6%~58.0%[9, 11-15],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即使在有可获得的健康资源情况下,部分发达国家仅有少数(20%~40%)围生期抑郁女性会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19-21]。Whitton等[22]发现,英国97.4%存在产后抑郁症状的女性体验到产褥期的心理状态较其他时间更糟,但仅有32.1%的女性会认为自己患有产后抑郁症,53.8%的女性会向家人或朋友谈论自己的情绪体验,11.5%的围生期抑郁女性认为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Fonseca等[23]报道,仅有13.6%的葡萄牙围生期抑郁女性会因心理问题采取实际行动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疗援助。而Barrera等[11]发现,3/4的西班牙孕产妇在围生期出现过明显的抑郁症状,但仅有44.8%的围生期抑郁女性主动寻求过帮助。
2.2发展中国家 Azale等[16]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仅有12.7%产妇因产后抑郁症状接触过医疗服务机构,实际上只有4.2%的产妇因为严重的抑郁症状寻求并获得了专业的心理保健服务。Park等[18]对15名越南美裔产后抑郁女性访谈发现,仅有3名产妇因为心理问题寻求过心理医疗援助。而在印度,受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极少数围生期抑郁女性会出现心理求助行为[17]。我国围生期抑郁发生率为17.4%,并呈上升趋势[24],目前对于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关于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数据暂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有必要评估分析我国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状况及影响因素,了解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需求,才能制订全面的心理促进干预措施,提高我国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
3 围生期抑郁女性求助对象和途径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的支持系统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指围生期抑郁女性向健康服务人员(护士、助产士、全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及心理咨询机构等求助,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是指向家庭成员(丈夫、伴侣、父母)、朋友等求助[6]。围生期抑郁女性更倾向于向家庭成员和朋友寻求帮助,极少数会向护士、医生等专业人员求助[2,25]。Fonseca等[6]发现,当围生期抑郁女性感知到其存在心理问题时,更倾向与家庭成员或朋友进行倾诉,并在家庭成员或朋友的鼓励下寻求专业的心理保健服务。Bina[26]对88名在产后6周筛查抑郁症状阳性的孕产妇心理求助行为偏好研究发现,69.3%因为抑郁症状寻求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心理援助,约23.9%向基层卫生保健人员、心理卫生保健人员等寻求专业心理援助,62.5%向家人、朋友等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寻求过心理帮助。除向家人和朋友进行内心倾诉外,通过电话、网络等同伴支持在围生期抑郁女性中获得较为积极的评价[27]。
4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4.1个体因素
4.1.1人口学特征 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会影响其心理求助行为。研究显示,低收入、高龄、经产的围生期抑郁女性更倾向于发起心理求助行为[23,26-27]。但低收入围生期抑郁女性是否采取了实际的心理求助行为还受居住场所及医疗机构往返交通状况和距离的影响[28]。围生期抑郁史和治疗史对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具有双向作用[26,29],既往存在不良治疗体验者存在更高的“病耻感”,会阻碍复发性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加重抑郁症状[29]。
4.1.2个体感知和态度 个体对疾病的感知、态度和信念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受孕产妇对围生期抑郁的感知和态度的影响。①感知因素:围生期抑郁女性能否感知和识别其抑郁症状,区分围生期的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及其自身的异常行为等都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研究显示,受抑郁症状的影响,部分围生期抑郁女性可能无法感知到其异常的行为(如哭泣、沉默、食欲不振等)[14,16],或者对其感知到的异常行为采取自我否认或逃避的应对方式,认为是围生期的正常反应,是由工作压力、婚姻状况、家庭关系、围生期激素变化等引起[26],而这种不正确的感知或错误的认知是阻碍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重要个体因素之一。②态度因素:个体对围生期抑郁态度和看法会影响其心理求助行为,如认为患有围生期抑郁的母亲是耻辱的,会被歧视和贴上“坏母亲”的标签,甚至被剥夺哺育、照顾和抚养子代的权利的围生期抑郁女性极少出现心理求助行为[30-31]。此外,还有部分围生期抑郁女性认为若被诊断患有围生期抑郁会影响其社会形象和工作,即使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如自杀的想法、自我伤害、哭泣等)也会拒绝向他人求助[28]。
4.2心理求助服务提供者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服务提供者主要为医务工作者(医生、护士、助产士、心理咨询师等),能否为围生期抑郁女性提供有效的心理保健和就医服务会直接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17]。医务工作人员作为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服务的提供者,心理保健知识是否充足,有无心理保健相关培训和实践,能否提供充足、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能否提供连续的围生期抑郁管理服务,治疗方案能否获得围生期抑郁女性的认可,能否平等对待围生期抑郁女性并给予适当的人文关怀等,均是围生期抑郁女性向专业人员寻求心理援助的影响因素[25,32]。研究显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缺乏心理保健知识、缺乏围生期抑郁相关培训和实践会影响医务人员提供心理保健服务能力,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评估、干预和转诊,给围生期抑郁女性带来不良治疗体验,从而阻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33-34]。而在围生期抑郁女性向医务人员进行心理求助过程中,心理求助服务提供者的态度是影响其是否选择接受围生期抑郁治疗的最重要因素,当围生期抑郁女性感受到来自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会促使其更多地表达内心需求,提高其就医依从性[35-36]。此外,医务工作人员在提供连续性管理服务过程中制订的治疗方案能否获得围生期抑郁女性的认可不仅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治疗的依从性,还会影响复发性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再次心理求助行为[15,28]。研究表明,既往无效的心理求助体验和治疗体验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降低其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不愿意与医务人员倾诉其内心真实感受[37]。
4.3社会环境
4.3.1公众认知 社会公众对围生期抑郁的固有印象或批判性语言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如为围生期抑郁的产妇贴上“精神病患者”等污名化标签[38]。而这种污名化的标签还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家庭社会关系,如配偶/伴侣、家人、朋友等对围生期抑郁的理解,从而阻碍围生期抑郁女性向配偶/伴侣、家人、朋友求助[13]。然而,在一些低收入群体中,这种社会污名化会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对其心理问题的认知和态度,阻碍其直接向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寻求帮助,致使其更倾向于向陌生人求助或者在网络上寻求匿名的帮助[17,38]。
4.3.2文化习俗 部分亚裔印度女性认为,围生期抑郁不属于医疗问题,是生育的自然结果[17],其会伴随身体的康复逐渐消失。另一项对以色列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明确的社会角色影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这类孕产妇更多地通过宗教求助来倾诉其具体的心理需求,在宗教团体的帮助下进一步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26]。此外,受西方文化和本国文化习俗的影响,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亚裔和移民女性认为抑郁症是“私事”“禁忌”,不应该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应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感受和想法等都会阻碍孕产妇的心理求助行为[39-40]。
4.3.3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缺乏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心理保健资源及资源分布不均衡、无相关心理服务政策支持等都是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31,41]。如在发展中国家或农村地区的围生期抑郁女性,由于心理保健资源的缺乏或未建立围生期抑郁的转诊制度,无法就医或者得不到连续的心理保健服务,致使其放弃就医或拒绝向医务人员倾诉其心理问题[32,42]。此外,大部分心理保健服务需要围生期抑郁女性自己承担或者通过医疗保险支付费用,而现有医疗体系中主要是通过自费的方式结算,因此心理保健的医疗费用会阻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7,14]。
5 建议
5.1加强围生期保健心理服务建设 我国妇幼保健系统相对完善,尤其是计划生育相关流程严密,妊娠女性从怀孕服用叶酸到产后42 d的访视都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目前的妇幼保健系统并未嵌套与孕产妇心理相关的围生期保健体系,对于围生期抑郁孕产妇心理服务相关保险政策也未制定,且地区间心理保健资源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未来研究有必要针对我国现有妇幼保健系统,结合我国特有的孕产文化(如坐月子),探索和研究我国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现状、求助对象和途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以发展适用我国围生期保健体系的有效行为改变或健康促进策略,加强我国围生期心理保健服务建设。
5.2加大围生期抑郁科普力度和深度 个体对围生期抑郁的错误认知、社会大众对围生期抑郁女性的标签化和污名化、某些文化习俗等都会阻碍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个体对疾病的正确认知有助于对疾病的预防和管理。在围生期保健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通过社会媒介、医院孕妇课堂、社区讲座和宣传等方式加大围生期抑郁病因、自我识别方法及预后等的科普力度和深度,促进个体以及社会大众对围生期抑郁发生原因、治疗和预后的全面理解,让个体和社会大众认识到围生期抑郁是可预防、可治愈的,以提升孕产妇对围生期抑郁的自我识别能力,改变孕产妇的不正确认知,发挥社会大众在促进围生期抑郁女性的心理求助行为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
5.3开展相关研究
5.3.1开展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均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阐述其求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缺乏理论解释。开展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心理求助行为对围生期抑郁女性的意义,并了解内在影响因素(个体感知和信念)和外在影响因素(社会环境、求助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指导医务工作者制订更切合实际的干预措施,促进围生期抑郁心理求助行为的干预策略的临床实践。
5.3.2注重行为转变干预研究 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大体可分为个体因素、求助服务提供者和社会环境3大类,但现有研究对于3个方面的因素如何作用及其相关性如何尚不清楚。未来研究需综合考虑其内部影响方式和相关性,在社会学科学、行为科学等相关理论指导下,探索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对象和途径的偏好,并充分考虑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在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中的积极作用和文化习俗的双向作用,开展促进围生期抑郁女性心理求助行为的干预策略,以提高干预策略的应用性和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