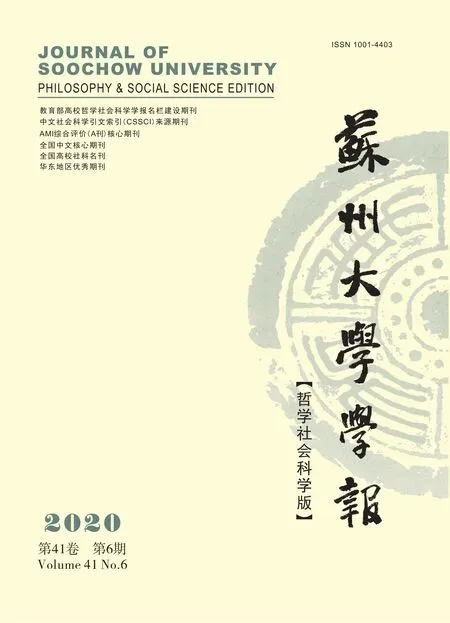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社会适应
2021-01-05陈云霞
陈云霞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一、引言
开埠以后,许多外省移民进入上海城市,他们由农民、小商贩、游民、手工业者等多种行业组成,构成了一个仍然相对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这些移民秉承籍贯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他们如何适应正在近代化的城市社会、如何在城市文化中维续自己的家乡习俗?这些问题是理解近代上海基层社会及文化生活的重要切入点。民间信仰自宋代以后就变为地域性的文化要素,成为组织地域社会的重要纽带。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高的移民城市,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有可能参与组织城市传统基层社会,帮助移民适应城市社会生活,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民间信仰对近代上海城市外来移民在适应新的城市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重新解读近代以来移民背景下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运转及其文化的形成。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适应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籍贯移民进入城市后,通过各自的民间信仰来达到身份认同,并据此建立社交网络。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围绕民间信仰形成特定的城市社会空间。目前学界对这几方面的研究包括:
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的传播、与社会控制及地域社会变迁的关系等方面。20世纪后期国内“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下,对信仰与底层社会的关系关注较多,开始讨论民间信仰与城市空间及社会组织的联系。尤其是对近代北京城市和江南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的关系讨论很深入,论述宗教场所及社群活动,描述祠庙与城市政治文化在空间上的联系,由宗教视角展现京城的城市生活和社会组织活动。滨岛敦峻、王健等关注民间信仰与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在社会结构中如何发挥作用。[1,2]对移民社会网络构建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领域,其中跨境移民适应通过建立同乡组织、校友会等各种团体、组织来实现,具体是以语言、文化习俗为媒介。西方学者认为移民是基于家庭、社区等关系的社会网络,因此强调群体在移民适应中的作用。这一群体即包括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也包括业缘等形成的团体。前者如日本学者广田康生(2005)《移民和城市》以秘鲁日裔同乡会的冲鹤会馆为例,采取问卷调查法复原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建构。[3]而中国境内的移民如城市务工人员、环境移民等,相关研究则关注其地缘关系和文化习俗要素。后者以汉口商业组织和社会以及城市冲突的研究为例,行会、会馆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身份认同方面。身份认同决定人的价值取舍和行为指导,从而决定移民参与何种社会组织、是否适应城市生活。对城市中不同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以美国大城市中意大利、中国等国移民社区为代表。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对波士顿东区的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研究,通过“参与行动”研究法分析了诺顿帮的身份认同、形成、内部结构、活动方式以及与周围社会的关系。[4]对上海的华人移民社区(地域社群)从身份认同角度进行探究,裴宜理等对上海外省移民的籍贯身份认同都有所关注,分别从地缘关系、职业关系等角度研究上海基层的社会组织。[5]
总的来说,对民间信仰和移民社会已有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对城市范围内的民间信仰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将它与城市基层传统社会组织联系起来,放在近代化背景下考量。移民进入上海时带入了他们籍贯地的民间信仰,并按照传统的地域社会组织方式来生活。本文着重研究移民如何凭借民间信仰这一传统文化形式来适应城市社会,复原以民间信仰为中心形成的移民社会网络,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研究其构建的城市社会空间,来探索近代城市转型中民间信仰在组织基层社会和构建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本文中民间信仰是指佛、道等制度性宗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它对神祇的系统归属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文的教义,信众是基于实用需求而非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移民在本文中特指近代国内其他省份进入上海的流动人口。
二、以民间信仰为纽带构建移民社会网络
移民作为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重要部分,在进入上海新的城市环境时,大多是通过乡缘关系、业缘关系、入帮派等形式进入并立足下来。而这三种组织形式又往往都是凭借某种民间信仰神灵这一纽带结合在一起,出于心灵上的慰藉而形成对特定地域来源人群的凝聚力。他们信仰同一行业神、地域神或者帮派神,组织相关的祭拜、神像游行等社会活动,从而建立有组织的社交关系网络,民间信仰祠庙在这两种关系中分别起到了组织群体和寄托乡情的作用。
首先,民间信仰祠庙是外省移民进入上海城市的重要媒介,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是这些移民进入上海城市时往往出于生活窘迫、无所依靠的状态,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寺观都好善乐施,经常成为难民的临时栖息地。无论是上海原有的祠庙还是开埠后移民新建的祠庙都成为移民进入上海后寻求帮助和落脚的地方。
近代上海闸北和虹口是江北移民分布最多的区域,也是民间信仰祠庙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以虹口昆明路下海庙为例,其周边往往是江北移民落脚上海的第一站。根据1948年《工业要览》和《老上海百业指南》的记载,下海庙往南不远的黄浦江畔分布着华顺码头、招商局码头、共和祥码头等众多码头,这一区域是码头工人集中的地方。往西的丹徒路有国华棉织厂和染织厂等,是纺织女工聚居区。往东是纱厂、纺织厂密集的杨树浦工业集中分布区域。[6,7]由于可以提供较多底层劳动的机会,下海庙区域成为江北人在上海的聚居区之一。1893年《申报》记载了263名江北难民借宿下海庙的情景:
前晚有江北难民二百余名,从江湾镇至虹口东北下海浦下海庙中住宿,美捕头闻之立即禀明英谳员蔡太守。太守派差役张福等会同包探唐宝荣江阿三前往弹压。……昨日午前曹君传问难民头目四名,均称姓张自徐州逃荒至此。问共有若干人,答称共二百六十三名口。(1)《资遣难民》,《申报》,1893年7月17日,第3版。
这一现象在开埠以后十分常见,他们进入上海后往往从事较为底层的职业,上海市社会局档案就记载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成员的职业和住址,其中位于虹口的大部分是从事猪业、盐业、纺织、运输等生活、生产服务类。(2)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江北旅沪同乡服务社注册登记等文件》,卷宗号:Q6-9-228。《申报》曾记载,盐城女工乔刘氏在丝织厂做工,其夫乔某是黄浦江畔水手。因刘氏沾染花会赌博恶习,求神问卜。听闻下海庙神仙灵验,将所有财物交与典当,用来祭拜神灵。(3)《花会害人不浅 求神灵孤注一掷 妄贪财竟致发狂》,《申报》,1928年5月21日,第15版。可见,移民在初进上海时对民间信仰祠庙有着很大的依赖。
以闸北为例,闸北是开埠以后江北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分布着与江北人相关的信仰。民国时期上海市社会局对寺庙的调查中记载:都天庙位于闸北中兴路,建于民国十一年。该庙由定居在沪北的江北民众捐建,供奉避瘟都天大帝等民间信仰的神灵。(4)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关于都天庙注册登记等文件》,卷宗号:Q6-10-218。通过检索《申报》数据库和《全国报刊索引》发现,闸北都天庙建立之前的报道都是来源于镇江、扬州、六合、清江、淮安等地,这说明都天庙是江北地区的地方信仰。而居住在闸北的江淮客民,每届阴历三月举行都天神会。(5)《闸北客民昨迎都天神会》,《申报》,1926年4月15日,第15版。根据调查档案,20世纪30年代都天庙的住持是南通人,其僧员中扬州籍2位、通州籍1位、盐城籍1位、南京籍1位、徐州籍1位、泰县籍5位。神灵主要功能是保佑沪北民众。(6)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关于都天庙注册登记等文件》,卷宗号:Q6-10-218。从创建人、住持和僧员的来源看,闸北都天庙是江北移民在上海建立并专为他们服务的地方信仰,以它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也是在旅沪的江北移民当中。例如都天庙1934年举行都天大帝万福胜会大游行……参加者有十万人以上,大会由闸北都天庙出发,经中兴路、共和路、梅园路、恒丰路以迄,舳板厂新桥折回该庙。自上午九时起,迄下午五时止,游行路线尚未终止。当时共和新路、新民路、光复路一带之观众如潮汹涌,而沿街店屋均挤满人头,水泄不通。(7)《闸北都天会》,《申报》,1934年5月14日,第12版。都天庙神像游行的范围集中在闸北火车站附近,是江北人集中分布的地方,围绕着闸北区域祠庙分布着大量的江北移民,成为江北人棚户最为集中的地方,甚至建造有江淮村。⑦(8)⑦《沪滨大风纪(四)》,《申报》,1915年7月31日,第10版。此外,位于附近大统路的太阳庙,建于光绪五年(1879),也是如此。在1925年《申报》记载太阳庙附近的一场大火时,焚去草屋三百余户,大部分是江北贫民,据统计波及人数在三千人以上。⑧(9)⑧《申报》,1925年4月22日,第13版。太阳庙主要供奉太阳佛等佛教神灵、太上老君等道教神灵,以及土地公婆、豆神王等民间信仰神灵⑨(10)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太阳寺注册登记等文件》,卷宗号:Q6-10-73。,可以满足江北移民的各种需求,他们在精神上依赖这些信仰,甚至在附近建立了徐州旅沪同乡会和旅沪江北同乡会,形成特定区域的社会网络。⑩(11)⑩《两同乡会消息》,《申报》,1926年6月21日,第16版。
另一种方式是进入上海之后,外省移民借助同乡、同业的纽带得以安顿,这当中由于拥有共同的民间信仰而得以凝聚在一起。一些移民进入上海时本身就是携带着自己家乡的民间信仰,甚至在上海重新建立他们家乡的民间信仰祠庙。例如开埠以后,旅沪的湖南籍移民在上海建立了瞿真人庙,奉祀湖南本地的神灵瞿真人。瞿真人庙受到湖南会馆的资助,后来直接供奉在会馆中,作为会馆神。
为了寄托乡情、融入新的城市环境,移民加入同乡会等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具有宗教性质的祭拜同乡神祇。新来的移民要想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归属于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又往往是同业或同籍,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经过祭拜神灵这个程序。《申报》记者曾经希望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信仰在上海移民关系网中的地位:
记者扮演乞丐,作为一个浦东乡下来的乞丐,借助乡缘关系与其他乞丐结伙。记者通过拜‘老头子’与其搭成关系。这种团体关系是有秩序的,需要支付侍奉费、磕头、到庙里烧香求菩萨等等环节。[8]277
拜老头子是近代以来中国基层秘密社会的组织形式。在这里乞丐并不是为了寄托乡谊,而纯粹是出于生存需要投靠跟自己有某种联系的“组织”,于是,“到庙里烧香”也就成为组织这种有秩序的团体关系必要的程序之一。
对于同业公会、公所、同乡会这些社会组织来说,祭拜共同的神祇无疑可以增强其团体的凝聚力,这也是仪式在群体信仰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浙绍公所肇兴中秋会碑》中记载的那样:
自乾隆初年间,邵郡商绅在上海地方贸易,立有铺户,计在久长。犹虑樯帆来往,无总会之局,于是就近本城北门内,置得隙地一处。当即具呈纳粮,建立公所。一则以敦乡谊,一则以辑同帮。惟生理之兴隆,全仗神灵之默佑。况我绍郡,最钦崇元坛正神。爰聚同事而谋曰:既有公所,正可供奉神明,以荐瓣言,而求保护。签曰:唯唯。遂乃鸠工庇材,聿宏庙貌。[9]210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绍兴的旅沪商人建立公所的缘由有二,即“辑同帮”和“敦乡谊”。这其中的“辑同帮”就是组织同行业、同籍贯的群体,而这一目标则是通过“奉神明”“聿宏庙貌”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在组织同业、同乡这一群体的过程中“奉神明”成为必须且可行的办法。
由于依靠同乡或同业关系进入上海,他们所建立的社交网络往往是在同乡和同业中间,而与其他的城市群体其实是隔离的。例如,上海原有的鲁班信仰在不同籍贯的水木业工人进入之后,产生了宁波籍、上海籍、广东籍之分,各自举办祭拜鲁班神像的活动,成为区分地域人群的关键要素。
移民通过同乡团体进入上海,并以共同的祠庙、信仰、社会活动为连接点构成相应的地域关系网。可以用简易的线路图来展示:
移民个体——联系在沪同乡——进入同乡、同业组织——祭拜神灵——参与群体活动
三、移民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民间信仰
原生环境的文化生活不仅能够帮助移民适应新的城市,还给移民在城市的身份打上了地域特色的烙印。移民所带入上海的民间信仰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渗透到地方戏曲、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生活习俗等形式中,在移民的生活中得以存续和传播。正是这些具有家乡味道的文化形式才满足移民的文化心理,帮助他们来适应陌生的城市环境。
地方戏曲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始就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联系。首先,民间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以戏曲为载体,通过信众们的传唱而进一步扩散。在这种情况下,戏曲的流传路径与所携带的民间信仰基本一致。同时,在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中也有戏曲的参与,例如某些民间信仰举行庙会或迎神赛会。在此过程中戏曲一直发挥着娱神娱人的作用,而戏曲的故事主题也是关于某位神灵的英雄事迹。
目前对上海地区的戏曲记载比较详细的资料多来自于早期访谈。当然,并不是上海城市每位民间信仰的神灵都会在戏曲和曲艺中体现,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民间信仰的祭祀仪式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上文所述,开埠以后,闸北江北籍移民信奉太阳菩萨,并在苏北人分布较集中的闸北区域建立太阳庙,这一信仰逐渐融合至上海城市流行的淮剧、长篇弹词中,体现了外来信仰借助戏曲等文化形式传播并凝聚地域人群的过程。这一信仰在上海城市的民间曲艺中有所体现,长篇弹词《描金凤》中就有关于向太阳菩萨求雨的唱段:
(表钱丢筊)背心上也觉着哉,辣豁豁,啥物事?往上一看,完,一轮太阳。那是好了,我巴望有点雨下来,我好活命,现在什梗一轮太阳一出,哪哼还有雨呢?我是必死无疑。
(钱丢筊)哈哈,太阳菩萨,倷倒早拉海,我一夜天不曾困,看来倷也是等天亮。
太阳出得啥能巴结……
油煎和尚我听见过,活烤道士倒忒新鲜。
(小道士白)霍险娘娘(12)“闪电”的意思。是姓霍呀,那哼姓许呢?
(钱丢筊白)俚娘家姓许,霍门许氏,我依俚笃(13)“他们”。娘家叫末算搭俚着肉(14)“亲近”“贴近”。点。[10]47-51
唱词中求雨道士提到太阳菩萨和霍险娘娘两位神灵,并认为自己能通过与其拉近关系的方式来实现降雨。虽然不能根据它复原出太阳神信仰具体的流行空间,但可以肯定它对上海城市戏曲的影响。除此之外,太阳庙路还是苏北人所喜爱的淮剧日常演出地点,在这里出现了“搭墩子”,即用筷子击盘底拍打节奏,坐唱淮戏。而苏北人在开埠以后进入到上海城市的同时也将家乡的民间信仰神灵带入到这里,移民、民间信仰神灵、戏曲三者在空间上分布的重合性正说明了民间信仰与其他两者的承载关系。苏北人所流传的淮剧,在开埠以后随着移民进入也在上海开设了许多相关戏院,并于1914年在闸北太阳庙创立第一间江北戏院。著名淮剧演员何小山曾回忆,其祖父等淮剧演员一行七人在闸北太阳庙路租赁房屋,用泥土堆砌舞台,招引观众看戏。而这些来自江北地区的戏班在家乡就往往选择在庙宇中搭台,有宝应城隍庙、兴化都天庙、建湖神台庙等。何小山回忆寺庙演出常在晚间,没有住宿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睡在菩萨脚下。[11]2,24根据张金贞的研究,闸北江北人集中的地区,分布着平安大戏院、交通大戏院、复兴大戏院、共和大戏院,都是以演淮剧为主。[12]而这一区域也是民间信仰集中分布的地方,除了太阳庙、都天庙,还有天通庵、黄大仙庙、神仙堂、胡神仙庙等。其中江北地区都天庙在迎神赛会时流行的跳马伕舞蹈,在开埠以后也伴随闸北都天庙的建立而在上海地区流行。[13]213
对具体某个民间神灵或祠庙的传唱除了上述几段之外,还有《苏武庙》《八腊庙》《三官堂》《逛庙》等戏曲片段。信众在奉祀民间神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仪式,如请神、酬神、送神等。这些仪式在执行中出现了一批相关的仪式曲调,如《酬神调》《神鼓调》《接神调》《请神调》《敬神调》。[10]1156这些曲调可以用于具体某位民间神灵祭拜仪式中,例如《茶神》选段中采用了《请神调》,《药神》唱段中采用的是《酬神调》,《八仙过海》唱段中采用的是《基本调》。当然,这些选段内容都是针对某位民间神灵,如《药王》中是采用酬神调唱出对神农氏的敬意。在这些受民间信仰影响的曲调形成之后,它们被填词运用于更多的场合表演。包公信仰也是近代上海城市民间的特色信仰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申报》对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寺庙调查结果刊登时就有记载,“包公庙,位于闸北会文路”(15)《申报》,1928年8月27日。。近代上海关于包拯的民间传说主要流行在宝山、长宁、虹口,主要有“包拯幼年过三关”“包拯审理井尸案”“刀下留人”“包公管闲事”。[14]71-77而较为常见的戏曲片段《铡包勉》《打龙袍》《铡美案》等也在近代上海地区流行,其内容都是关于包拯清廉任官、秉公无私的事迹。[15]9在包公祖籍的合肥地区同样也流行着庐剧的传统剧目《铡包勉》《打龙袍》《铡美案》等,只是上海地区以沪剧等形式呈现出来。再如澳门的包公庙,又称“睡佛庙”,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其建立的原因在于澳门流行瘟疫,当地居民迷信鬼怪作祟,于是从佛山请来包公神像坐镇。由此可见,虽然包公庙奉祀的对象都是包公,但是各地地方人群由于实际需求的不同,对包公信仰功能的解释也不尽相同。
这些戏曲、曲调在移民日常生活的许多场合得到展现,不一而足。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社会活动,根据其使用的场合可以大体分为庙会戏、堂会戏、行业戏、应节戏。上海自始就盛行迎神赛会,其中民间信仰和戏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某一民间信仰和戏曲得以扩散和传唱。例如在1893年5月的《申报》中就有对上海萧王庙迎神赛会的描写:
萧王庙供奉神像,乡人以三老爷呼之。只以年深月久、日炙雨淋,栋宇渐形倾塌,由董事王某集款兴修。迄今,工程告竣。遂于前昨两日迎神赛会,并雇英租界天仪戏团诸伶于十五、六、七等日登台演唱,裙屐纷至。(16)《古刹重兴》,《申报》,1893年5月2日,第3版。
迎神赛会的程序几乎是固定的,由信众升举神像游行,并伴有戏曲演出。可见,无论传唱的戏曲内容直接是某个特定神灵的事迹,还是在对神灵相关祭祀活动中演出戏曲,民间信仰都附着于戏曲并为移民所接受,客观上成为他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正是以上所说的这些民间信仰完全渗透进了生活习俗、地方戏曲、民间舞蹈,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一方面证实着民间信仰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推动着民间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客观上帮助了移民适应城市生活。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收集大量的民间传说里可以看到,传说所流行的区域也大抵是该信仰盛行的空间范围。以上海城市为例,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关民间信仰的传说,并且有明确的流行区域的,详见表1。
可以看到,这些民间传说的主角是民间信仰神灵,其内容多是该神灵生平信息以及相关显灵的事迹。从传说流行区域和祠庙地点的对比来看,呈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可以说在上海城市内一种民间神灵相关传说的流行多是在该信仰祠庙存在的周边,并对该信仰的传播、扩散起了一定的承载作用。正是这些带有民间信仰的民间文化形式,才帮助移民进入上海时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迈出参与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第一步。

表1 上海城市相关民间信仰传说及流行区域
四、民间信仰参与构建移民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和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可以反应移民对空间占用背后的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移民进入上海以后围绕着民间信仰祠庙分布居住点、工作点,还围绕民间信仰祠庙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例如举行祠庙神像的迎神赛会游行,最终表现为民间祠庙和移民活动空间、相关商业布局、营生地点及信仰神像游行范围在空间上是一致的,并产生移民对这一空间的情感认同。
首先,民间信仰祠庙本身作为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往往成为人们互动、交流信息等社会活动的重要区域,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对人群的集聚功能。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考察团进入上海老城,“在一个庙宇里过宿”,并且引来许多中国人来围观。而当英国使团向上海道台提出在城内居住遭到拒绝时,使团提出要在城内找到一处庙宇搭设帐篷。中国传统的城市结构中,与国家秩祀的寺观不同,民间祠庙是普通民众可利用的公共空间,他们若遇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可随时向祠庙的神灵申诉。这种祠庙多是捐建,在归属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在英国考察团进入上海时这种祠庙也可被视作没有明确归属的资产被他们使用,可作为一个公共设施以供其搭设帐篷。
由于这一公共空间在外籍人士眼里可以聚集大量的人群,因此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上海企图传教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祠庙。《民国史料丛刊》所收录的《百年来的上海演变》一书中就记载到这样的情形:
美国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极有希望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举动之中又有许多却使这班教士非常之惊骇。如过端午节拜太阳菩萨的生日、拜火神菩萨、拜灶司菩萨之类,尤其是新塑的佛像之开光,用鸡血去点这佛像的眼睛。中国人在举行这种节日的时候都兴高采烈,十分起劲,酒肉杂陈,锣鼓喧天,香烟缭绕,熏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有一天正碰着某庙里的菩萨开光,圣公会的两位牧师赛尔和斯实庭拿了些小册子走进去分派给那些来拜菩萨的民众。不料,大家竟抢着要这小册子,第一批所带去的片刻分完,两位牧师很是得意,这时已有了一大群民众围住了他们两人,在庙前的空场中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两位牧师便想趁此机会向众人讲一些教义。他们先向一个站在旁边的中国人询问:他是否真正相信这些异端的举动。那个中国人立刻回答说:他并不相信,他所信的只是吃饭罢了。而在牧师的调查中,所得结果大抵如此。
当传教士遭遇中国民间习俗,是选择在中国庙宇前传教。可见,民间信仰祠庙是中国普通群众聚集的空间,并且是开放的,没有国家祠庙那样的排他性。
作为社会活动的开放空间,上海城市的祠庙已经不仅仅是供祭祀之用,还成为特定群体表达公共意志的理想场所。近代上海水木业因工人籍贯区别分为不同帮派,并建立相应的鲁班信仰祠庙。水木业工人通过鲁班庙来解决争端、表达行业愿望等,并且以鲁班庙为基点开展相应空间内的游行示威,而这种携带神像出游的祠庙在上海频频可见。可以说上海城市的祠庙不仅作为行业工人和特定地域人群集聚的场所,也是普通民众开展社会活动的空间。
近代上海的民间祠庙仍然保留着迎神赛会传统的信仰习俗,但是由于不同地方的移民来到这里,他们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不同的祠庙,又使得这些庙的习俗被打上了区域的烙印。其中较大的经常会举办迎神赛会,并且会有自己固定的赛会路线,所游行的神像必须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申报》记载了三次虹口下海庙的迎神赛会,以1893年为例,第一次赛会的盛况万人空巷:每年春秋两季,下海庙的赛会有举国若狂的态势。这一次赛会,各会首齐集庙中,排列仪仗,旗锣伞扇之外,还有执事旗牌敕命等,马数十匹。“继以逍遥伞十顶,臂香臂锣,笙管悠扬。更有抺粉涂脂,肩负花篮,色染朝霞,香凝晓露,扮成各种故事。踏高跷者数十人,荡湖船一艘。神像以绿呢大轿,举抬经过张家浜、土家宅、新马路,穿里虹口。”(17)《乡人赛会》,《申报》,1893年4月10日,第4版。一路观礼膜拜的人填阡满陌,出巡所过之处的铺户人家均要摆设香案。下海庙的迎神赛会路线也正是其所信仰人群的大致分布区域,而超过其庙境范围则不允许巡游。例如1882年秋季的赛会就因出巡由里虹口至外虹口,再至头坝,超过巡境而未能出巡。(18)《赛会又志》,《申报》,1882年11月12日,第3版。不难看出,开埠以后的下海庙迎神赛会已经脱离了单一、单纯的信仰仪式,而是将社会区域群体纳入其中的狂欢行为。[16]
迎神赛会经过的地方可以看出其香客的类型、分布,而这一区域也几乎成为劳动者狂欢的公共空间。1933年《勇进》杂志的第7期就刊登了一篇《下海庙礼赞》,回忆了1930年前后的下海庙是劳动者“乐的地方”:
杂耍、本地滩簧、宁波滩簧、无锡滩簧,说文书、说武旧,小热昏卖梨膏糖,露天京戏、卖武艺等游艺节目。还有应时小吃摊,南翔蒸馒首、牛肉排骨面、油豆腐细粉、鸡鸭血汤、加利牛肉汤、白糖粥、五香豆、冷面、西瓜……测字问卜、看相算命、卖药草、拔牙齿、教戏法、祝由科……
有许多的摊贩是不捐照会的,因为是靠了附近一个七八间门的矮平房,平房里面有不少泥塑木雕的大小老爷。两旁安放了肃静回避的左右四块排版,烧香客每天是二二三三来,所以香烛是一刻不停地烧着。(19)萍:《下海庙礼赞》,《勇进》1933年第7期,第155页。
可以说,此时的下海庙区域已经发展成为门类齐全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各色饮食店面,有各类消费项目,宁波滩簧、无锡滩簧……满足各地的旅沪移民的休闲需要。
民间信仰对社会空间的塑造还不仅仅表现在公共空间、迎神路线,最重要的是移民相关的商业点、活动区域都是大致围绕着祠庙。例如居住在闸北太阳庙、都天庙附近的江北移民,一般在附近的工厂上班,围绕着太阳庙形成自身的活动空间。这些在太阳庙附近工作的江北客民一般都是在小沙渡、曹家渡一带的工厂从事体力劳动。19世纪末曹家渡开办缫丝厂、面粉厂、洋纱厂、织布厂等。1937年,曹家渡地区有面坊、竹器、木器、绸布、刀剪、饭菜等行业183家商店。而小沙渡地区更是面粉工厂、纺织工厂、缫丝厂等集中分布的地方,为移民提供了谋生的地方。(20)《太阳庙》,《申报》,1946年5月7日。(21)《人力车夫跌扑身死》,《申报》,1928年3月15日,第15版。
由于太阳庙区域社会空间的形成,太阳庙渐渐从一个民间祠庙的名称转化为一个城市区域的代名词,在1928年就出现了太阳庙派出所、太阳庙火警消防站、太阳庙公交站,甚至于1935年淞沪铁路在太阳庙设立停靠站:
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自开驶沪翔区间客车以来,所有南翔、江桥、真如、中山路等处往来旅客均称便利。现该局又在太阳庙地方添设停车处,以便该处旅客上下。(22)《两路局添设太阳庙停车处》,《申报》,1935年6月21日,第11版。

图1 下海庙迎神赛会路线图
正是由于移民量众多才使得站点设立成为必要,同时也促使太阳庙城市区域的进一步形成。在1946年《申报》的一篇文章就描写了人们对该区域的印象:
太阳庙……(难民)他们往往一批一批挑了全家的财产步行到上海。……他们一到此地,不到三天,空地上就有一个新村落发见。太阳庙的兴盛,也全靠这些源源而来的难民。(23)《太阳庙》,《申报》,1946年5月7日,第8版。
民间信仰由于参与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空间分布上与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致,也正是如此,特定移民的活动空间往往被打上区域的烙印,反过来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
五、余论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以来上海城市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时尚、摩登的代表。但其实,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在近代完成了其文化特征的塑造,这当中包含了移民所带来的各地传统文化。可以说,移民文化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信仰又是移民文化的重要因子。因此,研究移民社会生活中的民间信仰对理解上海城市文化特征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民间信仰作为俗文化的一种,是民间社会生活重要的体现。移民进入城市以后,民间信仰不仅作为心灵的纽带,还成为他们在城市身份的重要标识,参与城市文化的塑造。这些大多起源于封建农村的民间信仰进入城市以后,其功能、形式、信仰人群等都发生了变化,与城市文化之间产生双向互动的作用。近代以来,上海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色发生很大的转型,这当中移民文化为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也是江南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转变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移民作为存在于上海与其籍贯地间的两栖人群,将民间信仰等文化要素带入上海的同时,也将上海先进的城市文化带回家乡。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些可称为“文化腹地”的地区与上海之间产生了文化互动,从而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目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也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对它的关注可能有利于解决城市化伴随的弊病。近代以降,上海城市分别经历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初的三次移民浪潮。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政府文化服务功能的提升,新移民与20世纪老移民进入城市时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传统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习俗仍然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老移民民间信仰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寻找出新移民实现城市社会适应的方法和路径,以文化融入带动社会融入,从而增加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