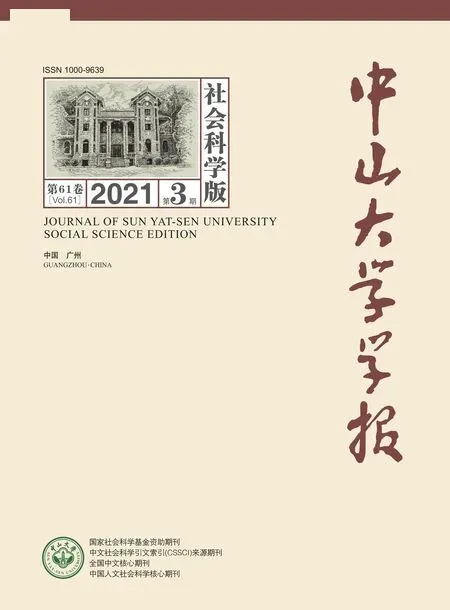从“大华语”的角度谈语言融合、语文政治化与语文教学*
2021-01-03新加坡周清海
[新加坡]周清海
1992年10月之后,我们预测中国的稳健发展,将给世界,特别是小国新加坡,带来重大的影响。作为新加坡的学术人员,我们有责任给新加坡年轻的大学生做好准备。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正式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开设了许多和现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有关的选修课程,也邀请了中国的学者来新加坡从事华语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颁发研究生奖学金给中国大学的毕业生,正式开始了和中国的学术交流①[新加坡]周清海:《我和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人生记忆》,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经过研究,我们对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的差距,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进一步思考语言交流之后可能带来的语言融合问题。在这个思考下,我和中国友人——邢福义先生、陆俭明先生、李宇明先生等人,共同提出“大华语”概念,也在李宇明先生的带领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编纂出版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并在邢福义先生的带领下,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②李宇明:《“大华语”的一面旗帜——序周清海先生〈语言选择与语文教育〉》,《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
华语的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在中国或者其他华语区学习华语的人,二三十年之后,可能在不同的华语区生活、流动,东南亚和中印半岛更是将来的发展中心。为了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现在的语言研究、语文教学,难免要考虑如何配合这个发展,如何调整我们所关注的重点等问题。这篇文章就在考虑这个发展的前提和设想下,讨论相关的三个问题:1.华人的迁移和语言的传播与融合;2.应该避免语言文字政治化;3.语文教育的调整。
一、华人的迁移和语言的传播与融合
新马的华人,16世纪就生活在新马一带。他们大多数是从中国南方省份移民到新马,很早就有华人移民和当地的土著女人通婚的少数例子。庄钦永先生收集的马六甲、新加坡的华文碑文,在汶来氏墓碑(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下解释说:“她是来自文莱的土著女人。她与其夫所生之子洪世,乃是马六甲早期的峇峇。”①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民族学研究所资料彚编12”,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年,第46页。这是庄先生收集的148个马六甲华文墓碑里最早的一个,也是现在能看到的华人与异族通婚的唯一墓碑。
从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移民东南亚的华人,大部分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他们所说的南方方言里也没有读书音的文读,只有白读。“峇峇”的语言,是白读的闽南话和马来语的混合语言。“峇峇”只是华人移民中的少数,早期都集中在马六甲,后来也移民到槟城、新加坡等地。他们保留了许多华人的习俗。
从20世纪开始,才有比较多的华人知识分子从中国向东南亚移民。他们给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带去了国文。这些移民知识分子,在东南亚用国文办学、办报,国文也就成为了东南亚华语区的书面语。东南亚的华文和中国当时的语体文是高度一致的。
华语区对中国晚清时期推翻清政府的活动,也是积极支持的,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后来国民政府推动的“国语”,华语区也是热情欢迎的。“国语”在华语区的推广,尤其是新马、印尼、菲律宾等地,是非常成功的。这些地区的华人,在教育语言上都主动地从南方方言转为“国语”。尽管大部分教师说的是带浓厚乡音的“国语”,准确度不高,而流利度却是非常高的。我中学时的华文老师,就是说着流利的海南话,而他自己以为说的是“国语”。广大华语区与中国的语言血脉相连,一直延续到现在。
1949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语区和中国失去了联系,很少交往。这一段时期,中国的现代汉语跟海外的华语也少有交流的机会,海外的整个大华语区是国语/国文的天下。这是汉语的分离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华语区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频繁,这就开始了汉语的大融合。融合的速度随着交流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目前,现代汉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华语区的词汇,这些词汇,有一大部分是“国语”词汇的回流。随着交往的频繁以及中国经济、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②2011年11月,我受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邀请,作为“世界杰出华人学者”,访问该大学。在对语言研究生演讲时,首次提出这些看法。[新加坡]周海清:《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汉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华语的现状。在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里,应该更注重各华语区之间在交流中达意的准确性,让语言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彼此的语言差异,才能减少差异,更好地为汉语的和谐融合建立基础。这是我和中国朋友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编纂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进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目的就是希望了解华语区的语言,使融合更和谐。
现在谈论华语的应用和规范问题,就必须从国际的视角观察,不能只从中国国内或华语区的需要考虑。《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为了国内规范的需要而编辑的词典,并不能规范华语区的语言应用。比如文字上将“榴梿”改作“榴莲”,新马印尼都只用“榴梿”。用“熔”替代“镕”,但在人名里,中国和华语区都仍旧用“镕”。华语区在“钻石”之外更创造了“瑄石”。有些地区,不愿意将锺/鐘都简化成“钟”,姓氏仍旧坚持用“锺”。这是华语的应用情况。
如果只从中国的立场,或者只从华语区的立场看待语言问题,就会出现许多似是而非的论断。《联合早报》2020年6月6日的言论版上《新加坡采用“华语”还是“汉语”?》一文说:
试问,如果把“峇峇”一词改为“巴巴”。我相信无人会知道这是何物。为了规范而不许用“峇”字的做法,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语文“霸权”,也使丰富的中国文字贫瘠化。
这就是彻底误解了中国的规范。中国的规范是为了全国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说“峇厘,今作巴厘”,我们不必反对,也无权反对。新马印尼喜欢用“峇厘”,就用“峇厘”好了。这和语文“霸权”毫无关系。如果我们非要中国用“峇厘”,不能用“巴厘”,那才是真正的“语文霸权”。
至于“峇峇”一词,在中国没有实用的价值,不是现代汉语里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当然可以不收的。如果为了参考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当然也可以收录。《全球华语(大)词典》就收了“峇峇”,解释说:“指14世纪中叶后,从中国移民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汉族男子跟当地马来族女子结婚所生的男性后代。他们已经不大会说华语而以讲英语或马来语为主,但仍保留华人的习俗。”《全球华语(大)词典》是站在全球华语的立场上而编纂的①[新加坡]周清海:《全球华语与全球华语大词典》,《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第58页。。
语言出现变异是免不了的,因此在语言的应用与推广方面,规范是必须的。尤其是“大华语”,所包含的各华语区的变异情况,更为多样,更为复杂。各华语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规范标准,很难统一,因此谈论规范,既要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尊重各华语区相对的自主性。从交流的需要说,华语必须保留共同的核心,才有利于华语的全球推广。各华语区,如何在交流的需要和自主之间保持平衡,是必须慎重考虑的。
为了汉语和谐融合的需要,我和陆俭明先生、李宇明先生也先后提出“大华语”概念。陆先生说:“建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的好处是,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做硬性规定,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不可,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②陆俭明:《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李宇明先生也写了《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一文③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二、应该避免语言文字政治化
我们既看到世界各地的华语有共同的核心,也看到各地华语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因此只有把握“大华语”的概念,才有助于减少语言的矛盾,让语言和谐地融合。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语言标准,去要求其他的华语区。这会造成不必要的语言矛盾。因此,我强调,华语有共同的核心,应该向普通话倾斜④[新加坡]周清海:《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这个观点,在我们的语文教学里是应该这样贯彻的:教学从严,评鉴从宽。也就是教学上尽量靠拢现代汉语,而在语言评鉴和应用上尽量从宽,容忍差异。
在汉语相互融合的现阶段,语言的差异仍旧存在,因此也常常被政治化。这是应该避免的。把语言政治化,受伤害的是下一代,将给下一代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新加坡成长的我这一代人,就曾经受过语言政治化的伤害。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时期,反殖民斗争在政治和教育上,也是反英文的,认为英文是殖民地政府的语言。新加坡华人团体发展华文教育,不重视英文学习,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有超过一半是华文教育出身的,他们的英文大体上都不好,在社会上也就失去竞争的条件。新加坡独立后,才实现双语教育。1999年,我对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①[新加坡]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序”,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又见于《务实的决策:新加坡政府华语文政策研究》“原版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
我们经过了四五十年,才化解了语言政治化的危机,更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双语社会。在新加坡学习语言(华语/英语/马来西亚语/淡米尔语),就可以在社会上直接应用。新加坡提供的语言应用的社会环境,是其他地区所不能企及的。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或者港澳地区,都没有办法制造应用双语的社会环境。社会应用双语,是新加坡的特色。这个特色,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台湾地区曾经将简体字称为“匪字”,有意将语言文字政治化。其他一些华语区,也有学台湾地区的,教育上只用繁体字,反对简体字。澳门地区有人强调“繁简由之”。中国大陆之外,新加坡是最早在教育上采用简体字的,马来西亚后来也跟随采用。我们政府的文告,用的是简体字,传媒也全用简体字。我们是从学生学习负担的角度考虑,认为简体字能减轻学生学习汉字的负担。新加坡建国以来,就不将语言文字政治化。
大部分的华语区,接受普通话,也接受国语和华语。交流中尽管可能偶尔出现一些达意上的小困难,但交流的障碍并不大。台湾地区有一个时期强调“河洛话”,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竟然用“河洛话”发言,用“河洛话”作学术总结,试图以“河洛话”取代国语。后来不得不放弃,因为“河洛话”只能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将语言文字政治化,可能牺牲下一代。
香港是比较特殊的地区,粤语代表了香港人的身份。粤语在香港地区的特殊地位,是这四十几年造成的。
1967年到1969年,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那时我不会粤语,香港人总亲切地问我:“你是不是上海佬?”当时,邵氏影片说的是国语,粤语影片是“广东残片”②友人邓思颖教授认为:五六十年代那些黑白粤语电影,称为“粤语长片”。因故事情节慢,追不上时代,因而谑称“粤语残片”。粤语“长”“残”读音相近。。
从对国语的认同,转变为对粤语的认同,有意突出粤语在香港人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这是语言政治化的做法。香港语言文字政治化的做法,大概发生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及之后,这是在政治上有意为之的——让香港人的语言身份和大陆不同。我希望香港的朋友,能研究这个课题。
二三十年后,华语的应用将是跨地区的,更国际化的。没有掌握好华语,香港人将面临语言交流的困难,也会失去不少的竞争优势。现在,人为地将粤语和普通话对立起来,让自己在交流中形成语言孤立,这个做法是不明智的。香港人将语言文字政治化的结果,将使下一代受到伤害。
面对华语跨地区的应用,香港如果要为将来出现的局面做好准备,语文教育就应该做一些调整。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香港人,有一半能用普通话沟通。这是好的发展。对普通话不必要的敌视,只会使自己失去竞争的条件。而令人挂心的是抱这种语言态度的大部分是年轻的香港人。
处理语言问题,应该避免政治化。我对新加坡的语言问题,说了这些话:“(新加坡)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母语(华语),我们更限制方言在娱乐和传媒里的应用,同时推行讲华语运动,使华语成为学生的生活语言。在有华语口语作为生活语言的基础上学习华文,也就容易多了。我们更从语文政策的高度,强调与维持华语共同的语言核心——向普通话倾斜。在语文教学和大众传媒方面,特别注重这个核心,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去。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互相吸收,提倡建立‘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新加坡这个只有人力资源的小国,是必要的;对于汉语的发展,汉语走向世界,我想也是必须这样做的。”①[新加坡]周清海:《语言与语言教育的战略观察》,《中国语言战略》2016年第2期“特稿”。
我强调“向普通话倾斜”,就是要让交流不会出现中断,让语言融合更和谐。在华语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将语言政治化,伤害的是下一代。华人有共同的语言,是一笔财富,一笔应该继续爱护和保留的财富。
三、语文教育的调整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需要;语言的应用,语法和词汇也有差异。如果不尊重各个区域的需要,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1949年之后,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口语。没有统一的口语,中国不可能实现今天的发展。口语的统一是中国语言规划最重要的成就。普通话能普及,靠的是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诚。中国广东人学普通话比较困难,但他们都愿意学,现在广东人说普通话也说得非常自然,非常流利。但在海外其他地区,可能做不到。
在华语区推广普通话,困难也比推广书面语大。我常常提醒在香港地区推行普通话的朋友:普及普通话比提高普通话的水准更重要。香港朋友说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也无所谓,大家听惯了,对语言有感情了,再去提高,困难就不大了。中国大陆的朋友不理解这点,香港的推普朋友也不能体味。他们在香港推广普通话就从提高开始,从标准开始,因此语言学习者所面对的困难非常大②[新加坡]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谈香港可以借鉴些什么》,《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2003年。。
内地在香港做事的朋友,如果能用不标准的粤语,说两句广东话,也能淡化语言的政治化。以前,我听到内地的朋友只会说“你好嘛?”,现在也能说“有无搞错?”“关你么嘢事?”,这也是一个进步。
新加坡从来没有一种共同语言,但建国后,各民族之间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英语,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为了新加坡的发展以及将来的需要,英文教育出身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学习华语。这是多大的付出!如果他没有决心学好华语,不能用华语演讲,不能用华语与中国来访的客人交谈,我们建国初期所面对的语言政治化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建国后所推行的双语教育,也不可能这么成功③[新加坡]李光耀:《一种共同语》,《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
台湾地区说闽方言的人有多少?整个福建省说闽方言的人数远远超过台湾地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闽南人人数,也超过台湾地区,但我们都学习普通话。尽管我们不能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们说的是“华语”。东南亚的华语区并没有将说闽南话和说普通话政治化。
语言问题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智,是最不能动感情的。如果我们接受“大华语”的概念,中国的汉语教师到海外教学,不是教普通话,而是教“大华语”的北京版。如果是教“大华语”,那么教的人就不一定是从中国来的,也可以是当地的华人,也有可能是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印度人等等。
教华语的不一定是中国人,应该作为华语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去当地培养人,让这些人在当地教学,让当地的人组编教材,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外来的事务。
如果我们接受“大华语”的概念,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的时代:推广汉语/华语/中文,责任不全在中国。中国一定要和华语区充分协作,不能把华语当作对外汉语,只考虑向外派人。在“大华语”的观念下,应该鼓励华语区参与华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充分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性。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有不少华语人才,如果马来西亚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或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以后由中国派到泰国去教汉语,恐怕比中国的教师更加了解泰国。
华语文课程与教材,也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今天“一带一路”提倡往外走,那么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往外派出的年轻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有所了解。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很多写得不错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中国或其他华语区的语文教材,或者作为儿童读物,都能让中国的年轻一代了解华语区,也能促进华语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应该通过语文教育,引导中国或华语区的年轻人走出去,愿意走出去。中国现在的语文教材,都只注重自己国内的历史、文化、文学等等,这不能配合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
语文教材容纳华语区的作品,对华语区的写作人,也是极大的鼓励。我们可以通过教材或读物,通过语文的学习,重建中国和华语区年轻华人的人际联系,让他们了解不同的华语区。文化上的认同,也应该充分体现在华语文的教材里,体现在教学中。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机构,有计划地收集与出版华语区的优秀教材、分级读物,并为华语区编写语文词典。汉语教材都在中国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应该在当地领导、组织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港珠澳大湾区的发展,更应该将这个纳入发展的范围之一。香港地区的出版业在华语区,有很好的基础,今后在这方面也应该能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