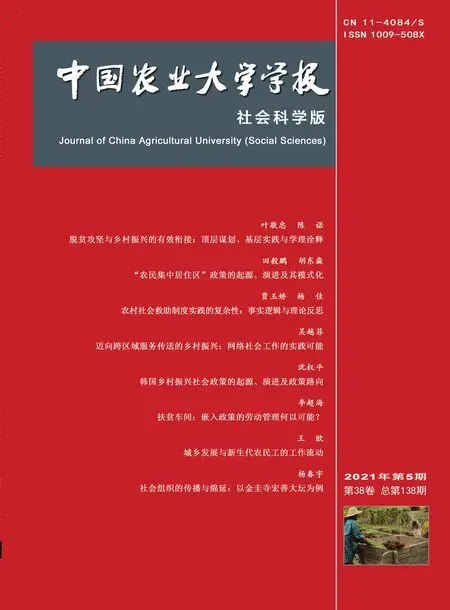“低端全球化”:世界多元文化互动图景的想象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2021-01-02张梅梅
张梅梅 马 妍
重庆大厦作为香港地标式建筑之一,是世界各地人们彼此交流的多元文化区域,给予人们无限的都市想象。十年前父亲前往香港出差,回来之时给笔者带了不少新鲜玩意儿:印有各种文字的糖果、零食,以及在内地商店从未见过的手表款式、裙子等。父亲口中的香港高耸的楼房拔地而起,交通便利,是繁花似锦的魅力都市。通过父亲的讲述,笔者充满着对香港的想象。然而,他也讲到了与同事前往重庆大厦的经历。父亲因听说重庆大厦里货物齐全且较为廉价,决定为亲朋好友带点礼物,可走到门口却犹豫了,因为门外是有别于亚洲面色的一群人,用父亲的话来说感觉有些人贼溜溜地盯着你,你下意识地想要摸摸背包是否还在肩上,于是他和同事决定止步。第二天他们找来导游一同前往,导游带着他们穿过熙熙攘攘的各种人群,这些人服饰、气味、语言都不一样。导游警告他们说,不要随意自己一个人前往此处,因为这里不安全。受此影响,父亲形成了对重庆大厦的初印象:危险、吸毒、混乱、挤满非黄皮肤的人群。但是,在他心中重庆大厦依旧是时尚的国际化之地。重庆大厦究竟呈现了怎样的人文景观,重庆大厦内部形成的文化如何向外部延伸,而外界的文化又如何在重庆大厦内部得到“再生产”“再适应”,这些是麦高登教授在《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以下简称《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中探讨的内容。
2011年《香港重庆大厦》英文版问世,麦高登以重庆大厦为田野点,以大厦内流动的人口为研究对象,论述了重庆大厦在香港的特殊地位。尽管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商业区的黄金地段,属于香港地标性建筑之一,但香港人却对此地怀着一种不认同的态度,并不愿意进入此地并与之有过多接触。麦高登出版此书前这种心理芥蒂是较为普遍的,许多香港人害怕走进大厦,因为关于重庆大厦的传言大多是负面的,人们认为此地是滋生罪恶的温床。但麦高登教授通过三年的田野走访,认识到了重庆大厦的特殊文化,五座拔地而起的17层大厦是全球文化交汇的中心,多元文化在大厦内部不断被认识和理解。通过2006—2009年的田野经历,麦高登教授用人类学方法记录并分析了重庆大厦不为外界所知的一面,在全球化来袭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由于资金、交易手段等因素的差异,迎来了“低端全球化”的共享时代。
本书最大的优势便是如同纪录片一般带领读者走进重庆大厦,穿越空间限制,行走在重庆大厦这片楼宇森林内。麦高登教授的《香港重庆大厦》主要在回答其心中潜藏的如下问题: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人们如何互动?不同的文化如何交流?“低端全球化”如何运作,它究竟指的是什么?重庆大厦的脉络缘起为何,及其在未来将面临哪些挑战?等等。笔者认为此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和提升,更是因为使用了翔实的资料作为打开香港重庆大厦的金钥匙,让在外面驻足观望、满怀疑虑的人们更为客观或怀有人文关怀地去看待一个文化现象,这正是人类学者研究的核心目标所在。
一、文化践行者——对文化的多维度探析
麦高登(Gordon Mathews)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1993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文化与认同、文化与全球化、人类学理论、语言、象征与社会等。其著作GhettoattheCenteroftheWorld:ChungkingMansions,HongKong于2011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便掀起一阵重新认识香港这一国际化都市的浪潮,重庆大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2014年杨旸将之翻译为《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引发了更多中国人的思考。重庆大厦的存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看似破旧不堪的重庆大厦为何迟迟未被拆除,大厦内部人群如何建立起相互联系等问题的答案是人们迫切想要知晓的,这些问题在此之前也是困扰麦高登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随着香港重庆大厦被重新定义,人们渐渐放下顾虑去探索在香港土地上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楼,年轻人开始走向大厦内部与不同国族的人群交流。麦高登对香港重庆大厦的深入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区。2014年6月此书获得香港图书奖,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在《香港重庆大厦》未出版前,麦高登已对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各族群间的互动、多元性等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通过多点田野的比较,思考文化间的互构,以及全球化如何形塑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主体的特殊结构。麦高登的著作试图阐释全球化进程中多族群内部的差异性和逐渐增加的相互重叠的时空秩序,各民族的文化以内部差异相互渗透的方式呈现出矛盾性、分离性和平衡性。麦高登对香港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的深入解读源于他早期在香港开辟的田野阵地。1983年,他作为游客进入香港重庆大厦,1994年在香港定居后,出于人类学者的学术敏锐,他将香港作为重要的田野点去进行记录、观察和分析。2002年他与刘泰隆(Tai-lok Lui)编撰的《香港的消费》(ConsumingHongKong)讨论了香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将香港文化置于当代理论话语中,着重探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体制改革、新兴文化与全球化扩大进程中的联系等等[1]。此外,麦高登、马凯克(Eric Kit-wai Ma)和刘泰隆开始尝试从香港的历史层面和文化互动层面去探析全球化与本土化如何衔接的议题[2]。 麦高登对香港文化的深入调研让缩于一角的重庆大厦被重视和重新解读,2006年麦高登正式开启了对大厦内部的人类学研究并于2011年出版《香港重庆大厦》一书。
除香港外,日本、美国,内地的广州诸城市也是麦高登的主要田野点,从麦高登的学术轨迹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去回顾,他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个案调查,带有极强故事性的叙事和自身如何开展研究的展示使麦高登的文化思考更具可读性。麦高登的跨文化比较实则是在回应全球文化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麦高登的早期著作意在阐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因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往彼此出现“文化联结与边界”(cultural bonds and boundaries)的现象。麦高登的研究是对文化多维度的再思考,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理解。例如,1996年出版的《何为人生之意义:日本与美国对自身世界的理解》(WhatMakesLifeWorthLiving?HowJapaneseandAmericansMakeSenseofTheirWorlds)于2001年由日本学者宫泽洋子(Yoko Miyakawa)翻译成日语出版。在此书中,麦高登通过研究美国和日本9对处境相似的个体来考虑生命的意义这个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探索来自日本、美国两种文化体系下的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生命意义的过程。他阐明了工作和爱情、宗教、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等是其重要的因素,以广泛而有趣的观点拓展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再思考。麦高登用日文术语ikigai——“最能让人觉得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that which most makes one’s life seem worth living)来探讨这些话题。尽管美式英语没有对应的词,但ikigai不仅适用于日本人的生活,也适用于美国人的生活,ikigai是每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本质的生活目标。麦高登通过采访这些人的生活故事,分析了全球文化互动中现代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如何受到社会角色和文化词汇的影响。他以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以理解他们的生活为出发点,为我们对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新理解[3]。
全球化的到来使接受新文化的个体与传统社会秩序间出现剥离和嵌入式的调节,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问题一触即发。2004年麦高登与布鲁斯·怀特(Bruce White)编撰的《日本新一代:年轻人是否创造一个新社会》(Japan’sChangingGenerations:AreYoungPeopleCreatingaNewSociety?)以日本年轻一代为研究对象,探讨日本存在的代际关系,其中“代沟”问题尤为突出,年青一代在进入成年社会、学会遵守成人社会秩序之前会出现一种对传统社会的抵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日本战后的情况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观念。报告中得出的潜在预言认为,虽然日本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对社会与政治进行公然反抗,但是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日本社会秩序感到不满,并进行了相应的抵抗。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就业、养育的方式等内容的不同可能导致未来日本与当代日本有很大的差异[4]。而这种变化与文化全球化存在相互的影响。
麦高登的文化思考中贯穿了全球化、文化多样性、都市族群文化互动等社会焦点。以全球化为背景,他提出了“全球文化超市”的概念。纵观21世纪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和讨论主要集中于归属和身份问题上,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正在消除差异,出现同质化,传统的身份类别已无意义或过时。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王爱华(Aihwa Ong)、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其他学者已在此种背景下研究了文化身份形成和展演的论题。麦高登于此时也加入了这个新兴的学术体系,通过考察日本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宗教人士三个不同国家群体去讨论核心概念——“全球文化超市”。在2000年出版的《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GlobalCulture/IndividualIdentity:SearchingforHomeintheCulturalSupermarket)一书中,麦高登以一种清晰而生动的风格打开了全球化、文化和身份等复杂的话题。“文化超市”(cultural supermarket)是他以全球化为背景去探讨的文化现象,文化超市被看作与自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个人有自由去选择超市中的东西从而形塑自己的人生。麦高登借讨论的议题发出疑问: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许多生活在富裕社会的人从全球文化超市中选择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食物、艺术还是精神信仰层面都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根源只是消费者的又一种选择,我们还能声称拥有一种基本的文化身份吗?[5]麦高登的疑问是对多元社会文化的一种理性反思,全球化促发多种文化碰撞的同时,身处社会中的人们其身份已不再单一,族群以“理性选择”去构建身份以适应文化的渐变。马里奥·马斯沙(Mário Mascherpe)在2002年将此书翻译为巴西葡萄牙语,伊娃·克莱克特(Ewa Klekot)于 2005年将其翻译到波兰,由此可见麦高登对另类全球化思考的视角在学术界产生的重要影响。
2012年麦高登与古丝塔瓦·林·瑞伯奥(Gustavo Lins Ribeiro) 、卡洛斯·艾博·维伽(Carlos Alba Vega)合编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世界的其他经济体》(GlobalizationFromBelow:TheWorld’sOtherEconomy)[6],这里的“自下而上”便是2011年提出“低端全球化”概念的理论提升。与以往“全球化”一词相比,“低端全球化”不再是跨国公司和精通互联网技术的上层技术人员或精英层的专用术语,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亦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低成本对各类生产要素实行重组,在适当的区域内进行经济活动,将“低资本投入”与所形成的“非正式经济”转化为一种区位优势,利用多元跨国参与者形成的社会网络帮助群体积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2017年麦高登与他的两位学生林丹、杨玚合著TheWorldinGuangzhou:AfricansandOtherForeignersinSouthChina’sGlobalMarketplace,201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译为《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麦高登2010—2014年间多次进入田野以广州为例呈现了又一新兴起的“低端全球化”中心城市,作者重新思考了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外国人群的生活状况,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将全球化与都市多元族群两个学术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去讨论[7]。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全球化,全球各地都有“低端全球化”的身影,如中国的非洲商人、加尔各答的街头小贩、墨西哥倒卖盗版CD的贩卖者等都是“低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不可否认,世界上大多数人实际上每天都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改变,跨国小贩行走在法律边缘,伴随风险和发财致富的美梦来到某处将产品带回自己国家销售,并与消费者建立并不稳定的互惠性经济往来。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剖析源自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关注,不断探寻文化实践者如何理解自我,定义所形成的文化事实。自1996年相继发表关于“追寻生活的意义”的文章后,麦高登从人际互动中看到了文化在塑造人们身份的同时也在解构强加于其身上的文化意义之网,例如《在香港寻求庇护的他者:生活的悖论》(AsylumSeekersinHongKong:TheParadoxesofLivesLivedonHold)[8]都是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怀着尊重之心客观细致地认识调研对象,走进看上去不被当地文化所认同的、被污名化的世界,这是人类学者基本的道德训练——尊重文化,尊重个体。
二、“低端全球化”的产生
麦高登在《香港重庆大厦》中从“地点”“人群”“商品”“法律”和“未来”五大方面解读大厦内“低端全球化”的产生,这也可以看作全书的主线。重庆大厦的文化交汇无不与其地点的特殊性、人群的复杂性、商品的流通性、法律监管的强制性与开放性以及大厦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关。“低端全球化”不是只发生于香港重庆大厦内,世界各个角落都在演绎着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共享全球化成果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实践内容。“低端全球化”并非独具创新的新概念,阿帕杜莱此前提出的“草根全球化”与之相应。阿帕杜莱认为,社会公共舆论中,小商贩、农民、商人、城市居民给人一种其被排斥在世界贸易圈之外的刻板印象,全球化的言论被不断分散成知识群体所掌握的话语,成为国际与国家间的交流内容,在社会形式的发展趋势下,一种依赖于代表穷人利益的全球化战略、愿景被称为“草根全球化”[9]。“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草根全球化”以及“低端全球化”运行的最大特点便是非政府组织,通过部分运动、部分网络、部分组织的新生社会形式从底层推进,向外部波及,开展全球化。总体来看,促使重庆大厦产生“低端全球化”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的特殊
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提供了分析全球化的又一研究范式。在了解“低端全球化”产生之前有必要对香港重庆大厦的历史脉络作简要梳理,因为重庆大厦的“低端全球化”与之密切相关,历史变迁使得昔日的重庆大厦由高档、繁华、象征身份的楼宇变为廉价商铺、旅店的集中地。
重庆大厦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油尖旺区尖沙咀弥敦道,1961年建成。如今大厦的风格尽管因修葺有所改变,但也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最常见的建筑风格。2005年业主立案法团对大厦进行了整改,使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内部结构并未有大的调整。正如麦高登在书中所指出的:“然而无论重庆大厦再怎么翻天覆地改造,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其他香港购物商城一样的建筑,只能继续保持其特有的国际化风格,包括它的破旧外貌”[10]43。重庆大厦在最初建成时是一栋高档建筑,19世纪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政府雇佣印度人为警员和士兵,大厦内开始有大量的南亚居民入住其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爆发对重庆大厦造成一定影响,火灾成为大厦的巨大安全隐患。也许出于安全考虑,20世纪70年代重庆大厦内常住的香港华裔家庭将物业权转交给新移民,自己搬离重庆大厦,大厦从私人住宅区日渐变成旅店,逐渐成为背包客和嬉皮士的圣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厦内除往来大量的南亚人外,非洲人作为新移民群体也开始出现于大厦内,这与1984年重庆大厦附近的九龙清真寺重建有关,到2000年大多数进入大厦的人群来自非洲。在贸易往来、寻求避难、旅行等日常活动的作用下,重庆大厦成为全球化的交汇处,成为特定全球化形式——“低端全球化”的载体,麦高登将之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10]19。重庆大厦与亚非地区构成的网络体系使得全球化的成果能被共享,历史的变迁中重庆大厦内“低端全球化”开始萌芽。
(二)族群的多元
如果说历史是孕育重庆大厦产生“低端全球化”的温床,那么大厦内流动的人口便是烧暖这张床的实践者。怀揣致富梦来此进行贸易的南亚、非洲商人,想要淘金变为人上人的临时工,寻求庇护的国际避难者,处于灰色地带的性工作者、瘾君子,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家庭佣工,探求刺激、寻觅廉价住宿或进行心灵之旅的游客构成大厦内的主要人群。群体依据自身职业的特性实行跨越族群式的互动,比如非洲人在重庆大厦内很难找到胃口相符的菜肴,只能在南亚小食摊位前踱步,反复询问店主是否是清真食品,以期找到能食用的菜肴;再如非洲批发商与南亚店主交易时,要懂得一些互动规则,在卖家面前尽量表现自我,以避免钱财损失。互动中的交流不可避免,大厦内汇聚着各种语言,但通用的却是英语,不会英语的人们在此地很难进行贸易。大厦内部的互动还来自雇佣关系,这体现了族群互动关系的灵活性,族群间的交流有长期与短期之分:短期关系包括店主低薪聘请避难者及与持旅行签证之人签约所形成的雇佣关系,或者性工作者与需要性服务的群体之间形成的买卖交易关系;而长期的族群交流包括商人与顾客、商人与店铺经理之间建立的以信任为纽带的长期合作关系。不同群体交流时氛围不同,有时是紧张的竞争关系,有时是亲密的伙伴关系。例如,华裔店铺的旁边有家巴基斯坦手机店,两者在贸易上可能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但如果一方遇到急事儿时,另一方会伸出友谊之手。群体间交流的灵活性还在于,有时此种交流会转化成恋爱关系。纵观之,多族群的互动促成了文化的多元,重庆大厦内尽管人际互动中存在矛盾冲突,有时表现得并非十分友善融洽,但也不至于发展成仇视敌对的状况。透过麦高登的著作可以看到穷人和富人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阶级冲突,促使“低端全球化”由发展中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流动。典型的案例是撒哈拉南部20%的非洲人使用重庆大厦销售的手机。“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穷人(在香港的穷人并非所属国的穷人,在所属国他们往往是中产阶层或上层社会的“精英”)铤而走险利用集装箱或行李箱运送货物,背井离乡跨越大半个地球来此寻找经济机会。对他们而言,最大的诱惑来自金钱,他们期望有一天赚够钱回到自己的家乡,实现个人理想,他们尽可能逃避法律对其的制裁和干涉,这是“低端全球化”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原因。
(三)商品的流通
重庆大厦的历史、群体互动是“低端全球化”的开端,历史搭建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展演舞台,群体互动使展演的舞台不至于缺少表演者,在参与者之间建立相互衔接的关系,而表演中最重要的道具就是商品。大厦中的商品成为建立群体互动关系的关键,如果没有商品存在,大厦便不复存在,也就不能形成“低端全球化”的交汇中心。“低端全球化”不同于全球化,不是通过大型跨国企业进行激进式的席卷和渗透,而是个体商人之间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经商活动。“低端全球化”的特点与人、商品、法律三者密切相关:(1)交易比较随意,有时是灰色交易,有时甚至游走在违反法律的边界上;(2)涉及法律的盲区,承担高风险;(3)现金交易,不需要信用卡、信誉卡等凭证;(4)通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其实遍布全球,如巴黎的刚果商人、纽约街头的非洲小贩等;(5)交易时以相互之间的信任而非合同为基础。由此来看,流动中的商品为“低端全球化”市场供应所需的货物,建立消费与被消费的供需关系,重庆大厦内商品的流动方向便是“低端全球化”延伸的路径。
(四)法律的监管
商贩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处,法律的实施和香港政策的改变,必然影响“低端全球化”的走向。重庆大厦内最常见的商品是手机,仿冒品、无牌手机、二手手机等贸易商品违背了法律体系准则,商人在逾越这道法网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不管是在过海关时被全部没收非法携带的货物,还是通过贿赂海关人员以减少没收商品带来的损失,都不可避免利益损失风险,甚至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重庆大厦成为香港中心位置的“内飞地”,贸易往来不断,“低端全球化”无时无刻不在上映。灰色贸易为何能在法制社会中流动?麦高登通过大厦内群体与警方的日常互动行为展开了法律论述。首先,重庆大厦的生意大多不受警方干涉,发生刑事案件后警察才会介入。持旅游签证的临时工、避难者、性工作者会在雇佣者那里得到相应的庇护,警察一旦突然搜查,大厦内会相互传递信息,使那些打工者逃离,雇主在向警察叙述时表示完全不知情或说是远房亲戚。面对“危机”大厦内部暂时形成一个“共同体”,以抵制外来的试图破坏平衡关系的警方。其次,香港的签证与居留权决定着“低端全球化”往来的贸易类型,不同国籍背景使他们持有的签证日期长短不同。比如,安圭拉、阿根廷、澳大利亚、伯利兹等国家的人可以在港90天,巴林、玻利维亚等国家的人可以在港30天,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人在港时间不得超过14天。签证时间的长短关乎金钱的多寡,是商贩、临时工、性工作者等人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些人想要长期留在香港的办法就是与永居香港的居民结婚,但能达成愿望的寥寥无几。外来者利用法律空缺往返于大厦内外,怀揣经济致富美梦,但终将面临各种生存挑战。
法律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使重庆大厦内生存的群体游走在法律边缘,为了生存的目标既尊重法律又藐视法律,避难者便是这对矛盾体承担者的代表。他们是重庆大厦内为数较多的一部分群体,由于在政治、宗教或种族上遭到迫害而被迫逃离故土,在到达新的地方后想要开启新生活,但他们的处境不容乐观,是一个困难且无助的群体。避难者之所以也是“低端全球化”中的一分子,是由于香港政策规定不允许任何避难者在香港拥有永久居留权,除非他们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并通过繁杂的面试。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消磨着他们的耐心,总期盼提出的申请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同意,可获得资格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虽然避难者的生活举步维艰,但是香港开放的边境政策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因为根据香港法律,寻求庇护的避难者一旦出国便不需要再次回国办理更新签证手续。沿着麦高登给出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避难者的记录实则是对香港法律政策进一步促成“低端全球化”的分析。
历史演进、群体互动、商品流动、法律政策的修改都在促使“低端全球化”在香港重庆大厦产生,这座大厦的存在引发了全球化的衍生,而“低端全球化”正在契机中寻找蔓延的路径以向更广阔的区域延伸。
三、“低端全球化”的文化思考
伴随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族群间形成新型的聚合与区隔空间,为中国带来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除香港重庆大厦外,广州小北社区、三元里社区,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国际社区,山东青岛城阳区等地都聚合了不同族群,他们操持不同的语言,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都市中主动聚集又主动区隔,“跨国移民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11]在各大城市中涌现,不再仅仅依靠传统主流力量——国家政府、跨国公司推动和控制,而是出现迈克尔·莱恩斯(Michal Lyons)所谓的“第三层全球化”(the “third tier” of globalization)[12]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力量。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现象,研究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并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族群聚居区,如戴春对上海国际化社区社会融入进行了研究[13];李志刚等[14-15]、莱恩斯等[16]、麦高登等[17]对广州“巧克力城”展开研究,分析了黑人聚居区形成的社会空间,认为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聚居在本质上是一种草根现象或基层现象(grassroots phenomenon)。这种草根现象创建了一个小额资本的全球平台,贸易商透过自我的胆识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技巧策略有效推动了贸易的发生和增长。
中国最为典型的“低端全球化”之地是浙江义乌,它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以来,义乌便成为国际性商贸市场,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在面积约为1 105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形成了一个商贸场域,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于此进行着跨国贸易。义乌市对2016年全年涉外人员的统计数据显示,此地境外人员达到15 000人(1)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6全年涉外数据统计信息。,不同国籍的人在所属国与义乌之间往返,形成“候鸟型”迁移。“低端全球化”的案例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了交汇口。全球化的市场不再是强调网络技术和优化资源配置、被富人统一控制的单一市场,第三世界的人们也有权参与其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费孝通先生1986年分析温州模式时提出“小商品、大市场”的概念,指出温州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是提供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使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费老预测性地呈现了“小”和“大”的关系,通过分享在德国柏林的所见诠释草根力量正在流动与崛起:有人敲开房门,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站在门外准备兜售,打开手提箱是日用小百货。费老所见的场景并非碰巧,在巴黎、柏林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依靠送货上门和优良的服务态度赚钱[18]。在欧洲的温州青田人与在广州的非洲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一样,自发在国外寻求贸易契机,利用低投入在半合法或非法的情形下形成跨国流动。
麦高登之前人类学界并未对“低端全球化”的概念给予重视,他的案例呈现了一个多族群的文化聚合之所,同时指出了“低端全球化”图景的主要特征。“低端全球化”的实践过程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或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中,在交易方式上有别于通过网络技术或跨国银行的协作,商品的流动以及人员的流动遵循一定方向,他们游走于不同文化和空间,在汇聚的空间中呈现多元的文化景致,即麦高登所谓的“全球文化超市”。他们在互动中构建了自己的身份,建立起单一或多重“文化身份”,个人依据不同的情景塑造并改变自己文化身份构成生存性策略。
全球化是较为复杂的运转过程,“低端全球化”是都市高度流动性的体现[19]。麦高登的研究是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重点,一个社区是一个微观型社会,在所处的都市中,人们对眼前的事物习以为常,对真实的状况却极为陌生,都市里熟悉的陌生人会时刻提醒我们“我者”与“他者”的差异性和趋同性,在穿越城市一角到另一端去探究问题真相时,会发现脑海中熟知的小区域别有洞天。“草根全球化”或“低端全球化”是有关空间的想象和实践,囊括了物理空间和文化的社会性空间,自下而上的策略性选择使霍米·巴巴(Homi F. Bhabha)、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所谈论的“第三空间”成为可能,在流动的、开放的界域中形成极大的包容和社会性关系,第三空间是物质与精神的超越,不同于固化的交往,第三空间具有嬗变性,使交流的边界更为宽泛[20]。全球化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全球的不平等分配。伴随着跨国的资金流动,自下而上的力量使边缘或半边缘群体逐级向中心流动。“低端全球化”过程中群体在实践中产生的新型空间是第三空间的一种显现,参与者成为跨越空间实践的主体,他们通过策略性的互动、协商,共享汇集地带来的多元文化,在聚合的内部空间遵循一定的秩序和协作机制。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织语境下,被一些学者狭隘地称为边缘族群的人们并不是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或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尽管轨道的修成并非由国家、地方政府的上层力量主导,而是族群内部自行解决,但路的修成是具有动机性的,是族群成员共享的成果。
都市中的人们不再深扎于固定和停滞的空间上,不再以血缘为聚集条件,而是多种复杂条件的聚合。不同族群相聚形成混杂的聚居区,文化在内部繁衍为多种新型文化元素。都市中的成员组成开放且多元的整体,外籍商人、临时工、保姆等各种职业的各国人口汇集于都市各个角落,拥有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不经意间所形成的场域下进行场景式互动,此场域浓缩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对地方的想象促使人口快速流动。
麦高登的研究为都市民族志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使学者重新反思在开放的环境下,文化在共享的同时更需要彼此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多元的潮流打破了理解、观察文化的单一视角,强调了文化群体的不可分割性。香港重庆大厦内部多族群构成的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的文化结构,拥有美国文化印记的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文化现象的研究是一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他反思了不同文化在价值上的平等,在竞争与共生的社会内部,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积极寻求生存空间,参与到全球化的联动体系中,他们的生存策略尽管不值得大力推崇,但他们为生活而奔波的精神却值得敬佩。麦高登的都市民族志研究中弱化了某些生存空间的隔离性和封闭性特质,对内部空间文化的研究是“基于对空间过程和人们生活方式理解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21]50。此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精英文化和社会主流势力的趋向,忽视社会结构的下层力量。但在高强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草根性声音和观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低端全球化”或“草根全球化”不是为了划分文化中心或文化边缘。在《香港重庆大厦》中作者用“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来定义香港重庆大厦,但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麦高登的都市民族志也在提醒每位研究者,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概念,“低端全球化”中的群体利用低投入和半合法化或非法的方式进行跨国流动,他们的身份也同样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切换。在异国他乡拥有较少资金的他们在相对固定的社区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回归所属国后倒手变卖物品使他们拥有了一定资金基础,成为跨国贸易的中间商,他们的位置又从边缘回归到中心。相较于全球化时代中的高端交易,“低端全球化”拥有自己的市场和自主的选择性。
在研究中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内容,例如各族群间如何互动,如何展开适应性策略?跨国贸易间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如何重构?跨国背景下如何实现文化认同?“低端全球化”是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式,这种形式突破了大型跨国贸易公司的壁垒,也突破了越来越两级分化的世界,将散落在边缘的、参与感较弱的穷人拉进了共享的社会机制中。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时空的延伸,通过现场的卷入与跨距离互动相关联,全球化的运作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可以以一种方式将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22]56-57。但吉登斯在论述中依旧是以发达国家为基点,讨论自上而下的力量,未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全球化转向纳入考究范围。世界越来越形成一个整体,人们趋于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通过空间流动实现了重新组合排列,同时也催生了对“多元化”的调适。“低端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补充是世界体系的内在构成。未来的重庆大厦可能会被拆除,未来的义乌市场可能发展成高端市场,未来的三元里社区、小北社区可能由于签证、户籍制度的强化使一部分人无法进行自由的跨国贸易,但“低端全球化”从来不会缺场,在下一个角落会重新出现一个重庆大厦、义乌市场、三里元社区,出现一个南中国的世界城。
四、结束语
回归本书,“低端全球化”发生在香港重庆大厦而不是其他繁华场域,足以说明重庆大厦的特殊性。全球化迈进世界各地时,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对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草根全球化”和“低端全球化”缺乏关注。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群被忽视,其尴尬的身份无法在香港得到认同,尽管有些人家在此地已经延续了几代,但依旧无法被当地人认同。然而,在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中,我们预测性地认为,香港当地人会逐渐接受外来族群,至少现在的重庆大厦不再是提之色变的“黑色心脏”。重庆大厦孕育出的世界主义氛围使人们在道德上变得宽容,来自敌对国的双方能够超越国家强加于其身上的身份、超越国家和种族矛盾带来的冲突建立友谊,民族主义强烈的人们在重庆大厦得到了“改造”,因为重庆大厦相处的第一条准则便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麦高登对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使读者理解了“低端全球化”的概念,用民族志的个案展现了全球化的多重维度。重庆大厦成为中国全球化的中枢地区,商人通过低成本的资金投入购买相对核心和发达国家的二手或仿冒伪劣商品,来往的贸易通过面对面的人际沟通进行,投资资本相较全球化资金来说数额较少,现金是常用的支付方式。在当今社会经济局势下,重庆大厦的脆弱性已经表现出来,其未来的发展已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可能会继续存在,但终究有一天会被拆除。这可能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签证问题的限制,以往非洲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重庆大厦,现在由于香港签证的限制和烦琐,非洲商人不断涌入中国内地,导致重庆大厦客源骤减;其次,寻求避难的人可能因为免签入境政策的改变而无法进入香港;最后,重庆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提议如果奏效,大厦将会被重新规制,高额的店铺租用费可能迫使店铺迁离。香港重庆大厦作为多元文化交汇中心,尽管可能由于多方面原因不复存在,但是“低端全球化”的现象却不会缺席,其依旧是未来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
在《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中,作者以贸易网络铺开社会网络,呈现空间和时间以及“他者”的关系,反思中心—边缘的概念,以及第三世界的人们如何利用自我的能动性主动参与到全球化之中。人们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也成为作者的研究对象,聚焦于那些为生活而远走他乡的普通人如何越过边界尽可能规避法律实现自己的淘金梦。“低端全球化”关注的是一种开放的边界、草根的声音,对思考如今的农民工问题、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海外华商、海外移民潮、留学潮等问题都有启发。与此同时,“低端全球化”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影响,如何规避和正确引导这一流通渠道使其合法化、公开化、社会化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仅仅依靠群体的信任机制和道德约束来维系“低端全球化”的运行是远远不够的,其需要更细分的法律作为后盾,涉外机关需进一步维护参与者的权利和权益,增强友好合作的社会风气,健全市场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将有助于思考“低端全球化”的未来动向,理解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