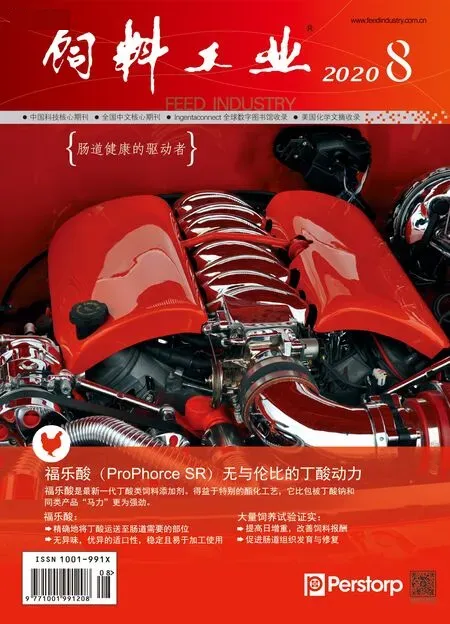后抗生素时代仔猪肠道健康维持和营养干预
2020-12-29穆钊坤林华林周加义王修启
穆钊坤 林华林 周加义 王修启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动物营养调控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642)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养猪大国,猪肉产量超过全球的1/2。然而我国养猪业的生产效率只有欧美发达国家的60%~70%[1]。农村农业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PSY)约为17 头,个别规模化养猪企业为23~24 头,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生猪养殖中仔猪腹泻率高达50%~60%,死亡率为15%~20%[2]。为防控仔猪腹泻,我国养猪生产中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滥用加速了耐药菌株的产生,造成了猪肉中抗生素的严重残留,引起了生态环境的污染[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18 年13 号文件—《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1 年)》明确表示药物饲料添加剂将在2020年全部退出。
后抗生素时代,养猪业面临无抗可用的境地,如何解决仔猪健康问题成为研究者和畜牧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除继续加强和规范仔猪管理外,营养与健康的关系又被重新审视和评估。研究表明,益生菌、抗菌肽以及某些功能性氨基酸等均具有缓解仔猪腹泻或促进仔猪生长的作用[4-7]。本文总结了仔猪腹泻诱因及其营养调控的研究进展,为防治仔猪腹泻和建立抗病促生长营养调控技术提供参考。
1 仔猪腹泻
腹泻是造成仔猪生长发育受阻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一般包括营养性腹泻和病理性腹泻,后者又分为病毒性腹泻、细菌性腹泻和饲料源霉菌毒素性腹泻。虽然腹泻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但它的本质都是肠道离子通道的改变引起水和电解质吸收和分泌功能的紊乱,且均会导致肠道结构和功能受损以及微生态失调[8]。因此,保障肠道健康是提高仔猪存活率的关键。
1.1 病毒性腹泻
引起仔猪病毒性腹泻的主要病毒有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PEDV)和猪轮状病毒(Porcine Rotarvirus,PoRV),它们都会引起仔猪渗透性腹泻,导致小肠肠壁变薄,肠绒毛萎缩[9]。PEDV 感染肠道的主要靶点是小肠上皮细胞[10],通过直接膜融合将PEDV 内化到细胞中诱导细胞溶解性急性坏死。李任峰等[11]观察到,在PEDV 侵袭的仔猪回肠绒毛M 细胞(Microfold cell)中存在PEDV 颗粒,而M 细胞是黏膜免疫系统中抗原进入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主要“门户”,它的死亡会导致高效的肠黏膜免疫应答能力显著降低,在十二指肠和空肠绒毛则没有观察到此现象,这可能提示回肠是PEDV 的主要作用部位。Li 等[12]同样发现,PEDV 感染会引起10 日龄仔猪严重的萎缩性回肠炎。然而,来源于仔猪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的隐窝干细胞扩增而成的类肠团均易受PEDV 感染,且包括肠道干细胞、吸收细胞和杯状细胞在内的多种类型细胞都为阳性。目前并没有文献对体内外PEDV 感染试验呈现出的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虽然类肠团模型可一定程度上模拟体内研究,但是肠道结构和功能毕竟要复杂得多,再加上肠腔中数以十万亿计的微生物与肠细胞的共生互作,因此离体水平可能无法产生与体内水平PEDV 感染一致的生物信息。此外,在PEDV 感染的早期,肠细胞干扰素(IFN)的含量显著减少,表明PEDV 具有调节宿主先天性免疫应答的能力[13];PoRV 能够有效感染肠上皮细胞,在黏附于小肠上皮细胞后产生肠毒素,可特异性诱发细胞内Ca2+升高和Cl-分泌,导致腹泻[14]。Zou等[15]发现,低活力的PoRV 可感染并损伤终末分化成熟的肠细胞,破坏宿主分泌途径,导致刷状边界酶定位错误,肠道吸收功能障碍,细胞通透性增加,进而诱导肠细胞死亡。但是在PoRV 感染期间,活跃型和储备型肠道干细胞群都得以保留。这些肠道干细胞,尤其是隐窝基底部的Lgr5+(Leucinerichrepeat-containing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5)干细胞的增殖、迁移和分化会促进肠上皮再生,且此过程依赖于Wnt 信号的参与。
1.2 细菌性腹泻
仔猪细菌性腹泻病原主要包括大肠杆菌和致病性沙门氏菌等。大肠杆菌大致可分为致病性大肠杆菌(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EPEC)、产肠毒素大肠杆菌(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ETEC)。EPEC 毒力基因主要位于肠细胞脱落位点致病岛(毒力相关的DNA 序列)上,可编码III 型分泌系统(Type IIISecretion System,T3SS)、转运紧密黏附素受体(Translocatedintiminreceptor, Tir)和大肠杆菌分泌蛋白(Ecolisecretedproteins, Esp)等,造成肠上皮细胞肌动蛋白的解聚和细胞骨架的破坏,引起典型的黏附和脱落(Attaching and Effacing,A/E)组织病变[16-17]。Gill 等[18]研究表明,EPEC 可通过抑制Cl-/OH-交换活性,降低肠道上皮细胞对Cl-的吸收,进而导致腹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EPEC 能通过T3SS将毒力因子注入宿主细胞中产生毒力效应。这些毒力因子包括EspF、EspG、EspH 和Map,其中EspG能破坏宿主微管网络,而只有完整的微管网络才能完成Cl-/OH-交换[19]。虽然EspF、EspG 和Map 不影响Cl-/OH-交换活性,但是EspF 能破坏细胞间的紧密连接,EspH 能改变宿主细胞骨架,Map 能改变线粒体膜电位[20-22];ETEC 能在小肠上皮细胞定植,产生不耐热肠毒素(LT)和/或耐热肠毒素(ST),LT 能激活腺苷酸环化酶,促使环腺苷酸(cAMP)浓度升高,进而激活氯离子通道,打破肠道上皮细胞的渗透压平衡,引起水和电解质大量进入肠腔,从而导致分泌性腹泻[23]。ST 在结构上与旁分泌激素鸟苷酸环化酶激活因子2B(Guanylate Cyclase Activator 2B, GUCA2B)同源,且相较于GUCA2B对鸟苷酸环化酶2C(Guanylate Cyclase 2C, GUCY2C)受体具有更高的亲和力,因而导致GUCY2C 过度激活。GUCY2C 将三磷酸鸟苷(Guanosine Triphosphate, GTP)转化为环磷酸鸟苷(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cGMP),刺激cGMP依赖性蛋白激酶(cGMP-dependent Protein Kinase,PKG)表达,进而打开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受体(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 CFTR),诱导氯离子沿其电化学梯度流向肠腔,进一步引起水的分泌,导致渗透性腹泻[23]。本实验室体内外研究表明,STp 可诱导肠道干细胞“囊肿”化,抑制类肠团出芽,降低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24]。而Smith 等[25]发现,Bmi1+(Bcell specific moloney murine leukemia virus insertion site 1)干细胞体外培养可形成“囊肿状”类肠团,而Lgr5+干细胞体外培养可形成“芽状”类肠团。这提示STp 可能诱导了不同类型的肠道干细胞之间的转变。
沙门氏菌主要作用于小肠,它不仅能黏附于肠道上皮细胞,通过T3SS 向细胞中注入效应蛋白,从而抑制肠道免疫系统,引发炎症的发生[26]。同时沙门氏菌还能分泌肠毒素,刺激环化酶体系,促进肠液大量分泌,引起分泌性腹泻[27]。Zhang 等[28]利用沙门氏菌侵染类肠团,发现沙门氏菌破坏了肠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降低肠道干细胞标记Lgr5 和Bmi1 的表达量。
1.3 饲料源霉菌毒素性腹泻
霉菌毒素是由曲霉菌、青霉菌以及镰刀菌等不同类型真菌产生的有毒次生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饲料中,对畜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其中猪对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T-2 毒素和呕吐毒素等最为敏感[29]。霉菌毒素进入仔猪体内会导致其肝脏受损,胆汁分泌减少,乳汁或饲料中的脂肪无法被消化吸收。肠细胞为维持内外渗透压,分泌过多水分进入肠腔中,从而引发仔猪渗透性腹泻[30]。大量研究表明,霉菌毒素会诱导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破坏肠道微生物菌群稳定性,引起肠道炎症[31-33]。本课题组发现,单次灌胃0.3 mg/kg BW 呕吐毒素即可导致仔猪隐窝干细胞活性下降,而2.0 mg/kg BW 呕吐毒素处理4 周龄小鼠5~7 d 显著减少了空肠中杯状细胞和潘氏细胞的数量,下调了隐窝和类肠团中肠道干细胞增殖和分化标志物的表达,且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介导了此过程[34-36]。
1.4 营养(生理)性腹泻
仔猪从母体到独立都会经历断奶阶段,断奶应激往往导致仔猪肠上皮细胞吸收功能障碍,从而引起渗透性腹泻[37]。且仔猪断奶由于其营养供给从富含蛋白质、脂肪和乳糖的高消化率母乳转变为消化率较低的以淀粉为基础的饲粮,导致其能量摄入量不足,难以维持肠上皮的有序结构[38]。断奶应激诱导肠上皮细胞损伤,而线粒体作为细胞代谢的中枢,是损伤作用的主要靶细胞器[39]。在正常细胞中,线粒体整合了能量产生和生物合成的分子途径,维持氧化还原平衡[40]。断奶应激引起线粒体内脂质、蛋白质与核酸的损伤,导致线粒体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造成肠上皮细胞死亡[41]。
2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和滥用
不可否认,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于畜牧生产后,有效降低了畜禽疾病发生率,极大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不规范用药导致的抗生素残留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我国每年生产的抗生素有超过四成用于畜牧业,其中90%的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10%用作治疗畜禽疾病,从而导致大量肉制品、乳制品中检测出各种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包括人畜共用型药物以及明令禁止的药物[42]。面对当前严峻形势,我们必须从大局出发做出抉择。而早在1986 年,瑞典便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规定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菌促生长剂(Antibacterial Growth Promoters,AGPs)。1999年,欧盟规定饲料中只能使用阿维拉霉素、盐霉素、黄霉素和莫能菌素,随后在2006 年全面禁止所有抗生素的使用[43]。2000 年丹麦宣布畜禽料中禁用抗生素,2011年韩国颁发禁用通知,2017年美国饲料中停止使用人类抗生素。紧随其后,我国也在2018 年将药物添加剂退出的时间定在了2020年。这一历史性决定提醒所有畜牧人需整合创新,迎接后抗生素时代的到来。
3 肠道健康调控
面对后抗生素时代的巨大挑战,许多致力于畜牧业的研究人员都在试图寻找有效的替抗策略。四川农业大学陈代文教授提出“抗病”营养的概念,且这一概念不断被试验所证实,如益生菌、抗菌肽和某些功能性氨基酸等。对这些营养源或营养素功能的挖掘有助于促进仔猪肠道发育,降低仔猪腹泻率。
3.1 益生菌
畜禽肠道中寄宿着数目庞大、种类众多的微生物,而菌群之间的平衡是维系肠道健康极为重要的一环。研究证实,饲料中添加益生菌制剂,如丁酸梭菌和乳酸杆菌,可有效改善仔猪肠道微生物菌群,恢复宿主免疫系统,降低疾病发生率[44]。丁酸梭菌又名酪酸梭状芽孢杆菌,在肠道中具有高黏附的特性,能竞争性抑制有害菌和腐败菌的生长,减少肠毒素的发生。同时,丁酸梭菌的主要代谢产物——丁酸可为肠细胞的正常生长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促进肠上皮组织的再生和修复[45]。另有研究报道,丁酸梭菌能够产生抗菌肽等抗菌物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赵熙等[46]在小鼠肠道中植入丁酸梭菌,发现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的数量增加,而有益菌群的增加占据更多的肠上皮位点,压缩了有害菌的生存空间。
乳酸杆菌作为益生菌被广泛应用于畜禽养殖、食品保健和临床治疗中。大量试验证实,乳酸杆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和调节肠道免疫力,从而改善肠道健康,促进机体生长[47-48]。这些功能的发挥除依赖于乳酸杆菌自身对病原菌的竞争(包括竞争营养物质和黏附位点)和排斥作用外,还与其产生抗菌物质如乳酸、过氧化氢和细菌素有关。乳酸和过氧化氢能分别通过降低肠道pH 值和激活过氧化物酶-硫氰酸盐反应系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而细菌素则通过改变致病菌细胞膜通透性和降低其DNA 的合成发挥杀菌作用。此外,乳酸杆菌及其代谢产物还能作为信号分子调控肠上皮细胞活性来增强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Hou 等[49]利用类肠团与黏膜固有层淋巴细胞(Lamina Propria Lymphocytes, LPLs)共培养模型发现,乳酸杆菌可通过诱导LPLs 分泌白细胞介素22(Interleukin-22,IL-22)激活STAT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信号,进而促进肠道干细胞再生,保护肠黏膜的完整性。
3.2 抗菌肽
抗菌肽(AMPs)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小分子肽类,具有广谱抗菌活性,且不易产生耐药性。研究表明,日粮添加抗菌肽可有效改善肠道上皮结构和屏障功能,缓解断奶仔猪腹泻,提高断奶仔猪生长性能。抗菌肽的胞膜穿透力是其发挥抑菌作用的主要途径,而其破膜的方式还存在争议。目前认为至少存在“环孔、毯式、桶板和聚集体”四种模型。此外,有研究指出,部分抗菌肽可直接进入细菌内部,阻碍DNA和蛋白质的合成,降低胞内必需酶的活性,从而导致菌体的死亡[50]。Yu等[51]研究发现,抗菌肽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降低过度的炎症反应,增强肠道屏障功能,修复肠上皮细胞损伤。
3.3 功能性氨基酸
近年来,包括谷氨酰胺(Glutamine,Gln)、谷氨酸(Glutamate,Glu)、蛋氨酸(Methionine,Met)和精氨酸(Arginine,Arg)等功能氨基酸被发现具有调节肠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活性,促进肠上皮更新和再生作用。Sukhotnik等[52]利用甲氨喋呤(Methotrexate,MTX)构建化疗性大鼠肠道炎症模型,发现补充Gln能显著增加模型鼠空肠和回肠黏膜重量、绒毛高度以及增殖细胞数量,提高黏膜中DNA 含量,上调TLR4/MyD88(Toll-like Receptor 4/Myeloiddifferentiationfactor 88)表达,表明Gln 通过激活TLR4/MyD88 信号通路促进肠上皮细胞的增殖,从而缓解肠黏膜炎症,降低MTX诱导的肠黏膜损伤。本实验室研究表明,添加Glu能增加IR/IRS/PI3K/Akt/mTORC1活性,提高猪肠道干细胞扩增为类肠团的生成效率和出芽指数[53]。不仅如此,在呕吐毒素存在的情况下,Glu 仍能重新激活Akt/mTOR/4EBP1 信号通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54]。Zhou 等[35]发现酶解小麦蛋白质(富含Gln 和Glu)能促进呕吐毒素损伤下肠道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维持肠上皮的完整性,且Wnt/β-catenin 介导了此过程。同样,Met 及其羟基类似物HMB 也能通过激活Wnt/βcatenin 信号抵抗呕吐毒素诱导的肠道干细胞活性降低和肠绒毛萎缩[38]。而用缺少Met的日粮饲喂小鼠会抑制小鼠肠道干细胞的增殖[55];Arg 则被证实是猪的条件性必需氨基酸,Arg 严重缺乏会导致动物高氨血症甚至死亡[56]。研究表明,断奶前补充Arg 能增加断奶后仔猪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促进肠道发育,提高仔猪体重[57]。
4 小结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禁用乃大势所趋。后抗生素时代,养猪业如何从“无抗”的阵痛期过渡到“安全、高效、优质、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期,除继续加强仔猪规范化养殖外,还需要整合和优化肠道健康调控技术,特别是抗病促生长营养理论和技术的开发和完善。随着分子生物学、营养学、药理学和病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仔猪腹泻的发生和发展机制逐渐清晰,这有助于对仔猪肠道施行更加精细化、动态化和具有靶向性的营养调控,以促进仔猪肠道内稳态平衡,预防或减少腹泻等肠道疾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