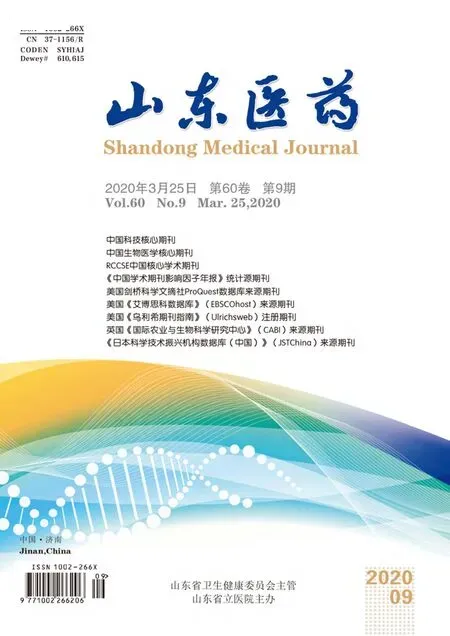阿尔茨海默病和抑郁症的共同病理学特征研究进展
2020-12-29唐培蔡玉洁谭声鸿崔理立
唐培,蔡玉洁,谭声鸿,崔理立
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省衰老相关心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广东湛江524000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以加速遗忘为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约占所有痴呆类型的60%~80%[1]。β-淀粉样蛋白(Aβ)在大脑中的堆积以及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引发的神经原纤维缠结是AD患者脑部最常见的两大病理特征。在AD的发病过程中常观察到精神障碍的存在。研究[2]显示,20%~40%的AD患者会伴发抑郁症。抑郁症是AD患者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之一。另一方面,抑郁症本身也是AD发病的危险因素。研究[3]发现,在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中,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全脑认知功能障碍呈正相关。此外,研究[4]还表明,患有重度抑郁症且症状逐渐严重的老年人患痴呆的风险较高。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AD和抑郁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近年来的研究[5]发现,AD与抑郁症存在一些共同的病理学特征,如神经炎症、突触数量减少、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下降、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下降等,现将相关研究进展情况综述如下。
1 神经炎症
神经炎症是导致各种疾病的一种病理学基础。小胶质细胞是大脑中具有免疫活性的一类细胞,具有动态监测内环境稳态的功能。小胶质细胞的过度活化会持续释放出炎症因子,促进神经炎症的发生。研究[6]表明,AD患者大脑中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聚集在Aβ和Tau蛋白附近,通过释放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导致神经元发生变性和死亡,从而引起神经炎症。另外,尸检结果也支持早发性和晚发性AD与大脑某些特定区域的神经炎症有关[7]。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项关于AD患者脑组织的研究[8]报道,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炎症与Aβ、Tau蛋白相关的神经病理学和认知能力下降密切相关。小胶质细胞活化引发的神经炎症也在抑郁症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9]表明,在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发病期间,其脑中出现的神经炎症与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存在因果关系。目前有关小胶质细胞调节抑郁样行为的分子机制仍不明确。动物研究[10]结果显示,持续的小胶质细胞活化产生神经炎症,而神经炎症的持续存在增加了慢性应激对小鼠抑郁样行为的易感性。
2 突触数量减少
突触是神经元之间进行信息传输及发生联系的重要部位。突触对神经递质的传递至关重要,突触数量减少常与AD和抑郁症有关,是这两种疾病的共同病理学特征之一,也是导致这两种疾病发生信号传导障碍的重要原因。AD与突触的逐渐丢失有关,突触数量的减少是AD出现认知障碍的重要性结构因素。在尸检研究[11]中发现,轻度AD和MCI患者的海马CA1区突触总数减少,但轻度AD患者突触数量减少更为明显,同时轻度AD患者海马CA1区的体积也明显减小。最近一项关于AD患者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成像研究[12]发现,AD患者海马的突触密度显著降低。另外,AD患者脑组织活检和动物模型研究[13]表明,突触数量的减少一般发生在树突棘形态改变之后,并且突触密度与树突棘形态改变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患者中也存在突触数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一项基于抑郁症患者死后尸检研究[14]报道,在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出现与突触有关的基因表达下调及突触数量的减少。最近一项研究[15]首次利用抑郁症患者活体进行PET成像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海马、扣带皮层的突触密度比正常人少,并且突触密度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即突触密度越低,抑郁症状就越严重。此外,基础研究[16]表明,通过慢性应激诱导小鼠抑郁样行为后出现突触的大量减少,抗抑郁药氯胺酮通过恢复突触的再生可以改善小鼠的抑郁样行为。
3 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
生理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对人体的生长、免疫以及各方面代谢均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机体遭到破坏时,过多的糖皮质激素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人类长期处于应激条件下会引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功能失调,从而导致血液中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糖皮质激素上调通过影响AD与抑郁症患者的神经内分泌紊乱,从而对机体产生不良影响,糖皮质激素上调也是这两种疾病的共同病理学特征之一。研究[17]发现,在AD患者的早期阶段出现皮质醇水平升高,而过多的皮质醇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以及加速病情的进展。另外,一项关于巴尔的摩老龄化纵向研究[18]发现,皮质醇水平升高增加了老年人患AD的风险。海马的主要功能是负责学习和记忆,含有丰富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研究[19]发现,皮质醇水平升高与AD患者海马萎缩有关。长期的HPA轴功能异常所致的应激激素水平的升高也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在动物实验中,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支持通过慢性不可预知性轻度应激可诱导啮齿类动物产生抑郁样行为。通过慢性应激诱导的抑郁样行为是目前啮齿类动物建立抑郁模型最经典有效的方法之一,该方法主要通过模拟抑郁症患者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的病理状态而建立的。在近几年研究[20]中,通过对灵长类动物(猕猴)诱导的抑郁症模型研究发现血清中的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另外,进一步研究[21]表明,在抑郁症患者中常发现HPA轴失调及皮质醇水平的升高。研究[22]认为,HPA轴的失调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引起强烈自杀行为的关键因素。
4 BDNF水平下降
BDNF是神经营养因子中的一种蛋白质,具有支持神经元生长发育以及营养神经的作用。BDNF是神经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关键调节因子。BDNF在AD和抑郁症中表达均下调,是AD和抑郁症共同病理学特征之一。在动物实验[23]中,BDNF的缺失和消耗会导致AD小鼠脑中皮质淀粉样斑块数量和大小的增加,加剧AD小鼠的神经病理学恶化,而血液中的BDNF水平升高可能减少异常Aβ的生成。实际上,通过细胞递送BDNF在AD小鼠脑中还可以改善记忆缺陷、树突棘密度及恢复突触可塑性[24]。最近的尸检研究[25]进一步发现,前额皮质中的BDNF基因表达水平不仅与AD神经病理有关,而且还与年龄呈负相关。BDNF水平的减少不仅与AD的发病机制有关,而且也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26]发现,在重度抑郁症患者脑脊液和血清中及抑郁模型小鼠的海马中BDNF表达水平均下调。动物研究[27]表明,通过慢性应激诱导的小鼠抑郁样行为其海马中BDNF水平下调。最近一项动物研究[28]进一步证实,部分抗抑郁药物可通过上调BDNF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从而减轻了抑郁症的行为。
5 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下降
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5-HT)。先前早有研究[29]报道,在AD患者下丘脑区域发现特异性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异常,特别是5-HT的显著减少,并且这种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减少与AD中观察到的一些非认知临床改变有关。另外,在AD患者死后尸检研究[30]中也发现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可能是导致AD患者精神障碍发生的原因。可溶性Aβ寡聚体可能与单胺类神经递质调节有关。在啮齿类动物研究[31]中,可溶性Aβ寡聚体通过降低5-HT水平以及激活小胶质细胞Toll样受体4,从而诱发抑郁样行为。另外,研究[32]还发现,通过对大鼠注射可溶性Aβ蛋白可诱导抑郁样行为的产生,同时伴随着大脑中5-HT水平的显著降低。单胺假说一直以来是抑郁症的主要假说。通过慢性应激诱导的抑郁模型小鼠中,发现海马中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以及其代谢产物均明显下调[33]。在最近的一项动物研究[34]中进一步支持了慢性应激会引发单胺类神经传递的改变。因此,在当前的抑郁症治疗上,绝大多数药物主要是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改善抑郁障碍,然而由于现下的抗抑郁药仅能改善一小部分患者的症状,并且需要数周才能起效,因此关于抑郁症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究。据研究[35]报道,单胺类药物不仅对AD患者有益,而且还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理解单胺类神经递质在AD及抑郁症中的确切病理生理学特征对于今后开发高效能、不良反应小、起效快的新型药物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神经炎症、突触数量减少、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BDNF水平下降和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下降是AD与抑郁症之间共同的病理学特征,通过这些共同的神经病理学特征可将精神疾病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紧密联系起来。当前的抗抑郁药物治疗仅对部分抑郁症患者有效,而关于AD的治疗尚无特效药来治愈。因此,我们通过对AD与抑郁症的共同病理特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可能有利于将来发现这两种疾病药物治疗的潜在新靶点以及开发出有利于干预早期AD及抑郁症患者的新型药物,这对于今后抗抑郁抗痴呆治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