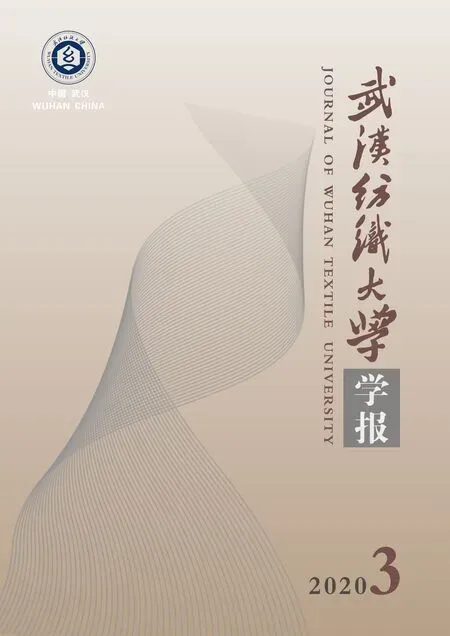唐诗中的女性服装色彩探析
2020-12-29刘烨
刘 烨
唐诗中的女性服装色彩探析
刘 烨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考察《全唐诗》中所见女子服饰,以服装色彩为角度,观察唐代女性对于色彩的深度体验。以三原色为主的色彩搭配构成了唐代女性服饰的主流,而多色系的调和使用展现出唐代女性大胆独立的审美追求。“色彩”的使用,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物质基础的丰富,也是诗人创作时想象力的极致发挥。有许多难以创造出来的色彩体验,被诗人附加在服饰之上,镶嵌进诗歌当中,刺激着读者的感官。
服装;色彩;唐诗;女性
唐诗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断地冲击着我们感官的正是缤纷绚丽的色彩。在唐诗当中,正是由于色彩的大胆使用,使得诗人可以自由的表达内心或是磅礴或是细腻的情感;也正因唐诗的流行,在文字和言语的参与下,色彩被更深层次地挖掘和运用。色彩不再单单是用来描述物色本身,而是成为诗人情绪的承担者,诗歌情境的营造者。我们在唐诗里,可以看到如此细腻的运用色彩来表达情感、渲染环境的内容,大多数都集中在与妇女或宗教相关的诗篇当中。男子的服饰大多严守等级规范,色彩运用方面少有奇妙的想象,宗教服饰部分出于其迷狂、虚幻的本性,其想象空间也十分广阔。而女子服饰所附着的色彩,除了不受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之外,往往还倾向于勾连男女情爱的部分,甚至可以直接指代女性本身,这一点是其他服饰在诗歌当中很难体现出来的。
一、三原色支配下的唐代女性服饰
在美术上,传统的说法对于三原色的定义是在色彩中不能被调和出来的三种颜色,即红黄蓝。现如今这种说法被进一步精确为黄、品红和青这三种颜色。我们在这里取传统意义上的三原色的定义,就可以从唐代的诗歌当中,发现色彩支配下的女性服饰之美。
(一)强烈的视觉冲击:红与黄
“纤腰宜宝袜,红衫艳织成”[1](p53),唐代的女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思想开放、勇于创新的时代。唐帝国辽阔的版图、富足的经济和强盛的文化,激励和鼓动着它的子民不断地超越前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体现在服饰之上就是款式与色彩的大胆尝试。相比于男权社会下,男子服饰的等级森严,女子服饰更能展现唐人对于美的追求和感受。女子不仅是人们审美的对象,而且也是美的创造者和源泉,唐代的女子们没有宋代以后理学的约束,反而在异域胡风的影响下,大量使用红色这种极具视觉冲击的色彩。这种颜色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强烈的感官效果,放在诗歌当中,我们一样能感受到诗人对于这种红色之美的热爱,仿佛白纸黑字里因为透着这一抹红色,而格外生动俏丽。
唐诗中的红颜色,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女性服装的每一个角落,从服装的结构来说包括了袖、袂和绶,从款式来说包括了衫、裙、帔、襦、冠、袜和靴,从质地来说包括了绡和纱。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图中,妇女身穿红裙、绿裙,外罩帔子,上身穿襦,质地轻薄。“中国的染色技术早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飞速发展。当时已经有茜素(红色)、靛蓝(蓝色)等燃料品类,染出的服色鲜亮、耐久”[2],唐诗中也有“蒨蒨红裙好女儿,相偎相倚看人时。使君马上应含笑,横把金鞭为咏诗”[3](p291)之句,这句诗中的“蒨”一作“茜”,“茜裙”就是大红裙子。红色在唐诗当中不只是一种大红色,如上文中有淡红色的帔子,还有绛色,“春深欲取黄金粉,绕树宫娥著绛裙”[4](p1454),这与上文所引用的“宫衣小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还有退红色。“缣罗不著索轻容,对面教人染退红”[4](p1067),“退红”是唐代的一种色彩,是粉红色被细化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颜色。色彩的细化,诗的诗歌的空间被进一步打开。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1](p1469)而最具有魅力的红色的女性服装,当属石榴裙。李凤墓的侍女图中,这名侍女身穿大红裙,颜色分外鲜艳。“石榴裙”不仅其裙幅错落有致,状如石榴花盛开之貌,其颜色也和石榴花一样娇红可滴。既然“石榴裙”取名自石榴花,那么自然就和石榴相关。石榴产自西域安石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胡葱、苜蓿、胡荽、黄蓝——可作燕支也”[5],张骞通使西域的时候将石榴的种子带了回来,并将这种水果取名安石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石榴。“玉佩石榴裙,当年嫁使君。专房犹见宠,倾国众皆闻”[4](p542),皇甫冉诗中的女子就是在出嫁的这一天,腰配玉佩,身穿石榴裙,取日子红火、多子多福的吉祥含义。
除却这层蕴含着祝福之意的传统习俗,吸引唐代女性钟爱石榴裙的原因,最为直观的就是它鲜艳的红色。有了这抹艳丽的红,穿着石榴裙的唐代女性在诗人眼中更加瞩目。“少妇石榴裙,新妆白玉面。能迷张公子,不许时相见”[1](p846),诗中迷倒张公子的是新装玉面还是红石榴裙?想必二者兼而有之,在张郎眼中,那流动于少妇足尖之上的红流,是他记忆力难以忘却的鲜活,因而才能令他痴迷心狂。“双鬟美人君不见,一一皆胜赵飞燕。迎杯乍举石榴裙,匀粉时交合欢扇。”[4](p1257)酒席之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轻盈扇风之间忽见一片红云闪现,那一片红云就是美人的石榴裙。被石榴裙吸引住目光的不仅是唐代的诗人们,还有翩翩飞舞的蝴蝶,“上林胡蝶小,试伴汉家君。飞向南城去,误落石榴裙”[6](p52)。蝴蝶被石榴裙所迷惑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唐代长安的女性有一风俗,“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7]。长安的女性会在游春的时候将红裙接连成片,当作宴会的帷幄,也难怪蝴蝶会被吸引误落其中。
石榴裙的红色,跨越了等级的限制,无论是“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1](p51)的杨贵妃,还是“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8](159)的蜀女歌姬,都可以穿着这种石榴红裙,这足以见唐代女子在服饰用色方面的大胆尝试。她们用具有极强视觉冲击效果的红色,来表达自己内心炙热的情感。或是吸引来客的目光,让欣赏者流连忘返,沉醉在大唐红色的裙衫之下。
同样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色彩是黄色,“别色官司御辇家,黄衫束带脸如花”[3](p324)。黄色的衣衫在唐诗当中要远比红色少得多,但是仍能看色彩的细腻划分在诗中的体现。
“郁金”是黄色的一种,“亦用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作紫绀色,或作郁金色”[9],杜牧有“烧香翠羽帐,看舞郁金裙”[6](p1257)之句。“郁金”的名称并不是唐人首创,《急就篇》就有“郁金半见缃白䋤”[10]之语,认为郁金作为染色材料,其最后染成的颜色为黄色。但是我们在唐诗中发现,“郁金”不仅和色彩相关,往往也和香料有关,“娼家美女郁金香,飞来飞去公子傍”[1](p573)。这种香料据说来源于异域,有两种说法比较盛行,其一为佛教的郁金,“郁金,此是树名,出罽宾国。其花黄色,取花安置一处,待烂压取汁以物和之为香。花粕犹有香气,亦用为香也”[11],佛教沐浴时常用此香。另一种说法为中国传统鬯酒所用,“秦桂林郡也‧‧‧郁,芳草也,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12],郁金香在这种看法里出自西南。作为香料的存在,梁武帝曾有诗曰“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13]梁武帝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诗中的郁金香、苏合香都产自异域。我们可以看出唐人对于色彩的命名不仅参考颜色本身,而且色香结合,不仅在体现在视觉上,还勾连于读者的在嗅觉上。郁金作为香料,在诗中又承担了颜色的属性,如此一件郁金裙给人带来的就是全方位的体验。这种色彩的表达方式不仅使诗歌更具意境,开阔了格局与空间。而且我们也能感受到唐人对于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巧的构思,视觉的冲击和嗅觉的想象仿佛通过文字向我们奔涌而来,一位唐代的少女正旋转着黄色的舞裙,遍体透着异域的香气,与长安的公子顾步相傍。
“缃裙”,是浅黄色的裙子。南里王村墓中有一组屏风图,其中图上一名侍女身穿黄裙。而相比于浅黄色“缃裙”的淡雅仙灵,金色裙子的感官体验则更加强烈。“看雨逢瑶姬,乘船值江君。吹箫饮酒醉,结绶金丝裙。”[6](p42)同样是写“仙灵”之感,“金丝裙”则比“缃裙”少了一下飘逸之感,而多了一些烟火之气。对于唐代的女性来说,不仅人与人之间服饰的等级差别界限十分模糊,连凡人与仙人之间的服饰差别也很小。仙人可以穿金丝织就的衣裙,而人间的美女一样也能穿金丝裙。“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6](p908)这位“东邻女”就是身穿金线盘绣的衣裙,在诗人的笔下仿佛重获新生,格外耀目。
(二)感伤的雅致:青与绿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6](p1243)与鲜艳暖色调的红色、黄色相比,冷色调的青色和绿色没有体现唐代妇女对于美的大胆追求,却展现出唐代妇女活泼明快、雅致精巧的生活态度。
和暖色调的女性服饰相比,唐诗中冷色调的服装多了一些惨淡的情愫。和李凤墓中的大红裙相比,永泰公主墓中这名宫女服装颜色暗淡深沉。而这种色彩的淡然,也寄托了穿着者自身的情感。“天寒翠袖薄”,天寒与翠色的冷调相互呼应,给诗歌平添了一丝冷意,如果替换成红袖,则难以表现出诗人的愁苦悲悯之情。同样的,“白妆素袖碧纱裙”中身穿碧纱裙的女子是一名丧偶的孀妇,如果替换成石榴裙,那么就令读者难以接受,在读者的内心已经接受了传统的设定,即孀妇的贞洁不易再花枝招展,应该出于避嫌的目的而穿素雅的服装。在这里碧色比红色更加合适,也更能渲染诗歌的气氛。在唐代侍女“通服青碧”,因此这两种色彩也常常出现在侍女的服装上。
除了青和绿这两种色彩,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也能体现出唐代妇女感伤而淡雅的追求,比如白、银。
白色的女性服装多用自然植物来比拟,比如“柳花裙”“藕丝衫”,“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沉香慢火熏。惆怅妆成君不见,空教绿绮伴文君”[6](1063)。藕和柳花都是淡白色,妇人身穿素雅的颜色,她的内心情感必然不是火热的激情,诗中的女子终日惆怅等待夫君,一袭白衣也更加凸显穿着者的伤感失落。“雨湿轻尘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半含惆怅闲看绣,一朵梨花压象床。”[6](p218)雨后的明净和暗香中,一名女子身穿白衣裳,她也同样惆怅,倚坐在床榻旁仿如一朵清雅的梨花,诗中用“玉人”“梨花”“象床”渲染出一个纯白色的环境,在这样一尘不染的院落屋阁之内,一名妇人“半含惆怅”就显得十分自然,安静的环境之下,人更容易陷入沉思,远非红袖翻飞的酒肆可比。
银色的女性服装要比金色的稍显清幽,比如“银泥裙”“银泥衫”。“银泥裙映锦障泥,画舸停桡马簇蹄。清管曲终鹦鹉语,红旗影动薄寒嘶。”[4](p1907)“银泥”是一种用银粉调成的颜料,银色的衣裙可以反光。因此才能“映锦障”,银色的冷峻和“清管曲终”“红旗寒嘶”相互呼应,凸显出离别的氛围。“金屑醅浓吴米酿,银泥衫稳越娃裁。舞时已觉愁眉展,醉后仍教笑口开。”[6](p606)这里的“银泥”一者是为了与上句“金屑”对仗,二者用来衬托舞者的愁眉心伤。如果是金色或是红色,所产生的热闹气氛与此时不服,因此银泥衫在这里更能和诗人的心情相呼应。
还有一种介于冷色和暖色之间的色彩——紫色,紫色在唐代属于贵色,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身穿紫衣。而紫色在女性服饰方面,却可以跨越阶级的壁垒,常常出现在歌姬的服装中。“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1](p248),这里身穿紫罗襦的就是唐代的一名娼妓。紫色服装出现在舞蹈当中比较多,“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6](p494),这一点将在舞衣部分展开论述。紫色介于冷暖之间,它的出现可以最大的程度包容诗人的情感。
二、多色系调和下的唐代女性服装
红裙和翠裙的颜色虽然都十分鲜艳明快,但毕竟都是单色。唐代女子,特别是贵族妇女,她们的服装并不会仅有一种颜色,或是搭配不同颜色的裙衫和巾帔,或是将衣裙染成裥色和晕色。她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展现出更加绚丽的服饰,唐王朝给予了她们这个机会,丰富的物产和经贸的往来以及印染技术的提高,使得唐代女性服装在多色系调和之下大放异彩。同时给予了诗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唐代女子就是最具诗化的人,她们善于观察生活、享受生活,她们的思想在自然之色中驰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想法逐渐形成,并迅速付诸实践,完成出一件件展现唐朝女性魅力的锦绣华服。
唐代妇女已经不满足于单个色彩的创新,而是开始寻求新的样式,这种样式就是裥色和晕色的运用,晕色就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颜色染成色彩相间的形状,两种颜色部分没有明显界限,呈现出晕染的效果。裥色则有明显界限。以上这两种方式,正是唐代妇女探索自身美的历程的体现,单一的三原色已经不能满足她们对于美的精神需求,于是便产生了单色搭配与裥色晕色的使用,形成了唐代五色绚烂的服饰美学。
“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受到社会道德、经济、文化、风尚制约和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乃至社会地位,成为表明其身份的象征性载体之一”[14]。从唐代的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贵族妇女所穿的衣服颜色更加多变,而普通的侍女往往都是单一的色系。虽然没有男子的服色制度,但是女性服饰的用色依然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来源于朝廷对于奢华风气的约束。“妇人服从夫、子,五等以上亲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凡裥色衣不过十二破,浑色衣不过六破”[15],这说明裥色的做法在民间已经很常见,但是官方并没有限制裥色,而是限制“破”的数量,其实其要约束的是妇人对奢华迤逦服饰的过度追求。
在唐诗当中最常见的搭配就是红色与绿色,例如新城长公主墓宫女图中的这几名宫女所穿的双色服。这两种色调鲜明又极具互补反差的颜色,使得诗歌中的文字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画面感。“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云起风生归路长”[1](p1684),这里是用翠色的钿头与红袖进行搭配,暗合诗中的青荷与红莲,相映成趣。“微收皓腕缠红袖,深遏朱弦低翠眉。”[4](p835)这里是用翠色的画眉与红袖进行搭配,使得诗中人物具有动态的张力。“摘莲红袖湿,窥渌翠蛾频。”[6](p1312)这里是用翠色的蛾子与红袖进行搭配,色彩与生物的碰撞,加深了诗歌的层次感。“春生翡翠帐,花点石榴裙。”[1](p759)唐诗中常常将服色与生活中的事物进行结合,利用颜色差来弥补黑白文字上的缺失,这里用石榴裙的红色与翡翠帐的绿色进行对比,使得春天的花红柳绿迁移到日常用品之上,生活气息与自然景致完美的融合,有不露痕迹,这都得益于唐代服饰对于色彩的细致把握。“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4](p1254)这里不仅有颜色的对比还与薄厚关联甚密,翠色更显轻盈,而红色则较为敦厚,适合厚一些的襦衣。“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4](p1918)中就有红色的夹罗襦衣,颜色在此有了厚度和重量。同样展现颜色重量的还有“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袴薄于云。”[6](p394)浅色的衣衫在诗人眼中更为轻盈。
红与绿的搭配,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更多的体现在酒宴舞席之上。“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6](p147)歌姬下身着红裙,上身却是碧色的袖子,舞动起来上下两种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看客不仅不会审美疲劳,反而被这种视觉的冲击所吸引。酒宴之上男女觥筹交错,“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6](p401),“红裙”指代宴会上的舞女歌姬,“绿袍”指代参加宴会的男子友人。在诗歌中红裙女与绿袍男形成对比,色彩的差别也就是性别的差别,身份的认同在这里通过颜色展现出来,而灰暗的灯光下,红绿杂错,炫目光离,离别欢送之情与不舍挽留之意在这一刻透过“红”与“绿”流进了后人的眼中心里。歌姬有多么艳丽?“若是五陵公子见,买时应不啻千金。青丝高绾石榴裙,肠断当筵酒半醺。”[3](p949)五陵的少年公子千金难买一见,发如青丝裙石榴,半醉一曲愁肠断。这里仍然是用青色和红色进行对比,美人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而是绚烂夺目的,因此在唐代,妇女喜奢,用缤纷绚丽的颜色装点自身。“此婢娇饶恼杀人,凝脂为肤翡翠裙,唯解画眉朱点唇”[4](p1938),凝脂为白,翡翠冷艳,而一抹朱唇点破了冷素的色调,平添了一丝生机,也成功凸显了此婢的“恼杀人”。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1](p1469)诗中的歌舞姬,眉如萱草之绿,裙如榴花之红,这里不仅仅是红与绿的对比了,还隐藏着一个传统名物思想的种子。那就是萱草代表着思念远夫,榴花代表着生机多子。这萱草和榴花也是一层对比,这两句诗内有两层对比,冲突更具有深度,色彩的体验与情感的寄托在此得到了融合。唐诗中关于女性的细腻色彩表达,正一步一步地指向情欲与爱恋,这些集中于女性身上的色彩体验,自然和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身体与情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样的还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6](p537)杨柳与榴花、绿与红、眉与裙的三层对比,将春深妓女的那种杨柳扶风的柔弱和石榴花开的娇艳都巧妙地编织进诗歌当中,令人回味无穷。
衣裙之上也不仅仅是纯色搭配这样简单,还有混搭的款式。“正抽碧线绣红罗,忽听黄莺敛翠蛾。秋思冬愁春怅望,大都不称意时多。”[6](p492)这里的红罗之上有碧色的线条,这种混搭也合乎春望秋思的色彩感官。“红绿复裙长,千里万里犹香”[8](p953),这种红绿复裙也是唐代常见的女性服装。在混搭模式下还有“银色”与“绿色”的结合,“秋白鲜红死,水香莲子齐。挽菱隔歌袖,绿刺罥银泥。”[6](p45)这里面就是将菱角的“绿刺”和“银泥”相呼应,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合乎月色的漉漉与烟波的清淡。也有金丝镶绣的衣衫,“红铅拂脸细腰人,金绣罗衫软著身”[6](p1126),金线绣成的罗衫更显奢华,而诗中用红、金这两种能给视觉带来强烈刺激的颜色来形容舞姬,使读者更容易想象当时的场景与画面。同样是跳柘枝舞的舞姬,“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6](p1105)这里的金丝与红衫搭配,金丝仿佛盘旋在薄雾之中,足见舞衣轻透,同时金色与红色的冲突在这里更加明显,被织绣在一起,更具有视觉吸引力。
混合模式不限于两种颜色,还有三种色彩的。李凤墓中手持浮尘的妇侍女,身穿红白双色裙,淡黄帔,此为三种颜色的混搭。而“著破三条裙,却还双股钗。”[6](p944)就是有三道花边的裙子。《玉台新咏》中有一首《定情诗》,诗中有言“何以答欢忻,纨素三条裙。”[16]可见女子衣着色彩繁复早在唐代之前便已有之。唐代女子还有穿着五种颜色的衣衫,“歌喉渐退出宫闱,泣话伶官上许归。犹说入时欢圣寿,内人初著五方衣”[6](p1121)。据《教坊记》所载,五方衣是指有五色绣襟的衣服,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分别对应着东、南、中、西、北五个方向。
唐代的女性衣服色彩艳丽多样,既离不开女子大胆的创新和对美的极致追求,也离不开诗人浪漫的想象与细致的观察。无论是纯色所寄托的诗人情感,还是裥色所表达出来的诗歌意境,唐代的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早已离不开女性服饰的色彩体验。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作为唐代审美的主要人群,男子的喜爱左右着女子的选择,整个唐代,由初期的色彩素雅纯一到中期的绚烂求备,再到后期的糜情奢华,都离不开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和社会风尚。当经济富足,民众趋于享乐,男子又饱受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约束,无法在色彩上追求美的享受。于是在男权社会,女性成为了美的承担者,也是美的体验者。男性将对于美的感悟投射到女性服饰之上,无法满足时,便在诗歌中进行想象与渲染。这种想象融合了女性自身的意识,再反射到女性本身,进行重新创造,于是就形成了新的色彩名称,这种色彩名称不再单纯的是一种颜色的名字,而是包含了当时人们的思考与五官体感的反馈,比如上文提到的“石榴裙”和“郁金裙”。除此之外,颜色的强烈对比与搭配,又为唐诗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即色彩空间的营造。这种既能烘托气氛又能表达作者内心与期许的模式,为诗歌与服饰的结合开辟了新的道路。
[1] 陈贻焮. 增订注释全唐诗 (第一册)[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 兰宇. 唐代服饰文化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43.
[3]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四册)[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 (晋)张华,等. 博物志(外七种)[M]. 王根林,等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
[6]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7] (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 丁如明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9.
[8]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五册)[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9] (晋)陆翙. 邺中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
[10] (汉)史游. 急就篇[A]. 丛书集成新编(第35册)[C]. (唐)颜师古注,(宋)王应麟补注.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439.
[11] (唐)玄应,(唐)慧琳,(辽)希麟音义.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M]. 徐时仪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42.
[12]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校正[M]. 陈桥驿校正. 北京:中华书局,2013. 794.
[13] 吴冠文, 等. 玉台新咏汇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84.
[14] 张玉升, 谢艳萍. 服饰设计与色彩运用[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 5.
[15]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530.
[16] (南朝陈) 徐陵. 玉台新咏笔注[M]. 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程克宏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1.
On Color of Women's Clothing in Tang Poetry
LIU Ye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omen's clothing in the whole Tang Dynasty poetry, and observes the deep experience of women's color in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thing color. The main trend of women's clothing in Tang Dynasty is the color combination of three primary colors, and the harmonious use of multi-color system shows the bold and independent aesthetic pursuit of women in Tang Dynasty. The use of "color" is not only the enrichment of material basis in daily life, but also the extreme exertion of the poet's imagination in his creation. There are many color experiences that are hard to create,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 costumes and inlaid into the poems by poets, stimulating the readers' senses.
clothing; color; Tang poetry; women
刘烨(1989-),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史.
闽南师范大学校长基金(sk19016).
TS941.42
A
2095-414X(2020)03-0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