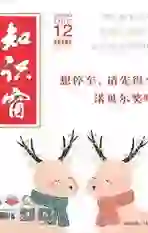无香不欢的宋朝
2020-12-28邢洁
邢洁
在宋朝,从皇室贵族、文人墨客到平民百姓,各类香方、香料、香器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香,是高雅情趣的载体,是诗意生活的灵魂。
更将花谱通香谱
自五代时期蔷薇水传入中国以后,花香与沉香结合的调香理念开始流行起来,在宋代被发展到了极致。
与南唐宫中的“花浸沉香”不同,宋人将“蒸花取液”“花液浸香”合二为一,把沉香与鲜花一起密封在容器中,放入蒸锅里缓蒸,这种制香的方法叫作“蒸沉”。凡是带有香味的花,如梅花、瑞香、荼蘼、栀子、茉莉、桂花及橙橘花等,都可与沉香一起熏蒸,如此熏蒸过的沉香,气味灵动清润。有诗云:“花气蒸浓古鼎烟,水沉春透露华鲜。”
蒸沉的香品通常以花名与香材组合的形式命名,如朱栾与沉香熏蒸的合香叫作“朱栾沉”。将沉香切成小片,与朱栾花層层相叠地铺在锡制的蒸馏器中,然后置于水锅上小火缓蒸,再用蒸出的花液浸泡蒸过的沉香。次日更换鲜花,蒸、浸三个来回后,将沉香片晒干封存。他日焚之,味香如在柑林中。
与“朱栾沉”不同,“柚花沉”有点儿类似窨花茶,不用火蒸,让柚花香自然熏染沉香。将沉香片与柚花层层铺叠,密封在洁净的瓷器中,隔天更换新鲜的柚花,如此窨制一个花期,香成。
无论是“花蒸香”还是“花熏香”,目的都是让沉香染上花香味。以火力蒸出来的香品,气味较浓烈馥郁;而香花自然窨制的香品,制作周期较长,香味相对清淡柔和。
万物皆可香
“捣麝成尘,薰薇注露,风酣百和花气。品重云头,叶翻蕉样,共说内家新制”。宋代宫廷有大肆消费名贵香料的风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香品是以“沉檀脑麝”为原料制作的“富贵四和香”,焚之有高贵清妙之意。沉香、檀香、龙脑香(冰片的别名)和麝香在当时都属于奢侈香料,普通百姓只能望“香”兴叹。
然而,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趣。用不起“富贵四和香”的贫士们就以果皮、果核、柏叶、蔗滓等物制作“小四和香”,被戏称为“穷四和”。陆游有诗曰:“发犹半黑脸常红,老健应无似放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穷四和伴儿童。”
对于追求朴素天然用香方式的人来说,自然界中的一花一木都是香。有人发明了一种最省钱的香方,以旧竹片代替沉香与香花熏蒸,名为“百花香”:把竹子切小片,与四时香花层叠放入瓷器中,在蒸笼里小火缓蒸,这样竹片就会浸染上花香。一旦入炉熏焚,四季所开过的百花香气便挥发升腾,别具一番清雅风韵,“若春时晓行山径”。
“富香”与“穷香”依香料价格划分,但香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像苏轼既熏焚名贵的沉香,“碧纱窗下水沈烟,棋声惊昼眠”,又常熏焚朴素的柏子香,“铜炉烧柏子,石鼎煮山药”。
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
宋代香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空前高峰,当时的文人以品香、调香为时尚雅事,还喜欢以香事为题吟诗作词。
杨万里的“起来洗面更焚香,粥罢东窗未肯光”,说的就是很多文人早起焚香的生活习惯。许月卿的《饭了》诗曰:“饭了庵中坐,高情等寂喧。井泉春户口,篆火午香烟。”描写了午时静坐,焚香安神的情景。朱敦儒曾提到夜晚床帐中熏焚木樨沈:“芭蕉叶上秋风碧。晚来小雨流苏湿。新窨木樨沈,香迟斗帐深。”木樨沈,即沉香与桂花制作的合香。由此看来,香与人须臾不可分离,无论晨昏早晚,总有芬芳之气萦绕其间。
说到香,就不得不提到黄庭坚,他是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也是首屈一指的香学大师。他对香有着独到的见解,且留下了许多独到的香方,最著名的是意合香、意可香、深静香、小宗香,被称之为“黄太史四香”。
黄庭坚六十岁那年被贬宜州,住在嘈杂肮脏的市集内,残破不堪的陋室根本无法阻挡各种叫卖声与难闻气味的入侵。然而,他并不以为意,焚香一炷,神闲气定。众人诧异,面对如此恶劣环境,怎可有如此的安适恬淡?其实,答案就在黄庭坚早年的一首诗中:“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露台湛空明。”
在真正的香家眼中,所谓品香并不只是用鼻子去闻香,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即所谓“鼻观”。对他们而言,香,是日常生活的良伴,是歌咏言志的依托,也是对心灵的净化与修炼。
人生短促,世事纷杂,何不烹茶焚香,以慰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