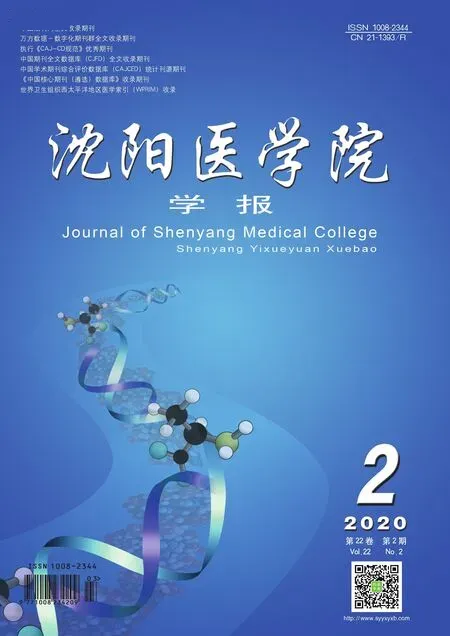双酚A 对雄(男) 性生殖系统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学机制
2020-12-25李昀谦梁书秋马明月
李昀谦, 梁书秋, 马明月*
(1.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2015 级学生, 辽宁 沈阳110034; 2. 沈阳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教研室)
双酚A (bisphenol A, BPA) 是一种由丙酮和苯酚合成的白色晶体。 在常温下, BPA 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为0.12 g/L, 易溶于有机溶剂如醇、醚等[1]。 大量研究表明酚类化合物是环境中广泛存在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其代表物为BPA, 进入机体后能对机体内源性激素的合成、 分泌、 转运、 代谢和消除产生干扰, 直接或间接损害机体健康[2]。 由于BPA 的分布来源广、 种类多、 数量大、 接触途径多样、 蓄积性强, 因此, 其对机体健康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尤其是在生殖健康方面[3]。 越来越多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BPA 对男性生殖系统功能的影响, 对包括生育力、 精子质量、 性功能、 激素水平、 出生体重、 男性生殖道畸形等方面均有相关报道[4]。 因此, 本文就BPA 对雄性生殖系统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学机制进行综述。
1 BPA 对雄(男) 性生殖系统影响
BPA 及其代谢产物可以对人体产生各种影响,包括对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 内分泌系统、 生殖系统等的影响。 其中,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较大,主要影响表现为生殖毒性。
1.1 BPA 对雄性生殖器官影响 在靳翠红等[5]的研究中, 给予小鼠腹腔注射BPA, 高、 低剂量组(500 μmol/kg、 100 μmol/kg) 与对照组相比, 精子数量显著下降, 活动精子百分率显著下降, 精子畸形率显著升高。 也有研究通过灌胃的方式以50 μg/ (kg·d) 的剂量对小鼠进行染毒, 其中实验组的精子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但生殖器官脏器指数没有明显差异; 将染毒小鼠与没有染毒的雌鼠交配后发现, 实验组每胎产仔率显著低于对照组[6]。 在周芩[7]的研究中, 以100 mg/ (kg·d)、200 mg/ (kg·d) 剂量的BPA 对小鼠进行灌胃染毒后发现, 各组睾丸、 附睾、 精囊、 前列腺脏器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考虑是染毒方式与染毒剂量的原因导致该结果与其他实验结果不同。
1.2 BPA 对雄性生殖相关细胞损伤 在成熟的雄性动物中, 睾丸支持细胞数量决定了睾丸大小和精子数量[8]。 邓茂先等[9]分离培养雄鼠睾丸支持细胞, 并进行BPA 染毒, 发现BPA 使睾丸支持细胞的波形蛋白表达量下降, 并阻碍了细胞骨架和胞间连接的形成, 使得支持细胞的形态在体外培养中发生改变, 结果表明BPA 破坏了支持细胞骨架并改变支持细胞形态, 导致雄性生殖系统损伤。孟祥东等[10]研究发现, 10-7mol/L BPA 即可引起睾丸支持细胞和精子细胞凋亡。 李玉华[11]研究发现, 低剂量组(50 μg/kg) 与对照组相比, 小鼠曲细精管管腔中可见脱落的生精细胞; 高剂量组(500 μg/kg) 小鼠睾丸中基底膜与生精细胞间隙变大, 生精细胞层次不清, 排序混乱, 并有大量生精细胞脱落, 部分甚至堵塞整个管腔。 Toyama等[12]按20 μg/kg 给成年雄性CD-1 大鼠皮下注射BPA 6 d 后, 发现精子细胞的顶体囊泡、 顶体帽、顶体、 细胞核都发生了严重的畸形; 支持细胞和精子细胞间的基质特化结构出现结构多余或缺失,并有发育不完整; 在停止染毒2 个月后, 发现睾丸组织形态和生育能力均恢复正常; 该现象说明BPA 的毒作用是暂时的, 造成的生殖系统损伤可能是可逆的。
1.3 BPA 对雄性生殖内分泌功能影响 BPA 已被证实是通过作用于雌激素受体而产生生物效应,其产生的拟雌激素效应与抗雄激素效应可对幼鼠的生殖发育产生影响。 从下丘脑-垂体-睾丸轴角度观察BPA 对生殖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 但结论有一定的差异。 在黄洁等[13]的研究中, 随着BPA 染毒时间的增长, 小鼠睾酮分泌逐渐减少, 与睾酮合成相关的酶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 胆固醇侧链裂解酶、 细胞色素P45017a 羟化酶及波形蛋白的基因及蛋白水平均明显下降。 已知精子的发生与体内激素的调控密切相关, 睾酮是雄性生物体内最重要的雄性激素之一, 主要生理功能是促进精子发生和参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中生殖激素的调节与控制。 睾酮可通过合成雌二醇而反馈性抑制下丘脑-垂体对卵泡刺激素和泌乳素的分泌, 而泌乳素在雄性体内又与睾丸间质细胞合成有关[14]。 有研究显示, BPA 可以通过睾酮的负反馈作用直接影响睾丸的功能[15]。 周芩[7]研究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 BPA 高剂量组血清睾酮含量明显降低, 而卵泡刺激素水平明显升高, 说明BPA 可能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对生殖系统产生影响; 此外,还发现在男性人群中尿液BPA 含量与血清雄烯二酮(AD) 和卵泡刺激素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性。Ramos 等[16]研究发现, 妊娠期BPA 暴露的大鼠,在15 d、 30 d 时观察到总睾酮短暂增长, 泌乳素水平上升, 同时雄激素受体下降, 但120 d 消失,表明产前暴露BPA 可能引起“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的改变, 从而对生殖系统造成损伤。
1.4 BPA 对男性生殖系统影响的流行病学调查 制造工厂的直接排放, 加工和处理过程中的逸散性排放是自然环境中BPA 存在的主要原因[17]。 Li等[18]进行的一项职业队列研究发现, 427 例中国男性工人尿液BPA 水平与性功能障碍有关。 Zhang等[19]在亚洲人群中共296 份尿液样本中发现,94.3%的样本中BPA 浓度在0.1 ~30.1 ng/ml 之间, 中国人BPA 平均浓度为1.10 ng/ml, 韩国为2.17 ng/ml, 日本为0.95 ng/ml。 BPA 可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对尿中代谢物质含量的检测可以侧面反映出机体BPA 摄入量[20]。 美国生殖医学会发现不育男性尿中BPA 浓度与精子浓度、 精子活力等精液参数呈负相关[21]。 但同时也有研究指出,职业暴露BPA 后血清BPA 水平上升, 但血清中BPA 水平与性激素水平间并无关联[22]。
2 BPA 致雄性生殖毒性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BPA 能够引起不同程度的雄(男) 性生殖系统损伤, 但其毒性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BPA可作用于神经系统, 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影响激素的合成、 分泌以及靶器官的多种生理效应。 也有学者认为BPA 可通过氧化应激对生殖系统产生损伤[23]。 目前,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BPA 引起的生殖系统损伤与表观遗传学有关。 表观遗传学是指在细胞和DNA 序列不改变的情况下, 基因发生可逆的改变[24]。 在BPA 对表观遗传学影响的研究中, 对DNA 甲基化、 组蛋白修饰、非编码RNA 等方面的研究较多。
2.1 DNA 甲基化 DNA 甲基化是由DNA 甲基化酶介导的一种化学修饰作用。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DNA 甲基化主要过程是: S-腺苷甲硫氨酸分子中的甲基通过DNA 甲基转移酶的作用转移到序列中CpG 二核苷酸内胞嘧啶的第5′碳原子上[25]。 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 DNA 双链中CpG 的含量趋于减少并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 一种是散在的CpG, 一般情况下处于高甲基化状态, 另一种是CpG 岛, 主要存在于基因的启动子和外显子区域中, 一般情况下处于低甲基化状态[26]。 在胎儿发育过程中, DNA 甲基化是调控基因表达的主要遗传机制[27]。 Ma 等[28]对围产期大鼠进行50 μg/ (kg·d)的染毒并对雄性后代检测后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BPA 染毒组肝整体DNA 甲基化程度降低, 血清胰岛素和胰岛素抵抗指数增加, 且肝脏葡萄糖激酶基因的表达量减少而其启动子甲基化程度增高,由此提示围产期BPA 暴露导致了胰岛素抵抗, 进而导致肝组织DNA 甲基化异常。 这些发现支持了表观遗传学在围产期BPA 诱导的代谢紊乱在胎儿重排中的潜在影响。 Doshi 等[29]的研究发现, BPA暴露可导致睾丸内雌激素受体ERα 和ERβ DNA启动子区甲基化异常, 其可能是BPA 暴露对精子发生和生育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机制之一。
2.2 组蛋白修饰 组蛋白修饰主要是指组成核小体的组蛋白N 端尾部氨基酸的修饰, 包括甲基化、乙酰化、 泛素化、 磷酸化等。 这些修饰使染色质结构浓缩或松散, 进而调控基因的沉默或表达[30]。有研究发现胚胎期BPA 暴露影响了出生后雄性仔鼠海马中的总组蛋白乙酰化酶的含量, 其蛋白表达量显著升高; 还影响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表达, 使HDAC1 及HDAC3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HDAC2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BPA 暴露还导致H3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 及乙酰化组蛋白H3 (Ac-H3)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31]。 李玉华[11]研究发现, 50 μg/kg BPA 暴露能引起子代小鼠精子中组蛋白H3K9Me3 水平下降, H3K27Me3、 H3K36Me3 水平显著升高, 表明BPA 通过引起小鼠精子组蛋白甲基化水平改变,从而对小鼠生精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李玉华等[32]的另一项研究中探讨了BPA 暴露对小鼠精原干细胞C18-4 的表观遗传机制的影响, 发现10-5mol/L BPA 暴露能引起C18-4 细胞中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 和Setd2 mRNA 的表达水平下降, 相应地,H3K27Me3 和H3K36Me3 的表达水平也显著下降。组蛋白修饰与DNA 甲基化通过联合作用来调控基因表达, 如组蛋白甲基化与DNA 甲基化结合, 加强对基因活性的抑制[33-34]。
2.3 非编码RNA 大量研究表明, miRNAs 在生物体生长、 分化、 发育、 免疫, 以及凋亡等各项生命活动中具有重要的调控意义[35]。 Zhang 等[36]研究了在新生儿、 成年人(25 岁) 和老年人(75岁) 3 个不同时期附睾中miRNAs 的表达情况, 发现新生儿、 成年人和老年人附睾中各有251、 109和125 种miRNAs 表达, 说明miRNAs 在雄性生殖发育的不同时期均起到调控作用。 有研究发现BPA 暴露可显著诱导小鼠睾丸间质细胞中miR-146a-5p的表达, 升高的miR-146a-5p 加剧了BPA 对睾丸类固醇生成的有害影响, miR-146a-5p是唯一经研究证实的在BPA 染毒后细胞和组织中被表达量显著上调的miRNA[37]。 马林[38]通过微阵列芯片分析技术, 筛选孕期BPA 暴露后雄性子代睾丸中差异表达的miRNAs, 与对照组比较, 0.05 mg/kg 剂量组有171 个miRNAs 上调和124 个miRNAs下调; 5 mg/kg 剂量组有133 个miRNAs 上调及136 个miRNAs 下调。 马林等[39]进一步对差异表达的miR-203-3p 进行了功能验证, 发现BPA (1 000 μmol/L) 暴露可导致小鼠睾丸间质细胞(TM3) 的细胞活力降低, 细胞凋亡率增加,并导致miR-203-3p 表达降低, 表明BPA 暴露可能通过影响miR-203-3p 的表达进而对TM3 细胞活力及凋亡情况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BPA 暴露对于雄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殖器官的发育异常, 导致睾丸等脏器系数及精子数下降, 活动精子百分率下降,精子畸形率增高等。 BPA 还能引起雄性体内性激素分泌异常, 进而导致生殖系统损伤。 BPA 可通过DNA 甲基化、 组蛋白修饰、 miRNAs 等表观遗传机制对雄性生殖系统发育产生影响, 但具体机制仍不十分清楚,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技术发展及运用,从非编码RNA 的角度研究BPA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机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