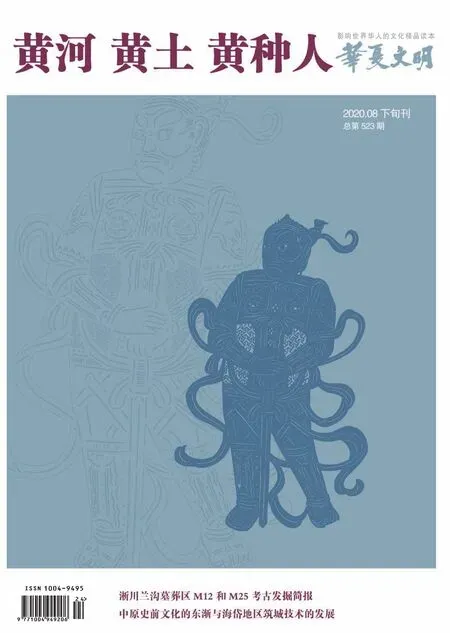中原史前文化的东渐与海岱地区筑城技术的发展
2020-12-25曹凌子郭崇文
曹凌子 郭崇文
截至2020 年年初,中国境内已发现史前有垣城邑逾百座,主要分布于北方、中原、海岱、巴蜀、江汉、太湖等六大史前文化区。 其中,中原、海岱两区经由考古工作证实的史前城邑数量较多,规划布局、筑城技术等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甚至一定程度先进性①这里所谓“先进性”是相对而言,毕竟“北方模式”“南方模式”城邑所处宏观自然环境、微观自然环境与“中原模式”城邑存在差异。的态势, 已有学者对史前城邑筑城技术给予过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别的专题关注[1]。 然而,就已刊文献而言,从文化交流、文化因素传播视角专门考量中原地区先民对海岱地区先民史前筑城技术影响的探讨为数偏少。 作为史前社会复杂化与早期文明化进程中重要的物化载体之一, 围垣城邑及其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有鉴于此,我们拟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因素东渐的视角对这两大文化区围垣城邑乃至其他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围垣城址筑城技术概览
就已有考古发现来看, 中原地区史前围垣城邑计15 处共16 座, 其中属于仰韶时代后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下王岗类型的有2处,分别为郑州西山[2]、淅川龙山岗[3];属于龙山时代后期陶寺文化的有山西襄汾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4],王湾三期文化的有博爱西金城[5]、温县徐堡[6]、登封王城岗[7]、新密古城寨[8]、新密新砦[9]、平顶山蒲城店[10]、郾城郝家台[11],后岗二期文化的有河南濮阳戚城[12]、濮阳高城[13]、安阳后岗[14]、辉县孟庄[15],造律台文化的有淮阳平粮台[16],合计13 处14 座。 也有学者曾将新郑人和寨聚落视作龙山时代城邑组成[17],但限于材料公开程度,所出器物指向的该城邑年代与新砦文化的关联似乎并不能排除,故本文暂未将该城列入其中。
海岱地区史前围垣城邑有25 处26 座,其中属于或可能属于龙山时代前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有5 处,分别为山东济南焦家[18]、滕州西康留[19]、五莲丹土[20]、日照尧王城[21],安徽固镇垓下[22];属于龙山时代后期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的有20 处共21 座, 分别为山东阳谷景阳岗[23]、茌平教场铺[24]、阳谷王家庄、阳谷皇姑冢、茌平尚庄、茌平乐平铺、茌平大尉、东阿王集[25]、东阿前赵[26]、济南城子崖[27]、邹平丁公[28]、淄博桐林[29]、寿光边线王[30]、五莲丹土龙山早期城、五莲丹土龙山中期城、日照两城镇[31]、日照尧王城、费县防故城[32]、沂源东安故城[33]、滕州庄里西[34],江苏连云港藤花落[35]。 其中个别城邑年代或许更早, 如地处鲁北地区的焦家被认为可能始建于仰韶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遗址之中,以教场铺聚落为代表的鲁西北几处聚落作为城邑的可能性在考古学界尚存歧见①承认或否定景阳岗以外鲁西北地区上述聚落为城的学者兼而有之,此处仅以张学海、孙波先生观点为例引用。,[36],本文虽暂从其属于城邑的旧识, 但也认为其性质究竟如何仍需留待将来更为深入、 系统的考古证据加以验证。 此外,新近发现的滕州西孟庄遗址海岱龙山文化小型围墙[37]的发现,似乎为该区史前聚落考古探研提供了新证, 但从现阶段材料来看, 其作为城的可能性似乎还很难得到学界公认。
除上述存在墙垣的城邑外, 这两大文化区都存在一定数量的环壕聚落。 据不完全统计,单以龙山时代环壕为例,中原地区如郑州大河村、禹州瓦店、汝州煤山、舞钢大杜庄、方城平高台、 信阳孙寨等, 海岱地区如招远老店、平度逄家庄、青岛南营、日照苏家村、日照大桃园、临朐西朱封、桓台李寨、桓台后埠等,可能在当时社会中发挥着高于普通聚落的作用。 早于龙山时代的仰韶时代环壕聚落乃至裴李岗时代环壕聚落在当时聚落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也与不存在相关圈围设施的聚落有差异。 笔者并不否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环壕聚落作为城邑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并认为同时存在环壕及围垣的城邑建筑技术有综合审视的必要, 但由于这些仅存环壕设施的聚落不存在城垣这种可以作为地方特色标志的物化载体,在讨论筑城技术时,本文暂予搁置, 单取城垣为证说之。 待将来条件成熟时,或可另文专论环壕相关议题。
就筑城技术视角而言,城壕、城门及其他相关附属设施系这两区乃至其他文化区共有之现象, 存在特殊性、 区域性的可能相对较小,而墙基的处理方式、城垣主体的建筑方式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区域文化因素来看待和比对分析。
在墙基处理方式上, 中原地区存在基槽的城址有西山、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王城岗、新砦、古城寨、郝家台、孟庄等,平地起建城相对较少,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另有两三处城垣,囿于材料公布程度,虽暂不详知其是否存在基槽等设施, 但其作为基槽城的可能性尚不能被轻易排除; 海岱地区除藤花落可能存在基槽外, 其余城址皆为平地起建[38]。就城垣主体的建筑技术来看,中原地区版筑城有西山、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王城岗、古城寨、郝家台、平粮台、戚城、孟庄,夯筑城有龙山岗、徐堡、新砦(不排除存在版筑因素的可能)、蒲城店、高城、后岗,堆筑抑或“拍筑”城有西金城,版筑比例最高,夯筑次之,仅使用堆筑一种技术的罕见;在既往材料中,海岱地区较为明确的版筑城仅景阳岗、藤花落2 处,庄里西可能存在版筑技术因素;近年新发掘的焦家城也存在版筑证据,可能使用夯筑技术的城有城子崖等几处,余者皆为堆筑城,堆筑城比例最高,夯筑城次之,版筑城占比最低。
综上,中原、海岱二区皆为土城,因其在城墙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性而被合称为史前城邑的“中原模式”[39]。 与长江流域等区的史前城垣相较, 中原与海岱地区的建筑技术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复杂, 是先民基于当地既有自然环境的文化适应策略,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相关文化区内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总的来看,两区都存在堆筑、夯筑及版筑城垣,但与海岱地区相较,中原地区多为基槽式城垣, 版筑—夯筑的复杂技术使用率高。 在上述筑城技术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新近有学者认为, 以狭义中原地区为代表的这种最复杂、 可能更为先进的筑城技术可称为“中原模式”下的“河洛亚模式”,海岱地区这种次复杂、 可能也具有一定进步性因素的筑城技术则被称作“中原模式”下的“海岱亚模式”[40]。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区之间筑城技术的差异性除来自文化与社会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仍在于自然环境。长江流域诸文化区、 北方文化区土壤等自然资源与“河洛亚模式” 所指向的狭义中原地区、“海岱亚模式” 所代表的海岱地区的确存在显著差异。 即便中原、海岱二区之间的土壤等一系列自然因素也存在差异。
二、史前时期中原文化东渐与海岱文化西进的大势扫描
作为中国史前黄淮流域的两大文化区,中原与海岱地区地理位置相近、 生态环境相似, 至迟自裴李岗时代起已开始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就狭义的史前阶段(下限在龙山时代,广义的“史前”或可包括二里头时代)来看,这种双向的交流到仰韶时代显著增多,龙山时代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了仰韶时代中期以来的强化交流态势。 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认为, 中原文明的最终形成离不开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贡献, 海岱地区早期文明中也不乏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因素。 鉴于诸多考古学研究者曾对黄淮流域这两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做过考古学视域下的文化因素分析考察,既有研究已然鞭辟入里,在中原、海岱两大史前文化区交往联络大势已渐趋清晰的学术背景下, 可能即使基于新考古发现的文化因素比较分析也难脱其范式。 故而本部分拟对此前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作学术史视域下研究综述式的梳理, 一则借以熟悉两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演变态势, 二则通过研究史的回顾管窥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路、心路历程,三则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假说。
(一)两区裴李岗时代文化关联
裴李岗时代,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兴盛,分布范围遍及河南省域, 后李文化在山东核心区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发展态势, 一改李家沟时代各自所在文化区的居址分布态势甚至文化发展程度。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较早参与过裴李岗文化知名遗址发掘、 对裴李岗文化研究有卓越贡献的李友谋先生较早关注裴李岗文化在所处时代的领先性问题, 通过对年代、发展水平及影响力的对比,李先生得出了裴李岗文化领先于磁山和老官台文化、在华北地区领先的观点[41]。 虽未直接涉及同时代今河南与山东地区的对比, 但裴李岗文化的发展程度可见一斑。 20 世纪90 年代,学界对这两支文化皆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 栾丰实先生在对后李文化的专题研究中, 认为两者在文化发展早中期,曾“缺乏人员接触和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偏晚阶段,裴李岗文化先民又东进至此, 使得当地文化面貌改变不小[42]。 进入21 世纪,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与材料的逐渐发表, 学界对两者间的文化关联思考更多。 譬如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若干裴李岗文化因素在其末期传入海岱地区,促使北辛文化的形成[43]。 另据靳松安先生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所做的文化分析, 后李文化的小口壶、个别侈口罐、乳足钵等器物皆系裴李岗文化影响的结果[44]134-135。 此后,在纪念裴李岗文化发现3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先生的文章也涉及二者关联。 例如,赵世刚先生据遗物遗迹论及二者时, 认为后李文化不但不可能对裴李岗文化产生影响, 反而受到了后者影响[45];栾丰实先生论及裴李岗文化与东方地区诸文化的关联时, 认为后李文化受其影响更多一些, 并重申了裴李岗文化对北辛文化的影响[46];鉴于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力,张松林先生提出“裴李岗文化时代”的概念[47],与栾先生既往提出的“裴李岗时代”[48]遥相呼应。靳松安先生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也曾专设裴李岗文化的领先性一节, 启发研究生检索资料并在文化因素分析基础上判断裴李岗文化的成就及其影响。 上述数例,远非学界前辈及后学对裴李岗文化与后李文化交往关系关注、研究之全部,但裴李岗文化对后李文化的影响及其在所处时代局部区域内的影响力已可见一斑。
单就裴李岗文化、 后李文化二者的彼此关联甚或文化交流而言, 这一阶段似以裴李岗文化对后李文化的影响为主。 至迟在裴李岗文化末期可能已经存在人群往东等方向的迁徙,合力促成了诚如韩建业先生所言的“黄河流域文化区”乃至“雏形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49]。
(二)两区仰韶时代的文化关联
仰韶时代, 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仰韶文化早、中、晚期,海岱地区则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期为代表。 在这一并不短暂的时间范围内, 两地之间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渐次加深。 从文化发展进程来看,仰韶时代前期、中期,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早期发展程度可能未及仰韶文化,似以中原对海岱地区的影响略占优势,到仰韶时代后期, 随着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强势发展, 两者间的交流以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强势影响为主[50]。
据栾丰实先生的文化因素分析, 北辛文化的鼎、小口双耳罐、三足钵等一系列器物皆是中原地区前一时期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因素,可在裴李岗文化中找到原型;即使到了更晚的大汶口文化,以獐牙、猪牙、龟甲等随葬的习俗亦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人有着较高的相似性[51]。 这些文化因素很可能皆系裴李岗文化及其余波影响的结果。 韩建业先生则认为, 北辛文化中的裴李岗文化因素并非直接来自裴李岗文化本身, 而是经由双墩文化这一媒介传入海岱地区的[52]。 此外,鉴于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外向态势, 韩建业先生提出了“庙底沟时代”[53]的命名。 虽然学界对北辛文化受裴李岗文化影响的模式或路径的问题尚存歧见, 但北辛文化乃至后续大汶口文化中若干与裴李岗文化相似的因素确系较为明显的现象。
就同时代文化因素的互动来看, 靳松安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作了系统且翔实的对比研究,北辛文化的小头球腹壶、大口圜底缸、彩陶装饰等都是明确的仰韶文化因素,可能与仰韶文化的影响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仰韶文化的三足釜等若干器物则系北辛文化因素或其变体。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钵、矮领罐、网纹彩陶罐等器物、彩陶等装饰可能来自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长颈壶、盆形鼎、部分折腹器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影响有关,此外,后者的背壶、部分尊或尊形器、豆等已经进入中原地区[44]135-155。
此外,何德亮先生研究显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弧线勾连纹、白衣花瓣纹、八角形图案的技法与仰韶文化相似, 可能是在后者影响下形成的[54]。 随着仰韶文化逐渐衰落,大汶口文化崛起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文化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 据杜金鹏先生研究,至迟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 中原地区的局部已被西进的大汶口人占据, 发展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55]。
(三)两区龙山时代的文化关联
龙山时代, 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态势进一步强化。 龙山时代前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强势崛起,发展势头强劲,中原地区进入了蓄势待发的庙底沟二期文化、 大河村五期文化阶段。 这两个地区间的交流在某些方面可能仍是海岱文化占据优势地位。
赵芝荃等先生认为, 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仰韶文化、 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影响较为突出[56]。 仍据靳松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的袋足鬶、平底尊、 部分杯具等一系列因素皆来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深腹罐、部分带流器等则可能与中原的影响有关[44]156-163。诚如张翔宇先生所言, 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不但促进了不同地区先民的融合, 而且为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7]。
龙山时代后期,随着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等文化所指向社群的强势崛起, 中原地区一度恢复了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外向态势, 但根据现有考古记录, 同时期的海岱龙山文化也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二者间的交流大致处于相对而言较为平等、互有往来的状态。 如学界长期争讼未休的造律台文化/类型或王油坊文化/类型究竟属于中原文化传统还是海岱文化传统,还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双向文化因素相互杂糅问题[58],或许正是二者你来我往、频密交流的反映。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初, 靳桂云先生在论及海岱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与后岗二期文化关系时, 曾注意到二者在差异性以外的相似性[59]。 栾丰实先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二者的交往中, 海岱龙山文化对后岗二期文化的影响是主要的,受后者的影响是次要的[60]。 张富祥先生则认为, 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互影响,并举了素面鬲、建筑、冶铜技术等实例[61]。 靳松安先生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综合考察了两区文化的问题, 认为王湾三期文化、 后岗二期文化、 造律台文化中的折盘豆、直领瓮、子母口器物等可能与海岱龙山文化甚至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有关, 而海岱龙山文化中的夹砂深腹罐、甗、白灰面房屋等则可能是中原龙山诸文化影响的产物[44]156-177。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梳理难称全面,但已可大致管窥这两大文化区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关联及其互动态势。 虽然不同学者研究篇幅、关注重点甚至立场可能存异, 但其基于文化因素的分析是两区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益于学者们的既有研究,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交流乃至融合的趋势愈加明显地呈现于学界乃至公众面前。 二者之间尤其是文化接壤地带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态, 直至二里头时代后期,豫东、鲁西南等地的岳石文化面貌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来自豫西、豫中、豫北乃至冀南等地的因素[62]。
(四)“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的形成
无独有偶, 除上述以陶器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外, 古代文献史料中也有相关线索。 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帝王世纪》称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①有研究认为,风后即东夷中风夷的首领,参见程有为2006 年2 月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动与汉民族的形成》。;《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舜耕历山,渔雷泽,淘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东巡狩, 至于岱宗”,《史记·五帝本纪》又云“舜……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倘若这些记载有一定合理性因素甚或确如部分学者所言乃早期族群的历史记忆[63],或可认为其系史前时期中原与东夷族群存在密切联系的反映。 前辈学者考证典籍后,得出了夷夏族人因混合而文化发展的结论[64],甚至认为这一阶段的华夏与东夷民族可能已结成部落联盟[65]。 将这些证据与考古学文化现象结合起来观之,二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互证的可能。 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有考古发现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书写史前史的条件,史前史的证据主要应从考古发现中找寻,不宜在文献史料甚或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硬套考古记录。
总的来看,与其他文化区相比,中原、海岱两区史前考古工作开始比较早, 发掘遗址比较多,就大的尺度而言,考古学文化序列较为完整,各时期文化面貌相对清晰,为两地不同时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从大的地理条件来看, 两地具有相似的生态环境,生业经济也有相似的演进模式[66],农业复杂化进程在时代的尺度上大致呈同步态势,文化演进过程具有相似性、相关性。 至迟从裴李岗时代起, 二者之间已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交流。 在后续的历史演进中,这两个地区联系紧密、相互渗透、彼此影响,“黄河流域文化区”逐渐形成并巩固发展,进而促使“文化上早期中国”[67]的态势更加明朗。
当然, 二者间的交流与融合建立在彼此发展的基础上。 从长远来看,二者曾存在过共同繁荣的时期, 但在交流中的主从关系上也一度呈现出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互通有无、你来我往的态势, 两地史前先民在竞争中交流,在融合中发展。 在中、东部地区史前考古工作视域下, 在已有考古记录尤其龙山时代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 或可将关系密切的中原、海岱两大史前文化区合称为“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甚至“中原—海岱史前文化共同体”。 在这一动态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 吸收对方的有利文化因素为我所用, 为彼此的文化发展注入了盎然生机与不竭动力, 最终促进了双方文化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向前发展。 筑城技术的传播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切面, 在双方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可能是两大区域史前先民之间交流与互动的重要产物。 石器时代以来这两大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态势到青铜时代前期继续发展,并已结成得到学界相对比较认可的“联盟”[68]关系。 因此,则龙山时代甚至更早即已生根萌芽的 “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 对二里头—二里岗时代商夷联盟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文化、历史乃至心理基础。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因素东渐的两种模式
从地理形势来看,地处黄淮流域的中原、海岱地区大部属于平原、丘陵地带,二者彼此之间不存在崇山峻岭等难以逾越的交通阻隔。 前已述及,就二者之间的交流而言,以互动为主,部分时段海岱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部分时段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势位置。 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互动的反映,其表现形式有人群迁徙、贸易、战争,等等。 在这一漫长的双向互动过程中, 可能既有中原先民的东进,也有海岱先民的西迁。
在中原先民东进、 海岱先民西迁这两种可能的模式作用下, 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渐东向扩展。 据前所梳理,文化因素分析所显示的文化间交流或许表明, 自裴李岗时代以来, 中原地区先民可能已开始了向东迁徙的历程,不断把中原文化因素带入海岱地区,在这种跨区域横向、 跨时代纵向的文化接力过程中, 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中逐渐增加了前一时代或同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认为, 中原先民东进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因素或许是中原文化东渐的主要模式。 除此之外,海岱先民西迁对海岱地区文化面貌的转变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类型学分析与聚落考古研究结果显示, 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海岱地区人群的西迁愈加频繁,规模亦远胜于前[69]。 虽不排除这些西迁的海岱族人在进入中原地区后有留在当地定居者, 也可能有短暂避难或强势入侵后再返回海岱地区者, 他们无形之中起到了二区之间文化传播使者的作用。
(二)文化交流载体的多元化
一般情况下, 两种都存在一定发展程度的文化间交流是双向的。 同理,就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而言,也往往是多样的,几乎不存在只传播一种文化因素的交流。 以史前食物全物化进程为例,既有中国起源的粟、黍等粟类作物的西传, 也有西亚起源的小麦等麦类作物的东进。 此外,不同地区独立起源的家养动物猪、狗、牛、羊等也逐渐融合到同一文化中[70]。 又如青铜时代全球化或青铜时代世界体系[71]的形成,除上述食物的多向传播与交融外,还存在以青铜冶炼为主的冶金术、土坯建筑技术甚至思想观念等精神世界因素的跨区域双向乃至多向交流。
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也是如此,除上述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具、生业工具外,也有诸如“白灰面”房屋建筑方式的交流。此外,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小麦等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青铜工具与青铜铸造技术等也很可能是这两个文化区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或物化表现形式。 精神观念方面的交流也有为数不少的证据, 譬如筑城过程中的人骨、兽骨祭祀坑,在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不少史前城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有所发现,这些行为应是特殊信仰观念的反映,在今后的城邑考古尤其城垣及其相关建筑技术的研究中应对这些现象予以更多关注。
多种形式的载体在文化间的交流中相继(明显不同时代)或打包(大致同时)进入另一文化区, 体现的正是文化交流中多元化的交往方式和表现形式。 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交流中,筑城技术作为集物质、技术、观念、认知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表现形式, 无疑是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两区文化与社会发展、 经济与技术进步的一定写照。
(三)中原史前筑城技术对海岱地区影响
就已有考古工作来看, 中原地区对海岱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影响, 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较为明朗的物化形式。 前已述及,至迟自裴李岗时代起, 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不断东渐,经庙底沟时代的强势发展,仰韶时代后期—龙山时代前期进入了短暂的低谷,到龙山时代后期又迎来了新的高峰。 多种文化因素进入海岱地区, 对当地文化面貌的形成和改变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另外,中原地区史前围垣城邑最早者在绝对年代上早于海岱地区最早者,技术上也可能领先于海岱地区。 一般情况下, 时代早的因素会对晚一些的文化有影响, 发展程度高的文化对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①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高度的发达性与领先性,但就筑城技术而言,若认为版筑技术复杂程度高于普通夯筑,普通夯筑技术复杂程度高于堆筑,则其确实较中原地区落后。的影响也要更大一些。
中原地区占据数量优势的基槽式技术、版筑技术在海岱地区相对少见甚或罕见,甚至并未出现于海岱地区的文化核心地带。 在焦家遗址新证公布之前, 我们曾认为海岱地区至早在龙山时代后期的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偏晚阶段甚至龙山文化中期才出现了版筑城垣,不但在时代上远晚于中原地区,而且在数量上也远少于中原地区。 孙波先生过去曾较为明确地提过海岱地区版筑等先进筑城技术受到中原地区影响的观点[72],近期又重申了此种认识[73]。 随着这两大文化区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 这一论点的支撑性证据一度愈加明显, 唯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城垣的新证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 然而,仅就焦家一处城垣的考古发现,尚不足以推翻既往认识。 在现阶段考古记录的基础上, 或仍可认为城垣版筑技术、 基槽技术有可能且很有可能系中原史前文化因素东传进入海岱地区的产物。
四、结语
本文以中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东向传播为视角,探讨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进筑城技术对海岱地区城邑建设的可能性影响。 “中原模式”史前城邑中的“河洛亚模式”“海岱亚模式”城址作为史前土筑城垣高技术、高复杂性的代表,在早期文明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原地区史前的基槽、版筑技术相对而言较为进步,对海岱地区筑城技术的发展可能起到了较为重要的影响。除筑城技术以外,这两大文化区史前先民在其他技术、经济、观念甚至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为广泛且深入的交流。 随着今后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与重复验证,若无挑战性、反对性材料出现,我们或可暂时将关系密切的中原、海岱两大史前文化区合并称为“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甚或在有更多证据支撑的基础上称其为“中原—海岱史前文化共同体”。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以大的时代概念为尺度的分析模式只是相对共时的比较,与考古研究尤其聚落考古中的“共时性”[74]概念尚存较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结论的确凿性。 本文所提的假说可能仅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犹待更多发现、更多证据加以检验,至少现阶段的考古记录并不足以使其具有排他性。譬如,过去有学者曾提出中原地区部分城址系大汶口文化人群筑造或受东夷集团侵扰而出现的不同见解[75],就可能不失为另一种极具合理成分的有益解读。此外,来自自然环境的差异乃至个别发掘者对海岱区史前城垣技术公布不详甚至不确切等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对本文所提假说存在一定冲击。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继续开展与城市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的认识或将更加清晰。
五、后记
近年来, 随着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阶段至晚期城的发现与材料的逐步公开, 海岱龙山文化的筑城技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可以在该文化区内部向前追溯的可能性迹象。 尽管如此,似乎也未能完全排除中原地区史前城邑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复杂且进步的技术对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甚至后一阶段二里头时代, 如岳石文化城垣乃至其他建筑技术影响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本文中, 我们未能将城垣与其他相关文化因素诸如城垣附属建筑、城壕、台基、房屋、灰坑、窖穴、 墓葬等一系列遗迹尤其是房屋的建筑方式予以综合考察, 这也使得现阶段的推论仍处于假说甚至很大程度上属于假说的状态,故此本文的初步认识可能仍难免失于片面,将来或可另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