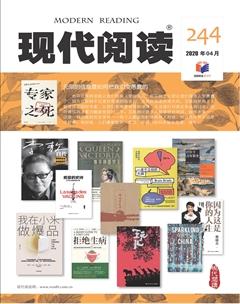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伟大友情
2020-12-24刘仕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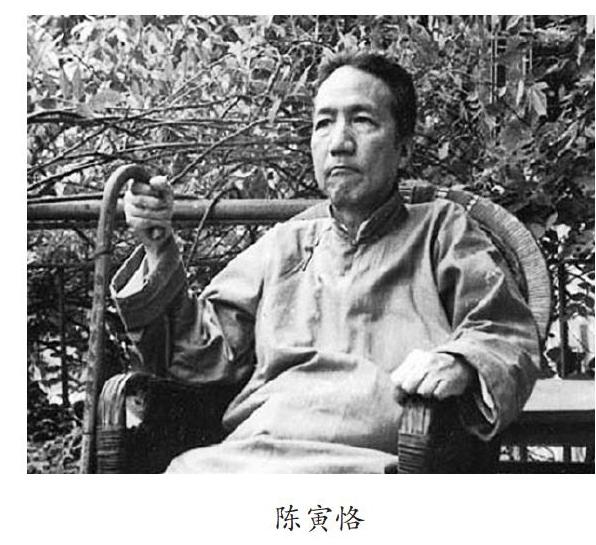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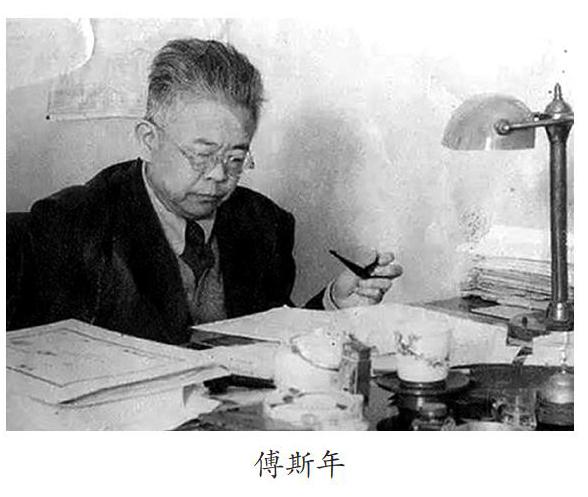
当陈寅恪与傅斯年相遇,便奏出了中国现代学术最动听的乐章。古人有闻弦而知心,陈寅恪与傅斯年则是携手共谱华章,相互砥砺,在学术之途上肝胆相照,共历风雨。
陈寅恪和傅斯年相识在1915年的春天,当时,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班读书,而陈寅恪也正是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两人由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认识。但由于这次的相识比较普通,只是一次简单的见面而已,所以两人并没有太多的留意,也没有预料到几年后两人竟然会在异国他乡再次相逢,自然,他们也不会知道,两人以后将会携手为复兴汉学而努力。
1923年的秋天,傅斯年离开英国去德国的柏林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意外地碰到同样正在这里学习的陈寅恪,异国他乡遇到同胞,再加上两人原本相识,这是怎样的缘分!两人都因此感到异常的兴奋,这次相遇后,两人便经常联系。
随着交往的深入,傅斯年渐渐发现了在陈寅恪身上蕴含的惊天的才华,陈寅恪的学识以及他对历史的看法与熟悉,无一不让傅斯年诚心拜服。
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将学习的方向转变到了比较文学语言和东方语言这一块上来,两人相互促进学习,在学术之道上有了首次的默契与合作。
后来,两人相继回国,但回国后两人一南一北,接触并不多。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更是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享誉天下。傅斯年则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学,重新开创了南方的学术风气,被胡适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后来两人再次在学术上合作是在1928年。
1928年,傅斯年领命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彼时,他也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之初,傅斯年就明确表示要与日本以及法国的汉学一较高下,并定下了要将汉学的研究中心从日本、法国转移到中国来的目标。
目标有了,接下来就是行动。凭傅斯年一人之力毕竟不够,此时正是需要大量的优质人才和学者的时候。这时候傅斯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寅恪。
早在德国留学时,傅斯年便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傅斯年曾说:“在德国有两位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正式给陈寅恪写信,希望将陈寅恪请到研究所,共同编辑和整理汉学史学资料。
陈寅恪同意了该聘请。于是,时隔多年,两位学术界的巨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是历史性的合作。
陈寅恪不能马上赶到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们靠书信往来商量如何更好地发展历史语言研究所。
首先,傅斯年通过书信往来和陈寅恪商议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事宜,后在1928年10月至1929年5月期间,陈寅恪多次写信给傅斯年商议研究所在北平分所地址的事情。根据傅斯年在信中指示,在原拟划拨的故宫博物院的房屋索之未得之后,陈寅恪看中了北海静心斋的一处房屋,但是直到3月,歷史语言研究所分所房屋的问题依旧还是没能解决好。于是,陈寅恪又给傅斯年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陈寅恪主要向傅斯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寄存在天津一处房屋内部分档案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关于研究所在北平的分址问题。
信中内容,陈寅恪皆是在评道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事情,虽然语句平淡,可是从中却能深深地体味到陈寅恪内心的一种焦灼之感。这种焦灼的感觉源自于对历史档案的珍惜,对学术,对史学研究的热爱和专注。
后来,内阁大库中的历史档案和资料终于被他们买下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有了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大师的联手,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首先就是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培养了非常多的学术人才,其中不乏大家,如赵元任、胡厚宣等。另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对明清档案的搜索、整理,在清朝大库存着非常多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第一手的,最贴近历史,非常珍贵。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使它们能够再现于世,功劳非常大。
此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迁了好几个地方,上海、长沙、昆明……当其迁到昆明的时候,陈寅恪与傅斯年终于再度相见了。此时,陈寅恪和他的家人一起住进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租赁的宿舍里。
其时,陈寅恪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昆明也是战乱四起,经常受到日军的轰炸。1937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痛惜国土沦陷,绝食而死。陈寅恪为父亲守灵时,因悲痛和频繁接待宾客,诱发了视网膜脱离,右眼尤其严重,已经不能视物了。医生告诉陈寅恪,他的眼睛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好的,但做完手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修养。思前想后,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放弃治疗则意味着陈寅恪的右眼就彻底坏掉了。他将这件事瞒着家人,继续用并不是完全健康的左眼工作。
在昆明的那段日子里,陈寅恪因为视力原因,行动非常不便利。日军轰炸时,所有的人都跑去躲到防空洞里,每每这时,傅斯年便会匆忙地逆着人群跑到楼上,跑到陈寅恪居住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把陈寅恪送到防空洞里,然后才安心地躲起来。
1939年,陈寅恪想去牛津大学讲授汉学课程,后来由于战争原因返回了西南联大。1940年,傅斯年写信给陈寅恪,希望陈寅恪能到四川任职。
陈寅恪当时也处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他已经身无分文,即使他十分乐意答应傅斯年的请求,却连路费也没有。万般无奈,陈寅恪只好给好友傅斯年写信,说明了自己的困境,傅斯年得知情况后,立即筹款寄给了他。
好事多磨,陈寅恪还没有收到筹款,日军就攻到了香港,香港沦陷,而陈寅恪的生活也陷入了绝望之中。后来几经辗转,陈寅恪进入了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拒绝了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大陆的企图,接受了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的邀请来到了岭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任教。这时的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了,生活、授课都极为不便,需要别人的帮助。
后来陈寅恪在清华园任教,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校长梅贻琦希望陈寅恪能够休息一段时间,陈寅恪拒绝了梅校长的提议,他坚决地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傅斯年是一位百年难见的学术大师。当时傅斯年教导青年“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这充分说明了傅先生的高瞻远瞩,他越来越看到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深刻地明白,古文才是立身之本,所以一定要学好古文。
他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更致力于建立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他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一直到其去世,这期间,他对中国学术作出的贡献实在不可斗量。
抗战胜利后,两位大师的情况稍微好转,可是不久,陈寅恪辗转多次到了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而傅斯年则带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到了台湾,到达台湾后的傅斯年不久就去世了。得知消息的陈寅恪悲痛不已,两人相交的几十年里,他们交流学术,在无数困境面前相互扶持,早已成为患难之交。所以,当其中一方溘然去世时,另一个人又怎能不悲痛欲绝?
傅斯年死后,陈寅恪写了一首诗以示悼念:
不生不死最堪伤,
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
霜红一枕已沧桑。
1969年,陈寅恪在痛病和折磨的双重痛苦中孤独地死去。这两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晚年的时候,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始终没有再见一面。
(摘自石油工业出版社《高山流水遇知音》 作者:刘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