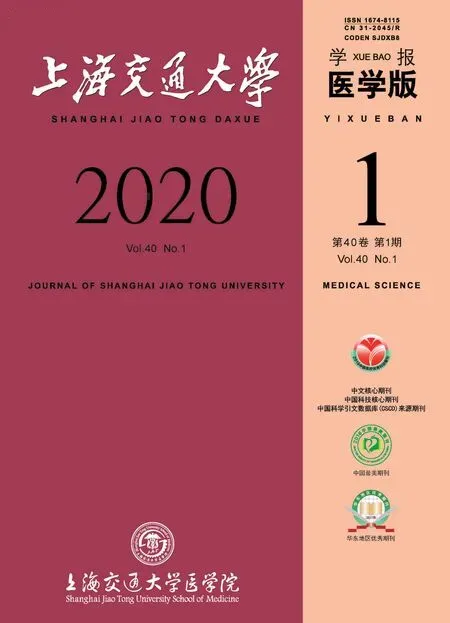单核-巨噬细胞在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2020-12-23安晓宁陈永熙
安晓宁,陈永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内科,上海 200025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s,AAV)是一类累及全身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小血管壁的炎症及纤维素样坏死为主要病理特征。在AAV患者中,ANCA致病靶抗原主要为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和蛋白酶3(proteinase 3,PR3),在中性粒细胞初级颗粒和单核细胞过氧化物酶阳性的颗粒中均有表达。除此之外,弹性蛋白酶、乳铁蛋白、阳离子蛋白及人溶酶体相关膜蛋白2与ANCA也存在反应性[1]。AAV包括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GPA)、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MPA)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EGPA)[2]。
AAV非罕见病,其发病与遗传、感染、药物等多种因素有关。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显示AAV与遗传因素有关[3-4],如PR3-ANCA血管炎发病主要与HLA-DP、PRTN3及SERPINA1等基因相关,而MPO-ANCA血管炎则与HLADQ多态性相关。此外,感染诱发的自身抗原互补肽和分子模拟[5-6]可在炎症状态下诱导ANCA产生。AAV在病变早期不典型,若未得到及时诊治,预后差且死亡率高。研究数据表明,AAV患者的5年存活率为75%左右[7-12]。传统理论认为AAV发病与中性粒细胞密切相关,研究[13-14]还表明单核 - 巨噬细胞在AAV的发病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单核 - 巨噬细胞在AAV发病中作用及可能机制进行综述,为进一步认识本病提供基础。
1 单核 - 巨噬细胞概述
1.1 单核细胞与巨噬细胞分类及特点
单核细胞发育自骨髓,在集落刺激因子作用下,进入外周血液循环,发育为成熟单核细胞。根据表面标志及其表达量的不同,发育结果亦有差异,在人体内根据表面分化抗原CD14和CD16分子表达强度的不同分为3类:经典型(CD14hiCD16neg/low)、中间型(CD14hiCD16hi)及非经典型(CD14lowCD16hi);而在小鼠体内,单核细胞的标志性分子为LY6C,LY6C高表达和LY6C低表达的单核细胞分别对应人单核细胞中的经典型和中间型[15]。人单核细胞中经典型占多数,在促炎反应和抗菌作用中起重要作用;中间型具有促炎作用,而非经典型具有血管巡视和抗病毒的功能。单核细胞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可分化为树突细胞或巨噬细胞,其中经典型单核细胞是树突细胞的主要来源,但所有的亚型都能分化为巨噬细胞[16]。
巨噬细胞是固有免疫的重要成分,属于髓系免疫细胞,位于全身各组织。根据激活方式,分为经典激活巨噬细胞(classic macrophage,M1巨噬细胞)和替代激活巨噬细胞(alternative macrophage,M2巨噬细胞)。M1巨噬细胞促进组织损伤,M2巨噬细胞则可促进组织修复。在刺激因子作用下,M2巨噬细胞又可分为M2a、M2b、M2c巨噬细胞3种亚型。巨噬细胞具有强大的吞噬功能,可吞噬内源或外源性致病物质,加工提呈抗原,同时分泌多种酶、细胞因子等,广泛参与抗感染、抗肿瘤、组织修复及免疫调节等。
1.2 单核细胞分化与巨噬细胞极化
CD14+及LY6C+单核细胞具有迁移能力。机体处于稳态环境时,单核细胞可不分化为巨噬或树突细胞而迁移到淋巴或非淋巴器官,同时转录模式发生改变。发生炎症或损伤时,单核细胞迁移活动显著增强,获得合成分泌炎症介质的能力,转变为巨噬细胞,称为炎症巨噬细胞。此外,多数组织在正常条件下同样存在巨噬细胞群体,在特定组织内具有特定名字,如库普弗细胞、肺泡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等。早期认为,这些组织特异性巨噬细胞由骨髓源性单核细胞发育而来;近来研究[17]表明,这些细胞起源于胚胎形成期,出生后主要通过自我更新维持细胞数量,其产生和维持与持续造血无关。
巨噬细胞极化是指巨噬细胞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点被激活,表现不同表型及功能,不同微环境可极化为不同表型和功能的巨噬细胞[18-20]。M1细胞可被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或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等细胞因子激活,释放多种致炎因子,如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IL-12、 精 氨 酸 酶 -1(arginase-1,Arg-1)等。Arg-1代谢可产生高水平的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M2细胞可由IL-1β、IL-13等因子刺激后产生,表达IL-1、IL-10、Arg-1、CD206、CD68、CD86、CD163、甘露糖受体等。根据刺激因子的不同,M2型细胞进一步分为多种亚型,包括IL-4或IL-13诱导的M2a,免疫复合物及部分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TLR)配体诱导的M2b,IL-10、糖皮质激素或开环甾体类激素诱导的M2c。
2 单核 - 巨噬细胞与AAV研究进展
2.1 单核细胞与AAV
2.1.1 单核细胞表达ANCA抗原 ANCA抗原不仅表达在中性粒细胞胞浆,也表达在单核细胞过氧化物酶阳性的溶酶体中[1];炎症时单核细胞抗原表达增加。体外研究[21]表明,用TNF-α刺激单核细胞,其表达MPO及PR3增加;用MPO-ANCA孵育单核细胞,裂解细胞后上清液中游离MPO减少,同时伴随膜表面MPO表达升高[22],说明在ANCA作用下胞浆内MPO向膜上转移。在3种单核细胞亚型中,中间型单核细胞较其他两型数量显著增加,MPO和PR3优先在中间型单核细胞中表达,表明中间型单核细胞在疾病进展中可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23]。
2.1.2 单核细胞参与AAV组织损伤及炎症反应 在体内,AAV患者单核细胞黏附分子表达增加[24];在体外,ANCA可刺激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IL-8、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及其他促炎因子的产生增加[21,25-26]。MPO-ANCA使单核细胞在LPS刺激下产生的IL-10水平下降[22];由于IL-10抗炎作用明确,提示ANCA可能通过减少抗炎IL-10分泌来促进炎症进展。动物实验[27]的结果也支持单核细胞参与AAV进程的观点,单核细胞耗竭及MPOANCA被动转移模型表明,单核细胞耗竭可显著减少肾脏肾小球坏死和新月体形成,并减少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在肾脏组织中的浸润。
2.1.3 ANCA刺激单核细胞效应 在ANCA刺激单核细胞释放IL-8的研究中,与完整的PR3-ANCA相比,Fab及F(ab')2不能诱导IL-8释放[25],提示Fc段在PR3-ANCA激活单核细胞释放IL-8中的重要性,这一结果与单核细胞Fcγ受体交联可诱导IL-8释放的研究结果一致[25,28]。在ANCA诱导单核细胞形成ROS的研究中,ANCA的F(ab')2段诱导单核细胞形成ROS的能力与完整ANCA相比无明显差异,而用Fcγ受体抗体预处理单核细胞后,ROS的形成下降[21],表明Fcγ交联在细胞激活中的重要性。然而,以上研究表明,F(ab')2在单核细胞激活中的作用存在争议。在AAV与TLR的研究中,AAV患者的单核细胞表达TLR2和TLR4的水平升高,而ANCA体外刺激正常单核细胞未见TLR表达的明显变化[29]。由于TLR信号通路在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提示AAV中单核细胞的激活可能与体内炎症有关,并通过TLR通路导致进一步损伤。
2.2 巨噬细胞与AAV
肾脏是AAV常见受累器官之一,在肾活检标本中可发现大量巨噬细胞浸润[30],且巨噬细胞主要浸润在肾小球中。这些结果表明巨噬细胞可能在肾损害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炎症肾组织中可检测到巨噬细胞增殖标志物,说明除炎症募集之外,细胞增殖也是造成局部巨噬细胞浸润的原因之一,炎症部位巨噬细胞增殖可能是损伤加重的重要机制[31]。
2.2.1 巨噬细胞释放MPO参与AAV组织损伤 单核细胞对ANCA有反应性,但巨噬细胞经ANCA作用无反应性。正常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有明确的抗MPO-ANCA和抗PR3-ANCA胞浆染色。而体外培养的单核细胞在分化为巨噬细胞时逐渐失去了与抗MPO-ANCA和抗PR3-ANCA的反应性[32]。肺泡巨噬细胞和腹腔巨噬细胞为成熟的组织巨噬细胞,二者均不与MPO-ANCA或PR3-ANCA反应。这些结果表明,ANCA只能与单核细胞直接相互作用,不能与成熟的巨噬细胞直接作用。可能在AAV早期,ANCA激活了单核细胞及早期巨噬细胞诱发炎症。
另一项关于MPO参与ANCA相关肾小球肾炎的研究显示肾组织中部分巨噬细胞表达释放MPO,通过CD68与染色质成分共定位证实了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阴性的胞外陷阱样结构为巨噬细胞来源,即巨噬细胞参与形成巨噬细胞胞外陷阱(macrophage extracellulartrap like structures,METs)[33]。MPO具有生物活性,对周围组织可产生氧化损伤[34],在ANCA被动诱导肾小球损伤的动物模型中,MPO敲除小鼠由于缺乏与ANCA相互作用的自身靶抗原,肾小球损伤明显减轻[35]。以上研究表明,由单核细胞分化而来的巨噬细胞仍可表达释放具有活性的MPO,但此时的MPO不再与ANCA反应,而是在胞外直接造成损害或通过形成METs参与损伤。
2.2.2 巨噬细胞极化与AAV 在AAV炎症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可极化为多种表型和功能不同的亚型,在AAV进展中发挥不同作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ory factor,M-CSF)是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生存分化的关键因子,研究[36]显示,抗MPO-ANCA通过增加M-CSF表达,促进单核细胞存活和向巨噬细胞分化,且CD206表达增加,表明巨噬细胞具有M2表型。新月体肾炎活动期,发现大量CD163+细胞,且CD163+细胞与新月体百分率、肾小球滤过率、蛋白尿密切相关[37],提示M2巨噬细胞参与肾功能不全、新月体肾小球肾炎的发生。AAV患者血清可诱导巨噬细胞向M2c极化[38],已知M2c细胞能有效吞噬凋亡细胞,因此AAV中M2c表达增高可能与组织在疾病中损伤修复有密切关系。2.2.3 生物标志物与AAV 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是巨噬细胞释放的一种炎症介质。MIF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循环中MIF水平与AAV活动密切相关。MIF在体内具有趋化作用,特别是促进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研究[39]证实MIF通过增加ANCA抗原易位来激活中性粒细胞,导致呼吸爆发和脱颗粒,提示MIF阻断是控制ANCA激活中性粒细胞所致炎症损伤的潜在治疗靶点。
单核 - 巨噬细胞浸润肾小球和间质在肾血管炎发病中具有作用,细胞浸润强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趋化因子特别是MCP-1,对单核 - 巨噬细胞有较强的体内外趋化作用[40]。MCP-1在血管炎患者肾活检中表达增加。在AAV中,活动性肾炎患者尿MCP-1水平显著高于无肾损害者,治疗后尿MCP-1水平明显下降,且尿MCP-1与肾小球巨噬细胞浸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41]。此外,MCP-1还被证明是鉴别AAV活动性肾损害和缓解期较好的尿标志物之一[42]。
CD163是单核 - 巨噬细胞谱系高度特异的标志物,尿可溶性CD163(usCD163)水平升高与肾巨噬细胞浸润密切相关。研究[43]表明在小血管炎中,活动性肾小球肾炎患者usCD163水平明显升高;但在活动期肾血管炎患者中,仍有部分患者表现为阴性。将usCD163和尿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urinary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uMCP-1)及蛋白尿结合在一起有助于诊断AAV隐匿性肾脏病变,提高诊断准确性[44]。另有研究[45]认为,尿中CD4+效应记忆T细胞增多反映了活动性肾血管炎疾病,故T细胞活化标志物被认为是潜在的疾病活动标志物,如CD25,可将其与CD163进行联合检测。结果表明,尿可溶性CD25(usCD25)和血可溶性CD25(ssCD25)在AAV患者活动性肾血管炎的检测中起到了补充usCD163的作用,两者水平的升高反映了AAV患者肾血管炎的早期发展,对早期诊断活动性肾血管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3 单核 - 巨噬细胞为靶点的AAV的治疗进展
随着单核 - 巨噬细胞参与AAV发展的证据增多,近年来针对单核 - 巨噬细胞及其衍生因子的治疗方法成为了研究热点。
单核细胞在AAV缓解期存在持续活化,阻断其持续活化的治疗对维持期AAV患者的缓解有益。CD14为单核细胞重要的标志分子,钙卫蛋白(calprotectin)可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在AAV患者中其水平升高可导致肾功能恶化、ANCA表达增加[46]。研究发现两者参与了感染和自身免疫之间免疫应答的相互干扰,可能在AAV的炎症放大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AAV缓解期,2种分子都处于上调状态[47-48],抗CD14单克隆抗体可作为减轻炎症方法[49],在AAV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50]发现活动性AAV患者血清钙卫蛋白升高,缓解期下降但未达到正常水平时提示存在亚临床炎症。在AAV常规治疗方法中,监测血清钙卫蛋白变化有助于预测AAV的缓解后复发[51]。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的AAV患者,若治疗早期未能控制钙卫蛋白使其下降则复发率明显升高;对PR3-ANCA患者的分析表明,治疗期间未复发的患者血清钙卫蛋白水平在免疫抑制治疗早期显著降低。由于利妥昔单抗越来越多地用于PR3-ANCA阳性患者复发时的缓解诱导,钙卫蛋白水平可能有助于确定需要强化或长期治疗的患者。
除单核细胞外,针对其衍生细胞因子的治疗是另一种有效方法。在AAV患者血清及活动部位中单核细胞产生的IL-6表达升高,而研究发现IL-6受体的单克隆抗体对伴有过敏或难治性患者有效[52]。IL-1和TNF-α均参与AAV病理过程。ANCA相关肾小球肾炎活检中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TNF-α和IL-1染色阳性[53],2种细胞因子均能介导实验性新月体性肾炎肾小球损伤。可用IL-1受体拮抗剂或TNF-α阻断剂来治疗疾病[54]。在吞噬细胞NADPH氧化酶(phagocyte NADPH oxidase,Phox)缺乏小鼠的实验中,IL-1受体阻断剂Anakinra显著降低了ANCA诱导的坏死性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的病理损伤及炎症细胞的浸润[55]。在ANCA作用下,敲除Phox可促进单核细胞浸润及炎症因子释放,并加重病变。因此,这项研究提示我们IL-1受体阻断剂对活动性AAV可能是潜在的治疗手段。关于TNF-α阻断剂在AAV及肾小球肾炎中的作用存在一些争议。在韦格纳肉芽肿依那西普试验(Wegener's granulomatosis etanercept trial,WGET)中,与标准疗法相比,联合依那西普治疗没有任何获益[56]。此外,自TNF阻断剂引入以来,陆续有药物性血管炎报道出现。由于这些原因,有学者认为抗TNF-α治疗AAV并不是值得推广的方法[57]。然而,应考虑到每种疗法都有其局限性,特别在WGET研究中,在中重度患者中使用依那西普疗效不佳可能是由于这部分患者对常规治疗反应好,故抗TNF-α疗效不明显。因此,抗TNF-α治疗仍有可能在AAV的治疗中发挥作用,可能对难治性AAV,或者在诱导期作为一种类固醇保护剂使用[58]。
4 展望
单核 - 巨噬细胞是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单核细胞内含有ANCA靶抗原,通过与ANCA相互反应,参与AAV的发生和发展。在炎症因子作用下,单核细胞表面PR3及MPO的表达增加,但是否直接导致循环中ANCA的增加,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巨噬细胞在成熟过程中失去与ANCA直接反应的能力,通过与炎症微环境相互作用,极化为不同亚型,其中M2型巨噬细胞在AAV以及ANCA相关肾损害中发挥优势作用。此外,与单核 - 巨噬细胞相关的一些分子参与了AAV的发展,有望成为诊断指标或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