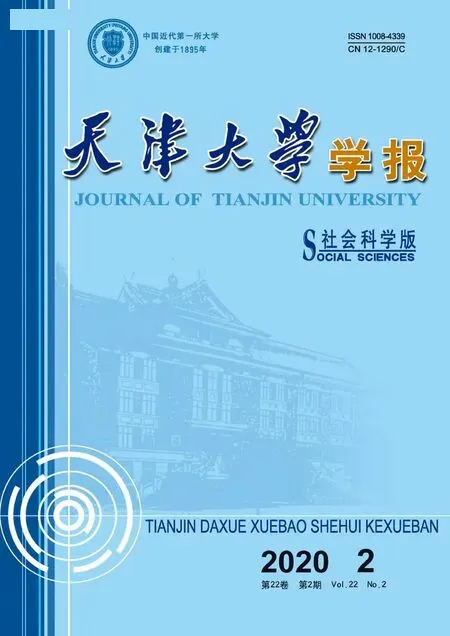《直报》与戊戌维新
2020-12-20项浩男
项浩男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100871)
1895年1月26日,商业报纸《直报》在天津创办,大约至1904年3月23日停刊[1]。从延续时间上看,《直报》比北京《万国公报》要早半年多创刊,其存在的九年,恰是晚清迭经国变的时期,甲午战败、戊戌维新、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在《直报》上留下了投影。在当时的京津乃至北方地区,这样的报刊都十分少见,且天津又是畿辅重镇,《直报》的价值不言自明。不过,有关《直报》的研究并不充分,或许由于获取和阅读存在难度——目前仅可见《直报》的影印版①,重要的报刊数据库均无电子版可供查阅。且因为严复曾经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五篇宣传自强救国、提倡西学的文章,《直报》基本被作为严复发表维新思想的平台而出现在诸多以戊戌维新或严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中[2-6]。其他一些成果虽然探讨了《直报》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但存在不足[7]。其实,我们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比如除严复的文章外,《直报》在戊戌维新期间是否还刊登过其他言论——支持或反对维新?《直报》与当时的其他报刊有无联系和互动?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在传播维新思想上,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有何异同?这些都关系到该报在戊戌维新中的作用和地位。
本文以1895—1897年的《直报》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其言论倾向与维新变法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其对维新思想的阐发,也包括舆论与现实的互动,并将其置于戊戌维新时期全国的舆论版图中进行考察,尤其注重《直报》与同时期其他报刊的联系和对比,凸显商业报纸的独特优势,力图揭示其发挥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以期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②。
一、 《直报》的维新主张
既有研究在论及甲午战后维新思潮的发展时,基本以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或重要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为线索进行叙述。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较少关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亦造成一种定见——只有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才宣扬维新思想,仍带有为报刊“定性”或“划定成分”的先入为主的嫌疑。其实,报刊的创办者、宣传的思想和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未必存在一致的属性。
《直报》的创办者是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1879年来华,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兼充李鸿章副官[8-9]。1894年11月15日,汉纳根被清政府委派训练新军而回到天津[10],翌年1月下旬创办了《直报》。如果从“性质”上来看,汉纳根是外国人,与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交往颇密,受清政府命令负责陆军训练,而从《直报》的风格来看,明显是一份商业报纸,愈到后期商业性愈明显③。但恰恰是这样一份报纸,在宣传维新思想方面却走在了不少重要报刊的前面。有研究者指出从甲午战争时期到战后,《直报》有一个将舆论导向变法维新的变化[11]。这大体不错,但如果仔细梳理《直报》创刊以来的社论和新闻的话会发现,《直报》的维新倾向自创办时起就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主张愈加开放、求新,主要可以概括为8个方面:1)反思洋务得失;2)兴办实业,广开利源;3)改良厘金、税收,振兴商业;4)废八股,改取士之法;5)倡导西学,学习西法;6)强调民本,倡导议会政治;7)兴修铁路,绅商出资;8)呼吁维新变法。
因篇幅所限,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不能一一详述,仅就学习西法和倡导议会政治两项进行简要分析。
在“倡导西学,学习西法”方面,《直报》认为:“欲致富强,势不得不亟兴人才,而欲兴人才,势不得不亟修学校,而欲修学校者,势不得不亟求西法”[12]。对西学的倡导贯穿在《直报》的诸多主张中,这不仅是泰西诸国富强与文明带来的启示,更是败于日本引发的反思。《直报》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即指出日本“无不曲尽西法之妙而精益求精”[13],反观中国,对于西方的先进之处,“除通商口岸以外,民尚疑为妖法邪术,绝不知其悉本实学之可仿效也”[14]。为倡导西学,《直报》登载了《原西法》一文,该文尽管实质是在号召学习西法,却采用了“托古改制”的方式,开篇便指出“乱今日之天下者,古人也,非古人能乱今日之天下,乃今人不善学古人遂以古人之道乱天下也”[15],如此言之,是因为所谓的西法,如经世、制器、实用等,原是中国古代圣贤的主张,只是被后世的学人遗忘而已。
今日之西法,即伏羲以来相传之遗意也,今日行西法即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吾中国数百万聪明之子弟日日困于故纸堆中,吾诚哀之,其甚者又以稽古为荣,而不使西学污之目,至终身不思变计,吾尤痛之。[15]
采取该方法是为了减轻大力倡导西法带来的阻力,将西学附会中学,欧罗巴诸国之所以能“精于制器”,是因为汲取了中学的精华,今日学习西法,实则是重新发现并运用“古人精神命脉”,且“甚为可学,亦非难学,学之以渐,异日或驾而上之”[16]。不过,《直报》并不是主张什么都要学,“学之有益则宜学,学之无益则不宜学”[16]。
在《倡西学论》中,《直报》对西学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对洋务运动最根本的反思。该文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根本原因“不全恃乎坚甲利兵,而深赖乎穷理劝学士耳”,尽管中国“竞言洋务”,“亦未尝不力求自强也,兵则练矣,械则备矣,机器则有局,船政则有厂,而于开矿务、筑铁路等政,亦无不次第举行,所以讲求西法者亦已亟矣”,但仍然是“独弱”,原因在于这些举措“或未得要领,或仅袭皮毛,良由西学未精,故未能措置悉当施之于政,亦殊鲜效”,不过是“欢虞小补之谋,非探本溯源之术,故或阻于清议,或格于难行,虽属因循,究由轻率”,而“国家之所以强盛者,不在用兵,而在教化”[17]。提倡教化,重在学校,学校教育应以西学为中心。《直报》建议:“倡西学应从宗室亲藩、大员子弟率先作则,派遣他们入堂肄业,或出洋游历,以开风气之先,乃能激励士庶,务使习悉洋务。”[18]《直报》对办学堂、讲西学不吝赞赏,其批评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劳民伤财,对他在武汉创办的自强学堂,却大加称赞:“以育人材,以备异时之用,实人臣以人事主之盛意也。”[19]天津博文书院得到了“今见博文既开,吾知学校修矣,西法求矣,人才有所兴矣,即富强有所由矣”[12]的褒扬。
在“强调民本,倡导议会政治”方面,《直报》多次阐扬“民”的重要性,如“得民者斯得天下”[20]“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善政无他也,去其病民者而已,谋其保民者而已”[21],而今日则是“民政之无足轻重,由来旧矣”[22]。“民”不受重视的根源在于“政”之失,如《直报》所言:
国之与立,民为本,举中华与海外盈天下者皆民也,一治一乱而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乱者民,治者亦民,民非能自为治乱也,有持民政者,其政有得而有失,故其民或治而或乱,欲民之长治久安而不乱,必使政有得而无失。[23]
“政”之失根源在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存在诸多弊端,1895年4月25、26、27三日连载的《知更者说》一文,对清朝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职能划分、行政流程,地方政府的办事规矩、地方官即州县长官的权力来源、职责,胥吏的生存实态,以及存在的各种弊病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22、24、25]。比如文章指出,官员官阶的升迁与否和民政并无关系,官员、胥吏之间因民之事互相推诿,民将所需所求诉诸官无异于缘木求鱼[22]。因此,改善民政的关键在于改良政体,《直报》推荐的方法是“众政自由”,即效仿西方的议会制,译作“巴力门”,《众政自由疏证》中介绍说:
西学之大要,在众政,即在自由,众政非但民政之国,即君政亦必先经议院,正所谓政以众成,众政之善,理甚为易见,譬如择智者千人为一院,更迭辩论而施行,又择其最智者一人为□,院独断以施行必千人,院所失较少者,良因最智之一人必不敌千智人之智。[26]
众政的要义是自由,君政亦受到议院制约,广集智慧能够规避独断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议院纳贤之法,则凡与国家有益无损无私为公者,不论士农工商皆可上书”[27],议院之内,四民平等,为公事建言献策甚至能“即可为官”,是获得政治身份的通道。而且,《直报》已经区分出了西方国家议会制度中的差别,其所说的“君政”相当于君主专制,“众政”更接近于民主共和制,其更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直报》指出泰西诸国中以英国为望国,“其政如君民共和之适中,又如巴力门之无分贵贱,以及经商讲武美不胜书”[28]。
不过,与提倡西法时采用的方式相同,对“巴力门”的介绍亦是以古人之说附会和解释西学之意的方式:
众政之义,孟子言之不一,如曰民为贵,君为轻,又言举措与用刑,皆必待国人尽同而后察行其事,实之存于载籍,则有如舜禹受禅,皆以民归为断,降及周衰,如阳樊之不服晋,可见其民犹能主持时事,迨近代久已歇绝,迂儒浅识,狃于习见,不如勤求古义,遂闻众政而骇,为夷狄之蔑大伦,不知古圣已尝默许之矣。[26]
《直报》强调:“以众政施于今日之华,则犹病热甚者之于芒硝,如疑其寒泄而不服,惟死而已矣,故为详推其先有于古,非创自西、取于西者,即所以法古并立可见效于今。”[26]《直报》的维新主张在戊戌时期并不罕见,其中不少建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反复申说过,但《直报》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时间性,现存的《直报》缺损比较严重,尤其是1897年,上文总结的维新主张,基本刊于1895—1896年,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才正式出版,上海的《时务报》更是1896年8月才创刊,《直报》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即开始反思洋务得失,先于《万国公报》倡言维新,在当时的报刊中独树一帜,其在维新舆论兴起和传布中的开创性和先见性应被重视。
第二是丰富性,检阅北京《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的目录,可以发现它们提出的维新主张限于铁路、兵制、学校、开矿等几个方面,且多是连载,再加上期次有限,实际刊登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内容不甚充实。反观《直报》,其涉及到了维新变法的方方面面,废科举、设议会等主张更是《万国公报》没有提到的,《直报》是日刊,每天都有社论,同一话题能有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进行阐释,视角全面,内容丰富,论述详备。
第三是专业性,《直报》的题材多样,但不是泛泛而谈,很多言论相当精深,如涉及到军事的多篇文章,对各种军事技术、作战要领、武器装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论述政治革新时,对清政府自中央至地方各层级的制度设计、行政运作十分熟悉,对州县长官、胥吏、幕府等群体的特点和弊端能够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专业性不是《万国公报》可以相比的,尤其是对清政府的政治运作如此了解,想必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维新人士能够认识到的,这应与《直报》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团队有关。由于现存有关《直报》的资料甚少,其刊登的社论基本没有署名,这对钩沉其撰稿人和编辑的具体情况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不过,仍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略加推测。《直报》的创办者汉纳根于1894年8月加入北洋舰队,他发现了舰队的诸多问题,如弹药缺乏、补给不足等[29]。他还对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战守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看法,提出募练新式陆军、加紧购买快船的建议[10]173-176。这段经历使汉纳根对北洋舰队的具体情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如果仔细比对会发现,《直报》中不少军事文章的观点和他本人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言论基本一致[30],汉纳根本人应该参与到了《直报》的编辑中。此外,在《直报》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的严复当时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办道员[31];《倡西学论》的作者何守仁甲午战争期间任旅顺口水雷营帮带,后在新建陆军服务[32]。可推测,《直报》的撰稿人应有一部分来自北洋水师,是清政府军事体制内的专业人士,很可能是汉纳根借助北洋水师军事顾问的身份延揽到的人才和稿件。那些探讨清政府政治弊端的文章,可能来自官僚体制内的人士,但由于资料匮乏,只能略作猜想。
二、 以报刊论政事
《直报》对维新思想的传布,既要与维新派报刊进行对比,也需要在特定的思想脉络中寻找其定位。自西方报业传入中国之后,其形式和效用吸引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注。甲午战败,面对民族危机,报刊成为进步人士寻求新的知识和思想的平台,也是公开表达政见、呼吁变革的途径,以办报促成上下通、开民智成为维新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维新思想的传布也依托了报刊发挥作用。既有研究通常关注王韬、陈炽尤其是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期间的报学思想和办报实践,忽视了其他重要的文本。
《直报》自创刊伊始就十分重视报刊对政治、对社会应发挥的作用,其在创刊号上登载了《直报说》一文,对《直报》的宗旨和期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释,设置报馆的初衷在“扶冀政教,整齐风俗”,以联上下之情谊,以广中外之见闻[33]。之所以在天津创办,是因为天津临近京师,又是五方杂处、华洋汇聚之地,“耳目环伺,听观广集,即首善之区,开自强之治,尤以周知民隐,备悉敌情为先务,诚能多立报馆,务求直言,斯万里之遥,如在户闼”[33]。因此,该报取名为“直”,一是因为天津为直隶属地;二是取“在直言直”的意思,秉笔直书,直言无忌[33]。《直报》主张凡有关国计民生者,均在其报道范围内,只有这样,“斯无负泰西设馆之本旨焉”[34]。
《直报》刊登了《论报馆宜多设》一文系统阐述了报纸的重要功用,该文分两次连载,不久之后又刊登了《宜广开报馆论》进行补充。《论报馆宜多设》首先介绍了“欧墨两州新闻纸之流通”的繁盛情况,泰西各国报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蔚为大观,报纸行销广泛,销量大,获利亦多,发挥了“通上下”的作用[35]。该文进而联想到中国,设立报馆、广办报纸,可收到诸多良好效果,最终促成“开民智”[35]。至于政府对报纸的管控,该文主张政府不能随意查禁报馆,除谤君上、污官长、揭人阴私、诬人反叛外,余若证据昭彰,不杂一毫私心,则官不得禁[35]。在续稿中,《直报》着重论述了报馆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例举了普鲁士的例子,普鲁士开报禁、设报馆,国王通过报纸察知民意,了解施政之得失,最终建立统一之基业[36]。文章认为,不仅英法德美诸国报业发达、获利颇丰,报论有益于国计民生,日本之强盛,也得益于开设报馆。
盖日本君臣自维新以来,数十年中甚恐民智卑狭,民气之不振也,以报章能以新民,故纵令多开报馆,虽政府与议院有不合处,不得不施禁令,而旋封旋开,终须耐心观听,俾各抒谠论,各献奇谋,诚集思广益知道也。当中日失和时,日本乡僻荒村亦传凯奏,用能人心鼓舞,敌忾同仇,且知西洋报力之宏,优待随军观战之士,每见左袒之电,即不收电资,是以西国先知东事,从人听闻,岂非近事之彰明最著者乎?[36]
《直报》认识到中国败于日本,并不全是因为武力不及人,深层次原因是“民智”,日本的维新重视报刊,以报刊“新民”,相比之下,中国报馆极少,仅仅通行于通商口岸,不过沧海一粟,且以取悦官场为职责,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论报馆宜多设》和《宜广开报馆论》相继例举了诸多具体的好处,多达十余条,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均能从报纸中获利。
戈公振曾指出:“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37]同样也很少见到报纸或报人对报纸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功用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作为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是一位先行者,其在创办《循环日报》时就认识到,学西方不仅要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章制度,还要着手像西方那样为富强活动开拓出一个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38]。王韬之后,最受关注和重视的是梁启超的著名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在该文中指出,报馆的作用是“去塞求通”,是国家的耳目与喉舌,中国之所以疲弱受侮,原因在于上下不通、内外不通,只有开设报馆、创办报刊,促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才能有益于国事,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39]。该文备受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如果与《直报》上的言论相比会发现,梁文的主要观点在《直报》上已经出现,比如梁启超提到:“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39]《直报》在发刊词中即指出:“君国大政,各报管主笔人亦得入议院与闻,退而直书其事,登报以传得失是非之故,使人人了然于胸中。”[33]至于上下通、开民智、宜多设、益国事等主张,《论报馆宜多设》中也已阐释的比较充分了。从发表时间上来看,梁文于1896年8月9日刊登在《时务报》上,而《论报馆宜多设》发表于1896年2月1日,《续前稿》发表于2月3日,比梁文早半年之久。从实践上来看,《直报》自创办伊始,就反思洋务,倡言维新,于政治、经济、社会、民政等事均有议论和新见提出,政论的色彩不可谓不浓厚。
三、 《直报》与京、沪强学会
《直报》自创办伊始就不断发表具有维新趋向的文字,但上文的分析尚属一种“静态”的考察,报刊舆论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应该将其放置于舆论网络中进行分析,这样的工作大致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报刊对具体事件乃至敏感事件的态度,这能体现一份报刊的价值取向;其二是在当时全国的舆论场域中,该报刊居于何种地位。本文在这一部分着重考察第一个方面。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陈炽曾言:“为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40]公车上书后不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骨干开始将办报刊、设学会的构想逐步付诸实践。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办,同年11月初,强学会正式成立,后改称强学书局[41]。北京强学会规模初具,康有为于10月中旬出京南下,筹备在上海设会开局之事,并拟定《上海强学会章程》[42]。但好景不长,北京强学会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注意,1896年1月21日,御使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43]。上海《强学报》仅出版三号就被迫停刊。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强学会、《万国公报》《强学报》自身的发展和遭遇,很少探讨其他报刊的报道和看法。遍检当时的报刊,强学会的消息集中出现在《申报》《新闻报》《益闻录》三份上海报纸上,以简短的、描述性的新闻居多,评论性的文字较少。在内容上,沪上报纸更关注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的遭遇,对北京方面很少着墨。作为一份天津报纸,《直报》发挥了支持北京、呼应上海的重要作用,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用较长的篇幅报道了北京强学会的成立,并给予积极评价。1895年11月23日,《直报》刊登了《强学开局》一文,开篇指出创设强学会的缘由:“现寓京诸巨公悯时局艰危,以天下为己任,讲求实济,力图富强,拟在京开设强学书局”[44]。书局的主要任务是“专主译印中外时务新书,凡中国旧有经世各图籍,中外各地图天图、奇物奇器、新法新事,有关国计民生者,即讲求刊布流传四方,以广见闻而开风气”,并对现阶段已取得进展进行了报道[44]。最后介绍了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等襄赞之人,认为“京华诸公极形踊跃”[44]。此报道并未见诸其他报刊。
第二,对杨崇伊弹劾强学会一事进行了抨击。既有研究大多援引《戊戌变法》第二册中收录的上谕,以证实杨的参奏导致了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但杨崇伊的行为是否引起了其他反应,由于资料的缺乏,并无人关注。杨折于1896年1月21日呈奏,当日清廷即发布上谕,但上谕只照录了前半部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原折全文如下:
小型紧凑化是高功率脉冲驱动源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1-4],能够产生近似方波脉冲的Marx发生器受到了广泛关注[5-8]。一般将传统Marx发生器中的电容器改为脉冲形成网络,可使发生器输出近似方波脉冲,再将各级脉冲形成网络以Marx发生器的形式进行叠加,即可达到增加输出功率、大幅减小脉冲驱动源体积的目的。
近来台馆诸臣。自命留心时事,竟敢呼朋引类,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计此二宗所入,每月千金以外。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故开办未久,集款已及二万。口谈忠义,心熏利欲,莫此为甚。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势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43]
“故开办未久”之后的语句上谕并未提及,其实杨崇伊的弹劾有两层意思在:一是指强学会勒索官吏、聚敛钱财;二则是给强学会扣上了妄议朝政、结党营私的罪名。1896年3月12日、13日、14日、16日,《直报》连载了《立言说》一文,17日又刊登了《某侍御请禁强学书局疏书后》,对“某侍御所奏请将强学书局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一疏”[45]进行驳斥。
针对第一条责难《直报》指出:“古今家国天下,无不患贫之人,即无不爱财之人,故以行贿诬人,莫论虚实,最易取信。”[45]杨崇伊的弹劾无非是以最容易被人相信的罪名进行诬告而已。至于“集款已及两万”《直报》辩驳称,这些收入一部分系售卖报纸所得,“以其阅之者多,故其销之也畅”。至于“函索外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这些捐助钱款的官员,“定系入会在局之人,断不能无故索诸局外,使向局外索之,人亦万不肯赏”,集款之多正说明入会官员之好善,对于办学会一事“大众乐成是举”[46]。
针对第二条责难《直报》指出:“侍御所谓恐以书生私议干朝廷之权,是指报馆新闻为言,又云党援门户皆基于此,是指强学会中诸公为言间尝论之赏罚者治世之大权。”[47]这项指控其实是很大的罪名,以报馆、新闻为基础结党营私、妄议朝政,最容易触犯到保守的统治阶层的禁忌。《直报》认为,开设报馆是仿效泰西之例,“原为宣上德,达下情,议执政之可否,以佐议院所不逮考”,日本设上下两议院,“其例尤以下议院为重,诚以民为贵,确有至理”[47]。再者,如今乃大一统之世,曰生曰杀,天下一人,没有人敢参末议,左右庆赏刑威之权[47]。无非是因为具体的意见不同,而稍加议论而已。但“人主无论贤愚,无不恶臣下之立党”,因意见不同而分门别户,最易被视为结党,“故小人之劾君子也,每以立党营私为罪案,史册俱在,历历可稽”[48]。杨崇伊弹劾之事,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
《立言说》分四次连载,言辞较为激烈,援引北宋和明末党争之例,指责杨崇伊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思协力同心,互为声援,设法以驱外来之强盗,乃以口舌之衅,负气相争”[47],实属“小人之用心”,使忠臣义士直道而行者横遭污蔑[49]。《直报》不断强调强学会诸公矢志可嘉,“皆出于忠君爱国之忱,虽于事无补,究于事何伤乎?”[49]《直报》对杨崇伊铿锵有力的抨击,明确彰显了其对维新变法的立场,而且这也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份公开支持北京强学会的报刊。
第三,最早全文刊登了《上海强学会章程》④。该章程是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资料,目前刊行于世并被广泛使用的《章程》,均以《强学报》第一号所刊作为底本,因第一号错漏较多,编者依据该报第二号《强学报正误》进行更正[50]。此外,汤志钧先生还根据《皇朝经世文三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进行比对,增补了几处缺漏,形成今天的通行本,如《康有为全集》和《康有为政论集》等,其他选录《章程》的资料,基本沿袭这一版本[51]。但《直报》的出现为考察《章程》的版本变迁提供了新的线索。
从时间上来看,《强学报》第一号出版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西历1896年1月12日。如果仔细核查当时的报刊,会发现有两份报刊早于《强学报》全文刊登了《章程》,其一是《直报》,于1895年12月27日和28日分两次连载了《章程》,其二是上海《益闻录》,于1895年12月28日刊登了《章程》,二者相差仅一天,比《强学报》要早半个月左右,可见《直报》应该是最早刊登《章程》的报刊。
从内容上来看,《直报》两期连载的《章程》并不是全本,与《强学报》版相比少了14个完整段落,个别段落中还存在缺字少句的现象,总体来看《直报》版大约比《强学报》版少了四分之一的内容。在文字表述上,总计有30余处存在差异,12月27日刊登的前半部分以用字用词的不同为主,均属细微的差别,12月28日刊登的后半部分则出现了较大的差距,缺少句子、语序颠倒、用词用语不同等现象较为突出。12月28日,《益闻录》也刊登了《章程》,与《直报》不同的是,《益闻录》刊登的是全文,并附上了《强学会后序》,与《强学报》相比,仅少了位于《章程》前面的《上海强学会序》。但是《益闻录》版的内容与《强学报》差别也很大,经笔者仔细比对发现,《益闻录》的前半部分,即至“联票皆有董事图章”一句之前,与《直报》版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变化。该句之后的部分,与《强学报》版相比,除了用词用字的差别,具体条款上亦存在较大出入,《益闻录》版中的个别条款,并没有出现在《强学报》版中,而是做了更替。
通过版本对比可以推测,《章程》在完成之后不久即为《直报》和《益闻录》获得,二者得到的应是同一版本,但是不知是因为版面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直报》并没有全部刊登。《强学报》于半个月后刊登的版本,很可能是康有为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综上所述,在京沪两地的强学会成立之前,《直报》在发表维新言论上非常积极,但与时事的互动比较少,所刊新闻也以直白的报道为主,甚少呼应复杂、敏感的重要事件。京沪强学会的成立,尤其是北京强学会遭弹劾一事,《直报》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连续刊文进行驳斥。既有研究者曾指出:《直报》的编辑力量、发行渠道、经营状况,因缺少资料,不得而知[1]。但据强学会一事可以推测,《直报》与北京和上海的维新人士有着密切接触,或者是维新人士直接为《直报》提供文稿和消息,如《上海强学会章程》,《直报》上刊登的应该是初稿或较早的版本,目前无法断定《直报》和《益闻录》哪家先获得了初稿,如果是康有为通过某种渠道将文稿交给了《直报》,说明《直报》与维新人士关系匪浅;如果《直报》是从《益闻录》那里获得了初稿,并早一日刊登出来,亦可以证明其维新倾向。驳斥杨崇伊一事,更是说明了《直报》与京中维新派人士的密切联系,《直报》获得了杨崇伊奏折的全文。《直报》有告白称:该报在北京宣武门设有京城售报处,负责人为陈午清[52],其人其事目前无从可考,但可猜测,该售报处是《直报》获取京师信息的驻点。
四、 舆论场域中的《直报》
报刊舆论在戊戌维新中发挥的作用已有学者关注,但基本集中在几份著名的报刊上,忽视了对《直报》这一由外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进行考察,进而也导致一些结论值得商榷。比如有学者认为百日维新之前,全国出现了两个宣传维新思想的舆论中心:北京的《中外纪闻》和上海的《强学报》南北呼应,康有为南下游说张之洞,也是为了构建南方的舆论场域[53]。《上海强学会章程》中确实有“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50]173的表述,但这只能证明康有为的构想,实际情况则需要另行考证。从时间上来看,《中外纪闻》于1895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1896年1月20日被封禁,共出版18期;《强学报》创刊于1896年1月12日,共出三号,约终刊于1月22日,存在时间极短[42]123。可见,二者能否形成舆论呼应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所谓“呼应”或互动不能仅仅看报刊的创立,更要看报刊的观点有无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当时全国的舆论场域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衡量:一是《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相互之间有没有援引观点,互相支持;二是其他报刊对这两份报纸上的文章有没有转载或报道。考察现存《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的目录,二者并无文章上的交集;而考诸当时其他的报刊也未发现有转载的情形。《申报》《新闻报》上基本是关于强学会成立与封禁的报道,《中外纪闻》也只是转载了原登于《新闻报》上的《上海强学会序》[54]。以此可见,《中外纪闻》在京师士人中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否在上海也产生了影响,很值得怀疑。至于《强学报》,其存在时间如此之短,产生的影响恐怕也仅局限于上海一地。因此,所谓《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南北呼应的论断,恐怕并不能成立。
针对既有结论进行商榷,目的在于重新厘清当时全国舆论场域的真实状况。在《时务报》创办之前,上海其实并没有出现时间较长的维新派报纸,而北京的《中外纪闻》栏目设置较为简单,每一期容量也不是很大,影响力恐怕只局限于京师之内。在京沪之外,天津的《直报》是传布维新思想的舆论重镇和信息枢纽,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供佐证。
第一,以读者来信的形式为维新思想造势。《直报》刊登过严复的五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⑤,这些文章后来经过增删改动,《直报》上的初版为剖析严复思想递嬗演变的迹象提供了文本依据[7]。除此之外,尚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一是《直报》在连载了严复的文章之后,还刊登了3封读者来信,第一封是1895年3月26日的《原强篇书后》,署名是知津小吏,该文赞赏《原强》“会通中西之学,迫于沉痛急切而发”,支持严复的观点[55]。第二封是1895年5月25日的《救亡决论书后》,注明是来稿,开篇即指出:“此篇读者共叹,淋漓尽致,愚则独见其涕泪满纸矣,不变必亡,变之首在改制科而讲西学”[56]。刊载这篇来信时,《救亡决论》尚未连载完,7月6日,《直报》刊登了署名韫辉堂的《救亡决论第三书后》,虽然该文对严复“不满于周孔”略有微词,但仍然承认:“华人于西事茫然,因鄙薄西教,而并弃西学,则甚于惩羹吹齑,有似因噎废食,故愚谓赖此言而此篇尚未未虚作”[57]。这样的读者来信,有可能是从若干来信中甄选出来的,也有可能是报馆自己创作的,这样一呼一应,有助于渲染和增强维新言论的说服力,也营造出取鉴西学、维新变法在读者中引起共鸣的氛围。其二,文本的流传也可以说明其影响力,经笔者考察,《原强》在全部连载之后不久,被上海《字林沪报》分6次转载,而且都是在第一版,并注明“录直报”⑥。《字林沪报》是上海很有影响力的著名报纸,在头版头条转载《原强》,无疑有助于严复的主张和思想在上海传播和接受。
第二,转载上海、英国和日本的报纸新闻,并在天津代售上海的报纸,促进形成南北之间的新闻网络。《直报》刊登的新闻,除报馆自己采访所得之外,经常转录其他报纸上的消息,经核查,国内报纸包括《申报》《新闻报》《沪报》等,国外报纸包括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日本的《朝日新闻》。《直报》刊登的新闻大多数都是关于京师、天津和直隶地区的,转录其他报纸的新闻,使阅读者获取的信息内容丰富了很多。但转录的新闻毕竟有限,开办后不久《直报》在天津开设了售报处,最初是售卖“由上海寄津新闻报纸、字林沪报,代送申报”,并宣称各种报纸都有[58]。后又不断加入新的报纸,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飞云馆画报等[59]。这些报纸都是上海的名报,《直报》在北京也有售报处,虽未明言,想必也有代售上海报纸的业务。《直报》相当于开设了一个信息中转站,将上海地区的信息传播到京津地区,促进了南北之间信息的流通。此外,天津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交互也是靠《直报》连接的,比如《直报》售报处也代售北京的《万国公报》[60],《中外纪闻》则将《直报》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中外纪闻》每一期都有“照译路透电”“选译西报”和“录各省报”栏目,据其凡例云:
一、本局新印《中外纪闻》,册首恭录阁抄;次全录英国路透电报,次选译外国各报,如《泰晤士报》《水陆军报》等类;次择录各省新报,如《直报》《沪报》《申报》《新闻报》《汉报》《循环报》《华字报》《维新报》《岭南报》《中西报》等类;次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次附论说。[61]
可见,《直报》是《中外纪闻》的新闻来源之一,与《循环报》《申报》《新闻报》等著名报纸并称,虽然目前留存的《中外纪闻》中尚未见到转录《直报》的新闻,但可推测其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眼中,属于具有一定价值的“新报”。由此观之,《直报》发挥了沟通南北、连接京津的重要作用,将新闻事业发达的上海地区的重要报纸传播到北方,在政治敏感、言论管制严格的京师附近,开辟出一个相对自主的舆论空间。
第三,为具有进步倾向的书籍做广告。《直报》是一份商业报纸,自第一期起就不断刊登各种广告,越到后期广告越多,商家的类别也越多样,但书籍的广告自始至终一直出现在《直报》上。最开始时,《直报》为文美斋和嫏嬛书庄两家书店做广告,发布在售书目,后来《直报》的售报处也经营卖书业务。这几家书商卖的书新旧混杂,有不少是流传于市井街巷的消遣书籍,在越来越长的书单中,“新”书籍越来越多,且不少是紧随时事而跟进的。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有关日本的书籍开始大量引进,如《日本新政考》《日本师船表》《日本史略》《日本地图》[62]《大东海计里图》《日本水陆计里图》《日本地理兵要》[63]《日本外史》《东胜纪要》《日本新政考》[64]等;俄国、泰西以及世界地理的书籍、地图、游记也被引进,如《中俄交界图》[63]《皇朝一统地图》《北洋中外沿海详细图》《四国日记》《俄游汇编》《中俄界约斟注》《俄罗斯地图》《中外交涉类要表》《西国近事汇编》《地球五大洲图》《亚细亚图》[64]等;此外还有各种军事、法律、工商、科技、医学书籍。值得一提的是《直报》对维新人物著作的介绍,1895年5月22日文美斋正式售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报》分别在6月8日和9月14日刊登了该书的序言,6月21日《直报》刊登了报馆拟定的推荐词:
盛世危言一书,香山郑陶斋观察所著也,观察负经世之才,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当今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凡有关于中外情势,商榷利弊,旁搜远绍无遗,随手笔录,积年累月共成五十篇,凡用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商务农工,治河防海防边,练兵等事,了如指掌,皆时务切要之言,凡士大夫留心经济者,家置一编,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使天下除厥弊端,不诚有裨于大局哉![65]
再如《公车上书记》1895年8月26日在文美斋出售,《直报》售报处后来也代售此书,还推出了小本版[66]。上述诸多传播西学、新知识、新思想的书籍,既具有“开眼看世界”的色彩,也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载体,连续不断、频繁更新的书籍广告,无疑为阅报人提供了接触新思想的契机。
综上所述,在上海《时务报》和天津的《国闻报》创办之前,很难说维新思想已经出现了南北舆论相互呼应之势,维新派自己办的报纸或者昙花一现,或者内容单薄,《万国公报》每一册只登载一篇论文,《中外纪闻》也没有广告,而且还不是日报,相比之下《直报》能够提供的信息量要丰富得多。此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上面刊登的文章部分是转载的,尽管也有出于梁启超和麦梦华之手,但质量和影响力无法与《时务报》相提并论,与《直报》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题材,也都逊色了很多。因此,在戊戌维新前期,至少是在1895—1897年,天津的《直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舆论重镇,而且发挥了沟通南北、联络京津、代售书报的作用,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五、 结 语
一份报刊能否长期生存,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有无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无素质优良的撰稿人、能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评论、是否拥有固定的读者群体,栏目设置、排版以及经营策略、营销手段等也很重要,这些因素综合运作,方能促使报刊产生影响力。以这些因素粗略衡量,无论是北京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是上海的《强学报》,尚属于草创阶段,很多方面算不上成熟,实际产生的影响力,不宜高估。相对而言,《直报》能够广泛获取信息并维持经营,每天都有社论刊出,提供题材丰富的维新主张,代售书籍和报纸,既关注北京亦沟通上海,促进了京津互动和南北呼应,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天津一隅,俨然是戊戌维新前期的舆论重镇。可以推测,《直报》拥有一个相当有实力、有眼光的编辑团队,其撰稿人和经营者,想必是认同并支持维新思想的,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上至朝廷动向,下至售卖经营,均能及时获取信息。这些优势,恰恰与其商业报纸的性质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本文对1898年之前《直报》的考察,目的在于揭示历史上的细微真相,《直报》这样一份商业报纸,在戊戌维新中发挥的作用被我们严重低估了。当然,也正是因为其商业性质,大抵是出于自保,在百日维新中,尤其是戊戌政变前后,其一贯支持维新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偏向保守。
注 释:
①天津博物馆所存《直报》最为完整,但缺号的情况也很严重,于2010年影印出版。(天津博物馆藏,直报:全十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②根据笔者阅读《直报》的感受,《直报》的言论倾向以1898年的“百日维新”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直报》的言论非常“求新”,甚至稍有些激进;“百日维新”前后则随着政局的变化逐渐趋向保守。
③《直报》每一期的版式都很固定,依次是上谕恭录、社论、新闻、京报节录和广告,1898年之前,《直报》每期4版,第4版是广告,从1898年开始增至8版,第6-8版是广告。
④下文简称《章程》。
⑤这5篇文章有4篇是连载的,具体刊登日期是:《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日、5日;《原强》,1895年3月4日至9日;《原强续篇》,1895年3月29日;《辟韩》,1895年3月13日、14日;《救亡决论》,1895年5月1日、6日至8日、6月17至18日。
⑥《原强》在《字林沪报》上分6次转载,分别是1895年3月20日第1版、3月24日第1版、3月25日第1版、3月28日第1版、4月12日第1版、4月1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