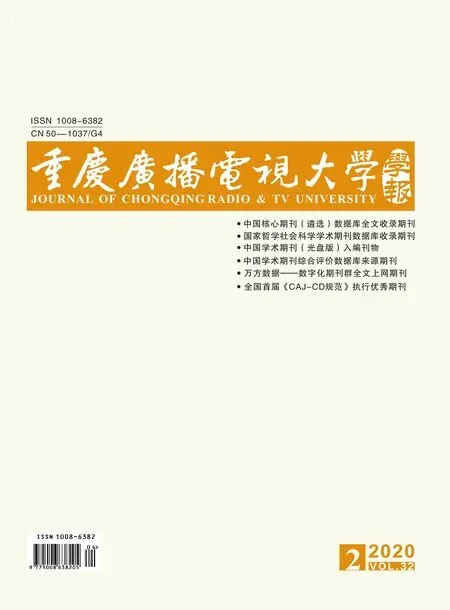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及其伦理危机
2020-12-14要欣委
要欣委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一、后现代语境下广告图像的转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提出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论断。其后,现代文化的后现代化走向也愈发印证了这一论断:意义更多地融入形象与类像之中,媒介的视觉化倾向培养了大众新的信息接收习惯,也刺激了视觉化欲望的膨胀。与此同时,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文化形态日益被以视觉为中心的感性主义文化形态所取代,人类社会进入图像传播时代。
作为典型的社会文化文本,广告传播过程中的图形化转向正与此相契合。纵观广告史可以发现,早期的广告形式以口头广告、实物广告为主,文字及印刷术的出现与使用为广告传播带来了文字转向。而后一直到近现代,广告文本中的文字一直居于意义表达的主要地位,近现代的广告大师也都是文案大师。以著名的广告人乔治·葛里宾(George Cribbin)为例,其创作的《我的朋友乔·霍姆斯,他现在是一匹马了》《幸运的寡妇》等作品脍炙人口,被奉为经典。在这些广告作品中,几乎没有配图。作为广告文本主体的文案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字,故早期的文案在广告文本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但在媒介更迭及广告制作技术演进等原因的影响下,广告图像的作用与地位逐渐增强:由早期的修饰功能向意义承载功能演变,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广告文本中的文字越来越少,而图像无论是在文本篇幅还是意义表达上,都占据了主要地位,且越来越追求视觉美感与视觉冲击。发展至今,一些新兴的广告形式,如长图广告、VR广告等更是通过图像主导来追求一种沉浸式体验,以期达到更好的广告传播效果。在广告业界,从广告从业人员分布上来看,美术指导、美工、画师、设计师等职位的人员数量正在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这些角色在广告创意过程中掌握的话语权也愈发重要。由此看来,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正在发生且难以逆转,愈发呈现出成熟之势。
二、广告传播图像转向的可行性
1.体裁优势:广告文本脱离文字枷锁
然而,对于广告来说,也未必如此。我们经常看到在一幅平面广告中,只有广告图片以及产品的logo,整个广告文本没有一个文字。有的广告短片也是如此,类似默片式的广告短片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语言信息,当短片快要结束时才有相关的产品logo出现。然而对于这类广告文本,受众似乎在没有文字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够无障碍地理解广告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甚至在广告传播图像转向的当下,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广告文本风格。而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广告在体裁上具有强大优势。
“体裁的最大作用,是指示信息接收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它能够引起读者某种注意类型或阅读态度。”[2]当受众接触到没有语言文字信息的广告文本时,平面广告和广告短片中的品牌logo会提醒受众,当前的阅读文本是一则广告,从而使受众调整自身的理解思维。对于广告来说,商品始终是广告文本表意的中心,也是文本解读的中心,受众在解读没有文字信息的广告文本时,会自觉地遵从体裁契约,将文本的意图定点落在商品或其品牌上,极大地避免了意义解读被无限衍义。基于此,广告文本的体裁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文字等语言信息的锚定功能,从而使得广告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文字枷锁,实现了图像解放。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表意较为复杂的广告文本,依然需要辅以必要的文字信息以达成编码解码过程的共识。但毋庸置疑的是,广告文本巨大的体裁优势,对于其图像转向意义非凡。
2.技术赋权:数字媒介助推图像转向
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归根到底是一次媒介事件,是基于技术赋权基础上的信息生产实践。在电视等电子媒介新兴之时,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已经悄然发生。发展至今,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电脑、手机、智能电视等信息接收终端的变革,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都在宣告着一场汹涌的技术洪流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媒介化、视觉化的信息社会。
数字化媒介的广泛应用助推了广告图像的飞速发展,广告图像从生产端到传播端再到信息接收端各具优势。在生产端,数字技术生产模式下广告图像的绘制、复制、合成、优化等制作手段发展迅速,广告图像呈现出近乎逼真完美的色彩、构图,给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图像形态动静结合,从二维到三维的图像化生产,快捷的数字化生产流程,使得广告图像得以批量生产、快速流通。在传播端,“数字化网络媒体等传播渠道又为消费时代的广告图像建构起一个巨大且开放的流动平台,广告图像的流通变得更加自由便捷,传播力度和对接更加快速,信息的传播效率被大大提高了”[3]。在信息接收端,相较于文字,图像的信息传播更为人所钟爱。有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人接收的信息中有80%以上都是通过图像获得的,人们更乐于接受制作精美、表意丰富的广告图像。与此同时,高度媒介化带来信息的大爆炸,相较于文字广告,图像广告传播信息量大,传播效率高,读图成为受众广告信息接收的首选项。
3.传播偏向:图像表意诸多优势凸显
相较于文字化的表达,广告图像符号表意具备诸多优势。首先,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跨国经济活动成为常态,这也就意味着广告的传播活动也要尽可能地适应这一形势,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与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时,广告图像传播的优势就得以凸显,文字作为一种规约符号难以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符号”,而图像化表达有 “让世界变平”的巨大优势。克南·多姆扎尔(Kernan Domzal)甚至喊出了“全球化,必先视觉化”的口号,他认为:“在有效的全球化广告中,文字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对广告主题的视觉体现加以解释,而一则文字广告却要求消费者懂得所使用的语言。”[4]广告传播图像转向在全球化表达中的优势可见一斑。
其次,与以文字为主体的传播方式相比较,以图像为主体的广告传播效率更加高效。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受众的阅读习惯愈发地碎片化,阅读文字需要占用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和阅读时间,文字信息显然难以适应传播需要。而图像化表达具有直观性、易读性较强的优点,广告的图像化表达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的暴露频次,实现更加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同时,广告的图像化能够迅速地向受众传递广告信息,极大地提高传播效率。此外,还兼具表现力更加丰富,传播渗透与传播黏性效果更强等优势。
此外,《宁德市志》[10]记录的是宁德城关方言老派发音,辅音韵尾有 5 个[m、ŋ、p、k、ʔ],其中鼻音韵尾2个[m、ŋ]。沙平[11]对宁德方言同音字汇的研究,记录的是宁德市城区老派方言,辅音韵尾有4 个[m、ŋ、p、k],其中鼻音韵尾有 2 个[m、ŋ]。 林寒生[12]所记录的宁德方言辅音韵尾有 5 个 [m、ŋ、p、k、ʔ],其中鼻音韵尾有 2个[m、ŋ]。
三、广告传播图像转向的伦理危机
广告传播的视觉化转向虽然推进了广告传播的全球化表达,提高了广告的传播效率,促进了广告表现的多元化,但其对消费伦理、文化与人类理性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遮蔽真相:广告核心功能旁落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广告图像作为一种“复制性中介”对物的真实到拟像的承递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过程:“第一阶段:它是某个壮丽真实的投影;第二阶段:它遮蔽了壮丽的事实并异质于它的本体;第三阶段:它让这个壮丽的真实化为乌有;第四阶段:它和所谓的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自身最纯粹的拟像。”[5]至此,物的真实被人为地遮蔽了,影像通过增殖形成景观,成为一种虚拟的实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因此称广告为“伪寓言”,他认为广告的形象画面主导使广告越来越远离客观的商业信息而成为一种寓言。
实际上,广告的视觉形象填补了文字化表达的苍白贫瘠,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感官世界,但却让消费者时时刻刻在“图片仅供参考”的提示中感到不安。深层原因便是广告的图像化传播使得广告的核心功能旁落,客观真实的商品信息永远是消费者最渴望知晓的,而这些信息的告知也应当是广告最本质、最核心的功能。但是,广告的图像化传播使得事实与信息之间的意义链条断裂,转而通过建构完美的物的形象、他者形象乃至理想化的场景来向受众传递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受众对广告图像的拟像化传播信以为真,在一定程度上其知情权就受到了侵犯,广告未能向受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从而形成广告功能的缺位。如果受众对这样的信息保持警戒甚至抵抗,对广告的公信力来说便是巨大的损耗。信息传递过剩,受者却处于“绝缘”状态,广告信息传播行为则难以形成闭合的回路。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一种尴尬与悲哀。
2.唤起欲望:人类价值理性的消解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曾提出著名的“二分法思想”,他认为文字等话语表达与图像表达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话语与图像的二分,隐含着现代与后现代的二分,话语表达以理性为中心,而图像化表达与欲望相对应,以感性为中心。文字等话语表达的理解过程,涉及深度的理性思维,而图像化表达则直接追求视觉冲击。
在广告中更是如此。广告成功的一大秘诀,就是利用图像使商品与其他形象之间建立一种隐含的关系,从而赋予商品更多的感性意义。利用景观化的书写,广告图像将美丽、浪漫、个性、自信等特质与商品牢牢地粘贴在了一起,广告的所指端形成大量的意义堆积。而这样的意义赋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消费者的物欲。例如,抽万宝路香烟,感觉自己像西部牛仔一样自由粗犷,喝百岁山矿泉水,幻想自己像贵族一样高贵。箱包、珠宝等更是将产品与成功等概念相关联,图像符号通过心理暗示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刺激其感性消费、冲动消费、激情消费,而购买欲望的达成成为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广告图像无限放大物质幸福感,利用视觉化的狂欢话语建构美好生活愿景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及自身的经济能力充满信心,诱发超前消费。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资本强大的利润动机,膨胀的欲望钝化了人们的判断力,人类的价值理性面临消解的危机,艰苦朴实等优良品质也遭遇到解构的危险。人们在物欲中释放自己,也迷失了自己,在丰盛的视觉挤压下,人类的精神开始贫困化。人被符号控制,被欲望支配。“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这些由人造出来的物不仅不能为人服务,倒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6]寻找人的自身价值,填补物品表面富裕背后巨大的空洞轮廓,是广告图像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3.图像暴力:过度侵扰与伦理失范
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同时造成了一定的图像暴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广告的图像化传播带有一定的强迫观看的性质,另一个则是指广告图像内容中常包含情色、暴力以及其他不宜传播的元素,给受众带来不安、不适的观看体验。
对于广告的传播内容,受众有看的权力,理应也有不看的权力,但在这样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这一权力好像受到了剥夺。随处可见的广告屏幕,铺天盖地的广告图像,网络弹出式广告等都将人置于图像与景观的包围之中,无处遁逃。与此同时,一些强制性的广告画面还占用人们的时间,海量的广告图像泛滥成灾,正在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人的视觉权力进行双向挤压。受众在其中受到了过度的侵扰,过量的视觉信息也造成了视觉疲劳与视觉麻痹,视觉符号意义过剩,人们面对这一视觉霸权不以为意或是无能为力,任由其愈演愈烈。
其次,在视觉化充盈的传播环境下,很多广告画面开始求新求异,甚至包含一些低俗化元素,挑战着伦理的底线,由此构成第二重图像暴力,不免让受众心生厌恶。同时,一些警示性广告中充满血腥暴力的画面,令观者不适。而图像化传播的含蓄性更是为这类广告大开方便之门,如保罗·梅里萨所说:“视觉说服所具有的隐含性的特征,与文字相比,图像承担较小的社会责任。因而一些用文字表达令人无法接受的广告内容可以通过广告图像加以表达。”[7]同时,图像传播的这一特性也成为其避免法律纠纷的一种潜在机制,但其无疑扰乱了传播秩序,对受众造成了隐形暴力,亟待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四、广告图像传播的风险应对
广告图像的传播过程离不开广告制作和发布者、广告受众、媒介及外部的环境规制等三个方面,要想将广告图像传播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同样需要三方协同发力。
对于广告制作者来说,首先应当避免利益短视,杜绝将广告的生产与传播滑向极端的功利主义。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广告制作中杜绝一切暴力、色情元素。要充分认识到广告人是公共文化的生产者和把关人,应保持较高的文化趣味,坚持以人为本的广告制作理念,摒除低俗恶俗的广告内容。其次,应当明确客观真实的信息告知是广告首要的责任,在广告制作中杜绝过度煽情,过度追求视觉冲击,尽量以平实易懂的图像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引导受众养成健康的消费观念。
对于广告受众来说,应当对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保持警惕,避免在视觉狂欢中迷失自我、随波逐流,在过度的物欲唤起中,追求价值理性和精神思索。要辩证地、保持警醒地看待广告图像传递的信息,审慎地对待广告图像的欲望诱导,树立客观、理性的广告信息解读意识,避免被广告文本所左右。同时,要弘扬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保持人的主体意识。其次,要培养高雅的视觉素养,坚决抵制低俗恶俗的广告图像,对虚假违法的广告行为绝不姑息,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扮演好广告图像消费者和监督者的双重角色。
对于广告信息发布的媒介来说,应当做好规范准入,承担好把关者的责任。把握广告传播的伦理边界,杜绝低俗恶俗甚至违法的广告图像流出,防范广告图像传播的负面效应。同时,应避免广告图像的过度暴露,重视广告图像的过度侵扰问题,用理性的价值观和高度的责任感来规范和引导广告行业发展。目前,在广告图像传播的规制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广告图像传播的一些特性仍成为广告逃避社会责任和避免法律纠纷的途径,必要的法律干预对于广告的视觉化传播必不可少,应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总之,人类永远不能离开观看。广告传播的图像转向难以逆转,而相关的风险应对任重道远。我们应当对广告的视觉化传播保持清醒,但大可不必将广告图像视为洪水猛兽,更无须对广告过分悲观。面对技术文明对人的异化,我们或许应当响应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呼唤,重新反思人类的生存状态,寻求内心的安详和谐与自由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