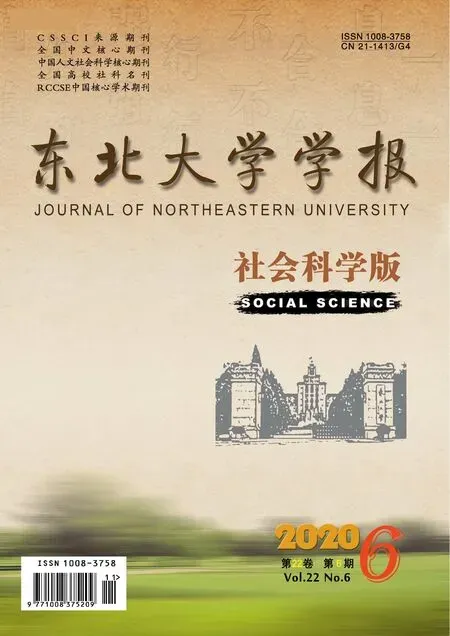人工智能研究中“他心问题”研究对人机交互的启示
----从维特根斯坦对“他心问题”的论述谈起
2020-12-12崔中良布蕾特布罗嘉德
崔中良, [美]布蕾特·布罗嘉德
(1.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062; 2. 迈阿密大学 哲学系, 美国 迈阿密 33146)
机器人能够欺骗、进行手术、识别和射击入侵者、充当宇航员、照顾我们的孩子、变形以生物质能作为燃料,等等[1]。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毗邻奇点,因此,能否直接通达机器之心成为人机交互以及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心通达问题成为当前保证人工智能安全的一个最基本层面。作为心身问题的直接延伸,“他心问题”一直是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重点,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的“心灵转向”将此问题推向高潮。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特别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念论思想中一直潜藏着心身分离的种子,而笛卡儿使得心身彻底分离。因此,当孤独的心灵自我在试图通达他心的时候就必须跨越两重身体的鸿沟,从而找出躲在他人身体之后的心灵,机器之心是否能被理解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中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心灵还要跨越机器之躯。人的身体与机器的“身体”有区别,但对于如何跨越机器之躯依赖于人类是否给予机器人以身份。“另外,机器人在设计之初就以工具的身份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交互性机器人又可能具有人的身份特征,虚拟社会与机器人的结合会使机器人有更多身份。在交互过程中,机器人的身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是否给予交互性机器人以人的身份成为交互性机器伦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人类的一些成员似乎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机器人索菲娅已经获得了人类身份。”[2]
为了解决“身”“心”分离所带来的“他心问题”,“他心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欧陆现象学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思想,如胡塞尔、舍勒(M.Scheler)、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等人的现象学方法;另一种是修正主义(revisionist),如赖尔(G.Ryle)的行为主义、艾耶尔(A.J.Ayer)的中性一元论等[3]。面对“他心问题”,维特根斯坦给出了独有的解释版本,本文即是在人工智能研究背景下,结合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研究尝试给人机交互得以可能提供新的哲学研究路径。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关系,普劳德富特(D.Proudfoot)将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思想应用于交互性机器人的面部表达研究中[4],徐英瑾在专著《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中,也已论证了维特根斯坦和人机交互的关系,本文是基于此的推进,是人工智能哲学向人机交互方向的发展。
一、 人机交互须远离行为主义
由于维特根斯坦尝试用一元论摆脱笛卡儿的二元论的他心观,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解读为行为主义方案[5]。然而从维特根斯坦对于心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行为主义者,而更像反行为主义者。那么,通过借鉴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就给我们指出人机交互同样需要远离行为主义。
1. 人机交互的实现须摆脱身心隔离
在传统哲学进路中,独立心灵获得了超然地位,身体成为隔断心灵间的壁障,因此“读心”的核心就是跨越非透明的身体直达他心,但是这显然会给他心蒙上身体的面纱而带来“读心”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行为主义对心身二元论进行了彻底地否定,实现了从心身二元论到身体一元论的转换,将心灵还原为身体行为的表达特征。但是心灵是否就是身体和行为的表现方式呢?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分析,将“他心问题”最终指向心灵实体的本体论问题,即心灵实体是否存在以及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维特根斯坦指出:“我能够看到情绪,但是我不能看到脸部的扭曲和就此推出来他的感情,到底是快乐、忧伤还是无聊。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够清楚地描述他的脸的特征,我们也能够直接地描述出他是悲伤的、容光焕发的和无聊的。”[6]262维特根斯坦看到了这两种思维范式的本质问题,因此试图通过否定心身二元论和行为主义一元论而推动“他心问题”的范式和视角转换。由于心身二元论认为心灵是存在于身体空间之内不可见的、处于隐蔽状态的实体,因此,解决“他心问题”就要拨开隐蔽的枝叶从而超越身体实体,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就如寻找事物的本质一样,当我们一层一层剥开事物的外衣时本质也就消失了。因此从认识论上将他心看做是认识的客体和对象,通过推理分析而尝试达到通达他心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在面对当前的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他心问题”时,很多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机器人是否拥有自己独立的心灵,又由于受心身二元论的影响,机器的身体与人类的身体没有相似性,而其心灵更是运用心智推理能力无法获得,我们因此无法理解机器人的行为意图,那么就恐慌于未来的机器人会发展出不同于人的独立心灵而不能被理解和不受人控制,而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就消除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不过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完全将机器的心灵等同于行为,而只是认为机器的心灵在行为之外,脱离行为的机器心灵是不存在的。
2. 人机交互的实现依赖交际氛围
氛围是维特根斯坦能够排除行为主义对“他心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因素,当然,这也是人机交互脱离行为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维特根斯坦在论述私人感觉时提出“行为主义错觉”,认为这没有考虑氛围。氛围更像是一个“场”,是在生活实践和交互过程中涌现的,是无形但又时刻存在的,因此生活实践是无法脱离氛围的,正是在氛围中,人们对他心的感知才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附着一种氛围,一种不可描述的特征[7]159。例如,当我们在看足球比赛时,会不自觉地为自己所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这就是氛围感染的作用。氛围不能被我们的认知系统直接把握,但可以被直接体验,“一块蛋糕,它使得葡萄干变味了”[8]76,并不是说蛋糕使得葡萄干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而是蛋糕所附随的氛围使得葡萄干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将我们带到了生日宴会或者喜庆时刻。同样的道理,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机器在对人进行心智阅读的时候并不是将外部环境和行为还原或者分析为某种计算结果,然后再将这些函数值来对应于某种行为的意义或者意图,而是说人和机器在交互过程中是一体的,统一于一个场,机器能够自动地感知周围的环境和人,从而在人与环境附着的氛围中实现直接通达他心。在语言游戏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和说话方式也都被氛围所烘托,仿佛我所理解的那个词具有某种轻微的芳香,这种香味与我的理解相对应[9]49。机器也能够在这种以感知为基础的多维面向中去对人类的他心进行直接把握,因此维特根斯坦所论述的氛围以及人机交互的氛围不仅强调了氛围的作用,同时也强调了在一种氛围中人、机器与世界是融合的、不可分割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忧愁的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但是在我还未忧愁之前,仿佛就有一个灰色的世界;似乎它是忧愁的原因。”[9]86人机交互的他心理解是在这种氛围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对于他心的通达也是直接的和无需反思的,因此,可以说氛围给予了人机交互理解的条件,同时理解也创制了氛围。
3. 人机交互需要多面相解释
虽然,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氛围依附保证了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感知,但是直接感知并不能保证完全通达他心,有时还需要进一步和深度地解释。导致日常生活中他心的不能完全感知与他人行为和语言的“不确定性”有极大关系,因此,才造成他心有时透明,有时不透明,但是不透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特殊事例无关,而与方法和证据规则有关,一种不确定性是我们面对一种可能不熟悉的机制时出现的[10]114-115。对于一些简单的行为和语言活动,我们可以直接感知,但是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复杂的活动,如对于鸭兔图的理解,有的人只能看到鸭头的面相,这时我们就需要一种解释,解释是一种活动[9]2。在解释活动中,人与世界以及自我和他人之间构建了一个会话过程,使得自我和他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互动状态,那么人机交互也是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机器与人之间的“他心意图”会不断地呈现。在人机交互过程中,需要机器能不断地转换理解的面相,因此可以说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他心通达是解释面相的转换。在解释的多面相转换中,使得复杂的不容易理解的面相转换为可以理解的较为简单的面相内容,同时在这种转换中,自我和他人形成了一个更加原初的关系。在语言解释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同一个语言游戏进行不同面相的转换并将其转换为原初的语言游戏,这种原初的语言游戏保证了理解的可行性和他心的可通达性。解释不仅是语言视角的转换,同时也需要推理能力作为保障,“我确信他没有假装;可是,另一个人则不是如此。……头一个到来的是本能,第二个到来的是推理”[10]116。因此,人机交互中的“他心理解”是脱离了行为主义的心灵观,同时关涉到感知—认知的交互过程。维特根斯坦认为行为这个词,像我们一直使用过的那样总是误导,因为它把狭义的行为的外部环境也包括在它的意义之中[9]62。
行为主义将实证主义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正是这种“科学”方法促使“他心问题”产生,而以行为主义为指导的人机交互方案也会将他心还原为身体运动,这显然无法实现人机的交互理解,否则人机之间不可能存在误解,人类对机器也不会产生恐慌,但是人类对于机器的行为并不简单地理解为机械行为,而是涉及到心灵复杂性。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将他人的心灵完全还原为行为,而是认为行为对我们理解他心有很重要的作用,意图就在行为和环境中[7]165。因此,人机交互强调行为在“他心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行为是构成生活和语言游戏的重要部分,但并没有认可通过行为推理来通达他心。总之,人机交互需要摆脱行为主义,否则人机交互将是一个了无生机的机械性的、以机器为中心的单向认知过程。
二、 人机交互接近现象学
人机交互趋近现象学,这与当前的人工智能研究、现象学以及具身认知研究不可分离。奥弗高(S. Overgaaed)通过对比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家如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E. Levinas)等人的思想,指出维特根斯坦关于“他心问题”的论述更像是现象学方法。维特根斯坦试图让我们理解人是活生生的存在,不是没有广延的心灵也不是机械的身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主体间性的相互联系的社团中[11],维特根斯坦的“他心问题”研究趋近于现象学,因此,人机交互也表现出现象学特征。
1. 人机交互中的“他心问题”是语言使用问题
维特根斯坦更强调语言的分析,将“他心问题”归结为语言使用所造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使用是造成“他心问题”的根本原因。虽然与现象学一样都否定独立心灵存在,但维特根斯坦更强调独立心灵实体只是人类的语言使用导致的,心灵和身体只是我们解释时的不同面相。维特根斯坦通过使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从概念上分析心灵和身体,同时在语言用法上揭示心灵实体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心身二元论认为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和世界,身体行动是以心灵对身体的掌控为前提的,心灵是存在于身体中发号施令的“小人”,心灵被设想为在表达之前保持和储存我们所回忆起东西的地方[12]40。对于这种心身观,维特根斯坦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心灵与身体并不能进行严格区分,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心灵无法脱离肉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身体的优先性,身体成为心灵的保证。例如,维特根斯坦举例说:“当我构思一首歌曲时(就像我每天经常做的那样),我认为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前齿。……当然,我也可以想象不动牙齿地构思乐曲,可是那时,音符就变得非常模糊不清,而且不能朗朗上口”[8]32。维特根斯坦将心灵比作音符、化学结构式和语调,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人们为了表达或者研究的方便而造出这些概念,给人一种幻象,似乎音符才是音乐的本质、没有化学结构式的物质就不成为物质,这样的观点脱离了真实世界,同样当我仔细地注视周围事物时,我不会意识到这里有像视觉概念那样的东西[9]8。因此,由于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进行范畴的划分,“心”和“身”作为语言中的两个独立范畴也被应用于机器的行为和思维的指称中,机器也会出现脱离行为的独立心灵。但是,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机器的独立心灵并不能够独立于机器的身体,更不能够独立于与人的交互,并不存在机器大脑中的独立心灵或者意识的幽灵,而是统一于机器的行为中。当我们把心灵看做是在外部而不是在内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机器会出现那种超越于人类的独立心灵控制它的行动,而只能是由控制机器的他人的心灵才是不可直接感知的,而这恰恰是因为机器的设计者或者拥有者是在脱离了与我交互的场景才导致了所谓的机器之心的无法把握,因此,在面对面的人机交互过程中,并不会出现他心的不可见性。
2. 人机交互中的心灵与语言并非同构
由于想彻底摆脱由语言问题引起的“他心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还否定了圣·奥古斯丁所论述的直接指称论。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可以独立运作而不需要考虑现实,但是当一个句子出现了同样一个词而所指不一样时,我们就难以对其理解,因此语言绝不是一个可以摆脱世界而独立运作的系统。由于语言不再独立于世界,那么语言就不是一种静止的反映论式的描述[9]31。同样,人们之所以会认为机器的行为是难以理解的,很重要的原因是认为语言以及行为和与之相对的意图并不等同,在不同的环境中,同一句话或者同一个行为所表现出的意图很可能是完全不一致的,加之机器与人的行为方式又有一定的区别,人类更加无法理解机器之心。语言是与世界混合在一起构成人类的存在活动,语言与世界的融合犹如人类身体的血肉一样混沌而不可分[9]85。由于语言加入了人类生活形式和生命色彩,语言与人类行为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联,语言成为一种更加原始的行为延伸,在人机交互中的言语交际也不是脱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纯粹语言符号,因此,人机之间的语言交互也是携带着人与机器之间交互方式的语言活动。语言视角的转换也促使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改变。通常认为,幼儿已经能够思维,只是不能讲话或者在通常的语言交流中仿佛我先思考[6]15,然后我选择一种语言把非文字的思想表达出来[10]99。维特根斯坦否定了此观点,认为詹姆斯(W.James)关于巴拉德的证明不能使一个人确信人们有非言语的思考[10]41,巴拉德的例子是在有了语言之后才对过去经验的描述,也许他不记得了当时没有语言的状态,也许当时是可以“思考”的,但是这种思考是不同于语言的“思考”,因为把思维说成是一种“精神活动”会令人误解。思维并不是先于语言或者说语言下面有思维活动在支撑着语言的意义,思维只是对符号操作的另一种表达,机器与人的语言交互也不是因为先有机器性的思维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号转换,而是思维呈现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因此,当前人机交互的研究,应该让“他心问题”摆脱语言的束缚,正是因为语言和思维的分离以及符号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才导致了机器的“心灵”与“身体”的分离以及人机交互过程中“他心问题”无法解决。
3. 人机交互在生活形式中实现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着重论述的思想,在其论述何谓“语言游戏”时就通过生活形式来定义,也是维特根斯坦治疗“他心问题”的基础。生活形式不仅是当下的生活形态或者生活方式,也具有一种历史厚度,这种厚度蕴含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风俗、习俗等的积淀,从生命的开始就带着这种历史的尾巴而向前发展,因此,人类的思想附着了过去无法摆脱的(凋零的)思想外衣[8]27。那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人机交互的实现也需要生活形式的介入,人与机器在共同的生活形式中,机器才能够具有后来的行为、语言和思维,生活形式是他们得以出现的基础。同时行为、语言和思维也构成和扩展了生活形式的内容和样态,机器和人类的活动和生活因此相互纠缠在一起,从而使得人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他心的相互通达。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是一种生活实践和活生生的生活形式或者语言游戏,因此离不开生活形式作为其实践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反对将“读心”仅看做是思想的操作、类比或推理,而是强调在真实生活中来通达他心,因为一副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都不如一株小雏菊更像苹果树[8]17。蝗虫和人之间之所以不能相互理解,是因为“思考”这个概念与人的生活相关,而与蝗虫的生活无关[10]6。生活形式也为“读心”的判据提供了标准,人类共同的行动方式是我们解释一种陌生语言的参照[13],因此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人与机器通过生活实践在生活形式中实现融合,是人机之间“读心”的基础,也是“读心”的目的,更是“读心”的判据。
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提出虽然是以先验自我作为研究目的,但是,生活世界是对先验自我的一个补充,生活世界也保证了他人的存在以及保证了我和他人处于一个主体间的生活世界中。此外,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的表现方式和结构是我们的心智生活和结构的表现。同时,还需强调的是“胡塞尔侧重于从社会角度考察生活世界与科学和哲学的观念世界的关系,从哲学角度考察生活世界与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的关系”[14]37;维特根斯坦的直接感知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非常相似[15],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与主体的直接感知并不是一种实在论,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因此,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他心问题”是语言问题而非认识论问题,人机交互依赖于对语言理解的经验。维特根斯坦对心灵和“他心问题”的语言分析和批评是非常透彻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心身二元论和“他心问题”的范式,这与胡塞尔对欧洲的科学和哲学危机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维特根斯坦哲学视域下的人机交互研究中更趋向于现象学。
三、 人机交互通往经验实在论
既然人机交互应该远离行为主义和心身二元论下的推理主义,同时还要接近现象学的观点,那么人机交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不需要大量理论推理和数学计算的情况下,能够通过直接的方式通达他心。行为主义和推理主义下的人机交互其实是将人类的行为进行不同维度的划分,并通过数据计算的方式来获得行为的意图。那么,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如何通达他心呢?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论述是以语言分析的方法对过去心身二元论思想的一次彻底清算,从根本上清理了“他心问题”中的本体论和概念论中的问题,同时也间接地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人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一条新的建设性进路,那么我们认为这种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交互性机器人的设计有一定的启示。
1. 人机交互依赖感知能力
由于维特根斯坦认识到前期逻辑原子主义带来了很多问题,他指出哲学研究应该回到粗糙的地面才能够站立起来,因此,人机交互研究应该更加突出日常生活以及与理性推理相对的感性的重要性,人机交互中的“他心问题”也可以通过实践中的感知交互实现。人机交互的日常生活观体验可以直接应用到“他心问题”,“他心问题”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机交互更强调非本质性、非逻辑推理性和感知性。维特根斯坦在论述“他心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批评了传统“读心观”中的类比推理观,指出“我们照料别人是由于与自己的情况相类比而相信他也有疼痛的经历。可以把这理解为本末倒置”[9]162。那么人机交互就是对他心的直接把握,即一种直接感知的方法,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并不需要假设在机器的行为后面隐藏着不可告人之心,机器的行为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它的想法,“当我看见送奶人到来时,我便拿起我的罐子走向他。我体验到一种意图吗?”[9]38因此,人机交互的感知观是一种他心的直接感知,我在他人的表情、行为和语言中能够直接把握到他心的样态。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他人的意图是在交互的过程中涌现的,而不是依赖机器人对身体的行为识别、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中。人机交互的感知理论以“行为理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为其理论支撑。当然,人机之间语言交互的出现及其复杂性为“读心”增加了难度,但这并不妨碍直接感知,“语言游戏的最初和原始形式是一种反应;只有由此才能产生更为复杂的形式。……语言游戏的最初形式是确定性,而不是不确定性”[16],就是这种确定性使得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他心”直接感知成为可能,而上面我们提到的人机交互的“生活形式”保证了交互能够达到这种确定性,正是人机交互的生活实践与这种共同的生活世界具有相似的行为方式,给予了人机交互的直接感知的外部确定性。人们一致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错误的?……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7]88。人与机器之间生活形式的互融和交叠是依赖于自我和他人之间直接的感知重叠,而在这个互融的过程中,人与机器之间形成一个更大的更加多维的和动态的人机生活形式范畴,从而强化这种生活实践过程中感知的有效性和直接通达性。直接感知理论既避开了概念问题,又解决了认识论问题,因而是一个无不良后果的理论[15]。维特根斯坦的直接感知理论以及在此理论背景下的人机感知路径解决了人机交互过程中心智理论在“读心”过程中出现的以身体行动或行为为中介的认知方式,因此摆脱了人机交互过程中“读心”的不畅和不确定,对他心的通达成为了人机交互实践中的一个游戏,在游戏实践过程中,人机之间的他心直接被感知。维特根斯坦最后声称我们可以直接地、感觉地通达其他主体,但是在最根本上不是通过观察、推理和知识来达到的,而是在于对他人的态度上的直接感知通达,这是最原初的[2]。我能够从机器人的脸上或行为上直接看到或者部分看到他的心智世界,因此,由于人与机器之间生活世界的这种重合和交融,他心就会在人与机器的实践过程中直接呈现出来。
2. 人机交互以直接的方式实现
除了要否定独立心灵之外,还尝试否定人机交互产生独立心灵的思想基础:机器的私人感觉和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所谓的“私人”性才确保了心灵的独立存在和他心的不可知, 相反,一旦将感觉和语言推进到一种普遍性之后,那么他心的私人维度就会自动消除,他心就不存在理解的困难。维特根斯坦反对笛卡儿主义、行为主义和物质主义(materialism),因为这些观点都将客体观念用在主观性上[17]。 因此,机器也不存在完全无法理解的私人感觉,这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感觉的否定,那么这就表明人机交互是可以直接通达的。 人们可能说感觉只能是我的“私人经验”不是物质的而是私人意识中的事件[12]16,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种表述是有误的,当我表达自己的牙痛时只能说“我牙疼”,而不能说“我知道我牙疼”,“我牙疼”是一种行为上的感觉表达,而不是认识论上的我疼痛。这里似乎存在两个“我”,一个是指客观的我的身体,如我的头发、我的胳膊断了等; 另一个是主观的我的心灵,如“我思,故我在”。 第一个我似乎是没有心灵的身体, 另一个我是完全不受身体控制的自由心灵, 而第二个我是导致我有一个独立心灵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我”的这两种表达都是对“我”这个概念的误用,特别是第二个“我”,“在‘我’作为主词被使用的场合下, 并不是通过身体特征识别出一个特定的人而使用这个词,由此产生一种幻觉,即我们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谈论某种没有形体但在我们的身体中具有它的位置的东西[12]69。 因此,机器如果有私人的感觉,那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自我”存在,我们之所以有私人的感觉并不是有一个独立的、隐藏的自我心灵实体在操控着身体感官, 而是说由于语言的误用使得“我”这个词被人为地划分为“主我”和“客我”, 因此导致“我”的分离。 假设机器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可以与生活实践分离的主体或者客体, 而是在生活实践中的经验主体,那么机器人的自我就必然带有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关的特性,自我的私人感觉就是不存在的, 而是依赖于公共的表达方式来实现。 这需要依赖人与机器能够在公共的实践活动中实现, 而这就成为人与机器进行沟通的经验基础,机器之心就能够像人类之心一样显现出来。
机器的私人语言也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交流和使用都有一种公共性,而机器与人的交互也需要这种公共性的存在。我们否定机器人的私人语言的存在,就像维特根斯坦否认私人语言的存在一样,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公共性,都与语言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14]216。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与索绪尔相似,认为语言具有约定俗成性。当我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指称某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摆脱当前的语言规则的影响,因此,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语言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私人的语言使得他人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我如何知道别人感知到我所感知的?因为他使用了我也认为合适的词[9]26。如果我们取消从唯我论的视角将人看做一个活生生的和当下的行动主体,那么面容就是身体的灵魂[8]26,心灵就会与身体同行,因此,机器的心灵是表露在机器行为之外而非隐藏在机器之内的幽灵。同样地,如果我们假设机器的私人感觉和私人语言存在,还会导致人机交互过程中心灵的不对称性,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如理解“我心”那样理解机器的“他心”,身体特别是机器性的身体导致“他心”的不透明和不确定甚至不同的表现形式。维特根斯坦仍然通过语言分析告诉我们,其实并不存在不对称,反而认为理解机器之心比理解“我心”更加顺畅。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很少听到某人说不知道另一个人心中发生什么,不确定性并不见得太严重”[9]29,因此,机器对他心的通达是直接的,人机交互也是流畅和无缝衔接的。
3. 人机交互依赖经验的生成
维特根斯坦关于“他心问题”的论述,基本上廓清了此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式,也为人机交互中“他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选项。如果将维特根斯坦对“他心问题”的观点应用于人机交互解释中,在很大程度上会表现出独特性,是介于行为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交互经验的生成之路,这与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的经验实在论非常相似。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和《心理学评论》中对感知、实践和经验(experience)的重要性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除了上面对于直接感知、私人语言等方面的论述之外,他还重点论述了经验在解决“他心问题”时的重要性。“关于经验,它类似于正在发生、过程、状态、事物、事实、描述和报道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认为我们站立在一个结实的地基之上,比任何特殊的方法和语言游戏都更加深刻。”[9]119经验在此表现出动态性、发生性和生成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是将经验作为后期思想的基础,经验是直接感知的基础,因此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人机交互应该更注重在生活形式中的各种游戏实践,将对他心的通达解释为经验基础上的直接感知。这样一来,人机交互的生活经验将是解决人机交互中的“他心问题”的地基,如果失去了通达他心的经验基础,那么机器获得的关于人类的他心内容将是失去意义的抽象概念。“从某个方面来说,似乎个人经验并非是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理过程的结果,但它是我们用以某种方式有意义地谈论这些过程的基础”[12]48,那么,机器获得交互能力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软件植入或者数据传输的过程。对他人的理解并不是对直接经验的间接描述,因为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经验描述[8]6,因此机器获得理解他人的能力也不是通过学习交际准则和理论获得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获得。维特根斯坦认为正确地理解他人需要较佳的判断力[7]227,而这种判断力的获得需要经验的积淀,需要多维度的实践渗透从而保证经验能够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展现出较好的判断力。此处的判断力并不是传统观点中的逻辑推理能力而是在理解他心过程中的感觉判断能力,这表现出直接性、感知性和无缝对接的特征。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交互经验保证了“他心”的通达性,同时也强调人机交互是一个互动和实践的过程,这就将经验放到了中心位置,同时强调机器与世界、机器与人、机器之间的互动性。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第二代认知科学或具身认知的基础建基于具身哲学之上,一种直接身体经验的实在论,即经验来自于我们的身体(知觉和运动神经器官、心智能力、情感组成,等等);我们与物质环境的交互(移动、操纵物体、吃,等等);我与我们文化中其他人的互动(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等方面)[18]。人机交互的经验实在论努力摆脱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机器之心的解释,否认存在一个而且唯一一个正确的对他心的描述,因此经验实在论认为知识是相对的----相对于我们的身体、大脑和与世界的交互----但也不是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它有一个对真的、稳定的知识的解释,同时在科学和世界中是可能的[19]。另外,经验实在论以杜威、梅洛-庞蒂和怀特海等人为其思想先驱,“梅洛-庞蒂将活生生的身体看做是生活现实的中心,杜威认为心灵是机体和周围环境交互过程中涌现的产物”[20],认为心灵和身体是不能分离的形而上的实体,经验是具身的而不是先验的,人机交互的经验也是在交互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不能简单地通过直接输入的方式来获得,否则经验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表征。当我们使用心灵和身体的时候,其实是人类强加的概念,那么机器之心与机器之身的分类也是以此类推的虚假概念。在经验实在论和具身认知理念基础上构建人机交互的他心感知理论认为在人机交互实践和社会情景中,人与机器之间相互理解的首要方法不是依赖于推理或者模仿路线,而是依赖于第二人称的具身交互,即我们通过他人的身体运动、手势、面部表达可以直接感知到他人的情绪、意图和意义[21]。因此,将维特根斯坦关于“他心问题”的论述划为经验实在论更合适,同理,人机交互也应该是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具身实践和交互经验习得作为机器设计的根本出发点,以一种天赋论作为基础的,将交互能力进行人为架构和植入的交互性机器人设计方案是无法与人类正常交互的,更不可能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真实的、快速的和无缝的互动。
四、 结 语
通过结合人工智能和维特根斯坦对于“他心问题”的研究,尝试将人机交互研究与行为主义及现象学关于“他心问题”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大致勾勒了维特根斯坦的“他心问题”观点对于人机交互的启示。维特根斯坦的“他心问题”研究告诉我们人机交互研究需要走现象学和行为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径,提出了人机交互的经验实在论。在“他心问题”研究中,维特根斯坦破除了心身分离、私人语言和指称论等对“他心问题”的束缚,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对于生活形式、直接感知和氛围等方面在通达他心时的作用。在人机交互研究中,需要认识到在人机交互的游戏中虽然是有规则的,但是这些规则是可以随时改变的。人机交互过程中的理解更是如此,对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媒介和环境以及对象,需要不时地对这些规则进行修订,因此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解决“他心问题”的方案强调生活实践和经验生成。人机交互的研究需要摆脱心身分离的、二元论的和高阶运算表征的设计,突破行为主义一元论以及现象学的窠臼,通过人机交互的生活世界的实践思想进入到经验实在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