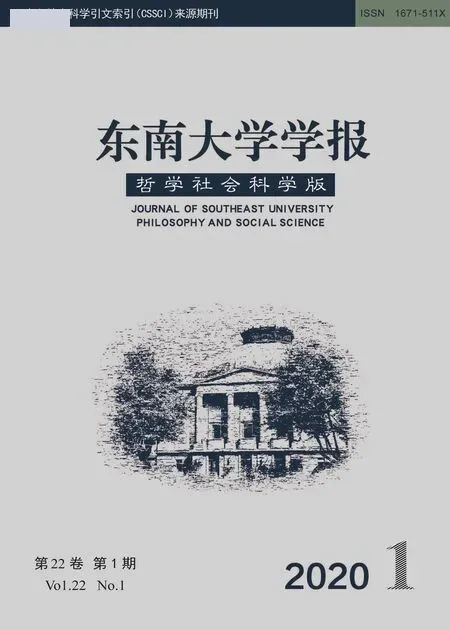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对道德义务根据的一种探究
2020-12-11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道德义务根据的思考可有诸多角度。本文以“苏格拉底自辩”与“艾希曼自辩”为关照,从义务论角度,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道德”与“伦理”的关系,从学理上进一步澄清关于“道德义务”根据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苏格拉底为什么选择既服从城邦法律的审判,又要做那著名的自我辩护?苏格拉底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深刻隽永精神是什么?如果将苏格拉底之死与康德自由意志精神、黑格尔区分“道德”“伦理”思想联系思考,苏格拉底的选择在义务及其根据问题上可以给我们哪些启迪?
因阿伦特“平庸的恶”思想出名的艾希曼,在法庭自辩中提出了“艾希曼的康德”问题。艾希曼声称自己的行动深思熟虑,遵循了康德“绝对命令”的道德哲学,认为遵守道德义务不需要任何特定理由,“你的义务”就是“履行你的义务”,遵守法则、服从元首意志的义务就是自己的义务(1)[英]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刘曦,杨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在艾希曼这里,康德义务论沦落为法西斯行为的辩护工具。“艾希曼的康德”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与苏格拉底自我辩护相比,艾希曼自辩的诡辩要害何在?义务是否仅仅只是服从命令?服从的是何种命令?义务的根据是否内在包含良知反思?任何命令都是绝对的吗?等等。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则不仅是对康德义务论的亵渎,更会在实践中导致严重社会后果。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可以理解为关于义务的学说,并认为道德义务是人基于绝对命令的自我立法。康德关于道德义务的思想无疑深刻揭示了道德义务的绝对性与神圣性,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如何在坚持道德义务的同时避免“为义务而义务”的抽象,如何使先验面对经验;另一方面,如何避免“艾希曼的康德”,避免“平庸的恶”。黑格尔在高度肯定康德自由意志精神的同时,不满其“为义务而义务”的抽象空洞(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6、137-138页。。他要在康德基础之上进一步引入共同体及其规范性秩序,使自由意志及其义务具有客观规定。黑格尔明确区分了“道德”与“伦理”,并使“道德”统一于“伦理”。黑格尔的这一工作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理解道德义务的空间:黑格尔区分“道德”“伦理”的真实旨趣何在?“伦理”与“道德”如何统一?“道德”如何在“伦理”中现实存在?主体的自由意志精神与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秩序如何协调?道德义务的根据究竟是“伦理”还是“道德”?现代社会的道德义务根据究竟何在?
现代社会有两种背景性框架:背景性制度框架与背景性价值框架。这两种背景性框架既互构互成,又规定了人们的义务,并塑造着社会成员的人格(3)参见[加拿大]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9-37页。。问题是:如果两种背景性框架不吻合,社会成员的具体义务依据究竟为何?作为背景性框架的制度是否可以脱离同样作为背景性框架的价值精神存在?在规范性秩序背景中,主体的自由意志精神或美德是否重要,如何存在?罗尔斯通过对制度性义务要求限制的方式对此做了大致回答,认为制度所提出的义务要求是职责义务,职责义务是相对义务,它以制度正义为前提(4)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6-90页。。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何以认定相对性的职责义务不再具有有效性?在职责义务失却合理性时应当以什么作为义务以及选择的根据?
伦理学总是要研究规范、规范性的。然而,如何理解规范、规范性?现代多元法治社会既有多种完备性学术体系、多种价值观念,又有制度体系所构成的规范性秩序。一个良序社会当然不可缺少行为层面的规范性秩序,不过,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注意或强调行为的规范性,是否会有意无意间忽略社会良知精神与人本价值文化?如果说规范性秩序是可持续再生产的,那么,此可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离开了基于良知的主体自由意志精神是否可能?任何具体社会行为规范总是有条件的,对那些失却存在合理理由的规范的自觉批判构成法治秩序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对这种内在否定性应如何看待?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给个体基于良知的自由批判精神留下空间,还会有活力吗?显然,这里有某种“伦理”与“道德”义务间的紧张问题。
20世纪末,何怀宏提出“底线伦理”,笔者提出“基准道德”,均强调道德义务的基本、底线特质。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一个社会(乃至人类)不能没有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在什么意义上提出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才与现代法治社会历史进程内在一致?另一方面,如何重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传统文化中哪些内容具有永恒性?这些具有永恒性的内容如何在今天焕发青春?对此类问题的追问总绕不过“伦理”“道德”。当我们说“底线伦理”“基准道德”时,大体上是从“伦理”角度而言。“伦理”的与“道德”的角度有区别吗?彼此间是否具有内在张力?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是否有合理理由以某种高贵、神圣的名义,强制要求人们去做某种高贵、神圣的行为?人们又应在何种意义上坚守高贵人格与良知?无疑,道德义务根据问题有待学理上的进一步澄清。苏格拉底之死、黑格尔关于“道德”与“伦理”的思想,则有助于刺激思考并澄清思想。
二、作为本分的义务
在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黑格尔“道德”概念的核心是个体自由意志及其反思性批判精神,其要旨是主观、主体;“伦理”概念的核心是实体性关系秩序,其要旨是客观、关系、秩序。在黑格尔思辨体系中,由“抽象法权”至“道德”再至“伦理”,“道德”最终统一于“伦理”,在“伦理”中实现了“概念的调和”(5)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2页。。黑格尔将“道德”统一于“伦理”是要引进社会历史性,克服道德的纯粹主观性,使个体自由意志在社会历史中得到现实实现。然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道德”统一于“伦理”,如何理解此“调和”?如何理解个体自由意志“在社会历史中得到现实实现”?
黑格尔区分“道德”“伦理”是在康德基础之上的前行。要合理、准确理解黑格尔这一做法及道德义务思想,就方法论而言至少须注意两个大的方面。其一,道德“义务”的客观性。此“客观”有双重意蕴,一是普遍性意义上的,一是摆脱空洞抽象性意义上的。主体自由意志道德行为选择当然须听从自己的良心,然而,道德自由不应是“病态的”(6)参见[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2、182-184页。。道德“良心”不能自我规定,它须有客观内容,须是那“绝对”、自由“理念”的命令,须是善(或中国古人所说天道、天理)在心。黑格尔区分“道德”“伦理”就是要进一步祛除康德道德义务论的抽象空洞性。黑格尔甚至否认我们能够在康德的意义上有自己的道德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在既有的机制性现实中,既有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对个人有某种“无法改变的约束力”(7)参见[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9-180页。。一旦道德义务不再是康德所说“纯粹”实践理性的,而是“人类学”经验生活意义上的,道德义务就是鲜活、具体、丰富多样的。离开了现实伦理实体及其秩序关系,就无法合理把握“义务”的具体规定与真实内容。其二,黑格尔的否定性是内在生长性的否定性,因而,其“伦理”对“道德”的否定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伦理”将“道德”收回自身,成为自身的内在要素。此否定性过程,既是“道德”在“伦理”中的现实存在过程,又是“伦理”实体自身的内在生长过程。具体言之:一方面,自由意志的“道德”精神只有在“伦理”中才能成为真实的。主体的自由意志精神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领域,只要有“伦理”关系、有人的现实活动,就有“道德”,“道德”现实地存在于“伦理”中。离开了伦理共同体及其秩序关系,则所谓自由意志精神,不是水月镜花就是任性。另一方面,“伦理”共同体是具有内在生长性的生命体。“伦理”的内在生长性离不开“道德”,离不开个体的自由意志精神及其创造性活动。主体听从良心的内在批判性使“伦理”实体获得不竭的生命源泉。黑格尔思辨体系中隐含的“道德”与“伦理”关系的此层意蕴,向我们展现了理解道德义务的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方面。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50节谈到道德义务、人应当做什么、如何成为有德的人时,有一段著名论述:“一个人必须做的事务,就是义务,他要履行哪些义务,以便成为有德行的人,这在伦理共同体中是容易说出来的——这不牵涉他任何别的事情,而仅仅涉及他的人事关系中预先表示过的、言语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务。”(8)[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9页。在此,黑格尔清晰地表明,道德义务是“必须做的事务”,履行道德义务的人就是“有德行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此“必须”?黑格尔意义上的“必须”是“伦理共同体”“关系”的规定、要求。所谓“必须”就是做此具体秩序、关系中所规定与要求的,这是应尽的本分。此“义务”因其是“必须做的”而成为本分。尽义务就是尽本分。所谓“本分”是事物内在规定本当如此、本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至于什么是“必须做的事务”或“本分”,只有在伦理共同体中才能做具体判断。所谓在伦理共同体中做“具体判断”,即是在伦理共同体具体伦理关系中所明确提出的那些“必须”履行的事务与要求。在此伦理关系中,“义务”具有具体确定性,而不再是抽象不确定的。它是伦理共同体对个体的具体要求,是在此伦理关系体系中的个体“必须”做的职责。它并不针对某一特定个体,而是针对身处此具体关系的任一个体,是实体对此具体关系纽结中的“角色”提出的“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求,在此意义上,它是角色的“义务”。它既是作为此“角色”个体不可推卸的义务,亦是维系此伦理共同体秩序所必要。此“必须”是实体对个体、共同体对角色的特定要求,是个体无法推卸的“本分”。显然,此“义务”根据排除了任何来自主体、主观的因素,不是主体主观,而是“伦理共同体”。由于此义务根据是“伦理共同体”且此义务是“伦理共同体”关系的具体规定与要求,它在根本上就属于“伦理的义务”,且不同于后面所述的“道德的义务”。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道德义务是做伦理共同体所要求的,且伦理共同体所要求的是关系纽结中的具体职责,那么就会面临几个困境:其一,这不合乎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道德”不是在“伦理”中获得生长,而是被简单抛弃。同时,这亦不合乎黑格尔的本意。这在紧接其后关于“正直”的讨论中可以体会到。其二,一切道德义务就是外在于主体的,主体的道德行为选择乃至一切人的活动中的主体、主观因素就会从根本上被湮灭,人只是规则、规范的机械服从者。其三,苏格拉底自辩就是不能被合理理解的,艾希曼的自辩就是合理可接受的。显然,道德义务的根据并不简单地只是“伦理的”,而是还有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此相应,人的“本分”亦应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
也许黑格尔意识到了“伦理义务”缺失主体反思性的局限性,意识到伦理共同体不能没有主体及其反思性批判精神,他在上述那段论述后紧接着就讨论了“正直”。此“正直”指忠实履行伦理共同体中这些“必须做的事务”。“正直”当然是种美德。不过,在黑格尔看来,“正直容易显现为一种较低级的东西,人们还必须超越正直而对自己和别人要求更高的东西”(9)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8页。。即,忠实地履行具体伦理关系中所提出的这些具体“义务”要求还只是“较低级的东西”,人还应当追求“更高的东西”。此“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可能的回答大致有二。其一,选择恰当的行为方式,做“恰当”的,以实现伦理的要求。这正是黑格尔稍后强调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所要表达的内容。其二,义务中的“自由”精神这一绝对内容。遗憾的是,黑格尔在此思想陷入混乱。在黑格尔心目中,“伦理”是“这更高的东西”,伦理性要求是“真”的义务。不过,如果依黑格尔自己的理路,一切义务都是自由精神的“定在”,那么,除非将“伦理”直接等同于“自由”精神这一“绝对”本身,否则“伦理”就不能成为这绝对、最高的东西本身(10)黑格尔确实将“伦理”作为“绝对”自身,视“国家”为地上行进的神,使自己原来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理论变得保守。。因为说到底,“伦理”也只是此最高东西的显现。道德“义务”中那“更高的东西”中的“最高”东西,是“自由”精神自身。这样,以“伦理”作为绝对本身并规定“道德”,就有僭越之嫌。此“僭越”正是黑格尔绝对体系中的含混与保守处。其实,区分“伦理”与“自由”精神本身极为重要。至少就本文思考范围言,一方面,伦理共同体及其规范性秩序本身有“真”“假”问题(即不是“伪”或“病态”的);另一方面,这种区分为“良心”及其反思批判性活动提供了存在的根据与空间。来自良心的反思性批判精神为听到那“更高”乃至最高东西的声音提供了可能。听取那来自更高乃至最高东西的要求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义务(本分),甚至是更为高级的义务(本分)。
这样看来,黑格尔试图通过“伦理”规定“道德”的方式克服康德抽象义务论的努力,未必如其所愿般成功。不过,黑格尔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将“道德”收回“伦理”并以“伦理”规定“道德”的思想,深刻且极有意义。首先,黑格尔以自己的方式在康德基础之上揭示道德义务总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离开具体社会关系的道德义务是抽象空洞的;道德义务的最终根据不是主体良心,而是“自由”精神本身;区分了主观良心情怀与客观规范性秩序,强调客观规范性秩序对于主观良心情怀的优先性。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共同体规范性秩序是现代宪法法治秩序的,他是在现代宪法法治秩序背景中区分道德、伦理的。黑格尔的“道德”指向主体反思性精神、良心美德,“伦理”指向共同体关系体系及其宪法法治规范性秩序。其次,黑格尔以自己的方式揭示“道德”不是主体纯粹心灵的空灵幻境,主体自由意志精神一定要呈现于外,显现为鲜活的行动。只有在“伦理”中,“道德”才能成为鲜活、真实的,主体才有可能尽其“义务”本分。不过,这就进一步提出问题:“道德”如何在“伦理”中存在?伦理的“本分”究竟有哪些?如何才是真的尽“本分”?
三、两种“本分”
如前所述,“伦理”之所以需要“道德”有两个基本缘由:其一,使伦理具有主观性,由自在的变为自在自为的;其二,“道德”精神的内在批判性是“伦理”的内在生长性机制。前一方面黑格尔有较为明确的揭示,后一方面则隐藏于其论述的字里行间。由于后一方面直接关涉对“本分”的全面深刻把握,故更应仔细发掘。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50节那段论述后谈到了道德崇高、天才,认为它们是对伦理共同体“未开化”状态这一“缺陷”的“弥补”。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本分”义务以及现代社会的道德义务特质。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德行只有在超常的处境以及在那些关系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地位和现实性。”他同时强调此种“冲突必须是真正的”。“当社会和共同体还处在未开化状态时……伦理性的东西及其实现更多地是某种个人的独卓的天才本性的表现。”(11)[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9页。什么是伦理共同体的“未开化状态”?为什么伦理共同体“处于未开化状态”时会更多地看到道德“天才”?什么是“真正的”冲突?黑格尔此处想表达什么?伦理共同体“开化”指分化、文明,所谓“未开化状态”指社会共同体缺少分化发育,社会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并未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与显现。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是“伦理还没有成长为独立发展的和客观性的自由体系”,还没有独立个性与自由意志。在此伦理共同体中,没有个体、个性、权利。伦理共同体的这一缺陷“必须由个人独卓的天才来弥补”(12)参见[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0页。。即,在“未开化”社会,个人应做什么的道德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主观理解或偏好,这给道德“天才”的产生提供了合理理由与现实空间。社会义务规定“未分化”的混沌性,使得一些人对义务的理解与担当会在“超常”情况下表现出“超常”的精神。
然而,在分化、文明了的“开化”社会,由于有了个体、个性、权利,由于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并明晰了权利—义务关系,一个人应当做什么的义务就有了客观明确规定,这些明确规定就成为“必须”做的“本分”事务。此“必须”是伦理共同体客观关系结构的明确规范性要求。这意味着当伦理共同体克服了“未开化”缺陷、分化发育形成了“自由体系”时,“必须做的事务”就在具体规范性秩序中获得明确规定,伦理共同体就在一般意义上不再需要来自道德“天才”的努力去“弥补”那“缺陷”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体系机制较为健全、权利—义务关系结构较为明确的现代社会,一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本分”义务,通常在共同体具体关系体系及其规范性秩序中有较为清晰、具体的规定——他只须做此具体伦理关系中所具体要求的。“这不牵涉他任何别的事情,而仅仅涉及他的人事关系中预先表示过的、言语承诺过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务。”(13)参见[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9-290页。也许黑格尔如此说有点绝对,但基本思维方向明确:对于伦理共同体言,一个人的道德义务首先是尽本分,做好那个角色所要求的,完成具体社会体系结构及其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具体规定、要求。做好这伦理角色本分即是履行道德义务。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如此履行了共同体规范性秩序要求就真的是“尽本分”了?是否在具有健全规范性法治秩序的“开化”社会中就不再需要主体的反思性精神了?宪法法治秩序生长的自身内在动力机制何在?主体在此意义上是否只是执行命令、服从支配的纯粹工具——如同艾希曼自我辩护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一切恶行均可在此“义务”名下获得合理性辩护。显然,尽“本分”的“义务”还应当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遵从共同体规范性秩序要求是“尽本分”,但不是全部,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此“尽本分”还只是基本道德义务要求。因为,一旦共同体中的个体缺失反思性精神、批判性态度 、自由意志能力,共同体就失却生命活力;个体基于良知的反思性精神也是共同体“尽本分”的要求。从“伦理”的内在生长性言之,“伦理”对“道德”、共同体对个体还有更高要求。换言之,共同体的“本分”要求有两种,来自“道德”良心的反思批判性精神是更高层次的“本分”要求。
杜威曾通过“风俗”与“道德”的关系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重要思想——个体道德不能自成根据,道德义务有其确定性标准,并认为“风俗构成了道德标准”。不过,杜威不仅强调共同体既有关系秩序乃至文化价值观念等对于个体道德的意义,而且极其强调个体反思批判精神对于共同体风俗重构演进的意义。杜威要为个体独立判断、批判性反思、创造性精神留下广阔天地,个体道德与社会风俗是开放性互构关系(14)参见[美]杜威《杜威全集(第14卷)》,罗跃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48、62页。。个体当然生活在共同体中,但是,共同体亦非游离于个体之外。共同体的生命力在于个体的批判性反思能力与创造性精神。
理解道德“义务”“本分”及其根据,不能离开伦理共同体生命活力、内在生长性。黑格尔区分“伦理”“道德”并将“道德”收回“伦理”,是以一种思辨方式表明“道德”是“伦理”自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它不仅使“伦理”由自在的成为自在自为的,而且还使“伦理”成为生长着的生命有机体。伦理共同体何以具有生命力与生长性?就“道德”与“伦理”关系角度而言,至少可以发现“伦理”共同体的生长不可缺少个体自由意志与“道德”良心反思性批判精神。黑格尔区别“道德”“伦理”并将“道德”统一于“伦理”、主张“伦理”较之“道德”具有价值优先性的思想有一前提:此“伦理”为自由精神的定在,是已经完成了规范性重构、确立起宪法法治秩序的伦理共同体。在此宪法法治秩序伦理共同体中,守法尽本分优先于个体良心。不过,根据黑格尔本人思想,伦理实体有真幻之别,如果伦理共同体不是真实的,仍处于“未开化”状态,那么,伦理共同体首先需要的是来自道德“天才”的良心反思性批判,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秉天命、天道、人心的道义担当精神。此种道德良心批判、道义担当本身就是伦理共同体的“本分”要求,是如同罗尔斯所说的基本的“自然义务”(15)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现在需要思考的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在建立起基本宪法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实现了规范性重构任务后,“伦理”是否还需要“道德”,“良心”批判是否还有存在的合理理由?黑格尔对此的思考是含混不清甚至是保守的(16)黑格尔在谈到国家法律义务时明确反对“良心”,将听从“良心”的声音视为“赤裸裸的任性”。其想强调法、制度的权威性是合理的,但是,在关于法、制度本身是否要经受持续反思,是否还要面对“良心”等问题上,却失之僵化保守。他在讲到主权关系、战争中的牺牲精神时甚至主张“绝对服从”、做“没有头脑”的机器。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2、344页。。他认为良心在伦理实体中“消失了”(17)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1页。。黑格尔这一说法所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在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权利—义务关系分化明晰的社会体系性中,伦理角色义务“本分”具有确定性;在摆脱了义务主观“任性”的意义上,良心“消失了”。这不无道理。但是,不能据此得出结论,以为在“伦理”中不再需要个体“良心”了。即便是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伦理共同体也不能没有道德良心。其实,即便根据黑格尔本人的思想逻辑,人类在双重意义上也永远不可缺少良心。其一,人类历史就是自由及其实现的过程,没有个体、个性及其自由意志,就没有自由。这在《历史哲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中均有明确表述。其二,“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未必总是合理的,对绝对精神、“天理”的追求是永恒的。主体道德良心反思性批判构成社会历史生长的精神动因。离开了主体良心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对公平正义伦理共同体体系的自觉捍卫,任何伦理共同体都不可能长治久安。罗尔斯在公平正义制度设计中为非暴力反抗、不服从留下空间,也就是为在政治生活中保留良心及其批判留下空间。
这样,主体在伦理实体中坚守道德良心的积极批判活动也是一种尽“本分”,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尽“本分”。换言之,作为道德义务的“本分”有两类,一类是具体伦理关系中规范性秩序的规范性要求,这是具体角色义务(18)此“角色义务”须做广义理解,它不仅包含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具体职责角色规范,甚至还包括作为具体角色所在共同体的一般习俗规范。因为这些一般习俗规范是构成具体角色不可或缺的部分,离开了这些一般习俗就无法准确理解具体角色及其职责规范。;一类是伦理实体精神本质的要求,它通过主体“道德”良心被把握,这是良心义务。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伦理实体,不仅要求人们尽具体角色本分,而且还要求并包容、容忍“道德”良心批判这一更高层次的本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通常所说“道德义务”的更为丰富的内容。我们习惯于说一个人要有“道德”,然而,它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的“道德”?这有两种相去甚远的理解:良心的,角色美德的,前者为“道德的”,后者为“伦理的”。良心意义上的道德义务指向的是关爱生命、尊重人格及其尊严、人道等,角色美德意义上的道德义务则指向责任感、纪律、诚实、守诺、礼貌等。也许我们说到“道德义务”时往往未区分二者,甚至更多的是角色美德意义上的,然而,这恰恰是需要澄清的。这未及“道德”要义。良心意义上的“道德”直接指向人性,是做“人”、成“人”。角色美德意义上的“道德”则直接指向社会共同体关系结构及其规范性要求,是各在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秩序,是关于具体成员的具体素质、职责分工的。如果讲“道德义务”只讲角色美德义务,不讲人性、生命关爱、人格尊严、人道等“成人”义务,只讲“伦理的”义务,不讲“道德的”义务,则缺失了人性与灵魂。它所追求的不是具有人性、自由意志精神的主体,而是循规蹈矩的工具。这正是“艾希曼的康德”的要害。
艾希曼以康德“绝对命令”义务论为自己的纳粹行为辩护,认为义务是纯粹的,遵守命令不用任何理由,只须服从。他认为自己遵循了康德的义务论哲学。艾希曼阉割了康德“义务论”的自由意志精神,不仅将其歪曲为纯粹形式的“绝对服从”义务,而且还使主体沦为没有反思性能力的、仅仅履行“命令”的纯粹工具或麻木行动者。但是,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艾希曼作为一个人难道不应当有人性吗?艾希曼真的是麻木不仁,真的对屠杀暴行没有任何心理、情感的人性认知判断吗?艾希曼真的可以没有珍惜人的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的”义务吗?众所周知,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行为主体是有自由意志能力、有判断力的,康德意义上的义务是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是“道德”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艾希曼只强调了康德义务论的形式绝对性,无视其自我立法的自由意志自律性。艾希曼钻了康德义务论过于强调形式化的漏洞(19)康德形式主义义务论的局限,不仅有黑格尔所说“为义务而义务”(只问动机,不问结果)的空洞、忽视义务的层次性,而且还有“艾希曼的康德”所暴露的因其形式化而进一步被抽象掉“善良意志”的可能,仅仅剩下“服从命令”的形式化义务。。艾希曼用康德义务论哲学自我辩护,不仅将“道德”的义务混淆为“伦理”的义务,而且还进一步将“善良意志”空壳化并偷换成纯粹形式化的“服从”,用“平庸”为其“邪恶”辩护,以“平庸”遮蔽其“邪恶”(20)参见[英]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刘曦,杨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313-314页。。
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中的艾希曼“平庸的恶”现象,为我们深刻理解在履行道德义务中坚守“道德”良心的重要性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案例。“道德”良心可以抵制“平庸的恶”。服从命令、履行体系机制的规范性要求是“伦理”的角色义务,而能够为主体提供不服从命令、抵抗体系机制规范性义务要求做有合理理由辩护的,正是“道德”良心。服从体系机制的规范性义务要求是“本分”,捍卫自由精神、抵抗“平庸的恶”的不服从命令亦是“本分”,而且是更高的“本分”。如果说耶路撒冷法庭审判中有“国家的法”与“人类的法”且“人类的法”高于“国家的法”(21)参见[美]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79页。,那么,作为行为主体得听从的命令就有来自于上级的(“国家的法”)与来自于良心的(“人类的法”),且在二者明显冲突时后者高于前者。艾希曼自我辩护中所提出的“艾希曼的康德”关键在于:以康德义务论的绝对命令之形式,遮蔽、阉割其灵魂;阉割义务的自由意志本质,仅仅强调服从,以“他律”取代康德的“自律”。“艾希曼的康德”中的义务,是无自由意志、无自律、无良心的义务。它所要求的只是无头脑的机器、无心肝的工具。是否作为主体存在,是否有善良意志,是否有良心,是否给主体保留有最后选择“不”的权利与空间,这些正是“艾希曼的康德”不同于康德义务论的原则之处。阿伦特斥责艾希曼为“平庸的恶”,这不失合理,但欠深刻。说其“欠深刻”的理由在于:“平庸的恶”概念具有模糊性,“平庸”的“恶”既未能深刻揭露其“邪恶”本质,亦未能从根本上有效回击艾希曼的哲学理论狡辩。“平庸的恶”混淆了“平庸”与“邪恶”,并有以“平庸”遮蔽“邪恶”的嫌疑。阿伦特晚年在明确提出反对“ 平庸的恶”基础之上,持续思考“集体责任”“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等道德责任问题,强调一个人要与“自我在一起”,要唤起“良知”“拯救道德”,这就深刻得多(22)参见[美]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112-115页。。一个人不能以集体、专制、暴政等为理由替自己的堕落、邪恶行为辩护。艾希曼的自辩以极为尖锐的方式揭示:应当合理区分“道德”与“伦理”两种义务形式及其根据。
迈内克在反思现代德国历史时深思:一个原本有着灿烂文化与法治秩序的国家是如何走向反自由、反文明的纳粹军国主义的?他揭示:德国军国主义之所以能一时兴盛并有力量,就在于它强调并拥有通常看来毫无疑问令人赞美的“高度道德品质”,如“铁的责任感”、严格的“纪律化”、不假思索的“服从”、服役时的严格“禁欲主义”等。拥有责任、纪律、服从、自律精神的集体,当然能具有非凡的力量与气势,然而,如果仅仅具有此等美德,而没有灵魂、良心,则是无心肝、无头脑的钢铁机器。此种机器一旦被邪恶力量利用或支配,其毁灭性令人恐惧(23)参见[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52、55-56页。。如果我们只是一般地讲要有“道德”,培养“美德”,而不首先关注人性的培养,不关注生命、尊严、人格平等这类核心、灵魂,则“美德”就有可能沦为奴役与支配的工具,沦为“平庸的恶”乃至邪恶。迈内克以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为例,对良心美德的多样性内容及其人道、人性、灵魂、精神的意义做了说明。有些人基于良心,谴责背叛效忠希特勒誓言者;另一些人则同样基于良心,认为背叛效忠、将祖国从罪犯手中解救出、使之免于更大不幸,是更为高级的道德责任。在迈内克看来,前者是简单的美德,后者则是高尚人性与灵魂的品质。能够做出这种背叛的,是那些能置一切于不顾的历史使命承担者。他们动机纯洁高尚,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具有殉道者的精神。士兵当然要有勇敢、服从、纪律等精神,然而,士兵不能丧失意味着“自己家园和生命气质”的某些东西。他们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人的工作”并受“时代精神”制约,且是以“责任心”“纯洁的、人道的和爱国的感情”去努力做这些“人的工作”(24)参见[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5、128、131、136-137页。。这些正是他们根本区别于艾希曼之处。
回到“苏格拉底之死”这一悲剧美学。离开了“道德”“伦理”及其统一,就无法合理理解苏格拉底既拒绝逃跑,又要为自己做那千古辩护的选择。苏格拉底服从伦理审判,维护城邦伦理秩序,但又坚持良心,拒不认罪。他服从城邦法律与公民审判,选择不逃跑,因为在他看来,城邦民主秩序及其法律的价值远高于个人生命。尽管城邦法律有错,但是,一方面,自己在很长时间内享有城邦民主秩序的好处,不能因为城邦民主的这一错误就不服从城邦法律,另一方面,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作为一个好公民,自己必须去死,一个人能为理念而死是值得的。苏格拉底这一选择,既服从城邦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约束,维护城邦法律秩序,又坚守良心殉道。苏格拉底是实践伦理优先、坚守良心的典范。任何伦理共同体总是具体的,因而总是不完满的。其成员不满足现状、基于良心的内在批判,构成伦理共同体演进的内在动力。遵守与维护伦理共同体的基本伦理秩序及其法治权威,批判伦理共同体违反自由、正义精神的反思性活动,是推动伦理共同体向着自由、文明方向持续演进前行的不竭动力。在此意义上,任何有生命力的伦理共同体都不可缺失自身的道德良心,不可缺失来自道德良心精神的内在批判。
四、“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
黑格尔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内在地包含着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合法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其“伦理”角色义务大致相当于对“合法性”的强调,“道德”良心义务则大致相当于对“正当性”的强调。“伦理”与“道德”两种义务关系有类似于行为选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关系。
人似乎生活在悖论、吊诡之中。一方面,人在既有伦理共同体秩序中生活,接受既有规范性要求,成为社会性的人。先在的伦理共同体秩序不仅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客观前提,并以其秩序规范性要求塑造人的“道德”良心。另一方面,伦理共同体本身是历史性的,它既是历史性建构而来,又是历史性生长着的,伦理共同体及其规范性秩序的持续再生产,其成员的道德良心(自觉反思、捍卫)不可或缺。服从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要求是道德义务“本分”,对伦理共同体的积极反思、捍卫亦是道德义务“本分”。如何统一“伦理”与“道德”,始终考验人类的实践智慧。
黑格尔以自己的方式敏锐地发现了“伦理”与“道德”间的紧张,并试图通过将“道德”统一于“伦理”的方式消解此紧张。然而,正如前文已揭示的,黑格尔的努力并未如其所愿。不过,黑格尔的努力向后人揭示了思考问题的合理方向:在本质的而不是在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伦理”共同体,在社会、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意义上理解“道德”良心,在鲜活的社会关系中理解“成人”“美德”,在人的存在本体的意义上把握“伦理”“道德”关系并寻求其内在统一机理。社会性是人的本性,共同体“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人(25)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页。。“伦理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实存关系、秩序现象,而有其精神、本体、本质、真。此精神、本质、真为“自由”,即,它是人的自由存在样式。这样,“伦理共同体”的“真”的问题可进一步具体化为伦理共同体成员间关系问题。一个“真实”的伦理共同体,具有如罗尔斯所说的“公平正义”关系秩序,此关系秩序经验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能为所有人通过日常生活体验。在此伦理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此伦理共同体是所有成员的生命家园,人们会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无论是遵守与服从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出于道德良心的积极反思批判,都是为了捍卫此生命家园。
尽管如此,在行为规范性意义上,“伦理”与“道德”的紧张仍然存在。行为选择依据究竟是伦理规范还是道德良心?即便依据道德良心,是否有其限度?道德良心无非是指向天理、理想、信念、目的性,且每一个人均可有自己的良心、天理、理想、信念、目的性,那么,这些具有不同良心、天理、理想、信念、目的性追求的人们如何在伦理共同体中存在,又如何能够使得伦理共同体长治久安?如果每一个人均以捍卫伦理共同体的道德良心为理由,拒绝伦理共同体的基本秩序规范要求,那么,此伦理共同体是否还能真实存在?
为了使思维清晰、简洁并得以进一步展开,我们在此进一步设定此伦理共同体具有“真”的属性,即:在多元社会,人们通过对话、商谈形成基本共识,建立起基本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拥有宪法法治秩序;以宪法法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的规范性秩序,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当的。这就意味着共同体基本规范性秩序进一步获得人们尊重与自觉遵守的庄重承诺。正是此伦理共同体基本规范性秩序使多元社会在富有生机活力的同时,能够长治久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将“伦理”与“道德”关系演变为“政治正义”意义上的权利间关系,具体化为多元价值之间共在、共生的权利问题。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是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体系的规范性秩序,对彼此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对话妥协,在社会自由中实现个人自由,在社会体系性规范中通过商谈、对话的方式达到共在共生,等等,是多元共在共荣的必要条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对伦理共同体基本规范性秩序的敬重与遵守这一前提。在此意义上,“伦理”对“道德”具有优先性。
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或者是权利优先还是良心优先,社会伦理秩序优先还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优先?(26)参见李泽厚《伦理学纲要》,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13-117页。这不是抽象无聊的概念游戏,它直接关系有原则区别的两种存在方式与实践路径,其实质为是否坚持宪法法治方向。多元社会有多元价值、多种意识形态。多元社会的这些多元价值、多种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多元道德良心。这些多元道德良心与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要求关系如何(尤其是当彼此发生冲突不一时)?如果以道德良心优先,且如果不合乎自己的道德认知判断,当如何选择?是我行我素乃至强加别人,或是“反了他”(如梁山众多英雄的口头禅)乃至“毁了他”(如那些极端教义者)?即便此时以“恕道”应对此类关系,其在根本立场上仍然是主观态度的,而非客观体系秩序的。有合理理由的立场是伦理优先。伦理优先是对宪法法治秩序这一社会基本规范性秩序的敬重与坚持。如果不是以伦理优先,不首先强调建立并敬重宪法法治秩序,那么,社会就没有基本秩序,没有对话与沟通的基本前提,就会盛行在“道德”良心名义下的“弱肉强食”并奉行丛林法则。
在现代社会,“伦理优先”的要旨是坚持与维护宪法法治秩序义务的至上性,而不是简单地指社会系统职责规范性要求的至上性。“伦理优先”并不否定“道德”良心,相反,它给“道德”良心留有充分空间,只是坚持“道德”良心自由并非“任性”,在公共生活中须以维护宪法法治秩序为轴心。施米特在面对魏玛共和宪法危机、纳粹党有合法执政的可能性时,曾转身关闭了“合法性”大门,提出要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27)参见[德]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施米特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要义在于捍卫宪法秩序,反抗纳粹通过合法执政的方式彻底毁灭魏玛共和的企图,在于“合法性”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伦理优先”坚持在既有宪法法治规范性秩序范围内活动,坚持程序、合法等体系规范性义务的优先性,与此同时,也并不否定主体的反思性精神,不放弃对伦理规范合法性本身的良心审视。
罗尔斯政治正义理论在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不仅明确揭示公平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社会长治久安有赖公平正义制度的建立,而且还合理揭示了现代社会宪法法治秩序的基本特质。但是,罗尔斯面临的问题是:伦理共同体不仅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亦是生长着的。公平正义制度何以建立?伦理共同体规范性秩序如何重建?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的伦理共同体如何持续再生产规范性秩序?这一切离开了同样作为背景性框架存在的社会基本价值框架、离开了社会成员基于“道德”良心或“天理”的持续不断慎思、批判,则无法想象。至少人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多次证明,宪法法治的伦理共同体及其规范性秩序不能没有来自追求自由、正义的道德良心的捍卫与维护。不过,我们今天能够从容地思考的良心美德问题,事实上均以罗尔斯所揭示的政治正义为前提:基本公平正义的宪法法治秩序,在现代性意义上基本完成了规范性重构的任务。这就如亚里士多德在讲希腊城邦公民美德、做卓越自己时,是以已经建立起雅典城邦民主制为前提。“伦理”的这一宪法法治秩序前提,使“道德”良心在具体背景性框架中成为具体、真实的。
任何抽象理论背后都有历史性规定或内容。“伦理优先”的实质是宪法法治秩序优先,是在宪法法治秩序范围内活动并受其有效拘束。不过,这里有两种具体情形。一是已经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的社会,一是正在建立宪法法治秩序过程中的社会。后者情况较为复杂。在一个缺失宪法法治秩序或宪法法治秩序不健全的社会中,如何做到“法治秩序优先”?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持续社会实践改变既有丛林法则社会文化,逐渐形成宪法法治社会文化;通过此种努力,在全社会建立起法治文化及其文明秩序。这是凤凰涅槃的过程。
在宪法法治社会,日常生活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伦理优先”是“包容道德”的“伦理优先”。“伦理”是社会体系及其秩序,为社会日常生活交往提供规范性秩序。无“伦理”秩序,则无日常公共生活规范性,无可预期性与安全感,不可能在普遍的意义上培育出健全道德人格。不过,如果有“伦理”而无“道德”,有秩序而无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则社会共同体缺少活力与生机——即使有所谓“道德”,也是蜕化了的,更多的是纲常秩序下的循规蹈矩驯服工具,而非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伦理”与“道德”有合理张力的社会,此合理张力是“伦理优先,包容道德”。以宪法法治秩序为核心的“伦理”为社会提供基本秩序,并对社会共同体做规范性整合。此规范性要求是所有成员应尽之本分义务,社会成员在尽本分过程的同时,拥有尊严、享有权利并塑造“第二天性”。这是“伦理优先”。但是,“伦理优先”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包容社会成员“道德”良心的反思批判精神。在此意义上,“伦理优先”就不是强意义上的,而是弱意义上的,即,不是以“伦理”遮蔽“道德”,而是与“道德”共在共生,包容“道德”良心反思批判精神。“弱意义”上的“伦理优先”,超越了“伦理”与“道德”的二元对立,严格说来是以宪法法治规范性秩序为基础,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的道德行为选择规范性立场。
康德晚年思考两个问题:人类永久和平是否可能?人类人性改善是否可能?对后一问题他并不乐观,他寄希望于一个正义的制度。然而,问题在于:正义的制度本身并不会自动到来,即使是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制度,制度本身在诸多条件下会在不知不觉间向着不同方向演进。因此,即使是为了人类人性改善的缘故,为了维护并持续再生产可使人类人性得以改善的制度,人们也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个体的反思性批判精神。没有反思性批判精神,没有道义良知,既不可能真的建立起宪法法治秩序,也不可能有宪法法治秩序的持续再生产。
伯林曾对自由做过“积极”与“消极”两种区分。伯林提出“消极自由”概念以对抗专制暴政强权,要为个人自由争得避风港,其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不过,“消极自由”具有滑向“平庸”的内在可能。“自由”首先是意志自由,是作为主体自由意志存在与行动的能力。如果不是在对抗专制暴政强权的意义上理解“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如果将“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完全退向内心自守、划地自保,则会使“自由”失却灵魂。那种主体听从内心道德良知召唤反思性批判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是人类极为珍贵的品格,即使是在规范性重构了的宪法法治秩序中,依然如是——只不过,这种“积极自由”有其规范性限度,这就是宪法法治秩序及其权威。
概言之,道德义务根据既不是“伦理”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是超越二者的,是“包容道德”弱意义上的“伦理优先”。弱意义上的“伦理优先”是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立场,它服从并捍卫宪法法治秩序,在宪法法治秩序中坚守道德良心反思性精神。苏格拉底自辩与艾希曼自辩尽管均服从“伦理”义务,但二者有原则区别,前者以“道德”良心批判“伦理”,后者则以“伦理”吞噬“良心”并试图以“伦理”洗刷内心邪恶。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的道德义务及其担当精神,正是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刻隽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