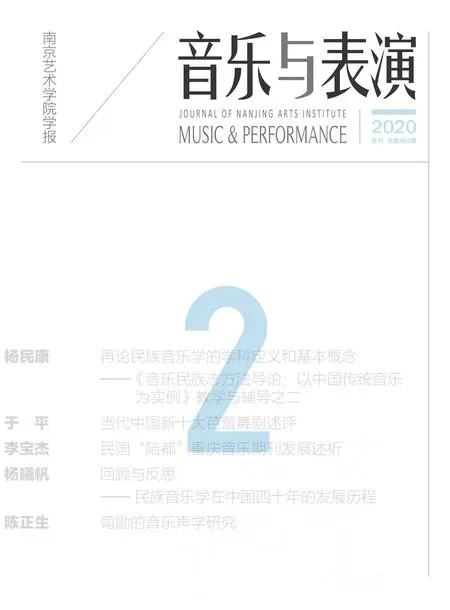中国戏曲理论“情节”探究①
2020-12-05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8
王 铭(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在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中,“情节”是一个高频出现的理论术语。“情节”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国进入“现代”以来,西方艺术理念以及西方戏剧观对中国现代戏剧观的强势影响有关。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诗学》里,对“戏剧”和“悲剧”有如下定义:“作为一个整体,戏剧包括戏景、性格、情节、言语、唱段和思想”[1]197,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1]65。然而,笔者在中国典籍阅读中发现,至迟到明代后期,对译亚氏悲剧六要素之一Muthos[1]197的那个汉语语词“情节”,就已经是中国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常用术语了。在此以前,“情节”是社会日常生活用语。再往前溯,在礼乐社会里,“情”和“节”分别是制“礼”作“乐”的动机和手段。这说明,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把“情节”视为戏剧的“根本”和“灵魂”,固然和西方艺术理念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强势影响有关;但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对“情节”的凸显,却有它来自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渊源,以及与中国戏曲发展密切相关的脉络。追踪中国戏曲理论对“情节”凸显的语境和脉络,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中国戏曲艺术品格的形成与衍化。
一、“情节”溯源
追踪汉语史可以发现,汉语中先有“情”和“节”这两个单字,后来才有由这两个单字连缀而成的汉语语词“情节”。“情”字本指人生来就有,“不学而能”,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心理本能及其活动。“节”字本指名字叫做“竹”的那种植物自然生长过程中,在自身上留下的标志其生长阶段性的印痕。“情”和“节”这两个单字,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在礼乐社会里,为了完善人、完善社会而制“礼”作“乐”。在制“礼”作“乐”的实践中,基于对人之“情”“性”状态的反省,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和“节”,才发生了意义上的关联。
“情”,《说文解字》定义为“人之阴气有欲者”[2]217。段玉裁对之详细注释道:“《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懼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3]502。段注引《礼记·乐记》七情“不学而能”,引《左传》昭公元年传“天有六气”[4]1342,人之情“生于六气”,是想强调人之“情”属于人的本能反映,它更多地与人之“自然性”关联着。与生于人之“阴气”表现为“欲”的“情”相对应的,则为生于人之“阳气”表现为“善”的“性”。《说文解字》这样定义“性”:“性,人之昜气性,善者也”[2]217。“昜”读若“阳”。《说文解字》“昜”字条段玉裁注云:“昜”是“阴阳”之“阳”的本字。[3]454在《说文解字》“性”字条“性 人之昜气性,善者也”句下,段玉裁注曰:“《论语》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3]502段注引《论语》,是要证明“使人善”的“人之阳气性”,是“天”所“命”于“人”而其他生物都不具备,只以“人”才具有的“相近”之“性”。引《孟子》,是要证明人之向“善”,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是“天”之所“命”之于“人”的“四端”,即“人”之“内在理性”的必然要求。由此可知,人之“情”,更多地和人做为“自然人”从而与“禽兽”无本质差别的本能欲望关联着。而人之“性”,乃是“天”之所“命”于“人”,从而使人成为“人”而有别于“禽兽”的基质。段玉裁“情”字条注引纬书《孝经援神契》,是要证明“情”和“性”,虽然两在“人”之身,涵盖了“人”这个类存在的全部心理内容;但在人向“人”的方向不倦完善的进程中,“情”和“性”分明有不同的表现。人之“性生于阳以理执”,在人向“人”的方向不倦完善的进程中,积极进取而能动有为,故而在中国“人性论”特别是在孟子一系的“人性论”中,一贯被视为人之“阳气”的表现而得以肯定。它是人向“善”的方向不倦完善自身的基础和动力。人之“情生于阴以系念”,人之“情”更多地保留有人做为“自然人”的本能欲望那部分内容。在人向“人”的方向不倦完善的进程中,人之“情”尽管表现得十分丰富,却经常安于“自然”而消极被动,虽然“率真”,却经常有悖“天”之所“命”而不自知。人之“情”,集中展现了人成为“社会人”而后依然“与禽兽几希”的复杂性。它是人经常会流于“恶”的根由。故而在中国“人性论”特别是在孟子一系的“人性论”中,经常被视为人之“阴气”的表现而加以否定。中国“人性论”特别是孟子一系的“人性论”,对人之“性”主张“率”——放开手脚去“扩充”①《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扩充”,参见:《孟子·公孙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杨伯峻《孟子译注》。;对人之“情”则主张“节”——设置一套规范,能动地消解“情”中的“自然”成分,让人在思想和行为中,“情”而有“节”,推动人向“社会人”的方向完善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对“人”这个类存在持如下基本认识:1.“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社会”是“人”这种“社会存在”的“存在本体”;2.人成为“人”的过程,是“自然限制无限退却的过程”;3.就“人”的发展前景而言,尽管“自然限制在无限退却,但自然限制永远也不可能退却净尽”。 参见:(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引论[M].白锡堃,张西平,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按卢卡奇的认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有“社会性”的一面,有“自然性”的一面。人的发展过程,是人的“社会性”不倦扩充,人的“自然性”不断退缩的过程。但人“存在的本体论”决定:无论人的发展水平有多高,人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人“广泛地和决定性地以生物学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宿命。卢卡奇认识中的前两条,和中国“人性论”中特别是孟子一系对“人性”的基本认识相通;第3条和中国对“人性”的认识相左。中国“人性论”——主“性三品”的董仲舒除外,对人的发展前景多持乐观态度,认为人最终能够完全彻底摆脱“自然限制”的宿命,成为“圣人”“真人”。但卢卡奇这一认识,仍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人性论中所谓的人“阴阳情性,两在其身”的意涵。。
“节”字的本义,乃是“竹”的那种植物自然生长过程中在自身上留下的印痕。《说文解字》云:“节”,“竹约也”,段玉裁注曰:“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吴都赋曰:苞筍抽节。引伸为节省、节制、节义字。”[3]189状如“缠束”的竹节,乃是竹自身生长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成为外界认识竹之生长状况的途径。“节”乃是竹自身的生长规律与外部认识竹生长状况之集结点。由此出发,其意涵逐步丰富,孳生出节制、节义等多重含义。《康熙字典》“节”字条网罗到的“节”的本义与引申义主要有:“《说文》竹节也。又操也……又止也,检也,制也……又符节,所以示信……又时节……又乐器,即拊也,所以节乐……”,等等。[5]909就本文的论旨而言,“节”字引申义中最可注意者,乃在“又乐器,即拊也,所以节乐”。“拊”是礼乐乐器。《周礼·春官·大师》述及职官太师的职能,有:“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击拊”[6]719。在礼乐表演中“击拊”,并不是要给歌唱和器乐演奏增加特别的音色,而是通过击拊,掌控歌唱和器乐演奏的节奏,使之“刚”“柔”相成,“清”“浊”相形,“高”“下”有节,“疾”“徐”有度,就像现在戏曲伴奏中的板鼓。故而从功能上,又把“拊”称作“节”。按中国乐论,乐的本质在“和”——把不协调的音声引向协调,把杂多的音调引向统一,给乐一个艺术的形式,让乐如“天地之和”那样完美。作乐的动机也在“和”——用乐之“和”陶冶人的心灵,通过“反情合志”,把不同等级的人协调起来,把不同情性的人统合起来,让社会如“天地之和”那样和谐。如《左传》中所言的:“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4]1340。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节”——按一定的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举止,按一定的章法节度人的情感发抒,就被置于制“礼”作“乐”的核心位置。礼乐之“节”,是希望给人的情感发抒和行为举止一个规范形式,遏制人“直情径行”,让人的情感发抒和行为举止更像个“人”。此即《礼记·乐记》里说的:“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节”,即利用“礼别异”之制度约束与“乐和同”之潜移默化,“以遏其欲。”[7]1263,1264“先王制礼作乐,人为之节”,礼乐之“节”,是人有目的的设计。其间有对人“情性”内部要求的顺应,又有来自制度的外部的规范。此即《礼记·乐记》里说的:“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郑玄注曰:“审一,审其人声也。比物,谓杂金、革、土、匏之属也。”[7]1334礼乐之“节”的核心内容,是节“行”节“情”,即通过有目的的设计,给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发抒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使之“媒介化”,以实现“反情以合志,广乐以成教”、动静举止合度中节的预想。此即《礼记·乐记》里说的:“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詘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郑玄注曰:“节,谓曲节。奏,谓动作。言作乐或节或奏,是依其缀兆,故行列得正,由随其节奏,故进退得齐焉。”[7]1335而“有意味的形式”的形成和“广乐成教”目标之实现,全在于制礼作乐者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人的“情”“性”之“度”,“或节或奏”,无过无不及。此即《礼记·乐记》里说的“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而不怒,柔而不慑,四畅文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词,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始终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7]1288,1289在礼乐的陶冶之下,情性得“人为之节”,脱离了“直情径行”的素朴自然,获得了有“节”有“奏”,或“行”或“止”,行止合节中度的“有意味”的“美的形式”,引导着人向“人”的方向不倦完善。故而有论者称,由“节”而衍生出的“节奏”,“节奏兼顾了‘美的形式’与‘陶冶人心’双方面的规定性”,[8]400“节奏”最能体现中国美学思想中“和”的理念[8]398。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而制礼乐。乐中有“情”有“节”。为什么作乐必须“本之情性”?因为“情性”最能见人之为“人”之“真”。此即《礼记·乐记》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情”字由此获得了与“伪”相对应的“真实不虚”的意涵。然而,“真实不虚”的东西,未必就“美”,就“善”。于是有“稽之度数”,“人为之节”,把“真”提升到“美”和“善”的要求。此即《礼记·乐记》说的:“人不耐(郑玄注:“耐,古书‘能’字也”)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导),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是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7]1333。
乐中有“情”有“节”。“情”由衷出,“乐中有情”。“乐中有情”,是出于对人情性之“真”的尊重;“节”自外作,“乐中有节”。“乐中有节”,体现了人对“美”和“善”的追求。“情”和“节”,两不可缺。缺“情”不是乐,无“节”不成乐。在乐中如何协调“情”和“节”,使有“节”而不窒“情”,有“情”而不逾“节”,让“情”与“节”交相养而不是互相害?便成了“乐体”“乐施”“乐化”中圆满实现“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的核心问题。对此,古今通人硕儒多持循“中庸”之道,持“过犹不及”的立场。前贤此意,以戴震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反省,以及汪烜对《礼记·乐记》核心精神的提示,表现得最为明朗。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说:“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9]10,11。性、情、理、欲,乃是只要是个“人”,就必然要面临的,根本无法回避的心理事实。理想的境界应该是,不去拒绝情、扼杀情,也不纵容情、放荡情,最终要在效果上体现出“无过情”与“无不及情”,从而与“天理”相通。在人的自尊自强中,实现社会和谐。“情”而“有节”,就像“天”“春生,夏长,秋敛,冬藏”有“节”有“序”一样。“情”与“节”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此即汪烜《乐经律吕通解·乐记或问》强调:“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的原因[10]398,399。天地阴晴变幻,寒暑易节,包孕百态而稳健发展,人之情性礼乐与之也有相感相通之处。情通感官,乐得以和合;制为质形,礼得以推行;礼乐合用,“情”以“通”之,“礼”以“节”之,“情”与“节”交相养而不互相害,既合“天理”又顺人情。至此,“情”与“节”发生了更紧密的意义交集:“情”是有“节”之“情”,“节”是顺“情”而“节”。有“节”之“情”,才能悦乐人心,净化人欲;顺“情”而“节”,才能顺畅地“反情合志”,把“情”的正能量饱满释放出来。“情”“节”互依而存,分则为二字,合则为一体。“节情”或曰“情节”,譬犹给人的“直情径行”打个“结”,从中分检出能够“合志”的那部分内容,对其中“合志”那部分内容集中进行优化处理,让人之为“人”的那种本质力量显现出来。人在日常交往中,也随时需要对自身的行为举止进行反省式的“分检”,以优化其中最能“合志”的部分。“情节”,于是成了广涉礼乐、心物、情事等复杂内容的社会日常用语。
《资治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六年》:慕容燕与石氏赵交兵。燕兵势如破竹,直逼幽州、范阳。赵之范阳太守李产为部下胁迫降燕。时李产之子赵之幽州别驾李绩,从幽州刺史王午守鲁口,立誓拒燕卫赵,与鲁口共存亡。有人言于王午云:李绩单身随军,家在范阳,其父已降燕,恐有贰心。劝王午先除隐患,以防不测。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当今丧乱,而绩乃能立义捐家,情节之重,虽古烈士无以过;乃欲以猜嫌害之……”[11]3104此处之“情节”,指李绩通过危难之时“立义捐家”一事表现出的“情性节操”。或曰王午从李绩行为举止中“分检”出的最能体现李绩人格力量的“大情大节”。《朱子语类》卷106 之“漳州”条:朱熹为漳州郡。提刑司发回一些案卷要求重审。朱熹邀集提刑司发回要求重审之各案件的主审官,一起逐案详核细察案由、判决书、上诉状、重判书,等等。“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写出,后面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或有未尽情节,拟断在后。”有冤情者重审,无冤情者结案,“未尽情节”即与事实有出入者,以事实为依据重新起草判决书,上报提刑司。[12]2648此处之“情节”,则为全部涉案事情一节一节的真实情况。时至今日,“情节”一词依然是法律中的重要术语,频繁出现在律法条文、公诉人的起诉状、辩护人的辩护辞、法院的判决书中。《水浒传》第四一回:各路英雄大闹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宋江,齐奔穆家庄。穆家兄弟杀猪宰羊,设筵款待。众英雄“饮酒中间,说起许多情节。晁盖道……”此处“许多情节”,即“闹江州”中一系列事件前前后后的经过。第八十三回:宋江奉诏征辽,在陈桥驿整装待发。一军校不满朝廷差官克扣犒劳三军的酒肉,反被差官恶言相斥,辱其“贼性不改”,一怒之下,手刃差官。三军哗然。“宋江自令人于馆驿内搬出酒肉,赏劳三军,都教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问其情节。”[13]539,1076此处的“情节”,即事情发生的缘由,事件的紧要核心点。《金瓶梅词话》第二一回中写到:“月娘道……我是那不贤良的淫妇,和你有甚情节?”第十二回中写到:“院中唱的,只是一味爱钱,你有甚情节?谁人疼你?”[14][541,319此处“情节”,义指“事情与人”“人与事情”之间的关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回:“又想起今日看见那苟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甚么意思,继之又不肯说出来,内中一定有个甚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了才好。”[15]48此处的“情节”,指某件事情中耐人寻味的节点。第十回“他的意思,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15]87此处“情节”即“前情后节”,指此事与彼事之间隐秘的因果关联。
社会日常用语中的“情节”,多指从事情中“分检”出来的事情发生的缘由。戏曲搬演的也是从众多故事中“分检”出的一段故事。故事发生有缘由,发展有经过。在故事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与事、事与人紧密交集。戏曲艺术就是靠“有节有奏”地铺述故事的曲曲折折,传写故事中人物的“情性节操”、命运遭遇,展示曲折故事中的耐人寻味的紧要处,从而吸引观众的。“情节”也就成了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关注点。
二、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情节”论
“情节”是在明代后期成为戏曲理论批评术语的。在此以前的文学理论批评中,把类似于“情节”所指陈的内容,素朴地称之为“情-事”。中国文学批评把旨在“敷陈”的“赋”,称之为“古诗之流”——“诗三百”的“流裔”和“变体”。称赋是“诗三百”的“流裔”,是因为“诗”是“言志”的。而从赋“敷陈其志”上说,赋沿袭了“诗言志”的传统。说赋是“诗三百”的“变体”,是因为“诗言志”的手段有三种:一曰“赋”,再曰“比”,三曰“兴”。而赋仅取“诗”言志三种手段里的一种——“赋”,去“敷陈其志”。更有进者在:“诗”纯是因事而言志;而赋则是“体物”兼“言志”。“诗”中的“风”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言一己之事,“雅”是“言天下之事”,“颂”是言部族兴盛之事。“诗言志”所“因”之事,无论是“一己之事”“天下之事”“部族兴盛之事”,都是实际发生过的。而赋——特别是汉大赋——“敷陈”的“志”,多数不是实际发生的,而是虚拟的。赋“体物写志”的惯用发生是:“设主客以首引”,“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虚拟一种情境,设置两个有冲突的人物,然后让两个人物以反复辩难的方式,展开想要言说的内容。东西晋之交的挚虞,在其《文章流别论》里论及赋体文学之流别时,称赋和“诗”一样,也必须有决定其性质的两大要素:“情”与“事”:“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16]190“诗”中有“情”有“事”。在“诗”中,“情”缘“事”发,“情”是经过提炼的“止乎礼义”的有“旨”之情。“旨”须“事”明,“事”是经过选择的最能昌明“礼义之旨”的有“境”之事。“赋者,古诗之流”,赋中也有“情”有“事”。不过,赋中的“情”,是虚拟出来的“情境”中有“旨”之情,“事”是虚拟出来的“情境”中才发生的事。挚虞所谓的“情-事”——尤其是赋之“情-事”,可以视为后世中国戏曲理论批评中反复凸显的“情节”的滥觞。
挚虞强调赋的创作方式是:“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就是说赋虚拟出来的“情境”中的有“旨”之情和有“境”之事,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予以体现,才能成为艺术存在。这意味着:有“旨”之情和有“境”之事,只存在于“媒介化”的文本中,经验世界里不存在有“旨”之情和有“境”之事。这一点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本论文下面的章节里,将能看到挚虞“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论在戏曲“情节”论上留下的印痕。
“情之发,因辞以形之”。将“情”与“辞”联系起来,在《易·系辞下》中可以找到出处:“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17]349王弼注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孔颖达疏曰:“辞则言其圣人所用之情,故观其辞而知其情也。是圣人之情,见乎爻象之辞也”。[17]349以此,则“情”——“圣人之情”即圣人对事情真实不虚的认识及圣人对事态发展准确无误的预测,可以通过“辞”来体现,“辞”可以成为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情”的渠道。但圣人为情尽辞之方式并非单一,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言道:“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4]20,“五例”分别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4]20-23圣人为情尽辞方式之多样,恰与待圣人处理的事“情”之复杂错综相应。正因为“春秋”294 年里发生的事情错综复杂,圣人“尽辞”时才格外谨慎,选用或“微而显”或“志而晦”等不同的言说方式,既要“不走样儿”地书写出真实的事态,又能曲折传达出圣人的立场态度、褒贬倾向,以实现圣人“惩恶而劝善”的书写目的。杜预标举《左传》:“为情五例”,无非是说圣人孔子所作的《春秋》,并非是“断滥朝报”的简单汇编,而是从“春秋”294 年里发生的事件中“分检”出最有“意味”的事件,然后用不同的“笔法”书写出来,因而辞简而意丰:“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其间有“情”有“节”:情、情皆有“节”,节、节都关“情”。乃是“制作之文”的典范。“五例”乃杜预理想中的叙事典范,并非孔子“撰《春秋》”时的实际操作。但杜预所标举的“为情五例”,对后世戏曲理论批评“情节”论中如何恰当处理情感抒发、叙事安排、“意义”注入不无启发。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情节”论中“情节”概念,是从日常生活用语中转换过来的。而创制这一概念的精神动力,却根植于《乐记》“反情和志”让“情”而有“节”的理念。受日常用语的影响,一般提及“情节”时,经常会简单地理解为故事的组成衔接、人物的命运遭遇等。加之这样的理解,和汉译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乃事件的组合”近似,故而流行一时。其实,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情节”,固然与故事本末、人物遭遇有关;但故事衔接、人物遭遇仅仅是戏曲的“本事”,并不就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情节”。戏曲的“本事”,无论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还是在生活想象中虚拟出来的事情,都停留在“生活状态”,因而只是戏曲的素材,还没有进入“艺术状态”。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情节”,则是戏曲作者从素材中精心提炼、精心加工,按一定的生活理念重新设计出来的,最能体现剧中人物心路历程,最能体现戏曲剧作者情感态度、思想倾向的艺术载体。“情节”和“曲辞”是戏曲艺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从明代后期开始,“情节”处理得是否得当,就日益明朗地成为戏曲理论批评评价一部戏曲作品优劣的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吕天成的《曲品》是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代表作之一。《曲品》在品评当时流行的戏曲剧目时,十分注意诸剧的情节处理。如吕天成《曲品》批评《龙泉记》说:“情节正大,而局不紧,是道学先生口气。”[18]195“局”即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常说的“局段”——构成情节整体的一个个“单元”。“不紧”,即是结构疏松。由此可见,戏曲情节以结构谨严,浑然一体为上。点评《蕉帕记》云:“传龙生遇狐事。此系撰出,而情节局段能于旧处翻新,板处作活,真擅巧思而新人耳目者!”[18]254由此可见,结构严谨的戏曲情节,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剧作家骋想象,运“巧思”,精心结撰出来的。而戏曲情节结构之“巧”,则全看剧作家能不能“于旧处翻新,板处作活”,“新人耳目”。点评《双珠记》云:“情节极苦,串合最巧,观之惨然”。[18]295“串合”,就是精选种种“苦”情“苦”事,通过“巧妙”的运思,“串”成一串,“合”为一体。由此可知,戏曲情节,是剧作家调动全部生活库存、知识库存,对之进行提炼、加工、改造,按一定的艺术匠心“串合”出来的。点评《绣襦记》云:“元有《花酒曲江池》剧。此作照汧国夫人本传谱者,情节亦新,词多可观。”[18]367由此可知,戏曲故事可以重复前人,因为故事只是戏曲的素材;戏曲情节必须花样翻新,戏曲曲词必须绮丽动人,因为情节处理、曲词结撰,才能显示剧作家独到的艺术匠心。在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和“情节”内涵趋同的批评概念,还有“关目”“布局”等。例如李贽称赞《幽闺记》:“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19]54。冯梦龙评《楚江情》:“此记模情布局,种种化腐为新。《训子》严于《绣糯》,《错梦》幻于《草桥》,即考试最平淡,亦借以翻无穷情案,令人可笑可泣”[19]134。一时之间,情节处理成了戏曲理论批评关注的重心。这一状况的出现,自有其来自中国戏曲发展内部的脉络,此处不赘。这里想突出的是,“重情节”已经延伸到了戏曲排练。李渔《闲情偶寄》“填词部”和“演习部”,是他撰写剧本,排练剧目的经验结晶。其中最可注意者,是李渔“唱曲一定要唱出曲情”的主张,为了落实“‘唱曲’一定要唱出‘曲情’”的主张,李渔要求他戏班里的演员,在进入正式排练之前,先须“解明情节”,然后按戏曲情节的要求,恰当处理好各自的“唱”“念”“作”“打”:“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义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20]112李渔此论,被日后戏曲界奉为金科玉律。例如《顾误录·度曲八法》言道:“曲有曲情,即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中为何如人,其词为何等语,设身处地,体会神情而发于声,自然悲者黯然魂销,欢者怡然自得,口吻齿颊之间,自有分别矣。”[21]85“解明情节”,就是“解明”剧中人“为何如人”、剧中人所唱之“词”“为何等语”。“解明”剧中人作“此等人”而不作彼等人、“词”作“此等语”而不作彼等语之“意义所在”。依此而论,戏曲“情节”事涉事件之组织、意义之注入、人情之琢磨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尤其值仔细琢磨的是:李渔所谓“情节”,乃是“曲中之情节”。“曲”既可以理解为“戏曲”“戏本”,还可以理解为“戏本中的曲词”。“情节”就是“曲(戏本中的曲词)中之情节也”。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对“情节”的理解,和西方戏剧理论中对“情节”的规定,“通”而“不同”!此是依照中国戏曲艺术之艺术特质对“情节”作出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的规定。惜乎既往的研究,对此很少予以关注。戏曲理论批评的出现,以及戏曲理论批评的关注点,从戏曲曲词结撰是否合乎“本色”,能否体现此创作者的“机趣”,进而关注戏曲情节安排是否新颖合理,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折。故而朱万曙称:“叙事角度的强化构成了明代戏曲评点的一大批评特点。”[22]109对戏曲“叙事性”体认的深入,正是本论文前面说的戏曲理论批评中重视和突出戏曲情节的内在脉络。
小说是单纯的叙事文体,更突出叙事情节。明清小说评点例如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把小说的叙事情节,称之为从“情理生出来的章法”“文字无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岂是信手写去者?”[23]598称之为“向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盖他本事向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则不在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又何以为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当平心静气,向人情中讨结煞,则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23]2更借“从一个人心中讨一个人的情理”,把明清戏曲情节论中明而未融的“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互为表里,情节安排以前呼后应、浑然一体为上之旨,活灵活现地提顿出来:“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23]38小说与戏曲内容上的互相借用及表现方式上的相互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出现,此处不赘。
三、当前戏曲研究中的情节观念
对中国戏曲剧本创作中情节凸显的过程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戏曲理论批评中,作为理论概念和批评术语的“情节”,其意涵是十分丰富的。那么,今日的文艺理论中情节是如何被界定的呢?其走向又是如何呢?以戏曲理论界为例,有这样的解释:“简单地说,情节就是戏里的事儿。”[24]94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如此定义“情节”,其中有中国传统戏曲理论批评中“情节”论的因子。更与对西方戏剧理念中的Muthos 理解上的不严谨、欠准确有关,例如上面征引的文字在定义“情节”时,反复强调“情节”就是“事儿”。其实,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作为戏剧理论术语的Muthos 并非“就是事儿”。
美国学者巴特沃斯把阿拉伯学者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著述《论诗术中篇义疏》翻译成英文,以广英语世界《诗学》研究的视野。在“导言”中就对阿威罗伊用khurāfah 对译muthos 这个术语是否得当,踌躇再三。最终将khurãfah 这个“新式翻译”,还原性地直译为myth,以彰显muthos 这个术语“被新式翻译掩盖”的“渊源”[25]16。巴特沃斯对用“情节”“寓言”“故事”等“新式翻译”对译亚里士多德戏剧、悲剧六要素之一的Muthos 恰当与否的挑剔表明,准确理解、正确把握亚里士多德Muthos 的真正意涵,不能盲从“新式翻译”,应该返回原典,到原典和生成原典的文化语境中寻“渊源”。大陆学者赵毅衡对“情节”(plot 或action)的辨析中,也表现出浓烈的回归原典的色彩,赵毅衡“情节的底线定义,就是‘被叙事出来的卷入人物的事件’”,及其刻意突出“情节只存在于媒介化的符号文本中”[26],很值得玩味。陈明珠称:《诗学》中“谜索思”(mythos)一词在日常用法中,含义有两个大类:“与行相对的言”及“故事”[27]。陈明珠想得出来的结论,即“情节乃叙述出来的故事”。美国学者乔纳森强调:“情节或者故事是被表述的材料,是根据一个特定的观点通过话语编排的(一个故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不过情节本身已经塑造了事件”,[28]89德国学者弗莱塔克强调:“戏剧的情节就是根据主题思想安排的事件,其内容由人物表现出来。情节由许多细节合并起来的,是由一系列戏剧性的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被有规则地安排起来,先后发生作用。”[29]18
上述征引显示,尽管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戏剧六要素之一的Mythos(汉译为“情节”),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有“所说的事”“所想的事”“故事”等义涵,亚里士多德《诗学》汉译本也把Mythos 理解为“事件的组合”,但更严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中西学者,在各自的研究著述中,仍然坚持给Mythos 所表“所说的事”“所想的事”“故事”之义的前面,追加上一系列规定,以彰显亚里士多德选择Mythos 这个词去表述戏剧六要素的西方文化“渊源”,到西方文化渊源中去把握戏剧六要素之一的Mythos 的真实意旨。用汉语语词“情节”对译的西方定义戏剧的术语Mythos,尽管和“事”“事件”“故事”有关联,但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其文学理论意涵并未被直接理解为“事件”“故事”。
如果说西方文化语境中的Mythos(“情节”)更多的与动作、事件等相联系,与叙述相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情节”除了建构事件,涉及叙述外,还与剧中人物的心路历程密切相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情节的展开媒介上,西方戏剧主要靠动作,中国戏曲主要靠曲词。例如前引李渔情节即“曲中之情节也”。在中国戏曲艺术中,情节主要靠曲词展开,我们在题曰“曲品”“曲评”“曲话”之类的中国戏曲理论批评著述中,可以看到有关论述。例如,《长生殿》评语中吴仪一论及《长生殿》戏曲情节展开时,就有:“以愁境引起欢情,转到追悔之意,无限宛转”,“两层热闹中,插李遐周冷淡一诗,文情更觉生动”,“常时银汉,陡觉异姿,境由情生也,可以静悟悲欢之理”,“且引起下文乞巧殿中,撤灯独步,增无限文情”,“结出雨后景色,文生于情”[19]333-337,等等。情、境转换,是中国戏曲情节展开的手段,而“情”“文情”以及情中之“境”,都是通过曲词传唱出来的。在诗词评论中,谈及情景交融、文情相生等,多指其为表现手法,然而,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讨论景、文及其与情的关联,实则可视为戏曲情节展开展现之方式与途径。戏曲情节,固然表现为事件以及随着而来的动作表现等,但事件的发生发展,是用曲词唱出来的。程式化的戏曲动作,只是曲词所唱情、景的传达媒介。包括凭戏曲动作出彩儿的《三岔口》,也是在前后所唱曲词、所念宾白制造出来的情境中,其动作的传神出彩处,才能够获得观众的欣赏。假如掐头去尾,《三岔口》那一套动作,只在戏馆训练学员身段功夫时才有意义。即便如此,戏馆在训练学员身段功夫时,仍需先“解明情节”,把有前后唱词宾白渲染的情境说给学员,才能进行有效的身段功夫训练。在戏曲艺术中,曲词的大量使用,有效地在剧中人物情境抒发的同时,推进戏曲情节的展开[30]。戏曲情节靠艺术媒介展开。杂剧、传奇正是以联套组曲为艺术媒介,才使得叙述得以可能,花部板腔体齐言句式,更是大段唱词汇聚成抒情叙述的汪洋大海。“优孟衣冠”式科诨戏、参军戏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曲,就因为其只有戏曲的因子,而缺乏戏曲应有的“边幅”。也就是说,科诨戏、参军戏里只有“科白”,没有戏曲靠曲词传达出来的跌宕起伏的戏曲情节。
笔者认为,戏曲曲词,就其抒情叙景而言,无别于诗、词。其间的分别全在于,诗(近体律绝)书写的只是瞬间的感觉,故而只讲情景交融。词(长短句)书写的是一片情事,故而在情景之外,还讲“铺述”。戏曲曲词传唱的,是一连串发生发展着的、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情境中的“情”与“感”。故而在“情感”发抒、情景“铺述”之外,还要顾及戏曲情节、戏曲情节的展开及戏曲情节的整体结构。对“情节”术语进行分析,并分析曲词在戏曲艺术发展中的多种而非一种功能,或许是解析中国戏曲艺术特色的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