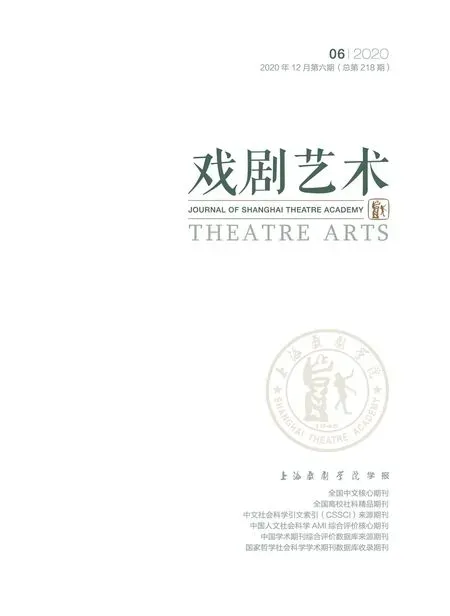“落难公子中状元”之成因
2020-12-03王云
王 云
对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中众多表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作品,五四以来批评家的恶评或讥评远多于好评,其中有一讥评大家耳熟能详,那便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一评语最初出自何人之口?似乎从未有人做过考论。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批评家都有过类似判断。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书信(1917年2月25日)中指出,“旧小说”中“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1)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鲁迅《论睁了眼看》(1925年7月22日)说:“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上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2)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他们说错了吗?当然没有。大量的古代戏曲作品有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何古代剧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在自己作品中呈现如是情节?比较现成的解释无非是,他们才疏智浅,故其作品陈陈相因,或者他们为了迎合普通受众恶俗的欣赏趣味所致。如果仅仅是三四流的剧作家描述了如是情节倒也罢了。我们可以说他们缺乏创作才华,故其作品落前人窠臼,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像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汤显祖、李玉等一流剧作家也都在描述如是情节。(3)参见关汉卿《拜月亭》《绯衣梦》、白朴《墙头马上》《东墙记》、王实甫《西厢记》《破窑记》、马致远《荐福碑》、郑光祖《倩女离魂》、汤显祖《牡丹亭》、李玉《永团圆》等。这些戏曲或有“中状元”,或有“落难公子”,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可都是各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呀,难道他们都是傻的吗?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这其中很可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乐见“落难公子中状元”之情节是普通受众恶俗的欣赏趣味之表现吗?即便是,那么如是欣赏趣味又是如何形成的?
为何有如此多的“落难公子中状元”?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为何有如此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落难公子中状元”大多出现于结局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曲中。不仅如此,前一种情节也确因后一种情节而生成,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后者的“标配”。而要探明众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之生成原因,我们不得不借助于马斯洛的基本需要说。
一
考虑到基本需要说及其衍生理论的复杂性,有必要对它们作一些介绍或阐释。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4)(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第29页。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马斯洛所谓的基本需要共有七个层次,即在上述五个层次之后添入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对此《动机与人格》(第3版)汉译本主要译者许金声在《译者前言:关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认为最可靠的说法仍是五个层次。除生理需要外,其他四种基本需要皆与演故事和说故事艺术作品的三类圆满结局有着密切关联。如果说赏善罚恶结局与安全需要密切相关,事业成功结局与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密切相关,那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则与归属和爱的需要密切相关。
马斯洛如是描述“归属和爱的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这样的一个人会渴望同人们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做)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尝到浪迹人间的痛苦”。(5)(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26页。
归属和爱的需要并非某一个需要而是某一类需要。如果说这一需要中的“归属”是指融入由“父母姐弟”“亲朋好友”“邻里”“族系”“熟人”“同事”等所构成的“家庭”“团体”或“社群”(6)(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27页。,那么其中的“爱”基本上也就是异性之间的情爱甚至与此密切相关的性爱。马斯洛说:“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达,一般是被暧昧看待的,并且习惯性地受到许多限制和禁忌。”“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需要决定,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7)(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27页—第28页。从这些论述中,你能清晰看到马斯洛所谓的“爱”的确切内涵。实际上,归属和爱的需要应该与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团圆”结局相对应。而“团圆”也并非某一个结局而是某一类结局。构成这一结局的内容既可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可能是家人失散后重聚,甚至可能是夫妻破镜重圆。因此,严格地说,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相对应的是爱的需要。为简洁明了起见,下文以“爱的需要”取代“归属和爱的需要”。
爱的需要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有何相关性?我们要从基本需要的主客观双重性质说起。马斯洛所谓的基本需要可拆分为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和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用美国学者戈布尔的话来说,“这些需求是心理的,而不仅仅是生理的”。(8)(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2页。也就是说,基本需要确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但它们同时又是心理需要。如果缺乏后一种含义,它们也不可能成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内容。马斯洛在阐述安全需要时说:“安全需要的满足会特别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安全感、更安稳的睡眠、危险感消失、更大胆、勇敢等。”(9)(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44页—第45页。“安全需要”中的“安全”是客观意义上的安全,“安全感”是主观意义上的安全。此语意谓,客观意义上安全需要之满足会导致主观意义上安全需要之满足。由此可见,基本需要兼具双重性质是基本需要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马斯洛确实没有对此做过清晰的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在从事艺术研究时运用这一学说,马斯洛也因此而错失了像弗洛伊德那样成为艺术心理学大师的机会。
主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有着如下复杂关系。第一,满足了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也必然同时满足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我们以安全需要为例:人在社会生活中是安全的(即满足了客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也必然会有安全感(即满足了主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第二,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也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安全,也必然没有安全感。第三,满足了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未必能同时满足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人有安全感,并不意味着他在社会生活中一定是安全的。第四,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未必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人没有安全感,并不意味着他在社会生活中一定不安全。
审视这四种关系,不难发现,主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有时相互联系,有时却又相对独立。前两种关系告诉我们:(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必然导致(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这是相互联系的一面。后两种关系告诉我们:(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未必(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基本需要,这是相对独立的一面。它们之所以相互联系,是因为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基本需要这一心理事实正确地反映了(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基本需要这一客观事实。它们之所以相对独立,是因为主观具有了脱离客观的自主性,(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基本需要这一心理事实不再是正确反映(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基本需要这一客观事实的结果。要探明众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之生成原因,我们特别要关注这四种关系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关系。
二
中国古代戏曲中为何有如此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首先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有情人很难成眷属,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造成的。这一婚姻制度有着两大核心内容,即“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者为实质方面的内容,后者为程序方面的内容。这两大核心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婚姻是极度不自由的。
何谓“门当户对”?今人大多认为,只要一对异性青年男女所属之家庭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大致相当,那便是门当户对了。这可不是古人心目中的门当户对。陈顾远《中国婚姻史》说:“凡遇阶级存在之场合,彼此不通婚姻,实为其主要鸿沟之一……此种阶级间之隔婚,或为良贱之关系,而以经济与政治之原因为主;或为士庶之关系,而以家望与世系之原因为主;惟后一关系,仅著称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间而已。”(10)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0页。由此可知,所谓门当户对有两种类型,一种以两个家庭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大致相当为主,兼顾两家的名誉声望和血缘传统;另一种以两个家庭的名誉声望和血缘传统大致相当为主,兼顾两家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前者以现实状况为主,后者以历史状况为主。北宋以降,后者式微,但并未完全绝迹。况且前者中同样有对“家望与世系”的考虑。由此可知,既要有情,又要门当户对,这该有多难!
即使门当户对,有情人就一定能成眷属了吗?没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他们依然不能。中国有史以来,直至古代社会结束,先后出现了三种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式,即劫掠婚、买卖婚和媒妁婚(聘娶婚)。大约至东周时,中国的主要婚姻形式演变成了媒妁婚。当然不排斥当时的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劫掠婚和买卖婚,也不排斥媒妁婚本身含有买卖婚的因素。要说劫掠婚和买卖婚,还真没有什么民族特色,然媒妁婚却实实在在地具有民族特色。儒家是媒妁婚的主要倡导者。孟子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国人父母皆贱之。”(11)参见《孟子·滕文公下》第3章。既要有情,又要门当户对,现在还得添上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对异性青年男女要成为有情人同样不容易。这是由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社会活动范围逼仄、男性与女性相对隔绝这两大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底层的青年女性还可以生活在由家庭成员、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等构成的熟人圈子里,那么,中上层的青年女性也就只能生活在家庭成员和亲戚之中了,平日里她们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人要有情,至少要有(较长时间)相互接触的机会,而中上层青年女性恰恰缺少这样的机会,这便有了“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前一句“私订终身后花园”,因为后花园是古代剧作家们不无依据的想象中唯一能让异性青年男女从容交谈的场所。不过,对这一话题本文不进行展开而将其悬搁起来,先验地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中有情人的普遍存在。
三
严酷的婚姻制度导致婚姻极度不自由,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并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这便是上述主客观意义上基本需要的第二种关系。如果青年男女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换言之,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是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爱的需要的表征?试以《牡丹亭》为例。在第十出《惊梦》中,杜丽娘唱(说)道:“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没乱里(12)参见(明)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49页,徐朔方等注:“形容心绪很乱。”,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13)(明)汤显祖:《牡丹亭》,第42页—第44页。杜丽娘何以有这莫名的烦闷和惆怅?“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14)(明)汤显祖:《牡丹亭》,第44页。显见正是客观上的“不得早成佳配”,才导致了主观上的“闷无端”和“怀人幽怨”。拜汤显祖梦里生花的妙笔所赐,我们才得以洞悉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杜丽娘是艺术世界而非现实世界中的人,况且她还是高门小姐,自有其特殊性。不过,我们多少能从她的心理状态推知古代社会中那些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的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
面对主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之无法满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听之任之,甘心领命。马斯洛说:“一个被剥夺了爱的人之所以恋爱,是因为他需要爱、渴望爱,因为他缺乏爱,所以他就被驱使去弥补这一致病的匮乏。”(15)(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197页。因为是“致病的”,所以就不得不去补偿这样的匮乏。如何补偿呢?当然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日常生活获得真实的补偿:一个缺乏爱的人因为他人爱他而寻找到了爱。获得真实的补偿实质上是满足了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顺带也满足了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如果不能得到真实的补偿,那么,一个有着如是匮乏的人也只能设法得到虚拟的补偿。
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也必然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但是,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会撇开正常途径(满足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而试图从非正常途径获得满足。这非正常途径主要是欣赏某些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表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经验性或超验性艺术作品。经验性作品有《西厢记》等,超验性作品有《牡丹亭》等。不管是经验性还是超验性,这些作品客观上的主要功能是,在无法满足人们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的前提下,直接满足他们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满足了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会顺带满足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吗?当然不会。即使在满足了主观意义上爱的需要之后,一个缺乏爱的人因为他人爱他而寻找到了爱,也即满足了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同样没有必然联系。这便是上述主客观意义上基本需要的第三种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严酷的婚姻制度不仅决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戏曲结局的生成,而且还决定了这种结局的大概率生成。马斯洛认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为“匮乏性需要”。(16)许金声:《译者前言:关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第6页—第7页。所谓匮乏性需要,也即“因匮乏而产生的需要”。(17)(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42页。有匮乏,就有需要;越匮乏,越有需要。正因为爱的需要为“匮乏性需要”,因而婚姻自由越“匮乏”,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越无法得到满足,而人们也越是需要通过满足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来获得虚拟补偿。
艺术作品呈现的可是他人的事情,与受众有何相干?作为艺术世界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何以就能满足受众的主观意义上爱的需要?这与一种心理效应密切相关。朱利耶《好莱坞与情路难》指出:“电影必须依靠具体的人物形象,它会产生一种连带效应,让观众找到自己的偶像,即一个理想中的美丽、诱惑或高贵的化身。只为一睹偶像影星的风采而去看电影,这固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有谁从来没有这么干过?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想象成银幕上自己仰慕的那个形象了。”(18)(法)洛朗·朱利耶:《好莱坞与情路难》,朱晓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第6页。梅尔《电影社会学》强调:“做梦者想象自己就是电影里的那个主角,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19)J. P. Mayer, Sociology of Film:Studies and Document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15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以观赏《奥赛罗》为例,描述了受众典型的心理体验:“我们也可以审美地同情奥赛罗,在想象中把自己和他等同起来,和他一起因为胜利而意气昂扬,因为恋爱成功而欣喜,和他一起听信伊阿古的谗言,遭受妒忌与愤怒的折磨,最后又充满绝望和痛悔,和他一起‘在一吻之中’死去。”(2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2页。把自己想象成演故事或说故事艺术作品中自己所同情、所喜欢、所仰慕的人物,这是受众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笔者姑且将导致这种心理现象的效应称为“代入角色效应”。正是这种效应使一种错觉或潜意识感觉得以产生,也正是这种效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的虚拟补偿功能之实现成为可能。
四
如果通过满足主观意义上爱的需要来虚拟补偿无法满足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这一社会心理机制无条件地有效,那么,我们应该在爱情题材的戏剧作品中看到清一色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然实情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戏曲作品几乎碾压式地呈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如关汉卿《拜月亭》、白朴《墙头马上》、王实甫《西厢记》、郑光祖《倩女离魂》、汤显祖《牡丹亭》、李玉《永团圆》等无数作品,但还是存在着朱有燉《香囊怨》和孔尚任《桃花扇》等寥寥几部呈现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之结局的作品,不过这两个实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曾有过“成眷属”的短暂经历。20世纪前西方戏剧既呈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也呈现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结局,前一种结局只是略多于后一种结局。就拿莎剧来说,既有呈现前一种结局的《维洛那二绅士》《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辛白林》和《暴风雨》,也有呈现后一种结局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作为英语中的熟语,“happy ending”主要指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21)That’s the explanation of “happy ending” i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Happy ending, an ending in a novel, play, etc., in which the characters acquire spouses,money, do not die, etc.”在所有英语词典中,牛津版的这部词典体量较大。就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而言,一个是碾压式的多,另一个是非碾压式的多。中西戏剧何以形成如是差异?
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上文提及的婚姻自由程度。就婚姻自由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远不如同时期的西方社会。(22)See Chester Holcombe, The Real Chinaman (189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Press,2009).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此书中记载了他对清末婚姻的观感。从他那显而易见的猎奇心态和惊讶口吻中,我们完全可以反推20世纪之前西方社会在婚姻问题上的相对自由程度。婚姻越不自由,艺术作品的受众就越会有缺失性体验(对婚姻自由缺失状态的体验),继而越会有缺失性需要(虚拟补偿如是缺失状态的心理需要)。在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互动机制的作用下,受众的缺失性需要有可能使创作者形成缺失性创作动机(以创作来虚拟补偿如是缺失状态的动机)。创作者最终是否会形成这种创作动机?如果形成了,这种创作动机是否强烈?这都缘于第二个原因,即艺术文化对虚拟补偿的认同程度。
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艺术本质论是强调艺术为情感之表现的表情说。表情说总体上充分肯定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强调创造性再现的真实甚至表现的真实,因此它与想象说有着天然联系。郎加纳斯《论崇高》指出,“所谓想象作用”,“现在用以指这样的场合:即当你在灵感和热情感发之下仿佛目睹你所描述的事物,并且使它呈现在听众的眼前”。(23)(古罗马)郎加纳斯:《论崇高》,周来祥主编:《西方美学主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而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则强调:“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纯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24)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这两段话都道出了感情与想象的关联性。感情其实也就是想象的内在动力,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感情越浓烈,越激越,想象也就越丰富,越奇特。当现实世界中的图景不足以承载艺术家的感情和愿望时,那么不同程度理想化了的图景在艺术家心中乃至作品中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汤显祖地下有知,一定会赞同上述说法。《牡丹亭记题词》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5)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五之二记王导言:“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礼断之。”这是汤显祖此语的先声之一。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6)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汤显祖此语表面上指杜丽娘一往深情从死亡中复生,实际上却言说了感情之极与想象之奇的关联性。
从根本上说,古代中国人是没有“真”(现象真实而本质真实)这一观念的,他们有的只是“诚”(感情真实与现象往往不真实)。艺术家在真实且淋漓尽致地表达一己之感情时往往会突破“理”的藩篱,从而使艺术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现象变形,使之看似不真实。然而,只要感情真实,即使它看似不真实,我们还是可以妥协地视之为“真实”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冯梦龙《墨憨斋新定洒雪堂传奇》说:“情到真时事亦真。”(27)参见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5页。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戏曲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的大概率生成与中国古代由别具一格的表情说、想象说和艺术真实说所建构的艺术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类结局——不管是经验性的,还是超验性的——都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正是中国古代的艺术文化赋予了它以正当性。
大异其趣的是,模仿说(再现说、反映论)是西方在19世纪之前占主流地位的艺术本质论。艾布拉姆斯认为,它是“从柏拉图到十八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28)(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迈纳说:“西方诗学的区别性特征正在于由摹仿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观念。”(29)(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6页。模仿说强调艺术是客观世界(自然或社会生活)的反映(模仿或再现)。大多数模仿说者主张艺术作品不仅应该反映客观世界的现象,而且还应该反映寓于其中的本质,或者认为若艺术作品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象,也必然会反映寓于其中的本质。
在一些低级形态社会的生活中固然有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现象,然并非每一对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甚至无法如愿者反倒占多数或绝大多数。从中可以推断,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是相关社会生活的全部规律而仅仅是某一种规律。社会生活的本质往往是由一系列规律来体现的。如果某一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过多地甚至一味地表现某一种规律,那么它们也就无法真正体现社会生活的本质。由此可见,模仿说在根本上与高频度呈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的倾向性相抵牾。理论是后置的,是对实践进行总结的产物,但它一旦成形,必然会对实践产生规范作用。在模仿说的影响范围内,高频度呈现这一结局的创作冲动必然被大大地压抑。
压抑这种创作冲动的还有西方的悲剧观。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人的主要倾向是重戏剧诗、史诗而轻抒情诗,在前二者之间尤重戏剧诗(除柏拉图等少数理论家)。而推崇戏剧诗的理论家大多又推崇其中的悲剧。亚里士多德《诗学》说:“显而易见,悲剧比史诗优越,因为它比史诗更容易达到它的目的。”(3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诗学·诗艺》,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7页。而叔本华和别林斯基等都认为悲剧是最高艺术体裁。既然如此推崇悲剧,那么包括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在内的所有圆满结局自然难有容身之地,因为它们不宜出现于西方式的悲剧中。西方理论家和五四以后的中国理论家在贬损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时所使用的理论武器之一便是西方的悲剧观。如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他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31)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中西婚姻自由程度的差异和艺术文化的差异共同导致了20世纪前中西戏剧在呈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方面的差异。
五
本文旨在阐明“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生成原因,却花费了大量笔墨阐明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生成原因,因为阐明后一成因是阐明前一成因的必经途径。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有两大核心内容:“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这两大内容严重妨碍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妨碍他们满足客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从而使他们产生烦闷和惆怅的情绪,使他们无法满足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古代戏曲力图以自己营造的乌托邦图景让受众撇开客观意义上爱的需要而直接满足主观意义上的爱的需要。
为达到这种虚拟补偿的目的,中国古代戏曲家就要与婚姻制度对着干。你要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我就杜撰各级官员赐婚甚至皇上赐婚,以行政权力强行改变有情人之家长的意志,以突破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这一屏障。一般来说,阻碍有情人成眷属的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干预他们意志的行政权力之等级也就越高。你要门当户对,我就杜撰门不当户不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因而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有情人”往往来自两个相差甚大的家庭。只要“有情”,只要将爱情进行到底,他们总是能够冲破封建礼法之桎梏终成眷属。
如何设置有情人的家庭地位?是将男方的家庭地位设置得比较高好呢,还是将女方的家庭地位设置得比较高好?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既有女方门第高贵而男方出身低贱,也有男方门第高贵而女方出身低贱(32)宋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宦门子弟完颜寿马与女伶王金榜终成眷属。元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秀才安秀实与妓女宋引章终成眷属。《救风尘》颇具样本意义,一个门第较高的青年男子与一个色艺俱佳的妓女终成眷属是最常见的。,但是,前者无疑多于后者。何以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青年女性很不容易在社会阶层间向上流动,而青年男性却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或经商等拥有如是流动性。就表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曲而言,如是流动性有时是必要的。
尽管艺术作品是虚构出来的,但它毕竟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哪怕它呈现的仅仅是虚构的真实、假定的真实。艺术家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让门不当户不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要让对实际生活中婚姻极度不自由有着深切感受的受众认同如是结局的真实性却是相当不容易的。(33)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说穿了也即艺术作品所建构的图景具有令人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性质。至于如何才能让人宁可信其有,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做法。中西皆有很多关于艺术真实的理论,西方的理论未必能解释中国的艺术作品,反之,中国的理论也未必能解释西方的艺术作品。即使你把这些理论都读了,也未必能对艺术真实有透彻的理解。笔者不无偏激地认为,“艺术真实”是个伪概念。纵然如此,笔者依然不能免俗地使用这一概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它以特定的内涵。原本杜撰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就是为了争取受众,现在如果不能让受众认同如是结局的真实性,同样也不能争取受众,这岂非“可怜无补费精神”!
既要杜撰作为有情人的高门小姐与贫寒之士终成眷属,同时又要让受众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既要虚拟补偿,又要艺术真实。于是中国古代戏曲家不经意间陷入了两难困境:前者要求实际生活与戏曲作品尽可能有反差,实际生活中门第悬殊的有情人很难成眷属,戏曲作品偏要杜撰门第高贵的青年女性与出身贫寒的青年男子终成眷属,反差越大(最好是门第很悬殊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虚拟补偿越有力,但也极其不可信;后者要求实际生活与戏曲作品尽可能无反差,反差越小,越可信,但虚拟补偿却极其乏力。
为了摆脱如是两难困境,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惯用“伎俩”是,或者“伪造”家史,或者“伪造”前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言以蔽之,也即杜撰“落难公子中状元”之情节。“落难公子”四个字表明,男主人公的血统是高贵的,艺术家力图以此来缩小有情人的家庭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中状元”三个字表明,男主人公的前程是光明的,艺术家力图告诉人们,尽管以前的家庭社会地位有差异,但状元这一身份已足以为其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由此可见,“落难公子中状元”是虚拟补偿性与艺术真实性博弈的产物,详言之,是虚拟补偿性与艺术真实性通过博弈而达成妥协的产物。也正因如此,它才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表现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戏曲的“标配”。因为要达成妥协,所以必须在虚拟补偿性与艺术真实性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既让作为有情人的高门小姐与贫寒之士终成眷属,又以彰显贫寒之士的高贵血统和光明前程来增加终成眷属的可信度。
如果有人问,出现概率高的是“落难公子”还是“中状元”?那无疑是“中状元”,因为它还兼顾了事业成功的结局,而如是结局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主观意义上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不仅如此,“落难公子”说的是血统高贵,而“中状元”说的是前程光明。血统高贵只不过是虚名而已,而前程光明却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千钟粟”和“黄金屋”。因此,一个高门小姐与一个状元联姻要比与一个落难公子联姻更具可信度。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为前相国之女,而张君瑞是前礼部尚书之子。张父生前正直廉洁,死后“只留得四海一空囊”。父母双双弃世后,张家家道中落。因此,崔张联姻实际上是一个高门小姐与一个落难公子的联姻。说穿了,这样的人物设计以及普救寺解围这样的剧情设计都是为了增加崔张联姻的可信度。然而,在崔张事实上的婚姻为崔母发现后,她却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赴京赶考。张果然争气,“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或许在王实甫看来,最能增加高门小姐与贫寒之士相联姻之可信度的还是“中状元”。“王实甫们”的这番心思鲁迅看得最真切,如前所引,所谓私订终身,也“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