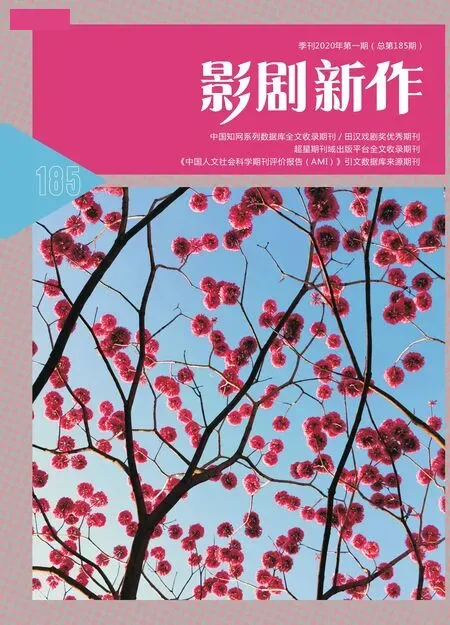传统经典的现代阐释
——评弋阳腔《芦花絮》的改编创新
2020-12-03黄国飞
黄国飞
一部戏曲能温暖心灵,教化民众,就是其主创具有恩泽苍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弋阳腔《芦花絮》接续传统,启迪当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响力,是文化自信的活态展示。
这部戏,挖掘传统文化《二十四孝》中的精华内容,传承新的孝道思想,从古典戏曲内容中绽放出新的时代精神。中国传统孝文化,在细腻动人的弋阳腔的演绎之下,绽放出震颤心弦的无穷魅力。
一、孝与慈
全剧的主题是围绕孝来铺陈展开的。编剧娴熟地运用现代心理学知识对人物性格进行细腻刻画,手法炉火纯青。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想法,都是不完美的好人,这样不但为矛盾埋下伏笔,也让最终的和解成为可能,为这部剧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没有突兀的性格转变,没有不合情理的剧情走向。这是一出“治愈系”的戏曲,编剧给出的剧中人物为:一个情商不高的父亲,一个一念之差的后母。没有绝对的坏人,有的都是有缺点的好人。继母内心对日渐长大的继子,突然生出一种惶恐和私心,而这种情绪又在父亲不吝对长子的称赞中,演变为其对继子实施迫害的具体行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阴谋产生了,家庭的和谐从而被打破,唯一能重新弥合这一裂痕的行动主体是前妻留下的孩子。
整部戏剔除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糟粕,保留了其精神精华,给人的感觉是犹如绵香醇厚的陈年老酒。而这种积淀感来自于编剧对于孔子所倡导的孝的精神的深刻理解,不同于后世腐儒对于孝的偏执和扭曲,使孝的精神得到真正张扬和提升,也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这一更深层次上更新了孝文化。孝文化在这部《芦花絮》中具体展现为父慈子孝。
传统《二十四孝》中有残忍暗黑的郭巨埋儿,有不合人道的王祥卧冰,有惨烈悲壮的尝粪忧心,这些糟粕都是要摈弃的,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而《二十四孝》中经常受继母虐待和百般刁难的闵子骞故事,在编剧的妙笔之下,却改成了继母面对丈夫偏爱读书优异长子的心理失衡,一念之差犯下错误,根源在于人人都有的自私自利,诱因在于父亲的偏爱和不吝赞美,继母实施的迫害继子的行为实属被其父的语言所激惹,换句话说是被父捧杀的范围,闵父的情商不高可见一斑。而原来故事中闵子骞因小事而被父亲不由分说的鞭打责骂,也被编剧改为推车无力,让父亲栽了一个跟斗后的恼羞成怒,所有的情节发展和推动都合乎情理,合乎逻辑,避免了让现代观众不理解不同情的剧情硬伤。
同为孝道的典型——让梨的孔融,最后却发展出蔑视礼法的反叛言论。《后汉书 · 孔融传》中记载有孔融的观点:“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其意为父母是受情欲所左右才生下子女的,生孩子只是享受过程所附带的结果。这是一种带有生物学视角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此种论调在王充《论衡》中就有了先声,“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作为孝道文化的典型代表却发出了这样反叛的论调。这样的思想是对孝文化的深刻反思,不再单方面的强调孩子对父母要孝顺,而是着重强调父母首先能够做到对孩子的关心爱护,自己做个好人,才能激发孩子的孝。这样的精神符合鲁迅、胡适、钱钟书等现代知识分子的对孝文化的反思和认识。
经过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孝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父慈子孝的相互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孝文化也是回到了孔子的初衷。剧中展现的父亲对孩子们慈爱、女婿对岳父尽孝,以及继母在事发之前的十几年对闵子骞的饮食穿着的照顾,无不体现了双向性的关爱才是孝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文化的自信就展现在接续传统、照见当下,意味着传统文化对当下现实的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家与国
孝是对于家庭稳定起重要作用的文化精神。对整个国来说,家是最小的单元组织,一个个小的家庭组成了大的国家。在戏文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咏唱“尽忠于国,尽孝于家”,这是编剧的情怀,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一体的深刻理解。爱国如同爱家,爱家是爱国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热爱自己的家庭而会去热爱自己的祖国。在生存意义上,有国才有家;在发展意义上,有家才有国。面临生死存亡、外族入侵的时候,有国才有家;面对盛世繁华快速发展的时代,有家才有国。家国一体的意义得以充分展现。
以家庭为核心,是任何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家庭生活其实就是平凡中起了冲突矛盾然后和解的过程,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有磕绊也有温馨,从冲突到和解的模式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所有这些家庭中的大大小小一家子人的家长里短中,男耕女织,做饭缝衣,凸显出平凡生活的温暖温馨温情。这就是戏曲展现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
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一直深受中国观众喜爱,可以让人百看不厌。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充分展示了新旧思想观念在家庭成员间的交锋,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在具体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讲述一些平凡的人生道理。如何克服观念不合的矛盾,那就是用爱和解,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换位思考,用机智巧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弋阳腔《芦花絮》亦是循此而作的一部戏。因为秉持不同的观念(继母的自私),进而造成不大不小的错误(芦花絮绵衣),从利益攸关的各方不同立场(继母也曾“终日操劳里外忙,白日厨下调茶饭,夜晚堂前缝衣裳,嘘寒问暖细照看,亲力亲为件件桩桩,子骞虽是前房儿,不是亲生是我养”),逐步化解矛盾(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劝爹留母在,保得一家安)。
韩国作为受汉文化影响十分浓厚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难免出现的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他们所经历过得一切正是我国当下所发生。所以他们的家庭伦理剧很受中国观众欢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就是我国出口的,现在反而转为内销。呈现文化传播中的回流现象。在细致描述家庭成员之间温暖亲情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韩国电视剧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点在弋阳腔《芦花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反复咏唱“尽忠于国,尽孝于家”)。
现代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不再是压抑个体,而看重的是每个人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起成长,共同努力,每个人的个性都得以保护、重要性得以展现。在《芦花絮》中继母的转变正好体现了这一方面,继母的重要性得到继子闵子骞的褒奖和赞扬。表面上是牺牲小我,成就全家的戏码,其实际意义是尊重像继母这样的每一个个体,这样每一个个体反而会对家庭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曾有专家在观剧之后提出,继母的行为转变在剧中铺垫得不够,为什么继母从一开始的对子骞还不错变成了进行迫害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宗法制所决定的。因为在宗法制的社会里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宗法制度”中最为基本的一项原则,简单解释就是权位、财产都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确立于夏朝的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其在商朝得到进一步发展,于周朝时期得以完善,然后它一直成功的延续到了清朝——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可见其根深蒂固。以周代为例,其宗法制度有“大宗”和“小宗”之分。“天子”即周王,被称为“大宗”,既是受命于天,上天的儿子,代替上天来管理天下百姓,也意味着王是“天下的大宗”。王的嫡长子在他归天之后继承王位,成为“天子”;王的其他的儿子即是“小宗”,他们要降一个等级,只能当诸侯。同理,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就成为这个封国的“大宗”。以此类推,社会以这种层层分封的关系,搭建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而且周武王明确规定王位只能“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而闵子骞的先祖是鲁国第四代国君鲁闵公,宗法制度在闵家可以说得到这个家族的严格执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闵子骞的嫡长子地位牢固不可动摇,继母本不坏的心思,在强大的社会观念制度面前,终于起了变化,所以提出让闵子骞出去学徒,分家单过。闵父毫不考虑这一建议,直接以孩子还小,以后要读书为由,一嘴带过,从这些细节可以找到继母为什么会出现恶行的蛛丝马迹。
三、新与旧
孝子闵子骞的故事已经数次搬演上舞台,从宋元戏文《闵子骞单衣记》,到明代传奇《芦花记》,再到清唐英的《芦花絮》,这就是经典的不断传承与重绎。人文精神需要叠加与积淀,在继承中得到时代的检验与创新。每个时代都需要对经典进行时代的重新解读,这种创新体现在继承之中,经典与创新从而成为永恒的话题。旧瓶装新酒成为重要的经典创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川编剧的《芦花絮》看上去是改编,其实也是一种重新创作。
优秀的戏剧导演奠定了一出剧最终的走向,编剧的思考深度决定了这出戏的思想高度。此戏的导演对古典戏曲的把握也十分到位,让第一次看的人完全觉得这就是一出传统戏,一出传承了百年的老戏。从文化精神上来看,其实这是一出新创剧目,虽然编剧谦虚地给自己定位为改编,其实从内容思想到人物塑造上的创新,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新创的戏了!说这部戏老,是完全的孝文化的精神传承,家国情怀的展现,也是古典戏曲程式化的传承;说这部剧新,是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这些新表现在编剧和音乐以及舞美上。我们之所以喜欢看一部老剧,是因为它能常看常新,其中包含着先进的符合当下时代精神和人类发展潮流的思想。由此可见,卢川编剧的《芦花絮》是一出好戏,一出可以传承百年的看家戏。
最好的戏曲创作应该是如盐入水,了无痕迹。生硬的说教和思想观念的口号式喊叫,不是一部艺术作品。好的戏曲如同做菜要五味调和,不凸显其中任何一种材料。剧本、导演、演员、音乐、舞美,各司其职,共同创造一部优秀作品。一出好戏不是某一个主创突出就能创作完成的。在这一点上,《芦花絮》的主创团队做得非常出色。风格即人格,从整个戏的风格来看,编剧是个温暖有爱的人。没有把继母写得怙恶不悛。从现代人的角度把继母还原为一个可以得到原谅,一个值得宽宥的人。不然人们看了特别坏的继母说什么也不会理解闵子骞为什么会原谅她的迫害、容忍她欺辱。
情理并重,情在前,理在后。编剧尊重女性,认可女性的付出和劳动,在剧中继母是一个为了家务和孩子整日操劳的形象,没有继母的忙里忙外,就没有孩子们嘴里的热饭,身上的暖衣。十多年的付出不是一个错误就可以抹杀的。而编剧给继母发现闵子骞发烧之后写的一段唱词十分有意思,唱词为:“陡然间发觉他脑热滚烫,不由我心下犯思量,莫非是芦花絮绵衣,数九寒天难抵挡?哎!他年轻气壮有何妨?我无事找事不值当。自入闵家为填房,终日操劳里外忙,白日厨下调茶饭,夜晚堂前缝衣裳。嘘寒问暖细照看,亲力亲为件件桩桩,子骞虽是前房儿,不是亲生是我养。为继子反将自身怨,又何必在此胡乱想。”这是继母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和情感切割,这个时刻编剧把她的心里矛盾完整的还原,从而可以让观众得到原谅继母的理由,编剧心细如发,在细节处可见一斑。
唐英的《芦花絮》中闵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家长,家人的一切都要服从他的意志。儿子赶车不利,鞭打;妻子虐待前妻孩子,休掉;他自己则是从来不计任何过失的,是伟大而又全能的一家之主。卢川的《芦花絮》中,父亲是一个榜样,在剧中开端处,孩童念错字之后,闵父的处理方式给予闵子骞一个学会原谅别人的范例,有错即改,即可原谅。才有了闵子骞后来的“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劝爹留母在,保得一家安”的这种宽容谅解,怀着感恩的心,选择原谅,去解决问题。从利更从情上,劝服父亲,晓之以利,动之以情。可见编剧深谙心理学,对角色进行了十足的心理分析。
唐英和卢川的《芦花絮》戏文都写了四出,唐英的四出为《露芦》、《归诘》、《诣婿》、《谏圆》;而卢川的为《受衣》、《送柴》、《露芦》、《谏圆》。唐英的第一出第三出都是以赏雪引出的故事,对季节轮换的重视,表明农耕文化下的剧作家和观众对时光的体认,雨雪对收成之间联系的确认,这在当时是一种经典展现方法。其戏文中不乏瑞雪与丰年的关系的多方描述,对劳苦大众的关心也在对天气气候变化的感叹中,点点渗透。这是唐英剧本的优点。而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与岁时节令相脱离,农作物已经可以反季节种植,人与土地和作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从而无法体认这种农业社会特有的天人合一的状态。如何让现代观众沉下心来观看节奏相对缓慢许多的戏曲,是当代戏曲编剧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芦花絮》则以很紧凑的剧情,细腻的心理描写,大刀阔斧地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细枝末节,比如赏雪,比如戏中戏,很好的回答这一时代提出的挑战。
现在的戏剧创作充满浮躁的风气,编剧其实光有才华远远不够,耐心才是重要的品质。一位编剧,拥有一颗沉潜淡定的心、具有一种精耕细作的写作精神,才能把故事编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这种细腻妥帖的处理方式,方能让观众沉浸在深厚悠远、流转绵长的中国故事,仿佛喝了一壶陈酒佳酿。虽然在戏里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然而温暖的结局,给人以安宁和治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