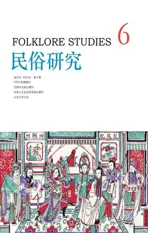16世纪末朝鲜人对外交往中的“风俗辩难”研究——以《大明一统志》为对象
2020-12-02解祥伟
解祥伟
从中国输往朝鲜和日本大量汉籍是古代东亚世界交往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朝鲜与日本社会对中国知识信息的高度重视和阅读需求;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大幅提升了东亚地区的整体文明程度。受传统中国“天下秩序”“华夷一体”理念影响,汉籍中有大量周边国家内容书写,而其书写是否准确,往往会引起国家间官方交涉或民间论争。例如,明代的《皇明祖训》《大明会典》等史籍曾记载,朝鲜王朝(1392-1910)的建立者李成桂为权臣李仁任之子,出身不正;且靠弑杀高丽国王而上位,得国不正。朝鲜认为其书写不确,对其王权合法性造成冲击,于是连年遣使赴明交涉、辩诬,力图修正相关书写。目前,这一问题已得到学界特别关注。(1)以《皇明祖训》《大明会典》相关记载为根源,造成明清中朝关系史上一系列的“宗系辩诬”问题。关于中日韩及欧美学界相关研究可参见黄修志:《十六世纪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系辩诬”与历史书写》,《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其实,朝鲜除了对中国史籍中的朝鲜国王宗系书写等政治性内容进行交涉外,16世纪末的朝鲜人在对外活动中,还曾就《大明一统志》中对其国风俗的书写等文化内容对外“辩难”,而且其辩难对象还包括了日本,成为跨越东亚三国的交涉史事件,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2)中国学界对《大明一统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编修、史源、版本、刊刻、编纂人员、纂修机构、史料价值等基础问题层面。关于这一问题,只有韩国学者李佑成有所注意。他在《金诚一与〈朝鲜国风俗考异〉》(《洌上古典研究》2019年第2期)一文中关注到《大明一统志》传入日本后,因其所记朝鲜风俗引发朝、日交涉,不过他没有将其放入日朝“文明争竞”背景下讨论,且未注意到朝鲜人在明朝也曾经遇到类似的困扰而有过类似的举动,从而未将相关事件置于一个比较视野之中进行考察。本文从东亚史视角出发,以具体历史事件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连贯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明一统志》的编写及其所记朝鲜风俗
中国史籍书写“域外”内容,与传统王朝的天下观念(3)古代天下观念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内外观念、中央四方论、夷夏之辨等三个方面,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2页。影响密切相关,在商周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拱卫中央的四方周边族群记载(4)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03-617页。,而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则形成了系统性记载周边国家的专门篇目(5)书中关于域外民族及历史的专门篇章包括《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并为之后历代正史所延续。这种书写传统及背后“天下一统”“华夷一体”的政治理念慢慢对地理志书的纂修也产生影响,宋代乐史(930-1007)的《太平寰宇记》最先专设“四夷传”,记载周边国家及民族史地知识。《大明一统志》是在之前历代地理志书的基础上纂修而成,自然也沿用了这一传统,以彰明一统盛世和巩固统一大业。(6)元代《大元一统志》,其名取春秋大一统之义,原本体量甚巨,有1300卷,惜现存仅十数卷,无从得知其具体的类目,但它是在《太平寰宇记》等志书基础上纂修而成,且其纂修具有体现强烈的大一统之目的,所以很可能也存“四夷”类目。《四库全书总目》说:“知明代修是书(《大明一统志》)时,其义例一仍《元一统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明一统志·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页)可见,《大明一统志》的编纂受之前各种地理志书影响颇巨。《大明一统志图叙》中说得非常清楚:“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7)李贤、万安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前,《大明一统志图叙》,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书内未标注页码),《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所以,除中国主体部分外,它也将“四夷”共58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纳入书写范围,成为“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无不备载,视古盖加详焉”的“全国性”地理总志。
《大明一统志》从朱元璋立国之初即开始纂修,中经明成祖、景泰帝、明英宗等诸帝推动,至天顺五年(1461)修成。其所征引资料十分丰富,包括历代正史、总志、方志、图册、政书、类书,文人题记、诗词、文集,等等。《大明一统志》后经增修与翻刻,共形成了天顺五年(1461)内府刻本及其翻刻本、嘉靖重修本、万历万寿堂刻本及其翻刻本三个版本。(8)参见杜洪涛:《〈大明一统志〉的版本差异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这三个版本内容互有差异、增删,但主要涉及的是中国主体部分,周边之国内容没有变化。(9)经笔者仔细核对各版本内容,关于朝鲜风俗的记载,三个版本无任何变化。因此,笔者依照最早的天顺五年内府刻本所记,将《大明一统志》中所记朝鲜风俗全文摘录如下:
风俗柔谨为风(《汉书·东夷叙论》: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昔箕子施八条之约,遂乃邑无滛盗。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戴折风巾、服大袖衫(《北史·高句丽传》:人戴折风,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贵者紫罗为之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妇人裙襦加襈,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为饰),男女相悦为婚(同上。俗多游女,夜则男女群聚为戏,相悦即婚,无财聘之礼),死经三年而葬(同上。死经三年而葬,居父母夫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埋讫,以死者服玩车马至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好祀鬼神,修宫室(《寰宇记》:形貌洁净,男女好祀鬼神社稷灵星,以十月祭天国。有大穴号隧神,亦以十月迎祭。多山少田,故节饮食而好修宫室,始为扶余别种,故习俗相类),俗知文字喜读书(《五代史·高丽传》)。饮食用俎豆,官吏闲威仪(宋徐兢《图经》:饮食用爼豆,文字合楷隶,上而朝列,官吏闲威仪而足辞采下,而闾胥陋巷,经馆书社三两相望,子弟未昏者则群聚从师,稍长则择友讲习),居皆茅茨,以秔为酒(《文献通考》:居民皆茅茨,大止两椽,覆瓦者十二,土无秫以秔为酒),多衣麻苎,巾帻如唐(同上。少丝蚕,多衣麻,纻市以米布贸易,器悉用铜,服尚素,男子巾帻如唐装,妇人鬌髻垂肩,约以绛罗,妇人僧尼皆男子拜),柔仁恶杀,崇释信鬼(同上。堂上设席,升必脱履,性柔仁恶杀,崇释教信鬼,拘阴阳,病不服药,惟咒咀厌胜,至亲有病不相视殓。俗不知医,后中国有往者始通其术),俸皆给田,刑无惨酷(同上。三岁一试,有进士诸科,士尚声律,百官以米为俸,皆给田,国无私田,计口授业,兵器踈简,强弩大刀,刑无惨酷之科,唯元恶及骂父母者斩,余皆杖肋,死罪贷、流诸岛累赦,视重轻原之)。(10)李贤、万安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外夷·朝鲜国·风俗》,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以上文字,加着重号的是所载朝鲜风俗的原文,而括号中则是《大明一统志》纂修者对原文的注释。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朝鲜风俗既包括“柔谨为风,俗知文字喜读书,柔仁恶杀,刑无惨酷”等符合儒家伦理标准的“美俗”,也包括“死经三年而葬,男女相悦为婚,好祀鬼神修宫室,崇释信鬼”(包括相关注释)等背离这个标准的“陋俗”。不过,无论是美俗还是陋俗,通过小注所示可知其基本因袭抄录自前代《后汉书》《北史》《五代史》《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文献通考》等中国官私史书,而不是实时实地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
风俗文化是一种社会传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单独存在,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11)丛振:《敦煌游艺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经过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朝鲜半岛自遣唐使开始便系统学习中国文教制度,文化上一意慕华,后来随着《朱子家礼》在南宋末年的传入,至明代,从儒家伦理标准看,其社会礼俗早已“移风易俗”而“文明化”了。(12)参见张品端:《〈朱子家礼〉与朝鲜礼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1期。而中国史籍中的域外书写,其重视的是“四夷”这一类目的存在,以满足体例上“华夷一体”的完整性,而对其具体的内容书写则较为随意,大多是抄录旧史而来,这在《大明一统志》关于朝鲜风俗记载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想见,这些记载传入朝鲜,必然会引发朝鲜士民的不满。
二、朝鲜官民在对明交往中的“风俗辩难”
《大明一统志》编纂完成后,除内府刻本外,也通过民间书坊刊刻,如福建建阳刘弘毅的慎独斋就进行过刊刻,这使得其流布较广。(13)参见周天爽:《〈大明一统志〉的书坊刊刻及其利用情况》,《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自朝鲜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一直存在书籍交流的现象。虽然天文、历法、地理、兵法等书是中国禁止流入朝鲜的,但朝鲜往往通过朝天使、燕行使等私买的方式购入。(14)参见季南:《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55-106页。因此,《大明一统志》于1461年刊布后,通过赴京朝天使臣,最迟在1477年便传入朝鲜。(15)《朝鲜成宗实录》卷八三,成宗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第9册,第495页。不过,朝鲜最初并未遣使赴明进行官方交涉,其原因在于朝鲜偷偷私贸明朝严令禁止的《大明一统志》原本就是一种违背其“礼义之邦”形象之举,且一旦明朝因其交涉而深究之,朝鲜不仅达不到改正相关陋俗书写、维护其文明形象的目的,反而可能会因此受到明朝的责罚。(16)朝鲜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后来在康熙年间,朝鲜曾以私贸自中国的野史《十六朝广汇记》中记载朝鲜“仁祖”事迹有误、影响其国形象为由,进行辩诬。清朝不仅没有同意其请求,反而以野史为禁书、朝鲜私贸为由,进行严厉指责。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八,肃宗五年三月七日,第38册,第405页。朝鲜也并非毫无反应,曾私下向赴朝明使进行抱怨,希望通过他们间接、非正式地向明朝方面传达朝鲜的意愿。
1488年,明使董越(1430-1502)与王敞(1453-1515)赴朝鲜颁明孝宗(1487-1505在位)即位诏。董、王2月25日入朝后,对朝鲜赠与的物品一件不受,且举止得体,得到朝鲜接伴使、吏曹参判许淙的高度评价(17)《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四,成宗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第11册,第312页。,宾主关系十分融洽,各自都少了一些拘束与防备。所以,3月5日许淙便私下与两使谈起《大明一统志》。许淙开宗明义地对《大明一统志》所记朝鲜风俗提出批评,认为其是沿袭中国古史记载而成,其中的很多记载已经不存于现时的朝鲜社会,其作为官方史书,记载偏颇,影响到朝鲜的文明形象,令朝鲜十分痛心。(18)《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四,成宗十九年三月五日,第11册,第314页。董、王二人通过与朝鲜士人的接触以及对朝鲜的实地考察,已经对朝鲜有了不同于《大明一统志》的印象。在这之前的2月29日,董越就曾对许淙说:“旧闻朝鲜读书知礼,今见宰相行礼,方信前闻之不诬。”(19)《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四,成宗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第11册,第312页。加之,《大明一统志》的相关注释明确表明了其内容是来自朝鲜所说的古史之言。所以,两使不但没有追究朝鲜如何读得禁书之事,反而对许淙的说法表示理解与支持。王敞当即提到董越归国后将参修前朝皇帝(明宪宗)的实录,可以改正《大明一统志》的相关记载。董越也表示朝鲜可将其现时的风俗文化尽录于他,他将代为奏达朝廷,将其记入实录之中。(20)《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四,成宗十九年三月五日,第11册,第314页。从史料的权威性来说,实录要高于《大明一统志》,因此,在董越看来,如果他能在参修实录时将朝鲜美俗载入,那么就可以弥补《大明一统志》记载朝鲜陋俗影响朝鲜形象的问题。
许淙向国王汇报,说他个人认为董越所说修实录时载入朝鲜今时风俗不一定可信,不过,依其所言,将朝鲜婚丧嫁娶等习俗写出与他,使本国美俗传播中朝也未尝不是好事。(21)《朝鲜成宗实录》卷二一四,成宗十九年三月五日,第11册,第314页。国王立刻同意了这个意见。很快,朝鲜将其本国良风美俗作成《朝鲜风俗帖》赠予二使。
《明实录》主要是围绕帝王纪录军国大政,不太可能录入外国风俗这类较为琐细之事,所以,董越归国后虽的确参与了《明宪宗实录》的纂修(22)《明孝宗实录》卷五四,弘治四年八月二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3册,第1064页。,但并没有达成所愿,将朝鲜提供的美俗尽录入实录之中。只是在其归国后私修的《朝鲜赋》一书中,关于朝鲜风俗的内容尽择自《朝鲜风俗帖》。《朝鲜赋》刊印后曾广泛传播(23)时人欧阳鹏就说:“(董越)磬其所得,参诸平日所闻,据实敷陈为使朝鲜赋一通,万有千言,其所献纳于上前者,率皆此意,而士大夫传诵其成编,莫不嘉叹,以为凿凿乎可信,而郁郁乎有文也。”参见欧阳鹏:《朝鲜赋原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6页。,但由于它毕竟是私人著作,无法撼动《大明一统志》对中国士人认知朝鲜的负面形塑。朝鲜人鲁认1599年的中国之行就对此体会颇深,并不得不与明朝士人进行“风俗辩难”。
鲁认(1566-1622),字公识,号锦溪,自少习儒业,精通性理之学,全罗道罗州人,1582年进士及第。1592年朝鲜半岛爆发壬辰战争,鲁认担任军事参画,屡立奇功。1597年6月,他在战斗中被俘获,后被掳至日本,在萨摩州度过18个月俘虏生活,期间,无日不思念故土,并主动搜集各种情报,希图归国后为朝鲜对日复仇献策。为此,他多次试图逃离日本,但均告失败。后偶遇一福建商船,当时中朝联军共同抗击日军的亲密情感使得鲁认与船主陈屏山、李源澄结识。船上有福建巡抚为搜集日本情报而派出的间谍林震虩。鲁认萌发先到“中华父母之国”,进而归国的想法,得到陈、李赞同,并介绍其与林震虩相识。林与其接触后,了解到他的身份及曲折经历,为其爱国之情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1599年3月17日在三人协助下,鲁认成功逃离日本,3月28日到达福建闽南。此后由明朝各地方官员派人护送进京,继而归国。
鲁认归国之后,撰成《锦溪日记》,记录其此次中国之行。目前留存部分全文将近4万字,主要记录他在福建滞留四个多月期间,与中国官员、儒生、百姓的交往及其各种见闻,涉及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记录了一件他围绕《大明一统志》所记朝鲜风俗与福建儒生进行“风俗辩难”之事。
1599年5月13日,在当地两贤祠书院,一众秀才与鲁认进行交流,有秀才向其表示,“愿闻贵国风教及婚丧祭等礼”。鲁认回答朝鲜“风教只依箕圣八政之教,婚丧一遵晦庵家礼”。这与《大明一统志》中的记录不同,秀才们便表示怀疑,同时“持来《一统志》,搜展四夷风土记中朝鲜记”,让鲁认观看。鲁认仔细审视后,对于书中所记的种种朝鲜陋俗十分不满,与许淙一样,立即表示其都是因循古史记载而成,并不准确,不值一哂,“此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一统志》,则太古之古史,泛修外国之史也”,并进一步进行了细致解释:
我国虽曰番邦,檀君与尧并立,而与中国肩比内附。故武王特封箕圣,衣冠文物礼乐法度,一遵华制,而吾道东者久矣。秦属辽东,汉封郡县,自晋时各分疆域,自为声教。然恭修职分,事大以诚,与诸夏无异。故自高丽时,世子十岁则入于中国大学馆参讲,而陪臣十人,亦皆参讲。有时乎通婚帝室,而鲁国大靖公主,亦出嫁于高丽。盖明君圣主,继世而作,崇儒重道,相尚以文治。名儒硕士,无代无之。若崔致远、薛聪、郑可信、李穑、崔冲、郑梦周类继入中华,或中科第壮(状)元,或官至翰林学士,或赐紫金鱼帒。大概我国文献,则文武科外,又别举孝廉科,故家序党塾国学,弦诵洋洋,达于四境。凡子生八岁,先教孝经心经,然后次学四书六经,皆以明经科为业矣。况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虽奴贱之人,父母之丧非独不用酒肉,至于居庐哭泣,啜粥三年,柴毁自尽者亦有之。或尝粪断指,流血入口,复苏父母,而旌表门闾者比比有之。家夫死则终身守节斋衰,矢死不他。三纲五伦礼仪廉耻,可轶于三代之上。故得称小中华之名素矣。(24)(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日记来源网站: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检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
鲁认从朝鲜蒙受箕子教化讲起,详述历代慕华事大,力行科举,举凡婚丧嫁娶都严格奉行儒家礼仪的教化历程,最后以朝鲜文化昌明,得“小中华”名号结束,洋洋洒洒、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尽管如此,众秀才《大明一统志》在手,“似信而不信”。于是,鲁认又进一步将朝鲜礼俗中特别重要的丧葬之礼写出(25)“我更示以自初丧敛袭入棺成殡成服,而朝夕奠哭无时,而国葬则五月而葬,士大夫则三月而葬。棺椁灰炭题主反魂,初二三虞卒哭大小祥禫服之制。一依晦庵家礼。”参见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日记来源网站: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检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其完全依遵《朱子家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最后,鲁认总结说《大明一统志》关于朝鲜风俗记载疏漏太多,对朝鲜极为不公,其归国后将上报国王,请求其与明朝交涉,改正其相关记载。“今此一统之笔,岂非疏漏而冤枉哉。不佞当回国之日,特达朝廷,然后因转报天朝,必欲改正一统之志也。”(26)(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日记来源网站: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检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如此,诸秀才方表示服气,并对朝鲜称赞有加,认为其遵礼守节甚至超过中国。(27)(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日记来源网站: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检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鲁认对福建儒生的“风俗辩难”方取得良好效果。
鲁认归国之后,随着其日记被朝鲜君臣广泛阅读,其在中国的经历被认为是“华国”之举,广受彰誉。不过,朝鲜对于《大明一统志》的偏颇记载,继续坚持不进行正式的官方交涉的态度,因此,其并未如鲁认所说,派出使臣交涉改正相关记载。实际上,《大明一统志》不仅塑造了负面的朝鲜形象,引得朝鲜官民抱怨、激辩,其传入日本之后,在朝鲜庚寅年(1590)通信使在日期间,更成为日本与之进行文化比赛的有力“武器”,使得朝鲜极为被动,不得不进行态度更为严厉的“风俗辩难”。
三、朝鲜使节金诚一与日本人的“风俗辩难”
通信使是15到19世纪,朝鲜向日本派出的正式外交使节。朝鲜和日本受华夷秩序扩大化的影响,在现实与观念层面都力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圈,并都试图把对方纳入自己的“圈子”,双方也都认为各个方面均比对方优越,彼此之间存在许多认识上的偏差。(28)参见刘永连、解祥伟:《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这在朝鲜通信使赴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葛兆光就观察到:通信使在日期间除了完成政治和外交使命,始终在与日本进行着明里暗里的文化比赛。(29)参见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比赛包括衣冠、风俗、学问、艺术等方方面面,实际上更是一种文明比赛。通常情况下,“朝鲜士人面对日本的时候,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优越心理,这种心理来自朝鲜人对自己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他们将日本看作是化外之地、蛮夷之邦,始终用一种俯视的眼光观看日本”(30)王鑫磊:《批评与回应:通信使与朝日“文化比赛”》,复旦文史研究院编:《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第199页。。但是,在1590年的朝鲜庚寅通信使之行中,朝鲜的文明优越感却遭到了日本的直接质疑,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其拿出的“证据”是来自朝鲜人口中“天朝上国”的《大明一统志》。
1590年(庚寅),应日本请求,朝鲜向其派出由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书状官许筬组成的通信使团。通信使团大概是3月从朝鲜出发;5月到达对马岛;7月到达堺滨的引接寺,同月22日到日本国都;11月7日,见到关白丰臣秀吉;来年2月,回到朝鲜复命。通信使团自踏上日本土地起,双方的角力就开始了,朝鲜多次指责日本不够文明,有违礼之举。先是日本在朝鲜使团到达对马岛时,没有派出宣慰使(31)宣慰使是负责欢迎和接待入境外国使节的官员,差遣宣慰使是外交礼节之一。接待,朝鲜指责其违背外交礼仪;其次,国分寺观光时,日本对马岛主义智在通信使前没有下轿,金诚一指责其“虽曰夷狄无礼,亦有君臣上下之分,义智何敢乃尔耶?”(32)(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答许书状》,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901册,第395页。;再次,朝鲜使团7月至堺滨时,“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礼单,其书曰:朝鲜国使臣来朝云云”。朝鲜使臣认为“来朝”二字是侮辱朝鲜之举,金诚一更强调使臣职责:“夷狄虽无知,使臣亦无知乎?”拒绝接受日本礼单。(33)(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倭人礼单志》,第1902册,第16页。复次,日本在使臣到达国都后,关白迟迟不予接见,朝鲜认为其违背了与邻国相交之礼。(34)(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五,《拟与上副官都船主》,第1901册,第405页。最后,日本在回复朝鲜的国书中称朝鲜国王为“阁下”,所送礼品为“方物”,遣使东行为“入朝”,显然视朝鲜为藩臣,令使臣极为不满。(35)《朝鲜宣祖修正实录》卷二一,宣祖二十四年三月丁酉,第25册,第601页。
通观这些外交摩擦,可以发现,日本处处是以朝鲜为“来朝”之藩臣来进行接待,而朝鲜则针锋相对,以“夷狄”无礼进行指责,这背后实际上是有关本国尊严的文化高下、文明优劣之较量。在朝鲜使臣看来,日本公然违背交邻礼仪,是“夷狄”之风使然,彼此高下立判。不过,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却令朝鲜稍显尴尬。
朝鲜使臣到达日本国都,等待关白接见期间,某日,有官方背景的日本僧人名宗陈者来访,闲谈之际,拿出《大明一统志》在通信使面前展示。(36)这里牵涉到《大明一统志》传入日本的问题,巴兆祥认为由于相关资料记载残缺不全,难以确定准确的传入时间,推测应该是在江户幕府时期通过唐船持渡的方式传入。参见巴兆祥:《〈大明一统志〉的出版及其东传对日本地志编纂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7页。笔者认为,从宗陈向通信使展示《大明一统志》来看,《大明一统志》在江户幕府(1603-1868)成立之前的1590年已经传入日本。这与鲁认在中国的遭遇类似,但鲁认当时并非朝鲜官方使臣,众秀才也无官方背景,且当时朝鲜也不存在与中国进行文明争竞的问题,而此时朝鲜通信使之行不同,其在日本所遇到的任何公私事件都事关“国格”,义智在朝鲜使臣面前不停轿之举在朝鲜一方看来都难以忍受,何况是有官方背景的日本僧人明显刻意之公开嘲讽,所以气氛陡然紧张起来。金诚一立刻拿出纸笔,“举国中通行礼俗,各注其下,以辨其诬,为《朝鲜国风俗考异》一册以与之”。(37)(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一二,《行状》,第1905册,第496页。这也与鲁认举动相似,不过,其情绪要激烈得多。鲁认不过是大概交代了朝鲜的文明情况,最多是把朝鲜丧葬礼俗详细介绍一下,而金诚一则是对照日僧持来的《大明一统志》相关记载,无论是“美俗”还是“陋俗”都逐条进行了注解与辩诬。例如,关于“柔谨为风”这条“美俗”,金诚一注到:
柔谨为风。我国人性,谦恭逊顺,慈祥恺悌。入则修事亲敬兄之道,出则尽忠君死长之义,和睦宗族,周恤邻里。吉凶相助,患难相救。士大夫崇礼义,励廉耻,农商工贾,亦守本业,无犯分陵上之习,非但柔谨为风而已。(38)(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朝鲜国沿革考异》,第1902册,第29-30页。
金诚一对朝鲜人“柔谨为风”进行了详细阐释,认为《大明一统志》相关记载远远不够,朝鲜“非但柔谨为风”。关于“俗知文字喜读书”这条“美俗”,金诚一进行了类似论证后,也说:“此则颇详记国俗,然我国之人,非但知文字喜读书而已。”如此,可以想见,金诚一对于相关“陋俗”记载反应则更为强烈,例如“男女相悦为婚”,金诚一便写道:
我国素秉礼义,婚姻之际,尤致其谨。不娶同姓,虽异姓,近族则不娶。又有三不娶:逆家子不娶叛逆,乱家子不娶淫乱,世有恶疾不娶。必择门户相适,家风修整者,与之议婚。先使媒氏通言,两家相许,则有问名,纳采,纳吉,纳征,纳币,亲迎等六礼。行六礼时,必先告祠庙。王公贵人,则备六礼,士大夫以下,则只行纳币,亲迎二礼,从简故也。至婚日,两家乡党宗族,各会其家,以相其礼。两家父母,各醮其子而命之,壻(婿)往妇家,奠雁再拜,遂迎妇而归。妇入夫家,夫妇行交拜,同牢,合卺之礼。翌日,妇谒舅姑。舅姑坐堂上南向,妇行四拜于堂下,有献币进馈之礼。第三日,主人以妇见于祠堂。妇四拜于阶下是日,(婿)往妇家,见妇之父母,(婿)行再拜礼。国朝婚姻之礼,谨严如此,安有相悦为婚,无聘财之理。中国传闻而误记之,不亦可痛矣哉,如庶人则不能备礼,多有苟简之风,然其父母,必通媒妁,纳币而成礼,亦无相悦之婚。所谓相悦者,如贵国倾城者之所为也,我国亦间有此等淫风,而国人贱之,不齿人类,其所产子孙,不通仕路;士族妇人,则不许改嫁,失行则绞,子孙亦禁锢。(39)(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朝鲜国沿革考异》,第1902册,第32-34页。
金诚一先是详细叙述了朝鲜关于男女结婚的一系列仪节,论证“国朝婚姻之礼,谨严如此,安有相悦为婚,无聘财之理”,进而证明《大明一统志》所谓“男女相悦为婚”是“传闻而误记之”,表示这是十分令人痛心之事。同时提出,即便庶人之家,因为贫穷可能有所简省,但基本仪节也都具备,根本不存在相悦之婚。另外,还不忘提到日本,说所谓“相悦”,应该是与日本的“倾城者之所为也”类似,而朝鲜虽间或有这类淫风,但“国人贱之”,有诸多惩戒措施,而日本则似乎没有。金诚一在此说明《大明一统志》记录不实的同时,还捎带着将日本数落一番。再如“死经三年而葬”,《大明一统志》中关于此条的注释中曾提到“以死者服玩车马至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的哄抢葬品现象。金诚一对此辩解,先是详细介绍朝鲜的丧葬之俗,认为其国“丧礼谨严如此,宁有三年不葬之事”,予以否认,然后针对《大明一统志》关于此条的注释也进行了批驳:
至于埋讫,以死者服玩车马至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则尤悖理也。盖我国之俗,凡民有丧,莫不匍匐救之。亲戚朋友之丧,则必以钱财衣服香烛等物来赙。哭泣吊祭,各尽情礼。若于葬日,争取死者之物,则是与禽兽盗贼无异也。曾谓礼义之国,而忍为此乎。(40)(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朝鲜国沿革考异》,第1902册,第39页。
金诚一认为这一现象“尤悖礼”,葬礼现场亲戚朋友是互帮互助“哭泣吊祭,各尽情礼”,根本不存在哄抢葬品这样的陋俗。其他的如“死经三年而葬、好祀鬼神修宫室、崇信释鬼”等条的辩解也与此类似。最后,金诚一对日僧说,他刚刚只是就《大明一统志》的记载进行逐条解释,朝鲜的国俗之美当然不仅仅包括这些。此外,他还解释了《大明一统志》收录朝鲜所谓“陋俗”的原因:朝鲜自箕子以来,礼俗就与中国无异,只有委巷间有一些土俗不同,中国道听途说了这些不同之俗,加上很少有人到过朝鲜,便予以坚信并录在志中。同时提到,按照这个逻辑,《大明一统志》中所记日本风俗大概也多有不实(41)《大明一统志》同卷有《日本国》,其中记录日本风俗也有“黥面文身,被发跣足,信巫好戏,信佛法”等陋俗。参见李贤、万安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外夷·朝鲜国·风俗》,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日本并没有资格以此来问难朝鲜。(42)“我国自箕子以来,礼义成俗与中夏无异,其中所不同者,乃委巷间小小土俗也。皇明收拾道听之说,录在志中,其语多鄙俚无稽。外国之人足迹耳目,未尝及于我国,则必以此志为可信,岂料其伪也哉。”参见(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朝鲜国风俗考异》,第1902册,第46-47页。金诚一通过这样饱含激情、严谨、系统的辩解,将日僧对朝鲜风俗的嘲讽最大可能地予以消解。日僧当即书示:“蒙示《朝鲜国考异》一册,贵国风俗,一举目可得其实,深荷深荷。后日见博陆侯(关白,即丰臣秀吉,笔者注),当对举云云。”(43)(朝鲜王朝)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卷六《朝鲜国沿革考异》,第1902册,第48页。他表示心悦诚服,回去后向关白报告。
四、余 论
中国史籍将周边“四夷”纳入历史书写,最根本的还是受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在儒家政治秩序观念中,中央的华夏与周边的夷狄共同构成王朝政治共同体,二者缺一不可。但是,这种书写主要是强调“四夷”这一类目的“在场”,至于类目之下的内容之详实、准确与否却并非重点。这一情况无论是在历代正史还是在各类地理志书中都普遍存在。具体到周边之国朝鲜,王元周就观察到中国史籍虽对其有很多记载,“但是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来记述,对其历史沿革、制度兴革很少用心去考证,中国正史中对朝鲜的记载也是陈陈相因”(44)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大明一统志》因袭古史,关于朝鲜的风俗书写充斥大量陋风陋俗,就是这种较为随意的域外书写的具体例证。
朱子学在13世纪末传入朝鲜后,很快成为朝鲜王朝的正统思想,对朝鲜社会生活、风俗习性等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45)参见朱七星:《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福州,1990年。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其文化自信,更因其与中国享有的同质性文化根基而成为中国眼中的“礼义之邦”,受到特殊礼遇,如朝贡场合朝鲜使节总是被安排在首位;朝鲜朝天使臣在北京受到约束较小,等等。《大明一统志》关于朝鲜风俗的记载不够准确,虽会对明朝民间士人的“朝鲜认识”起到不好的影响,但官方层面不会因此否认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成效,收回对朝鲜“礼义之邦”的认知,现实外交中更不会因之取消对朝鲜的特殊礼遇。朝鲜对此应该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始终没有派出官方使节进行交涉,因为他们的外交利益并未因此受损,其交涉反而会暴露其私贸明朝禁书的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葛。至于朝鲜仍对明使董越进行私下抱怨,鲁认更公开与众秀才进行辩难,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朝鲜人刚接触到这些记载,尤其是被明朝人当面质问后,与其长期以来以“小中华”自居而产生的心理期许落差太大,一时难以接受。不过,同样是以《大明一统志》作为根据,1590年的金诚一面对日本僧人的质疑时,情况却发生变化,变得严重起来。
对于朝鲜通信使来说,其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主动靠近,并以“天朝”上国认定自己的特殊文明地位来从精神上压制“夷狄”日本,而逐渐脱离中华文化圈的日本根本没有资格与其一较高下。未承想日本僧人却以《大明一统志》所记朝鲜陋俗为武器,借“中国”之口,暗讽朝鲜文化落后,直接否认了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教化效果以及朝鲜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文明地位,这是对朝鲜有力的“精神反制”。因此,与鲁认相比,金诚一的身份、面对的对象、所处的具体情境都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他的应对情绪、方法便不得不有所改变而更为震动、激烈。在这一事件中,《大明一统志》成为朝鲜、日本两国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载体,正如葛兆光所论,“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46)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
最后,如果我们放宽视野,16世纪末,鲁认与明朝福建儒生,金诚一与日本僧人宗陈等围绕《大明一统志》的“风俗辩难”实际上是超过两国范围,以朝鲜为桥梁的东亚三国之交涉史事件。从具体交涉过程来看,朝鲜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辩难,都在努力强调其风俗早已按照儒家文化标准而“文明化”,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这说明中华文化是朝鲜极为欣赏、服膺的文明标准。而日本则不同,《大明一统志》中对日本的书写同样包括许多其国之陋俗,但日僧宗陈并不避讳,仍然以之为嘲讽朝鲜的工具;金诚一在与之辩难过程中,也直接指陈此点,宗陈亦未如金诚一这般情绪激动而激烈反应。这表明,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即便其认为中华文化仍然有过人之处,但并不值得日本如朝鲜般这样重视,更不在乎中国书籍如何书写其社会风俗,日本对中国与朝鲜文化上的疏离显而易见。而这种文化上的欣赏服膺、淡漠疏离与各国间政治关系之亲疏似乎也若合符节。有明一代,朝鲜与中国建立起“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47)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朝鲜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307页。的紧密关系,而日本与中国则时近时疏,至16世纪末则早已脱离出费正清所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日本对朝鲜则一直心存蔑视,意图兼并,且很快在壬辰战争(1592-1598)中付诸实践。细梳16世纪末朝鲜人对外交往中的“风俗辩难”事件,留意文化远近与政治之离合,可以发现中、朝、日三国之间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关系中存在着异常丰富的细节与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