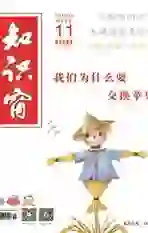让我们背上行囊,出发吧
2020-11-30施崇伟
施崇伟
余秋雨说:“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余秋雨说这段话时,正在遥远的巴基斯坦。而位于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都)附近的塔克西拉,曾有两个中国僧人先后到达:法显和玄奘。他们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这些山脉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却被这两个佛教旅行家踩到了脚下,载入他们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
走得远的古人,全靠体力行走,有时候可能会有马或骆驼,但肯定不仅是体力——法显和玄奘,有信仰的力量;商人,是利益的驱动;军人,是天职和使命有身。可文弱的诗人呢?
以四川为出发地的李白,脚头散漫,自由自在。他“一生好入名山游”,20出头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除了中年在长安供奉翰林两年半,他一生几乎都在路上,“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有人统计过,李白的足迹遍布18个省、206个州县、80多座山,以及60多条江河湖泊。我们何以知数旅程?他留给后世的诗歌,成了他的“游记”:《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数不完的行吟诗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他一生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无数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都是在路上吟诵出来的。
远行诗人中,最了不起的是边塞诗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边关战事既是青春男儿建功立业的机会,又是“文学青年”边地漫游、采风作诗的体验。国家有需要,自己有抱负,便唤起了边塞诗人策马边疆远行、挑灯看剑吟诗。“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即使是战死疆场,也在所不惜。“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边塞风光雄奇壮丽,戎马倥偬激发创作豪情。这样的远行,更悲壮;这样的诗人,更豪迈!
旅行,讓诗人的目光悠远而深邃;征途,让诗人的心胸宽广而大气。余光中说:“古人旅行虽然备尝舟车辛苦,可是山一程又水一程,不但深入民间,也深入自然。就算是骑马,对髀肉当然要苦些,却也看得比较真切。”
一遍遍的勾勒描摹、一次次的低吟唱浅,诗人将诗情化作文字下酒,纸背也透出乡愁的感伤。酒入肠,泪千行。但是,诗人们依旧背起行囊,选择远方。为什么?也许万里路的行途才是他们的归宿,而故乡是在异乡用尽一生追寻的信仰。
回观当下,现在诗人多做牛毛,呈现所谓的诗歌“欣欣向荣”。可这些诗人,有多少经历过古代诗人这般生活的炼狱和踏破铁鞋之后的深情吟哦?“细雨骑驴入剑门”,让我们背上行囊,出发吧,去寻找远方的诗歌和诗歌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