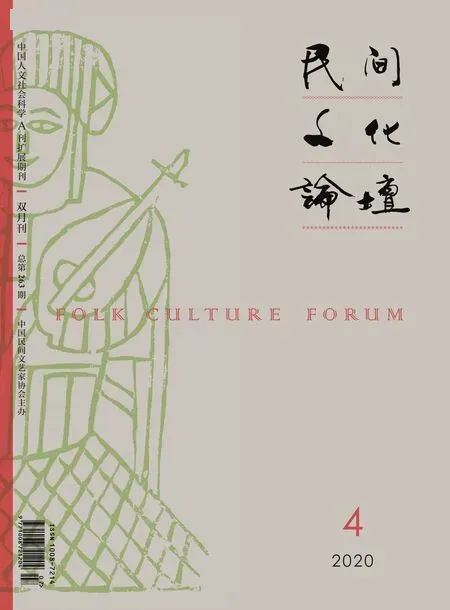日尔蒙斯基《<玛纳斯>研究导论》述评
2020-11-30刘慧颖
刘慧颖
《玛纳斯》学作为一门世界性学科,已有160年的历史。以文艺理论蜚声世界的日尔蒙斯基亦将自己的学术精力投入到中亚民间口头创作研究之中。当前,对于日氏的《玛纳斯》研究探讨暂付阙如。
一、日尔蒙斯基生平及治学历程
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1891—1971)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文艺学家、语言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兼任英国、丹麦、德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同时还担任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欧洲多所知名学府荣誉教授。他出生于耳鼻喉科医生家庭,从少年时期就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在切尼舍夫中学(Т е н и ш е в с к о е у ч и л и щ е)读书期间的文学老师瓦·吉皮乌斯对其产生很大影响。1908 年中学毕业后,日尔蒙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随后转到历史-语文学系日耳曼语言分部。1912年大学毕业后赴德一年,主攻日耳曼语文学。从1913年第一篇《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表到1969年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做序,其学术创作道路前后持续60年。a马晓辉:《日尔蒙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理论及现代应用》,《时代文学》,2013年12期。
日氏的学术研究发轫于日耳曼文学,1924年通过了题为《拜伦与普希金》的博士论文答辩。科研兴趣领域极为广泛的他在随后的几年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研究上,直至1930年代初,再次折回到文艺学研究领域。1935年,他的《比较文艺学和文学影响问题》报告奠定了苏联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基础,亦被他视为自己“学术发展的转折点”。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所决定的文学历史过程统一性的观点。他说:“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在社会历史发展同一阶段上出现的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比较,不管这些现象之间是否有直接影响。”b陆嘉玉:《比较文艺理论家:日尔蒙斯基》,译自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列宁格勒,1979年。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被疏散到塔什干的日氏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搜集民间文学材料,为《<玛纳斯>研究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最初于1948年以油印版形式由前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研究部印刷,后又编入作者《英雄史诗》(1962)、《突厥英雄史诗》(1974)等著作中正式出版。c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不啻如此,借助于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中亚民族史诗成为其战后研究重心,这一阶段他笔耕
不辍,撰写了《阿勒帕米西的传说和勇士故事》(1960)、《奥古兹英雄史诗与<先祖阔尔库特书>》(1962)、《中亚口头史诗》(与N.K.查德维克合著)等。a参见维·马·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6页。著述琳琅的日尔蒙斯基在近乎一个甲子的学术生涯中,涵盖了文艺学、民俗学、诗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四百多篇论著,对苏联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玛纳斯>研究导论》概述
《<玛纳斯>研究导论》由六部分组成:叙事传统、史诗《玛纳斯》的情节、观念与形象、史诗的起源与沿革、塞麦台依与塞依铁克以及作者的结论。
(一)叙事传统
最早对史诗《玛纳斯》有所记载的是出自16世纪赛夫丁·大毛拉之手的《史集》b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而对其内容研究却是在两个世纪之后,由哈萨克族民族志学家乔·瓦里汗诺夫(1835—1865)和俄籍东方学家瓦·拉德洛夫(1837—1918)先后对史诗内容搜集、记录。瓦里汗诺夫在1856年首次对史诗部分片段进行记录,他将这部吉尔吉斯史诗称为《草原上的<伊利亚特>》。他认为:《玛纳斯》——百科全书式地荟萃了吉尔吉斯神话、童话、传说,且同时间聚焦在一个人物身上——勇士玛纳斯,在这部宏篇巨制的史诗中,亦可体察到吉尔吉斯人的生活方式、风俗、地理、宗教和医学知识,以及与近邻民族的关系等。拉德洛夫于1862—1869年间游历西伯利亚、中亚地区时,首次记录下史诗三部曲c在日尔蒙斯基成书之时,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只记录下《玛纳斯》《赛麦台依》和《赛依铁克》史诗三部曲,现在记录有五部;而在中国境内记录史诗有八部,分别是《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铁克》《凯涅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及《奇格台依》。,他认为史诗《玛纳斯》是“吉尔吉斯人民生活全貌和所有愿景的诗意写照”,并指出,这部史诗,如同《荷马史诗》,展现了全民族精神生活和风俗的清晰图景;用宏大的叙事线条勾勒出他的军事远征、结亲、祭奠活动、赛马、日常风习等。
前苏联时期第一位研究《玛纳斯》的哈萨克作家、学者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按照荷马史诗歌手分类方式将玛纳斯奇分为两大范畴:第一类,说唱家(а э д),即“大玛纳斯奇”,吉尔吉斯语中称“交莫克楚”。这些歌手对史诗三部曲了如指掌,能够演唱所有主要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通常这类全能歌手凤毛麟角,且在民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第二类,串编歌唱艺人(р а п с о д),即“小玛纳斯奇”,吉尔吉斯语中称“厄尔奇”。他们仅能够演唱史诗的某些片段,在民间主要扮演着普及史诗的角色。d参见维·马·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演唱的《玛纳斯》也不尽相同,大玛纳斯奇能够在数月期间不重复地演唱。他们按照听众的意愿扩展或压缩内容,有时将内容稍作调整以适应观众品味。因此,一名优秀的玛纳斯奇通常具备这些特点:即兴创编、神灵梦授。
在传统范围内创编和组合自己的唱本展现出歌手的“个性”,而他们之间的“共性”则于演唱的“固定不变的关键诗章”中彰显。因此,叙事歌手技艺的掌握还和师承前贤息息相关。通过研究不同唱本,可知悉在吉尔吉斯境内有两大流派:天山流派和伊塞克湖流派。
天山流派代表人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1867—1930),是著名的阿肯诗人,纳伦州人。与其他歌手不同的是,奥诺兹巴科夫识文断字并且接受过穆斯林教育。青年时期的他作为民间抒情歌手而出名,特别是擅长礼仪哭调。在耳濡目染中学习了许多有名的老一辈玛纳斯奇(巴雷克、特内别克及那依曼拜依等)演唱《玛纳斯》,但究竟哪一位是他的老师,至今不明。1922—1926年间,由伊·阿布德拉赫玛诺夫和卡·密弗塔霍夫两位民间教师先后记录其唱本,然而,由于奥诺兹巴科夫身患重疾,未能演唱后两部,实为当代学术界一件憾事。作为史诗古典演唱流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演唱具有古典式特点:演唱波澜起伏,与听众融为一体。a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世界<玛纳斯>学读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171页。缺陷在于他的演唱中宗教色彩的渲染过于浓重。
伊塞克湖派代表人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1894—1971)出生于伊塞克湖州。由于出身贫寒,目不识丁,他早年参军。随后向自己的同乡伊塞克湖流派著名玛纳斯奇歌手巧尤克·奥姆热夫学习史诗演唱技巧。他口述的超过50万行的三部曲于1935—1947年记录,现存于吉尔吉斯科学院档案馆。他的唱本以其完整性和描绘战争场面的广泛性、生动性而独具特色。b同上,172 页。
两大流派在一些情节处理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依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研究员卡里姆·拉赫玛图林的观点,两位玛纳斯奇演唱的《阿勒曼别特的到来、《玛纳斯娶亲》和《远征别依京》等篇章各有千秋。
(二)史诗《玛纳斯》的情节c 本文对史诗情节及内容分析比较基于乔·瓦里汉诺夫、瓦·拉德洛夫搜集的异文及歌手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和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唱本,共四种版本。
在世界史诗视阈中,古法兰西史诗中关于伟大的查理和他的勇士、俄罗斯基辅系列壮士歌、卡尔梅克人的《江格尔》及突厥-奥古兹人的《先祖阔尔库特书》等口头创作中的统帅(如查理大帝、弗拉基米尔红太阳、江格尔、巴云杜尔汗等)虽是领导者,但一般不参与战斗,集结在其身边的勇士不仅唯其马首是瞻,而且分别是独立叙事传说的主人公。他们只是在形式上依附于叙事君主麾下,且这种从属往往是最新加积的结果。d参见维·马·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33页。纵使像勇士江格尔既是领导者,又是征战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传奇的英雄业绩,也不会遮挡住其他勇士的锋芒,但《玛纳斯》的主要结构特点在于遵循君主作为中心人物的谱系式叙事原则:玛纳斯是集剽悍勇士与传奇领袖于一身,这种统一,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在史诗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而言,作为整部史诗的主干,玛纳斯本人的生平不断从内部充盈饱满;另一方面而言,在共同的生平经历衬托下涵盖了其他勇士的功绩,起初他们是独立叙事传说中的主人公,随后成为玛纳斯的战友或敌人:阔绍依、阔克确、托什图克、楚瓦克、阿勒曼别特、交劳依等。根据拉德洛夫记录的版本,一些重要篇章(如《阔阔托依的祭奠》《玛纳斯娶妻》《阔兹卡曼》、《阿勒曼别特的到来》《伟大的远征》等)至今依旧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而另一些(如《艾尔托什图克》等)存有独立版本,但与《玛纳斯》整体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研究其中的统一性和相对独立性,需要搜集大量不同的演唱文本。e同上。总体而言,史诗的主人公是玛纳斯,故整体情节脉络和结构层次均围绕他展开。大致轮廓由以下四组事件融合而成:1.戎马生涯:生平主题(出生、童年、娶亲、死亡);2.同室操戈:与氏族和附庸的分崩离析;3.觥筹交错:平和生活图景——民间节日和宴会(《阔阔托依的祭奠》等);4.彪炳千古:玛纳斯的远征。
(三) 观念与形象
说唱艺人塑造的玛纳斯形象集身强力壮的勇士特征于一身,这些特征符合“军事民主制”时期英雄英勇豪迈和强壮体魄的典范,亦是早期封建时代的叙事君主最新特征。玛纳斯的形象塑造主要分为以下六类:
兽形类比威猛可畏的勇士a穆塔里甫:《英雄史诗中勇士形象兽形艺术类比的审美观念》,《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拔山举鼎般的超人力量;神奇的无法攻破性;彪悍勇武的喋血英雄;传奇的动物与武器为伴;厉兵秣马的四十勇士。
属于兽形类比玛纳斯形象范畴的是其绰号——“青鬃狼”(kök-jal)玛纳斯。狼是中亚民族史诗和民间创作中广泛流传的图腾动物,而在吉尔吉斯民间诗歌语言中,“青鬃狼”与勇士一词如出一辙。史诗中理想勇士的英勇、大无畏和体力会体现在与凶猛动物的对比上,说唱人将玛纳斯比喻为雄狮、猛虎、猎豹、鬣狗等。经对比可发现,这些名称逐渐演变成英雄的绰号,进而取代他们的本名。
玛纳斯的超人力量通常借助异常夸张手法描述其硕大无朋的体格:鼻子像整个山丘,鼻梁似山岭;他的胡子好比箭筒;小胡子犹如峰顶;方海阔口,眼睑犹如悬崖峭壁一般;他的骨骼是浇注而成的,头似大块黄金,甚至穿的衣服最少时也有一个骆驼的重量;好似他就是天与地之间的巨柱,好似他是由月亮和太阳缔造而成,只有大地才能承受他的重量。
神奇的无法攻破性既是突厥语民族史诗中古老的诗体程式,也是世界史诗中普遍的主题(如《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菲及《列王纪》中的埃斯凡迪亚尔等)。他们无法被攻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灵魂外存,他们的灵魂一般寄存与海底、遥远的岛上或是小匣子等隐蔽的地方。
史诗中,凡能征善战、战功显赫的英雄都嗜血。在初民看来,杀敌—流血—英雄是一个统一的概念。b参见郎樱:《玛纳斯形象的古老文化内涵》,《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用特性形容词“kankor”形容玛纳斯则体现出统治者的强壮与威严,他在多次血战中叱咤风云。苏联东方学家叶·埃·别尔捷利斯(1890—1957)认为该词是对波斯语中土耳其苏丹王封号的重新解读。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骏马是英雄亲密的伙伴和忠心的战友。勇士与战马之间的联系自出生之日起就建立起来了。在奥诺兹巴科夫的唱本中,玛纳斯和他的战马阿克库拉出生在同一天:在玛纳斯出生之时母亲难产,而父亲加克普则帮助黑母马生出浅黄色的小马驹阿克库拉。除了玛纳斯,他的勇士甚至敌人都有自己心爱的坐骑,与其一道参加比赛、远征。战马如同英雄的双翼,敌人会通过袭击坐骑进而击败主人公。失去战马的英雄会变得束手无策。例如,恰逢玛纳斯侦察别依京之际,战马阿克库拉不在场,在过河之时险遭夙敌空吾尔拜袭击。此外,主人除了与战马之间的无比默契的深厚情谊外,还有犬神库马伊克、奔驰迅速的神驼哲码洋和白矛隼阿克舒木卡等忠诚于勇士。所有这些动物在英雄牺牲后为之哭泣、守护其陵墓。之后,他们又将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视为自己的主人。
玛纳斯拥有的武器亦是天下无双:阿奇阿勒巴尔斯神剑、色尔矛枪和阿克凯勒铁神枪。在过去,金属加工工艺尚未普及,这种著名的宝剑被认为是战利品或者祖先遗留。和动物一样,获得英雄的宝剑也被认为是战胜对方的一种体现。通常在歌手演唱中,会对武器本身及其神奇的诞生过程描述,勇士的宝剑出自神奇的能工巧匠之手。在拉德洛夫记录的文本中提及过铁匠焦克尔,他在玛纳斯奔袭交劳依前为其修理好神剑和铠甲;而在奥诺兹巴科夫演唱的文本中被称为“来自埃及的能工巧匠”,他借助神奇的技艺为玛纳斯锻造了宝剑和矛枪。
除了上述各项,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玛纳斯率领着一个传奇的主力部队——为其披肝沥胆的四十位勇士。作为玛纳斯的主要军事力量及其权力的可靠保障,他与四十勇士一道构成战斗集体:同仇敌忾,师直为壮。
据拉德洛夫目击证实,通常认为能列举所有“四十勇士”的姓名是歌手精湛技能的最佳诠释。然而,他们口中传唱的“四十勇士”名单并非一致。但总体而言,与玛纳斯关系最亲密的战友是阿勒曼别特、巴卡依、楚瓦克、色尔哈克、阿吉巴依,亦有藩臣阔绍依、阔克确、托什图克、加木额尔奇,他们每人性格迥异、个性鲜明,各有所长。
(四) 史诗的起源与沿革
关于《玛纳斯》产生年代和背景以及史诗中关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问题是相当繁芜庞杂的。和其他古老民间史诗一样,经过了世世代代歌手反复传唱的《玛纳斯》在创编、演述及流布的演进过程中,新的历史事件、观念和形象会层层加积在旧的故事情节上。数世纪沿袭的宗法部落体系、军事化游牧日常及在人口数量上不占优势的吉尔吉斯人民,凭借着英勇的斗志对威胁其自由、独立甚至是存亡的强邻的顽强抵抗,这就是吉尔吉斯英雄史诗至臻繁荣的社会历史前提。
早期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尔吉斯部落于9—10世纪达到部落联盟国家的鼎盛时期,该时期被历史学家瓦·巴尔托尔德称为“吉尔吉斯帝国时期”;随后是与契丹、回鹘和其他临近部落的长期军事冲突;而吉尔吉斯人与卡勒玛克人斗争的历史背景可能于15世纪初形成,当时在蒙古帝国废墟之上建立了新的卫拉特(卡勒玛克或卡尔梅克)国家,直至18世纪中期,被清政府(1758年)摧毁。这也为史诗的叙事外交定下基调。a维·马·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71页。
这样一来,吉尔吉斯史诗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深层古老的史前时期(6—14世纪),属于浓郁神话幻想色彩为主流的古老形态的勇士故事;第二阶段,旷日持久的漫长战争岁月(15—17世纪),奠定了主要的历史—政治主题—吉尔吉斯人与卡勒玛克人和契丹人的激战以及玛纳斯在这些交战中作为首领的作用;第三阶段,脆弱而模糊的穆斯林化时期(17—19世纪),玛纳斯由超凡卓绝的古老英雄形象力挽狂澜的统治者逐渐演变成中亚穆斯林民众的领袖。b同上,第 90—91 页。
(五) 《赛麦台依》与《赛依铁克》
描述英雄玛纳斯子孙的《赛麦台依》和《赛依铁克》不仅是《玛纳斯》的接续,而且与其一道在情节上构成完整的叙事三部曲。相比于第一部,后两部的情节取材十分有限,更多的是集中在生平主题上。如果说第一部《玛纳斯》反映的是内容广博而高深、古老的超人力量与传奇英雄主义,那么后两部更接近日常生活和现代观念:第一层面首先叙述的是家庭和氏族关系、氏族成员之间的纷争,也出现了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随后才是一些临摹性质的战争场面(特别是赛麦台依征伐空吾尔拜),再现了与古老史诗相似的场景和情节。
尽管后两部与《玛纳斯》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性,但通过谱系联系形成有机的内部连贯机制。从民间创作准则的角度看,叙事情节谱系延续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大众所青睐的英雄悲剧死亡后成了当务之急。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民间创作的乐观主义就在于不会忍受尚未解决的悲剧不协调。狡诈且凶狠的敌人粉墨登场不可能成为终结;在英雄的死亡和敌人弹冠相庆之后,紧接着恢复被践踏的公正和对施暴者的复仇。按照风俗,血仇和恢复人民承认的合法权力是儿子的职责。这就确定了第二部史诗的内容,既是第一部的延续,又是具备完整叙事情节的“第二阶段”。
在《赛麦台依》中新增以下情节:1.玛纳斯家庭被驱逐、赛麦台依的出生和童年、返回塔拉斯;2.与氏族成员、附庸汗王及玛纳斯亲兵的纷争;3.征伐空吾尔拜、志枭逆虏;4.赛麦台依迎娶阿依曲莱克;5.赛麦台依的牺牲。最后一个情节也为第三部《赛依铁克》(为赛麦台依复仇)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赛依铁克》在情节布局上较《赛麦台依》简单:作为史诗三部曲的尾声再现了后代中流击楫、替父报仇的叙事特点。卡拉拉耶夫在演唱《赛依铁克》时纳入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主人公并未死去,只是隐居在遥远的印度阿拉尔魔岛上。
所有这一切迹象,均指明《赛麦台依》和《赛依铁克》是较晚时期形成的(约17—18世纪),它们在内容和风格上更符合大众品味,受到大众追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吉尔吉斯史诗演述人所演唱的剧目中《玛纳斯》逊色于《赛依铁克》。因此,便相应地出现了著名的“赛依铁克奇”,他们仅对《玛纳斯》部分片段略知一二,却十分擅长演唱“卡妮凯逃往布哈拉”和“赛麦台依娶妻”(又称“阿依曲莱克”)等片段。a维·马·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125页。
日尔蒙斯基认为,史诗《玛纳斯》研究刚刚起步,而他这部《<玛纳斯>研究导论》仅仅涉及到叙事三部曲的内容及历史起源等初步问题。不宁唯是,他还对未来《玛纳斯》研究者提出中肯的建议,并希望他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确定这部吉尔吉斯民族史诗的主题和艺术内容;应结合吉尔吉斯民族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及业已形成的民族性格、民间风俗、传统和信仰特点阐释史诗内容及发展过程。
除了对史诗内部进行研究,日尔蒙斯基认为,像其他民间史诗一样,不可忽视且应该更加明确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特殊贡献。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就是有意打破这种壁垒,将吉尔吉斯史诗与其他民族的类似作品(尤其是与吉尔吉斯人有着数百年共同历史命运的中亚人民口头创作)进行系统比较。这种比较并未淡化吉尔吉斯民族史诗的独特性,相反,正是因为在历史和社会典型背景下才更能彰显吉尔吉斯民族的性格特点。鉴于此,我们主要将其归纳为:
一方面,在不同民族的叙事创作中总可以找到关于在观念、形象、母题、情节、结构、风格等方面的相似特点,哪怕是这些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未曾有过直接接触和文化交流。比如,勇士保卫祖国抵抗异族侵略者、英雄的神奇诞生、魁梧的身材、少年的功绩、英雄提亲、尚武姑娘形象、战马的角色、英雄的魔法不可攻破性、英雄决斗等。这种相似最终被解释为是在社会同阶段发展中意识形态现象的相似。此类对比有助于我们揭开史诗观念和形象、母题和情节的历史规律性及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从叶尼塞河畔到阿拉套山麓的迁徙,为史诗反映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情节和形象持续发展与重构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对比瓦里汗诺夫、拉德洛夫、奥诺孜巴科夫和卡拉拉耶夫的记录本(或唱本):玛纳斯的形象经历了一系列持续性转型——从神话故事里的神奇勇士、部落首领、勇士亲兵首领再到力冠群雄的封建统治者和世界征服者;英雄玛纳斯娶亲之旅中降服执拗的新娘,或是武装力量掠夺而来的被父亲按照穆斯林传统携带大量彩礼上门提亲。史诗的形象与情节是多阶段发展的,并且保存在更多古老的连续积层中。研究者的职责就是在吉尔吉斯史诗中揭开这些累积层。通过寻绎和对比不同的唱本,将篇幅浩瀚的史诗分解为若干要素,进而分化出更为古老的部分,勾勒出持续多世纪且复杂的叙事情节形成和发展之过程。
结 语
秉承“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学术观点的日尔蒙斯基具有深厚的比较研究功底。既谙熟西欧史诗又饱学中亚民间创作的他跨越地理藩篱,在《<玛纳斯>研究导话》一书中旁征博引,将《玛纳斯》与中亚乃至世界其他民族史诗进行对比研究,这开辟了中亚民族史诗研究之先河。
当然,此书也有局限之处,其主要表现为:唱本集中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歌手,正如日尔蒙斯基所言,应该拓宽史诗演唱地域,关注中国新疆玛纳斯奇的唱本;另外,他认识到两大流派的创作特点对歌手演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究竟如何形成,因书面记载罕有,故无从知晓;文中还存在一个谬误,就是史诗中描述的契丹都城“别依京”被认为是现在的北京。
虽然存在上述细瑕,但依旧不可泯灭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它为后世从事《玛纳斯》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即依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统一与规律,东方和西方的叙事诗犹如统一文化历史进程的两个分支,在比较视野下,将史诗《玛纳斯》与其他突厥语族民族史诗以及西方史诗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