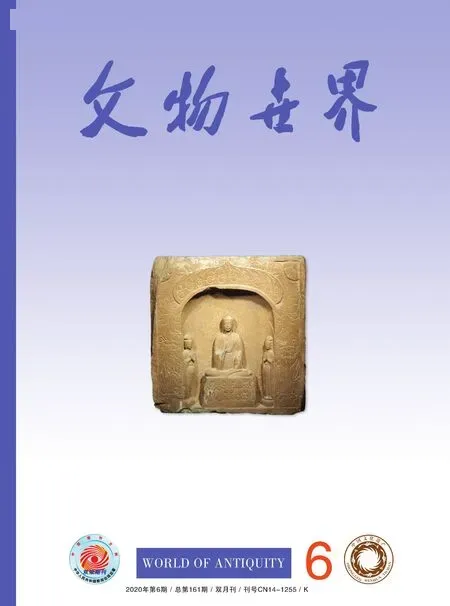三晋文化视域下的古建筑琉璃文化
2020-11-30任昆龙
任昆龙
“三晋”即“三家分晋”的简称。据史书《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三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国合称为三晋。《商君书·徕民》提到:“秦之所以与邻者,三晋也。”北魏王遵业撰写《三晋记》之后,三晋便作为山西地域的雅称而被广泛使用。
一、三晋琉璃文化概述
山西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其地貌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境内东太行、西吕梁、南中条、北恒山、中间汾河沿岸的狭长地带为一个南北大通道,其东西两山的支脉分割形成雁同、忻定、晋中、晋南和上党五大盆地,均为人口集聚之地,经历史积淀,逐渐形成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地在生活方式、典章制度、民风民俗、传统习惯、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独特性和差异性。从文化类别上,可分为根祖文化、晋商文化、佛教文化、边塞文化、上党文化、黄土文化六大文化板块,共同形成内涵极为丰富的三晋文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均有体现,它不但是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而且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既具地理环境形成的自然属性,又有历史传统造就的人文属性,其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博大精深[1]。
中国古代建筑是不同时期社会文明和人的情感对现实地理空间的综合映射,记载着所属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礼制等。古代建筑中的琉璃制品在承担实用功能的同时,更多地承载了远远超出其实用功能之外的附加功能,以有形的外观和无形的内涵彰显着建筑自身的身份,成为民众认同的符号和象征。
琉璃本身具有空灵细腻、含蓄静谧的气质,其造型是琉璃匠人时代审美取向的表达。因此,琉璃不仅是一种材料,更是一种文化。琉璃作为一种建筑装饰材料,随着在屋面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通过长时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表达秩序、宣传礼制和求吉纳福的重要路径。历代营造者和琉璃匠师通过对古建筑屋面装饰审美的继承、诠释和发展,使其告别了青砖灰瓦的沉闷,绽放出耀眼的光彩,煌煌越千年。三晋琉璃作为中国传统琉璃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拥有琉璃发展的共性,也有异于其他区域琉璃发展的特性。凭借琉璃作品多样的形态、绚丽的色彩和变幻的纹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涵,使山西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建筑能在全国范围内独放异彩。
二、三晋琉璃窑址的分布
琉璃用于建筑的史籍记载始于北魏平城宫殿。琉璃作为烘托建筑恢弘、彰显建筑等级的构件,主要使用于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中。鉴于琉璃制品供给宫廷建筑,分布于宫殿营造地周边、作品质地良好、便于运输等是促进琉璃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山西距离元大都和明清国都的京城较近,境内土质、矿产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为山西的琉璃烧造提供了独特的条件。煤炭资源丰富的阳城县、太原市、河津市、介休市等地成为琉璃窑的主要分布区,并涌现出了以阳城乔家、太原马庄苏家、孟家井、河津吕家、介休侯家为代表的琉璃烧造之家。
1.晋南主要的琉璃窑址
2016年发掘的河津固镇遗址,其中老窑头遗址周边山体发现较大规模的瓷土矿。明代时,河津琉璃窑多集中在城西的东、西窑头村,并以东窑头吕家琉璃影响最大。窑头村所在的九龙岗下土质上乘,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是灰陶琉璃烧制的理想场所。
洪洞地区煤矸石含碳量低,是理想的烧陶原料,也成为琉璃产品的主要生产区。
2.晋东南主要的琉璃窑址
阳城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境内群山耸立,沟壑纵横,沁河主流在县东部自北向南贯穿全县。山川如龟蛇缠绕交杂,沁河宛转萦回。沁河水不但滋润了当地的气候,而且由它形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沁河谷,此处矿产资源丰富,制瓷历史悠久,千年来从未间断。
3.晋中主要的琉璃窑址
介休东南的丘陵地区,有丰富的森林煤炭资源和烧制琉璃的原料柑泥。洪山窑址在洪山镇的喊车沟、磁窑沟、龙王沟、琉璃窑村、采皮沟等地均有古窑址发现。琉璃烧造历史甚早,历经金、元、明、清数代,烧瓷历史达千年之久。
上述地区所生产的琉璃制品,是融合各地区社会背景、经济基础、地域风俗和文化底蕴的产物,是三晋文化在琉璃烧造业的综合体现。
三、三晋琉璃技术的传播
伴随营造活动急剧增长,单纯依靠运送琉璃制品已难以满足营造所需。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朝廷申令把山西朱氏窑户的长支迁至曲阜城西,设窑场烧制黄色琉璃瓦,以供曲阜孔庙扩建之需,琉璃瓦制作技艺开始在曲阜传布,拉开了三晋琉璃传播的帷幕。
1.元朝琉璃技术的传播
元统治阶级定都北京后,大兴土木,引山西成熟琉璃技术入北京成为必然。山西榆次善制釉陶砖瓦的赵氏家族被诏入京,专为北京宫殿、庙宇、园林烧造琉璃建筑构件,长期承担符合皇家规范的建筑琉璃构件和琉璃装饰品,并将其造型和尺寸标准化、定型化,历经元、明、清三朝兴盛不衰,被匠师奉为标准样式,故被称为“官式琉璃”[2]。
2.明代琉璃技术的传播
太原马庄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已生产琉璃,有苏、白、张三大家族,影响最大的是以苏氏家族,太原周边建筑所用的琉璃大都出自这里。苏姓早年从洪洞大槐树移居到了苏家湾,之后来到马庄村,不久又去代县吴家窑、北京等地。
明代时,河津地区的琉璃制品具有质地优良、工艺精湛、造型奇异、色彩绚丽等特点,特别是孔雀蓝釉色为独家首创。故宫屋顶的琉璃许多出自河津工匠之手。
明代时的介休,形成了以侯、王、秦、乔氏为主的琉璃家族,其中侯姓家族侯安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移居辽东海州析木镇缸窑岭安居,并将祖传的烧制琉璃技术带到本地。直至清朝初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所建宫殿和陵寝建筑所用均由侯家烧造,并借此更其窑名为皇瓦窑。侯氏家族的琉璃制品在继承中原地区传统烧造技术的基础上,为迎合满族统治阶级的审美,将满族的装饰理念融入其中,黄琉璃瓦绿剪边、螭凤琉璃正吻、琉璃宝顶、五彩琉璃墀头等都具有典型的满族特征,是三晋琉璃匠人对琉璃作品文化的发展。至清乾隆时期,满族统治阶级已完全汉化,建筑中的琉璃装饰在尊重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与关内同时期同类建筑琉璃相比已基本趋同[3]。
明中叶以后,北京琉璃工匠中的山西籍匠人很多,北京琉璃制造工艺深受山西琉璃技术的影响,形成了山西系琉璃的官式做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山西琉璃作品无论工匠技艺,还是产品形态都呈现出不断创新和发展之态势,客观上扩大了三晋文化的影响。
3.清代琉璃技术的传播
清兵入关之后,大兴土木,内务府造办处下设专司琉璃砖瓦烧造的“琉璃厂”,琉璃制品的应用和普及范围呈现多层次、多元化格局,开创了官造与民造齐步发展的鼎盛时代。山西琉璃文化吸收了山西地域文化元素,中国建筑琉璃的发展注入了三晋文化的血脉,实现与中国传统核心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文明贡献了精彩篇章。
四、三晋琉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是自汉以后各王朝宫殿建筑的定位。帝王因佛生威,神之居所庙宇地位借此被抬高,建筑等级直逼天宇,终使琉璃这种民间可望不可及的重器用于宗教建筑中,合乎“天地君亲师”的等级构想,与儒家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琉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颜色、造型和数量三个方面。
1.三晋传统文化在琉璃色彩上的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上琉璃色彩的使用,受封建礼制的影响。五行色彩体系是在五行说指导下形成的,其中金、木、水、火、土对应的色彩分别是白、青、黑、赤、黄,据此,琉璃瓦色彩等级以黄色、绿色、黑色、其他色为序,是等级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黄色为五色之首,自古为居中的正统颜色,因此故宫、皇家道场、后土圣母等至高无上建筑均采用黄色琉璃装饰。
2.三晋传统文化在琉璃造型上的体现
在造型上,《大清会典》载:“康熙二十年议准,琉璃砖瓦、兽件大小不等,一共分为十样。”每种都严格按规格样式制作,并规定了具体的烧造日期和备办程序。清《钦定工部续增则例》对各个部分的琉璃瓦件在选料、制泥、烧制和釉料的配制等方面做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3.三晋传统文化在琉璃数量上的体现
在数量上,宋《营造法式》详细记载了建筑装饰构件的规格制度、应用范围及其对应的功限、料例,对鸱尾、兽头、嫔伽、蹲兽和火珠等构件的造型、大小、奇偶、数目都有严格规定。屋面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的排列有严格规定,其数量根据建筑规模和等级而定,多为一、三、五、九等奇数,数目越多,级别越高。
三晋琉璃构件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大的历史背景下,其创作遵循封建礼制的要求,并形成了对琉璃构件的普遍认知,且代代相传,琉璃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装饰材料,而是体现“天地君亲师”的等级的象征,被赋予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建筑文化以及封建礼制的文化内涵,承载了不同时代的宗教、风俗等人文思想以及传统文化内涵。
五、三晋琉璃的创新
山西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根脉,使三晋文化具有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博大胸襟。琉璃文化作为三晋文化的一个分支,在琉璃造型、色彩及使用范围上不断创新,并在创新领域为后人留下了独具价值的琉璃作品。
1.三晋琉璃在造型上的创新
晋城玉皇庙是古代泽州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道教庙宇,宋熙宁九年(1076年)创建,金泰和七年(1207年)重修。其营造顺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琉璃构件烙上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烙印。出自元朝艺术家刘銮之手的二十八宿像泥塑,是古代造像遗产中的孤品。难能可贵的是,金代“琉璃匠元庆社李道真”将这二十八星宿对应成神仙与动物,制作成了胎体,附上色釉入窑口烧造,是三晋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孤例,实现了琉璃构件与道观文化内涵上的良好契合,是琉璃构件造型的创新。
2.三晋琉璃在色泽上的创新
永乐宫营造工程始于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中统三年(1262年)建成,主殿三清殿两尊琉璃鸱吻高达2.8 米,五品合成,“红泥作胎,施孔雀蓝釉。整体为一条巨龙曲折盘绕而成……”。元代以前,古建筑中并没有以龙造型作为主体的大型鸱吻,三清殿龙型琉璃造型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属初创,为明清两朝多种样式的龙形鸱吻开创了先河。纯阳殿、重阳殿的大吻高度在1.9~2.1 米之间,吻的尾部略向外卷,尾后插簪花一枚,是明清卷尾吻的先声。永乐宫这座完整的元代建筑群,其主体建筑以琉璃成就着元代建筑的恢弘[4]。
琉璃瑰丽的外表源于传奇色彩,琉璃烧造的核心技术是配制釉彩,其中孔雀蓝釉因釉彩配方复杂、制作难度大被视为“绝技”。河津吕氏祖传的孔雀蓝琉璃烧造绝品技术,是琉璃色彩领域的创新,在琉璃艺术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六、三晋琉璃中传统文化的体现
三晋琉璃是山西不同历史背景下,源于地域范围内民众主观能动性而创造的装饰产品。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心灵手巧的山西古代匠人,以自然资源为依托,形成了三晋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琉璃制造圈,一方面受社会发展、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人文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地域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琉璃的通透和富有表现力的具象性已超越了材质所容纳的范畴,体现了三晋地域文化背景下所属时代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信仰以及审美,是三晋文化的载体。
1.宗教文化内涵
佛教经典将“形神如琉璃”视为佛家修养的最高境界。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载:“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莲花和忍冬纹是佛教装饰艺术中最常见的纹样,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至清至纯而被象征修成正果;忍冬为蔓生植物,越冬而不死而被视作灵魂不灭、轮回永生。佛教中的佛、菩萨、金刚、罗汉、嫔伽、仙人、力士、化生童子等均为琉璃常见的装饰题材。迅速发展的佛教与方兴未艾的琉璃装饰相结合,琉璃建筑构件大量用于佛寺建筑中[5]。
广胜寺飞虹塔为明正德至嘉靖年间(1506-1566年)的作品,塔身采用蓝、黄、绿、褐、白、赭、黑等色琉璃装饰,每层饰以不同的琉璃饰件,第一、二、三层的琉璃饰件更精美。既有菩萨、金刚、诸天、明王等佛教内容,又有盘龙、祥云、宝相、流苏、芙蓉、牡丹传统祥花瑞草,为洪洞县公孙村乔氏的琉璃作品,是佛教艺术与传统民俗相融合的艺术精品。
阳城海会寺如来塔为明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六年(1565-1572年)的遗构。塔第十层外置的平座栏杆为琉璃;第十层楼阁束腰部镶嵌琉璃浮雕。阳城阳陵村寿圣寺琉璃塔,塔刹及各层斗檐全为琉璃,每层角棱上隐出琉璃倚柱,塔壁镶嵌佛与菩萨等佛教人物琉璃浮雕。这两尊塔均体现了佛教装饰内容与佛教文化内涵的高度融合。
2.吉祥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下,古建筑屋面琉璃的仙人走兽在发挥“明贵贱、辨等级”作用的同时,也赋予了吉祥、驱邪等寓意。
龙是中国人崇拜的吉祥物,是神武和力量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尊贵、华丽和威武,是民族的守护神,得到了民众始终如一的叩拜和尊崇,其形象演变的历史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价值观和审美意识。龙在建筑琉璃中以吻兽、照壁为主要载体,屋面脊饰以龙及其龙子为雕塑。
大同琉璃龙壁从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到九龙壁均有,是自然地理环境、军事及经济条件以及宗教文化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龙壁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壁,面积大,拼图工艺复杂,制作难度高,显示了北方特有的粗犷和壮观气势。特别是代王府的琉璃九龙壁,集建筑、浮雕、图案、琉璃等艺术于一体,其规格、材料的选用以及制作技术代表了明代琉璃龙壁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琉璃烧造艺术的完美结合。城隍庙作为护佑一方民众的庙宇,是人们企盼幸福、向往美好生活的吉祥地。民间的琉璃烧造工匠,将对城隍的传统认识、地方特色融入其中。脊饰中雕饰的莲花为道教八仙的法器之一,在脊刹上方放置宝葫芦或宝瓶,在下方承以狮子或大象,寓意“太平有象”的祥瑞,体现了人们祈求镇邪和纳福的美好愿望。
3.民俗文化内涵
琉璃装饰题材中的民俗文化,是普通百姓生活的直接反映。民俗文化中的龙凤呈祥、二龙戏珠、龙穿牡丹、麒麟送子在琉璃构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建筑正脊的宝葫芦与宝珠琉璃构件表达了升官晋级的民俗文化内涵,仙鹤与梅花鹿表达了长寿、福禄的意愿,身负宝瓶的大象则用以象征太平景象,是对国泰民安、海清河晏美好生活的期盼。
七、结 语
三晋古建筑琉璃历史久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建筑琉璃文化的精髓,在遍布全省各地以及由山西籍琉璃匠师烧造的省域外建筑背后,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互动,也有对外域文化的吸纳和创新。山西建筑琉璃的发展,不但体现了琉璃文化的交流和科技艺术的融合互鉴、交汇碰撞,而且体现了山西匠人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三晋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注释
[1]王志华、王晓枫《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 期。
[2]柴泽俊编著《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2012年5月。
[3]徐超英《北京故宫藏明代山西琉璃初探》,《历史档案》2009年第3 期。
[4]王伟《论山西古建筑中的琉璃装饰》,山西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5]薛冰琳、袁琳《浅议闽台文庙建筑的脊饰艺术》,《建筑与文化》2018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