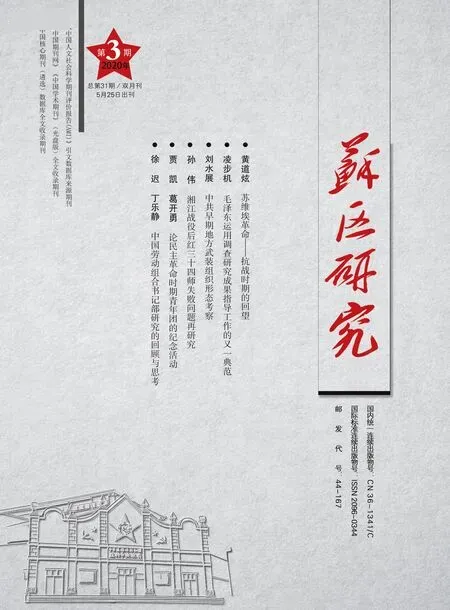论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的纪念活动
2020-11-30葛开勇
贾 凯 葛开勇
提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它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也几经调整。青年团举行的纪念活动,主要包括举行纪念集会、刊发纪念文章、发表纪念宣言、提出纪念口号、创作纪念诗歌等形式。这些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有重合之处,而对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国际青年日、死难青年战士的纪念则是青年团特有的纪念类型。青年团举行的纪念活动起到了强化历史记忆、宣传政治主张、发展组织力量、协调派别关系等政治功能。综观青年团的纪念活动,可以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面相。
人物、事件和节日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人物、事件和节日的纪念活动具有再现、操练历史过程的效果,进而展现丰富的历史细节。因此,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关于其过程、细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纪念活动研究无疑是一种新视角。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1)相关研究大体起步于2009年,主要成果有胡国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童小彪:《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以党报党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陈金龙:《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陈金龙:《毛泽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抗战纪念》,《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郭辉:《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展的运动,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无疑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以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的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期丰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一、青年团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
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是全面抗战时期,青年团被改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年组织;四是从1946年至新中国成立,这是青年团的重建时期。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它的纪念活动的演进。
(一)从创立到大革命时期青年团纪念活动的初步探索
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2)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党、团活动很难完全分开,这也体现在纪念活动方面。根据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和《中国青年》来看,青年团纪念的人物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孙中山、死难青年战士等,纪念的节日包括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日、国际青年日、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纪念事件包括二七惨案、三一八北京惨案、五卅惨案等诸多惨案。显然,青年团的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多有重合之处。为纠正这一趋向,中国共产党要求,“S.Y.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可由S.Y.专任之”。(3)《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按照这一要求,青年团的活动要倾斜于文化、教育性质——争取青年工农群众,而不是政治性质。青年团对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国际青年日、死难青年战士的纪念,体现的便是这一点。1927年1月青年团发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列宁纪念周告青年》,更以大篇幅文字介绍青年团是“代表中国青年工人和一切被压迫青年的利益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同时亦就是中国青年学习列宁主义的唯一的实际教育机关”(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列宁征集周告青年》,《中国青年》第150期(1927年1月15日),第643页。。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团纪念活动的走向成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阶段。192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做工农运动,团做学生运动”“党是政治的,团是文化的”现象,认为青年团的主要任务“乃是引进并领导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整个的革命斗争,在整个的革命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必须要有合乎青年情绪,合乎青年迫切要求的工作方法与内容”。(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十七号(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党团两中央联席会议对于C.Y.工作决议)》,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82页。而纪念活动是青年团争取青年群众的重要方式。青年团中央当时发布的《为纪念上海暴动告劳动青年群众》《为“五三”惨案周年纪念宣言》《“五一”“五五”纪念宣传大纲》《广州暴动第二周年纪念——反对军阀战争》,很明显体现出这种意图。中东路事件之后,宣传“武装保卫苏联”成为青年团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1932年五一纪念之际,青年团中央要求各地方团积极发动反帝国主义战争运动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要求各省将“武装保卫苏联”活动与四一二纪念活动联合起来。(6)《中央紧急通知》,《列宁青年》第5卷第3期(1932年5月10日),第6—11页。总之,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的纪念活动呈现出青年化、政治性特点,起到了争取青年群众、宣传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作用。但是党员、团员年龄相差不大的客观情况,使得党、团的纪念活动很难截然分开。
(三)全面抗战时期青年团纪念活动的战略转向
1935年9月,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大会指出:“迫切要求把青年人联合到真正群众性的非党的青年组织中去,不仅吸收共产主义的,而且吸收社会主义的以及无党派的、民族革命的、和平主义的、信奉宗教等的青年人加入组织。”(7)《关于青年统一战线任务的决议(节录)》,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页。这实际指出了青年团群众化、非党化的改造原则。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8)《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41页。青年团改造工作随之开始,新组建的西北青年联合救国会暂时作为各地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导组织。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青年运动。(9)《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3页。“青委”领导下的青年救国会组织,是抗战时期影响最大的革命青年团体。其纪念活动主要围绕巩固青年抗战统一战线开展,“嵌入了抗战动员的内容”(10)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第75页。。这一时期诞生的五四青年节,成为各青年抗日团体联合、团结的重要节日。1939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中,中央青委指示:“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参战运动周。”(11)《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69—470页。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也离不开抗战议题。1941年的国际青年日,除开展各项纪念活动之外,格外重视“分区的检阅青抗先,加强青抗先的工作,动员青年参加军队和扩大青年的武装组织”(12)《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纪念国际青年节的通知》(1941年8月1日),《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73页。。总之,抗战统一战线是当时纪念活动的中心议题。
(四)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团重建过程中纪念活动的延续
抗战后期,青救会等青年组织的吸引力已不甚理想,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重建青年团问题。1946年9月,《在陕甘宁试办青年团的计划》发布后,延安、绥德、米脂开始试点建团。(13)孟学文主编:《中国共青团大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同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提出成立更加青年化、群众化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14)《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634页。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随之开始重建共青团。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青年团的正式重建。试点重建后的青年团,彻底消除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党”倾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相关纪念活动也主要是贯彻党的政策、意志。青年团一方面通过纪念活动开辟了以学生运动为主的第二条战线,另一方面通过纪念活动争取、团结了广大进步青年。如华北学生为纪念七五惨案举行大示威大游行运动,晋绥地区为纪念刘胡兰而开展纪念活动(15)李株:《英雄赞——刘胡兰英勇牺牲二周年祭》,《晋绥日报》1948年12月17日,第4版。;1949年华东学生联合会为纪念五四筹备各项活动。总之,青年团以五四纪念、七七纪念等活动为契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生活的摧残,为党和军队输送了有生力量。
二、青年团纪念活动的丰富形式
青年团纪念活动的开展,依托于丰富多样的纪念形式,主要包括举行纪念集会、刊发纪念文章、发表纪念宣言、提出纪念口号、创作纪念诗歌等。青年团举行各类纪念活动之前,一般都要制定宣传大纲、计划,事后还要撰写活动总结。即使在深受“立三主义”影响、青年团组织几乎取消的情况下,纪念活动也并未中断。如1934年陕北的青年团组织在筹划五卅纪念时,计划召集群众大会、制定两个传单和一个宣言、开展支部纪念、举行纪念周、发展团员、组织抗款斗争等。(16)《共青团陕北代表关于恢复团组织情况的报告》(1934年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一)举行纪念集会
纪念集会由于参与者众多、声势浩大、感染性强等因素,是政治动员力度强、传播范围广的重要纪念方式。青年团举行的纪念集会包括纪念大会、罢工、示威、游行、体育运动会、革命竞赛、文艺晚会、追悼会等形式。1933年共青团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六周年、苏区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筹备的活动十分隆重:纪念会场张贴“完成并超过中革军委扩大红军计划”“拥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保卫与扩大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等标语;要求全体团员参加大会时,“拿着棍,带着领带去参加纪念大会,并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组织示威大会、提灯庆祝大会;在纪念大会之前召开儿童团晚会等文娱活动。(17)《中央儿童局给各省、县、区儿童局信——怎样来纪念今年的十月革命节》(1933年10月5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青年团体组织的纪念活动规模更大。1941年的七七抗战纪念活动中,“各界特于下午五点在文化沟体育场举行盛大纪念会……各机关、学校、部队、群众万余人排队到场,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亦整队参加”(18)《延安各界万人集会纪念抗战四周年 打倒日德意法西斯强盗保卫中国保卫苏联!》,《解放日报》1941年7月8日,第2版。。与纪念大会相比,检阅、晚会、运动会等纪念活动则相对活泼。1930年,青年团中央要求开展童子团大检阅,以此作为五卅纪念的预演。上海童子团为保障检阅活动顺利进行,通过童工大会、标语、传单、画报、歌曲等形式扩大宣传,充实童子团生活,健全童子团组织。(19)季冰:《动员中的上海童子团大检阅》,《列宁青年》第2卷第13期(1930年5月25日),第41—44页。1942年为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延安市俱乐部协会、青年俱乐部、延安舞联会等青年组织于7月2—6日举行各种晚会,深受延安各青年团体的喜爱。(20)《本市热烈筹备纪念“七七”》,《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第2版。
(二)刊发纪念文章
以出版纪念特刊形式刊发纪念文章,是青年团开展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由于纪念专刊往往是一组纪念文章刊发,因此社会影响力大,也是运用最广泛的纪念形式。青年团创建之初的机关刊物《先驱》创刊两年时间内,出版了7期纪念特刊,分别是“里布克奈西特纪念号”“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五一纪念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国际少年日纪念号”“苏维埃俄罗斯五周年纪念号”“少年国际大会号”。另一份团刊《中国青年》也出版过“列宁特号”“九七特刊”“苏俄革命纪念特刊”“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周特刊”“国际妇女与巴黎公社特刊”“哀悼孙中山先生特刊”“国际青年纪念日与九七国耻纪念日特刊”“中国青年五月特号”“十月革命号”等纪念特刊。继《中国青年》之后于1928年创刊的《列宁青年》也有多期纪念特刊出版。
与纪念特刊对于重要人物、事件的纪念相比,分散性刊发的纪念文章灵活性、时效性更强。恽代英、任弼时、邓中夏等时任青年团领导人都撰写过纪念文章。如恽代英撰写的《悼廖仲恺先生》《苏俄与世界革命》《妇女运动》《孙中山逝世与中国》,任弼时撰写的《李卜克内西》《列宁与十月革命》,邓中夏撰写的《少共国际运动与中国少年运动》《同志黄仁之死》等。分散性刊发的纪念文章往往篇幅较短、语言简洁,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青年》《列宁青年》所载纪念文章已十分可观,而各地方团所刊发的纪念文章数量则难以计数。
(三)发表纪念宣言
宣传工作对于青年团具有重要意义。1933年7月《列宁青年》所载《论团内的宣传工作》强调:宣传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第一生命,没有灵活充分的宣传工作,我们的政治影响是不能融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的。(21)笑蠡:《论团内的宣传工作》,《列宁青年》第2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第18页。这段论述可谓对青年团宣传工作重要性的精辟概述,其中篇幅适中、主张凝练的纪念宣言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影响。如1923年发布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案宣言》、1926年发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国际青年纪念日宣言》、1927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共青团“五卅”二周年宣言》《中国共产青年团为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宣言》、1928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为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宣言》、1929年发布的《中国共产青年团“八一”宣言》、1930年发布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为“四一二”流血纪念宣言》等。由于青年团发布宣言的频率很高,几乎涵盖民主革命时期各大纪念活动,对于青年政治动员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以1934年三一一惨案宣言为例,青年团中央于惨案发生当天便发布宣言,揭露“帝国主义最残忍的手段实施于美亚四千余工友的头上”,号召“全国劳苦青年们罢工罢课援助美亚工友对法帝国主义,组织援助美亚工友后援会,进行募捐的运动,援助罢工工友及死难工友的家族。要求惩办凶手,抚恤伤亡的工友”。(2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援助美亚十个厂罢工及“三一一”惨案宣言》(1934年3月12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2册,第495—496页。从中能够看出,惨案宣言既有新闻报导职能,又深具政治动员功效。
(四)提出纪念口号
发表纪念宣言的同时,青年团一般还会提出纪念口号。由于简短、易传播、鼓动性强等特点,纪念口号影响更广、更深。青年团提出的纪念口号具有诸多特点。一是强调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国际性,如1930年5月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五一节宣言》,提出“参加五一大示威!”“全世界无产阶级青年联合起来!共产青年团万岁!”(23)《中国共产青年团五一节宣言》,《列宁青年》第2卷第12期(1930年5月1日),第2—3页。等口号,很好地体现了国际主义色彩。二是贴合青年群众生活。如第四次反“围剿”时青年团中央针对白区青年提出的纪念口号“伤残青年士兵要双饷!要津贴!退伍青年要救济费!伤亡青年士兵家属要抚恤金!”(24)《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号召白军青年士兵反对四次“围剿”的口号大纲》(1932年7月22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就是以改善青年士兵生活为切入点。三是口号注重通俗易懂。如1935年青年团中央提出的八一节纪念口号:“抗捐、抗债、抗租,抢米分粮吃大户!不分大人小孩一律向政府要救济!作苦工要工资!不给日蒋修公路、铁路、飞机场!参加反日反蒋的游击战争!”(25)《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纪念“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四是有些口号富有地方特色。如广东饶平县于1931年8月2日提出的纪念口号:“为彭(湃)、颜(昌)、杨(殷)、邢(士员)四革命领袖复仇!”“为‘九七’、‘九五’死难烈士复仇!”(26)《“八卅”、“九五”、“九七”纪念标语口号》(1931年8月2日),中共饶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饶和埔诏苏区史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总之,青年团提出的纪念口号宣传、鼓动效果很好,甚至成为苏区青年的口头禅。(27)《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肖邮华主编:《井冈山革命斗争史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五)创作纪念诗歌
由于篇幅、韵律等特点,纪念诗歌与纪念宣言、纪念口号类似,都能起到悼念死难战士、激发青年抗争精神的作用。青年团领导创作的纪念诗歌,深植于中国青年的生活实践,使其文本纪念活动形式更加丰富。如1925年9月14日《中国青年》所载《悼战士》诗歌,控诉了帝国主义国家对牺牲者所犯罪行,鼓舞着青年为民族独立与自由奋战。具体如下:
啊!啊!英武伟大的牺牲者啊!
你们为了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
与那凶横残暴的英日等帝国主义,
在前线上拿着鲜热的赤血与他们肉搏,
至于丧失了你们底性命!
啊!啊!!壮烈光荣死的啊!
你们流的沸腾之赤血,
已经重复灌入到我们个个同胞的血管里;
你们那反抗的、英武的、奋不顾身的精神,
已经传导到我们个个同胞的神经里。
“独立”“自由”之血旗,已经遍悬于全国中了,
上海、青岛、汉口的前锋战士,
已经继你们而起,
继你们而与那凶横残暴的帝国主义肉搏死斗了!
战啊!!战啊!!
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战啊!!!(28)《悼战士》,《中国青年》第95期(1925年9月14日),第679—680页。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组织创作的纪念诗歌可谓不胜枚举。以典型的“红五月”纪念活动为例,青年团创作的纪念诗歌以不同形式表达着反帝反封建思想,不断强化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青年的记忆。如《吊五卅以来殉难诸烈士》《血祭》《哀思》《悼五卅烈士》《沪案新乐府》《悼战士》等。
三、青年团纪念活动的特有类型
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开展的纪念活动,主要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四个方面。既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国际视野,又反映着中国革命的本土特色;既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般性的反映,也有对青年运动特殊性的侧重。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团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有诸多重合之处,而对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国际青年日,以及死难青年战士的纪念,则是青年团纪念活动的特有类型。
(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先驱。1919年1月15日,他们在领导柏林工人起义过程中被捕牺牲。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几乎每年都会纪念他们。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即为“里布克奈西特纪念号”,强调纪念意义:“我们纪念他们是纪念他们不挠不屈的独立的人格、实行的意志和革命的精神。我们纪念他们的是因为他们和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努力,使马克斯主义得庆更生,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重新得着他们的运动的好指导。”(29)本社同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里布克奈西和卢森堡?》,《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第6版。1923年1月15日,《先驱》再次出版纪念专刊,所载文章有《卢森堡和中国女子》《去年的今日和今年的今日》《去年的特刊和今年的特刊》,还有山川菊容著、施存统翻译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1925年之后,青年团对于李、卢的纪念最终以纪念周的形式固定下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团对于李、卢的纪念更加成熟,注重宣传他们的伟大事迹、分析世界和中国形势、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三个方面。其中1929年1月15日发布的《中国C.Y.中央李列纪念周宣言》很有代表性。首先,介绍二人的伟大事迹:“李卜克内西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战士,他是领导青年运动,创造少年国际的始祖。在帝国主义大战一开始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就曾经领导过成千成万的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所有的革命分子要将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阶级战争。他曾经领导过英勇的斯巴达卡斯团进行壮烈的武装暴动,反对资产阶级。李卜克内西同志就是这样光荣的在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民主党尖枪利刃之下牺牲了!和李卜克内西同志死难的还有卢森堡同志,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女战士,她也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始终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其次,重点分析世界和中国局势,指出“各帝国主义相互间为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必不可免的要爆发第二次大战”,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已经给与我们工农群众以最可怕的反动统治,他们又在积极制造那更可怕的军阀混战”。最后,强调:“我们要继续列宁和李卜克内西的工作和精神,始终不渝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阀混战,并且要高高举起列宁、李卜克内西的旗帜,做我们前进的明灯。”(30)《中国C.Y.中央李列纪念周宣言》,《列宁青年》第1卷第8、9期(1929年1月15日),第1—6页。不难看出,纪念宣言体现了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辩证统一。这并非个例,如1930年的纪念宣言同样在最后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反对军阀混战,武装保护苏联及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31)《中国共产青年团为李列纪念周宣言》(1930年1月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7册,内部发行,1959年版,第38页。等口号。
青年团对李、卢的纪念,形式十分丰富,并不局限于文本纪念。1930年1月2日,青年团中央指示各地充分调动青年参与罢工、罢课、罢操、飞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开展反军国主义斗争和兵士运动,吸收新团员,加强团的力量。(3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五字第七十六号》(1930年1月2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7册,第13—16页。为开展好1931年的李、卢纪念活动,青年团中央早在前一年的12月25日发出《共青团中央关于李列纪念周宣传大纲》,要求围绕年关斗争、冬季冲锋季开展,此后要求“坚决的在反李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精神之下,执行实际工作中的彻底转变”(3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四号——为年关斗争,列李卢纪念,“二七“纪念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内部发行,1961年版,第7页。。各地方团也积极贯彻相关指示,团福建省委指示下级团部,称纪念活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巩固]闽西苏维埃红军的胜利”(34)《团福建省委通告(第四号)——纪念“李列”,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1931年1月),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组织文件(1928—1931)》,中央档案馆1985年印刷,第217页。。抗战时期李、卢纪念活动频率有所降低,但没有中断。如1940年1月15日,《中国青年》刊发《纪念卢森堡》一文;陕甘宁边区青年组织发起纪念大会,号召“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全民反对帝国主义征服者拯救祖国的斗争”(35)《关于青年统一战线任务的决议(节录)》,《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08页。。
总而言之,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对于李、卢纪念活动十分重视。而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的李、卢纪念活动则较少:大革命时期《新青年》《向导》未专门刊载纪念李、卢的文章;抗战时期对于李、卢的文本纪念也较少,仅有《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德国人民解放的道路——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文章零星出现。(36)《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群众》第4卷第2、3合期(1940年1月30日),第38—40页;《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群众》第8卷第1、2合期(1943年1月16日),第4页;茹纯:《德国人民解放的道路——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群众》第9卷第2期(1944年1月25日),第95—100页。
(二)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
1915年,国际青年大会将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国际青年日,作为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重要节日。青年团创立之初,便对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十分重视。1922年8月2日,青年团中央指示各地方团:“一律在其可能形势之下举行一种大的集会或大的示威运动,一以唤醒国内劳苦少年,二以响应国外革命少年。”(3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十四号——国际少年日运动》(1922年8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内部发行,1957年版,第168页。《先驱》还组织出版了“国际少年日纪念号”,配合相关示威活动。此后,国际青年纪念日逐渐成为青年团的固定纪念活动,即便是抗战时期也未中断,只是由于五四作为中国青年节的确立,其相关纪念活动被五四青年节替代。
国际青年日不仅仅是纪念日,更有其现实价值。1924年《中国青年》出版的“九七特刊”,一再提醒中国青年勿忘国耻,团结起来共同斗争。(38)林根:《“九七”纪念》,《中国青年》第43期(1924年9月6日),第1—2页。此后,国际青年日的“双重纪念”色彩愈发浓厚。1925年《中国青年》出版“国际青年纪念日与九七国耻纪念日特刊”;发布《为国际日告全国被压迫青年》《国际青年日历史及在中国的意义》,向中国青年发出纪念号召。(39)《为国际日告全国被压迫青年》,《中国青年》第93、94合期(1925年9月7日),第639—642页。1929年《列宁青年》所载《我们的国际青年日》明确指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念日,他是表示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旗帜与口号的忠诚。这一日是表示我们为着解放无产阶级,为着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者被榨取大众,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而始终如一的继续斗争,而且是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日。”(40)文彬:《我们的国际青年日》,《列宁青年》第1卷第22期(1929年8月25日),第13—14页。从中不难看出,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的现实动员色彩愈发浓厚。
青年团制定的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对于具体活动开展的指导可谓事无巨细,也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如1928年上海青年无产阶级在青年团领导下开展的国际青年日活动十分隆重,包括青年团代表发表演讲、成千上万青年群众参加、在上海各重要工业区普遍举行的飞行集会;当天举行的十分钟总同盟罢工、怠工;各区、各工厂劳动童子团举行检阅仪式;工会举办群众大会、青年工人大会;标语、传单、画报、歌曲等宣传品在各工业区散布,及在墙壁、机器上普遍张贴;举行青年工人示威运动,伴随着传单高飞、口号狂呼;青年工人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总要求;十七条革命口号的提出和宣传。其实际效果非常显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豪绅地主被国际青年节的纪念运动“震骇得发抖”,青年工人阶级认清了敌友和出路。(41)振鹏:《国际青年日的上海青年工人》,《列宁青年》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22日),第32—39页。
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不仅体现了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还反映着青年团整合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统战意图。如1926年青年团中央的国际青年日纪念大纲将“这一日中国青年的责任及要求”明确分为五类:“国际的”——全世界革命的青年联合起来,“本国的”——被压迫各阶级青年群众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学生的”——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青年工人的”——改善青年工人待遇,“青年农民的”——改善青年农民生活和普及教育。(42)曾延:《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中国青年》第131、132合期(1926年8月31日),第155—156页。
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还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如1929年的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包括三个层次:第一部分是宣传国际青年日的纪念初衷——“国际青年日是全世界革命青年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反世界大战的纪念日”;第二部分则阐述纪念国际青年日的当前任务,包括“应加紧青年反对世界大战的危险”“应加紧保护苏维埃的工作及苏联与青年的关系”“应加紧鼓动一般青年的经济斗争和争自由斗争,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第三部分是指出青年如何纪念国际青年日——“要号召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庆祝少年共产国际十年来的奋斗历史”。(43)《今年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1929年8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6册,内部发行,1958年版,第109—114页。
(三)纪念死难青年战士
纪念中国革命死难战士是纪念活动的重要类型,但党、团纪念的重点不同:党侧重孙中山、廖仲恺、李大钊等对中国革命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偶尔涉及基层战士;团对于死难青年战士纪念的频率高、规模大。(44)主要依据团刊《先驱》《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党刊《向导》《新青年》,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19册)判断分析。青年团对于死难青年战士的纪念,有助于激发青年的情感共鸣、斗争热情。以对黄爱、庞人铨的纪念为例,1923年1月15日《先驱》刊载《四个死者,一个精神!》《黄爱和庞人铨》,首要目的是宣传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贯、百折不挠、牺牲一切去为无产阶级底解放而奋斗的精神。”(45)光亮:《四个死者,一个精神!》,《先驱》第15期(1923年1月15日),第1版。同时还刊发了黄、庞二人小传,借纪念他们的革命精神来鼓舞青年奋发向上。
对于死难青年战士的系统纪念,始自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时期。1928年10月22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1卷第1期载有《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一文。文章开篇即指出纪念对象和纪念目的:“到现在我们才能对一年来死难的青年战士做个总追悼!去年四月十二以来,刮[国]民党疯狂的白色恐怖,造成了空前的屠杀记录!他用了千古未闻的残暴手段,想以此消灭革命,献媚于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至死不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与共产青年团员,以及革命的工农群众!全国各地,无不涂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我们不悲伤!我们不哭!我们要继续先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为他们复仇!”文章同时枚举了各地牺牲青年战士的名单,强调说:“同志们!起来纪念我们的先烈!起来继续他们的精神与工作!”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死难战士主要指白色恐怖时期被屠杀的“有忠勇的无产青年先锋分子”。(46)记者:《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列宁青年》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22日),第45—48页。
对于死难青年战士的纪念,一般是先述其生平,再介绍其牺牲经过。如对武汉青年团员梁振亚的纪念,重点宣传其革命精神:“反动军阀将他捕去后,他很慷慨的承认他是共产青年团员,反动军阀用种种残酷的严刑拷打要他招认一切,但他始终不吐半句,在监狱里谈笑自若的过了二十八天……他就义时年仅十九岁,临刑时很慷慨激昂,沿路高呼革命口号,听者无不感伤掉泪,那执法的士兵,亦为他手软,连打了五枪方才气绝。”纪念死难青年战士的落脚点则是号召继承其遗志——“我们也不要伤心,也不要流泪,我们要很勇敢的踏着他的血路往前进,以完他未完成的责任,为他复仇!”(47)张孟君:《悼梁振亚同志》,《列宁青年》第1卷第14期(1929年5月1日),第50—51页。
除文本纪念之外,青年团还通过示威、讲演等纪念形式扩大动员范围,提升鼓动效果。如1926年段祺瑞屠杀北京爱国学生的惨案发生以后,青年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扩大这次运动到广大的城市及乡村的工人及农民群众中间;号召民众起来示威,讲演日本帝国主义与段祺瑞的罪恶,他们如何内应外合,摧残国民军,屠杀爱国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准备着与吴佩孚,张作霖,英日帝国主义作一决死战争,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48)《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中国青年》第118期(1926年4月3日),第474页。与死难青年战士纪念相关的,还有各种惨案纪念,如关于二七惨案、五卅惨案、三一八北京惨案的重复纪念,这既能强化青年对于反动力量罪恶的记忆,又可以激发青年的斗争情绪。
四、青年团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
关于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49)陈金龙:《毛泽东与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表达》,《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第50页。。而纵览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纪念活动相关资料,特别是报刊、档案所载纪念活动的“宣传大纲”和“工作总结”,可以发现其纪念活动有着丰富的政治功能。概括而言,相关政治功能主要包括强化历史记忆、开展政策宣传、扩大组织力量、协调派别关系等几个方面。
(一)强化历史记忆
强化历史记忆是开展纪念活动的首要功能。彼得·伯克指出:“为了帮助保持和传承记忆,物质的形象,即‘纪念物’早已建构起来了,诸如墓碑、雕像和奖章,还有各色各样的‘纪念品’……纪念碑既表达又塑造了民族的记忆。”(50)[英]彼得·伯克著,丰华琴、刘艳译:《文化史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类型包括人物、事件和纪念日相同,青年团的纪念活动也大体如此,不同之处在于青年团还要纪念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人物、事件和纪念日,以及悼念、纪念中国革命死难青年战士。这些在各地、每年不断重复、操演的纪念活动,尽管会根据时局做相应调整,但是不可否认,宣传纪念活动本身是首要目标。若是涉及相关人物纪念,则概述其伟大事迹;若是纪念运动或惨案,则要介绍其历史价值、伟大意义,或反动力量对于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如1934年青年团厦门市中心市委的五卅纪念,首先便是向青年劳苦群众介绍五卅事件概要,指出“民国十四年时,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因为反对厂主的压迫,引起罢工斗争,其后领导工人斗争的英勇领袖顾正红竟被枪毙,因而爆发了全国工人、商民、学生空前的反帝大运动。但是结果这个运动是给中国的军阀拍卖投降了”(51)《团厦门中心市委为“五卅”惨案九周年纪念告青年劳苦群众书》(1934年5月2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组织文件(1932—1934)》,第315页。,既展现了五卅运动和工人斗争的正义性,又包含着对军阀的控诉。这类政治行为有时会衍生出其它自发行动,如对施洋烈士的纪念活动中,“多数工人焚纸致祭,文华附中(教会)学生,特遣花圈”(52)《继渠致团中央信——关于团地委成员分工、发展新团员及纪念日活动情况》(1924年5月19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192页。,这让组织者都深感意外。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它们通过描述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53)[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二)宣传政治主张
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和宣传,有助于实现青年的“无产阶级化”。1922年青年团“一大”强调,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宣传机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即须细加以分析,议决对付和宣传的方针,通知本团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54)《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1922年5月),《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第3页。。其中政治主张的宣传是工作重点,即便是关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人物的纪念也是如此。如1924年的《列宁之思想》(仲英)、《列宁的政治主张》(敬云)、《列宁与中国革命》(代英),1929年的《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少峰)、《列宁李卜克内西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得钊)。由此可见,政治宣传与青年团纪念活动有着不可分割之关系。同时,开展纪念活动也是贯彻政策、主张的良机。如1925年7月30日,青年团中央号召开展“五卅惨案二周月”时,指出:“我们民众应当要求武装,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不象现在各军阀私养军队,不能抵御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却只会压迫人民。真正人民的武力——只有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服从人民的中央政府的军队”(55)《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五卅”二周月纪念告上海工人学生兵士商人》(192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9页。,由此体现了五卅纪念的现实诉求。总之,每一次纪念活动的开展都是青年团表达政治主张的好机会。
(三)发展组织力量
大卫·科泽认为:“组织依靠其象征性的表征来维持认同感和凝聚力。”(56)[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纪念活动无疑是其中的典型,而组织力量发展程度也是评价纪念成效的重要指标。如1931年团广东省委在筹划五一节纪念活动时指出:“在‘五·一’的准备和斗争中正是发展团的组织和辅助组织的最好机会,各地团部应当进行广大的招收团员运动,招收赤色工会会员的运动,进行广大的征调青工雇农到红军中去的运动。到‘五·一’的工作结束后应当在太古内增加一倍的团员,在水师铎也要有二个同志的发展,发展一个新的汽车支部至少须有三人。”(57)《团广东省委“五·一”工作通告》(1931年4月1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组织文件(1931)》,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4年印刷,第110—113页。苏区团组织或临近苏区的地下团组织,则将扩红视为开展纪念活动的重要目标。1932年青年团厦门市委在筹备十月革命和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庆祝活动时,强调:“将红军最近胜利的消息传达到群众中去,发各种宣言、传单、标语来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应动员青工去当游击队红军”,“动员青年贫农雇农参加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少先队,轻骑队”,“用各样的方式去接近士兵,散发各种传单”。(58)《团厦门市委关于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周年纪念工作决议》(1932年10月2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团组织文件(1932—1934)》,第116—118页。从中不难看出,厦门市团组织力图通过对红军和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庆祝活动,增强扩红对于国统区青年的吸引力。这也是青年团“胜利纪念”活动的重要特点。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青年团纪念活动的实际效果未必都很理想。如团广东省委在总结1926年李列纪念周活动时,不无遗憾地总结说:“在此周内吸收同志太少。”(59)《团广州地委关于李、列纪念会经过情况的报告》(1926年2月8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一),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3年印刷,第134—136页。
(四)协调派别关系
规章、制度对于政治力量、派别关系的界定,与各政治力量、派别的实际关系有着一定的矛盾和张力。其解决路径并非依赖规章、制度的完善,而是在现实活动中具体调适,共同举行纪念活动则是协调关系的重要时机。首先,维护国际统一战线。1926年国际青年日期间,青年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青年团举行大示威,高呼“统一青年工人的联合战线”(60)《青年共产国际为第十二个国际青年日致全世界青年工人和农民书》(1926年8月16日),《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176页。;1934年8月12日,团中央发布《团中央关于“九一”国际青年节的决定》,指出:“必须在武装保护苏联,组织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基本口号之下,加紧宣传反帝的六条纲领,利用每个新发生的具体的事实解释这六条纲领的正确。”(61)《团中央关于“九一”国际青年节的决定》(1934年8月12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2册,第687页。由此能够看出青年团话语中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统一关系。其次,协调党、团关系,消除“第二党”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联合纪念方面。1929年党、团在北京惨案、巴黎公社纪念活动之前,联合发布纪念宣言。(6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纪念“三一八”宣言》(192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195—196页。即使是在国际青年日纪念活动之前,党、团召开联席会议筹划行动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再次,协调与非共势力的关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26年的李、列纪念活动期间,团广州地委采用学联会发起、团员实际组织的方式开展,竟然出现多所学校主动参加的好现象。(63)《团广州地委关于李、列纪念会经过情况的报告》(1926年2月8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一),第134—136页。总之,纪念活动对于青年团协调派别关系具有直接作用。
余论
从创立至苏维埃运动时期,党对于团有政治领导关系,团有开展政治、文化、教育运动之自主权。不论是党还是团,其奋斗目标都是政治动员、社会革命,因此党、团工作不可避免有重合之处。就实际效果来看,党、团工作的交叉或重合起到的是“强化”作用,而非“掣肘”。从全面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团经历了由群众化、非党化到重建的发展转变,广大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如前文所述,青年团组织举行的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有诸多重合之处,甚至很多活动是由党、团联合举行。以发展组织力量为例,青年团开展纪念活动时,不仅要发展团员,还要协助发展党员。大革命时期公开活动的青年团代表秘密的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取得很好效果,令与之合作的国民党人都十分佩服。正因如此,邵元冲在1925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阅‘C.Y.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可言耶?”(64)《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在重合之外,青年团纪念对象还涵盖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领导人,国际青年日,中国革命死难青年战士,相关活动呈现出“青年化”“群众化”特点。这也是青年团纪念活动的显著特色。综观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团中央、各地方团的相关资料来看,关于各类纪念活动的计划、总结可谓不胜枚举,这既反映了青年团对于纪念活动的重视,又映射出纪念活动对于青年团实际工作的价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举行相关人物、事件、节日纪念活动的目标,并非仅限于纪念其伟大意义,根本落脚点乃是激励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以及借助纪念活动更好地宣传政治主张。这也是时至今日党、团仍然隆重纪念各类人物、事件和节日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