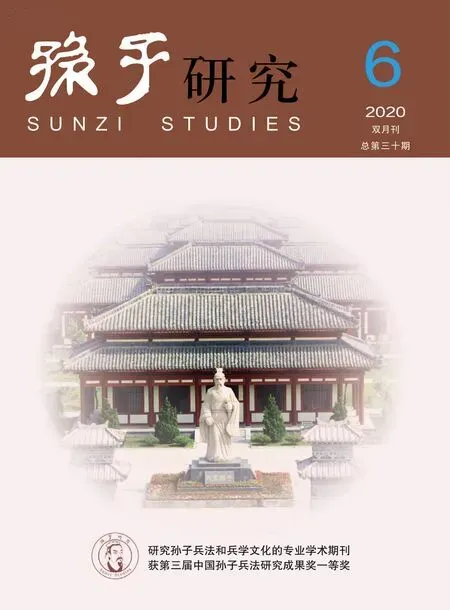孙子兵学历史传承的路向
2020-11-30蔡传聪熊剑平
蔡传聪 熊剑平
明代学者茅元仪对《孙子》留有这样一句评语:“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武备志·兵诀评》)从中可以看出,茅元仪将其他先秦兵书都视为《孙子》之注疏。早出兵书,《孙子》已充分予以吸收;晚出著作,则无法逃脱《孙子》之藩篱。有意思的是,茅氏所论,仅及先秦兵六家,但不少人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一段——“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从而将《孙子》之地位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判断此论允当与否,需对数千年兵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非常艰深而且费时,但直觉告诉我们,此论存在人为拔高之倾向,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实际。在笔者看来,仅就思想发展层面来说,用茅元仪这几句话对我国古典兵学史进行概况和总结,不失为允当之语。当我们谈起古典兵学思想时,最终都免不了会提及《孙子》。但是,如果就整个古代兵学体系来说,想用这句话进行简单概况,则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孙子兵学的历史传承始终存在多个路向,既有忠实诠释者,也有尖锐批评者,更有大胆改造者,并非只有掌声和鲜花。
(一)逐层深入的注解
历史上曾有难以计数的军事家和学者投入地研究《孙子》。他们在精心研读字句的同时,也勤奋笔耕,从而用注解的方式实现了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逐层深入。这是孙子兵学思想得以长久发展和继承的主要方式。
通过考察银雀山出土文献,尤其是几篇《孙子》佚文,我们可以对《孙子》的早期注释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有关这方面内容,前面已经有专题讨论。几篇《孙子》佚文体例不一,风格多样,总体上看都是注解类文字。至于《四变》,则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这一特征。随着银雀山竹简的出土,清代孙星衍等人认为曹操是《孙子》注释第一人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1]早在先秦时期,很可能已经有人在为这部兵典进行注解工作。
因为著名军事家曹操的工作,《孙子》的流传和继承都迎来一个新局面。曹操抛弃了过去种种繁复的注解方式,改而使用简略文字注解《孙子》,确实有扭转乾坤之力。曹操不仅投入地研究《孙子》,还积极运用孙子的兵学理论指导自己的战争实践。这同样引领了时代潮流,也极大地提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孙子》研究水准。
在曹操之后,有不少学者研读和注解《孙子》,并留有注释作品,比如张子尚、贾诩、王凌等。遗憾的是,这些注解之作,今天都已经失传。有一些只能从《隋书·艺文志》等书中见到零星著录,有的则连姓名都未曾留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连连有着直接关系。这个时期,书籍损毁非常严重,《孙子》注作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无法得到妥善保管和流传。幸运的是,大浪淘沙,仍有曹操的《孙子略解》得以妥善保存。这可能和曹操显赫之身份有关,更是曹操注本非常出色使然,曹注长期得到广泛流传,充分证明了其不朽价值。
到了唐代,吕尚被尊奉为武成王,并享有高规格献祭。孙武则连同吴起、韩信、李靖等人一起,分置左右: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列于左,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列于右。[2]由此可见,孙武在唐代初期,其地位并不突出。既然如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那些君臣问对,包括李世民盛赞《孙子》的话,就统统不能当真。当然,在这部兵书中,作者模拟唐太宗与李靖的口吻研讨兵法,在一问一答之间完成了对《孙子》兵学思想的诠解和传承,从而为后人留下一部精彩的论兵之作。
在唐代,《孙子》不仅得到广泛流传,精彩的注释作品也层出不穷,并在形式及内容上都有创新。这时期产生的重要注家有李筌、孙镐、贾林、杜牧、陈皞、纪燮等。此外,杜佑在编纂《通典》时也阐发了自己对于《孙子》的独到见解。这些注解文字经过辑录,大多保存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成为后人研读《孙子》的重要参考文献。杜牧受祖父杜佑的影响,也关心政治,关注兵学,曾投入地研究和注解《孙子》。身为文学家,杜牧的注解文字不避繁琐,令陈皞讥其“疏阔”。陈皞不时攻击杜牧,欧阳修却将他们二人的注文收录一处,加上曹注一起,并称为“三家注”。此外,唐代还有贾林注《孙子》,虽说留下的条目不是很多,但同样很受重视,被辑入《五家注孙子》。这些注解之作,对推广《孙子》兵学思想,也为宋代《孙子》兵学地位的最终确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资料显示,在唐代初期,《孙子》还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影响力从中原进一步扩大到东北亚地区。[3]
唐代注家中,李筌注解《孙子》稍显另类。虽说他也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学思想特点,并注意关注个别词句的细节,但也更表现出“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特点。注语中偶或掺入的兵阴阳内容,既与其他注家迥异,也违背了孙子“不可取于鬼神”(《孙子·用间篇》)的根本原则,与孙子的精神背道而驰。[4]
在《孙子》被确立为兵经之后,宋代《孙子》研究迅速升温,注解和研习之作不断出现,创造了注释《孙子》的高峰期。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是其中代表,其注语均收录于《十一家注孙子》中。
《十一家注孙子》收录张预所注词条最多。张预注重从整体上考察孙子兵学思想,关注《孙子》篇次问题,对每一篇的篇题都有留意,重视发掘十三篇之间的内在联系。梅尧臣的注释词条,数量仅次张预,语言简练,显示出文学家独有的深厚文字功底。王皙之注,相对偏向于文献学,注重训诂和校勘。只知姓氏的何氏,注文不拒繁琐,文字颇有气势,和曹操的“略解”形成鲜明对比。郑友贤的注解文字不是很多,总称《遗说》,同样非常重要。他从情报的角度出发,指出《孙子》篇次安排的精妙,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金人施子美所撰《武经七书讲义》中的《孙子讲义》,对阐述与传播孙子的兵学思想,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代研习《孙子》的风气,在明朝得到延续。明代留下的兵学著作非常多,仅就存目兵书来看,几占历代兵书总和的三分之一左右。[5]与《孙子》有关的著作多达200 余部。[6]明代的武学科考更加规范和制度化,为应付策试而刊印的标题讲章之类,也在明代逐渐发展起来。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甚至被官方钦点为教材,成为法定军事教科书,对《孙子》的流传和普及起到积极作用。郑灵、陈天策、曹允儒、黄献臣、李贽、何守法等人的注本,也曾影响一时,对于研习《孙子》也不乏参考价值。明代出现了不少综合性大型兵书,有不少只是完成了对《孙子》等兵书的辑录和注解,如《兵钤内外书》等。
清朝统治者对于兵书的态度比较暧昧,他们一方面对兵书有着一种恐惧和打压心理,批评《武经七书》“未必皆合于正”和不合“王道”,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也对兵书予以大量删减,《孙子》注解作品全被抛弃,只留下一纸白文;另一方面,他们又依靠武举来选拔人才,将《武经三子》(即《孙》《吴》《司马法》)作为武举的必考科目,虽大量禁毁兵书,却不禁《孙子》。为适应武举考试的需要,截至雍正朝,已产生与《孙子》有关的著作41 种。[7]众多文字浅显、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促进了《孙子》的流传。清代的《孙子》注家就多达50 余位,王瞰的《孙子集注》也广泛收录旧注,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相比前朝,清代《孙子》研究在文献学上尤其是文字校勘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邓廷罗、顾福棠、黄巩、毕以珣、孙志祖、洪颐煊、俞樾、孙星衍、于鬯、王念孙、孙诒让等学者,对此都有所建树,这对准确解读孙子兵学思想不无裨益。
民国时期的学人在注《孙子》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一面是取法传统,以陆懋德为代表;一面则是响应西方兵学理论发展潮流,紧密贴近时代脉搏,这以蒋方震等为代表。陆懋德的代表作为《孙子兵法集释》,成书于民国四年(1915)。陆懋德认为《孙子十家注》“词冗而义晦”,对其进行大量的辨正和删削,总体上仍是遵循传统,尤其受到儒家注解经典的影响。和陆懋德一样采用传统注解方式的,还有易培基,代表作是《读孙子杂记》。蒋方震更注意援引近现代理论注解《孙子》,紧跟时代步伐。无论是和刘邦骥合著的《孙子浅说》,还是独撰之《孙子新释》,都注意将《孙子》与西方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多借鉴蒋氏之法,比如夏寿田《孙子选注》、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刘文垕《孙子释证》、齐廉《新注孙子兵法直讲》、吴石《孙子兵法简释》、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陈华元《孙子新诠》、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萧天石《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等。支伟成的《孙子兵法史证》、周传铭的《孙子兵法古今释例》和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大量援引古今战例注解《孙子》。其中,钱氏所著《孙子章句训义》更是充分注意援引现代战例,使其著作更受世人瞩目。
(二)战争中的运用
《孙子》毕竟是一本讨论战争之法的兵书,理应受到军事家们更多的关注。在中国古代,《孙子》因为其不朽的思想价值而受到众多军事家的广泛赞誉。在战争实践中借鉴和运用孙子兵学原理,也是继承发展的主要路向。
在先秦时期,《孙子》就已经广泛流传,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按照《史记》的记载,孙膑系孙武后人。孙膑不仅在军事理论上忠实继承孙子,也在军事实践中巧妙借用其战术思想。比如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就成功运用《孙子》“避实击虚”等战法,击败强大的魏军,取得了胜利。
到了秦汉之际,韩信指挥的“背水阵”之战,正是充分借鉴和运用孙子有关“死地”的作战理论,最大程度地激发士兵的作战潜能,从而成功地击败敌军,创造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孙子在《九地篇》论述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战原则:如果士卒被投入“亡地”,就会拼死力战,以此求活;一旦陷入死地,就会向死求生,拼死奋战。这就是孙子所谓“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孙子·九地篇》)。韩信在战争中,准确而及时地变换攻守战术,灵活地部署兵力,合理地配备阵形,充分借鉴和运用孙子“死地”作战之法,从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孙子在《谋攻篇》中曾论及“君将关系”,认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在《九变篇》中,他再次强调“君命有所不受”,希望国君对军中事务尽量少加干预。此论在皇权高度发达的中国专制集权时代无疑极具震撼力,但也因为含有相对合理成分而受到追捧。西汉名将周亚夫“细柳治军”,充分体现了孙子“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汉文帝犒劳将士,在到达周亚夫的营寨时,被守门士卒告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文帝很受感动,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感慨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很显然,汉文帝幸得知兵之将。
孙子致力追求战争中的“高效益”,所以力倡“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篇》)。谋略用兵和诡道之法,都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孙子认为“以火佐攻者明”(《孙子·火攻篇》),积极主张火攻制敌,为此特劈专篇讨论火攻之法。如果没有新的出土文献,《火攻篇》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系统讨论火攻战法的专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历史上不少军事家重视火攻,都是受到孙子的启发。战国时期诞生的著名兵学《六韬》也设《火战》篇,专门讨论火攻战法。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等,之所以成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也与借鉴和运用孙子“以火佐攻”战法有着直接关系。
曹操对《孙子》有着精湛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言简意赅的注释之外,也在战争实践中积极运用孙子的军事谋略。诸葛亮曾在《后出师表》中形容曹操的用兵特点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在与袁绍的官渡决战中,曹操充分运用了《孙子》“夺其所爱”的战法以及火攻理论,偷袭了袁绍粮草储备之地乌巢,从而改变了战场态势,最终达成以弱胜强的目标,一举击败袁绍。
赤壁之战则更为著名,火攻战法的地位更加突出。在这场战争中,孙权和刘备结成军事同盟与曹军抗衡。他们灵活使用多种战略战术,针对曹操轻敌的缺点,充分利用地理、天时等条件,果断实施火攻之法,给予曹军致命一击。显然,孙子的火攻战法,是帮助孙、刘联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诸葛亮同样对《孙子》有着深入研究。在和司马懿对峙过程中,诸葛亮曾多次使用诱敌之计,没想到司马懿始终坚守不出,不为所动。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的服饰,试图以此侮辱和激怒对手。对此,司马懿立刻上书朝廷,做出请求出战的姿态。诸葛亮立即明白,司马懿本无出战之意,只是故作姿态而已。他引用了《孙子》“君令有所不受”这句名言,并指出如果司马懿果真想出战,就不会请示魏主(《晋书·宣帝纪》)。而事实正如诸葛亮所料,司马懿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使用诡计。
韦孝宽是南北朝时期一位非常善于用间的军事家。他曾深入研究孙子的用间之术,精心设计和策划了多起间谍活动,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战果,非常生动地注解了孙子的用间理论,充分证明了孙子“赏莫厚于间”(《孙子·用间篇》)的合理性以及“五间俱起”(《孙子·用间篇》)的威力。制造伪信离间对手,编造歌谣瓦解敌军等手法,都是孙子“用间”理论的巧妙运用。韦孝宽所设计的几起间谍活动,也都成为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经典案例,充分证明了孙子用间理论的深刻性与实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子》不仅为军事家们在战争中所借用,同时也已深刻地影响当时的军事学术著作。《将苑》旧题为诸葛亮所著(实际也可能是托名之作),其中就有不少出自对《孙子》的模拟。尤其是十七条“相敌之法”,大多可以从《孙子》的“相敌之法”中找到出处。包括《便宜十六策》,也可见到受《孙子》深刻影响的痕迹。比如其相关“五间之道”的论述,相关将帅的论述等,其论述形式和内容等,都可以从《孙子》找到影子。除此之外,司马彪在所撰《战略》中也多次引用《孙子》,可知当时的战略理论研究已经非常注意借鉴和运用《孙子》的兵学理论。
就战争筹划而言,孙子曾主张积极夺取主动权,即“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虚实篇》),强调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要想达成“致人”的目标,不仅是依靠强大的力量,也依靠积极的战略筹划。孙子指出:“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孙子·虚实篇》)如果能抢先到达决战地点,就可以赢得主动;反之则会陷入被动。高明的指挥员一定要善于通过“示形动敌”来夺取战争主动权,力争达成“以实击虚”。唐太宗李世民少年从军,也非常善于学习和运用《孙子》,世人甚至托名写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世民经常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也非常注重战前侦察,尽可能做到“知彼知己”。在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李世民运用孙子“示形动敌”之法调动对手,在虎牢关一带拦住窦建德援兵,引诱追兵进入己方伏击阵地。此后,他又利用王世充急于突围的心理,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兵力部署,指挥大军迅速在虎牢关一带集结迎敌。为进一步达成“示形动敌”,李世民下令部署千余马匹在河边放牧,窦建德指挥军队倾巢出动,抢夺马匹。李世民耐心等待对方军队气势转衰,适时发起攻击,将窦建德大军击溃。很显然,李世民投入学习孙子兵学思想,收到了丰厚的回报。
在《虚实篇》中,孙子还主张通过“形人之术”而实现“我专而敌分”,由此而达成“以众击寡”和“避实击虚”。其中之关键,一方面是“形人”,通过多种手法来探知敌人的虚实,另一方面则是“我无形”,巧妙地隐藏己方的战略意图,让对手摸不清我方的虚实情况。这两方面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形人之术”,也即“形人而我无形”。明代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充分借鉴和运用的是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理论,巧妙地隐藏己方行动计划,待时而发,是朱棣成功夺占皇位的关键。两军僵持之际,朱棣得到宦官提供的情报:“京师空虚可取。”(《明史·成祖本纪》)他立即破釜沉舟,全力攻打京师,就此夺取战争主动权,一举扭转战局。这正是孙子“避实击虚”战术的巧妙运用。
明代著名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也是善于学习和借用孙子兵学思想的高手。这一点也早已为日本学者所察。[8]考察王阳明的军事实践和著作,都可以看出他曾对古代兵学经典下过很深的功夫。在《武经七书评》中,王阳明对《孙子》《吴子》等兵经作了要言不烦的评点,从中尤其可见他研习古典兵略的功力。比如对《孙子·火攻篇》,王阳明点评道:“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实不可轻发。”(《武经七书评·孙子》)这一点评,与孙子“非危不战”非常契合。再如对《军争篇》,王阳明点评道:“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武经七书评·孙子》)这是巧妙运用老子的“不争之术”对“军争之法”进行解读。为了做好“严守以乘弊”,王阳明借用《孙子》“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篇》)一语,说明加强战备、增加防守实力的重要性。关于用兵,王阳明强调“捐小以全大”,注意借用孙子“佯北勿从,饵兵勿食”(《孙子·军争篇》)的道理。在平叛战争中,王阳明眼见形势不妙,便运用伪造檄文的办法来威慑对手,体现出出众的胆识,对孙子的“形人之术”有精深的研究。《明史》中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9],显然并非夸张之词。
孙子的“十围五攻”之法,体现的是集中兵力和机动用兵思想。孙子认为,用兵的奥秘就在于“避实而击虚”(《孙子·虚实篇》),努力达成“以镒称铢”(《孙子·形篇》)。如果想在战争中获胜,就要努力实现兵力上的优势,或是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孙子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已被无数战争实践所证明。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军事家指挥的战争,也充分折射出孙子的兵学思想。努尔哈赤指挥的萨尔浒之战就是避实击虚、集中兵力的经典战例。在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取得了对优势之敌的辉煌胜利,从而根本地改变了明与后金之间的战略态势。
孙子的战术千变万化,变化是其灵魂。孙子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孙子·九地篇》),正是主张根据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战计划。这其实也就是“因敌而制胜”(《孙子·虚实篇》)。皇太极进攻北京的战斗中,非常好地贯彻了孙子这一战术主张。皇太极充分发挥骑兵善于机动的特点,针对明军的布防情况及时改变战术,彻底贯彻了孙子“践墨随敌”的战术。后金军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都显得游刃有余,很好地调动了明军,也令袁崇焕一直疲于应付。眼看时机成熟,皇太极及时抛出反间计,令崇祯皇帝冤杀大将,将这出“践墨随敌”的大戏推向了高潮。
总之,《孙子》是一部战争之法,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不断地在战争实践中借鉴和运用孙子的军事理论和谋略思想。这不仅是继承和弘扬孙子兵学的重要路向,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孙子兵学思想需着力关注和借鉴之处。
(三)战争之外的借用
由于《孙子》充满哲理和智慧,其影响力早已扩散到军事领域之外,对政治、经济、文学、医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孙子》所揭示的诸多原理,如杂于利害、以迂为直、避实就虚等思想方法,对于各行各业都有启示价值。既然如此,企业管理,商业运营,乃至竞技体育等,都可以借用孙子的兵学思想,达成趋利避害、出奇制胜的目标。
就商战而言,由于其中充满竞争,《孙子》的智慧与谋略便大有用武之地。先秦时期就已有白圭借用《孙子》经商,并取得佳绩。《孙子》有关用兵的重要原则,比如不避诡诈、情报先行、慎重决策、利益为上等,都可以在商战中得到借用。
商战与战争一样,也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等重要因素,《孙子》所论“知彼知己”和情报先行原则,强调全面考察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主要因素,对商战决策而言完全适用。要想成为合格的企业领导,必须首先认真做好情报工作,充分占有各种有利筹码,并进行科学计算和慎重决策,才能在商战中保持不败。商战尤其需要高举利益原则,《孙子》所提倡的“非利不动”原则,完全与之吻合。当然,也有不少高明的企业家和商人基于“双赢”原则,也能够获得丰厚利润,但在实际商战中,那些主动使用奇兵和奇计,不按常理出牌,大量使用诡诈之术的,往往能够赢得主动,获取更多利益。《孙子》提倡的“兵者诡道”及“兵以诈立”等原则,也由此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商战竞争之宝典。商业也存在对抗性竞争,企业领导也需懂得抓住最佳时机发力,合理编配团队,也要学会集中力量,《孙子》所强调的“善战者,求之于势”和“避实击虚”等原则,同样可以适用。《孙子》的主动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可以在商战中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企业家和商人能够做到主动出击,努力达成所谓“先胜”,积极依靠“超前战略”,就更容易赢得主动局面。
在商战中,《孙子》早就有被成功借用的案例。前面提到过,最早成功借鉴《孙子》兵学谋略经商的,怕是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贾白圭。白圭是西周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非常善于捕捉商机,他总结经商经验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知,白圭之所以能赚钱,经营、生产非常成功,就是因为他向兵家学会了权变之术和决断之法,也深谙“人取我予”的奥秘。
白圭明确承认其经商之术,有许多是取法“孙、吴用兵”之术。需要看到的是,这里的“孙”既然是排在“吴”之前,那么他应当是指孙武,而不是孙膑。白圭的经商之术,是取自《孙子》,而非《孙膑兵法》。通观白圭的经商谋略,诸如人取我予、把握时机以及与部下同甘共苦等,都可以从《孙子》的兵学思想中找到出处。在介绍白圭时,司马迁特别强调其经商之法是“能试有所长”,并“非苟而已也”(《史记·货殖列传》),并非鲁莽行事,而是慎重决策,未雨绸缪。就这一点而言,《孙子》一贯强调的“慎战”,必然会对白圭的慎重决策和谨慎经商产生一定的影响。
《孙子》强调情报先行,由此而建立了以“先知”为核心的情报思想体系,这对商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由于情报工作出色而取得成功的商战案例,在历史上俯拾皆是。战国末期的巨贾吕不韦,就是因为提前得到若干重要情报,故而就此致力于“人货”生意,敢于针对政治人物做出一笔大买卖。结果,因为保护异人有功,吕不韦顺水推舟地做成丞相,从而名利双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位曹姓商人,也因为情报先行而受益。他由高粱茎内的害虫判断出当年之收成,于是果断出手大量收购高粱。虽然当地高粱果然因为虫害而严重歉收,但这位曹姓商人因为早有准备,事先大量囤积高粱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中国人秘而不宣的经商秘诀中,有不少都受到《孙子》等兵法的启示。司马迁总结经商之道时指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史记·货殖列传》)此语明显是从《孙子·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一语化出,强调的是用人问题和抓住时机。所谓“择人”,也有释为“释人”。其实,由“择人”也可延伸到“择地”和“择时”等。商战也是如此。《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一个“择地而任势”的生动案例。秦国在击败赵国后,强迫卓氏迁徙,卓氏看到汶山下面有一片沃野,于是要求迁往附近经商,最终顺利实现致富的梦想,富可敌国。《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孙子·地形篇》)“知地”对作战极其重要。卓氏则成功地将其运用于商战,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医学领域,尤其是传统中医学领域,《孙子》也备受重视,其用兵理论被中医学大量借用。就目的论来说,兵法和医学都高度关注生命的存活。就方法论而言,二者之间相似性更多,比如先知敌情、果断出击、集中力量等。在病人和医生眼中,病魔就是敌人,是需要设法打败的对象,故《孙子》的用兵之术自然也会受到中医学的重视和借鉴。
著名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也有借鉴《孙子》的痕迹。在《灵枢经》中,作者曾借用《孙子·军争篇》中“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一语,探讨针灸之法,提醒人们抓住时机,对症下药。《黄帝内经》袭用《孙子》词句,构建了独到的“刺法”:“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对针灸的时机及部位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孙子》强调“先知”和“先胜”,力求通过“伐谋”和“伐交”等,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黄帝内经》的理念与之相似,强调“治未病”和“治未乱”,力求做到防患于未然。作者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境界追求受到启发,将减少病人的痛苦作为终极追求。就病情治疗方法而言,《黄帝内经》受《孙子》启示尤多。《孙子》用兵强调“杂于利害”,辩证对待战争得失。《灵枢·终始》则主张“必通阴阳”,辩证看待救治过程中的得与失。此外,《黄帝内经》大量吸收《孙子》“治气”“治心”“治变”“避实击虚”等用兵原则,建构起“因时制宜”“务求治本”等一整套辩证施治的中医学理论。
系统总结《孙子》与医学的关系,将孙子用兵理论最大程度引入传统中医学理论的,要数清代的名医徐大椿。徐氏著《难经经释》《伤寒类方》《医学源流论》等,全面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重要医理。在《用药如用兵论》中,徐大椿借用孙子的“十围五攻”[10]之法,积极主张医治病人时贯彻“以众击寡”之法。徐大椿不仅主张在医治病人时,需充分借鉴孙子“知彼知己”“因敌制胜”“避实击虚”等用兵原则,将医生的临症处方视为“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甚至指出治病之法尽在《孙子》。“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此语显然是中医学界给予《孙子》的最高褒奖,全面总结了用药如用兵的医理。
《孙子》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辞优美。古代众多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曾投入研究其语言艺术,在撰写文学作品或文论作品时也会借用其理论。
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曾组织文人编选《昭明文选》,选录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七百余篇,其中多次明引或间引《孙子》的文字,仅《势篇》就引用9 次之多。[11]刘勰也盛赞《孙子》:“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文心雕龙·程器》)字里行间,足显示出对《孙子》的赞赏之情。就连《文心雕龙》的写作,也受到《孙子》兵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刘勰论及布局谋篇时,广泛借用《孙子》兵学思想,大量引入奇正、变化、诡谲等词语。
唐代以后,文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孙子》。李白诗歌立意新奇,非常契合孙子的“出其不意”,其中宏大气象也受孙子“造势”理论的启示。白居易、高适、罗隐等诗人,都曾在诗歌中直接提到《孙子》,甚至写有专篇怀念孙武。比如,高适在《蓟中作》中曾写下“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抒发自己志在报国的壮烈情怀,又在《送浑将军出塞》中写下“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的诗句,表达了对右武卫大将军浑释的赞赏之情。白居易在《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中写下了“庙谟藏稷契,兵略贮孙吴”的诗句,表达出对《孙子》高超兵学谋略的钦佩之情。宋代,《孙子》连同《六韬》等被立为兵经,文人论兵和研读《孙子》渐成为时尚。黄庭坚曾借用孙子兵学理论,主张行文时要做到“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譬如用兵,奇正相生”(《渔隐丛话》卷一〇)。词人姜夔论诗也曾借用兵法,主张诗歌创造应该做到“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最终达到“出入变化,不可纪极”(《白石道人诗说·自序》)的境界。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一度追求平淡自然,讲究性灵,但唐宋以来形成的“以奇制胜”理论并没有遭到完全抛弃。高明的文学家,则是强调“传奇”与“自然”的统一,在这二者之间追求所谓中庸之道。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并不代表《孙子》“以奇胜”的理念遭到彻底无视。
围棋的诞生虽较《孙子》为远,但围棋界对《孙子》的借用也非常普遍。弈棋之理与作战之理,毕竟存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棋道中人纷纷借鉴《孙子》的作战原理来提高棋艺。
众所周知,围棋是一种智力游戏,对弈过程始终需要运用谋略。两军交战,更需要施展谋略,所谓“上兵伐谋”。在古代,围棋成为很多军事将领的业余爱好。关羽在刮骨疗毒时弈棋,表现出勇敢无畏;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弈棋,表现出镇定自若。他们既能在兵战中巧用谋略,也能在对弈时借用兵法。中国古代探讨棋理的著作,如敦煌写本《棋经》、王积薪的《围棋十诀》和宋代张拟所著《棋经》,都注意将棋道与兵法进行对比讨论。南宋国手在《棋诀》中称“棋者,意同于用兵”,因此在撰写围棋秘诀时,力求“粗合孙吴兵法”。张拟所著《棋经》,不仅挖掘《孙子》用兵谋略,甚至在体例和篇数上也都完全模仿《孙子》,著成十三篇之制,而且有若干篇名与《孙子》完全相同——如《虚实篇》,包括《得算》《度情》等篇名的设置,也明显借鉴《孙子·计篇》。在《棋经》中,《孙子》用兵谋略的精髓,如“避实就虚”“因敌制胜”“知彼知己”“奇正相生”等,都得到大量借用。
(四)间或出现的批评
对孙子兵学理论提出批评的,历代不乏其人。这些批评之辞,或为有的放矢,或为过于苛求,或为不得要领,或为无中生有,但对孙子兵学的继承而言,并非坏事。常言道,批评使人进步。就兵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而言,也是这个道理。孙子兵学理论同样也需面对和接受各种批评。
早在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及楚国名相春申君就曾批评孙子“尚诈而轻义”。荀子批评孙子的诡诈,主张“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进而提倡兴“仁者之兵”。[12]春申君也认为孙子的“势利”和“变诈”均不合于“仁义”。[13]这种声音在后世引起不少共鸣,比如《汉书·刑法志》批评孙子“任诈力”。即便《孙子》获得兵经之首的崇高地位,儒者仍然前赴后继地批评孙子疏于仁义。南宋学者戴溪、叶适,明代学者闵振声、俞大猷,清代学者汪绂、姚鼐等,都曾批评孙子“仁义不施”。但这种批评更像是一种苛责,前面已有介绍,此处不赘。
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曾批评孙子“重谋而轻力”。在他看来,孙子的诡诈和过分注重谋略对于军事实力营建和军事斗争而言,有害而无益,只会造成“言战者多”和“披甲者少”,故而会出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韩非子·五蠹》)的现象。韩非子的批评之声,得到南宋学者戴溪的响应。戴溪不仅批评孙子“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而且认为孙子兵学“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将鉴论断·孙武》),并非“安国全军”的长久之策。此后,唐甄、闵振声等学者也持类似批判态度,这在前面也曾提及和辩驳。
除“尚诈而轻义”和“重谋而轻力”之外,苏轼曾批评孙子有“扶将而弱君”的倾向[14],但响应较少。此外,也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孙子用间理论的批评。苏洵及何守法等人持续跟进,对用间之害进行了探讨,这在论述用间之术时,也已介绍。苏洵还从战法上对孙子展开批评,指责孙子“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在他看来,吴王率兵出征,被越王从背后袭击,乃至自救不暇,孙武不能免责:“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权书·孙武》)孙子“因粮于敌”的后勤补给之法,也饱受诟病。孙武指挥吴国士兵经过多日艰苦作战之后,终于取得伐楚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但吴军在楚国烧杀抢掠,留下不少恶行,不仅引起了楚国人的激愤之情,也永久地记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清代高士奇说,吴军入郢之后,“仁义不施,宣淫穷毒,楚虽挠败,父兄子弟怨吴入于骨髓,争起而逐之”(《左传纪事本末》卷五〇),对孙子给予了严厉批评。
进入现当代,随着学界对《孙子》研究的深入,批评之声更加尖锐,内容也更加具体化。郭化若、关锋、钮先钟等学者,堪称其中代表。
郭化若首先是从政治层面,总结了《孙子》的缺陷,批评孙子持有“观念论”:“思想上看,首先就会看到在《孙子兵法》中包含着观念论的因素。他对于战争的解释,用‘兵者,国之大事’的空话,来掩盖当时统治阶级进行的不义战之阶级政策的本质。”[15]与此同时,缺少辩证思维也成为郭氏批判的靶子:“由于种种原因,孙子思想上没有也不能贯彻辩证法的思想方法。”[16]此外,没有“义战”思想,也成为郭氏的批判对象。在郭化若看来,孙子的愚兵思想等,都与此紧密相关:“首先他就把战争作为无类别地看,忽视义战与不义战的区别,于是他的战略思想若干地方就只能为不义战服务……同样因为他掩藏了政治的阶级性,所以他对本国居民、本军兵卒的办法只有愚民政策、利诱(所谓厚赏)与镇压(严刑)。”[17]
相比政治层面的批评,作为领兵作战的优秀将领,郭化若对孙子作战理论方面的批评似乎更可称心得之见。他首先是批评了孙子对“持久战”的无视:“强调速决战时,就根本否认了持久战。”[18]与此同时,他也对孙子的攻防战术提出了批评:“对攻防之相互渗透、相互推移,也完全没有谈到。”[19]就孙子的战略战术,郭氏最为不满的似乎是其消极因素:“在战略上战术上,还带了不少消极的因素……敌人背丘,有时是可逆的;敌人的归师,有时是可遏的;包围敌人,有时是不可阙,而不应阙的;最后穷寇则极应追击。”[20]
关锋主要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孙子》的思想缺陷。关锋首先指出孙子在政治层面的缺陷,认为孙子对影响战争胜负的政治因素之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关锋承认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但还是着力批评孙子的“愚兵政策”,认为这种愚兵思想的产生,正是“不义战争”使然。[21]不仅如此,在关锋看来,孙子既不了解战争,也不能对“战争这个社会现象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22]不仅如此,在关锋看来,即便《孙子》蕴含了军事哲学思想,但其中也包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比如就君将关系,关锋似乎受到苏轼影响,认为孙子强调将帅的主观作用,“却达到了一个片面、极端”[23]。在承认孙子哲学思想的成就之余,关锋也认为“《孙子兵法》中,并不是以精确的哲学语言说出的,而多半出以比喻的形式,许多概念是不精确的”[24]。
台湾学者钮先钟则辟专门之章——《孙子的缺失》,从六个方面对孙子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批评,分别是:一是战争与政治,二是大战略与经济,三是治疾与养体,四是失败的研究,五是战争与道义,六是深远的未来。[25]钮先钟所论,气势十足,咄咄逼人,但并非完全出自本人的发现。其中也有部分观点是从前人袭来,比如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道义的关系讨论等,也可见出传统儒家的影子。至于“治疾”“养体”云云,也是袭用了唐甄之说。[26]
还需为孙子抱不平的是,钮先钟批评孙子“对于君(主)道几乎很少论及”,明显是苛责。孙子申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谋攻篇》),包括“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明君慎之”(《孙子·火攻篇》)等,其实都是在探讨为君之道。此外,钮先钟批评孙子“对于平时应如何厚植国力的问题在其书中是完全不曾加以讨论”,这显然是对《形篇》的“称胜理论”的无视。退一步说,即便孙子对这些论题缺乏讨论,也属情理之中。因为这本属政治家的职责范围,不该是军事将领所应关心的论题。
其实,无论是郭化若,或是关锋,抑或是钮先钟,在批评孙子时,都不乏苛责之辞。当然,他们多少也注意到孙子是受到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才会出现若干缺陷。《孙子》毕竟是一部古兵法,上述批评之词,虽然透着含有苛求的成分,但多少也能折射出孙子兵学理论在面对新情况时无法完全自洽的实情。换句话说,《孙子》并非亘古不变的真理,无法包打天下,也不能包治百病。既然如此,根据历史条件和作战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孙子兵学理论进行必要和恰当的改造,也是历史之必然。
(五)结合时代的改造
《孙子》固为不朽之经典,其兵学思想对战争实践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但如果过于拘泥而不知变通,就一定会像纸上谈兵的赵括那样,必将受到战争的严厉惩罚。毕竟历史是一直朝前走,战争环境和军事科技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再高明的兵法也需要结合战争历史的发展现状,与现实军事斗争充分结合。故此,历史上那些高明的军事家往往非常注意与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在继承孙子兵学理论的同时,也适当加以改造。这其中,尤其要数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和革命领袖毛泽东。
戚继光曾长期学习古代兵学经典,对《孙子》为代表的传统兵学有充分的学习和继承。总体而言,他从战略筹划和攻守战术等方面继承得更多。比如,沿着孙子的“庙算”理论,戚继光提出了“算定战”,其内涵与孙子基本相同,只是使用词语小有变化。对孙子的攻守之道,戚继光也有继承,强调“攻守结合”和“攻守适宜”:“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纪效新书》卷一三《守哨》篇)
就防守而言,戚继光针对当时的海防新局面,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略,更加具有针对性。戚继光非常清楚当时防务松弛的情况,他说:“当承平久,外寇以掠为务而弗力攻,故多讲战,腹里尤绝不言守,卒然有变,何以应之?” (《纪效新书》卷一三《守哨》篇)所以,戚继光非常看重依靠山川之险和修筑炮台,认为“守险”和“恃险固守”,是“正全国之道”(《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二),既可以事半功倍地御敌,也可以在防守中找到反攻机会,打击来犯之敌。这与偏爱进攻的孙子,未尝不可以形成互补。无论是疆防,还是海防,戚继光都非常重视情报。他甚至模仿孙子的相敌之法[27],提出了内容新颖的“海上相敌法”(《纪效新书》卷一八《水兵》篇)。这是戚继光基于时代变化而主动求变的具体表现。与《孙子》相比,戚继光在战术思想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当时明军已经拥有火炮、火铳等较为先进的热兵器,无论是对付蒙古族骑兵,还是对付倭寇,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就海上作战来说,明军的舰船也较为先进。为对付骑兵,明军还专门研制了狼筅、大棒等特别的兵器,结合快枪、鸟铳等远射火器杀伤敌人。所以戚继光战术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充分发挥武器方面的优势。第二,寻求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通过合理的战术编组和扎实训练,让士兵和武器之间及各种武器装备之间,形成良好的配合,尤其是冷热兵器有机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在战术改革方面,戚继光努力寻求车兵、骑兵、步兵和水师等多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他将车兵、骑兵和步兵合为一营,通过合理编组和严格训练,令骑兵、车兵和步兵只能紧密相依,步调一致,不发生“车前马后,马前车后之误”(《练兵实纪》卷一《练伍法》)。相比《孙子》,戚继光的兵种和战术,尤其是鸳鸯阵法等,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毛泽东对孙子兵学理论的改造力度更大。在名著《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他曾多次引用《孙子》,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曾经数次引用。对孙子“兵以诈立”的战争观,毛泽东也充分予以肯定。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主张采用各种方法欺骗敌人,狠狠批评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28]。毛泽东非常欣赏孙子的“示形之法”[29],对孙子的“治气”理论也表示高度认同。[30]毛泽东学习《孙子》,却从来不迷信,对其中精髓充分加以借鉴,对其中不足也大胆予以摈弃或改造。
《孙子》强调政治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认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谋攻篇》)。孙子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计篇》)通过“道”这一概念,孙子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希望统治者基于“修道而保法”(《孙子·形篇》)而达成“胜败之政”(《孙子·形篇》)。但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一个“令”字多少暴露出其统治阶级的本性。在孙子看来,平民百姓必须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统治者。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建设一支完全服务于人民、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从毛泽东1937年前后几封电报文稿中,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比如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31]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2]。他又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33]如果将这些论述与孙子进行对比,便可以立即见出高下。毛泽东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目光比孙子更为高远,对战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直至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关于作战方针,孙子主张的是速战速决,强调以合理之决策和突然之进攻达成战场上的速胜。孙子有一句名言:“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篇》)在孙子看来,如果战争拖得过久,就一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作战篇》)。通读十三篇,速胜是孙子的一贯主张。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与孙子主张速胜的理论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抗日救亡的危急时刻。其时,太过悲观的“亡国论”与盲目自信的“速胜论”交织在一起,一度让国人无所适从。毛泽东并未被当时极度流行的论调所左右,也成功摆脱了孙子“速胜论”的束缚,从而提出“持久作战”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个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34]在他看来,暂时的挫折并不影响大局:“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35]毛泽东的这些名言很快不胫而走,为中国抗战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最终以中国获胜日本战败而结束,《论持久战》的战争决策思想和科学预见等,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当然,对于孙子的速胜主张,毛泽东并非全盘否定。他认为,在战术和战斗中都应当集中优势兵力,努力达成速战速决。这与战略上的持久并不矛盾,相反,它正是在为战略上的持久创造条件。“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36]这些认识,无疑要比孙子的一味求速更加全面。
与速战速决主张相适应,孙子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孙子·谋攻篇》)的战法。如果实力不济,则需及时地或逃或避:“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孙子·谋攻篇》)毛泽东同样强调集中兵力,重视以优势兵力对敌。他说:“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37]与孙子相比较,毛泽东并不拘泥于“十”或“五”之类数字游戏,而是认为最低只要达成三倍于敌的优势,便可以寻找作战和歼敌之机。
中国革命力量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处于劣势,但毛泽东坚信,如果策略得当,是完全可以实现“以弱胜强”的。他的这一理念明显地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更加接近,与孙子“以镒称铢”(《孙子·形篇》)等主张似背道而驰。当力量处于相对弱势之时,毛泽东并非完全避敌不战,而是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大量开展运动战有效地调动敌人,以期造成局部的优势,再争取歼灭敌人的时机。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38]。仅从战法上打量,也要比孙子更加多样化。毛泽东基于其特有之大局观和辩证思维能力,从战略和战术的不同层面看待强弱问题,因此提出比孙子“十则围之”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战略思想及更加精彩而实用的作战之术。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39]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不同层面出发,客观看待敌我强弱和力量分合问题,无疑也比孙子更为深刻。
“穷寇勿追”也是孙子之名言[40],意在告诫将领注意敌人绝境中的反扑,防止在追击逃兵之时被反咬一口。毛泽东著名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虽是从中化出,却完全和孙子背道而驰。1949年,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追击阶段。蒋介石一面依靠长江天险积极布防,一面抛出“假和谈”等欺骗手段争取喘息之机。针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果断地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1]。毛泽东大胆舍弃孙子“穷寇勿追”的主张,果断下令对敌实施穷追猛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的迷梦,从而为中国革命赢得了一片新天地。
总之,《孙子》的历史影响存在多种路向。相比之下,就兵学发展而言,批评之声比溢美之词更有意义,更具价值。结合时代特点,对孙子兵学思想加以合理改造也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固然要承认《孙子》的不朽价值,但也不宜将其过于拔高,更不可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良方。
【注释】
[1]清代学者孙星衍在《孙子十家注·序》中说:“秦汉已来,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云‘撰为略解’……”详参《孙子十家注》,《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 页。
[2]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 页。
[3]详参熊剑平《日本的<孙子>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 期。
[4]李筌的《太白阴经》因为大量充斥占星、望气等内容,被张之洞斥为“荒诞”。参见张之洞《书目答问·子部·兵家》曰:“《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荒诞不经。”
[5]据《中国兵书知见录》记载,包括民国在内,历代存世兵书共计2308 部,明代则有777 部,加上明代存目兵书也有246 部,两者相加,有1000余部。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1 页。
[6]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 页。
[7]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 页。
[8](日)冈田武彦:《〈孙子兵法〉新解:王阳明兵学智慧的源头》,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 页。
[9]《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10]《孙子·谋攻篇》: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11]吴琪:《〈文心雕龙·辨骚〉“奇正转换”论》,《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 期。
[12]详参《荀子·议兵》。
[13]详参《战国策·楚策》。
[14]《东坡全集·孙武论下》:“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将)立毫芒之功,以借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15]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 页。
[16]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 页。
[17]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 页。
[18]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 页。
[19]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 页。
[20]郭化若:《孙子兵法之新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 页。
[21]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 页。
[22]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 页。
[23]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 页。
[24]关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十家论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 页。
[25]钮先钟:《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8 页。
[26]详见《潜书·全学》。
[27]详见《孙子兵法·行军篇》。
[28]《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2 页。
[29]毛泽东指出:“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详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3 页。
[30]1936年底,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对孙子的相关“治气”的字句进行了引用:“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详见《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09 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 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 页。
[3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 页。
[34]《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 页。
[3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6 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7 页。
[3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 页。
[38]《毛泽东军事文选》,总参谋部出版部1961年版,第91 页。
[3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46 页。
[40]《孙子·军争篇》。《十一家注本孙子》和《武经七书》均作“穷寇勿迫”。《四库》本等作“穷寇勿追”。参黄朴民《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 页。
[41]《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