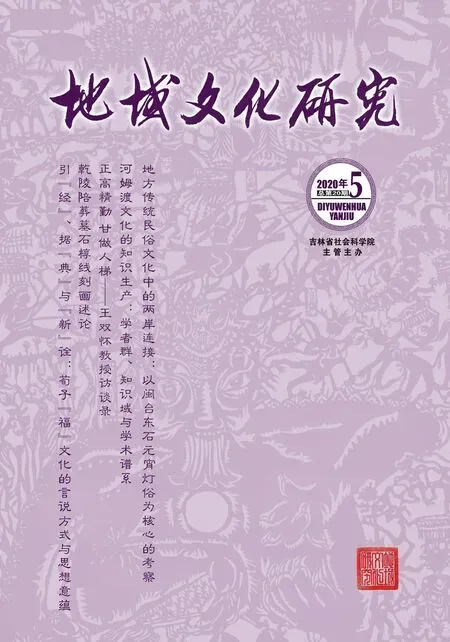宋辽金时期壁画墓及孝行图分布所见文化差异
2020-11-30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直接导致唐王朝走向式微的同时,也间接促成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与此同时,周边北方民族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在10 至13 的几个世纪中,契丹、女真等民族顺势兴起,先后成立强势的政权,与汉族政权两宋王朝相互对峙,民族的互动、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时代主题。处理好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契丹、女真等民族面临的一大难题,两民族相继建立政权后,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仍不忘保留自身的民族特色。过往史学界多通过史籍中的文字记载去观察这一时期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汉化现象,随着大量考古学材料的发现,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力图从丧葬的视角,从壁画墓及墓室壁画中的孝行图出发,重新思考契丹和女真的汉化问题。
一、契丹的汉化与壁画墓
于契丹民族而言,其面临的汉化环境比女真民族更为有利。早在唐代前中期,契丹就已经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产生较大影响,武则天时期发生的营州之乱,就是契丹为主参与其中,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东北亚格局和唐朝的历史①肖爱民、孟庆鑫:《略论契丹“营州之乱”对武周立嗣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面临藩镇割据,无力再对边疆地区有效经营,契丹乘机兴起成为漠北地区最为强大的势力。907年唐朝灭亡,五代时期来临,中原地区陷入政权轮替的局面,契丹的实力急剧扩大,于916年建国,国号辽(有过几次更改国号),并多次参与到中原地区事务中去,如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耶律德光领兵进入中原等等。北宋建立后,辽与北宋也多次发生冲突,直至澶渊之盟确立,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契丹族自活跃起,就与唐、五代、北宋有着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因而其对汉文化有着更多的接触与了解。契丹人的汉化,有着一个主动接受的过程,《新五代史》《辽史》等史籍中就有耶律阿保机重用汉人,实行汉制的记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8页。。从记载来看,契丹的汉化自辽太祖、太宗时期就已开始,其汉化程度,考古学上从丧葬方面就可以窥探。契丹人最初并没有筑墓埋葬的习俗,契丹早期的丧葬为“树葬”,文献中记载契丹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②(唐)李延寿:《北史》卷94《列传第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8页。。甚至于在立国后契丹人一度丧葬用棺也较少,其用棺习俗学自宋朝,宋代沈括曾经记载:“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③(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二》,摘自《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然而随着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契丹以皇帝贵族为首纷纷学习汉族葬制,出现了砖室墓,并装饰了壁画。这种现象在辽代早期考古材料中就有发现,著名的宝山1、2号辽墓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属于辽早期贵族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的砖石结构,墓室内绘壁画,有契丹人物、犬马、花卉、几案厅堂、高逸图、降真图、“寄锦图”、“颂经图”等,学界公认此两墓壁画具有浓郁的唐朝风格,吴玉贵先生曾对“寄锦图”、“颂经图”两图进行考释,认为颂经图应为“杨贵妃教鹦鹉图”,寄锦图为“苏若兰织寄廻文锦图”,两图有浓郁的唐人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等画家曾绘有此类作品⑤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文物》2001年第3期。。宝山1、2号辽墓的出现表明在辽早期,其汉化已初见成效,甚至连丧葬习俗都能从“树葬”转变为修建砖室墓并装饰壁画。
如果说以宝山1、2号墓为代表的辽早期壁画墓还是契丹民族囫囵吞枣式汉化成果的话,属于对唐风壁画直接采用,那么自辽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壁画墓,则已经形成了契丹民族的特色,如辽中期的床金沟5 号辽墓、陈国公主墓,辽晚期的滴水壶辽墓、库伦辽墓群等等,契丹人的日常生活场面出现在辽代墓室壁画中,壁画中的人物契丹人、汉人俱备,所从事活动极具辽地特色,其绘画风格已经脱离了唐风,融合民族特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虽然整体壁画特征与同时期的北宋一致,反映的是墓主个人日常生活,但于辽墓壁画而言,其反映的契丹人日常诸如宴饮、出行、放牧等等场景,与中原地区北宋墓室壁画中的汉人日常生活场景交相辉映,也表明至少自辽中期开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已经逐渐消化吸收,并融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别具一格。正如史籍中所记载,有辽一代实行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⑥(元)脱脱:《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总结下来,契丹民族是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基础上进而学习汉文化的汉化形式。
另一条考古学发现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点,墓葬中随葬金属面具或金属网络是契丹特有的葬俗,不见于其他民族,文献中记载“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有之也”①(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9,引(宋)文惟简《虏庭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页。。一些辽代墓葬在装饰壁画的同时,依然使用这种金属面具的葬俗,如陈国公主墓、解放营子辽墓等等。这表明,契丹民族的丧葬虽有一定规模的汉化,但葬俗方面仍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色。
考古发掘的契丹墓葬表明,从丧葬方面来看,契丹对汉式丧葬吸收内化后,学习了一些因素,例如砖室墓、长斜坡墓道、墓室壁画等等,同时保留了部分自身民族特色,例如金属面具和金属网络,因而这是一种有所取舍的汉化形式。
二、女真的汉化问题
女真民族的兴起速度堪称迅猛,1115年阿骨打起兵反辽,1125年灭辽,1126年靖康之变灭北宋,仅用十余年时间就连续灭亡了辽和北宋两大政权,统治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北方地区,其汉化环境与契丹相比较为不足。
一方面,契丹与汉文化的接触时间长,跨度大,如果从唐前中期的营州之乱开始算起,至澶渊之盟止约三百余年,经历了大半个唐朝、整个五代和北宋前期,女真与汉文化的接触时间短,时间上看约有几十年,交流较少,而且其接触更多地为部分汉化的契丹,与正宗汉文化代表的北宋接触较少。另一方面,辽与北宋在较短时间内被女真相继灭亡,其势力在女真兴起时期已相对弱势,继而建立的南宋偏安一隅,三者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对强势的女真民族影响力不足。
无论史籍记载如何,从考古学的墓葬上来看,女真民族在丧葬方面的汉化与契丹无法相比,不仅对砖室墓的继承没有契丹那么广泛,对墓室壁画这一装饰形式更是完全没有接受。
现今考古学发现的金代女真贵族墓葬,如齐国王墓②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为土圹石椁墓,墓葬为一“凸”字形土圹,内置石椁,石椁由石板拼成,石椁内有木棺,墓主齐国王夫妇葬于石椁内的木棺中。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为土圹砖椁墓。房山金陵M6,为石圹石椁竖穴墓。这些已经发现的金代贵族墓葬均未采取砖室墓的形式,依然使用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石椁。这表明女真贵族在丧葬上较为保守,与辽代贵族的丧葬相比,女真贵族无疑对汉式丧葬接受度不高。
金代壁画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北方地区,位于长城以北地区的材料寥寥无几,仅有朝阳李幹妻翟氏墓、朝阳马令墓、朝阳七道泉子金代壁画墓几例,这三座墓均为迁居当地的汉人壁画墓,壁画题材为汉式家居生活,与中原地区汉人壁画墓的题材一致,较具特色的是部分墓葬吸收了一些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如翟氏墓中随葬的铜面具③朝阳博物馆:《辽宁朝阳市金代纪年墓葬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3期。,就体现了契丹民族的文化因素,反映了丧葬上的民族融合的特点。金代壁画墓绝大多数位于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是传统的汉文化区域,这些地区的金代壁画墓与宋代壁画墓相比几无变化,墓主多为民间富裕地主或商人,壁画主题也延续了北宋晚期的墓主个人日常生活,除了部分壁画主题细节上和各类型题材占比的较小变化外,与北宋时期较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壁画墓分布的中心由河南地区转移到山西地区。金代,山西地区成为仿木构砖雕壁画墓的中心,砖雕精美复杂、繁缛华丽。在这些壁画墓中,有墓志、榜题、铭文砖的墓葬,其墓主均为汉人,其他由于各种因素,基本无法辨认族属,但结合已有发现大致可以推论,金代壁画墓的墓主均为汉人,从未有女真人。
综合来看,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至今为止发掘的女真人墓葬材料,从未发现有墓室壁画,砖室墓也较少。从丧葬方面来看,女真民族的汉化是不如契丹民族深入的。对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学习,女真人无疑是较为保守的。另一点有趣的发现可以侧面反应契丹的汉化程度,在河北地区发现了几座金代明确墓主身份的壁画墓,主要有萧仲恭墓和时立爱夫妇墓,《金史》中有两墓墓主的明确记载,两人的身份均为辽末金初时降金的辽朝官吏,并在金朝继续从仕。时立爱最终以“侍中、知枢密院事,加中书令”①(元)脱脱:《金史》卷78《列传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75-1777页。身份致仕,萧仲恭则在“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②(元)脱脱:《金史》卷82《列传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8-1850页。后去世。从记载来看,即使均为辽人,降金后的两人也都成了金朝高级官吏,虽然这一时期辽已灭亡,但在金朝继续生活的他们,墓葬形制上选择了辽代晚期的传统,采取了多室墓的形式,并装饰了壁画。由此可见契丹人汉化的深入程度,即使国家灭亡,已经生活于周围都是女真人的金代,但这些遗民仍然使用契丹汉化后的丧葬形式,不难看出契丹在丧葬方面的汉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三、辽金两代的汉化与孝行图
孝行图是宋元时期流行于中原北方地区的一种墓室壁画题材,大约兴起于北宋中晚期,盛行于金元两代,元末以后随着壁画墓的消失而消失。学界目前已对宋元时期孝行图的产生、流行等相关问题有过诸多探讨,胡志明③胡志明:《宋金墓葬孝子图像初探》,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邓菲④邓菲:《关于宋金墓葬中孝行图的思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邓菲:《图像的多重寓意——再论宋金墓葬中的孝子故事图》,《艺术探索》2017年第6期。等学者所做工作较为典型。从目前已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看,北宋中晚期,中原北方地区中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河南、山西两地开始大量出现孝行图,并逐渐扩展至陕西、山东等地,这种习俗一直流行至金元时期。
关于孝行图在宋代兴起流行的原因,从历史背景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赫赫炎宋,专以孝治”,北宋政府推崇孝道思想,孝治占有较大比重,鼓励提倡各种孝道行为。思想文化上,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在孝道上三教实现了交汇,都大力提倡孝行,民间信仰基本被囊括于三教之中。其他方面,北宋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广泛普及,平民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引领了文化世俗化的潮流,孝行体现了平民美好的祈愿。这是平民崛起后,汉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孝行图流行体现的是汉文化自身发展,那么其流行地域分布,反映的是汉文化影响力范围。从北宋中晚期兴起开始,孝行图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今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传统上汉文化强盛的中原北方地区,长城以北地区的壁画墓中基本不见孝行图。
至今为止发现了大批辽代壁画墓,但在其分布的主流地区——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这片契丹人壁画墓集中的区域几乎无孝行图出现。比较特殊的情况出现在辽宁中部地区,鞍山辽阳等地发现少量装饰孝行图图像的辽墓,主要有:鞍山汪家峪墓、鞍山苗圃墓、锦西大卧堡M1、锦西大卧堡M2、辽阳金厂村墓等等①部分学者对这批墓葬的年代认定具有争议,如方殿春认为这批墓葬应该属于金代,但证据并不充分。多数学者仍认为这批墓葬属于辽代。参见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这批墓葬的墓主一般认为是迁居当地的汉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原汉地流行的宴饮、乐舞、备宴等壁画题材,已经较多出现于辽代契丹人或汉人的壁画墓中,滥觞于北宋中晚期中原北方地区壁画墓中的孝行图却始终不见于辽代主流壁画墓中②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发现了斋堂壁画墓,其中有孝行图图像,简报发掘者认为墓葬属于辽代,但冯恩学先生、董新林先生均已指出,这座墓葬属于元代壁画墓。详情参见鲁琪、赵福生《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冯恩学《北京斋堂壁画墓的时代》,《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董新林《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美术研究》2013年第4期。,可以看出,契丹人对孝行图的认同度不高,进而对孝行图所代表的孝道文化似乎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文献记载中辽代的汉化一直广为人知,辽道宗曾有名言传于后世,“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③(宋)洪皓:《松漠纪闻》,摘自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8页。但在“修文物不异于中华”的背景下,辽境内契丹人壁画墓中基本不见同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孝行图,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观察契丹民族的汉化问题。正如辽道宗所言,契丹的汉化更多集中在“文物”方面,即所谓文玩珍奇、礼仪乐舞等等物质与制度方面,甚至于宗教方面的佛教也有接受,但在更高层次的思想层面,整体上并未接受很多。辽境内除契丹人外,还有大量汉人生活,但即使在汉人壁画墓中也未发现孝行图的身影。
步入金代,孝行图的流行范围仍没有较大突破,将金代墓室壁画放到金代版图上观察,根据孝行图的分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南北分界线。这条线西起今山西省北部,东至河北省南部,将金墓壁画南北分为两区(图一),整个金代,流行于南区的孝行图始终没能进入北区。需要特别表明的是,这条分界线西段在山西省内基本稳定,东段河北省内随着越来越多壁画墓的发现,这条分界线可能会南北移动,不过其东段大致不会超出现今的河北省内。申云艳、齐瑜两位学者在过往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条分界线,他们当时观察到的分界线尚在长城一带,到现在,更多墓葬材料的发现导致这条线已经南移至河北省南部,当时两位学者对这一现象并未深入讨论,只是分析为受全真教、理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④申云艳、齐瑜:《金代墓室壁画分区与内容分类试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结合宋代墓室壁画来看,对此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
结合金代壁画墓墓主身份来看,孝行图的这一分布基本为北宋中晚期汉人传统的延续,与金代女真人的丧葬习俗关系不大。文献中对女真的汉化有诸多记载,金朝政府对以孝行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十分推崇。金世宗完颜雍为帝时曾对左右言:“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⑤(元)脱脱:《金史》卷7《世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页。,“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渊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⑥(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页。,他还听取了大臣梁肃的提议,仿照汉代的羽林军都通晓《孝经》的事迹,将《孝经》赐予护卫人员。“肃奏:‘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①(元)脱脱:《金史》卷89《列传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4-1985页。金朝政府还推行多种奖励措施鼓励孝行行为,“三代同居孝义之家,委所属申覆朝廷,旌表门闾,仍免户下三年差发;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并委所属申覆朝廷官,支绢五匹、羊两羫,酒两瓶,以劝孝悌”②(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正·杂色仪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2页。。在种种倡导孝行的行为后,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实行这些措施的效果情况,不过从考古发现观察,金朝政府实行种种鼓励孝行的举措,最显而易见的是南区的墓室壁画题材延续了北宋中晚期的习俗,尤以孝行图传播流行更为广泛普及。而对于女真人来说,壁画墓这种汉文化葬俗都尚未接受,更遑论在墓葬中装饰孝行图像了。
因此,可以推断,女真人的汉化情况与契丹人相似,女真贵族更多垂涎于中原汉文化里丰富的物质文化及奢侈生活,在灭亡北宋后,女真人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并用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在文学等方面,女真民族学习较多,一些皇帝尚能吟诗作赋,但是女真人并未接受汉文化中的思想层面的观念及习俗,女真统治者之所以对孝行大力倡导,一是借助儒家思想教化人民,稳定社会形势。二是属于一种汉化过程中囫囵吞枣式的学习,这种倡导孝行的行为更多对中原地区的汉人影响较大。
《续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有关孝行的事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代人民对孝道的认知:
“张先生弥学,东阿人,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良辅之父。神道碑载其事。内座右铭云:‘欲求聪明,先当积学;欲求子孙,先当积孝。’世以为名言”③(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页。。
《金史》孝友传中列述了金代六名孝子的故事,这六人分别为温迪罕斡鲁补、陈颜、刘瑜、孟兴、王震、刘政④(元)脱脱:《金史》卷127《列传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5-2747页。,其中刘政的事迹较为知名,不仅见于《金史》,还载于《续夷坚志》中。从另一方面看,正史所载的六名孝子中女真人只有一位,汉族五人;而在宋代文献中,仅《宋史》孝友传所载就有孝子近六十余人⑤(元)脱脱:《宋史》卷456《列传第二百一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85-13416页。,还有大量笔记小说记载了更多的孝行故事。
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以推断,宋金两代,民间对孝行十分认同与推崇,这种认同主要是汉人为主,契丹人、女真人对孝行的接受程度从考古资料上看是不如汉人高的。因此可以认为,宋辽金时期的番汉文化分界线,具体化表现在考古上大致上是墓室壁画中孝行图分布的界线,长城一线与这条分界线大约重合。番,代指以契丹、女真民族为典型所创造的北方民族文化;汉,代指汉族代代相传所形成的汉文化。长城以北地区是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活动区域,长城以南地区属于传统上汉文化的势力范围。由于北方民族对汉文化学习程度的差异,契丹学得汉式壁画墓习俗,而女真则不见这种丧葬形式,也形成了契丹、女真人的墓葬中不见孝行图的现象。
结 语
从考古学上看,番汉文化分界线所反映的南北差异,主要表现在丧葬习俗上的巨大不同。宋辽时期,随着契丹对汉式丧葬学习的深入,南北双方壁画墓尚能交相辉映,各具特色,但到了金代,壁画墓在南区仅为北宋传统的延续,北区则基本不见。
南区壁画墓传统源远流长,发端于两汉,盛于隋唐,宋金元时期是其最后的辉煌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经历魏晋及五代的分裂时期,但这一传承并未断绝,一直延续。北区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等原因,多为以游牧或渔猎为生的北方民族活动范围,汉族中原王朝对北区的影响力略有不足,因而壁画墓在北区的流行情况取决于活跃在该地的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程度,学习汉文化较多的民族,则壁画墓习俗十分流行,以契丹为例,早期“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①(唐)李延寿:《北史》卷94《列传第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8页。,建立政权后,以皇帝和贵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士带领整个契丹民族广泛使用壁画墓的丧葬形式;反之则少见壁画墓,以女真最为典型,从建立政权兴起到金朝灭亡的始终,女真上自贵族下至平民其葬俗从未流行装饰壁画,“女真贵族墓流行‘类椁式墓’……尽管中晚期逐渐有‘类屋式墓’,但不见壁画等壁饰”②董新林:《长城以北地区金墓初探》,《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这条文化分界线基本以长城为界,所形成的南北两区是中国境内十分重要的一种分区方法,从更深层次的因素考虑,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尤其是气候因素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自然地理上中国境内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约正是长城一线,降水的多少形成了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貌上则表现为森林与草原。生活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为适应环境创造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长城一线也成了中国境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正如《辽史》中所言“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③(元)脱脱:《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辽史》中的这句话正是当时人们对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深刻认识,而这条文化界线也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