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社会学到社会学诗学
2020-11-28苑辉
苑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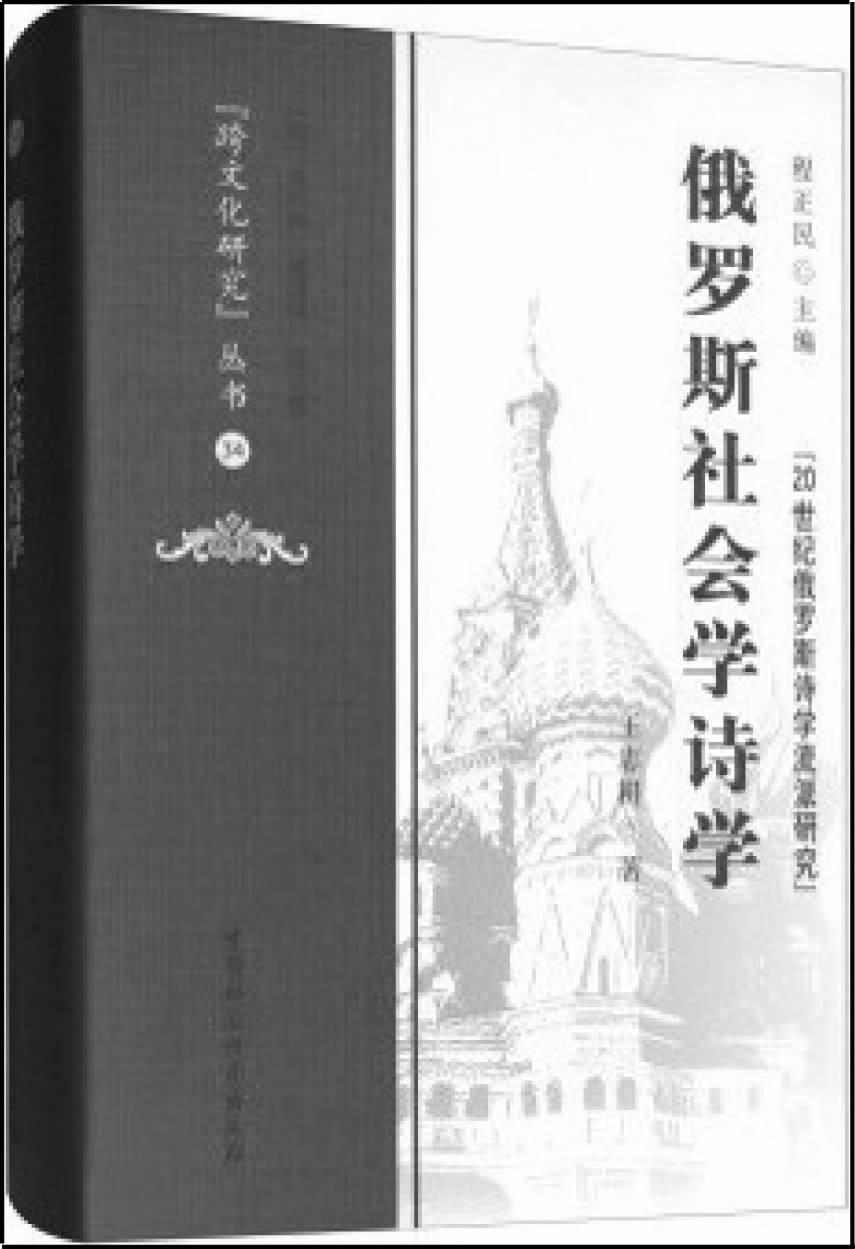
文学社会学批评是俄苏文学批评的主导话语,但由于部分庸俗社会学批评家从政治乃至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文学,使得文学社会学被污名化了。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巨大声誉,除了那些群星灿烂般的伟大作家,如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等之外,还有赖于起着推动、引导、对话、论争、诠释作用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社会学批评,除了19世纪三巨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之后的普列汉诺夫、巴赫金、卢那察尔斯基、赫拉普钦科以及各个时期较之文学创作的活跃度毫不逊色的批评界的“杂语喧哗”。因此,我们说,在俄罗斯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中一直存在着审美之维,存在着由社会学向诗学的转换,这也是其文学社会学批评在俄罗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王志耕的《俄罗斯社会学诗学》[1]在这一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由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为俄罗斯的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发展梳理出一个明确的脉络:从“自然派”的命名到“审美之维”的确立,从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出台,从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到文化诗学形态的形成。从这个脉络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只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一种崇高的艺术理想的追求。
一、从“自然派”命名到“审美之维”
对19世纪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误解源于那个时代对文学的实用性要求。
许多人都谈到,当社会变革无法通过政治渠道进行的时候,人们对文学就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文学来对民众加以启蒙,对沙皇政权起到反推的作用。如克鲁泡特金就说:“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俄国,文学批评是一条吐纳一般人政治思想的运河,五十年来它在俄国的发展和地位的重要,是各国所没有的。……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曾有一班不断接踵而起的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过极大而且极广极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力是任何其他各界中的小说家著作家所不能企及的。”[2]这种情况是从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之后就开始的,俄国军队中的知识分子随着亚历山大一世开赴西方,遭遇了一次伟大的“震惊”,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变革的愿望。恰达耶夫最先开始了对俄国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除了“野蛮的不开化”,就是残暴的统治。[3]35在这种境况下,俄国社会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即关于“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思想”[3]39。也就是说,恰达耶夫首先提出的诉求是思想的启蒙。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那是个渴求思想的时代,尽管这些人只是少数,但也正是这些少数人,看到了那些多数遭受压迫、穷困潦倒、没有文化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使他们感到愤怒,在个人内心充满无法忍受的负罪感”[4]222。
俄国的批评家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完成他们矫正文学创作方向的使命。别林斯基最先明确地要求文学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他在其费时最久写下的专门论述普希金的著作中,对主张艺术至上的普希金及其创作进行全新的解读,倡导新时代的诗人要为新的时代服务。他说:“一个诗人,如果他的诗并不是在他所属民族本身的生活土壤中生长的,他就不可能称作人民的诗人或者民族的诗人。除了鼠目寸光、精神猥琐的人之外,没有一个人会强要诗人必须去歌唱那赞美善行的颂歌,或者以讽刺挞伐罪恶;但是每一个聪明的人,都有权要求诗人的诗或者对时代的问题做出回答,或者至少对这些沉重的,无可解决的问题充满悲伤。”[5]386别林斯基在他晚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桩大家熟知的事,就是对“自然派”的命名,从而对他身后的俄国文学确立了一个思想的方向。先是保守派批评家布尔加林在1846年《北方蜜蜂》第22期的文章中对那些模仿现实的作品贬称为“自然派”,而把坚守艺术第一的创作倾向称为“修辞派”。但别林斯基趁机利用了这一称呼,对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作家直接以“自然派”命名,并大加赞赏:“自然派,今天已经站在俄国文学最重要的地位上;一方面,我一点不是因为什么偏私的迷恋,而把事情夸张,我们可以说,公众,就是说,大部分读者,都是支持它的:这是事实,而不是推测。”[6]563他認为,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从书本转向生活,从学校转向社会”[6]565。别林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拖着沉重的病躯,写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他对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表示不满的文章和书信,表达了他坚持文学要为俄罗斯现实社会服务的信念。
也正是因为别林斯基等批评家的这一立场,使得我们一直以为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不讲艺术性,只讲人民性、社会性、现实性。但我们应当看到,19世纪也是俄国文学的自觉意识产生的时代,尽管整个社会对文学充满了“思想”的要求,但文学从来也没有失去对艺术的追求。人们常常把普希金的诗句当作诗人自由的宣言:“诗人啊,请不要重视世人的爱好,热狂的赞誉不过是瞬息的闹声;你将听到蠢人的指责,社会的冷嘲,可是坚持下去吧,你要沉着而平静。你是帝王:在自由之路上自行其是,任随自由的心灵引你到什么地方;请致力于完善你珍爱的思想果实,也不必为你高贵的业绩索取报偿。”[7]虽然,包括普希金的类似观点以及接下来的唯美主义倾向受到了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家的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批评都是庸俗化的,仅仅将文学视为某种社会宣言。
我们还以别林斯基为例。一般认为,早期的别林斯基是受到黑格尔、谢林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而产生了某种唯美主义理念,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对艺术性的要求并不逊于对社会性的要求。但即使是晚期,当他发生了对其早年观点的“一种彻底和痛苦的批判”[4]231之后,仍然对文学创作的艺术标准有明确的诠释。比如,在上面我们提到的论普希金的著作中,他随时都在强调普希金首先是一个具有高超艺术水准的诗人:“普希金所以是伟大的诗人是在于:他通过一些生动而优美的现象把自己的诗的观照具体化了,而不是在于他想要成为一个思想家和问题的解决者。”[5]386也就是说,作家或诗人首先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艺术品,而不是成为政论作品,才能成就艺术的伟大。当然,仅仅追求形式的唯美也许是缘木求鱼,艺术本身因为负有更高的使命而成为伟大的艺术。所以,别林斯基说:“艺术本身的利益不能不让位于人类更重要的利益,艺术高贵地承担起为这些利益服务的担子,成为它们的发言人。然而它丝毫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艺术,而只不过是取得新的特征。”[6]596-597因此,我们看待别林斯基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不能忘掉,黑格尔的哲学渗透在别林斯基的全部思想之中,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一直坚守着辩证法的观念。如王志耕在《俄罗斯社会学诗学》中评价的:“艺术如果仅仅为社会而存在,反而无法达成对社会的作用;艺术只有首先成为艺术,才能成为为社会服务的艺术。这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的社会性了。”[1]35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19世纪俄国的文学社会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学观,尽管这种美学观因为创造者思想的不成熟而存在许多漏洞,但不妨碍它仍然是在美学的框架内展开的。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即生活”的命题,还应当注意到,他对美的生活的理解是“应当如此的生活”。他说:“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8]所以,王志耕将其称为“社会学批评的审美之维”是有道理的,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那一时期文学社会学“文学”的一面。
二、从庸俗社会学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如前所述,苏联时期的文学社会学的名声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出现而受到影响,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学被置于政治、经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忽略了在整个苏联时期,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也是文学社会学批评的一贯主张。
以赛亚·伯林如此博学,仍然偏执地看待俄国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他说:“这种批评,对生活与艺术的界线故意不予过分清楚画出;对艺术形式与人物角色、对作者的个人特质与小说内容,评者自由发抒其褒贬、爱恨、钦佩与鄙薄;以上种种态度所动用的标准,无论为有意的或含蓄的动用,都与判断或描述日常生活里活生生人类的标准相同。”[9]不错,这种由别林斯基所开创的批评模式在20世纪初期的形式主义批评失势之后,一度占据苏联批评界的主流话语位置,并且在此后同样遭受到批判之后,仍然在后来的批评中时有显现。如苏联学者所说:“庸俗社会学派的残余的生命力是相当顽强的。分析或批判地评价一部艺术作品是一件复杂而又细致的事情。在作者的理论观点没有经过准确的检验,而被研究的对象的特性又没有经过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会为形形色色的庸俗化创造良好的土壤。”[10]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是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文坛上也出现了许多出色的文学社会学批评著作。这其中包括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初版)、古德济的《托尔斯泰评传》(1939)、布拉果依的一系列论古典作家的著述以及仍然保持批评活跃度、转向社会学批评的形式主义者们的著述等。在这些著作中,巴赫金的文字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它融合了社会学批评、文化批评和形式批评,成为一种程正民先生所说的“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历史和结构相结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贯通”的整体诗学。[11]而巴赫金的这些著述,包括他后来发表的关于拉伯雷与中世纪民间文化的巨著,也主要是在庸俗社会学还有广泛市场的30年代完成的。
其实,就庸俗社会学批评而言,这也是一个标签化的命名。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类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文化现象,很难将其与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割裂开来,它们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以何种程度为限,本来就是一个十分主观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细读这些所谓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著述时,可以发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庸俗不堪”,而是如王志耕在《俄罗斯社会学诗学》中所论述的,庸俗社会学既有其内在矛盾,却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比如,对文学文本的阶级分析,本来文学叙事要关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形式的奴役关系,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今天的后殖民理论框架内来审视这个问题,它的合理性就越发凸显出来。“在后殖民理论发展到不仅关注殖民话语霸权、也要关注解殖后阶级控制问题的今天,弗里契对文学的阶级分析,适足以提醒我们关注艺术内容中的权力运作规律。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透进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而隶属于特定话语权力,这正是艺术批判所要揭示的根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批判的层面上,也正是要揭示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及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渗透,而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利益权力的作用对艺术的影响。”[1]273-274由此可见,任何标签化的认识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下加以重新解读。
在苏联文坛二三十年代经过形式主义、庸俗社会学的双重批判,促成了后来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出台,这一概念也由此带有官方制定色彩而备受诟病。同样,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也应该先行“去蔽”,把标签拿掉,用今天的社会学诗学的整体性来衡量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面。所谓“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12],我们如果把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一词去掉,这一原则在结构上不过就是亚里士多德说法的翻版:“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3]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规则没有问题,至于是否符合“革命”的要求则是一个变量条件,不同的时代会对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做出不同的解读。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第二条,“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同样的道理,艺术的教诲功能毋庸置疑,至于如何来艺术地实现这种功能也是一个变量条件。你可以通过强制的说教来进行教诲,但如果这种方式不被读者接受,则谈不上功能的实现。因此,它还要求“艺术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当然,如果一部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它的艺术性也就与教诲功能结合起来了。所以,王志耕指出:“如果我们把它仅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来看,应当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指称的内容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解并无根本差异。”[1]292我们回顾苏联时期的文学创作,尽管出现了相当多的按照“无冲突论”原则以及官方“定制”要求写出来的作品,但同时也出现了像《静静的顿河》这样世界一流的巨著以及普里什文、特瓦尔多夫斯基、帕乌斯托夫斯基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此外,当我们认为像布尔加科夫、帕斯捷爾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重量级作家并非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也能创作出一流作品的时候,也就说明,在苏联文坛上,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艺术标准的遵守。
三、从人道主义回归文化诗学
在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坛迎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这时我们看到,他们掀起的第一波思潮是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成为俄罗斯文学社会学批评向社会学诗学或文化诗学转型的一个前奏。
我们说,文学是人学,尽管这并非高尔基的原话[14],但这的确是一种揭示文学实质的说法。文学既可以理解为人类理想生活的重构,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类个体的生存权利的辩词,缺少了后一种理解,则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其真正的文化价值。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对“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反复论述,却没有在“人道主义”(humanism)这一概念的本义上进行过讨论,尽管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已经体现了对作为个体的人尤其是小人物的关注。当然,这也说明了文学创作相对于文学批评的自律性,但在文学批评自身的自律性中,也不能缺少了人道主义的内核,或者说文学本质的内核。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文学报》主编留里科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光荣而高尚的人道主义使命是被付托给先进的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我们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的精神丰富和纯洁、反对野蛮和腐败、反对人格的堕落而斗争的。”[15]249这就为此后的人道主义讨论奠定了一个基调,就是赞美个人的幸福权利和否定人格的堕落。而更重要的是,在此后的讨论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个是将“党性”转换为“人性”。在上述留里科夫的讲话中,他对过去加在文学标准上的“党性”做了新的解释,即党性就是“深刻、宽广、思想的明确性、高尚、人性”[15]237。用《俄罗斯社会学诗学》中的话说:“这样,就把党性引到人性的层面上来了,也就为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对更多个人化的人性描写打下了一个理论上的基础。”[1]373另外一个转向是将“人民性”转换为“个性”。人民性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别林斯基时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将俄国文学从古典主义的贵族性中解放了出来,因此,这个概念中包含着明确的平等观念和底层意识。但这一概念在苏联时期往往被替代为“集体性”,从而剔除“个体性”或者“个性”的内容,在新的语境之下,“人民性”概念的积极意义变为压抑个性的一种说辞。因此,明确人民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并将个性视为人民性的起点,在整体的文学观念中十分重要。美学家包列夫的话说明了这种转向的重要意义:“社会上,人的发展、人的不断成长应当为了人,而社会的发展应当通过人而为了个人——在这种人与人类的辩证法中有着最高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审美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应为实现这些理想并将其切实贯彻到生活里去而努力。”[16]不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所有的艺术形式,其真正的本质都是对人的,尤其是对个体的、弱势的人的负责。或者如布罗夫所说的:“人道主义,是崇高的艺术的活命之水,是艺术存在的条件。”[17]
正因为有了将人道主义引入文学社会学批评的过程,才导致了20世纪后期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批评界的文化诗学转向。所谓文化诗学,就是将人的总体生存境况纳入文学视野中,来考察每一个个体的微生态的研究。因此,文化诗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整合性,而在价值论上强调的是个体性、异质性、边缘性。如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宗教意识的复活,其根本指向是个体精神的复活,通过个体精神的复活达到文化的更新。如王志耕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重建文学研究的传统宗教文化之维,与以往的社会学批评中的社会意义诉求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试图通过以文学形式唤醒人们的现实改造意识来达到最终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前者则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宗教内省意识来达到改善现实生活的目的。”[1]452而文化诗学中的文化批判,则一方面以个性化的修辞方式来表达解构性的后现代观念,另一方面揭示当代社会的“悖谬逻辑”(паралогия)和“历史创伤”(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равма),以寓言化批评方式来讲述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社会学批评,尽管已经失去了它的称名,但这种批评模式却内在地嵌入了当代的文化批评话语之中,只要文学仍然是人类生活的镜像,或者说,只要文学是由社会的人来写作的,那么,这种批评模式就将长久地存在下去。”[1]458
注释
[1]王志耕.俄罗斯社会学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俄]克鲁泡特金.俄国的批评文学[J].泽民译.《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10):1.
[3][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M].刘文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4][英]以塞亚·伯林.艺术的责任[A].现实感[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A].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C].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6][俄]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一篇)[A].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C].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俄]亚历山大·普希金.致诗人[A].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C].查良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329.
[8][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
[9][英]以塞亚·伯林.辉煌的十年[A].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43.
[10][俄]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斗争[A].回顾与反思——二三十年代苏联美学思想[C].盛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18.
[11]程正民.巴赫金的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
[12]苏联作家协会章程[A].周扬译.苏联文学艺术问题[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5.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8.
[14]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刘保端.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J].新文学论丛,1980(1).
[15][俄]留里科夫.苏联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A].刘辽逸译.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上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16][俄]包列夫.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A].江劲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下册)[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201.
[17][俄]布羅夫.艺术的审美实质[M].高叔眉,冯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43.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