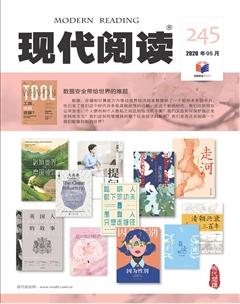丁玲:今生有缘无分,唯愿各自安好
2020-11-28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著作《梦珂》《韦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关于丁玲与瞿秋白之间情感状况的猜测,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提到瞿秋白在给她的信中说“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而丁玲又曾说,完整的这一句是:“只有天上的梦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资格批评他。” “梦可”是瞿秋白对妻子王剑虹的昵称:而“冰之”正是丁玲的字……这半句,似乎补上了丁玲与瞿秋白二人情感拼图的最后一片空白。
少女时代的丁玲兴趣广泛,涉猎颇多,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越发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清秀,已经成为湖南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其间,丁玲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王剑虹。1919年,“五四”运动如一声惊雷,划破了阴沉、晦暗的天空,沸腾了无数学子的热血。王剑虹很快以出众的口才和影响力成了全校学生中的领头人物。此时,丁玲已经和王剑虹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丁玲和王剑虹、王一等人带着一腔热血,上街游行、演讲,希望借此唤醒更多人。
丁玲越发向往和平、民主的新世界,胸膛里激荡着热血,笔下流淌着激情。那时,丁玲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剪掉了长发。一时之间,各种异样的眼光投来,有赞赏、欣羡,亦不乏惊讶、鄙夷、排斥……凡此种种,丁玲并未放在心上。
此时的丁玲,不仅相貌出众,更是满腹诗词学问,很快成为学校平民夜校的老师。丁玲年纪虽小,却充满热忱,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为“崽崽先生”。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这年暑假后,丁玲便转到了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入学后,由于聪颖好学,丁玲很快受到国文教员陈启民的青睐,陈引导丁玲阅读了大量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如《新青年》等。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陈启民被学校解聘了。丁玲悲愤之余,将书本撕得粉碎,不肯再踏入周南女子中学的校门。
时隔不久,辍学在家的丁玲便规划好了自己的前途,准备到上海平民女學就读。
对于这段往事,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中曾有详细描绘:“大约是1921年吧,上海出现了一个平民女学,以半工半读为号召。那时候,正当‘五四运动把青年们从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唤醒了,‘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地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的理想的生活来了,上海平民女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叛逆的青年女性。我们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学的学生。”
彼时,丁玲最好的朋友王剑虹正在上海平民女学就读。王剑虹也不失时机地邀请丁玲一起到上海平民女学学习。丁玲不胜欢喜,心中暗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上海。
现实往往是冷酷的。丁玲很快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舅舅听闻此事后,十分震怒。母亲一直鼓励丁玲求学上进,在舅舅看来,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不需要读太多书。然而丁玲毕竟不是自己的女儿,且不需要自己供给一应费用,所以舅舅以往并未阻止丁玲求学。
其实,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也是存有一种私心。舅舅的儿子与丁玲青梅竹马,年纪相当,二人从小一起玩耍。外婆便为二人定下了“娃娃亲”。如今,丁玲一年比一年出落得端庄,五官似有雕琢之美,且丁玲读书多年,眼界、谈吐也远非寻常女孩可比。舅舅便想将丁玲许配给自己的儿子。
为免夜长梦多,舅舅命丁玲半年后便与表哥结婚。因为再过半年,丁玲刚好毕业。
知道舅舅的想法后,丁玲大为震惊。一直以来,丁玲对表哥只有兄妹之谊,并无男女之爱。丁玲对舅舅的决定十分不解,更难接受。一连数日,家中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家庭大战中,母亲是和丁玲站在同一战线的。
母亲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心知丁玲思想叛逆,读了这么多年书,越发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是绝不会屈就于包办婚姻的。母亲断定,若女儿一朝嫁人,必定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僵持了数日,舅舅方明白此事难成,愤慨之余,无奈地放弃了这一念头。丁玲终于摆脱了这场包办婚姻,心中如释重负。仿佛一片广阔天地展现在眼前,丁玲又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
再过半年,丁玲才能顺利毕业,并拿到文凭。然而,丁玲等不了那么久了。向来爽朗的丁玲轻易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决心去上海闯荡。舅舅虽一直想亲上加亲,让丁玲做儿媳,却从未真正表露心迹。自那日舅舅将一切言明,丁玲与表哥皆尴尬不已。同处一个屋檐下,进进出出,低眉抬眼间,偶然撞到对方的目光和身影,丁玲不由慌张闪躲,表哥也无法神色自若。表兄妹间一时尴尬、生疏起来。
一想到这一层,丁玲越发对上海充满了向往之意。
1922年,丁玲来到上海,虽然她在上海没有一个亲戚可以投靠,除了王剑虹,也没有相熟的朋友,但凭借独立、坚强的个性,加上王剑虹的帮助,丁玲顺利在上海安顿了下来,并如愿进入陈独秀和李达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
丁玲外表端庄文雅,内心却向来有叛逆的一面,从此以“冰之”为名,废去了“蒋”姓,以示对封建传统的蔑视。这是继剪发后,又一大胆的举措。后因“冰之”二字,称呼起来略有不便,便选了一个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作为姓氏,以“丁冰之”自称。
“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丁玲入读上海平民女学仅半年后,一切戛然而止。上海平民女学在办学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以至于难以为继。渐渐地,学生们各寻出路,偌大的校园,很快空了大半。丁玲再次与王剑虹商量,二人思忖一番后,决定离开上海,到南京闯荡。
到达南京后,丁玲和王剑虹吃住在一处,每日勤奋自学,互相督促功课,彼此都进步很快。
转眼到了第二年。丁玲和王剑虹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瞿秋白。此时,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周身散发出一种进步知识青年所特有的气息,见闻广博,谈吐不俗。三人一见如故。渐渐地,瞿秋白成了丁玲和王剑虹“家”的常客。二人居住的地方虽然略显简陋,却打扫得十分整洁,满桌书籍文章,令瞿秋白不禁对丁玲和王剑虹刮目相看。
三人相聚一处,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瞿秋白常与丁玲、王剑虹畅谈文学,谈人生,也谈社会时事。不知不觉间,时间飞逝,窗外已是日落黄昏,三人便一起出门到街边吃馄饨。有一次,吃饭时,瞿秋白询问二人今后的打算,丁玲略微一怔,王剑虹手中的筷子也停顿下来。
时间过得很快,丁玲和王剑虹早已习惯了南京的生活,习惯了这里的长街窄巷,街边的小吃。至于今后,二人心中尚未有规划。此时听瞿秋白提起,丁玲和王剑虹才感到南京并非长久之地。
时隔不久,瞿秋白就离开了南京。丁玲和王剑虹心中不由一阵怅惘,少了一个可以谈心和互诉衷肠的朋友。一连几天,丁玲心中空落落的。丁玲对感情后知后觉,此时才发觉自己已经对瞿秋白生出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愫。
此时的南京,在丁玲眼里,已物是人非。没有了瞿秋白的南京,便是一座空城。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而瞿秋白正是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乱世之中,能再次相见,三人皆不胜欢喜。丁玲见到瞿秋白,虽满腹情思,却不曾倾吐半句。三人还像以往一样,经常相聚一处,畅谈诗词歌赋,慨叹世事磋磨。
丁玲和王剑虹很快适应了新的校园生活。在上海大学的时光,同样是充实而快乐的。更令丁玲惊喜的是,她还在上海大学见到了一些曾经的师生。陈望道在此担任教务长,自己一直仰慕的茅盾也在上海大学教授小说研究。再次入学,丁玲愈加勤奋,每日忙于功课。
一日,丁玲偶然在王剑虹处看到一沓诗稿,少女情思,跃然纸上。丁玲手握诗稿,不由一阵眩晕。此时她才明白,一直以来,钟情于瞿秋白者,并非只有自己一人,王剑虹同样深爱着瞿秋白。一个是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钟情的男子。一时之间,丁玲不知如何是好。
这件事令丁玲内心格外颓唐、沮丧,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一直倾慕瞿秋白,只是羞于表明心迹,不想王剑虹也是如此。二人果然是至交知己,秉性相近,爱上同一人,怀着同样的心事。
丁玲细细回想着,揣测王剑虹是何时对瞿秋白生出好感的,却茫无头绪。正在自己犹豫不定时,王剑虹向丁玲表示要回四川老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丁玲不由方寸大乱。一直以来,她早已习惯了和王剑虹相依相伴,一想到这样的時光就要戛然终止,丁玲内心先彷徨起来。
一时之间,丁玲顾不上二人与瞿秋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愫,决定先设法使王剑虹留下来。王剑虹并不知道丁玲已看过自己的诗稿,此番回四川老家,内心已决定要挥剑断情。
在丁玲心中,王剑虹是世上最好的人。丁玲不想与王剑虹分离,更不希望王剑虹带着满腹深情和心事与瞿秋白天各一方。王剑虹和丁玲一样,都是内里情思澎湃,外表不显露分毫的人。王剑虹虽然是果敢的女子,在感情上却格外含蓄。相比之下,丁玲更豪爽一些。丁玲再三思忖后,觉得应该让瞿秋白明白王剑虹的心迹,令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可以使王剑虹顺理成章地留在上海。
丁玲当下拿着王剑虹的诗稿找到瞿秋白。瞿秋白看到诗文中流露出的真挚而炽烈的感情时,惊问诗文是何人所写。得知是王剑虹的手笔后,心中越发惊讶,不由恍惚,一时无话。半晌,瞿秋白才醒转过来,询问丁玲的看法。
丁玲从瞿秋白的眼眸中读出一种难言的深情。原来一直以来,自己并非单相思,瞿秋白亦对自己有意。
丁玲踌躇了一番,仍决定成人之美,便坦荡、自然地表示自己年纪尚轻,暂时不想考虑爱情与婚姻;又说起王剑虹的种种好处,希望瞿秋白能与王剑虹结为伴侣。
瞿秋白沉默了。他走向丁玲,轻轻握了下丁玲的手,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安慰,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瞿秋白顺应了丁玲的意愿。
瞿秋白和王剑虹由此走到了一起。王剑虹自是喜不自胜,打消了回四川老家的念头。她沉浸在与瞿秋白的二人世界中,对于丁玲所作出的牺牲毫不知情。
在王剑虹饱受单相思的煎熬,决定回老家时,丁玲极力促成了这一对佳侣。但二人真正在一起后,每日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衬托得丁玲形单影只,他俩与丁玲相伴的时光也少了许多。
原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瞿秋白不仅知识渊博,且教授技巧娴熟,很快便使丁玲和王剑虹初步掌握了俄语。如此一来,二人便可以更好地阅读俄罗斯文学,领会普希金诗歌的美妙之处。
在瞿秋白心中,丁玲和王剑虹都是心思玲珑、文采斐然的女子,尤其是丁玲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瞿秋白希望丁玲日后能走上文学之路,“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对于丁玲,瞿秋白无疑是寄予厚望的。在瞿秋白的鼓励和期望下,丁玲对未知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并且一直为此暗暗努力。
如今,三人相聚在一处的时光少了许多。
1923年夏天,丁玲度过了人生中一段低落的时光。转眼到了冬天。天气晴好时,丁玲偶尔也会和王剑虹、瞿秋白相聚一处,畅谈文学和诗歌。是年冬天,王剑虹和瞿秋白结为伉俪。对于这一天,王剑虹期待已久。
这桩美满的姻缘,得益于丁玲的撮合。丁玲暗暗告诫自己:从此之后,一切便只能深埋在心底了。那一腔不为人知的深情,一段无法言说的爱意,今生再也无法言说,也不必再言说。
丁玲深知,瞿秋白是谦谦君子,既与王剑虹结为秦晋之好,便不会再对自己存有怜惜之意,心中不由对瞿秋白又多了几分敬重。她告诉自己:人生路漫漫,难免与一二知己擦肩而过。今生有缘无分,唯愿各自安好。
王剑虹结婚后,便搬了出去,不再与丁玲同住。
但当听闻瞿秋白生病了,丁玲还是带着瞿秋白最喜欢吃的点心、水果,来看望他。几日不见,瞿秋白清瘦了许多,王剑虹也是满面愁容。丁玲的内心有微微的痛楚,却面色如常,如寻常朋友一般,关切地询问了几句。王剑虹不时替瞿秋白应答几句,神色间略显不自然。丁玲捕捉到王剑虹愧疚、尴尬的神色,猜知王剑虹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和瞿秋白之间曾经有过的一段朦胧的情愫。
原本以为,一切会被岁月深深湮没,不想王剑虹还是知道了。可丁玲并不想打扰王剑虹的幸福。
彼时,丁玲人虽还坐在王剑虹和瞿秋白家中,却已暗下决心要离开上海。如此一来,王剑虹便不会对自己心生芥蒂。自己和王剑虹的友情,王剑虹和瞿秋白的爱情,便都可以保全。
丁玲在王剑虹和瞿秋白家中又坐了片刻,叮嘱瞿秋白按时服药,要多休息,便离开了。王剑虹送出门来,丁玲对王剑虹提起自己打算离开上海的念头,王剑虹吃了一惊,劝说丁玲留下来,然丁玲去意已定。
世事如沧海桑田多变幻。对丁玲而言,此时的上海,早已不是自己当初满怀期待和憧憬的热土。世事蹉磨,她的爱情之花,未及盛开,便无声地凋落,永远埋葬在此地。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丁玲传:历尽磨难,一生灿烂》 作者:张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