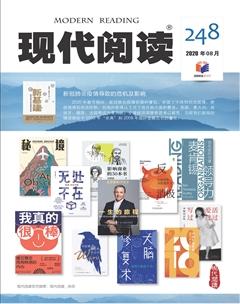加纳:黄金像萝卜一样生长的国家
2020-11-28
大约在公元951年,波斯地理学家伊斯泰赫里断定摩洛哥的西吉尔马萨离一处金矿不远。他补充道,“据说没有任何一座金矿比这儿更大、金子比这里更纯净”,而且“通往这座金矿的道路异常艰难”。如果说跨撒哈拉贸易的事实削弱了第二句断言的可信度,因为黄金正是通过跨撒哈拉贸易被运往萨赫勒,那么金矿的情况的确存在疑点——西吉尔马萨城附近并没有金矿。即使到了10世纪中期,这位地理学家获得的信息还是有误。半个世纪之前,雅库比已经能够确定金矿位于撒哈拉沙漠另一端的加纳王国之中。进一步来说,即使没有根据,但更加真实的情况是,非洲王国加纳所在的毛里塔尼亚南部地区也没有金矿。地理学家混淆了黄金的生产地和购买地,后者总是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信息提供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更多关于金矿的情况了。15世纪中叶,一位热那亚商人,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位前往撒哈拉的拉丁天主教徒安东尼奥.马尔方特,他的穆斯林庇护人在回答他黄金来自哪里的问题时,这样说道:“我在黑人国家中居住了14年,从来没有听过谁能够笃定地说:‘我可以作证,我们就是这样找到并采集黄金的。”虽然这个人也是一位商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对对方撒谎,但我们可以确信一点: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旅行家或者地理家能够得到更为确切的情况,只能确定沙漠驼队所到达的黑人贸易国家不产黄金,黄金来自更远的地方。
采摘黄金的神奇传说让黄金的来源地越发地扑朔迷离。10世纪初,一位作家写道:“加纳王国中的黄金就像是植物一样从沙地中长出来,就像胡萝卜一样,人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采集。”14世纪中叶,开罗王宫主管大臣尤马里一板一眼地记录下了他的听闻。人们采集的黄金作物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在春天,在雨季结束的时候从沙漠中长出来:叶子长得像四季青,根部是黄金;而第二种黄金作物一整年都生长着;人们翻凿土地,获得状似石子和沙砾的黄金根。”诸如此类的故事编织出一幅由非洲掌权者和西非穆斯林所维护的人造传说图景,告诉北非贸易伙伴金矿的位置,用来哄骗他们,防止他们直接开采金矿,从而对金矿进行控制。这幅图景的主要目的是引发好奇心,此外,毋庸置疑,如果撒哈拉沙漠政权只比北部贸易伙伴多知道一点黄金矿脉的消息,他们绝不可能直接掌控矿区的開采权,也不可能对黄金开采产生更多影响。让我们看一看尤马里关于这个话题还写了什么吧:每年,人们从马里把在黄金国中采集的黄色金属果实带给素丹;素丹还与黄金国签署了一份友好协约。“如果素丹想要黄金,就得服从规定。但这个国家的国王贸然尝试过,如果他们占领任何一座黄金城市,在其中大行伊斯兰教的话,黄金只会不断减少直到荡然无存……因此,这些国王任由异教徒掌控黄金国,服从规定,交纳商定的黄金税赋。”外交斡旋无能为力。可以说,出产黄金的撒哈拉政权与他们名义上的政治君主一样,双方了解的黄金情况都是间接的。
我们不禁问道,既然黄金的开采地点不仅仅不为购买者所知,而且对供货商来说也难以捉摸,而且黄金开采似乎并没有被完全掌控,那么这种贵金属的商业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首要的原因是,伊斯兰商人在撒哈拉边界遇到的那些供货商同样是中间商人。他们有一个名字:万加拉人。万加拉人起初是撒哈拉边界的一个族群,几个世纪之后他们一跃成为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专业团体,遍布西非各地。他们曾被赋予各种名字,如今他们被称作迪乌拉人。万加拉人形成了一个流动商业网,这些流动商贩是不知疲倦的行者。伊斯兰商人走出沙漠时,在加纳或马里市场上——两个对称的商业网之间的联络点——遇到的人可能正是万加拉人。
从阿拉伯作家记述的时而混乱的材料中可以推断出,万加拉人定居在尼日尔河的岸边,他们的住处在所谓的内三角洲(每年洪水期间,湖泊、支流以及被淹没的水塘交汇形成的水域网络)方向上,或是在尼日尔河和巴尼河之间全部的“河间”区域,该地区可能更加符合史料中记载的“岛屿”这一名称。不过该地不出产黄金。主要的大型矿脉位于塞内加尔河及其支流法莱梅河之间的班布克、上塞内加尔和上尼日尔之间的布雷、上沃尔塔地区(布基纳法索旧称)的洛比以及位于尼日尔的锡尔巴河谷,这些矿脉勾勒出万加拉“网”在热带大草原上活动区域的边界。这个区域网细密地覆盖了大大小小的矿区,或者说以一处枯竭后紧接着开采下一处矿区的方式覆盖所有矿区,他们通过如毛细血管般的渠道将黄金输送至二级市场,其后再由流动商贩将黄金送往撒哈拉沙漠中各王国的城市中。因此并不是这些国家在统筹黄金贸易,况且他们在矿脉地区只有微弱的干预能力。并不是黄金贸易国购买其南部的黄金再转卖到北部,而是中间国建立了两种贸易系统,并使交易安全且公正地进行。中间国赚取的不是差价,比如购买贵金属矿产再将其卖出,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来自收取过境商品的税费,比如来自这边的黄金,或是另一边的盐。
这种两个陌生世界的遥远关系,是一天或者一个短暂季度的合作关系,双方不清楚对方是来自哪个世界的中间人,这种关系也是层层嵌套的,那个时代的作家试图明白它的交易方式。比如10世纪中叶的麦斯欧迪这样解释道:“他们(拥有黄金的黑人)有一条分界线,来他们国家进行交易的人无法跨越这条界线。带着商品的商人一直走到这条界线之前,把他们的货物和衣服放在这里,然后退下。而苏丹人拿着黄金上前来,在商品旁边放下一定数量的黄金,随后退下。如果商人认可的话,他们会再次上前,如果不满意的话,他们便离开。然后,苏丹人回来再加注黄金直到成交。”或者像雅谷特在13世纪初所叙述的:“精疲力竭的驼队终于走到与黄金主人见面的地点。到达附近时,商人便开始敲打随身携带的大鼓。鼓声一直传达到另一方耳中……当商人意识到有人听到他们的鼓声时,他们便摆开各人所带的货物……随后便退回营地。苏丹人带着黄金来到这里,在每个商品旁边放下一定量的黄金然后退回去。商人再次上前,拿走苏丹人放在他们商品旁的黄金。最后商人击鼓离去。”
不同国家的人如何见面,语言不通的人如何交流呢?——通过击鼓。买卖双方计量单位与货币均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调节临时市场的供求,如何规定双方的交易用语?——通过不断加注黄金。这种交易没有公共法律的监督,那么这种无人管控的交易该如何保证呢?——通过脱下并放下衣服的行为。无数次被记录,但再没有出现过的“哑巴交易”故事能够解答现在的人所提出的一切疑惑。当然,这个故事就像“采集”黄金的奇妙篇章一样,使中世纪撒哈拉市场中黄金贸易的实际情况更加虚无缥缈,但同时,展现了黄金交易的具体情景以及黄金贸易给北非商人带来的忧虑。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 作者:[法]F.-X.福维勒-艾玛尔 译者:刘成富 梁潇月 陈茗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