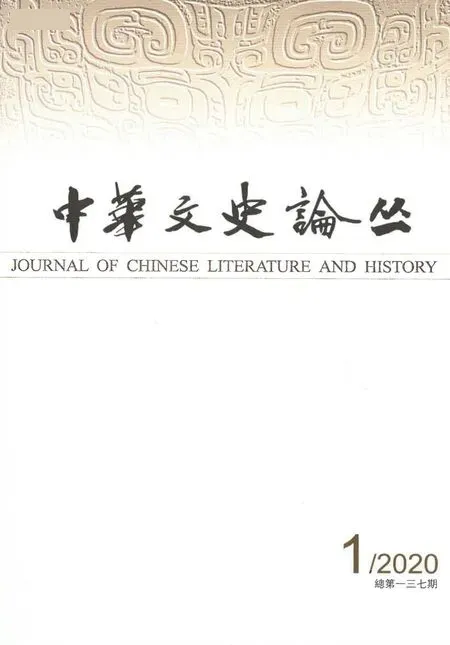論西夏佛教之漢藏與顯密圓融
2020-11-27沈衛榮
沈衛榮
提要: 本文通過對《大乘要道密集》收録的“大手印”傳軌文本,黑水城出土文獻《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欲護神求修》與《四字空行母記文》四種漢文藏傳佛教文本的分析,披露西夏時代所傳藏傳密教所附帶的明顯的漢傳佛教和顯宗佛教成分。同時,本文試圖展現在西夏時代,傳譯者們努力讓一個本來對於漢傳佛教徒來説陌生迥異的藏傳密教儀軌變得相對容易理解和接受,這些均反映出了西夏佛教具有漢藏和顯密兩種佛教傳統交融的特色。
關鍵詞: 西夏 漢藏佛教 顯密圓融 黑水城文獻
一
《大乘要道密集》集西夏、元、明三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之大成,它與黑水城出土漢文、西夏文佛教文獻一起,是迄今所見研究藏傳佛教於西夏、元、明三代於中原和西域傳播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資料。(1)參見沈衛榮《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卷收録二十餘種與印藏佛教“大手印法”相關的文本,其中有一短篇大手印修習要門,題作《心印要門》,全文如下:
修習行人,結跏趺坐,脊骨端直,如壘金錢。結三昧印,曲頸如孔雀,目視於鼻尖,觀面前空,而發願云: 爲利法界一切有情,願成佛!發願既已,身如鏡像,語如響聲,意如陽焰,了達虚假。身離作務,語離談説,意離思念,自性清淨,應依真空,無念而住。當此之時,心無所緣,亦無所思,善惡邪正,都莫思量。又不思有,亦不思空,過去不追,未來不引,現在不思,妄念起滅,一切皆無。亦無能緣,能所清淨。如鳥飛空,而無蹤迹;如海雪消,泯絶諸想。如無雲空,寂然顯現。縱蕩身心,坦然而住。如初生嬰孩,飲乳充足,安然而住。無諸思念,不思空有,不思好惡,不思有情,不思正覺,不思父母,兄弟姊妹,不思彼此。不思忻厭,無分别念,不思淨穢,無愧恥心。夫愧恥者,若作盜賊,則應愧恥;若取他物,則應愧恥;若作妄語,則應愧恥;若造罪業,則應愧恥;不解要門,不能修習,則應愧恥。若於密杵生愧恥,則於手足應生愧恥;若於蓮宫生愧恥者,則應於口亦生愧恥。如彼嬰孩,安然而住。修習行人,上則不求佛果,下則不怖輪回,應念真空,一味平等。於彼無念,亦不應住。又如顛狂行人,而應安住,不着諸相,寃親等觀,金土無異。有漏無漏,有相無相,有體無體,世俗勝義,妍醜苦樂,所愛所憎,思念造作,所有外相,一切都無。放蕩身心,縱任而住,内心清淨。無本離根而安住,則如樹無根故無身,無身故無枝,無枝故無梢,無梢故無葉,無葉故無花,無花故無果,世間果報,必不發生。然此定中,無念是化身,無生是報身,超意是法身,法爾清淨是自性身也。昔有大師,號風捲輪回,於天竺國諸勝住處成就師等前,聽受要門,皆依此宗修習。又大寒林及金剛座,南吉祥山成就佛等,亦依此宗修習。西番中國布當拶巴等處殊勝師等,亦依此宗修習。又康斡隆迎所説師等,亦依此宗修習,是故師資相承,以心印心,正謂此也。(2)莎南屹囉等集譯《大乘要道密集》卷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葉76—78。
心印要門 竟。
顯然,上録《心印要門》是西夏時代所傳藏傳密教“大手印”(phyag rgya chen po)修法的一部“要門”。所謂“要門”,通常是指某位西天或者西番上師爲指導密教行者實修某種由其特别傳承的儀軌、修法(sdhan,sgrub thabs),而專門量身打造的一種修習指南類文本。藏文稱這一類文本爲“manngag”或者“gdamsngag”,與它對應的梵文詞是upadesa(優波提舍),西夏和蒙元時代通常將它譯作“要門”,時或亦譯作“劑門”。(3)關於“要門”這一藏傳密教文本類型的介紹,見Matthew Kapstein, “gDams ngag: Tibeta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José Ignacio Caben and Roger R. Jackson eds.,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6, pp.275-289。上録這部《心印要門》是一位“號風捲輪回”的大師,“於天竺國諸勝住處成就師等前聽受”,後“西番中國布當拶巴等處殊勝師等,亦依此宗修習”。儘管對傳習這個要門的風捲輪回和布當拶巴二位上師的確切身分,一時還難以確定,但據此已經可以肯定《心印要門》是從印度經西番再傳至西夏(河西)的一部修習“心印”要門,更準確地説,它是一部典型的“大手印”求修要門。“西番中國”曾是西夏人對西番,即古代西藏的一種常見的稱謂,它或當是藏文Bod yul dbus一詞的直接翻譯。藏文文獻中較早將西番稱爲Bod yul dbus,或者逕稱yul dbus,意謂“中國”。這樣的稱呼或藴含有二層意義,一是將Bod yul dbus,即“西番中國”與地處西番邊緣的mDo smad(朵思麻,即今安多)和mDo khams(朵甘思,即今康區)等邊緣地區分開,其意義或與dBus gtsang(烏思藏)或者Bod dbus gtsang相同;二是爲了凸顯西番當時已取代西天(天竺、印度),居於佛教世界之中心地位,故而自稱Bod yul dbus,即“西番中國”。原初在藏文文獻中yul dbus是對印度的稱呼,或稱’Phags yul dbus,譯言“聖〔域〕中國”,隨着佛教於印度漸趨消亡,西番佛僧或已當仁不讓地將雪域番地稱爲yul dbus,即“中國”了。與此相應,接受了藏傳佛教的西夏人亦就將西番稱爲“西番中國”了。(4)以往關於“西番中國”這一稱謂之意義的討論參見孫伯君、聶鴻音《西夏文藏傳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經典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8年,頁251—253。關於藏傳佛教傳統中對聖地印度的構建,參見Toni Huber, The Holy Land Reborn: Pilgrimage and the Tibetan Reinvention of Buddhist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儘管從其形式和傳承來看,《心印要門》當是一部藏傳密教修法要門,但從其文字和内容中,我們卻又見不到藏傳密教中常見的那些“秘密”或者“甚深”的東西。僅有“若於密杵生愧恥,則於手足應生愧恥;若於蓮宫生愧恥者,則應於口亦生愧恥”這一句,或較容易令藏傳密教行人和學者們聯想起“欲樂定”,即俗稱“雙修”的瑜伽修法,感覺它或是在替“欲樂定”正名。除此之外,這篇要門中的其他文字和内容則更容易讓人誤以爲是一篇與漢傳佛教,特别是禪宗佛教相關的文本。其標題中的“心印”似乎是指漢傳禪宗佛教之本意,所謂心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5)《祖庭事苑》(X.1261)卷八,《卍新纂續藏經》(64),頁424下。或者亦可以把它當作是漢傳密教的修法,因爲後者以《大日經》所説名爲“心印”,並將“心印”作爲廣開一切法門之方便。
可是,這篇《心印要門》所説的“心印”顯然與《大日經》無關。如前所述,它出現於《大乘要道密集》内一組與“大手印”修法相關的要門之中,儘管看似與“大手印”無關,可事實上它就是大手印的一種修法,不過在名相上以“心印”替代了“手印”。若將《心印要門》與同見於《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中的那幾部大手印修法要門,特别是其中的《大手印赤引定要門》和《大手印伽陁支要門》略作比較的話,則不難看出它們所述之求修法同出一轍,甚至其中所用辭句有不少也完全一致。特别引人矚目的是,這部《心印要門》通篇文字順暢、優美典雅,令人難以相信它是一篇由藏譯漢的翻譯作品,讀來根本感受不到任何違和之感,看不見任何古之路贊訛(lo—ts—ba,譯匠)們留下的斧鑿之痕,它更像是由某位兼擅漢藏兩種佛教傳統的西夏上師或者學僧自己創作、傳習的一篇要門。殊爲遺憾的是,迄今爲止我們尚未能找到可與這篇《心印要門》相應的藏文原本,也未能對文中出現的大師名號和地名等做出可信的認定和解釋,故對這篇要門的來龍去脈幾乎一無所知。
由於《心印要門》和與它形成同一系列的那一組大手印修習要門,是流傳至今西夏佛教文獻中一組完整和有特色的文本,代表了西夏佛教圓融漢藏和顯密兩種傳統的鮮明特色,是故解讀這篇要門、弄清其源流,對於我們理解西夏佛教的形成及其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往,於討論和研究漢藏佛學時,我們或用心探討漢傳佛教在藏傳佛教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意義,或着力於研究藏傳佛教於中原和西域傳播的歷史和影響,而專業研究西夏佛教的學者們,又或側重於討論藏傳密教對西夏的包圍,或依舊强調漢傳佛教不可動摇的主導地位。(6)參見沈衛榮《漢藏佛學比較研究芻議》,《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頁51—63;沈衛榮《西夏佛教文獻與歷史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8年。實際上,西夏佛教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漢藏、顯密圓融的特色,可爲我們思考和研究漢藏佛教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提供另一種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新途徑。
我們或可以這樣來理解西夏佛教。在處於漢藏之間的西夏王國内,當西夏的佛教徒們——其中既有西夏人,也有漢人,甚至亦還可能有西藏人、回鶻人和蒙古人等等——開始接受、實踐和傳播佛教時,他們同時受到了來自漢、藏兩種不同的佛教傳統的影響。於是,如何來兼容和調和這兩種不同的傳統,特别是化解顯密之間的巨大差異,形成適合自己傳習的獨特的佛教傳統,便成爲西夏佛教徒們曾經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而諸如《心印要門》這樣的一系列兼具和圓融漢藏、顯密佛教之不同義理和修習法門的文本的出現,不但讓我們看到了西夏佛教徒們曾經爲兼容并蓄,並有機整合漢藏和顯密這兩種不同的佛教傳統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在這種努力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西夏佛教,即這個圓融了漢藏和顯密兩種不同傳統的西夏佛教,或即我們以往所討論的、可與印藏佛教相對應,並鼎足而立的漢藏佛教的最好代表。甚至可以説,西夏佛教的一個更合適的稱號就應該是漢藏佛教(Sino-Tibetan Buddhism)。
自然,這僅僅是在迄今對源自西夏時代的部分漢文和西夏文藏傳佛教文本所做初步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對西夏佛教及其歷史提出的一個十分大膽的構想,要證明這個構想言之成理,還需要我們做更多、更細緻的文本和歷史的研究工作。下文筆者將對西夏時代所傳的幾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藏傳佛教文本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從中來觀察和討論中國佛教史上一個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的大問題,即西夏佛教是如何嘗試圓融漢藏和顯密兩種佛教傳統,並進而形成爲一種典型的漢藏佛教傳統的。
二
《心印要門》是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之一系列共二十餘種“大手印”要門中的一種,後者主要由以下三個部分組成: 一、 《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二、 《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三、 《新譯大手印金瓔珞等四種要門》。這三個部分的每一個總標題下又由若干篇獨立的“要門”組成,上引《心印要門》即見於第二部分《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之中。按其題記所示,《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乃“大巴彌怛銘得哩斡師(Maitripa, 986—1063)集、果海密嚴寺玄照國師沙門惠賢(Shes rab bzang po!)傳、果海密嚴寺沙門惠幢(Shes rab rgyal mtshan!)譯”。而《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則同樣是“果海密嚴寺玄照國師沙門慧賢傳、果海密嚴寺沙門慧幢譯”。《新譯大手印金瓔珞等四種要門》題下未標明其傳譯者,唯其中的《金瓔珞要門》末尾標明是“路贊訛辢麻光薩譯西番”。看起來這三部大手印要門都應該是從西番,即西藏文文本中翻譯過來的。(7)對這些文本及其内容的介紹,參見沈衛榮《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第二章《薩思迦道果法之大成: 〈大乘要道密集〉篇目解題》,頁102—110。
但是,長期以來卻僅有吕澂先生於1940年代找到了與《金瓔珞要門》相對應的藏文原本,它是《吉祥烏氏衍那處修集會輪時四十成就瑜伽行者所唱金剛歌覺受要門明點金瓔珞》(dPalUdiyanartshogs’khorbyaspa’idussurnal’byorpagrubpathobpabzhibcusrdorje’imgurbzhengspanyamskyimanngagthiglegsergyiphrengba)的一個節譯本。(8)參見吕澂《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1942年,乙種第一册,《漢譯藏密三書》之《大手印金瓔珞要門》,頁1—16。後來經過比照又發現,與這個常見於藏文大藏經中的本子相比,與《金瓔珞要門》的文字更加接近的藏文文本是另一部同樣傳爲銘得哩斡師編集的《大手印金瓔珞》(Phyagrgyachenpogserphreng),它是銘得哩斡師匯集諸得證成就的瑜伽師和班彌怛之語録而編成的一部要門集——《大手印大寶金剛歌金瓔珞》(Phyagrgyachenpordorje’iglurinpochegsergyiphrengbazhesbyabagrubpathobpa’irnal’byorpadangpaoditamangposgsungparnamsrjebtsunmnga’bdagmatripasgzhunggcigtubsdebspa’igdamspabzhugsso),傳由班彌怛銘得哩斡本人和馬爾巴譯師(Mar palotsabaChos kyi blo gros, 11世紀人)一起譯成藏文。(9)Nges don phyag chen rgya gzhung dang bod gzhung, Khreng tu’u, Si khron dpe skrun tshogs pa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2009, Vol.5, pp.373-399.
近年來,隨着藏傳佛教文獻電子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越來越容易接觸到越來越多的早期藏傳密教文本,可是,我們卻依然很難找到可與上述這一系列大手印要門中的絶大部分文本大致對應的藏文文本,以至於令人對其來歷和形成過程産生種種懷疑和推測。(10)近日方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楊傑博士找到了與見於《大乘要道密集》卷四中的兩部短篇要門,即《大手印纂集心之義類要門》和《那彌真心四句要門》相對應的藏文原本,它們分别是崗波巴鎖南輦真上師所造之《具五心要義》(sNying po’i don lnga ldan)和《阿闍梨端必兮嚕割之密意》(sLob dpon dom bhi he ru ka’i dgongs pa),見於《三界法王吉祥無比崗波巴衆生怙主鎖南輦真全集·如意寶》(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 dpal mnyam med sgam po pa ’gro mgon bsod nams rin chen gi gsung ’bum yid bzhin nor bu),Kathmandu, Khenpo Shedup & Lama Thinley Namgyal, 2000, Vol.3, pp.244-246,459-460。《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雖然標明爲“大巴彌怛銘得哩斡師集”,但其文中卻多次出現“啞斡諾帝巴師(銘得哩斡師之别名)云”、“銘得哩斡師云”、“銘得哩瓦師”等等,這表明它或不是銘得哩斡師本人親“集”,而更可能是他的傳人“果海密嚴寺玄照國師沙門慧賢”根據其所傳多種要門和語録重新集録、編排而成書的。《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的傳譯者與《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相同,但没有説明其原著(集)者是誰,從其文本内容和行文風格來看,應該也是銘得哩斡上師。因爲其中一部《大手印伽陁支要門》詳列其師承次第,其中即有“啞斡諾帝”,而其直接的傳人是“辢麻馬巴”,最後一位宗承師是“玄照國師”,所以,可以基本肯定這部《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與《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一樣,也是玄照國師根據銘得哩斡上師所傳要門和語録傳譯而成的。(11)《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67。
還有,《大手印引定》中所引的黑足師(Nag po)、當精斡師(Tog rtse pa)、得呤浪巴師(Tilopa)、捺浪巴師(Nropa, 956—1040)、絶語持槍師(諾遮崗巴大師,mDung can lkugs pa)、方甲師(啞達堅甲大師,Phyogs kyi glang po, Gos can)、那彌形嚕噶(葛)師(Dombiheruka)、妙勝師(賢妙大師,Samantavajra, Bhadra)、無敗持劒師(勝勢器仗大師,Mi pham ral pa)等上師語録,也全部見於同爲銘得哩斡師所傳的《金瓔珞要門》中,其中有些相應段落的譯文基本一致,而更多段落則有或多或少的差異,明顯出自不同的編譯者之手。(12)《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61—67。《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和《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兩個文本的文字質量遠高於《新譯大手印金瓔珞等四種要門》,前二者行文讀似原創作品,而後者則譯匠硬譯的氣息相對比較濃厚,很多句子明顯辭不達意。當然,即使是前二者也是西夏時代之“新譯”作品,其中所引《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中的段落,大部分與西夏釋智所譯文本有明顯的不同。(13)參見沈衛榮《論〈大乘要道密集〉的成書》,《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頁11—20;亦參見同氏《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頁36—43。
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這一系列大手印要門大部分不見於迄今所見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漢文佛教文獻中,迄今僅見到一部題爲《九事顯發光明義》的短篇要門,其内容與見於《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中的一篇《大手印九種光明要門》基本一致,但其文本内容和文字風格似都不如後者詳細和精緻。(14)TK285,《俄藏黑水城文獻》(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74。但是,這一系列大手印要門源自西夏時代當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因爲除《金瓔珞要門》外,其他文本都同時有相應的西夏文譯本傳世,它們亦都見於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中。這些西夏文文本與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相應的漢文文本基本一致,當是同時從藏文本翻譯而成。另外,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中,人們還發現了一部題爲《大印究竟要集》的文本,乃西夏著名譯師、“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直接用西夏文所造。然其中所列宗承師名録,共九傳至德慧本人,其中第五本師即銘得哩斡上師,可見它與上述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一系列大手印文本也有明顯的關聯。(15)對於這些西夏文文獻的解讀和研究參見索羅寧《西夏文“大手印”文獻雜考》,沈衛榮主編《漢藏佛學研究: 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頁235—266;孫伯君、聶鴻音《西夏文藏傳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經典研究》。
對於《大乘要道密集》中出現的這些大手印要門的來歷和歸屬,以往學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將所有與大手印之義理和修法相關的文本統統歸結爲噶舉派(bKa’ brgyud pa)的傳統,因爲大手印法於後世被認爲是噶舉派所傳根本大法;而另一種意見則將它們歸屬爲薩思迦派(Sa skya pa)所傳道果法(lam ’bras)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爲後者有“三續道”之分,即含藏因續、身方便續和大手印果續,而《大乘要道密集》本身又主要是一部道果法文本的集成,所以其中的大手印要門看似當屬於薩思迦派的傳軌。(16)談錫永《序言》,《大乘要道密集》,頁8—9。於今看來,當這些文本在西夏傳承的時候,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劃分尚未成型,是故將它們簡單地劃歸噶舉派或者薩思迦派顯然有違藏傳佛教歷史發展的時代順序,失之武斷。在藏傳佛教最終於17世紀左右被明確劃分成噶舉派、薩思迦派、格魯派和寧瑪派等四大教派之前,討論藏傳佛教後弘期的歷史更當以“舊譯密咒”(gsang sngags rnying ma)與“新譯密咒”(gsang sngags gsar ma),或者以“新譯密咒隨行道果”(gSang sngags gsar ma lam ’bras rje ’breng dang bcas pa’i skabs)、“馬爾巴所傳達波噶舉”(Mar pa nas brgyud de dvags po bka’ brgyud ces grags pa’i skabs)、“阿底峽所傳噶當”(Jo bo rje brgyud pa dang bcas pa’i skabs)和“大手印法”(Phyag rgya chen po’i skabs)等幾種主要的教法傳軌爲重要線索。而其中的“大手印傳承”則正好就是由銘得哩斡上師所傳,且獨立於“道果”和“達波噶舉”傳承的一種自成體系的傳軌。所以,於此確定這些源自西夏的大手印要門均來源於銘得哩斡上師的傳軌,顯然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它們對於西夏佛教形成和發展歷史的意義。(17)關於藏傳佛教教派劃分的最新討論,參見沈衛榮、楊傑《略述西夏和元朝所傳藏傳佛教之宗派源流》,王頌主編《宗門教下: 東亞佛教宗派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頁189—218。參見Marc-Henri Deroche, “’Phreng po gter ston Shes rab ’od zer (1518-1584) on the Eight Lineages of Attainment. Research on a Ris med Paradigm”, Brandon Dotson eds., Contemporary Vision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betologists,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9, pp.319-342.
對於西藏所傳“大手印法”的來源,以往於藏傳佛僧和後世學者之間均曾有過激烈的爭論。甚至曾經有人以爲它源自漢傳禪宗佛教,是和尚摩訶衍當年於吐蕃所傳禪法的殘餘,認爲是一種被稱爲“唯一白法”(dkar po chig thub)的萬應靈丹式的邪説。(18)對這種觀念的分析和批判參見David Jackson, Enlightenment by a Single Means: Tibetan Controversies on the “Self-sufficient White Remedy”, Wien, Verlag der Österrie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4.顯然,這種説法反映的是後弘期佛教早期的門派之爭,而並没有可靠的教法和歷史依據。從理性和學術的角度入手,我們更應該深入探尋大手印法於印度佛教中的來源和變化,通過細緻的文本梳理和比較研究來理清它自印度傳至西藏、並於西藏傳承和發展的歷史過程。近年來,維也納大學印藏佛學研究專家Klaus—Dieter Mathes教授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精雕細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他基於工珠無邊慧(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1813—1899)上師對顯教(mdo lugs)、密教(sngags lugs)和精要(snying po lugs)大手印的三分框架,(19)對這三類大手印的判定與解説,見工珠·元丹嘉措《知識總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卷,頁381—383。對銘得哩斡上師所造一系列圓融大手印修習與顯乘“極無所住中觀”(rab tu mi gnas pa)的論典進行了十分仔細的文本研究與義理分析,清晰地呈現了顯教大手印的印度起源及其在藏土被接受的過程,他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今天理解西夏所傳大手印法具有極大的啓發意義。(20)參見Klaus—Dieter Mathes, “Blending the Sūtras with the Tantras: The Influence of Maitripa and His Circle on the Formation of Sūtra Mahmudr in the Kagyu Schools”,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Praxis: Studies in its Formative Period 900-1400, Leiden, Brill, 2006, pp.201-227; A Fine Blend of Mahmudr and Madhyamaka: Maitrīpa’s Collection of Texts on Non-Conceptual Realization (Amanasikra),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ie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5.
顯而易見,印藏密教,特别是其“欲樂定”等修法於西夏的傳播,一定曾引起過漢傳顯乘佛教信衆們的强烈質疑,所以如何爲密教正名曾經是印藏密教傳播者和修習者們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於今日所見西夏漢文藏傳密教文獻中,我們見到了不少類近於密教解釋學(Tantric Buddhist hermeneutics)的文字。(21)有關密教解釋學的作品,參見Robert Thurman, “Hermeneutics of Vajrayana”, Buddhist Hermeneutics, Donald S. Lopez Jr. ed., Kuroda Institute: Studies (轉下頁)如在西夏時代所傳的一部集合了“欲樂定”和“拙火定”等多種求修要門的長篇道果法儀軌《依吉祥上樂輪方便智慧雙運道玄義卷》中,我們就讀到了這樣一段當是傳譯者自行添加進去的文字,云:“問淫聲敗德,智者所不行;欲想迷神,聖神之所遠離。近障生天,遠妨聖道。經論共演,不可具陳。今於密乘,何以此法〔爲〕化人之捷徑,作入理之要真耶?答: 如來設教,隨機不同,通則皆成妙藥,執則無非瘡疣,各隨所儀,不可執己非彼。又此密乘是轉位道,即以五害煩惱爲正而成正覺。”(22)(接上頁)in East Asian Buddhism 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p.119-148; Christian Wedemeyer,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Indian Tradi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23)《大乘要道密集》卷一,葉29。它將密乘稱爲“轉位道”,即將“五害煩惱爲正而成正覺”的方便法門,以此而爲密教正名。當時密乘佛教對顯密的分别通常是如此界定的:“聖教中説欲成就究竟正覺者,有二種,一依般若道,二依秘密道。”(24)《拙火定》,《大乘要道密集》卷一,葉32。“若棄捨煩惱而修道者,是顯教道;不捨煩惱而修道者,是密教道。今修密教之人,貪嗔癡等一切煩惱返爲道者,是大善巧方便也。”(25)《光明定玄義》,《大乘要道密集》卷一,葉49。所以,密乘的修法是一種轉位道,或者説是“轉爲道用”(lam ’khyer),即將貪嗔癡三毒等一切煩惱轉爲可以憑藉而修習的成佛道路。是故,欲樂定是“以貪返爲道者”,拙火定是“以嗔恚返爲道者”,光明定是“以愚癡返爲道者”,幻身定是“要返無明而爲道者”,它們都屬於密乘佛教無上瑜伽部的修法。
於《大乘要道密集》和黑水城出土文獻中,我們均發現了大量屬於“捺囉六法”(Nrochosdrug)的密教求修儀軌,如拙火、中有、捨壽、夢幻身、光明等各種瑜伽修習要門等,顯然它們都曾於西夏藏傳佛教信衆中有較廣泛的傳播,同時這也表明以“捺囉六法”圓滿次第修習爲前行的“大手印”法曾於西夏得到了廣泛的傳播。(26)捺浪巴(Nropa)上師造,馬爾巴(Mar pa Chos kyi blo gros)翻譯的《耳傳金剛句》(sNyan brgyud rdo rje’i tshig rkang)即“捺囉六法”的根本所依綱要,由其展開的含攝“欲樂定”之“勝樂耳傳”(bDe mchog snyan brgyud)圓滿次第(rdzogs rim)道軌連同依托於勝樂金剛、金剛亥母等本尊禪定的生起次第(bskyed rim)修習以及後續的大手印法共同組成了一套環環相扣、涵蓋無上瑜伽三續部的完整階梯,上述緊密聯繫的三大次第修軌皆已傳入西夏,這在迄今爲止我們所見到的漢文和西夏文文本所呈現的修法中有極爲鮮明的體現。有關《耳傳金剛句》的研究見Fabrizio Torricelli,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Karoatantravajrapada”, East and West (48), 1998, pp.385-423; 同氏“Padma dkar-po’s Arrangement of the bDe-mchog snyan-brgyud”, East and West (50), 2000, pp.359-386.於大手印的教法體系和修習傳軌中,上述屬“捺囉六法”的各種瑜伽修習是“方便道”(thabs lam),屬於“大手印”法修習的前行(sngon ’gro),而“大手印”本身則是“解脱道”(thar lam)的修法。作爲正行(dngos gzhi,或曰正體)的“大手印”修法通常是一種練習定心、直指心性,以證悟自性本淨、入樂空無二境界的禪定。《依吉祥上樂輪方便智慧雙運道玄義卷》在詳述依“行手印”(las kyi phyag rgya)修“欲樂定”儀軌後,復略述分别依“記句手印”(dam tshig gi phyag rgya)、“法手印”(chos kyi phyag rgya)和“大手印”(phyag rgya chen po)修“欲樂定”的種種修法。其中明文規定“今依密教,在家人則依行手印入欲樂定,若出家者,依餘三印入欲樂定,契於空樂無二之理也”。(27)關於四手印參見Klaus—Dieter Mathes, “The ‘Succession of the Four Seals’ (Caturmudrnvaya) Together with Selected Passages from *Kropa’s Commentary”, Tantric Studies, Vol.1, Center for Tantric Studies, Hamburg, University of Hamburg, 2008, pp.89-130. 亦參見沈衛榮《四手印與欲樂定: 〈依吉祥上樂輪方便智慧雙運道玄義卷〉讀解》,同氏《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頁157—220。其實四手印修習中僅有依行手印纔是實修,依記句手印入欲樂定是觀想,依法手印入欲樂定則是觀身内三脈四輪,運用拙火燃降,漸生四喜,入空樂不二定。而“若依大手印入欲樂定者,然欲樂定中所生覺受,要須歸於空樂不二之理。故今依大手印,止息一切妄念,無有纖毫憂喜,不思不慮,凝然湛寂,本有空樂無二之理,而得相應,即是大手印入欲樂定,歸空樂不二之理也”。(28)《大乘要道密集》卷一,葉28—29。這段對大手印法的描述可令人想起達摩祖師《二入四行論》中對“理入”的定義,即“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即於理冥符,無有分别,寂然無爲,名之理入”。
若將上引這段修習大手印的文字和達摩祖師傳《二入四行論》中的“理入”部分乃至六祖以前諸祖師所著論典相比較,(29)其中之典型可參見三祖僧燦之《信心銘》、五祖弘忍之《最上乘論》等。則不難看出,於印藏佛教中所傳的大手印法的正行,實際上與漢傳禪宗佛教中的禪定十分類似。進而言之,較高次第的密乘佛教修習,如“大手印”和“大圓滿”法等,都已經基本脱離了那些必須依靠氣、脈、明點來修習的印藏密教儀軌元素,超越了有相(mtshan bcas)而躍升到了無相(mtshan med)的層次,其重點在於對心性本來面目(30)“本來面目”乃漢土禪宗的常見名相,而在藏文的大圓滿、大手印文獻中亦能見到與之詞、義(sgra don)皆近似、相合之詞,此即rang zhal,例見噶舉派上師文殊勇(’Jam dpal dpa’ bo, 1720—1780)所造《了義大手印導引次第明示·現前明現真如本來面目之鏡》(Nges don phyag rgya chen po’i khrid rim gsal byed de bzhin nyid kyi rang zhal mngon sum snang ba’i me long),收於《噶舉寧瑪衆多大士之大手印、大圓滿教誡集要·必需之寶庫》(dKar rnying gi skyes chen du ma’i phyag rdzogs kyi gdams ngag gnad bsdus nyer mkho rin po che’i gter mdzod),Darjeeling, Kargyu Sungrab Nyamso Khang, 1978-1985, Vol.2, ff.251-567;另見第一世敦珠仁波切摧魔洲(bDud ’joms gling pa, 1835—1904)所造《現證自性大圓滿本來面目教授·無修佛道》(Rang bzhin rdzogs pa chen po’i rang zhal mngon du byed pa’i gdams pa ma bsgom sangs rgyas),收於《化身大伏藏師摧魔洲甚深伏藏秘密法部》(sPrul pa’i gter chen bdud ’joms gling pa’i zab gter gsang ba’i chos sde),Thimphu, Lama Kuenzang Wangdue, 2004, Vol.16, ff.291-358。此承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楊傑博士示告,於此謹致謝意。兩種語言的文本中存在的諸如此類的法義、構詞皆相近的名相爲翻譯時的無縫對接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即所謂“赤裸覺性”rig pa gcer bu〗)的究竟體證,故而與禪宗“心地法門”之理念與觀修具備天然的親和力和高度的可融性;而西夏時代傳世諸大手印文本的集、傳、譯者,無疑都具備紮實的漢土禪宗基礎,他們身爲跨越多語種的橋梁,在編譯、纂述這些大手印文本時,可以直接熟練地調用自身儲備的禪宗語料庫來對譯大手印法的名相,而無需再生造一套令漢傳佛教徒感到陌生的名相,並在義理的闡釋與發揮上進一步借助禪宗的相關理念和表述模式,故最終呈現出來的作品自然禪味醇厚,既文辭華美,誦之有抑揚頓挫、珠玉琅琅之韻,復法義曉暢,修之有相應受用、如飲醍醐之感。
《新譯大手印頓入要門》對大手印修法是這樣描述的:“次依宗修行分二,初加行方便,後禪定正體。初加行方便分三,初坐如大柱,次語離談説,後目不開合。後禪定正體者,謂心直如槍,若槍邪曲,用不的中,須要端直。修習行人,亦復如是。一切善惡,邪曲妄念,都莫思量,離諸妄想,寂絶而住,稱順本心。”(31)《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60。不管這是否就是Mathes教授所主張的“顯乘大手印”修法,可以肯定的是,不但從外相來看,西夏所傳大手印的密教修法與漢傳的禪修已十分類似,而且,從佛教了義的角度來説,漢藏、顯密兩種傳統於此已經達到了一種十分自然的合流和圓融的境界。這大概就是爲何像前引《心印要門》等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一系列大手印要門文本看起來與漢傳顯宗的禪修類文本如此類似的原因所在。同樣,這也可能就是大手印法得以在西夏廣泛傳播,並成爲西夏佛教的一大特色的重要原因。(32)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漢藏和禪密圓融的傾向最早出現在吐蕃王朝滅亡之後的敦煌地區,從現存的敦煌古藏文禪宗佛教文獻,以及像《禪定目炬》等與寧瑪(轉下頁)

原夫真實究竟明滿,爲利有情,演説八萬四千法門,欲令顯示離於言説、昔成無生大手印本源理故,初以方便義,隨所化機,演説歷位彼岸乘法;次以決定義,隨所化機,演説共同密乘教法。……後以真心義,爲利上根堪解脱者,演説不共大手印無比要門。如是乘教要門之中,欲依要門了本源者,須解枝義。不知枝義,難達本源。若了因枝外道、二乘、唯識、中道、四本續等之見宗者,於自見宗決能發生斷增益智。(36)此處對顯密佛教宗派的劃分與《喜金剛本續》中所述基本一致,《吉祥喜金剛本續王後分注疏》,《喜金剛空行綱律儀品第八》,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凡了見宗,有其四類,謂太過、不及、偏墮、的中也。然無住中道及大手印是的中者。此有同有異,有近有遠。同者,輪回圓寂不二之理,乃因果二乘共同見解也。異者,因乘捨位以爲其道,起對治智而斷於惑,遍於輪圓法界空理,久時調習而欲克證也。果乘轉位以爲其道,起俱生智,於能所輪回了大樂法界,即以三毒煩惱爲道。……今此果乘,見之與行,互不相違也。遠者因乘,修心以爲其道,蓋由不了心性本淨,歷三袛劫,欲證佛果也。近者果乘,煉身以爲其道,如治目翳,由了心性本清淨故,現身成佛也。修習行人,若了如是同異遠近,即於見宗能善分别是非、取捨解離一切而不捨一。(37)《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48—49。
可見,雖然“無住中道”和“大手印”分屬因、果二乘,但在見(lta ba)、行(spyod pa)、果(’bras bu)三者上無甚殊異,二者的分野僅在於修(sgom pa),前者以捨位、修心爲道,後者以轉位、煉身爲道,由是而在與證果目標所隔距離上有遠近之不同,由於二者皆謂的中,殊途同歸,故可圓融無二。(38)“是以銘得哩斡師欲令行人,了解淺深及優劣,故爲上根人引於教證,令人修習甚深之道而得解脱也。三了見宗已,安住禪定者,然此見宗若望因乘,即乘即煉淨其心,而觀於空;若據果乘,依緣起道而觀大樂、光明、真空。然其因乘所修之道,准餘文知。今此果乘,依大手印而修道也。此亦分二,初漸入安心,後頓入安心。銘得哩瓦師隨有情機,漸之與頓,俱許修習。”《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55。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確定西夏時代所傳大手印修法應該主要是出自銘得哩斡上師的傳承,其特色便是將顯宗的“無住中道”與密乘的大手印進行類比,以圖連接和圓融因果或顯密二乘。儘管我們目前尚難完全確定見於《大乘要道密集》的那些大手印要門是否全部是西夏譯師對藏文原本的忠實翻譯,還是其中有些文本是西夏佛僧根據其所得師承要門所作的再創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文本的集、傳、譯者們都應當對漢傳禪宗佛教有相當深度的瞭解,故能用帶着地道禪味的文字,出色地表達和發揚銘得哩斡上師圓融“無住中道”與“大手印”的甚深密意。或正因爲如此,大手印法遂得以成爲西夏佛教的一個重要内容,而它又最充分地表現出了西夏佛教圓融漢藏和顯密佛教的鮮明特色。(39)值得一提的是,藏傳佛教後弘期雖以“新譯密咒”著稱,但其所弘佛法兼融顯密。如史載“新譯密咒”開山祖師輦真藏卜(Rin chen bzang po)上師“弘傳《波羅蜜多》和父續、母續二者的教授、要門,尤其專重弘傳瑜伽續部(lo chen rin bzang gis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dang/pha rgyud ma rgyud gnyis ka’i bshad bka’/bye brag tu rnal ’byor rgyud gsal bar mdzad)”。但他所持宗見,傳説就是“極無所住”之中觀見(lo chen ’di’i lta ba ni rab tu mi gnas pa’i dbu ma ba yin par bshad do)。土觀·洛桑卻吉尼瑪(Thu’u bkv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土觀宗派源流》(Thu’u bkvan, grub mtha’),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4年,頁52—53,56—57。
三
俄藏黑水城文獻TK128號、孟黑録182號文書爲西夏刻本,它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爲《佛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二部分爲《持誦聖母般若多心經要門》,均乃“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奉敕譯、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詳定”。第三部分則爲“御製後序”。這部《佛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同見於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佛説聖大乘三歸依經》(TK121、122)、《聖大乘聖意菩薩經》(TK145)、《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録》(TK164、165)、《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録》(TK164、165)等,都是於西夏仁宗皇帝在位時由西夏國師德慧新譯的幾種大乘佛典,後幾種佛經不見於任何以往結集的漢譯佛典中,當是西夏時代首次漢譯的文本。
筆者曾將這部新譯《佛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現存於漢文、西藏文《大藏經》中的多種《心經》的漢、藏文譯本作過對勘和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德慧的這部新譯本當與現存的兩種藏譯《心經》没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它應當是根據與現存藏譯本所據的梵文原本不一樣的另一種梵文本所譯,或者它亦可能是根據另一種現已不存的藏文譯本翻譯的。與此類似,同是德慧所譯的《佛説聖大乘三歸依經》、《聖大乘聖意菩薩經》、《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録》和《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録》等四部不見於漢文《大藏經》的西夏新譯大乘佛典也都與和它們對應的藏文譯本不同,故同樣應該是德慧根據梵文原本或者現已不復存在的另一種藏文譯本直接翻譯的。(40)對這幾種西夏時代新譯大乘佛典的漢藏文本的對勘和研究,參見沈衛榮《西夏佛教文獻與歷史研究》,頁87—113,194—226。
頗令人不解的是,與《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組合成爲一個文本的《持誦聖母般若多心經要門》,雖亦明確有題記稱其爲“德慧奉敕傳譯”,但迄今我們没有能夠找到與其相對應的梵文或者藏文文本,故其來歷不明,很難確認它究竟是一個譯本,還是一個德慧自己編集的儀軌文本。這種將持誦《心經》作爲日常修習對象,以求消除業障、速證菩提佛果的修法,不常見於漢、藏二種佛教傳統中。故對這一文本之形成的初步探索,或亦可幫助我們瞭解西夏佛教呈現出的漢藏、顯密兩種佛教傳統交融的基本特質。
於此,我們先將這個文本照録如下:
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
蘭山覺行國師沙門 德慧奉 敕傳譯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 詳定
敬禮般若佛母!
夫般若者,三世諸佛,出現之源;六度萬行,究竟之因。理智冥符,空有無礙,遠離二邊,即契中道。所以暫時憶念,頓摧業障,悉增福惠,等同佛行。超越二乘,爲菩薩首。濟三塗之苦,施人天之樂。若復有人,晝夜時中,修此觀行,讀誦受持,所獲功德,盡劫無窮。故龍樹菩薩,見此功德,依彼佛敕,集成一本《聖佛母多心經觀行要門》,祖祖相傳至於今,爾廣獲其益矣。
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誦《聖佛母多心經》者,每日早晨或空閑時,於寂靜處,掃室令淨,遍布名花,洒妙香水。其室中央,置般若佛母等像。其像面前,花、香、燈等,諸般供養,隨力置之。并置一盤白淨施食。然善男子、善女人,其像面前,端身而立,焚燒妙香,應發願云:“爲利法界一切有情離苦獲樂,故我今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如發願已,而禮三拜。其像面前,軟穩氈上,跪合掌,專觀佛像,應誦所有十方世界中,乃至回向衆生及佛道,如誦一遍,而禮三拜,結跏趺坐, 二手合掌,而執花米,應如是想,自己面前,於虚空中,頓想般若佛母,一面二臂,身真金色,二手心前,作説法印,左右脇下,而出兩根優鉢羅花,過於二肩。其二,花臺上各置般若經,頭髮結繫,具喜悦容,額嚴寶冠,身嚴衣珞,花月輪上,結跏趺坐,光明皎潔,佛母徘徊。頓想無量諸佛、菩薩、聲聞、羅漢,如是想已。然善男子、善女人,專觀佛會,應誦《聖佛母多心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乃至信受奉行誦一遍已。手中花米抛在空中,般若佛會,即時佛會,猶如霔雨,從空而來,入自己頂,遍滿一身,想爲不二。自從無始所積業障、諸惡重罪,猶如墨汁,流出足底,入於地中。無盡福惠,想令圓滿。如是周而復始,誦《聖佛母多心經》三遍、七遍、二十一遍至百八遍,隨力誦已。奉施食者,應如是作,於施食上,誦唵啞吽呪三遍,其食變成百味甘露,自己心間出光照耀虚空,以光召請般若佛會至於面前,意作供養,誦奉食呪曰: 唵 啊渴麽渴 薩唥斡麻捺 啊唥拽啊與切你身鉢捺咄怛 唵啞吽癹 莎訶 呪三或一遍,其彼佛會,受食歡喜,求索願事,想令允許。其彼佛會,從空而來,入自己頂,遍滿一身,想爲不二。然善男子、善女人,於一念頃,頓捨妄念,不思不慮,凝然而住,久久習之。若起妄念,心散亂時,所見萬象,如夢如幻,虚虚影影,而令觀之,應作回施云:
諸佛正法菩薩僧 直至菩提我歸依
我以施等諸善根 爲有情故願成佛
如誦一遍,起般若佛母慢,方可起之,隨意遊行。依如是例,每日持誦,則其善男子、善女人,持誦一遍《聖佛母多心經》者,等誦一部大般若經所獲功德。於現身上,不遭八難,衆人愛敬,心無邪見,恒契真理,所作所爲,皆同佛行,不成過僭。無始已來,所積宿障,十不善業,五無間等,諸惡重罪,頓然消滅。無漏福惠,自然增進。所有寃敵,一切邪魔,慈心相向,恒常覆助。辯才智惠,諸病不侵,永無夭壽。所祈隨意,十方諸佛,一切菩薩,憶念其人。一切諸天,常隨擁護。臨終之時,住於正念,十方諸佛,速來接引,安慰稱善,隨意往生,諸佛淨土,無量功德,悉得莊嚴,速能證得無上菩提也。(41)對於“觀空”與持誦密咒所獲之福利在《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中有很詳細的説明,其云:“二所修善法,識其優劣者,謂佛演教門,各隨機器而讚福利,(轉下頁)
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竟(42)(接上頁)或依别意説,或依決定説,據理分别,有多優劣。准《空行隱密本續》云: 若人承侍無量諸大家,又造塔像書寫教法藏,多劫精懃雖作衆善事,不及想念真空之一分。又云: 雖歷百億諸聖迹,不及觀空一分福。又《普賢觀經》云: 一念思維甚深理,百萬億劫罪消滅。又准《空行密無比本續》云: 若人祈福齋百億近善所獲福利,不如齋彼沙彌七人或二十一人乃至百人所獲之福。此福不如持戒比丘四人受齋所獲之福。此又不如誦般若經一遍之福。此又不如具等持人誦滅惡趣密咒一遍所獲之福。諸經真心是密咒,故彼本續云: 無如密咒能救者,如是福善一一。雖修百億萬倍,不如暫時獨居靜處而於樂明無念之理。不動不亂,無作意住所獲之福,勝前百千萬億之倍。”《大乘要道密集》卷四,葉53—54。
……朕覩勝因,遂陳誠願。尋命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重將梵本,再譯微言。仍集《真空觀門施食儀軌》,附於卷末,連爲一軸。於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開板印造番漢共二萬卷,散施臣民。仍請覺行國師等,燒施滅惡趣中圍壇儀,并拽六道,及講演《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作法華會,大乘懺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等事,懇伸追薦之儀,用答劬勞之德。仰憑覺蔭,冀錫冥資,直往淨方,得生佛土,永住不退,速證法身。又願六廟祖宗,恒遊極樂,萬年社稷,永享昇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餘祉,下逮含靈。
天盛十九年歲次丁亥五月初九日,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謹施。(43)《俄藏黑水城文獻》(3),頁73—77。
上録這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前序,交代這個文本的來歷,稱它是祖祖相傳至今的、由龍樹菩薩依佛敕而集成的一本持誦《聖佛母多心經》的觀行要門;第二部分即是這部要門所傳修法本身;而第三部分則是“御製後序”,説明譯、集和印造這部觀行要門的緣起及其實際用途。從前、後兩個序言來看,這部黑水城出土漢文佛教文獻中或僅有其前一部分,即《佛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當確實是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奉仁宗皇帝之命,“重將梵本,再譯微言”。而其中的第二部分,即《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則或當是德慧按照龍樹菩薩所傳修法集成的一部《真空觀門施食儀軌》。
衆所週知,《心經》是大乘佛教中的一部流傳極其廣泛的重要佛典,古往今來於漢、藏佛教中亦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譯本,大乘佛教兩大傳統之諸多不同教派也都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出發,對《心經》做過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解讀。迄今所見對《心經》的釋論和對釋論的釋論不但數量上已難以計數,而且在觀點上也互相滲透、融合,難以完全分辨清楚。然而,漢藏兩種佛教傳統對《心經》之解讀有一個最大、最明顯的不同點,就是漢傳佛教通常僅將《心經》作爲一部攝集般若部佛法之精要、開示大乘空觀的顯乘經典,而藏傳佛教則將它同時作爲大乘佛教顯、密二種傳統都必須依恃的一部重要經典,西藏文《大藏經》有時甚至將《心經》作爲“續部”(rgyud)的首要重典。
於西藏文《大藏經》中,我們見到有八種《心經》的主要釋論,它們分别代表了印度佛教解釋《心經》的不同傳統。(44)關於《心經》的各種詮釋,參見Donald S. Lopez, Jr., The Heart Sūtra Explained: Indian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Donald S. Lopez, Jr., 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ūt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談錫永等著譯《心經内義與究竟義——印度四大論師釋〈心經〉》,臺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其中有二部釋論以《心經》修法(Sdhan, sgrub thabs)形式出現,代表了從密乘角度解釋《心經》的傳統,它們分别是傳爲龍樹菩薩(Slob dpon chen po Klu sgrub snying po)親造的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修法》(Shesrabkyipharoltuphyinpa’isnyingpo’isgrubthabs),以及另一位印度上師Dva ri ka pa自稱根據佛語和龍樹菩薩的傳承(rgyal ba’i bka’ dang nva gva rdza na yi gsungs ba la brten)而造的另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修法》。(45)《藏文大藏經》丹珠爾(bsTan ’gyur),北京版 (pe cing), No.3464, Vol.65, pp.521-525; No.3465, pp.525-528.於印藏佛教對《心經》的解釋傳統中,凡將《心經》作爲一部密續,並爲其制定修習要門,則通常都歸諸龍樹菩薩的傳承。雖然,我們並没有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找到前述八部《心經》釋論中任何一部的漢譯或者西夏文譯本,但顯然譯、集這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的德慧國師對印藏佛教中的《心經》解釋傳統已有非常好的把握。他將這個文本稱爲“要門”,即與前述“心印要門”一樣,明確表明這是一部持誦、修習《心經》的密教要門,而不是普通的顯乘釋論。與此同時,德慧在這個文本的“前序”中又明確將它直接歸爲龍樹菩薩的傳承,説“故龍樹菩薩,見此功德,依彼佛敕,集成一本《聖佛母多心經觀行要門》,祖祖相傳至於今,爾廣獲其益矣”,讓人覺得他傳的這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實際上就是龍樹菩薩所傳的《聖佛母多心經觀行要門》。
可是,德慧所集的這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顯然不是見於藏文《大藏經》中的分别爲龍樹菩薩和Dva ri ka pa上師所造二部《心經》修法的直接翻譯,於具體的修法細節上,它們之間也基本上没有共同之處,故説《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直接傳自龍樹菩薩所造的觀行要門,有可能是德慧推行他所集的這種持誦《心經》修法時運用的一種善巧方便。不難看出,這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所傳修法當屬於密教中“行部”的修法。按照藏傳佛教的傳統,“聖教中説,欲成就究竟正覺者,有二種,一依般若道,二依秘密道。……然秘密中有所作、所行、修習、大修習四種本續”。(46)《拙火定》,《大乘要道密集》卷一,葉32。而這部要門的修法重視佛慢與佛行,先持佛慢以修,再持佛慢而行,觀想般若佛母爲對生本尊,視本尊與己平等如友伴,所以,它當可以歸屬於所行部本續的修法。
如果我們對《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這個文本再做進一步分析的話,則可發現它似乎不完全是一部典型的藏傳佛教的修法儀軌,至少不是一部如龍樹菩薩所造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修法》一樣的修法儀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前序”中説,這是龍樹菩薩所集《聖佛母多心經觀行要門》,而在它的“御製後序”中則又説,這是一部《真空觀門施食儀軌》,其中提到了“觀行”和“施食儀軌”這兩種或可分别歸諸漢、藏兩種不同的密教修習系統的修法。而當我們仔細地閲讀這部觀行要門的内容時,則不難發現它所傳的修法或正是由“觀行”和“施食儀軌”兩部分組成,或者説它是將這兩個儀軌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個兼融二者的新儀軌。
“觀行”是唐以來漢傳密教所傳修法,曾於漢傳佛教徒中有較廣的傳播,今於漢文《大藏經》中可見唐不空上師翻譯的《無量壽如來觀行供養儀軌》等七種不同的“觀行儀軌”。從這類儀軌中所描述的“觀行”修法來看,它與藏傳密教中的“本尊禪定”類似,可歸爲密教行部的修習法。所謂“觀行”,與藏傳密教中常説的“見(lta ba)、修(bsgom pa)、行(spyod pa)、果(’bras bu)”中的“修”和“行”對應,其中的“修”即指“觀修”或者“禪定”。顯然,這類“觀行儀軌”也曾於西夏得到過廣泛的傳播,不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見到了如《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行觀行儀軌》等文本,而且同樣見於西夏黑水城文獻中的一部傳自西夏皇建年間(1210—1211)的藏傳佛教所傳觀音菩薩修習法門匯集——《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其明確標明乃“重依觀行對勘定畢,永爲真本”,文中多處偈頌也都注明“依觀行録”。儘管我們無法確定這部觀音修法所依據的“觀行”儀軌是哪一部,但由此確認“觀行”修法曾於西夏流行,並直接滲入藏傳佛教所傳的儀軌中,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47)參見李嬋娜《黑水城文書〈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文本特徵與漢藏源流考》,沈衛榮主編《漢藏佛學研究: 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頁175—234,特别是頁175—178。
而“施食儀軌”則是西夏所傳各種藏傳密教修法,特别是各種本尊禪定和護法修法中非常常見的一種儀軌。見於《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中的這種“施食儀”相對比較簡單,但其基本内容與見於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的其他多種藏傳密教修法,如《欲護神求修》、《大黑求修并作法》、《金剛亥母集輪供養次第》和《金剛亥母略施食儀》等修法中所傳的“施食儀軌”基本一致。(48)《欲護神求修》,《俄藏黑水城文獻》(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34;《大黑求修并作法》,《俄藏黑水城文獻》(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2—59;《金剛亥母集輪供養次第》,《俄藏黑水城文獻》(5),頁241—244;《金剛亥母略施食儀》,《俄藏黑水城文獻》(6),頁275。無疑,見於《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中的這種施食儀軌不見於出現了“觀行”法門的唐代漢傳密教修習中,故它當是藏傳佛教的修法。值得一提的是,《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與傳爲“元天竺俊辯大師唧銘得哩連得囉磨寧及譯主僧真智等譯”的《佛説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的前半部分在結構上十分類似,後者雖然更加簡單,但其修法同樣也分爲類似“觀行”與“施食儀”的兩個部分。(49)《佛説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T.977),《大正新修大藏經》(19)。實際上,這部《佛説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是西夏時代的譯本,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及其發願文於西夏遺珍中亦多有發現,可以肯定大白傘蓋修習法於西夏時代已有較廣泛的流傳,(50)參見史金波《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及發願文考釋》,《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頁8—16;浜中沙椰《モンゴル時代におけるチベト仏教信仰に西夏が與えた影響——コデン統治下における白傘蓋經の刊行を通して》,《日本西蔵學會會報》第64號,2018年,頁1—12。所以,德慧或依此類儀軌的樣式,融合“觀行”和“施食儀軌”這兩種分屬於漢藏密教修習傳統的不同修法,創造了這部漢藏交融的《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
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這個文本中出現如下一段“回施”偈,曰:“諸佛正法菩薩僧,直至菩提我歸依,我以施等諸善根,爲有情故願成佛。”這是藏傳佛教中最有名的一首“歸依發心偈”,它常見於後世藏傳佛教各教派著名上師們的各種著作和説法中。這首“歸依發心偈”最初當出現在藏傳佛教後弘期初期來西番傳法的印度最著名“孟加拉”上師、噶當派鼻祖阿底峽(Atisa Dīpamkara Srījna, 982—1054)所造的多種論著中。至少在阿底峽的《發心與律儀儀軌次第》(Semsbskyeddangsdompa’ichoga’irimpa)、(51)《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卷6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2004年,頁669—670[1071]。《初業菩薩入道説示》(Byangchubsemsdpa’lasdangpopa’ilamla’jugpabstanpa)、(52)《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卷64,頁1801。《菩提道燈釋難》(Byangchublamgyisgronma’idka’ ’grel)(53)《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卷64,頁1687。等三部著作中,都曾出現了這個“歸依發心偈”。例如,於《發心與律儀儀軌次第》中,阿底峽上師云:“如是,發心之補特加囉爲增長發心故,至少晝夜各誦〔下偈〕三遍:‘諸佛正法菩薩僧(衆中尊),直至菩提我歸依,我以施等諸善根(施爲),爲有情故願成佛。’如是發菩提心。”(54)de ltar sems bskyed pa’i gang zag gis byang chub kyi sems spel bar bya ba’i phyir tha na nyin lan gsum mtshan lan gsum du sangs rgyas chos dang tshogs kyi mchog rnams la/byang chub bar du bdag ni skyabs su mchi/bdag gis sbyin sogs bgyis pa ’di dag gis/’gro ba phan phyir sangs rgyas ’grub par shog/ces byang chub tu sems bskyed par bya’o.《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卷65,頁669—670。《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中出現的這首“回施偈”,當是阿底峽造“歸依發心偈”迄今所見的最早的漢譯文。德慧於此將它如此自然無礙地運用進了應該是他自己造的這部融合了漢藏兩種密修傳統的持誦《心經》要門之中,這不得不讓人對德慧國師所代表的西夏佛教之融合漢藏佛教的水準刮目相看。
事實上,不僅《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或曰《真空觀門施食儀軌》這部修持《心經》觀行要門凸顯了漢藏圓融的性質,而且從這個文本的“御製後序”所云:“請覺行國師等,燒施滅惡趣中圍壇儀,并拽六道,及講演《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作法華會,大乘懺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等事,懇伸追薦之儀,用答劬勞之德。”也可以明顯看出西夏時代佛教修習的特色就是漢藏、顯密兼修,或者説是漢藏、顯密圓融。
四

《欲護神求修》是一部修習黑色天母,以其爲欲護神護法的長篇求修儀軌。其中共包含三十八種不同的修法,它們是:
初正明禪定,二伏寃魔,三建立中圍,四應奉施食,五截病加行,六折伏盜賊,七害寃法事,八截諸疾病,九憎法事,十和要門,十一生熱患要門,十二追盜加行,十三截風法事,十四脱獄加行,十五截買賣儀,十六經榮利便,十七買賣門通,十八生熱患,十九生風疾,二十寃人離鄉,二十一藥上加功,二十二足疾要門,二十三淨眼行,二十四勾召神鬼,二十五擁護田苗,二十六回避惡夢,二十七截患,二十八除方惠本病,二十九求資糧行,三十勾勝惠,三十一寃人哩俄行,三十二班衣緊行法,三十三哩誐卒亡,三十四自他擁護,三十五唯他自擁護,三十六龍王施食,三十七慶輪法行,三十八緊行勾法。(59)《俄藏黑水城文獻》(5),頁16—17。
從上引諸修法的名目來看,這部儀軌非常獨特,與我們常見的西夏和元代所傳的大部分藏傳密教儀軌很不一致,其中有些看起來甚至會讓人聯想起古代漢地曾經流行過的巫蠱或魘勝之法等,如其中的“寃人哩俄行”(lingga, ngar mi)等,所以,今人很可能會懷疑它是後人僞托蓮花生大師所造的一部僞經。以往人們對藏傳密教修法更多接觸和注意到的是密教四續部最高層次的修法,也就是其大瑜伽(大修習)或曰無上瑜伽部的各種修習法,如包括被人習稱爲“雙修”的欲樂定在内的無上瑜伽圓滿次第的氣、脈、明點修習等。事實上,藏傳密教的修習同樣也包括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修法。(60)關於密教四續部的建立,詳見楊傑《論藏傳佛教續部分類之形成及其印度源流》,《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4期,頁56—65;同氏《公哥寧卜所造〈續部總安立〉譯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349—361。而這部題爲《欲護神求修》的密教儀軌即當屬於密乘佛教下三續部的修法,從其結構和内容來看,與寧瑪派的部分“伏藏”(gter ma)類似,説它乃“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薩鉢瓦造”恐並非没有根據的僞托。雖然,迄今我們尚無法找到與它完全相應的藏文原本,但不難在藏文佛教文獻中找到與它類似的文本。例如傳爲蓮花生大師心子的著名掘藏師法自在上師(Gu ru chos dbang, 1212—1270)所發掘的一部題爲《具鐵髮髻黑馬頭明王修法》(rTa[mgrin]nagpolcagsralcangyisgrubthabs)的伏藏,不但其文本的形式和結構都與《欲護神求修》有相似之處,而且還明確標明它是蓮花生大師親自巖藏的伏藏,並列出了自蓮花生大師經松贊干布、赤松德贊等傳承至法自在上師的完整傳承次第,但是其内容顯然要比《欲護神求修》簡單得多,而且比較而言或更顯現出寧瑪派所具有的西藏本土特色。(61)Gu ru chos dbang,rTa [mgrin] nag po lcags ral can gyi sgrub thabs. 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水城出土文獻中也出現過一部題爲《鐵髮亥頭欲護神求修續》(TK322)的漢文密教儀軌,爲元寫本,可惜大部已殘,無法得見其廬山真面目。從其標題來看,卻很容易讓我們將《欲護神求修》儀軌和《具鐵髮髻黑馬頭明王修法》連接在一起。楊傑博士指出,《黑馬頭明王》之十三支修法名目如下: 觀本尊、誦咒、迎請智慧(轉下頁)
此外,在俄藏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中,我們還見到了一部題爲《大黑求修并作法》(B59)的元代寫本,其中所描述的種種修法與《欲護神求修》中的修法十分類似,明顯是同一種傳承和類型的修法。(62)(接上頁)尊、護輪、寶瓶儀軌、塗藥、調伏兇暴厲鬼、降雨、止雨、調伏夭折鬼、誅殺與鎮伏、防雹、食子等。其修法内容有較明顯的西藏本土化特色(如止雨、防雹),更重要的是具有典型的寧瑪派大瑜伽特徵。即一、 依三等持(ting ’dzin gsum,真如定、遍照定、本因定)漸次生起馬頭明王本尊,而欲護神儀軌無此操作,而直接頓成欲護神;二、 誅殺鎮伏儀軌部分,與寧瑪派所有大瑜伽誅殺法一樣,唯用金剛橛(rdo rje phur bu)釘住象徵魔祟之哩俄,其餘步驟則唯有觀想(無書寃人姓名、用寃人迹下土、針紮線纏等細節),與欲護神求修所見害寃人(此爲令實在的活人生病、死亡)法事的操作模式與目的明顯不同。簡言之,廣見於寧瑪派伏藏體系誅殺法(主要存在於大瑜伽之“八大修部”bka’ brgyad〗修法中)本質是實施誅滅後將誅滅對象(魔障)的神識超度至解脱的界域,故英文將sgrol ba翻譯爲liberative killing。對於這一理念的詳細解説見Cathy Cantwell, “To Meditate upon Consciousness as Vajra: Ritual ‘Killing and Liberation’ in the rNying-ma-pa Tradition”, Helmat Eimer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wien, Verlag der Österrie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pp.107-118。筆者於此感謝楊傑博士上述精到論述。由此可見,寧瑪派稍後所傳之具鐵髮髻馬頭明王之修法與屬於下三部密續的欲護神、摩里支的誅殺法有非常明顯的不同之處,比較而言,後二者或許更能反映出下三部密續於印度初傳時的原初面貌。(63)《俄藏黑水城文獻》(6),頁42—59。這或可用來作爲確定這部傳爲蓮花生大師所傳的《欲護神求修》儀軌肯定不是西夏人僞托的一個有力證據。實際上,《欲護神求修》是屬於“黑色天母”部類的一種修法,而《大黑求修并作法》同樣也是“大黑天〔母〕”部類的修法,它們都將黑色天母作爲一種護法神來修習。欲護神本爲一發惡願之女,被黑色天母折伏而成爲護法。欲護神和大黑這兩種修法本質上均屬“事業法”(’phrin las),所以其中各種具體的修習法非常類似。這些修法與黑水城出土文獻中出現的其他衆多以觀修爲主的“本尊禪定”修法不同,前者或更多是事部和行部的修法,而後者則是瑜伽部乃至無上瑜伽部的修法。
例如,《欲護神求修》中的“寃人哩俄行”修法是這樣的:“弟三十一殘害哩俄儀者,於五月五日,采寃人足印土,造四八指哩俄像,心頭三角坑,於樺皮上書畫哩俄名像,入在三角坑内,入定、念咒百八遍。次用四指量鐵金剛,栓一個法骨亦得。若臨壞時,其面向日,語誦本咒,尾添寃人名,馬囉野吽癹,將金剛栓於寃人心上,一咒一刺。如是每日加行作法,至三日滿時,決定成就。法事畢時,將前哩俄棄流水中,念解脱咒: 啞諦莎訶。”(64)《俄藏黑水城文獻》(5),頁31。
同樣,我們在《大黑求修并作法》中見到了多個與上引“寃人哩俄行”基本一致的修法,雖然具體修法有詳有略,但基本的結構和次第完全一致。例如見於《大黑求修并作法》中的一個完整的“大黑求修法”是這樣的:
敬禮吉祥形嚕割
夫修習人,先已作大黑,親念福足訖,欲作法行時,用寃人迹土,或大水合流處土、古城土、絶門人土、屍林等諸不祥土,與之熱相和,作一量藺葛。然屍林布上,用毒藥、塩、菜子作末,并人血等相和,爲以人脛骨,或鷀烏翎筒内,作筆,畫寃人相,彼相心頭,仍依喉喉字字,畫輪中央,書一字,周圍字頭向外,左書八二合摩訶葛辢某甲吽吽癹,然自入所樂佛定,心頭及面前,大黑心頭,出無數智大黑,向寃人擁護佛神等處,如是白云矣。
爲毁滅正法 護寃神汝聽 彼具大毒心
破懷三寶師 滅法害有情 惱諸修習人
墮千闍那下 極受地獄苦 我今速遠離
受色界天供 汝者莫擁護 具業人速捨
依此委曲已,於護神處,真實供養。若是智神者,奉送於所依宫位,或入自身;若是卋間神,則令折伏,囑付法行,將寃人想,令神等捨離。應如是緊誦:八囉二合摩訶葛辢也某甲阿葛折也拶吽吽癹咒。出無數大黑化身,遠離護神寃人,用鐵鈎鈎心,羂索練(縛?)項,及種種器械中捶撻,想彼等不得自在。令勾入前畫相内,誦: 八囉二合摩訶葛辢也某甲馬囉也吽吽癹咒。用毒藥、菜子、熱水,將畫相洒潑已;然從足緊卷,以黑色線十字,繫定藺葛心頭。又依先出神等已,塩、菜子、毒藥水内蘸棘針,於五根及枝節上竪劄,安息香上令熏訖;復毒將(將毒)藥、菜子、三熱水依前,誦大黑間名咒,洒潑,然與大黑伸供讚嘆,囑付法行,如是晝夜六時,作二十一日,此者求修法行竟矣。(65)《俄藏黑水城文獻》(6),頁45。
顯然,上引這兩個法儀都是借助大黑天母求修來修誅滅“寃人”之法,雖然具體的修行程式不完全一致,有繁有簡,但二者都采用了借助“人偶”來表徵“寃人”,從而對其施行密法的方式而作求修。有意思的是,在《欲護神求修》中,表示“人偶”的詞稱作“哩俄”,而在《大黑求修并作法》中,它卻被稱作“藺葛”,而不管是“哩俄”,還是“藺葛”,它們無疑都應該是梵文lingga一詞的音譯,其意義於此即爲“人偶”、“人形”,大致與藏文詞ngar mi相應。“哩俄”大致代表了西夏時代lingga的譯音,而“藺葛”則反映了元代的譯音。(66)西夏時代河西方言中,“哦”的聲母爲疑母ng,帶同部位的塞音g,音標寫作ŋga,與“哩”(li)相連,讀爲“liŋga”,故以“哩俄”音譯lingga頗爲貼切。若用《蒙古字韻》反映的元代官話來讀,則作“li ŋ”,差距較大。西夏時代河西方言中,“藺”字屬於“真韻”,讀爲葛”字屬於“曷韻”,讀爲“ka”,二者相連即與lingga讀音差異較大。相反,此處“葛”字即後世音譯用字“噶”,若用《蒙古字韻》反映的蒙古官話來讀,則爲“lin ka”,與lingga的讀音一致。因此,從“哩俄”到“藺葛”音譯用字選擇的變遷,折射出翻譯用方言的語音變化,同時也間接標示了二者的時(轉下頁)
如前所述,見於《欲護神求修》和《大黑求修并作法》中的這類“寃人哩俄行”修法當是密教下三續部中常見的一種修行儀軌,藏傳佛教學界以往對這類修法的研究不多,故至今没有人對出現於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的這類儀軌有足夠的注意。(67)(接上頁)代區隔。以上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杜旭初博士惠示,於此謹致謝意。(68)由於下三部密續及其修法在印藏密教發展進程中逐漸被邊緣化,而無上瑜伽部在西藏占據了絶對主導地位,故學界對於下三部密續在後續高階密續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有明顯的低估,對其傾注的研究力度也明顯不足,這也導致了部分學者對一些保留有前弘期所傳事續部教法元素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未能作出正確的解讀。有關這些問題的具體討論,詳見Robert May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derworlds: Asuras’ Caves in Buddhism, and Some Other Themes in Early Buddhist Tantras Reminiscent of the Later Padmasambhava Legend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2007, Issue 3, pp.1-31。像“寃人哩俄行”這類修法對於我們太過陌生,以至於會懷疑它是否真的來源於藏傳佛教。可幸的是,晚近有人於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藏的黑水城出土文獻中又檢出一批原來被以爲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本,它們正好是一系列與大黑天修法相關的文本,其中的部分又恰好就是與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中那幾種與大黑天求修相關的儀軌文本對應的藏文原本,這無可質疑地證明了西夏時代所傳的這些大黑天求修法確實是藏傳密教的傳統。即使是“哩俄”(“藺葛”)這樣看起來類似漢地早已流行過的巫蠱類修法也確實不是西夏佛教徒的僞托或者僞作,而確實是傳自藏傳密教的。前引《大黑求修并作法》的藏文原本即見於晚近披露的這一批黑水城出土古藏文文獻中,其中關於“藺葛”修法的段落既可幫助我們讀懂這個本來不易理解的漢文譯本,同時也證明了它的確切來源。(69)Alexander Zorin, Buddiyskie ritualnye teksty. Po tibetskoy rukopisi XIII v., Nauka, Vostochnaya liteatura, 2015, pp.82-83. 與前引《大黑求修并作法》中(轉下頁)
上述這類文本的發現本身,(70)(接上頁)“藺葛”修法相應的藏文原文如下: dpal he ru ka la phyag ’tshal lo/nag po chen po’i bsnyen pa sngon du song bas//las bsbyor bsgrub pa ’dod na//bsgrub bya’i rkang rjes pa dang/chu chen po ’dul ba’i sa dang/grog ’khar gyi sa dang/rab chad shul gyi sa dang/dur khrod la sogs pa’i bkra mi shes pa’i sa rnams dang//tsha ba gsum bsres pa’i de’i ling ka gcig byas la/ro ras la sogs pa la dug dang tsha dang/ske tse rnams myi khrag la sogs pa’i snag tsa la myi rkang ’am bya rog gi sgro’i bsnyug gus dgra’o ’i gzugs bris pa’i snying kar/e’i dbyibs can ’khor lo bris la/de’i dbus su om bris pa’i mthar g.yon bskor gyis/om badzra ma h k la ya che ge mo m ra ya hūm hūm phat/zhes pa’i ’go phyir bstan pa ’bri’o/de nas bdag nyid lhag pa’i lha’i thugs ka dang/mdun kyi nag po’i thaug ka nas ye shes ’gon po dpag du myed pa spros pas/bsgrub bya bsrung bar byed pa’i lha gang yin ba de la ’di skad ces/bde’ mchog du sgogs nas rang gi snying ka nas bde’ mchog spros pas lha dang dbral ba la bsogs pa bya/des mdun gyi ’gon po’i thugs ka nas ’gon po spros pas dgug gzhug bya’o/bstan pa ’jig par byed pa’i/dgra’o srung bar byed pa’i lha khyod tshur nyon/dgug pa’i sems ldan dgra’o yis/dkon cog bla ma la smod cing/bstan la sdang zhing sems can tshe’/rnal ’byor ba rnams brnyas ’gyur nas/dpag tshad stong du lhung ba’i/dmyal ba’i sdug bsngal myong bar ’gyur/bdag gis myur du bsgral nas ni/gzugs kyi lha rnams mchod par bgyi’/khyod kyis bar bar ma byed cig/sdig can dgra’ ’di myur du yongs/zhes bkra’ bsgros bar bsams la/de’i lha yang dag par mchod cing ye shes pa yin na rang bzhin gyis gnas su gshegs pa la/rang la sdu’o/’jig rten pa yin na dam la btags la las bcol lo/bsgrub byed lha de thams cad kyis sangs par bsams la/de nas ngag du ’di skad ces//om badzra ma h k la ya che ge mo kar sha ya dzah hūm hūm phat/ces drag du brjod la/sprul pa’i ’gon po dpag du myed pa’ spros pas/skyabs dang bral ba de lcags kyu dang zhags pas snying la nas bkug nas bzungs ste/tshon cha sna tshogs kyis bdeg cing rang dbang myed par bkug pas/bris pa’i ling ka la bstims la/dug dang tse ske dang tsha ba’i chus/om badzra ma h k la che ge mo’i m ra ya hūm hūm phat/ces pas brjod cing brab po/de nas rkang pa nas dril la skud nag gis rgya gram du bskris la/ling ka’i snying kar bcug la/yang sgnar bzhin spros pa la sogs pa bya ste/tshigs rnams dam po rnams su dug rang khrag dang ske tse tsha’i chus sbags pa’i tsher ma btsugs dang ske tse tsha’i chus sbags pa’i tsher ma btsug la/gu gul nag pos bdug cing dug dang ske tse dang tsha chu sngar bzhin du/nag po chen po’i sngags sprel tshig dang bcas pas brab po/de nas nag po chen po la mchod pa dang gtor ma dang bstod pa byang zhing/las grub par gyis shig ces brjod do/de bzhin du zhag nyi shu rtsa gcig du nyin mtshan du thun drug du bya’o/.或正説明於西夏、元代民間所傳的藏傳密教修法更多的並不是後人津津樂道的“欲樂定”一類的無上瑜伽部修法,而是這些或更受民間普通信衆歡迎的下三續部的修法儀軌。值得一提的是,既然上述這些於西夏和元代流行的藏傳密教修法多爲屬於密教下三續部的修法,那麽它們自然亦當可見於以弘傳下三續部修法爲主的漢傳密教之中。果然,我們在北宋著名譯師天息災(?—1000)翻譯的一部題爲《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的密教文獻中,發現了與上引《欲護神求修》和《大黑求修并作法》中出現的這類修法十分類似的儀軌,足可證明像“寃人哩俄行”這樣的修法不僅見於其來源一直受到懷疑的西藏舊譯密咒的伏藏之中,而且它應該是印度密乘佛教下三續部中比較常見的修法,不管是求修哪個本尊、護法,其具體修法中都可以出現這類誅滅寃人的修法。進而言之,漢傳密教與藏傳密教於此類修法中出現的這種相似性質復足以證明二者實際上具有同一來源。
我們在《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中發現了諸多可與《欲護神求修》和《大黑求修并作法》中所述“寃人哩俄行”相似的修法,儘管其中並没有出現“哩俄”或者“藺葛”這樣的名稱,譬如:
復有成就法,能令寃家生其病苦,爲害不成。用燒卻人灰土及骨粖,復取寃家腳下土,同和一處爲埿,作寃家形。復用毒藥、芥子乳、阿里迦木同合,書寃家名及真言,書在屍衣之上。其真言曰: 唵引摩引里支引阿母劍入嚩二合里拏誐里二合恨拏二合誐里二合恨拏二合波野吽吒娑嚩二合引賀。復誦此真言八百遍,藏寃家舍下,令彼生病。或用一髑髏,以前毒藥乳等,於髑髏上書寃家名,及書一字,於字周回書四箇囉字,以佉禰囉木火炙其髑髏。彼髑髏 作惡相,藏在寃家舍中,決定生病。若欲殺寃家命,亦用毒藥鹽芥子自身血合爲墨,以人骨爲筆,亦於髑髏上書寃家名,并書吽二字,念真言八千遍,彼決定死。真言曰: 唵引摩引里支引吽阿母劍摩引囉野吽吒娑嚩二合引賀。誦此真言已,若將髑髏埋在屍多林中,第三日命壞。(71)《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卷一(T.1257),《大正新修大藏經》(21),頁264中。標點爲筆者所加,下同。
復有成就法,用河兩岸土及寃家足下土同合,作彼人形。如前所説藥物等,於屍衣上或樺皮上,書彼人名及真言,置彼心中。用無憂樹木作橛,長八指,釘彼形心,誦真言,稱彼名,三日之内,設是聖人,須見降伏,何況凡夫之類。(72)《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卷三(T.1257),《大正新修大藏經》(21),頁270上。
不難判定,上引見於《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中的這兩種成就法與見於《欲護神求修》和《大黑求修并作法》中的“寃人哩俄行”修法本質説來是完全一致的,它們都是源自印度的屬於下三續部的密乘修法。(73)依藏土密續部建立體系,與摩里支(Mrīci)相關的續典及其修法被判爲事續。例如,克主傑(mKhas grub rje dGe legs dpal bzang po, 1385—1438)於其《密續部總建立廣釋》(rGyud sde spyi’i rnam par bzhag pa rgyas par bshad pa)中指出光明天女(摩里支)爲事續中如來部之部妃續:“部妃即光明天女及五羅刹女,有《光明天女陀羅尼》説陀羅尼及其殊勝利益;又有一《光明天女經》廣説陀羅尼義,及修成就法詳細儀軌。此二種皆共許屬事續。”依談錫永譯《密續部總建立廣釋》,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頁81。英譯見F. D. Lessing and A. Wayman,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antric System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8, p.11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主宣六臂大黑天的《吉祥大黑天續》(Srīmahkla-tantra)也被歸爲事續,屬如來部之天龍藥叉等續,見談錫永上揭書,頁88。以上亦承楊傑博士惠示,於此謹致謝意。由此可以證明黑水城出土文獻中這部標明爲“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薩鉢瓦造”的《欲護神求修》的真實性,説明西藏所傳舊譯密咒中出現的這類修法有其確鑿的印度來源。宋初經天息災、施護、法護等譯師翻譯的大量密教續典而傳入漢地的那些密教修法,顯然與同時代或略晚傳入藏地以及西夏等地的藏傳密教修法,有很多相同或者類似的内容。無疑,這是一個至今鮮爲人知,尚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重要學術課題,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去深究,其成果則必將整個地改變漢藏密教史的寫作。
五
於俄藏黑水城出土漢文佛教文獻中,我們還見到了一部題爲《四字空行母記文》(俄藏TK329)的密教文本,它是一部對某一種金剛瑜伽母(亥母)求修儀軌的釋論,其中對其由印度經西番復傳於西夏的傳承世系有明確的記載,是研究西夏時代藏傳佛教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尤爲珍貴的是,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獻中,我們也見到了一部題爲《亥母耳傳記》的藏傳密教文本,其内容與漢文本《四字空行母記文》基本一致,但較後者更爲完整,可略補漢文本中之殘缺和不足。(74)對這兩個文本的前期研究分别見孫鵬浩《有關帕當巴桑傑的漢文密教文獻四篇》,《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77—188;孫伯君《西夏文〈亥母耳傳記〉考釋》,沈衛榮主編《大喜樂與大圓滿——慶祝談錫永先生八十華誕漢藏佛學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頁145—180。同時有西夏文和漢文兩種文字的版本存在,對它們作比較研究,顯然可爲研究者正確識讀和理解這個密教文本提供極大的幫助。
西夏文《亥母耳傳記》有題記注明它是“西番中國松巴明滿名稱師造”,故知其作者當是一位西藏的上師,其名字當可構擬作Sangs rgyas grags pa。漢文本《四字空行母記文》闕題記,然於其所列遠傳、近傳宗承上師名單時,也列有“辢麻松巴性散哩結章光正覺寶昌師”名,此人當就是西夏文本中提到的那位“西番中國松巴明滿名稱師”。儘管知道他的名字是Sangs rgyas grags pa,譯言“明滿名稱”或“正覺寶昌”、“覺稱”,或者“散哩結章光”等等,但這位“辢麻松巴”的確切身分依然難以確認。於這一時代比較著名的上師中名Sangs rgyas grags pa者,或可推傳爲來自西夏的西番上師rTsa mi lo tsa ba Sangs rgyas grags pa,譯言“草頭譯師覺稱”。(75)參見Elliot Sperling, “rTsa-mi lo-tsa-ba Sangs-rgyas grags-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Tibetan Relation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Oslo, 1994, pp.801-824. 關於松巴明滿名稱師的名字和身分的討論,也參見索羅寧《〈金剛般若經頌科次纂要義解略記〉序及西夏漢藏佛教的一面》,《中國藏學》2016年第2期,頁93—101。對“辢麻松巴性散哩結章光正覺寶昌師”的討論參見高山杉《玄密帝師與無生上師》,《讀書》2012年第3期,頁31—40。
由於既難以確定這部《四字空行母記文》或者《亥母耳傳記》作者的具體身分,又找不到與它們相對應的藏文文本,所以要正確地解讀這兩個密教文本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前所述,西夏文《亥母耳傳記》注明爲“西番中國松巴明滿名稱師造”,而漢文本《四字空行母記文》乃“辢麻松巴性散哩結章光正覺寶昌師”所傳,故它們應當就是同一個藏文文本出於同一時代的二種不同文字的譯本,對它們進行比較和對讀至少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這兩個文本的字面意義。其實,即使是我等專業學習藏傳佛教的學者,在找不到相應的藏文原本的情況下要讀懂這類密教性質的漢文文本誠非易事,要確定其每一個句子的準確句讀,領會每一個讀來覺得冷僻的詞彙的微言大義,都頗費思量。而對於從事西夏文研究的學者來説,要正確理解和解讀西夏文密教文本,其難度無疑更大。如果他們不太理解文本中所傳印藏密教的甚深密意,則非常容易對文本作出錯誤的對應詞彙選擇和句讀。所以,若能有同時代的漢譯本作爲參照,並對西夏文、漢文兩種文字的文本進行逐字逐句的比對、推敲,則無疑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確定這個文本的句讀,並正確理解這個文本的基本意義。顯然,這樣的對讀和比較研究,對於我們更準確地重構和理解西夏文文本,互相補足文本中缺失的和難以理解的部分,進而獲取更多有關這些譯本的傳譯者身分、翻譯年代和版本等信息,從而對這一印藏密教文本的内容和傳習歷史,甚至對西夏佛教的性質得出不同的理解和思考,都將極有幫助。
通過對漢譯《四字空行母記文》與西夏文譯《亥母耳傳記》的對照閲讀和比較研究,我們很驚訝地發現,如果説《亥母耳傳記》或是一個藏文原本直接的西夏文翻譯的話,那麽,《四字空行母記文》應該是一個已被其漢文傳譯者做了不少有意的改譯和增删過後的文本,其中明顯摻入了一些當不見於其藏文原文本的、純粹屬於漢傳佛教和漢文化因素的内容。這些内容顯然是傳譯者爲了使這個文本及其所傳達的密教義理和儀軌更容易爲漢人信衆接受和理解,而有意爲之的一種非常善巧的改變。例如,《四字空行母記文》對其標題《吉祥金剛修習母求修》中的“吉祥”與“金剛”二詞作了如下解釋:“不依華言釋者, 言吉祥者有二: 一自吉祥者,自悟真理,無外所證,本自清淨,故名自吉祥。二他吉祥者,依法修習,慈悲深厚,令諸有情得利益,故名他吉祥。言金剛者,金即不壞,堅固爲義,剛即能摧衆魔,息除煩惱,快利爲義。從喻得名,表顯法身,無相可得,等同虚空,遍衆生心,了諸妄想,無分别相,一念悉知三知世法故,空樂自性亦復如是。譬如幻師,亦現無邊,隨順衆生,無心所現。大樂妙性,本無煩惱、貪嗔等念,即是五佛母,了知佛母是空樂自性,無深無壞,故名金剛。”(76)《俄藏黑水城文獻》(5),頁117。而同樣的段落在西夏文本《亥母耳傳記》中僅簡單地作:“吉祥謂者,有自、他二種;謂金剛者,不壞義也。”(77)孫伯君、聶鴻音《西夏文藏傳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經典研究》,頁268—269。可見,《四字空行母記文》中這段對“吉祥”和“金剛”的解釋很可能不見於其藏文原文本中,它們當來源於漢傳佛教的某種解釋。
我們知道,不管是在梵文中,還是在藏文中,與漢文“金剛”一詞相對應的語詞Vajra和 rdo rje都不是一個可以被如此分開來解釋的語詞,如果硬要把藏文的rdo rje分解開來解釋的話,那也只能把它分解作“石王”,然後分别對“石”和“王”進行解釋,與上引這種對“金剛”一詞的解讀完全不一致。而將“金剛”作如是解釋者,在西夏文佛教文獻中卻顯然不是頭一次出現。例如,在西夏文本《金剛般若經頌科次纂要義解略記》中,就出現了與《四字空行母記文》中完全一致的釋文,其中作:“名字中‘金’者,堅固,以它不能壞之;‘剛’者,剛巧,以之能破一切他物故。”(78)參見索羅寧《〈金剛般若經頌科次纂要義解略記〉序及西夏漢藏佛教的一面》,《中國藏學》2016年第2期,頁96。
此外,《四字空行母記文》中對“亥母”的解釋顯然也比《亥母耳傳記》要詳細和複雜得多,其中顯然也有添加的成分,其云:
言亥母者,法體無二,應物現形,是毗盧之妙體,法身之真用,故現亥母之身軀,傳密契之妙法。説法應機,故詮内、外、密求修也。又言亥者,表斷陰陽之見,非屬晝夜、離二邊也。欲義釋,則無增愛之念,現無分别性,又超於輪回,度諸有情,令得圓寂,入法界故。此望增義説究竟説,則阿瓦恧帝,遠離二邊,以無執着,空樂常顯,不着時分而出生故,故名亥也。言母者,表現勝惠之相、法性之理,具出生故,空無質,能利有情,出生諸法,内契於理,内合衆生長養義故。望增義説也究竟説則中脈體空,能生涅盤(槃)生死之脈,具四輪相,轉生諸脈,長養身軀體,所生世出間世(世間)皆從阿瓦恧帝而出生故,故名母也。有此无比具勝德故,故名亥母也。(79)《俄藏黑水城文獻》(5),頁116—117。
而與此相應的段落在西夏文《亥母耳傳記》中僅作:“亥母者,如無愛憎之念,依無分别之勝義,謂亥;現陰相,謂母。又亦謂亥者,輪回中特出,及度救拔諸有情,令得圓寂入法界,謂亥;謂母者,依法性之義,謂母。”(80)前揭孫伯君《西夏文〈亥母耳傳記〉考釋》,頁158。它只相當於《四字空行母記文》中的“義釋”部分,而省略了對它的字面意義和究竟意義“究竟説”的解釋。不僅如此,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四字空行母記文》對“亥母”(varahi, phag mo) 之“亥”字的字面意義的解釋,竟然是按照漢族以天干地支爲時間之分野的概念,説“又言亥者,表斷陰陽之見,非屬晝夜、離二邊也”,此即是説,亥時乃十二時辰中的最後一個,故它隔斷陰陽,且連結晝夜。或者説,亥時表示陰陽交接之時,所以不屬於晝夜,不着時分,遠離二邊。這純粹是一種只有懂得漢文化傳統的人纔能理解的解釋方法,顯然它應該是這個文本的漢文傳譯者爲了使它更容易爲漢人信衆所接受而有意加入進去的。
這個發現再次説明西夏佛教從本質上説正是我們要挖掘和研究的漢藏佛教的最好代表。很多西夏時代出現的漢文藏傳密教文本或都像《四字空行母記文》一樣,其中已經被傳譯者摻雜了不少原文中没有的純粹是漢傳佛教,甚至只是漢族傳統文化因素的内容,並做了十分符合漢文閲讀習慣的文字修飾和加工,成爲一個十分漢化了的文本。這給我們確定這些文本的來源,尋找其藏文的原本,製造了難以克服的障礙,但同時也爲我們理解西夏時代漢藏佛教交流和交融的歷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珍貴資料。
六
從以上對源自西夏時代的四種漢文藏傳佛教文本所作的文本分析和研究來看,西夏時代所傳的藏傳密教都附帶有明顯的漢傳佛教和顯宗佛教的成分。見於《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一組印藏佛教所傳“大手印法”文本,當既不是馬爾巴譯師所傳達波噶舉的内容,也不是薩思迦派所傳道果法中的三續道之一,而是源自銘得哩斡上師的“大手印”傳軌。這種“大手印傳軌”既有與“極無所住中觀”對應的顯教大手印,又有以修習氣、脈、明點的無上瑜伽“方便道”修法爲主的密教大手印,但作爲“解脱道”的大手印之正行修法通常是一種練習定心、直指心性,以證悟自性本淨、入樂空無二境界的禪定,它與漢傳禪宗佛教的修法有高度的契合,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違礙。見於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的那部《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則整合了唐代漢傳密教所傳的“觀行”修法與藏傳佛教中流行的“施食儀軌”,形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融合漢藏密教的《心經》修法。這部儀軌的造作者覺行國師德慧上師,顯然不但兼通梵、藏、漢、西夏諸種佛教語文,而且對印藏、漢傳和顯密佛教傳統都有非常深刻的瞭解,所以能如此自如地融合這幾種不同的佛教傳統,創造出像《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大手印究竟要集》這樣融合漢藏、顯密的西夏佛教文本。
傳爲“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薩鉢瓦造”的《欲護神求修》這一屬於舊譯密咒之伏藏類的密教儀軌於黑水城出土佛教文獻中的發現,使我們知道不僅是大瑜伽(大修習)或曰無上瑜伽部的各種修習法,如包含被人習稱爲“雙修”的欲樂定在内的無上瑜伽圓滿次第氣、脈、明點修習等,而且還有像“寃人哩俄行”這樣的或更受民間普通信衆歡迎的下三續部的修法儀軌等也曾在西夏流傳。而這類修法並不純粹是藏傳密教所傳的儀軌,在漢傳密教中也能找到與它們相應的修法。例如在漢傳密教所傳的《佛説大摩里支菩薩經》中,我們同樣可以見到這類誅滅寃人的修法。這一發現不但足以證明二者具有同一來源,而且也説明西夏時代所傳的藏傳密教修法具有圓融漢傳密教的成分。而通過對漢文、西夏文兩種文字的《四字空行母記文》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這個藏傳密教文本的漢文本並不是一個嚴格的翻譯本,其中加入了很多不見於原文中的内容,它用漢傳佛教甚或是純粹漢文化的成分,對文本中出現的“金剛”、“亥母”這樣純粹是印藏密教的詞彙作了全新的解釋。通過這種改變,傳譯者讓一個本來對於漢傳佛教徒來説非常陌生和難以接受的藏傳密教儀軌變得相對容易理解和接受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西夏佛教上師們爲圓融漢藏和顯密佛教所做的積極努力,而這正好反映出了西夏佛教具有漢藏和顯密兩種佛教傳統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