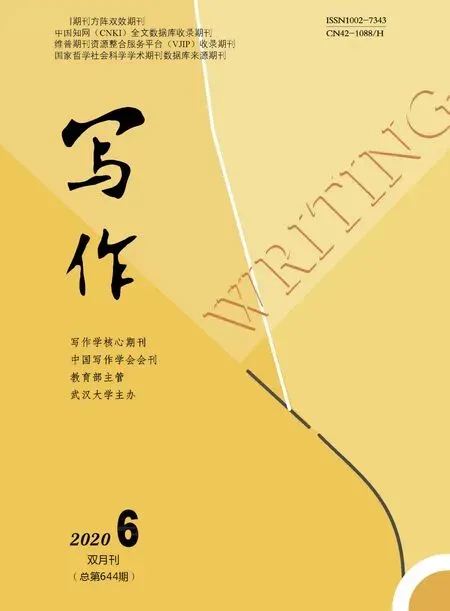文化批判的“鬼土”修辞
2020-11-25马兵
马 兵
“五四”潮起之时,奉“赛先生”之名,鬼神志怪之类都是被弹压的对象。不过,当新文化阵营的主将们经历了“五四”的落潮所带来的凄惶之后,虽然他们仍普遍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否认鬼神灵怪的现实存在,但也暗暗推动着作为一种重要人文资源的魅性叙事的潜滋暗长,各种关于“鬼”的谈说也渐渐多了起来。丸尾常喜在讨论鲁迅《阿Q 正传》时有一个颇有启发的说法,即阿Q 等于阿鬼,他认为阿Q 身上显示出“国民性”之“鬼”与民俗之“鬼”的兴味“深刻的复合”,并“由此展开了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民俗’的规模宏大的作品世界”①[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11 页。。不止鲁迅,现代作家不少也都有类似的表现。其实,对新文学自身而言,过分祛魅所造成的人文魅性的丧失,也导致审美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窄化,对新文学发展未必全是好事,何况就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的,道家的“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为中国本土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 “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不绝如缕。这其中,种类繁多的入冥故事为现代作家提供了可做现代之转化的特别资源。
一
死亡的发生和灵魂的观念催生了先民对于地府的想象, 入冥游历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都不鲜见,尤其在源头性的民族史诗中都会包含英雄游历阴间世界的情节,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这种降入冥府的行为同太阳每天的落入地下相对应”②[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6 页。,体现了先民对彼岸世界一种蒙昧又英雄主义的认知。中国中土冥界想象的形成其来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说:“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传·隐公元年》有很著名的“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一句,还有宋玉《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黄泉”“幽都”都是亡魂聚集之地。 两汉时墓葬考古发现的“墓券”,类似为死者购买埋身之地而出示给冥界的证明。 不过,先秦两汉时人们虽有冥界的意识,也出现了顾炎武说的“泰山治鬼”之论,但关于冥府的构想还是较为原初的,基本没有亡后或生人游历冥界的记载。
魏晋时,各种对冥府的记录和想象多了起来,如《搜神记》中有《胡母班》一则,说的是胡母班在泰山附近被“泰山府君”召见,替他给女婿河伯送信,又多次往返泰山鬼府,为父亲和孩子求生续命的故事。 与之相似的是《列异传》中的《蔡支》一篇,临淄人蔡支误入泰山,也被泰山君召见,要其帮忙送信给自己的外孙天帝,任务完成后,天帝允其死去三年的妻子还魂。 《列异传》中还有《蒋济亡儿》一则,说的是蒋济的儿子死后托梦给母亲,告知其母太庙里的西区道士孙阿任泰山令,他希望母亲能代为贿赂,可使自己在冥界得一禄位,后果心愿得遂。 这些冥府游历的故事,多写人与地府府君的交通,行鬼事如人事,虽也记录人死后在阴间服役之事,但尚未有强烈的地狱之罪谪和恐怖的观念。
到了南北朝时,情形有了较大变化。 这是因为自汉末之际,佛教西来,佛教中的地狱、果报之说开始与中土的冥界想象结合,重构出一个阴间系统,因此顾炎武道:“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 ……是魏晋以下之人,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30,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年版,第1313 页。
刘义庆的《幽明录》和王琰的《冥祥记》中有大量的冥府巡游故事,而且对冥府的描绘与前不同。《幽明录》中的《赵泰》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过渡性文本。 小说讲的是,赵泰“卒心痛而死”,停尸十日又复活,向世人陈述自己的冥府经历,他被阴间之鬼误拘,从“如锡铁崔嵬”的大城,后“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又在“开光大舍”见到佛主,复见“更变形城”等等。这则小说,一方面保留了“泰山府君”“泰山治鬼”的本土元素,另一方面则大大加重了地狱、形变、报应的佛教观念,如初入阴间,要被追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何功德,作何善行”,又被告知要以“惟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人生之乐。《幽明录》中还有《康阿得》《舒礼》《石长和》等数则类似的故事,另《冥祥记》中的《程道慧》《沙门慧达》等也如出一辙,或述地狱刑罚之酷,如“刀山剑树”“抱赤铜柱”,有“牛头人身”之怪和犬鸟啮人;或讲礼佛之人可免地狱之灾,显明了所谓“释氏辅教之书”的性质。
综合而言,这些以“入冥”为看点的短章在中国小说中“首次具体细致地描写了入冥和地狱,给小说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入冥母题和叙事模式”②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493 页。,对后世影响较大,像唐代《冥报记》《灵验记》《广异记》《通幽记》《朝野佥载》《玄怪录》《酉阳杂俎》《河东记》,宋代《东坡志林》《夷坚志》《墨庄漫录》等都大量包含入冥的题材,并有《崔环》《董慎》《杜子春》等名篇,艺术性大大增强,且在“辅教”之外,别有怀抱。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敦煌变文中有诸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敷衍“入冥”故事的作品,可见这一类型在民间的影响。唐宋以后,在宝卷、话本小说、杂剧戏曲等亲近民间的文学类型中,地府巡游的情节屡见不鲜,“目连救母”等更是广泛流传。
说到底,入冥既体现时代的文化认知和宗教信仰,更关乎世相人心。 因此,冥府如何呈现、意旨何在,就成为这类作品的一个关键。 《聊斋志异》中有《潞令》一篇,说的是潞城县令,为人残暴,公堂之上被仗毙的百姓甚多,此人还洋洋得意,某天忽然暴卒。蒲松龄就此言道:“幸有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声起矣,流毒安穷哉!”③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48 页。这里将人间公义系于阴曹,自然是反讽之意,而这正可代表各类入冥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方向,即“义”失而寻之于“鬼”——“入冥”叙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讲“冥判”的,如著名的“司马貌断狱”,便将历史事件和人物纳入果报的体系之中,人间的失道与得道最终逃脱不掉地府的终极裁判。 与之相对,还有一种入冥小说是将阴间等同于阳间,阳间的不公与腐败被照搬到阴间,阴间官僚和阳间庸吏是一丘之貉,如《广异记》的《六合县丞》《李洽》《张御史》,《冥报记》中的《王璹记》等都有阴司索贿的情节,可见徇私枉法之害无孔不入。
清乾嘉时期,文言志怪小说像《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秋灯随录》中入冥类的故事也不少,另张南庄所写吴语白话小说《何典》以“下届”“阴山”“鬼谷”三家村的土财主活鬼和儿子活死人一家两代的所闻所历为线,敷写鬼蜮,“鬼话连篇”,与传统的生人入冥类叙事有所不同,但对阴间地府众鬼吏的塑造颇有可观之处,尤其戏谑无忌的文风,“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小说使用大量的俚语歇后语,弃雅向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对圣人之言、果报之说都予以了痛快淋漓的拆解。“何典”即“出自何典”,暗含自立新体之意。鲁迅对《何典》有一妙评:“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 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 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①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8 页。某种意义上说,《何典》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相当一部分来自五四诸人的阐释和建构,鲁迅之外,刘半农、钱玄同、吴稚晖、周作人等对该书有所解说②参见袁一丹:《“吴老爹之道统”——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及思想资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2 期。。 这自然也引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现代作家如何看待鬼蜮、冥府、地狱之论,传统的“入冥”在现代文学中又会有怎样的转化和新变。
二
晚清时不少社会小说都有将现实忧患和批判托付冥界的构思,如女奴的《地下旅行》、书带子《新天地》、佚名《立宪魂》等,但大都水准平平。 另李伯元《活地狱》一书,算是谴责小说中格调较高者,此书用15 个故事揭露衙门黑暗、监狱积弊,取“活地狱”为名,是说“阴曹的地狱虽没有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 所以我说他的厉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③李伯元:《活地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1 页。。 1941年,华北沦陷区作家王朱著有长篇小说《地狱交响曲》,记述下等妓院里女性屈辱卑污、惨遭蹂躏的人生,“地狱”之喻与李伯元类似,旨在写人间罪恶之酷烈,让人有“非人间”之感。 这两部作品中间,还有不才的《醒游地狱记》、华清的《地狱游记》等,也大都类似,“地狱”的冠名只是为了表明小说揭露的黑暗之强度,与传统的入冥之叙事、地狱之理解等并无实际的关系。
在现代文学史上,对“地狱”的追问和表现最深切的是鲁迅。 1925 年6 月22 日,鲁迅在《语丝》发表了《野草》之十四,题为《失掉的好地狱》。 对于此文,鲁迅后来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 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④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65 页。。 孙玉石认为,“废弛”的“地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整部《野草》都可看作“那些被压在地狱中的‘鬼众’发出了深沉的诅咒和反叛的吼声”⑤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5 页。。如此理解,那鲁迅的这篇《失掉的好地狱》虽文笔奇崛高妙,远非前面列举那些挂名“地狱”的现实通俗讽刺小说可比,但在以地狱喻现实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木山英雄则认为,将鲁迅此文中的“魔鬼”“天神”和“人类”比附为现实政局中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射并不恰当,因为这会减损文中的“魔鬼”与“地狱”语义的丰富性。 他指出,文中的“魔鬼”乃是“青年鲁迅用梵语的mara 音‘摩罗’来翻译西洋的saturn 作法的延续,且在中国固有的‘神’‘人’‘鬼’谱系当中似乎基本上属于‘鬼’一方面的”①[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32 页。。张闳在对该文的解读中提醒读者,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地狱”意识,而“地狱幻象”更是构成《野草》的特殊图景②张闳:《于天上看见深渊——鲁迅〈野草〉中的深渊意识及沉沦焦虑》,《文艺争鸣》2018 年第5 期。。 的确如此,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借但丁《神曲》这样说:“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③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5 页。从对“摩罗”诗人的呼喊,到对“异端”的所爱,鲁迅的“鬼气”不但体现在对“亡魂”与“鬼”的二重理解中,也体现于对亡魂汇聚的“地狱”的二重理解上。
一方面,鲁迅的“地狱观”体现出很强的本土佛学信仰的渗透。 1912 年周氏兄弟在合作的《望越篇》中提出“种业”的概念:“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 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惯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 ……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④此文发表于《越铎日报》1912 年1 月18 日,署名独应,周作人后编入自己文集,孙郁认为此文是周作人执笔,鲁迅改定的。“业”的梵语音作“Karma”,本为行为和造作之意,佛家以为,众生因无明而造作诸业,包括善业和罪业,而凡自身所造之业因,必由自身承负所造成的苦、乐之果,此谓之“自业自得”。周氏兄弟这里所谓的“种业”即是国民根性,它是先验地存在于民族的基因中又遗传到每个个体身上,所以这“业”的源头才在“幽冥之界”“在死者”。 后来,在《坟》的后记中,鲁迅又说过:“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 ”这意味着“地狱”里的众多“死人”构成的“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是鲁迅国民性改造必须要面对并与之周旋的强大势力。
另一方面,青年鲁迅又相当看重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灵魂之说对人心之“信”与“诚”的意义,它们可以让人“欲离是有限相对值现世,以趣无限绝对值至上者也”⑤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2 页。。在谈到自己最喜欢的无常鬼时,鲁迅说:
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 人是大抵自以为街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⑥鲁迅:《无常》,《鲁迅全集》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8-279 页。
这正体现了前文说的,中国民间的地狱想象,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义”失而寻之于“鬼”,以阴间的裁决遥指阳世的不公,由此地狱中以“无常”和“女吊”所代表的鬼魂具有一种正义的复仇意志和维持公义、蔑视权贵的精神。 鲁迅对于以地府巡游为情节内核之一的目连戏评价之高,也是因为他在戏曲里的无常等形象身上看到了文学家断断做不出来的“人情”“知过”“守法”和“果决”⑦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2 页。。看似非理性的冥界审判,却具有呼唤正义的巨大势能,这自黑暗的地狱而来的黑暗气质恰恰可以成为“民魂”建设最倚赖的资源,甚至可以表现为一种难得的民族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而言,造成“种业”遗传的“幽冥之界”又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地狱的二重性该如何平衡,当它成为一种困扰和悖论时,又当如何化解呢?
在《失掉的好地狱》发表前大约两个月,鲁迅在《莽原》发表的《杂感》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为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 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①鲁迅:《杂语》,《鲁迅全集》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7 页。这几句对我们理解这篇散文诗有重要的提示意义。 散文诗在《杂感》的神与魔之外,又多了一方势力,那就是人,描述的是魔鬼、人类和神灵为了建立一个“好地狱”而展开的对抗和斗争,地狱的控制权几经更迭,循环往复。 结合《杂感》可判断,将该文的解读落在“军阀争权夺利斗争”这一现实指向上是有充分依据的,不过,值得追问的是,人类/鬼魂、人间/地狱,以及神/魔的关系到底该作何解? 这也许要从理解“好的地狱”来入手。
在魔鬼对叙事者的倾诉中,地狱经历过三变:先是天神统治时的废弛状态——“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 然后是魔鬼收服地狱并亲临地狱——“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再之后是人类同反狱的鬼魂一起战斗,把魔鬼赶出地狱,“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坐在中央,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人类“整顿废弛”,让地狱一改“先前颓废的气象”——“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丸尾常喜认为,好地狱是指第二个阶段,即魔鬼治下的地狱,“这篇作品里最不可思议的是,‘魔鬼’虽然掌握了统治一切的‘大权威’,但是对于强化其统治、恢复地狱秩序,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魔鬼’所做的,几乎唯一的只是用它那‘大光辉’照见地狱和鬼魂”。而不管沉默多少年,那些‘大光辉’总能让鬼魂们从冷油与温火中觉醒,在他们的前面照见惨白小花,让他们想起曾经住过的‘人世’,从而发出反狱的绝叫”②[日]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3 页。。 按说,就地狱的功能来看,它从废弛的状态中恢复到油沸火热,才应该是“好的”模样啊,为何丸尾常喜说第二阶段才是好地狱呢?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地狱废弛的时候,群鬼都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地狱备下惩罚阳间恶人的各种刑具也不再威严可怖,在这沉滞的环境中,是生长不出来像女吊、无常那般令人觉得可敬可亲又有点可怕的鬼来的。 群鬼“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而人类的应声而起可以理解为一种招魂,鲁迅在《女吊》中是这样写的:“‘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 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 ”③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8-639 页。正是在魔鬼的统驭之下,地狱才有可能让横死的亡灵从麻木昏聩中醒来,凝聚成底层的正义暴力。 及至地狱在人的威临之下恢复了,那些反狱起义的鬼魂被人类警惕,人类通过收买牛首阿旁等鬼卒,瓦解阴间的力量,搬演人间的计谋,用更残暴的地狱酷刑压制,将不驯顺的鬼魂置于“剑树林的中央”,受那“永劫沉沦”的刑罚。
在神、魔和人三者间,地狱最为残暴的景象居然是处于人的治下,他们“威棱且在魔鬼以上”,这是整首散文诗最悖论的地方,也是充分彰显鲁迅“地狱观”二重性的时刻:鲁迅看重冥界的鬼魂因为阳世不公而于地下积攒的复仇力量,尤其当这力量来自那些横死的冤魂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反狱”的呼告! 然而,鲁迅又警惕,当这些冥界的鬼魂打破地狱,又会在人类“种业”的积习之下成为被利用的对象,最终沦落到更不堪的永难翻身的幽暗之地。 全文以魔鬼的倾诉连缀,最后魔鬼道:“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几个月后,在《朝花夕拾》的《琐记》中,鲁迅又一次对魔鬼发出了呼喊:“但是,哪里去呢? S 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 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 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①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3 页。
由上,我们或许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涓生在《伤逝》中对于“地狱”的呼喊是真诚的,而《祝福》中“我”对于祥林嫂“地狱和灵魂之有无”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恐怕也不尽是一个受现代科学启蒙的觉醒者不愿自我欺骗又充满人道同情的犹疑,还在于“地狱的有无”是“我”本人必须面对、无从逃避的终极之问。祥林嫂无疑是一个深受国民性“种业”遗传留播所害的可悲者,她的将死唤起“我”巨大的同情,也有深深的无奈,“我”深知死后的她不会变为无常,也不能像女吊那样,成为一个朝向吞噬她的社会的复仇者,她将成为幽冥之地一个死的沉默大多数,且将继续成为累积的“魂魄”附在新生者身上并扼杀新生者。假如我们认可叙事者“我”有鲁迅本人的影子在里面,那么“我”自然也是认可地狱的存在的,但是这个地狱并不是柳妈告诉祥林嫂的那个只讲业报、救赎,充满刑罚与恐怖的所在,而是同时容纳了众多的“横死者”,在一个有着反抗意识的魔鬼的统驭下向阳间发出反叛之声的“好地狱”。只是,谁能来当那个统治地狱的魔鬼呢?“我”曾经是“摩罗”的信徒,但现在却变得万事寥落起来。 涓生和子君曾经是“摩罗”的信徒,结果却是“伤逝”的终局。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既是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 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②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3 页。——发出这呐喊的涓生尚且有一丝不泯的向地狱而求悔恨的愿景,虽然所得也不过是虚无。 若干年后,当鲁迅又一次谈到地狱的时候,却是“好地狱”已经真正失去甚久的空茫了:“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③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20-521 页。因为“好地狱”的失去,人间变成了“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 鲁迅的地狱想象,用了一点传统的入冥叙事的元素,尤其体现于地狱的描写上,但他笔下的地狱与人间并非一个简单的比照关系。 在他那里,地狱是透射着深邃的文化批判意识的一种深渊处境,是拯救,也可能是陷落;是“充满诱惑、令人迷恋的”“异端”,也可能是“永劫沉沦”的刑罚。
三
与鲁迅有交谊的文坛后辈中,张天翼是自觉地沿着鲁迅开拓的国民性批评的道路,聚焦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书写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最被鲁迅看重的“左联”作家之一。1930 年,25 岁的张天翼在友人创办的《幼稚》周刊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鬼土日记》,翌年的7 月,单行本由上海正午书局出版。 在现代文学史上,这部小说是为数不多的按照传统的入冥叙事框架,大肆搬演地府巡游的讽刺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叙事者韩士谦学得“走险”之术,可以出入阴阳。某日,他安顿好肉身,焚化一信给十年前去世的朋友萧仲纳,要朋友到鬼土去迎接他。韩士谦“走险”成功,得入阴间,开始了一段时间的鬼土经历,见证了种种匪夷所思之事后,复又回到阳世。小说写的是入冥的故事,但冥间并非阴曹地府、阎罗鬼卒的所在,而是一个与阳世颇为相类的等级分化的社会。 小说开篇有一篇叙事者交代日记来历的信,内中说到:
“先生,你刚读这日记时,你也许会感到鬼土社会里的人和事,有点不近情,或是说有点可笑。是的,就是我,刚一到那边时,也觉得它滑稽,矛盾,一个畸形的社会。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和我们阳世社会是不同的。但先生,我要请你观察一下,观察之后,你会发见一桩事,就是:鬼土社会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是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这两个社会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因此,先生,我请你不要觉得它有点滑稽,矛盾,畸形,不合理,如你万一有这感觉,那你对阳世社会里为什么没有感到这些呢? ”
作为讽刺小说的好手,张天翼在此已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盘托出,无非以鬼土影射时代,在看似荒诞不经的阴间游走中,揭批时代的腐朽,寄寓犀利的现实批判。
小说中的鬼土首先是一个阶层固化、等级区分严密的地方。 出入鬼土的第一天,韩士谦就被告知:“地狱虽没有十八层,却有两层。 我们这层叫高层,住着有钱人,绅士,学者,即上流人。 下面那层叫低层,住着粗人,工人,农人,即下流人。 ”鬼土颁布有《最新市法大全》,对上流和下流人士的居住之区域有明确的划分,规定“下流人有‘来’高层之必要者,(如筑屋,运输,听差等),须由一上流人证明,向地方政务局请求发给临时执照。 该执照有效期内得出入高层。 ”上层人准备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如“剥猪猡法”等等,以恫吓和防范下层人的违令造反;而当下层人团结一致形成反抗的巨大声势时,上层人又会施战怀柔之策,从内部实施瓦解,用“这种柔软的压力使他们再也跳不起来”。 其次,上层社会内部不和,坐社”与“蹲社”两大党派随时为争夺权势和金钱而展开激烈角逐,而这两派最大的“政治分歧”在于他们一排坚持坐着出恭,而另一派则固执坚持蹲便。 在鬼土中,大企业家有特别的称谓——“平民”,以显示这些上层社会精英以平民社稷为重的“苦心”。 小说着重塑造了“三大平民”潘洛、陆乐劳和严俊,尤其是彼此明争暗斗不断的后两位。 再者,鬼土还是滋生各种文化怪胎,以及各种附庸风雅、趋炎附势之辈的温床。小说登场的鬼界活宝有“颓废派文学专家”司马吸毒、“极度象征派文学专家”黑灵灵、“后期印象派艺术专家,兼国立文艺大学校长,兼浪漫生活提倡人”赵蛇鳞、“恋爱小说专家,兼诗人、兼幸福之男人”万幸等等,张天翼用他的戏谑之笔点染出一副鬼土文化艺术界的群丑图。
值得注意的还有,《鬼土日记》里有一个核心的意象,即鬼土人士人人都带一个鼻套。 这个细节意象包含着以后为张天翼一再抒写的一个道德话题, 那就是国人一方面对性的问题在公共场合讳莫如深,一方面却又在隐秘的范围津津乐道。初入鬼域的韩士谦最诧异的是鬼界人士个个皆以鼻套蒙鼻,因为“据有些书上说鼻子是象征性器官的,性器官的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之一种表现,故‘上处’也常上套子”。鬼土的礼防比阳世还严、还小心翼翼。但接下来,张天翼便证明了越过分越讳莫如深地回避性问题,就越表示内心深处不健康的欲望尤为强烈,小说对此有两段对照鲜明的描写。 一幕发生在陆乐劳家的茶话上,在“很有秩序而严肃”的氛围中,“忽然,厅上有一个声音破空而起,一个人打喷嚏”。 这引起朱神恩教士极大的不安,他“严重地叫:‘Men,我用虔诚的基督信徒的名义唤起你们的注意,有人在这场所打喷嚏,并且喷出上处的污物,这是渎神,这是万恶之薮,这是上流人灭亡的恶兆,上帝耶和华会用雷殛他。 ’”另一幕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朱教士“将他的小乖乖坐在他膝上,吻她,将她的鼻套丢去,摸她的鼻子”,且肉麻地说道:“呵,小乖乖,多好一个鼻子,鼻子,鼻子! ”这种在性观念上的道貌岸然确实是国民的一大道德缺陷。 《鬼土日记》之后,张天翼又创作了《温柔制造者》《找寻刺激的人》《脊背与奶子》《砥柱》等短篇小说,主旨皆是关乎“性”的。 其中《砥柱》的主人公黄宜庵直可视为朱神恩在阳世的化身,满脑子的肮脏思想,却还得伪装成方正卫道之士,是继鲁迅《肥皂》四铭之后又一文学史的典型。张天翼在揶揄嘲弄中呼唤树立健康自然性观念的初衷,实际构成了一种道德批判,作为政治批判的补充,使《鬼土日记》具有了更宽泛的象征意义①马兵:《想象的本邦——〈阿丽思中国游记〉、〈猫城记〉、〈鬼土日记〉、〈八十一梦〉合论》,《文学评论》2010 年第6 期。。
这个小说与其时张天翼的其他短篇作品一样,存在着鲁迅说的“有滑稽的风格”,但“过于诙谐”“失之油滑”的问题②张天翼:《张天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2 期。。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此时张天翼的政治立场是偏向左翼的,并且在小说出版后大约两个月即加入了“左联”,但左翼文学内部对其的评价并不高。 在《北斗》的创刊号上,瞿秋白和冯乃超不约而同评论了这部作品。瞿秋白特别提到了《鬼土日记》以“入冥”启动的叙事架构,认为小说中的“鬼话连篇”是无可奈何,小说“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作者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太大了。‘鬼土’里面没有一个真鬼。 幻想的可能没有任何范围”,又认为“鬼并不是不能够画的,大家不要以为鬼没有作用。 法国人有句俗话,叫做:‘死人抓住了活人。 ’中国情形,现在特别来得凑巧——简直是完全应了这句话。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孔夫子的鬼,他还想统治全世界。 礼拜六的鬼统治着真正国货的文艺界。 ”③董龙(瞿秋白):《画狗罢》,《北斗》1931 年创刊号。显然,在瞿秋白看来,阴间世界和鬼蜮众生若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应该是作为文化批判对象的“国民性故鬼”的形象存在,《鬼土日记》的着力点在于讽刺只讲时髦、不讲真学的混文艺界的骗子,以及虚伪的性道德,重心失当,批错了对象。 冯乃超倒是看到了《鬼土日记》里除了文化讽喻之外,也有很强的社会针对性,他说:“《鬼土日记》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图——漫画了的缩图”,只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作者自身空想的”,这让小说“失掉了讽刺文学的价值”。 冯乃超同时将《鬼土日记》与但丁的《神曲》以及《何典》等中西作品对比,认为小说虽然采取了“冥土旅行”的方式,但“看不到和上述作品有相像的地方”,因为在张天翼这里,“鬼土”漫画的成分更大一些,对阳世现实的讽喻并不像小说开头叙事者自道的那么强烈④李易水(冯乃超):《新人张天翼的作品》,《北斗》1931 年创刊号。。
《鬼土日记》写作之际正逢1920 年代后期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余波波及中国,国内劳资对抗加剧,民族资本主义为谋生而展开倾轧拼杀,官僚垄断资本得以坐收渔利。 小说中大平民之一的严俊借海外石油垄断集团之力一举击垮陆乐劳的情节,倒是与两年后出版的《子夜》中赵伯韬扼杀吴荪甫的一幕颇有几分相像。 这说明,张天翼塑造鬼土世界并非没有现实针对性,只是笔力不够成熟,又有一意诙谐的任性,所以出场的地府人物大都类似,缺乏个性和神采。 瞿秋白和冯乃超对《鬼土日记》的评价,其实与新文学“感时忧国”的关怀有关,“感时忧国”不但表现为内容主题上的忧患,也要体现于文学形式上的匹配。《鬼土日记》之外,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几部以奇境的旅行为架构的小说,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老舍的《猫城记》等,在其时也未获得多少肯定评价,以至作者日后谈起亦有悔其少作之态。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将上述三个长篇并论,称赞它们能在“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 他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542 页。。 这种“特殊的现代气息”之于《鬼土日记》,自然就是托言冥界想象中国的方式,这种构思未必一定是受到传统入冥类小说的启发——无论在中西,虚构奇境的旅行都是讽刺寓言类的作品常用的表现方式。 不过,张天翼的巧思确实与传统的入冥之作形成对话的关系,也在新文学中留下难得的巡游地府的狂欢,并给左翼文学带来别样的审美。
张天翼并不像他尊敬的鲁迅那样有自己的“地狱观”和“鬼气”,对鲁迅而言,“地狱”是陈死人累积并攫取生人的历史负累,也是横死者不屈地向阳间发出抗争的前哨,他以“地狱”为修辞的文化批判在两端展开,既容留了传统地狱的恐怖功能,也带有一个现代存在者对地狱的新的赋意。 张天翼借地府的旅行展开其他的辛辣之笔,阎王没有了,代之以权倾朝野的“三大平民”;牛头马面没有了,代之以一众颓废放荡的无聊文人;无常女吊没有了,代之以居于地狱下层不甘被愚民政策统治的民众。随着叙事的展开,“鬼土”一面被“去地狱化”,一面也不断建构新的地狱面目。瞿秋白和冯乃超看到了《鬼土日记》的笑闹、浮夸和漫画化,以为这样的写作对现实是无力的。 但其实未必如此,张天翼在后来论及他的“幽默”观时,曾这样谈到:“态度么:他只要把世界上那些假脸子剥开,露出那烂疮的真相就算数,不再加一句话,不批评。 他样子很冷静,但其实对人世最关心、最热烈,因为他爱真实……你看看幽默家是超然的,而实则他有他的立场——那就是真实。 因此幽默家是严肃的。 ”①张天翼:《什么是幽默——答文学社问》,《夜莺》1936 年第1 卷第3 期。——“鬼土”所带来的表达效果可做同样的理解,“走险”进入鬼土的韩士谦何尝不是在暗夜里更深地潜入现实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