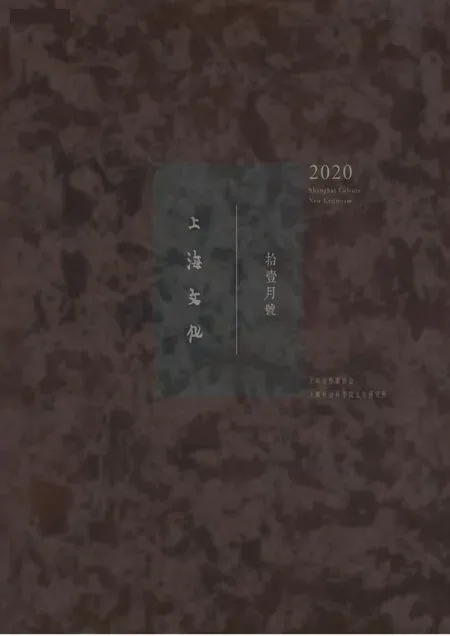记录小人物的“灵魂的深”
2020-11-25李肇正的作品
李肇正的作品
靳路遥
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上海位育中学语文教师、业余作家李肇正进入了他的创作井喷期。从1993到2003年的十年间,李肇正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八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共计三百多万字。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都应该引起当时上海文坛足够的重视,可惜在那个时候,这些作品却极少刊登在上海本地的文学杂志中,为其赢得声誉的几部重要作品如《女工》(1995)、《城市生活》(1998)、《石库门之恋》(1999)、《亭子间里的小姐》(1999)、《傻女香香》(2003)等,也都不是发表在上海的刊物中,关于他的评论,更是极少见诸上海评论家的文字。可以说,当时李肇正的创作并未进入上海文坛的视野。
真正对李肇正开始重视是从他去世的2003年后开始的。2003年9月,时任《上海文学》主编的陈思和在当月的杂志上不仅编发毛时安、阮海彪两篇追忆李肇正的文章,更在“编委会报告”中组织了一场对“李肇正写作现象”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除了向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致敬,更重要的是对他生前的被忽视表示惋惜。然而,抚今追昔,李肇正的文学成就仍然未能在这些事后的研究中得以正名。就在大家迫不及待地为其在文学史的坐标中寻找位置,将他集中而明显的都市底层社会题材作品归类为“平民文学”、“平民生活的叙事者”、“‘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时,其实并未准确地概述出他对当代文学史的意义。
李肇正最强有力的书写发生于1990年代。那是中国文学环境正经历着“变脸”的时代。商品大潮摧毁了旧有价值体系和理想主义,1980年代那种“拨乱反正”后一波高过一波的国家文学大合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文学四顾彷徨,开始呈现“驳杂”的局面。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第一轮的实践成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首先显现,描写城市乃至都市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历史性地呈现出与乡土文学并驾齐驱的态势。例如张欣通过对广州的书写,开启了都市小说写作潮,她笔下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所见到处都是对金钱顶礼膜拜的男男女女。“女性写作”则显然更多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的刺激,男女两性开始呈现大面积的敌对关系,而战斗的结果则是女性对男性的抛弃和由此建立了一个自足的女性世界。“新写实小说”从细部表达了对这个时代人生的绝望,好处是帮莫名烦躁的人们找到了烦躁的根源,坏处却是让人更加烦躁和绝望。而河北“三驾马车”领衔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本质上同“新写实”一样对生活的阴暗面进行暴露,并触碰到了当时最为棘手的体制改革问题,但与“新写实”干将相比,他们的笔力明显不足,缺少前者在暴露时的从容和幽默,更多时候,“冲击”出的作品更像是无关痛痒的报告文学。以上这些文学潮流轮番登场,形态各异,却都在讲述日益膨胀的欲望都市。就连新历史主义作家莫言、苏童、叶兆言、余华也未能幸免,《红高粱》、《妻妾成群》、“夜泊秦淮”等作品都通过民间视角切入历史,但构筑的却千篇一律是个权利、物欲和性欲组成的欲望空间。在1990年代驳杂的文学外观中,有一个不变的“欲望”主题。
其实,这样的写作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欲望都市”的确是对那个时代表象的准确归纳。只是,文学的意义应不止于对表象的捕捉,更在于对人云亦云表象背后的质疑和探寻。从后人的追记中,李肇正跟以上这些文学潮流都产生了关系,有人说他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干将,有人说他是都市小说作家,还有人因为他作品的叙事题材集中于对上海底层市民的书写,将之归入“平民小说”的作家行列。但谁都没能穿过这些令人目眩的名词,看出他作品对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的致敬与回归,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种现实主义是对欲望都市的有力刺破,并继而抵达那个时代小人物的“灵魂的深”。
一 对《阿Q正传》的模仿——《石库门之恋》
尽管李肇正没有像鲁迅写《阿Q正传的成因》那样做一篇关于此文的成因,也没有写过相关的杂文供人互文见义,但不妨碍我们看出《石库门之恋》对《阿Q正传》的模仿。
如同鲁迅通过阿Q 的性格刻画展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全像,中篇小说《石库门之恋》围绕一个绰号叫“阿胡”的上海底层小市民,对1990年代转型期的上海底层市民社会进行全景式的呈现。
“阿胡”这一人物形象,诸多的性格特征与阿Q高度相似,他身上寄托的作者对底层市民性格的理解,与鲁迅通过阿Q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如出一辙。阿胡与阿Q都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最底层,都是既奴性又虚荣、既懒惰又贪婪,属于被大多数人唾弃的那类人。当人生没有产生变故前,他们都在漫无目的地过日子,阿Q游荡于乡野、偷鸡摸狗、得过且过,阿胡是弄堂小混混,钞票和女人是他全部的追求。当他们感受到社会风暴的来临,第一反应都是想投机倒把,趁机大捞一笔。阿Q跑到城里去“革命”是想鲤鱼翻身抖威风,结果虚惊一场,只好做贼偷些衣服贩卖,回来还趾高气昂沾沾自喜;阿胡下岗了,却不屑于做扛大包的苦力,整日美美地做着发财梦。他投机股市、贩卖黄碟,都是想不费什么力气“吃吃白相相”,就能“赚大钞票”。“阿胡像只快乐的苍蝇,热烘烘地朝灯火照耀处扑去。”
阿胡与阿Q一样,是充了气的纸气球,外表虚张声势,内心充满了奴性,只是阿胡的奴性更多表现在对金钱的膜拜,他的情绪随着与金钱关系的亲疏而变化多端。比如他幻想自己将成为股市大亨,迅速膨胀,迫不及待地买了西装、拷机,在街坊“党委书记”和保安面前洋洋得意。他幻想着自己有钱,就真的要进到夜总会潇洒一番。他对美芳用情深厚,得知美芳当了坐台小姐、又成了张老板的“金丝鸟”后,恨由心生,然而最终也并未在行动上有所作为,因为他深知自己不是“金主”张老板的对手。金钱是阿胡活着的第一要义,为了它,阿胡可以违法,可以放弃人格、尊严、爱情和廉耻。
同鲁迅一样,李肇正也用漫画般夸张的笔法描写阿胡的“精神胜利法”。比如描写他在幻想中飘飘然的景象。他对美芳垂涎而不得,骂自己骂到狗血喷头,之后就觉得“酣畅淋漓,好像他是个英雄救美的角色,就有了许多满足感和迫切感”。他想象自己有钞票,就真的觉得自己有钞票了,于是就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到夜总会开洋荤。再如写他的“健忘”。阿胡骂了车间主任之后,饭碗危在旦夕,然而他却浑然不觉,在麻将桌上赢了两次,打了一场保龄球,就把骂主任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又高高兴兴地“白相相”去了。还有他错把“彬彬”西服当“杉杉”西服被嘲笑,一时尴尬,但很快自我解嘲:“管他呢,西装是我自己穿的,只要我把它当做杉杉就行了!”股市蚀了本,他不免悲怆地赌咒发誓,但“赌咒发誓似乎是很用力气的,阿胡马上饥肠响如鼓,昂首阔步地走进点心店要了一碗大肠面。大肠像口香糖一样有咬劲,还有一股骚气,阿胡走了几条路还是余味难尽。太阳真好,像玻璃一样光亮。”



李肇正写阿胡、美芳等深不见底的穷困和在这中间的不断堕落,同时不忘追究这穷困和堕落的根源;写他们下岗后迫于生计投奔股市、倒卖黄碟、沦落风尘的悲苦,也不忘写他们身上小市民的庸俗、虚荣、投机和奴性。他如实地写出阿胡、美芳们由于出身、经历和眼界限制无法具有更高的觉悟和跨世纪的本领,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能力,也写出社会转型、工厂下岗、股市风云等大时代的变革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沦为牺牲品的惨烈真相。他们这类人人数众多,也最经得起牺牲。他们的悲剧隐藏在历史之下,廉价、不为人觉察却又比比皆是。作者通过以一当十的手法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更写出了现实之下这类人物“灵魂的深”。
二 不虚美、不隐恶——对小人物的尊重
李肇正表现都市生活独辟蹊径。作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并不回避大都市中人们对欲望愈演愈烈的追逐,他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个个都被心中欲望的魔鬼折磨得死去活来。《石库门之恋》里阿胡和美芳为了金钱一个放弃了人格,一个被摔得粉身碎骨。《城市生活》写物欲如何拆散了杜立诚和宋玉兰这对夫妻,并将妻子人性毁灭的过程拆解出来一步步演示给我们看。《亭子间里的小姐》的亭子间女儿小玉绝不同于王安忆笔下的弄堂女儿们,她是那么软弱无力,在似乎触碰到了城市上层生活的边缘后,又被命运无情地拉了下来。《啊,城市》中来沪读书的农村大学生文东一开始就被身着连衣裙的女同学宋小宛照亮了内心世界,但不幸这是一个黑色的预言,预示了他最终卷入都市诱惑的深渊中无法自拔。

《啊,城市》中的文东是另一类被城市欲望吞没的人。他是人们常说的来自农村的“凤凰男”,背负着母亲和全家的希望到大城市读书,希望借此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和家族世代扎根农村的命运。然而他在骄傲与自卑的纠缠中种下了欲望的心魔,这种心魔随即与他身边的两个人发生了化学反应,一个是文东刚入校就偶遇的“女神”宋小宛。对文东来说,她是纠缠他一生的性诱惑的象征;另一个是他的室友、城市“富二代”子良,他是物欲的象征。二人一个镜花水月,一个近在咫尺,一起将文东引向万劫不复之地。文东对宋小宛日思夜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如同《红楼梦》中“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幻想中的宋小宛对他而言既是高贵的女神,又是吸干其精血的妖怪。文东终于在自慰和意淫中抽空了身体。“官二代”子良则带着文东去见识城市生活的潜规则,让他渐渐知道考试成绩可以买卖,写黄色小说比文学作品更加有人气和赚钱,而这一切都遵从着市场经济的买卖法则。在子良的诱导下,文东逐渐丧失斗志,不务正业,沉迷于看黄色录像和写市侩小说的快感中。虽然文东最后没有像贾天祥一样绝精而亡,却在这中间被抽空了志向,夺去了精神,以至最后沦为房东老板娘的泄欲工具。


此处,李肇正的写作立场值得尊敬,因为他不是以自上而下的审视视角将文东写成一个值得怜悯的外乡人,不以城市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外乡人抱有那种同情式的温情脉脉,而是在表达同情的同时,也批判他身上潜伏的劣根性,将他作为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对待。而这才是对平凡人生真正的尊重。
这样的视角也同样表现在《勇往直前》中的阿芳身上。这部中篇小说通过阿芳与张先生的夫妻关系,探讨了女性如何在婚姻中自处的问题。阿芳与张先生两人的婚内地位极其失衡,对于张先生来说,阿芳只是替他养儿子的女人,她除了拥有妻子的名分和每月从丈夫那里得到的一笔可观的生活费之外,没有任何“人”的尊严。张先生的冷落、侮辱乃至明目张胆的出轨,都一次次被阿芳含泪隐忍。


三 并非苦难叙事
因为都是描写城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且故事也大都以悲剧结尾,因此李肇正很容易被拿来与“新写实”作家以及描写苦难著称的余华、刘恒等作家进行比较。
在“新写实”作家那里,作家往往把生活琐碎、庸俗的一面放大展现给人看,将他们这种对生活缺乏诗意的理解总结为生活的意义推送给读者。于是,当池莉将男性描写为只会侵占女性身体的恶魔,爱情就被消弭了;当刘震云将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生活描写为一地鸡毛,那渗透在平常、安稳中的温情就被消弭了;当《活着》、《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弱者面对灾难的坚持被刻画成弱者的苟活理念时,蕴于其中的悲壮就被消弭了。这些书写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学本身对人格向上的提升功用被消弭,作品唤起的不是人们的悲悯情怀和充满希望的努力,而是对生活加倍的绝望。
李肇正却不是这样。例如在《秦小姐》、《亭子间里的小姐》、《姐妹》、《石库门之恋》等描写两性关系的作品中,尽管女性也往往被写成被欺凌与被损害者,却不像池莉的《不谈爱情》、《来来往往》、《烦恼人生》、《生活秀》等将两性置于激烈的敌对状态,在描写男性丑陋肮脏嘴脸的同时告诫女性男人之不可救药与爱情之不可信赖。




此外,面对灾难,李肇正也并非让他的人物像《活着》中的“富贵”或者《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张大民”那样张扬弱者的苟活哲学。余华让富贵经历了亲人一个个死去的悲痛后又让他一个人苟延残喘地活着,目的不是为了显示他的坚强不催,而是彰显苟活的意义。张大民的生活困顿如是,竟还能不断饶舌贫嘴,可是并不能让人感受到人性中的坚强乐观,反倒是自我麻痹、得过且过、甘于下位的妥协。李肇正在《女工》中刻画的精业羊毛衫厂女工金妹,其人生惨烈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富贵和张大民,作者给她的却不是苟活或自我麻痹的药方。李肇正直抒胸臆地写出女工命运的悲惨和当权者的冷酷无情,对当权者杀人不见血的冷酷进行斩钉截铁的批判。作品结尾的那副对联是对女工一生悲惨命运的写照和控诉:

结 语

然而,中国1990年代出现的不少文学潮流尽管都显示了立足当下、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但这种现实主义更多着眼于对社会阴暗面恶狠狠地暴露和批判,眼界狭窄、庸俗,缺少激励人心向上的力量。那些曾出现在1980年代《哦,香雪》、《老井》、《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中、带有爱与美的理想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品,再也难觅踪迹。

❶ 写于2004年的李肇正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赵长天序中说:“我们常常抱怨上海缺少好作品,缺少表现上海生活的好作品,缺少贴近现实的好作品。可眼前李肇正的小说恰恰就是这样的好作品!”言语间表达了对上海文坛错失这位作者的惋惜。李肇正:《城市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7页。
❷ 毛时安在纪念文章《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中写道:“李肇正在上海文学界是一个除不尽的‘余数’,是一个文学观、文学趣味与主流不尽相同的‘异数’”。《上海文学》2003年第9期,75页。杨扬说李肇正的作品:“有着非常丰厚的生活积累。这是上海作家中少有的,这才是底层文学。另外,对他的过世,的确,像很多文学界人士所讲的,传媒过于冷漠了。”罗岗认为:“他是一位‘潮流’之外的作家,他的作品像煤一样朴实,可是在今天这个需要霓虹灯的闪烁和聚光灯的照耀才能领‘潮流’之先的世界里,或许从他拿起笔来写作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以上均节自“编委会报告”,《上海文学》。2003年第9期,112页。
❸ 这些事后的研究还包括2003年1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钱定平《关于“李肇正现象”现象》以及2005年毛时安主持对李肇正作品的整理,最终结成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这是李肇正唯一的作品集。
❹ 前揭杨扬文。
❺ 前揭毛时安文。
❻ 黄柏刚:《有境界者自成高格——李肇正、郁达夫“落魄文人与女性”作品之比较》,《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
❼ 前揭李肇正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74页。
❽ 前揭李肇正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70页。
❾ 前揭李肇正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