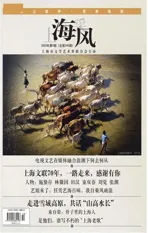那些年,迷上了译制片
2020-11-22庄大伟
■庄大伟
我小辰光跟大多数小朋友一样,不大欢喜看外国片,主要原因是看大不懂里厢的情节,两只外国面孔常常会得搞错脱。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看翻译小说,记忆中那些年看了勿少苏联长篇小说,也开始喜欢看苏联电影了。再后来,就慢慢迷上了译制片。
小辰光不欢喜看外国片
上海老底子电影院里放映的外国片,配音交关推扳(糟糕),有辰光听上去好像还是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翻译”。我家老早住在复兴中路上的复兴坊,走出弄堂勿远,隔壁就是上海电影院,这是一家专门放映外国片子的电影院。记得爹爹、姆妈经常会带我去上海电影院看外国电影。打仗的片子我还可以静下心来瞎七搭八地看看,图个闹猛。而碰到放映的是外国生活片、爱情片(依稀记得有《出水芙蓉》《废品的报复》《穷街》等),我就吃酸了,坐不牢了,难过煞了。所以一听他们要带我去上海电影院看外国片,我就滑脚(溜走)。不过对于国产影片,我是从小就喜欢的,记忆中最早看的一部国产故事片是《红孩子》。
后来我家搬场了,从卢湾区的复兴中路搬到虹口区的广灵二路。搬到新地方,大人们关心的是附近的商店、菜场、学堂、医院在啥地方,离家远不远,而我关心的是电影院在啥地方。从我家出发,朝北走十廿分钟是江湾电影院,朝南走十廿分钟是永安电影院,两段路的路程差大不多。不过如果朝永安电影院方向走,过了永安电影院,沿四川北路再朝南走,一路上还有群众剧场(也放电影)、国际电影院、胜利电影院、解放剧场(也放电影),一直到四川路桥桥脚下的邮电俱乐部,那里面也经常会放电影。
记得永安电影院夜场电影票要卖到三角五分一张,那是小青年轧朋友谈恋爱的辰光才会去买的票子;而去江湾电影院看学生场(大多数是早早场),最便宜的只要八分钱。由于囊中羞涩,我基本上只看学生场。对于一个月只有几角零用钿的我来讲,看电影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的零用钿主要花在看电影上面。
记得每个月月底快,江湾电影院就会出售一张下个月的电影排片表。有了这张排片表,就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故事片,在上面做好记号,到辰光去看。我一般选择礼拜天的早早场或早场,学生场的票价便宜。
学生场很少放外国电影,要放映多半也是打仗的外国片。打仗的外国片交关好看,像苏联电影《夏伯阳》,骑兵的场面令人震撼。还有《丹娘》《愤怒的火焰》《智擒眼镜蛇》等影片,都交关好看。看惯了黑白片,有一趟看《攻克柏林》,那是部彩色故事片,那就更加令人震撼了!
我老早就感觉到,外国电影里的战争场面,比国产片拍得真实。那些年有些国产故事片拍得比较概念化、程式化,比较虚假,好人勿大会一枪就被打死,身上吃了好几枪也不会死,还要讲好多话,还要“交党费”……而外国影片看上去就感觉到比较真实,当然有的镜头真实得有点血淋溚渧,吓人倒怪。
印象中到了1960年代初,外国电影的配音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看外国故事片就变得像看国产片一样省力,我也慢慢改变了偏爱看国产故事片的习惯,会经常去看一些外国故事片,并且不再局限于战争片题材了,比如看《魂断蓝桥》《摩登时代》《巴格达窃贼》等。
记得有一趟看了印度故事片《流浪者》,被拉兹潇洒而又有点油腔滑调的风度所感染,在学校里大声哼唱起《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啊——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完全沉浸在拉兹的“流浪世界”里,全然勿晓得已经打上课铃了,自己一个人还在拔直喉咙高歌:“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很快我就被叫到校长室,被校长夹头夹脑(劈头盖脑)臭骂了一顿,还让我把手臂上的中队长标志摘下来。后来我才晓得,这天正巧有外国来宾到阿拉学堂里来参观,校长这才大发雷霆的。
印象中,我在小学中年级辰光就开始阅读长篇小说,看《水浒》,看《青春之歌》,看《敌后武工队》。后来也看一些翻译小说。特别是进入中学以后,学校图书馆有不少外国长篇小说,最多的是苏联长篇。虽然我特别讨厌苏联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好长的一串,记都记不住,我也讨厌书中整页整页出现的风景和心理描写,不过对此我都可以“唰唰唰”地翻过去。
要晓得苏联长篇小说里的人物情节,都非常抓人,好看!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还有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几年里我读了好几遍,有些章节甚至能够背下来。
前两天上网查了一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作者叫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名字长吗?),这是部纪传体小说,里面写的全部是真人真事,讲的是卓娅和舒拉姐弟俩如何成长为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故事。他们俩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同龄人。资料显示,这部1950年在苏联首次出版的书籍,195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发行了几百万册。
在读苏联长篇小说的同时,我也爱上了看苏联故事片,记得看过的苏联故事片真不少,有《复活》《智擒眼镜蛇》《牛虻》(以前一直把它误读成《牛忙》)《保卫察里津》《蓝箭》……
凤毛麟角的译制片
正当我逐渐喜欢看外国影片的辰光,1966年的“文革”来了,除了样板戏,看不到故事片了。那段辰光只好躲在家里偷偷翻翻过去的《电影画报》。后来被爹爹发现了,他慌忙把整叠整叠的《电影画报》扔进了垃圾箱。到了1970年代初,随着《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国产故事片的开禁,一些外国故事片也逐渐进入电影院,记得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里,瓦西里与妻子的接吻和四只小天鹅跳芭蕾的镜头,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极具看点)。
那辰光的译制片虽然凤毛麟角,倒也有一股清新的味道。后来伴随着国产故事片慢慢复苏(记忆中有《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艳阳天》等国产影片),译制片也逐渐多了起来,印象中有阿尔巴尼亚影片的《地下游击队》《创伤》《海岸风雷》《伏击战》《脚印》《第八个是铜像》,朝鲜影片《摘苹果的日子》(里面的“600工分”倒是印象深刻,一度成为“胖子”的代名词)和《原形毕露》,还有罗马尼亚的《沸腾的生活》《爆炸》等。记得曾经流传过一句顺口溜:“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有一部越南故事片《山区女教师》,由于没有“飞机大炮”,也非“哭哭笑笑”,看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我看过,是《解放日报》送的票子,在黄浦剧场看的,说是看后要写一篇影评。我是带着写作任务去看这部片子的,心里蛮有负担。记得在墨墨黑的放映厅里,我眼睛一边盯着银幕,一边用笔在本子上“盲记”影片里的台词。回家后匆匆写了一篇影评,标题是《满腔热情,循循善诱——看越南故事片〈山区女教师〉》,文章很快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出来。今天我从几十本发表作品的剪报集里,好不容易寻找到那篇文章,1973年7月9日的《解放日报》第4版,署名是“虹口区工人业余写作组”。那辰光用个人署名的文章很少,常以这类“集体创作”的名义呈现。
“忽如一夜春风来”,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类外国翻译作品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早先出版的《摘译》外,各家出版社又办起了《外国文艺》《译林》《世界文学》等专发翻译作品的刊物。译制片也像野火遇上了春风,“呼——”地一下燃烧起来。1984年初我已在广播电台供职,经常有机会观摩到一些供业务学习的“内部片”。我们经常会去岳阳路的音像资料馆看内部电影,大部分是没经过配音、只打字幕的原版片。后来新光电影院每个礼拜也会播放一些原版片(只打字幕)和少量译制片。我们当文艺编辑的都办了年卡,一到播放译制片的日脚(好像是每个礼拜二的上午),总会放下手头工作去新光电影院观看译制片,不肯轻易放弃每一次观摩外国片的机会,有《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爱德华大夫》《胜利大逃亡》《两个人的车站》《未来世界》……这些曾经的“内部片”,后来都公映了。
万人空巷的《姿三四郎》
记忆中1981年由上海电视台译制并首播的日本引进电视剧《姿三四郎》,曾经引得万人空巷。《姿三四郎》讲的是热爱柔术的男青年姿三四郎,如何从一个莽撞少年成长为一名优秀柔道大师的故事。剧中的姿三四郎对柔术的执着,对爱人的专一,无不深深打动中国观众的心。这部电视剧一共26集。那个辰光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电视剧,一天只播放一集。一部26集的电视剧,要播放将近一个月,天天钓牢你看。记得每当这部电视剧播放的辰光(大约在19:30左右),马路上就立刻变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这部电视剧。传说《姿三四郎》在北京播出的某一日,正好有几个区停电,为了不影响观众们观看此片,供电局特意安排临时供电一个小时。《姿三四郎》在当时中国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那些年,我经常为《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写一些儿童小说和童话。记得当时为《儿童时代》写的一篇小说《一个下雪的早晨》,为了“蹭热度”,我在描写小主人公一段梦境时,特意写了一节“(梦见坏人)一个黑影闪到玻璃门前,是桧垣”。小说稿寄给了当时《儿童时代》的编辑王安忆。随着播出的《姿三四郎》故事情节的发展,看到后来“桧垣”并非坏人,我连忙写信给王安忆,要求将“桧垣”换成剧中的一个坏人“蓝眼睛里斯特”。今天我又特意找出那本《儿童时代》,那篇《一个下雪的早晨》其中有一段“一个黑影闪到玻璃门前,是蓝眼睛里斯特。我慌忙钻到床底下。里斯特瞪着可怕的眼睛,用拳头使劲砸门,砰砰砰……”小说发表在《儿童时代》1982年1月号上。记忆果然没有出错,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后来引进译制的日本电视剧《血疑》《排球女将》,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也引起上海电视屏幕上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狂潮。与此同时,国外不少电影故事片经过译制也蜂拥而来,进入人们的视野。我跟现在好多年轻人一样迷上了译制片,现在手指头随便扳扳,就能说出好多译制片的片名:《叶塞尼亚》《虎口脱险》《尼罗河上的惨案》《三十九级台阶》《老枪》《巴黎圣母院》《简·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追捕》《人证》《砂器》《东方快车谋杀案》《大篷车》《奴里》《疯狂的贵族》……到后来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第一滴血》《超人》……数都数勿过来。
当时好多译制片里的台词,如今还记忆犹新。
“你跳呀,朝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你倒是跳啊!”(《追捕》台词)
“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台词)
“她跳舞跳得这样动人,难道是我的错?她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她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巴黎圣母院》台词)
“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记住,时间能够医治一切。”(《尼罗河上的惨案》台词)
……
还有好多好多。译制片中的好多插曲、音乐,也曾经风靡一时。《排球女将》中的“嗨,接球、扣杀,来吧,看见了吧”;《桥》中的那首“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追捕》的“啦呀啦——啦呀啦——”;《人鬼情未了》里的那首“Oh,my love,my darling”……都让我百听不厌。
与此同时,一直在幕后默默耕耘的上海译制片厂的编导、配音演员也出现在前台,邱岳峰、苏秀、赵慎之、毕克、尚华、刘广宁、李梓、童自荣、丁建华、乔榛、曹雷……
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于1957年4月1日,早先在万航渡路618号,1976年搬到永嘉路383号。在这里的一栋小楼里,译制片厂的编导、配音演员缔造了1980年代译制片的辉煌,《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等一批上乘的译制片经典在此地诞生。那个辰光译制厂的好多配音演员,经常到我们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我有不少译制片厂的朋友。记得当初去译制片厂联系工作,我总是会抽空钻到他们的录音棚里,饶有兴致地看他们对着屏幕配音,也学到了不少相关知识。
比如,译制片上出现的外国男孩,他们的对话其实都是女演员配音的。一问才晓得,原来如果选太小的男小囡来配,他们往往对人物性格把握不准,老师辅导很长时间也不容易达到要求。而找年岁大一些的男小囡来配,如果已经进入变声期,那他们的公鸭嗓配出来更加不行。又比如,配音时的对口型,只有很好地处理好声音和口型之间的配合,才能使观众不会在看译制片觉得别扭,从而更好地表达出应有的视觉效果,增加观众对影片的兴趣。译制片厂的老师告诉我,录制时配音演员需要能够顺利地一次通过。由于当初录音技术有限,在录制阶段容易因为个人的失误,导致大部分录制的失败。这就需要配音演员对台词进行反复认真的记忆,只有对台词进行反复地排练,才能在录制阶段中更好地表现。对口型中表达出角色的情感,也是最难的部分。
角色的性格等表现除了通过演员的外貌特征和肢体等方式来进行表达外,语言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刚正的、奸诈的、和气的、柔美的、魅惑的等等,都需要通过语气和语言来表达。不同国家的说话语气、语言顺序、语气节奏等,不同体型、年龄、男女等外形都是通过语音来表达的。在女声方面,较为丰满的女士在女高音方面比较突出,而瘦小的女声则多表现出一种较弱质感。而男声,有张飞那种粗犷之感,有唐僧那种方正平和之感,有皇帝那种高端大气之感等等。年龄方面,有稚嫩的儿童声音,有血气方刚和敢打敢拼的中青年的声音,也有较为孱弱的老人的声音……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必须具备各种高超的变声技巧,才能够适应更多的角色。
我想起一位在某个联欢会上认识的小伙子,他声音模仿能力超强,在十来分钟的表演时间里,一个人“化声”七八个不同角色。联欢会结束,我立刻留下他的联络方式。后来我们录广播剧时把他请来,果然角色演绎到位,录得相当顺利,可谓旗开得胜。后来他便成了我们这里的常客,再后来他干脆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游走于全国各家译制片厂配音岗位,我经常会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认为配音是需要一定语言天赋的,如同一个人如果天生“色弱”,就很难成为一位画家一样。
如今,上海译制片厂搬进了我们虹桥路1376号广播大厦。我有更多机会跟译制厂的朋友们聊天,看“棚虫”们依然在孜孜不倦地配音,录制一部部新的译制片。译制片从当年的小河游进大江,又从大江游向大海。
尽管现在不少年轻人喜欢观摩“原汁原味”的原版片,可译制片仍然还有众多的“粉丝”,仍然拥有广大的观众市场。外国影片的译制是一门语言艺术,我想她不会在百花盛开的艺术花园里消亡。我为译制片的“二度创作”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