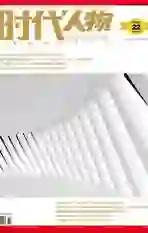关于“隐孕入职”问题之探析
2020-11-18张润华
张润华
摘要:近年来,“隐孕入职”事件屡见不鲜,引发社会舆论热议,究竟是女性为了一己私利而刻意为之,还是迫于隐形就业歧视的社会现状所实施的无奈之举,不禁引人深思。“隐孕入职”背后所折射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困境,从源头规避此现象必须多方发力,本文将从多层面探究如何规避“隐孕入职”现象,缓和用人单位劳动力成本投入与劳动者生育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营造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赢。
关键词:隐孕入职;双向困境;缓解矛盾
一、“隐孕入职”背后的双向困境
1、未孕女性劳动者遭遇隐形就业歧视
新时代的女性不再只肩负相夫教子的家庭责任,而是更多地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国家和社会也给予了女性劳动者一定的特殊保护。尽管女性的生育权与劳动就业权在法律层面得到了保障,但是求职时遭遇的隐形歧视却依然存在,尤其是育龄女性其面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根据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育儿网站调研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58.25%的女性曾遭遇过求职应聘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的女性遭遇过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还有6.39%的女性遭遇过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经济效益是用人单位考虑的首要指标,招聘育龄女性劳动者所投入的成本显然高于没有生育压力的已孕女性,甚至高于部分男性劳动者,这就使得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慎之又慎,从而女性劳动者求职中遭遇婚育限制的社会现状比比皆是。用人单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减少用工成本,同时又不得不遵守法律给予女性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特殊保护的刚性规定,其往往会采取极度隐蔽的内部操作规避招聘未孕女性劳动者,看似正常的行为实则侵害了女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隐性就业歧视,不仅人为地提高了就业门槛,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性别歧视在职场上的进一步蔓延,使女性劳动者面临生育与就业的双重压力,最终导致法律对女性生育权与劳动就业权的保障形同虚设。面对此种压力,女性劳动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应对这种隐形歧视,保障自己平等就业的同时实现生育权,进而便衍生出了”隐孕入职”的现象。
- “隐孕入职”使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增加
女性劳动者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到相关法律规范的特殊保护,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更是人权保障之精神所在,与此同时也意味着用人单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给予女性员工一定的孕期保障。但是站在用人单位角度,其招聘的主要目的是广纳贤士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赢得市场竞争力,招聘未孕的女性劳动者无疑需要面临其生育期间给单位带来的人力资源损失,无形中给企业增加压力,尤其是给中小型企业造成的负担更重。更有甚者恶意“隐孕入职”,利用法律规范中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将企业当做孕期的“避风港”,单纯享受生育期间的权益保障,待产假结束立马辞职,此种行为加剧了用人单位的损失同时也激发了用人单位的风险防范意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不得不基于女职工怀孕后岗位空缺填补、工资支付等成本因素的考量而慎重招聘未孕女性劳动者。
如何规制“隐孕入职”问题
- 用人单位审慎行使知情权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该条规定虽然赋予了用人单位一定的知情权,但是用人单位应当合理行使,避免过度权利滥用而侵害劳动者的隐私权。“隐孕入职”事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利用知情权询问劳动者有关生育状况,以便隐晦地利用内部操作排除未孕女性劳动者的求职,从而减少人力成本投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但是用人单位此举给劳动者造成无形的就业压力,激化了劳资矛盾,不利于劳动关系的良性发展。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必须对用人单位的知情权进行一定限度的规制, 权衡用人单位知情权与劳动者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比例原则审慎行使知情权,女性生育情况并非势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对此关于应聘女性劳动者的生育状况用人单位一般不得主动了解,除非特殊岗位需要并出于对女性劳动者孕期保护的必要可以适当涉及生育状况的询问,否则,应当尊重女性劳动者的生育权。
- 加大就业歧视惩罚力度
“隐孕入职”现象所反映的是用人单位对育龄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正是因为这种歧视,使她们在求职时不得不选择隐瞒怀孕情况以期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争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用人单位之所以肆无忌惮地通过隐蔽的方式规避法律规范的禁止性规定,对未孕女性劳动者实施就业歧视的主要原因是违法成本低于人力投入成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相关案例,基本上对用人单位的罚款数额偏低,这种惩罚力度不足以对用人单位起到震慑作用。用人单位权衡成本投入自然而然甘于选择承担对未孕女性劳动者进行隐性就业歧视所产生的责任,长期以往对未孕女性劳动者的歧视便会成为行业常态,加剧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更多未孕女性选择“隐孕入职”。要想有效规制“隐孕入职”现象,必须考虑对用人单位加大惩罚力度,设立一个严格而又合理的惩罚标准,给予企业相应的行政处罚,落实单位负责人的个人责任。如果相应的惩罚措施力度不足以对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产生惩戒作用以及对其他用人单位起到警示作用,那么“隐孕入职”现象便无法得到缓解。因此,对歧视育龄女性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
- 女性劳动者自身应诚信
实务中,女性劳动者“隐孕入职”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用人单位不得以其未如实告知怀孕情况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这也就成为了女性劳动者“隐孕入职”的根本所在,甚至部分女性并不是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而隐孕,而是滥用权利只为寻求孕期“依靠”,此行为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女性劳动者有恃无恐地“隐孕”只会让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提高警惕,从而加重对未孕女性劳动者的歧视,造成劳资关系紧张的局面。为了缓解“隐孕入职”所引发的矛盾,单靠规制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行为远达不到理想效果,还需要女性劳动者诚实守信,不得滥用权利。女性劳动者应聘的岗位属于孕妇禁忌岗位或者不适合孕妇从事的岗位应当如实告知生育情况,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劳动纠纷,激化劳资矛盾。虽然在强资本弱劳工的行業形态下,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一方,但是仍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能盲目且恶意地“隐孕入职”以获取特殊的孕期保护。对于恶意应聘享受孕期保护后又恶意辞职的“隐孕者”可以考虑建立诚信应聘档案,将其恶意行为记录在内,严重者可考虑列入“黑名单”,让其为自己的恶意应聘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 社会理应承担部分责任
“隐孕入职”现象究其根本是用人单位与育龄女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缓和此冲突不应只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博弈,社会理应承担部分责任,缓解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成本压力,更好地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生育权与劳动就业权。如对于女性生育期间本应由用人单位完全承担的责任改为由社会与用人单位共同承担,采用资金倾斜等手段激励并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提供公平就业机会的责任。建立健全生育保险制度,在三期内可采用弹性标准将部分费用由保险支出,小额部分由企业进行补充负担,如此下去用人单位对孕期职工的投入成本负担减少,就不会对育龄女性劳动者进行过于严苛的要求。同时,社会层面需要给予育龄女性劳动者多一些关怀与照顾,通过免税、优惠甚至补贴等办法,缓解其生育压力,从而使其不必为了“蹭”孕期待遇而恶意“隐孕入职”。
“隐孕入职”是劳动力市场严峻态势下的产物,是女性劳动者“消极维权”的一种方式,平衡好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规制“隐孕入职”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劳动者诚信应聘,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适当考虑用人单位的需求,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充分地尊重和平等的就业机会,是解决“隐孕入职”恶性循环的必要。此外,社会理应承担部分责任,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同时兼顾用人单位的经济效益,使“隐孕入职”从源头上得到缓解,从而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章伟平.我国女性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0.
周欣怡.缔约阶段劳动者告知义务研究——以“隐孕入职”为视角[D].兰州大学,2019.
刘丽丽.劳动者入职欺诈问题法律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8.
何 霞 谢志灏.“隐婚”“隐孕”:就业欺诈抑或就业歧视?——基于司法判决的文本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黄桂霞.女性生育权与劳动就业权的保障:一致与分歧[J].妇女研究论丛,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