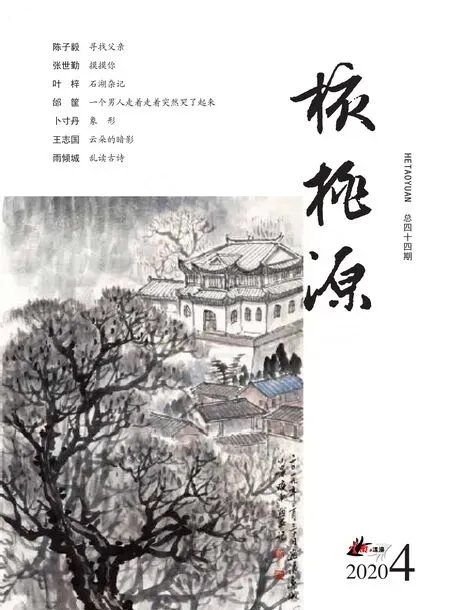寻找父亲(节选)
2020-11-18
父亲走了,在二零一七年春节过后十几天的一个下午,西边一缕残阳掠过,父亲驾鹤西去。一家人的悲痛持续了很长时间,无法去回忆离去前的这一段短暂、漫长而又痛苦的时光,每一个人心中的悲痛都是不一样的,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够抹去所有家人这一切伤痛。
二零一五年的夏天,父亲查出患结肠癌并已经肝转移,在手术后的一年多的化疗和其它各种治疗后,没有什么好转,最后还是于二零一七年春节后病逝离开了我们。
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抗衡的自然规律。总想写点什么,用来纪念父亲。生命生生不息,只是在父亲七十多年的生命长河里,留给家人太多的爱和记忆,时常在夜晚或某个白天,会回忆起一些过去几十年里的生活片段,于是想起了什么,就写下些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就是这么渺小,就把这些渺小的事情记录下来,用这些简单的文字来记忆我的父亲,今后我们的孩子们成年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或许也有些纪念意义。
爷爷奶奶是山西太原人,爷爷自幼父母早亡,是由他姐姐抱着讨百家奶养大的,长大后学医。就读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从军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曾任职少校军医。也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少校军医,让我的爷爷和父亲在后来的一生吃尽了苦头。爷爷很早就离开了国民革命军,凭借自己的医学手艺,早年在陕西汉中开了一家医院,奶奶出生于大户人家,毕业于教会学校的护理专业,夫唱妇随的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从爷爷时代家里一些古老的黑白照片可以看出来,当时爷爷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非常殷实富足的。
爷爷奶奶应该是一九四六年来到昆明的,我奶奶的父亲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当时很早已经在昆明落脚了,或许是西北的战事越来越紧,于是爷爷带着一家从泸州来到云南,投亲靠友。父亲是一九四二年夏天生于四川泸州的,听父亲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是,父亲是因为奶奶得疟疾,打摆子早产的,大概只有七个月就出生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父亲能得以存活下来,或许是上帝的恩典。长大后的父亲浓眉大眼,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性格开朗,热爱生活。
父亲七十五年的人生旅程中,虽说是苦辣酸甜样样都经历了,但总是觉得幸福快乐的日子还是最多。
我总是不断地回忆起儿时和父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我想把每一个回忆就凌乱地写在这篇回忆父亲的小文里,一小段一小段,记录下父亲的爱与温暖。
壹 钓鱼
2017年夏天雨水真多,全国普降暴雨,很多地方都遭水灾了,香港也回归二十年了,看着香港回归二十年的庆典现场直播,内心无比激动,心潮澎湃,时间真是快啊。
漾濞是大理苍山西麓的一个县城,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地,母亲的故乡,父亲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十四个年头。以前不太喜欢下雨,成年后开始渐渐地喜欢雨季,特别是喜欢那种一下就是十几天的雨季。
我在少年时代是很爱钓鱼的。记得也是一个雨季,雨下了很多天,漾濞江水量猛涨。那时我估计七八岁,一个午后雨下的很大,我一个人在漾濞江上的一座大桥下面用竹竿钓鱼,桥是七十年代初建的滇缅公路的大桥,桥上游三百米左右是一座废弃的老吊桥,老吊桥在抗战的时候是抗战战备物资运输的必经通道。
河里涨水是很好钓鱼的,漾濞江里有一种石头鱼,和泥鳅大小差不多,本地人叫“沙特”。鱼钩穿上蚯蚓,鱼钩上部做一个铅坠,用根普通的竹竿绑了鱼线扔到河里,鱼一会儿就上钩,那天是我钓鱼历史里钓到鱼最多的一天,三五分钟一条,不一会儿时间,穿鱼的旧电线上已经穿了长长一串鱼。雨越下越大,河水也越涨越猛,红黄色的江水奔涌而下,江水里还有很多上游林场被冲下来的木材,我是蹲在岸边的桥墩上钓鱼的,河水离我蹲的桥墩已经不到一米,记得当时还是有几分害怕的,这条河里,每年我们县城总是有几个小孩或者成人要在河里丧命的,尤其在夏季洪水来临的时节,街坊邻里时不时会在传讲谁家的孩子被河水冲走了,都说河里是有鬼的,每年都要弄几个进去才会善罢甘休。
这么大的雨,河水涨的这么快,我想今天回家估计是要挨揍的份了。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桥边走了下来,原来是父亲找来了,我先是一阵惊恐,想着要挨训斥了,可是父亲并没有斥责于我,只是说他估计我就在这里,知子莫如父呀。父亲没有立马让我回家,而是蹲下来,陪着我一起钓鱼,看着当天钓鱼的收获,父亲反而非常高兴。这个生活的小小片段,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还是无比的温暖和幸福。贪玩的孩子在大雨天外出钓鱼,让父母担惊受怕,父亲冒雨来找不听话的孩子,没有打骂,也是奇迹,父爱的温暖,时常在回忆中感受着。
父亲在家里有个百宝箱,里面有很多鱼钩和鱼线,这些鱼钩和鱼线好像是父亲学生时代在昆明上大学时候购买保存的,用鱼线拴鱼钩是个技术活,父亲教过我用“猪蹄扣”的结绳方法拴鱼钩,这个简单打结方法,几十年过去后,我依旧记得,捆扎行李或者拴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常常用起,对工作和生活都有极大的帮助。
记忆中父亲在漾濞生活的岁月里,并不记得他去钓过鱼,或许是当时生活的艰辛,父亲已经不可能有闲暇的精力和时间去垂钓了,漾濞在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养鱼塘,市场经济也不发达,集市上很少有人卖鱼的,即使有卖鱼的,也是有人用网在江里捕捞或是用炸药炸了鱼后拿来卖的,家里是不会买鱼来做了吃的。
父亲退休前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部门里有一个鱼塘,他开始经常钓鱼,那时候就用花鸟市场买来的鱼竿,鱼塘的鱼好钓,家里也有吃不完的鱼。父亲是山西人,吃鱼的时候常常说:“老西吃鱼,两手不离。”就是比喻山西人不会吃鱼,记得他说旧时在山西的宴席上,会有一个菜是木头雕的一条鱼,我们听来无比好奇。在记忆中爷爷和奶奶是很少吃鱼的,看来山西人确实不擅长吃鱼。
每一个人在时光面前都是平等的,只是这种回忆让人在伤痛中又充满无限的幸福感,总想穿越回过去,再来一次。
2017年7月1日
贰 学会游泳
漾濞江是漾濞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大理州剑川县,最后流入澜沧江,江水夏季洪水滔天,冬春季节则可以清澈见底。三十几年前,没有过度开发水电站和大搞城市建设的时候,这条江的景色还是无比秀美,江里怪石嶙峋,各种鱼群在水清的时候都能看得到,小时候太多的童年欢乐都来自于这条江。
五六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玩水,喜欢去沟里和大河里捞鱼捉泥鳅,看着一般大的孩子都会在水潭里嬉戏游水,好生羡慕。我学游泳是父亲教会的,父亲用换下来的自行车轮胎,打了气之后,作为我学习游泳的简易救生圈。夏季的漾濞江在雨季没来的时候,是孩子们消夏游乐的圣地,父亲会带着全家到河边来游玩,顺带我也可以学习游泳。父亲是会游泳的,好像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体育老师教过一些标准的游泳方法,什么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父亲都能来那么几下子,我在水浅的沟里、水潭里已经戏水玩耍过很多次了,父亲用自行车轮胎浮着我的头,在河里教我练习划水和蹬腿,其实我记得我学会游泳的那一刻,就是在水中掌握了平衡后,把头潜入水里,用蛙泳的姿势往前游,就这么容易地,游泳就学会了,其实现在觉得更多地是来自于父亲在旁边给与的安全感,学什么都会很快的。父亲后来六十岁了还去学驾驶,他一生喜欢机械和电器,我和妹妹都曾轮番地教父亲实习驾驶车辆,如今想来,父亲与孩子们的缘分其实很短。
学会了游泳,我却差点在江里丢了命。这是刚学会游泳后的几天,天气好的下午父亲又带我去江里游泳,江里很多人,我刚学会游泳,所以父亲规定只能在江边水浅的地方来回的游一游。这时,江对岸有人在用网捕鱼,好像是捕到了大鱼,很多人就游过江对岸去看,父亲也过去看热闹,我不出声响地跟在父亲后面游过江去,夏日枯水期,江面很窄,父亲到了对岸已经站了起来,我自己觉得也可以站立了,不想初学游泳的孩子对水深的判断有误,我没能踩到水底,水还是比我身高要深,一惊慌我落入了水底,就在水底扑腾了几下,这时候刚好父亲回头看过来,父亲在水中几个健步朝我冲过来,把我从水中拉起来,救回了我的命。
生命的存在有时的确是一种偶然,如果不是父亲在这个夏日的一个回首,我或许早就逝去很多年了。
2017年7月16日
叁 林场砍柴
滇缅公路最早的线路是从大理进漾濞后再通往永平和保山腾冲,国际上称作“史迪威公路”,这条公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谓是赫赫有名。这路在漾濞境内有几十公里,路面用狗头石铺成,记忆中有来来往往的运输卡车,大多是运送木料的卡车和拖着加农炮的军车。小县城里的人家,家家户户都是烧柴的,木柴要么在集市上买来,要么就自家到附近的山里去砍,谁家厨房门口的柴垛堆得越高,好像就觉得日子过的要红火一些的感觉。
父亲是个外乡人,大学毕业后随母亲到了漾濞县城工作,不知道当时他是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的。爷爷是外科医生,解放前来到云南的一个盐矿上工作,收入在当时是很高的,为此,父亲少年时代的生活是非常优渥的,文化大革命中爷爷受到残酷迫害,家道中落,父亲当时随母亲来到滇西小县城工作,也是当时特殊历史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最常见的命运。
记的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滇缅公路山里的林场去砍柴,那时我估计五六岁,详细的过程已经很模糊了,只是有些镜头在记忆中无法抹灭,现在想来依旧历历在目。
虽说是砍柴,其实不需要砍树,山里的林场伐好的木头周边有许多削下的树枝,把这些树枝砍成短枝装载在手推车上拉回来就可以了。手推车是去林场拉柴的核心运输工具,这种手推车在当地农家很普遍,套上马就是马车了,这种车有两套刹车系统,一套是在前面扶手上有一个手柄连着钢丝通过两个轮子后面的一根原木,通过手柄拉动钢丝牵引圆木与轮子摩擦来制动,原木上用铁丝捆扎废旧轮胎的胶皮,另一个制动系统是在推车底部绑扎一根长木头,木头长出车尾部,在下坡的时候,把车把头抬高,让长出的木头与地面接触,通过摩擦产生的阻力来制动。
林场离家估计有十多公里,在山上,去的时候是上坡,父亲拉着空车,我在旁边走着,到了林场已经是中午,把家里带来的饭热一热,要吃中饭,饭是用锣锅带的,林场里四处都是林场工人做饭用过的火膛,其实就是几块大石头垒的一个火坑,里面有烧过的柴火和炭灰,再拣点树枝点燃,把锅架在上面就可以了。
可是天气太热,父亲说饭馊了,我不记得我吃了多少,只记得父亲把馊了的饭都吃了,现在依然能记得父亲抬着锅,把馊了的饭大口大口地吃完,吃的过程中,有一辆拉木料的卡车从我们旁边开过,父亲还大声地和卡车司机打招呼,邀请司机吃饭。这个几分钟的人生历程在我的记忆里就像一个短视频一样,永远地清晰着,几十年过去了,影像依旧那么清晰,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无法形容是什么感觉,只是记得饭馊了,父亲把一锅馊饭吃完了。
回去的路都是下坡,我坐在手推车的柴堆上,父亲在前面拉着车,肩上还套着一根拇指粗的麻绳,车速快的时候,父亲要把车把抬高,让车尾部的长木头与地面摩擦来减速,父亲是强壮的,背部和手臂上的肌肉在汗水的浸润下,被太阳照的闪闪发光,感觉就是一匹骏马拉着车在奔驰。
有时候,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幅漫画,就是父亲拉着车,我们兄妹和母亲坐在车上,父亲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一路拉着我们几十年,直到最后罹患癌症病逝,离我们远去。
2017年8月2日
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在儿时的记忆里,家里有一个电熨斗,和现在这种喷水汽的不一样,很重,表面镀络,锃亮锃亮的,包装是个纸盒子,纸盒子上有父亲的笔迹,写着:背包谷的工钱,24.5 元。那个年代,父母的工资非常微薄,每个月就是几十元钱,市场经济还没有萌芽,可以挣钱的路子是少之又少,我们住的单位的房子旁边是粮食局的粮仓,这个粮仓很大,有两个大院子,估计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粮仓是青砖碧瓦的砖木建筑,估计是民国时代就留下来的,粮食局当年是很要害的单位,那个时代,粮食局的粮仓是最好的建筑,粮食局墙上刷的大字是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粮食局的粮仓时常有卡车运来粮食,卸货是按每吨多少钱来支付给卸货的人工,由于与粮食局管粮仓的负责人有些来往,父亲被照顾了几次卸货的苦力活,挣了几十块的血汗钱,父亲不买烟不买酒,买了一只电熨斗,让我母亲平时缝缝补补,浆洗熨烫有个好用的电器来帮手。
漾濞小商店里有一种本地糕点厂生产的蛋清饼,九分钱一个,记得父亲后来和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常常说起一件事,就是蹲在母亲家的老屋子门口,看着对面的副食商店,肚子饿了,想买一个九分钱的蛋清饼,犹豫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没有买了吃,那个困苦的年代,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父亲需要责任和担当的年代,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生活中总会有些不期而遇的倒霉事。那个时候,为了改善生活,增加一点经济收入,家里养了一头猪,我最主要的家务就是每天放学回到家后,背上背篓去田间地头找猪草,每年秋天,粮食局的粮仓都会有很多人来加工核桃,漾濞出产核桃在全中国都有名气。每天下午,加工核桃的工人们走后,场地上都会有一些扫不干净的核桃渣渣及碎末,父亲在母亲的指使下,就用簸箕去打扫这些核桃渣渣,拿回家来煮在猪食锅里,给猪增加营养。这年三妹妹刚刚出生,有一天下午,父亲背着小妹妹,前往粮仓场地上去扫那些核桃渣渣,不想守粮仓的一个老头不乐意了,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冲突中父亲的眼睛受伤了,小妹妹还差点从父亲背上掉到地上。冲突过后一切都很容易就平息了,毕竟母亲是本地人,家族从清朝就一代代繁衍下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亲戚关系,没有人会再找我父亲这个外乡人的麻烦。
多年以后,读到“贫穷是万恶之源”这句话,觉得是十分有道理的,父亲一介书生,为了些许生计,也曾经出过这么窘迫的糗事,想来真是无比的悲哀。
2017年9月3日
伍 塑料攒钱罐
爷爷退休前到了昆明安宁附近的一家化工厂,一九七六年的冬天,三妹出生了,爷爷奶奶退休后,父母决定把我送到爷爷家里生活一段时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漾濞到昆明,依然走的是老滇缅公路,老公路的里程估计有五百来公里,需要两天的车程,那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为了来往路程的便利,父亲结交了很多卡车司机朋友,许多往来于滇缅公路的卡车司机朋友,记忆中家里总是好酒好肉招待他们,就是为了亲戚和家人往来的路途中,可以请司机们行个方便,搭个免费的随风车。
离家的时候乘坐的是一个湖南司机的卡车,司机姓冯,淳朴善良,我和父亲就乘坐冯师傅的车前往昆明的化工厂爷爷的家。
儿时出门旅行是无比快乐的,坐在卡车驾驶室里,观看沿途的风景,心里无比的欢呼雀跃,司机是父亲的朋友,那个卡车就像自己家的一样,我一路上可以了解车的刹车,油门,离合器,拍档,车灯开关等,好像觉得自己也可以把卡车驾驶在路上行走。
旧式卡车的车速是很慢的,尤其上坡的时候,发动机嗡嗡的嚎叫声,驾驶室里相互聊天都听不清,而这种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像旧时的摇滚乐一样伴随着我们的旅途,估摸着是走了两天时间,路途中住了一个夜晚,才到了昆明。
人生的时光记忆中,总有些场景是你无法忘记的,我记得和父亲分别的场景,好像是在客运站,客运站就在老滇缅公路旁,父亲是在这里把我交付给爷爷的。客运站对面是百货商店,父亲说要给我买个玩具,在商店玩具柜旁,我看着那么多的玩具,可以说是目不暇接,我看见有电动玩具火车等很多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玩具,而父亲只是买了两个价格不是很贵的塑料攒钱罐,一个给了司机冯师傅的儿子,一个给了我。攒钱罐是一个欧式小屋子的形状,白色的房子、红色的斜屋顶,屋顶有烟囱,烟囱就是投放硬币的地方。那个时候的硬币只有壹分、贰分和伍分三种,小孩能攒个几角钱就是大富翁了。小房子的门是活动的,就是取钱的机关,攒钱罐不大,十多厘米见方的样子,我只记得父亲蹲在我旁边和我说了些什么,具体说的什么却已不记得了。父亲上了冯师傅的车,冲我和爷爷挥手告别,依稀记得父亲的表情是不开心的,有几分依依不舍,我好像是眼睛里噙着眼泪,我自小就不是爱哭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只是觉得当时的感觉是怅然若失。
后来父亲老了之后,说非常后悔在我童年的时候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寄养的这一段时间,而我只是觉得这段生活在我的人生历程里有了里程碑的作用,我学会了不怕孤独,学会了独处,学会了自己洗衣做饭独立生活……
后来在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个小小的塑料攒钱罐一直是我的心爱之物,每天都要拿出来玩上一阵子,现在想来,一个塑料物品,真的没什么可以玩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无法抹去。
如今父亲已经离去,我也年将半百,觉得记忆中还珍藏着这许多美好的回忆,把它写出来,也是对父亲的一种缅怀。
2017年9月27日
陆 一碗小锅饵丝
小县城的生活大多是自给自足的,地处边陲之地,商业不发达,人口也不多,每家每户都养鸡养猪,种菜浇地。每周日,县城都有集市,山区的少数民族都会赶着骡子马匹到县城集市,卖些木炭、柴火或者山货,再买些生活必须品回去,集市有着独特的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我还有着清楚的记忆。有一次集市,有些人在公路边偷偷卖酒,酒是用医用的500 毫升葡萄糖瓶子装着的,大人们不出面,让小孩在路边蹲着卖,山区的少数民族大多爱好喝酒,他们看见小孩在卖酒,都会蹲下把葡萄糖瓶子的橡皮塞子拔掉,喝上一小口,尝尝浓淡,看看酒里的水掺的多不多,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就会付钱买走。当时这样卖酒是违法的,我记得街上有套着红袖套的执法人员,对这种私自卖酒的是要没收的,有两个带红袖套的男人把一个小孩面前的两瓶酒没收拿走了,这个孩子立马跑回家去,叫了家里的人,估计是这个卖酒孩子的父亲一路狂追后,硬是从这两个带红袖套男子的手里把酒抢了回来。我和父亲在街上走着,看了这一幕,父亲对我笑笑。
一九七八年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市场经济也开始在小县城里四处萌芽,国有的饮食公司在县中学的大门口开了一个早点铺子,我们家几个孩子的早餐,常常是包子馒头,父亲是山西人,会做面食,家里总是发面蒸馒头,我们的早餐就是拿着一个热好的馒头,夹点腐乳,就边吃边去上学了。
或许是想换个口味,听同学说学校门口早点铺子的小锅饵丝很好吃,有一天早上下了早自习,就和同学来到早点铺子,进去后看见父亲在吃着一碗小锅饵丝,饵丝应该是刚端上来,还没有吃几口,父亲让我赶紧吃他的那一碗,父亲也没有重新去买一碗,就出了早点铺子,去办事去了。
那一碗小锅饵丝很好吃,虽然只剩下四分之三碗,现在想起来,好像吃了很长时间。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脑子里对这个场景永远都无法忘记,就记得父亲看见儿子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站起来让自己的儿子来吃,或许父亲刚刚才吃出了小锅饵丝的几分滋味,就放下筷子起身离去了。这一碗饵丝,我吃下去的是父亲淳朴无私的深爱,以至于我在成年后,接触到基督圣经故事里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
这顿早餐,对于我来说,就好比父亲对我灵魂的救赎一样,每次想起总是泪流满面,永远无法忘怀。
2017年10月2日
柒 一对沙发
父亲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他年轻时候的业余爱好是做家具当木匠。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父母在县农业局的兽医站里工作,一年下来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所以有大把的时间拿来种菜养鸡和做木匠活。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在父亲的木工房里,看着父亲锯木头,用推刨推木板,用墨斗弹线,父亲的木工工具很全,锯子和推刨都有很多很多,家里的柜子,书桌,大床、小床都在父亲的手里一件一件制造出来,父亲大学里学的外语是英语,虽然不算是精通,还是略懂一些,于是每一件家具制造出来,父亲都会在家具背板上面用英文写上:MADE IN CHINA。
做木工活,会产生很多刨花,这用来生火做饭是最方便的,不同的木料,有不同的木头香味,有松木、樟木、水杉等等,松软的木料很好加工,但是容易变形和受潮,硬质木料难锯也难刨,但是做出来的家具就厚重和牢实,不容易变形,从小跟着父亲在木工房里玩耍,我成年后的动手能力也还可以,自己家里的插座、灯泡、地漏、水管什么的,也能自己维修不用找人,但总的来说,还是赶不上父亲的动手能力。
后来在北京工作的时间里,参建的一个古建筑工程,需要采购一批明清家具,就去参观了北京清朝时候就给皇家打造家具的龙顺成百年老字号家具厂,看着那些紫檀木,红木等各类名贵木材打造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讲解员介绍所有龙顺成出品的家具全是榫卯结构的,没有一颗钉子和螺丝。想起父亲年轻时候在我们家自己的木工房挥汗如雨地制造家具,感慨万千,父亲亲手做的衣柜、大床和书桌家里现在还在使用,那些四十年前的榫卯结构依旧没有损坏,父亲的家具也从来不用钉子和螺丝,全是榫卯结构,业余木匠能达到如此精良的水平,实属不易啊!每次看见这些父亲亲手制作的家具,看着岁月在家具上留下的陈旧的颜色和搬动过程中破损的痕迹,内心无限地伤感和怀念。
大概是八零年左右吧,改革开放让经济开始活跃了,中国人家里开始有了沙发,沙发是外来词,是英文SOFA 的音译叫法,我们小时候在县城里生活,各家各户是没有见过沙发的,父亲从朋友那里搞来了一套单人沙发的图纸,自己做了两个沙发,沙发的制造比其他家具的制造简单得多,只是需要买许多弹簧来自己用麻线绷出坐垫和靠背,总之父亲没费多大的力,两个漂亮的单人沙发就顺利完工了。沙发油漆好了,放在家里,一下子觉得房间的档次就上去了,两个单人沙发中间还配有一个木制的茶几,茶几在后来的几次搬家中估计是扔掉了,两个沙发至今仍然还在家里放着。
这两个沙发从父亲手里制造出来快四十年了,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坐来坐去,坐走了多少美好的家庭时光和回不来的美好岁月。
父亲在这两个沙发上坐的时间是最多的,几乎所有业余在家的时光里,父亲都是坐在这两个沙发中的一个,看书、看电视。父亲病重的最后这一年多的岁月里,白天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坐在这两个单人沙发上,吃饭也都是在这沙发上吃,一直到弥留之际前几天,还是一如既往地坐在这两个沙发上。
自家的东西用惯了,就是那么顺手,沙发设计的很好,坐着很舒适,我每次回到父母家也是一屁股就在这两个沙发上一坐,就不愿意起来,有时候还会在沙发上打盹,尤其是在下午时光,坐在沙发上就想合着夕阳的光迷迷糊糊地昏睡一阵子。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一首诗《你还在我身旁》:
瀑布的水逆流而上
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
太阳从西边升起 落向东方
子弹退回枪膛
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
我交回录取通知书 忘了十年寒窗
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
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
关掉电视 帮我把书包背上
你还在我身旁
这首小诗或许是无数个失去了父母的人内心最最真切的感受了,看见沙发,就仿佛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的样子,止不住泪流满面,心痛不已。
2017年10月9日
捌 山西面食
我们兄妹三人都爱吃面食,这和家里一直以来爱吃面食的习惯有关。父亲会蒸馒头包饺子,还有烙葱花饼,这些美味的面食从小就伴随着我们兄妹三人的成长,成年后去过几次山西故里,才知道山西的面食有几百种做法,父亲的面食的做法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一点点传承下来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父亲常常在厨房里和面,这是个体力活,面和好了还要醒一整子,然后盖上一块纱布放一夜,第二天早上,面就发酵了,父亲把面一块一块地揪下来,揉成馒头的大小,放进蒸锅里蒸。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又大又白,口感劲道,回味无穷。蒸馒头是个辛苦的活计,可父亲为了让我们兄妹早晨去上学的时候都有热腾腾的馒头做早点,夜里要和面然后放置好发面,早晨六点不到,就要起床来蒸馒头,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伤感。而今,满街都是做好的馒头包子,价格也便宜,想吃买来吃就是了。只是那个我们兄妹都还小的年代,父母微薄的工资不能让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在外面吃早点,父亲就辛苦起早贪黑为我们蒸馒头。
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
父亲一生也有理想,也有情怀,但他一直都接受着自己的平凡并一生都享受着平凡而又快乐的时光。我们兄妹三人都不会做面食了,想吃了都是街上买了或者点外卖送到家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方便和快捷,但是那和面和发面的生活经验也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的饺子包得很有形状,肉馅是韭菜的,从小时候的记忆,父亲包的饺子就非常的好吃,我们一家五口人,每次包饺子都要包一百来个,我们三个孩子是看着父亲包了无数次的饺子、吃了无数次的饺子长大的,每一个饺子的回味,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只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美好的回忆了,人世间已经不可能再吃到那种滋味的饺子了。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开始和面,发酵以后,蒸成馒头。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开始包饺子,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包出父亲当年的味道。
2017年10月26日
玖 脉地下乡
父亲是学兽医专业的,在县城兽医站工作。小时候记得父亲经常要去下乡,帮助山区农村搞牲畜的防疫工作,替村民的猪牛羊马治病。
脉地是漾濞县的一个乡,离县城有二十来公里,现在好像是已经改名为漾江镇了。记得是我十一二岁时候的一个暑假,父亲去脉地下乡,就带着我一起去了。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的,自行车是那种载重的上海永久牌,我坐在后座上,从县城去乡里的公路还是土路,一路上我们欣赏着美丽的山水风光,很快也就到了目的地。
我们在那里的住所是在一个坡上的一栋农村普遍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只有一层,我们使用靠左边的一间屋子,房子的门口有一颗板栗树,树冠非常高大,八九月份,正是结果的季节,树上结满了板栗的果实,我随身带着弹弓,对着树上打下几个板栗,第一次认识板栗的果实原来外面还包裹着一层毛刺的外皮,剥开外皮,里面才是二个或者三个板栗的果实。
从山坡上能看到下面的乡镇村落,一户挨着一户,墙体是土夯的,屋面是青瓦,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乡下没有什么好玩的,除了山还是山,人烟稀少,傍晚时分,父亲开始做饭了,我们住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木床,没有别的什么家具,做饭是用一个烧柴的小炉子,先是用锣锅煮了米饭,然后炒了个洋芋,也就吃饭了。夜晚来临的时候很无聊,父亲带着几本书,胡乱地翻看着,我也早早地睡了。夜里有蚊子,后来听父亲说,有只蚊子停在我的额头上,父亲用手指把蚊子就地摁死,那蚊子已经吸了好多血,摁死后,我的额头上都是蚊子血。
一个上午,有个老乡牵了一条水牛来看病,牛摔伤了后腿,后腿的髋关节部位被岩石蹭掉了巴掌大的一块肉,好长时间没有好起来,伤口部位已经化脓长蛆,好多蛆在伤口处的肉里蠕动,父亲用碘酒给牛的伤口消毒,用止血钳把腐烂伤口处的蛆虫一个一个拿掉,最后用黑黑的沥青一样的鱼石脂(去腐生肌拔脓的兽用外用药)涂在牛的伤口上。整个过程父亲认真而细致,干净利落,我远远的站在旁边看着,想着牛会不会踢人或者跑动,却见整个治疗过程中牛都十分的配合,安静的站着反刍。
乡下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落后、孤独和寂寞。父亲的青年时代就在漾濞的各个山区和乡镇里燃烧着他的平凡岁月,没有激情,但却充满着生活的希望。
父亲说学习兽医这个专业也是无奈,父亲立志要学医,或许是受我爷爷是外科医生的熏陶和影响,父亲高考了三次,最后才被云南农业大学的畜牧兽医专业录取,原因是我的爷爷曾今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医,当年那些手握权力的掌权者认为我的父亲这样出身的人如果学了医之后,在为广大劳苦大众治病的时候一定不会救死扶伤的。
兽医成了父亲大半生的职业,其实在那个农耕文化为主的小县城里,这个职业也还是很吃香的,猪牛羊马等大牲畜都是农家的重要财富,很多人都有求于父亲,县城周边乡下一些大户人家,家养的牲畜比较多的,逢年过节、杀猪宰鸡的时候,也常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做客,好酒好肉地招待我们。
县城里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来做,住的地方就是工作的地方,由于场地宽阔,父亲自己盖了猪圈、鸡圈,打了水井,种了自留地,我们兄妹三人的少年时代过得是幸福的,肉食从来不缺,家里养的几十只鸡,每半个月就要吃一次鸡,过年杀一次猪,腌猪肉可以吃到第二年的秋天,蔬菜都是新鲜的白菜、南瓜、玉米、豆角、韭菜等等,地里的蔬菜基本上吃不完。
当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在那个城里人闹饥荒,凭票供应肉蛋油的时候,我们家在这个小县城过的是肉菜富足的生活,想起这些,便深感父亲的平凡而伟大。
2017年11月3日
拾 阑尾手术
十三四岁上初中是最快乐的时光,除了上课学习就是贪玩,觉得时间是如此的不够用,打篮球,河里游泳,打鸟,总之记忆中就是玩。一九八二年的冬天,我连续几天觉得肚子痛,在校医务室要了点胃舒平,吃了也没啥作用,便回到家里昏睡。那些时爷爷正在我们家小住,爷爷退休前是外科医生,爷爷看了我的情况,对我父亲说快带去医院。县医院有几个优秀的医生也是和我父亲的命运差不多,都是家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小县城,他们平时和父亲的私交都很不错,或许是命运相似,所以惺惺相惜。
父亲吃过晚饭,带着我直接去了李医生家里,很有经验的李医生判定我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小县城有小县城的方便,当天夜里,我的阑尾手术就实施完毕了,整个手术和之后住院的医疗费用是五十元,现在想来,或许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早就已经享受过了。
我做这个手术时,碰巧母亲下乡去了,父亲把两个妹妹和爷爷安顿在家里,就陪着我在医院,手术是局部麻醉,我能躺着看到手术台上的无影灯,通过无影灯的镜面反射,我能看到我的肚子在医生的手术刀下被切开,后来就是扯心扯肺的疼痛,嘴里干燥和苦,待迷迷糊糊的醒来已经躺在病房的病床上,好像是深夜了,父亲陪在我的病床旁。我感觉伤口开始无比的疼痛,父亲叫来医生,医生给了一剂杜冷丁,疼痛很快解除,我于是便又入睡了,再醒来已经是早晨,父亲已经回去做好了很有营养的饭菜送来给我。
我康复得很快,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出院回家休养了。我是家里第一个做阑尾炎手术的,在后来几十年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还有二妹也都在不同的年份里做了阑尾炎手术,这真是有些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家里的饮食习惯或者遗传基因有什么关系。
这次做阑尾炎手术,班里有一个女同学来看我,还给我买了橘子罐头,那个时候的水果罐头还是很贵的,这个女同学的叔叔是乡镇的兽医,和我父亲平时有业务往来,也是很好的朋友,常常请我们全家去他们乡下的家里做客。而再次见到这位女同学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2017年11月11日
拾壹 举家搬迁
1983年的秋天,我们全家搬到了昆明。父母亲大学毕业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再由于出身不好,大多都是被分配到偏远的地州和县上。1978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所好转,父亲为了我们三个孩子能有更好的教育和未来的工作,终于找到了把工作调往昆明的机会,于是我们全家举家搬迁。
那个年代没有搬家公司,父亲结交了很多的司机朋友,这些司机朋友在昆明往滇西运输的过程中,常在我们家里受到好的招待。靠着良好的关系,一个司机朋友顺道免费为我们搬家,一辆老式的卡车,搭载着我们一家五口以及所有的家具物件,甚至连家里养的猫和狗都一并载到了车上。
那一年父亲四十一岁,父亲凭着强壮的身体一趟一趟把各种物品搬运到车上,搬了整整一天。那一车我们全家的财产估计有七八吨重,父亲汗流夹背的身影至今依稀还在我的眼前晃动,结实的身型就像山一样,给了全家安全的依靠。
车离开故乡,父亲和当地亲友依依告别,父亲好像流泪了,漾濞这个地方,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生活了十四年,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父亲基本都靠着双脚走遍了,就连母亲这个本地人没去过的深山老林,父亲也都留下了他年经的足迹,父亲退休后常常回漾濞访亲问友,每次回去都很开心和幸福,我以为父亲一生最幸福和值得回忆的时光应该就是他在青年时期在漾濞的这十四个春秋。
搬家的旅途是漫长的,我们沿着老的滇缅公路向昆明进发,车拉的重,开的也慢,我还不幸得了腮腺炎,两个腮帮子肿的无比难受,一路上水也喝的少,饭也吃的少。
在旧式卡车的近三天的轰鸣声中,我们到了昆明的新家。这个新家比我们想象的要失望太多,这是文革时代滇池围海造田的成果,当年的昆明海埂五七农场,一片荒原,遍地沼泽,荒原上一处库房就是我们的新家。三十几年过去了,这里却成了风水宝地,地价飙升到最高,不得不佩服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策。
这一次的举家搬迁,对于我们全家是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我们兄妹三人未来的人生命运也因为这次搬迁而彻底地改变了。
我们的新家就在农场的几百亩牧草场中的一个晒场周边的库房里,虽说简陋,但是居住面积是足够大了,还有院子和厨房,我们后来垒了鸡圈,屋外大片的土地可以供你开垦来种菜种瓜,我们于是又开始了和在漾濞一样的农耕生活。家里离昆明城里有七公里,只有一趟郊区的公交车,公交车站离家有二十分钟的小路,我们兄妹上学就要乘这趟公交车。这一年,我们的生活是彻底地改变了,生活和学习远远没有在漾濞县城那么方便和舒适,现在回想起来,刚到昆明那几年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冬天的早晨,上学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而放学坐公交车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父亲说我们过的是两头见星星的日子。
人往往低估了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全家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适应了各自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我们兄妹三人都开始学习说昆明话,我们来自县城的口音常常成为同学嘲笑的话题,地域歧视在全世界都是广泛存在的,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们兄妹三人在上海金茂大厦吃饭的时候,妹妹一阵感慨:漾濞县城的三个土娃子,今天能吃上这样的餐食,觉得像在做梦一样。
2017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