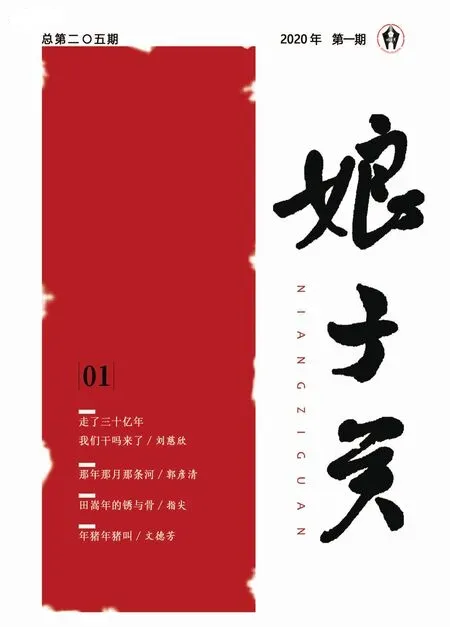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2020-11-18申飞凡长治
文 申飞凡(长治)
1
母亲从玉米地回来时,夕阳吹拂着她憔悴的脸颊,黄昏的光线绕过小路两侧渐次稀疏的白杨,稠密地覆盖在她的身上,似乎要融为一体了,她们彼此加深着各自的颜色。山风携带自身的锋刃君临塬面广袤的黄土地,驯服落日,扎进深处落霞的天色里。继而癫狂的黑从脚下向外弥漫,席卷至天边,隐约中遥远的炊烟爬上半坡散成残月的光晕。这条土路常年是黑咕隆咚的,鲜见人影,只有农忙时才有几缕人影被杨树巨型的荫翳吐出来。夏时,万物隐秘的末梢遮挡住了坐井观天的最后一丝希望,只有入冬后杨枝面目狰狞,短兵相接,像禁卫军般执戟而立,一把把长矛直刺敌人胸膛。
雨季,乡下的土路无法抵御风雨的鞭打,坑坑洼洼的,裸露出生活的苦难与沧桑。就像我们无法抵御岁月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斧斫刀刻的痕迹。老去成为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年岁增长,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骨缝里的光阴泄露,皱纹悄悄爬上面颊,还有那些像儿女般的白发承欢膝下。必然,多年以后,我开始白发,少语。像一截干瘪的枯枝,伸展在残叶之上,战战兢兢地时刻警惕捕猎者或拾柴人的脚步。
乌青的天,黄昏出现在塬面的弧线之内,跨连绵的山丘。傍晚,满脚泥泞地从垄岸下的玉茭地爬出来,每个人都尽显劳累,脸色凝重,双眸无法抹去力竭的疲乏。来宝作别,示意院中摊着萝卜干,入夜,露水湿重,需及时收回。母亲点点头,干脆一屁股坐在垄道的石牙上,一声不吭,就这么坐着,目光盯向远山,仿佛生锈的两枚钉子,失去光彩。她休整半天,和耕地数日的笨牛一样,反刍着劳累。深蓝的上衣袖子被往上挽了好几褶,绣着补丁的土蓝长裤肥嘟嘟的,泥土钻满了细微的布孔,一方头巾沾满汗液围着她瘦小的脸庞。离得那么近。她一声不吭,间或让两只紧紧裹在褪色的蓝色帆布鞋里的已经奔忙几里地的小脚出来透口气。这双鞋于我而言,早已不合时宜。母亲觉得丢掉怪可惜的,倒不如上地穿,还能顶工作鞋。显然这双鞋的码数小,脚背挤压得膨胀起来,勒出的血痕泛青。野草身披晚晖,放牧睡意,霞光粗糙,映得母亲如衣襟上弹落的灰尘。
显然,因为鞋不合脚。鞋里灌进了大量泥土,和脚心捂出的汗液和在一起粘连在脚底板和脚趾缝里,携带着一股陈旧的泥土气息。母亲拍拍石头上的灰尘,示意让我坐下。我贪恋这样的晚霞,贪恋母亲手掌厚茧的温度般安抚我对暮晚沉落的忧伤。我缩在石上,靠肩打盹,朦胧中,我变成一尾波浪,扩散,感受到汹涌的海力,最终成为自己的波澜,平息、平静。
突然地抬头,月亮挂得很低。我和母亲动身离开。刚走进村子,犬吠声就响动起来。村子里几近八成的人家都养狗,这畜异常灵敏,有一丁点儿响动,只要有一只犬挑头,邻近的也跟着吠起来,狂吠一声高过一声,波浪式涌向周遭。黑暗、静寂。村庄从夜色里挤压过来,灯光在细雨中跳闪。土塬从不会空荡,人会。暮晚下的小村落在银辉的光晕中保持着静态的绵延,清一色的土坯房、青砖房错乱且零星分布。树梢没入静默如湖的夜空,枝杈间有风,往返于山顶山谷间,母亲身体里的风湿总是夜夜回涨。
2
村子用一面土塬做靠山,零零散散的刺木错落有致铺排开,护佑着山塬的巍然和脚下的山村。它们长得并不似绝壁斜逸的松柏高大,却依然固执地固守在塬面。或许,他们先于我的祖先来到这里,过着自己庸常的一生。在漫长的岁月中,旱涝已习以为常,早些年时,以祖父为邻的几户住在塬下。开门见塬,三面土丘在地平线上浮动,近在咫尺。可天公不作美,丰年雨水一连下几周,除零星的野草外,塬面袒胸露乳。雨水汇集泥沙从塬的陡坡面狂奔而下,猝不及防冲毁了塬下的庄稼,玉米蹚着水欲图往高地跑去,土坯房被浸泡在洪流里,随时有倾倒的可能。不得已祖父和邻近几户向后撤退数十米,重新选择房址。村大队为防止山体再次滑坡,召集大伙儿开始绿化陡坡。不过种下去的树木九死一活,即便成活也和村里耄耋之年的人一样,瘦小干瘪,弯腰驼背,活在山额的沟壑里。
攀爬至塬顶某个稍微开阔的地带。山下的村落,低矮的篱栏缱绻怀抱,曲折中被时光赋予桃花源的闲适,不经意间更多的切面于蜿蜒中呈现出开阔之态,半盆地状的低处平原,田洼顺势被雨水、粪水养大、养肥。在我巴掌大的故乡,比塬面更为神秘的是云影、风影、石影。云朵成群结队在塬面之上开出一片蔚蓝,天空低垂下来,仿佛有交谈之意。大风驮着草木跑进塬面跌跌撞撞的胸口,石与石更决绝对立,没有南方石林的波谲云诡,呈现出宽厚和宁静。芬芳的气息中,塬面被流水冲蚀的阵痛,已被葳蕤的草木治愈。
雨来得没有一点儿预兆,就携带着沙土在村落久久徘徊,在野地上起起落落,折腾了月余。雨声达到了极点,才肯放缓步履。土坯房里潮气重,拨亮土灶柴火,暖暖房。这样的天气我最喜欢躺在土灶上酣睡一晌。风声掠过我,化为马蹄,踏破山间云层的黑云,山沟沟瞬间化晴。
雨过万物生长,各式野菜蹿出地表,保持茂盛的长势。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诸如灰灰菜常被乡下人作为吃食择回家,煮熟后凉拌。
村子的秋天格外得短,玉米秆越发得焦黄,披着一身黄袍自由地行走。多年来,父亲和云生爸外出打工,只在年节时回来。母亲或许早已习惯这种分离,便自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秋收时,为了赶在日头落山之前回到家,母亲和我总是在天还未透出一丝光亮的时候便早早动身了。来来回回重复数日,一年的收成就收回了家。
挑个晴天,将玉茭收回家后,就堆起了玉茭垛,在乡间恒久地装点着农家的门面。遥遥望去,我想起凡·高的《向日葵》,不同程度的黄色色块交织叠摞在一起,发出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因此在凡·高和乡下人奔放不羁的笔触下,每朵向日葵和小院都被赐予强烈的生命力和蓬勃燃烧的张力。起伏的山梁和凹凸年迈的土坯房再次被时光唤醒,流露着显而易见的贫穷、古朴,但画龙点睛式的玉米垛、满山阳光,吐纳着年少遗梦和灵魂皈依的平庸、窃笑。
燕行回旋,鸟声清宛如水,万物窸窣泊于草木中,预告着绵绵细雨的到来。乡下人都明白,他们暗享着这片土地的哺育和他的一切。
3
明月从山塬上升起来,撒下遍地碎银,映亮了母亲的发丝,散发出银辉。有月光的夜晚,能看到猫的影子在草里穿行,却甚为幽静。跃入耳帘更多是窸窸窣窣的声在草野里响动,在远处听得清朗,寻声而去戛然而止,无法辨听出声音的出处。稍稍离远,便又从地面弹向高空。这样的夜晚,晚饭毕,全家围坐在火炉旁剥玉米。
颗颗饱满、璀璨的金黄玉米粒包裹阳光的光芒被改锥从棒子上撬到簸箕里,我右手持玉米,左手顺着粒生长的胎床,一列一列用手掌掰下。掰下的玉米聚在簸箕中,朴实得像泥土里的孩子,沾满人间的烟雨,连心脏也带着跃动的地理,豢养深深的乡愁。堆积的玉米需平铺在阳光栖身的台阶上,舒舒服服泡个“日光浴”。秋的日子,阳光逐渐褪去了锐气,变得柔和,在横亘的田埂上甩出巨大的根须。其时,小葱也撒种了。
一连数十日剥好的玉米预估够家里一年的吃食,便把剩下的无论好坏、颗粒大小,一股脑儿全都卖给镇上的收粮站。一时手头富裕起来,给家里置办物件,再买些肉。当然,建一幢体面房子是每个农村人的愿望,可这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至今,我还记得荒废已久的一些细节。八岁那年,父亲用买粮的钱和自己的血汗钱置办了家里第一台长虹牌彩色电视机,使我长时间的“黑白世界”多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此外,当电影下乡甚嚣尘上,只要某街巷一搭白色幕布,未至晌午放电影的消息就在村子里不胫而走。尤其是夜间放电影时,开演前,村民就搬着自家的小板凳和相熟的一起坐在幕布前,姑娘们、小伙子们成队扎在四周。若是在二月十七看大戏,他们早就消失不见了。等灯一瞎火,到处黢黑,幕布反射的放影带的光墨淡了满天星空。
黑压压一片人海,密不透风。相熟的中年妇女有说有笑,忽又环顾四周。不难揣测,他们说道的铁定是东家长西家短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很少去关注电影的内容。闻大家哄堂大笑便也跟着邯郸学笑起来,自己也不知道要笑个啥。直到电影结束他们才肯散去,倒是打扰得旁侧看电影的灰溜溜的。小孩被大人抱在怀里,不消片刻,索性倚在父母的肩上睡着了。若被惊醒,瘪瘪嘴,立即大哭起来,由近及远,声音落在地面,再被横一脚竖一脚踢向高空,窜到小巷里乱逛,潮起潮落。
农忙的就干脆躲在家里不出来,谁叫也不开门,倒也落得个清静。母亲擀面下面,收拾收拾,便挑黄豆洗黄豆,厨房的灯一直亮到公鸡打鸣时。一进入腊月,东村口的石磨和石碾总是闲不下来,磨豆、磨米的人排了队,一时间空寂的街道变得喧闹起来,人语嚷嚷,脚步声鼎沸。不知不觉中,日头已近晌午。
下午从家门出来,暮色渐侵,我晃晃悠悠走到石磨和石碾处找母亲。磨豆、磨面的人依旧人影绰绰。磨道和碾道里的人挨过了晌午轮到自己磨,嘴角挂了一丝微笑,又突然严肃起来认真拾弄着自己手里的活。思忖半天,在乌泱乌泱的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云生。云生跟着父亲排在后面,有些不耐烦。见状,等轮到他家也在傍晚。索性我和母亲作别,找云生去烤地瓜。
4
这是云生离开乡下后第一次回来。
秦奶奶思孙心切,云生亦如。再加上八十大寿,她常感自己行将就木,殷切希望多看看自己的孙子。八十整寿村里人讲究要大摆家宴,流水席上觥筹交错。只要近邻全都喊来帮忙,母亲磨完豆也紧赶着去了。
往昔,我和云生在同一所学堂上学,便结伴同行。村东头有家早餐店,营业二十年。从小学开始我和云生隔三岔五就来喝豆腐脑。他家的豆腐脑有一股木香,甘甜细腻,味美价廉。在秋风凉凉的清晨,喝上一碗,一下就暖和起来。
我从家中翻出地瓜,朝我俩的秘密基地走去。
黄土高原的秋夜,是夜间的冬天。月明如初,与半年前塬上的明月拥有相似的皎洁。我和云生坐在垄岸上,身后半米不到的火堆被秋风扑哧扑哧吹着,一闪一闪的。那些未及烧尽的枯枝冒着白烟,吐出几口烟晕。火星在秋风的撩拨下像是年轻时云生爷爷打出的铁礼花,绚烂而短暂。寒风嗖嗖往脖子里钻,我们准备离去。途中,我们谈起好玩的琐事,将目光平铺在路边荫翳的杨树上,杨叶吹得黑暗发出飒飒的声音,茫茫盖住了我们稀疏的脚步声。落叶挣脱杨树温热的胸腔,完成落叶归根的仪式。在我们抵近道路时,谈话声惊扰了树梢的飞鸟。一大群麻雀在灰蒙蒙的天空扑翅,继而分散。遽然而至的空荡与冷寂让我想起去年,云生尚不敢走夜路,听老辈讲鬼故事都躲得远远的,可到城里上学不及一年,他已变得坦然,曾经的胆小怯弱也已烟消云散。栖在他眉宇间的自信,与生俱来一般散发开。
寿毕。自此分离后,云生回城念书。我们少见面,渐行渐远的眼界如代沟成为本不属于我们两小无猜的标签。秋深暮晚,上学归来,途经云生家。大门紧锁,落叶悉堆门前,像晚风捎来的旧消息,只收,不启、不寄。
可以想象到,他从深山的村庄走到盆地的小城,泪水一定刺痛了双目。
夜市散落在大街小巷,霓虹灯似不断变色的灯笼,人们三三两两地吃喝,来来回回的车子像赶集的人潮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这是云生和我长谈中提到的城市印象,我依旧记得他当时讲得热切,溢美之词络绎不绝,他的眼神幽深而清亮,仿佛一汪倒映着月光的泥沼,一不留神儿就会被吸进去,让我怯怯地萌发长大后翔抵城市的羞涩梦想。
5
自云生进城。城市成了悬在村里人额头前的蛋糕。
村里人如过江之鲫般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曾经喧闹,还有些聒噪的农村渐渐平寂下来,村落十室八空,少了些欢声笑语,只剩孤寡老人和幼童留守。
秋风不断添加着自己的寒冷,南飞的雁阵彻底离开村庄的视线。村口那条泥泞的土路结板成巨幅的木板雕画,黄昏深一脚浅一脚斑驳落在脚边,冒出的千层霜在夜色中摇晃像雪粒散落在棱角分明的雕画上,霜色透过脚印清晰可见。土路的尽头,袅袅升起的炊烟宛若乡村里一段最柔美的丝绸摇曳在天边,远山半遮面朦朦胧胧地倾向千沟万壑间叠起的塬。深冬后,土路两翼的杨树光秃秃的,朔风敲打树梢的无眠。雪花像鸽群飞抵人间,生命中的丧失感愈发强烈,悲伤、啜泣将我包裹,祖父撒手人寰时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我,幼时叛逆的我,乖张的我。
淡淡的秋风下埋藏着沉重的无法翻动的新土,踽踽独行,把身体走成茫茫夜色,把灵魂走成漫天繁星,几只沉默的乌鸦飞过,人散……
一根根白骨挤在一起成为历史的内伤,一座座坟埋葬的血肉又将在黄土地反馈,而当这种习俗成为习惯,死亡变成一种无法与人分享的仪式,所以能以完整的魂灵叶落归根大概是每个太行人一生的期许。
祖父辞世时已逾九十岁,村里称为喜丧。
归途,难以抑忍的痛苦溃堤而出,泪水无觉中从眼角涌出,如刀锥心,此后多年里我都不敢提及这段往事,类似伤口的波纹,在心头持续发酵。
脚下的咯吱声愈来愈响,车轮压实的雪面又被新雪替代。我抖动着身上的雪,回头望去,祖父的一生,也曾路过风,拥过雨。千帆过尽,人间陈旧,他佝偻的身影已褪变为田垄间的一抔黄土。那红木棺材,从老屋的正堂,沿街沉泣,移到满山草木中,九十年的光阴被新土掩埋。母亲泣不成声。恍惚中,我蒙眬看到祖父拾柴的身影,阳光稠密地落在他的身上,它们关联的词语——枯黄与衰败。
追风去。我明白,挣扎与迷失、宿命与姿态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与心,在日益剪裁的余生里,不论追风何地,我的行囊里梦想和故土无法全都留下。而我唯愿,在漫山雾岚里,保有初心。
起伏的土丘上,依稀可辨的只有历经数载的土屋。离去那日,暮色落下,大片大片的白将夕阳搂在怀里,我的身后几行稀疏的脚印亦被风雪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