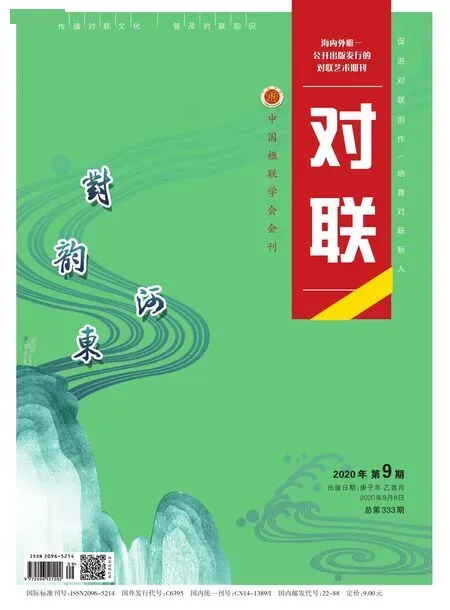在道义与功名的夹缝中求生
——扬雄《逐贫赋》品鉴兼论义利之辨
2020-11-17李牧童
李牧童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也是有名的思想家。虽然家世清贫,但他年少好学,博览群书,且安贫乐道,志趣不俗,『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扬雄传》)。年轻时的他也喜欢舞文弄墨,因为仰慕同为四川老乡、且同患口吃的前辈司马相如,于是先后模仿其文风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多篇赋作。此外,又仿《论语》写下了《法言》,仿《易经》写下了《太玄》等两部思想著作,可以说,他是一名成功从模仿秀中脱颖而出的实力选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三观颇正的有为青年,一生却郁郁不得志,年过四十了才出道,历仕成帝、哀帝、平帝三朝,曾经的同僚如王莽、董贤之辈,都已经位列三公了,他还是老样子,徒然作《解嘲》以自宽。哪怕在王莽称帝后的新朝,一堆人拍马逢迎加官晋爵之际,他也仅仅因为工龄长而做了个大夫,甚至还曾在弟子刘棻出事时,因害怕受到牵连而从天禄阁上跳下来,差点死掉。应该说,他的一生都付与了名山事业,志希圣贤,寄望于后世的知音,所以能够淡泊名利,对自身的际遇相对释怀,正所谓『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法言》)。晚年的扬雄更是潜心于思想领域,看透了辞赋铺陈的华而不实,认为其起不到讽谏的作用,效果适得其反,将之鄙为『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之儿戏。他反感那些只懂得欣赏他的文采却接受不了他的思想的人,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和『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的中道主张。他的中道思想还体现在了『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刚则甈,柔则坏』『龙之潜亢,不获中矣。是以过中则惕,不及中则跃』『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法言》)等诸多言论之中。
《逐贫赋》是扬雄辞赋中颇能自抒胸臆的一篇。赋文通篇以四言句式为主,最大特色在于将『贫』人格化,而展开了一场不失诙谐的问答诘辩,将个人的处境际遇和道德操守巧妙地表现出来。赋文中,作者向『贫』大吐苦水,抱怨它为什么老是阴魂不散地跟着自己,以至于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日常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如意的,且饱经劳作之苦,人情淡薄,仕途更是无望,所谓『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宫凌迟』。无奈的是,作者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局面,『贫』依然如影随形,『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由此问也不难看出,扬雄何尝没有普通人的欲望?内心何尝不希望自己富贵显达呢?但为什么依然一贫如洗呢?下文借『贫』之口给出了答案。
在『贫』看来,自己紧随作者,给他带来的完全是『福禄如山』,何以故?自己的祖先原来一直陪伴在崇德尚俭的圣君如帝尧者左右,而远离末世穷奢极欲、酒池肉林的亡国之君。我能在你家,岂非你有德行的体现?那可是对你莫大的抬举,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报啊!更确切地说,好处多着呢!首先,『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从小没有娇生惯养成长在温室之中,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无畏寒暑气候变化,而得健康长寿;其次,『桀跖不顾,贪类不干』,因为你一穷二白,没有任何油水可捞,那些敲骨吸髓恣意妄为的暴君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强盗正眼都不瞧你一下,直接把你给忽略掉了,这样,你的人身安全又得到了保障;再次,『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因为身无长物,也就没有任何牵挂,不需要像富家巨室一样,费尽心思重重保护,或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没有了世俗的烦恼,你的心灵也得到了自由和解脱。有这三大利好,还不够吗?想来确实也挺有说服力的,作者最后折服表态:『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后世不少文章便受到了《逐贫赋》这种笔法的影响,唐朝韩愈的《送穷文》就是典型的一例,布局谋篇大同小异,文风亦庄亦谐。只是韩愈在文中更进一步地将穷鬼细分为五: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通过对这五鬼的描述,相当于是将自己的事行品性分五个方面予以了总结。
从深层次来看,《逐贫赋》中所体现的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命题:义利之辨。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片面的舍利取义,而是见利顾义,而不以利害义,这何尝不是中道。义与利本如阴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早在《易经》中便有『利者,义之和也』的说法。孔子的义利观便是如此,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不是一个刻意排斥功名利禄与富贵荣华的人,他在乎的是取得它们的途径和方法是否符合道义。他赞赏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安贫乐道,本意并非让人固守贫穷,而是提倡素位而行,分清义利的主次轻重,穷达如一。所谓『君子固穷』,说的是君子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在身处逆境时能够坚定自己的操守和原则,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正道和努力去追求富贵荣华。显达亨通之际,自有另外的标准和要求——『富贵不能淫』。这和孔子主张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意义是相通的。
换言之,精神建设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清人袁枚说:『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名利如工具,本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如何得到它,用它来做什么。文章并不一定非得『穷而后工』,也不一定是『憎命达』,就像贫穷酝酿出的并不必然是勤奋和节俭,也有冥顽、刁诈和堕落;而富有催生的同样也不一定是奢华和糜烂,也可以有素质、优雅和品位。影响一个人命运穷达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投胎的技术之外,还有能力、学识、道德、家庭、人脉、资本和时势等等。更何况,作文、从政、经商、学艺,本就各有其道,且各有其评判标准,岂能一概以经济价值或一身一时之穷达来衡量成败?另一方面,世人之中,通性者少,偏才者多,自己到底是哪一块料,需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和定位。清人张潮说:『才子而富贵,定从福慧双修得来。』(《幽梦影》)跨界并非不可取,前提是先具备相应的技能与素养,如果只懂咬文嚼字,其他一窍不通,却又整天奢望着加官晋爵或日进斗金,明明是偏至之才和偏执之性,不思完善,却非得怀揣一颗多欲之心,贪大求全,最终往往误入歧途乃至酿成大祸。
当然,话又说回来,古代知识分子求取功名富贵的途径很少,大抵都要依靠仕途,仕途不得志,往往也就意味着此生功名利禄如梦幻泡影。而现实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义与利往往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少知识分子也就此痛苦地活在了道义与功名的夹缝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