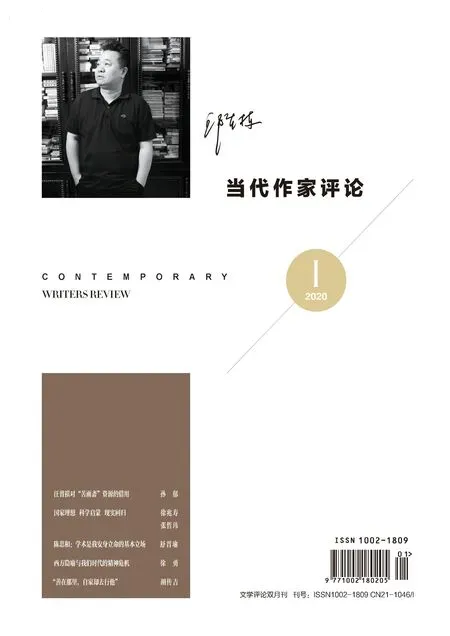“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
——论冯骥才的民间“史记”
2020-11-17胡传吉
胡传吉
冯骥才文艺皆能,是全才,也是奇才。文学之“文”,绘画之“艺”,以情为信,以美为善,以智为力:由情、美、智等因素孕育而成的文艺良知,促使这位理想主义者成长为知行合一的行动主义者。冯骥才之“记述文化五十年”〔《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搁浅》(暂未出版)《漩涡里》〕,是惊心动魄的民间“史记”,也是冯骥才历经劫难之“五十年精神的历史”。
以情为信:冯骥才的文学“列传”
司马迁“列传”之例,可喻冯骥才“文化五书”(目前为四书)的文学之道。司马迁之《史记》列传,作“伯夷列传”第一,其由在“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312页,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里面有微言大义。大时代,“无路可逃”。“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后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2)冯骥才:《自序:五十年并不遥远》,《无路可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即便“无路可逃”,但只要人在,文学就可以在,文学是跟着人走的。文学能让人在绝境中自救,能以自我烛照他人,很大程度是基于人有情感这个常识:人之成为人的最低限度是有情感。
文学“列传”,是识别自我、辨别集体中的个体之有效办法,也是借个人命运反思历史的重要途径。冯骥才的文学“列传”,始于对“自我”的认知与发现。《无路可逃》里的“墙缝里的文学”,是冯骥才的文学自述。好友刘奇膺从牛棚里放出来之后,感慨一番:“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3)冯骥才:《无路可逃》,第64、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庄严感与使命感,使冯骥才拿起了笔,“我的文学油然而生”。(4)冯骥才:《无路可逃》,第64、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但这种写作,只能秘密进行,连妻子都要隐瞒。“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别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5)冯骥才:《无路可逃》,第64、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东藏西藏的过程,加剧了恐惧感,“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6)冯骥才:《无路可逃》,第76、68、1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恐惧感如果是人的天性,那一定首先是来自死亡的威胁,死亡的威胁直接引发生理上的不适,这些恐惧感跟“自然”紧紧相连。恐惧感如果是被驯化而成,那一定跟人害怕失去尊严、自由、独立、自我、人格有关系。勇敢心与恐惧感相生相克,人类在鼓励勇敢心的同时,也不断增强恐惧感。社会制造的恐惧,常以灾难和不幸预言等恐吓方式实现。有如被宗教尊为圣者的预言家,“他们基本上都以未来的各种灾难和不幸预言吓唬人民”,“所有这些恐惧当时使人们更加害怕上帝,因为恐惧产生听话和崇拜,没有恐惧,任何一个宗教也不能存在”。(7)〔俄〕谢尔巴特赫:《恐惧感与恐惧心理》,第38页,刘文华、杨进发、徐永平译,徐永平校,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恐惧感是实实在在的:肉身无处可逃,精神备受羞辱,惩罚连带亲友,死后也不得安宁。社会制造的恐惧,远远大于“自然”条件下死亡带给个人的不幸。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公共情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看上去,基本人伦关系下的私人情感被压抑。但就常识而言,公共情感与私人情感所共用的是同一个身体,私人情感并不必然完全被公共情感所吞没,只要人还要吃饭,还能遇到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还要结婚并生育下一代,人的基本私人情感就不可能完全泯灭。身体感官被公共情感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情感也很难终身被压抑。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说,“对生活的厌倦,当它还没有达到令人沮丧的程序,当它还容许一个可喜的矛盾——对光荣的爱存在的时候,它可以启发崇高美好的情操。那时,你对一切事物都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予以考虑,一切事物都以强烈的色彩呈现在你面前”。(8)〔法〕斯塔尔夫人:《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徐继曾译,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对个人而言,恐惧心越强烈,那一点点美好的孤独与情感就越鲜明,文学让那一点点美好的孤独与情感更为明确。发自内心的强烈求生欲与尊严感,在暗地里坚定了个人对“幸运”的期待与相信。于是,在交织着恐惧感、孤独感、自由感、神圣感和崇高感的秘密写作中,冯骥才实现对“自我”的认知与发现,“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9)冯骥才:《无路可逃》,第76、68、1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当冯骥才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他回到历史去探索。70年代中后期,他着手《义和拳》(前身为《天下第一团》《刘十九》,与李定兴合作)的写作,幻想像历史小说《李自成》那样获得出版机会。但下笔之际方知道,情感的“自由”对意志的自由,并无实质的帮助,虽有“文学的良心在”,势单力薄的个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但天津这个地方,又老又新,耐看耐写,“中西精神文化在天津这里的冲突极具思辨的价值,此外还有众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以及宗教意义上的神秘色彩”。(10)冯骥才:《无路可逃》,第76、68、1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这一面向历史的文学试探,也许为冯骥才将来把情感之“爱”、以美为善之“善”、以智为力之“力”放在民间文化传统这里——在古典符号里嫁接现代元素,提供了前提。《神鞭》是摆脱“异化”、放下“伤痕”的重要转折点,冯骥才熟悉天津的“历史、地域、风物、俗规、节庆、吃穿、民艺、掌故、俚语”等,(11)冯骥才:《激流中》,第95、96、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市井的传奇、民间的段子,《聊斋》和《西游记》荒诞的笔法、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的魔幻、武侠小说和章回小说的招数,由我信手拈来”,“这样,我觉得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现代小说”,(12)冯骥才:《激流中》,第95、96、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也即“以地域性格和集体性格为素材,将意象、荒诞、黑色幽默、古典小说手法融为一体的现代的文本写作”。(13)冯骥才:《激流中》,第95、96、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神鞭》之后,文学思潮便再难将冯骥才归类。得益于天津历史上的“中外冲突”,他的写作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进退自如:当人们沉迷于形式主义时,冯骥才看到唐宋传奇、笔记体小说及《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的现代审美价值;当众生迷恋复古时,冯骥才看重现代精神对古典再生的意义;当人们怯懦失语时,冯骥才推出他的民间“史记”。不趋时、不从俗,疏离于时代,冯骥才得以保住自己的文学敏感与文学良心。
文学“列传”不仅有冯骥才之“叹曰”(自述),也有那些集体中的个人“列传”。三楼的女主人孙大娘、李家的二妈、二妈的老保姆、“我”的母亲、“我”的女友、刘奇膺、同昭的二姨、顾以佺等,还有疯狂的少年们、贪污公款的苑会计、王姓同事等,他们的故事,是太多故事中的一个。时代剧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团结里那一侧的街边失声痛哭,呜呜地哭出声来。他一定有一个痛切难言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记得我还听到鞭炮声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伤”。(14)冯骥才:《激流中》,第2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也有很多人,再也没有机会“狂喜”并“哀伤”了。情感的自由,并不必然到达意志的自由。文学的良心,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无名的人事立传。冯骥才把个体的面貌从宏大的集体中辨别出来,为民间的无名者立传。这种做法,正是以“无数偶然”以及无数的个人命运,印证时代的无情与历史的残酷。在“借调式写作”中,冯骥才遇到许多文学同路人,如严文井、李景峰、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编辑家,(15)冯骥才:《凌汛》,第9、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同时见证许多老作家的“隔世重生”。冯骥才笔下的韦君宜,尤其能让人过目不忘。背地里,人们把“君宜同志”亲热地称呼为“韦老太”“老太太”,“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录》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16)冯骥才:《凌汛》,第9、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韦君宜识才、爱才、护才,但从不谈私谊。五十五万字的《义和拳》初稿,韦君宜逐字逐句地细看,仔细修改。韦君宜担心冯骥才修改书稿被累垮,为“冯大个”特批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贴,却从未当面说起。冯骥才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引起争议,“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此后这么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17)冯骥才:《记韦君宜》,《凌汛》,第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沧海遗珠,惊鸿一现,今日不复有。还有足以改变文学方向的“四只小风筝”事件(《激流中》),也值得立传。这些往事都带有不可复制的历史荣光。光芒一闪而过,极其珍贵。没有民间“史记”,这些荣光,必将被时光湮灭。没有对历史真实的追忆与正视,沧海遗珠也就永难再现。
为文学与人立传,冯骥才的“文化五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回望历史残酷,最难抑制的是激情:因恐惧而生的激情,因受难而生的激情。由激情获取延续生命的快感,没有多少写作者能逃脱这激情的咒语。冯骥才做到了,他的“文化五书”,语言始终克制,在细节处懂得适可而止,在修辞方面化繁为简。事到史成,意及理到。不啰唆,不沉溺,不骄傲(有许多写作者视受难为骄傲的资本,进而消解施虐者的邪恶与不可饶恕),行文非常有智慧。“文化五书”的整个气派,有如辛弃疾所叹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18)辛弃疾:《丑奴儿》,《辛弃疾词集》,第96页,崔铭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语言可以去到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欲说还休”。历史恩怨,休止于古典审美趣味,这是中国式的史家笔法。
以美为善:冯骥才的绘画“自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9)王国维:《人间词话》,第5-6页,黄霖、周兴陆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文学再怎么简洁,也是要说很多话的,藏得再深,“我”还是躲不过去,语言是文学逃不脱的咒语。绘画则不然,“我”不需要借助太多的语言,就能去到“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之无我之境(元好问《颖亭留别》)。(20)王国维:《人间词话》,第6页,黄霖、周兴陆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冯骥才的绘画之路,既自然而然,又充满传奇色彩。传统中的某些技能,既能养人,也能养心,绘画便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冯骥才通过中央美院初试,但出身不好,复试被拒绝。所幸,学院不是唯一的绘画成才通道,而是勤奋加个人际遇。冯骥才与妻子顾同昭在同一个书画社工作过,他们都从事古画临摹,“她(同昭)喜欢花鸟和仕女,习画时师从天津美院的两位老画家溥佐和张其翼;我长于山水,老师是惠孝同和严六符。我俩都从宋画入手,临摹也多是绢本,在书画社里都算是高手,靠画画吃饭应该没什么问题”。(21)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从宋画入手,入门很准,起点非常高。“一般说,宋画的画面气象万千,是生活之美的集中,是一部交响乐章”。(22)傅抱石:《傅抱石谈艺录》,第8、70、73页,徐善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可惜时代发生变化,吃饭问题面临考验。但绘画,尤其是中国画,常能去到无我之境,甚至是无人之境,这是由其技法所决定的。“中国绘画是从笔墨为基础的”,“反映在具体的表现技法上,就形成了没骨、重彩、淡彩、白描——从色彩到水墨、从纯争到无色、从多色到单色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23)傅抱石:《傅抱石谈艺录》,第8、70、73页,徐善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我个人还有一个偏见的看法,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永远都是阔大的”(傅抱石)。(24)傅抱石:《傅抱石谈艺录》,第8、70、73页,徐善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没骨、重彩、淡彩、白描等表现形式,可在“写生”“写意”“写真”(25)“中国绘画以写实为基础,针对不同的主题内容提出了不同的基本要求。对于花卉、翎毛的要求是‘写生’;对于山水的要求是‘写意’;对于人物的要求是‘写真’(传神)”,见傅抱石:《傅抱石谈艺录》,第69-70页,徐善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之间来去自如,有我、无我、有人、无人,不同境界,可回旋的余地很大。谋生困难,“触发我的自救之谋的还是红袖章”,书画社改行为线印作坊,“专印袖章和各种旗帜”。(26)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热闹散去之后,丝印版画成为新的活路,生活中总是需要画的,“太阳、葵花、海浪”这些图案,放在任何版画上,都合宜。以技法为生,以画工为业(放下文人身份,回归手艺人身份),“我”与“人”,接近于“无”。1972年以后,被冻结的书画社“老业务”有了缓解,书画社接了外贸工艺品公司的画鸭蛋(彩蛋)业务,“我们以前没有画过鸭蛋,蛋壳不容易画,如同画瓷器,不是画在平面上,是画在圆圆的凹面上,必须悬笔立腕,笔锋随着弧面转动。我们书画社确实有些能人,很快就把这技能掌握了,所画鸭蛋十分精美”。(27)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为说明画彩蛋不是“四旧”,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冯骥才向主事者解释说,“只是些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婴戏图上的人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小孩”,(28)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这才过关。由此,书画社的人们,得以重拾笔墨丹青。手艺与绘画,历经波折,殊途同归,最终还是得在“美”这里寻求答案。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29)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也许是天性所致,也许是精神所求,冯骥才的“唯美主义”一直都在。书社画的手艺,对应的是生计。家里画的“伤感的水墨”,对应的是绘画的本质,“尽管我的画仅仅属于个人,但它从属于一己和自由的心灵”。(30)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70年代,冯骥才的画风发生改变,“我走过的道路就像由宋到元的中国绘画,从原先画师们的写实与具象,改变为文人一己的抒情与写意”。(31)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绘画是另一种“语言”,甚至可以说是比文学更困难更难习得的“语言”。冯骥才以宋画入门,基础好,对线条的把握极有悟性,由写实与具象转抒情写意,不算困难。60年代至70年代,他的一些居家生活系列速写,如“新房”速写,画出简陋之“美”:干净整洁,有生活的味道,这大概是在“简陋”生活里,人能自守的仅有的美。冯骥才的《北山双鸟图》(老夫老妻系列之一),(32)冯骥才:《无路可逃》,第45、47、149、151、138、1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线条密集,风格粗粝沉郁,画家借风雪巧妙处理光影、留白存虚,双鸟相依为命,有乱中求生之感。树法乃山水画最基本的手法之一,此图最出彩的是树法,立干不算新奇,但其穿枝手法果断而大胆,点叶有时密集,有时疏淡,双鸟附近略有生气,离双鸟稍远处密集(沮丧),立干、穿枝、点叶、双鸟之分布,繁复的景,衬托出深厚的“情”。冯骥才的文人画,画风多变,能于简繁之间,变化自如。不少画家,能至简,但难至繁(繁意味着要处理更复杂的空间、更多的线条等,对技法及时间的要求更高),冯骥才是两者皆可。能有此境,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对古画的临摹。冯骥才曾花一年多的时间,为温斯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一笔不苟地临摹了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图》的全卷”,(33)冯骥才:《无路可逃》,第1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工程之巨,耗时之长,令人震撼。原作艺术价值之高,无须赘述。临摹者之临摹,在结构及技法方面所得益处,不可尽书。山水草木,房屋楼阁,人物,动物,各种生活场景,可谓应有尽有,能一笔不苟地临摹出来,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个临摹者,到自己创作时,在技法上,能去到随心所欲之境。精细处丝毫不为难,大格局不会走偏,这是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好处。文学语言去不到的地方,文人画里的抒情写意也许可以去到。这个文明的语言文字在原创之初,线条的哲学“设计”过于严密——如以线条指向卦象,实为极其严密的哲学“设计”,文字借线条建构的秩序,有边界,有设限。有时候,想要“说”出语言文字秩序以外的内容,还是得靠“画”来“说”,毕竟,画先在于文,它有文不可替代的“指事”“会意”“象形”功能。能兼得文学与绘画之美,只能说,历史大势中,有个人的小幸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倾向,‘美’和‘善’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充实之为美’是指得到了一种高尚享受的精神境界”(汤一介)。(34)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冯骥才之以情为信与以美为善的境界,正是借助文学与艺术的“情景合一”来实现的。
知行合一:行动的知识分子
“情景合一”,以情为信,以美为善,可以修自我之身,是属于“知”的范畴。冯骥才借助文艺,先去到“知”情、“知”美的境界。“至于‘善’,虽然各个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看法不同,所立的标准各异,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大都认为‘知’和‘行’必须是统一的,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善’”,(35)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朱熹之所以重‘行’,则是因为他把‘知’与‘行’问题从根本上视为道德修养问题,所以他说:‘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36)《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之“力行”,参见《朱子语类》彙校一,第238页,黄士毅编,徐时仪、杨艳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善在那里’是‘知’的问题,‘自家却去行他’是‘行’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必得‘知行合一’,才可以体现至善之道德”(37)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汤一介)。
在道德实践层面,“知行合一”,是通往“至善”的办法。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正是“知行合一”的体现。领悟过情感与美感的人,必有不忍之心:不忍情与美毁于一旦,不忍“力”对“古旧”进行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改造”。“改造”是20世纪以来的重要历史关键词,譬如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等。90年代以来,另一种“改造”汹涌而至,“任何过往的历史事物都有可能被丢弃和废除的可能”。(38)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全因那“情景合一”(情与美)而成的“不忍之心”(善),冯骥才开始其文化遗产保护之路(知行合一)。“卖画救文化”是冯骥才走上文化遗产保护之路的重要“第一步”(39)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90年代初,冯骥才在上海办画展之际,到周庄一游,得知“迷楼”(曾是“南社”成员茶聚议事之所)可能不保,冯骥才决定卖画保楼,房主连连涨价,后来周庄的管理人员传话说,“你们一个劲儿非要买,已经把房主闹明白了,他知道这房子将来可能会值大钱,不卖了,也不拆了”,(40)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迷楼”保住了。冯骥才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可以“卖画救文化”。(41)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之后,冯骥才卖出许多精品,全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宁波画展中,“在画展最后边也是画幅最大的那部分挑选了五幅,都是六尺对开的山水,全是我的精品”,又将“余下的画交给宁波市政府全部卖掉”,(42)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宁波的贺秘监祠得以保存。之后的文化遗产保护路上,冯骥才被迫卖画救文化的事情还很多。比如,为成立基金会筹款,冯骥才拼命画画,“我不能太自我,必须回到这次创作的缘起与原点——民间文化在向我们紧急吃救。这时,我感到这次卖画有如卖血”,(43)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在南京公益画展卖掉自己的力作《心中十二月》,“这些心爱的画全卖了,一时我有家徒四壁之感”。(44)冯骥才:《漩涡里》,第15、19、1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但一个人靠卖画怎么救得了文化遗产,说来说去,这只不过是以精卫填海之精神,来推动有识之士、志愿者及政府力量一起参与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这个工程极其浩大,单靠个人之力不可能有持久的成效。由抢救历史遗址开始,冯骥才与同道者倡办杨柳青年画节,以民间年画节的方式办文化艺术节,展示地方民俗、民艺、工艺、戏剧与曲艺等城市传统文化。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中,关于老城的“坏消息”接连而来,老城说没就没了。冯骥才与志同道合者,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收集专家意见,编撰老城影像集,把意见转呈给城市的决策者,推动城市老城博物馆的建设等。慢慢地,“我已经不知不觉从甜蜜的自我中走了出来,一步步走向一个时代的巨大的黑洞般的漩涡”。(45)冯骥才:《漩涡里》,第73-74、113、21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在这个过程中,有成效,亦有失败,有欢欣鼓舞的时刻,更有孤立无援、绝望无助的时刻,“历史不断表明,文明常常被野蛮打垮”。(46)冯骥才:《漩涡里》,第73-74、113、21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到了后来,冯骥才更自觉地从国际视野及科学应对方法来反思文化遗产保护的可延续性,他在“建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古村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人保护等方面”有持续的思考,(47)冯骥才:《漩涡里》,第73-74、113、21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并尽可能地付诸实施。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功德无量。冯骥才之事功,不可尽书。
冯骥才把他的文学、绘画及文化遗产抢救事业,归之于情怀。“作家的情怀是对事情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我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学者式的,首先是作家的”。(48)冯骥才:《漩涡里》,第73-74、113、21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这个情怀,是感性的,也是美学的,“美学以至美感要解决的正是把人的感官从生物性升华为社会性,升华为优秀人性”。(49)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第28-29、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由情与美塑造而成的“不忍之心”与“优秀人性”,也许挡不住时代浪潮的各种冲击,但知行合一是通往至善的“德”(也可视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合一),“人生艰难,又不仰仗上帝,只好自强不息,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天行健,人也行健,这种依靠自身的肩膀、承认悲乐全在于我的本体精神,才是强颜欢笑和最为深刻的悲剧”。(50)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第28-29、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冯骥才的文化五书,有游于文艺的自由“至乐”,更有中国士人的深刻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