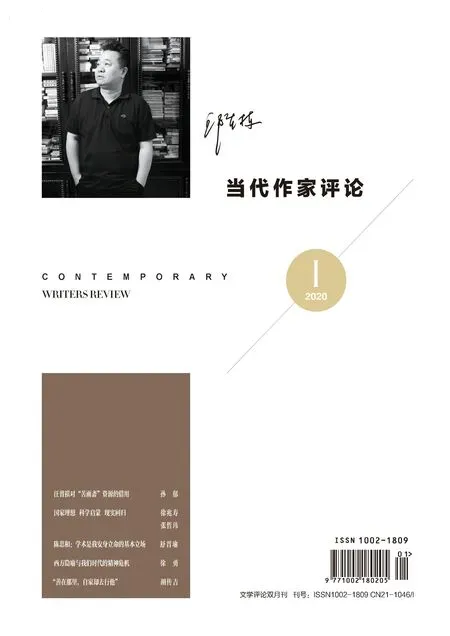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子关系探析
2020-11-17宋雯
宋 雯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很多进步观念传入中国,封建文化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被奋力推倒的对象。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都看到了封建家族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根基,在反父权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长期活动在狭小家庭空间的母亲们,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她们很多以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出现,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通过书写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作家达到了批判封建文化的目的。此外,歌颂母爱和书写母女关系的作品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出现,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十七年”时期的母亲形象塑造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很深,政治伦理凌驾于家庭伦理之上,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母亲要么是大公无私,坚决拥护革命的“革命母亲”,要么思想落后,和积极进步的子女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十七年”文学中还常出现一种精神血缘意义上的母亲,她和她的“子女”没有血缘关系,是革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如《长长的流水》中的李云风,本是一个跟小战士素不相识的革命干部,可她对小战士的爱护和关心使得她更像一个慈母。在“十七年”时期,阶级论理强化,家庭伦理弱化,国家号召人们走出家庭干革命,为了增强凝聚力,顺应人们心中的家族情感,突出革命大家庭的温馨,这种精神血缘上的慈母爱子的构建显得极为必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中的“母亲”。以往文学中常出现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及无私坚韧的圣母式母亲有个共同点,即她们都是“像母亲的母亲”,而先锋文学中的“母亲”却突破了我们的底线,让我们觉得她们根本都不像一个母亲,如在残雪的很多作品中,母亲的行为举止都显得变态而疯狂,她们和《金锁记》的曹七巧不一样,曹七巧的心理扭曲是有原因的,她自己本身也是封建制度和炎凉世态的受害者,而残雪并未直接在小说中交代母亲变态和疯狂的原因,梦呓式的叙述语言也使得这些母亲更加脱离日常,这种异乎寻常的恶母形象与盛行于80年代的西方非理性哲学思潮、现代派文学与作家当时对于精神真实的叙事追求有着密切关系,极大颠覆了母亲无私、温柔及作为精神家园的叙事能指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都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型,此时中国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褪去“圣母”光环的平凡母亲
与以前的文学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卸下了“人民伦理大叙事”的负担,母亲作为受害者、弱者及精神家园的叙事能指意义减弱,因此这个时期的“母亲”,开始真正回归到平凡和日常中。《太阳出世》(池莉)中赵胜天和李小兰的母亲一个是小市民,一个是离休干部,可是她们都不具备为儿女无私付出的传统母亲的品质。赵胜天的母亲举止粗俗,不愿牺牲自己打麻将的时间去带孙子,李小兰的母亲虽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女儿却较冷漠,见到孙子也只是礼貌性的问候,不愿做实际的付出。《太阳出世》是以当下为时代背景的,在这个经历着剧烈转型的时代,人们的家庭伦理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十分关注现实的新写实主义作家,池莉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点。《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母亲对王琦瑶也是淡漠的,王琦瑶给李主任做情妇,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认为王琦瑶对康明逊的感情是“自作自贱”,她在乎的不是女儿是否幸福,更多的是自己从中可以得到什么。这种淡漠的母子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伦理观念的变迁,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家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思考。在父权社会中,母亲是无私奉献的象征,“慈母”是父权社会对母亲的期待,父权文化认为,母亲是天生爱孩子的,她们为了孩子会呕心沥血,甘愿奉献自己的所有,而《太阳出世》中赵胜天和李小兰的母亲以及《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母亲无疑是对父权社会价值理念的一种背离和挑战。
从《苦菜花》的仁义嫂到80年代《麦秸垛》的大芝娘再到90年代《你是一条河》的辣辣、《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这是中国小说中的“底层母亲”书写谱系,她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在艰难困窘的日子里咬牙为子女撑开了一片天。与90年代小说中的底层母亲相比,之前文学中的底层母亲更具备“圣母”的特征,她们的胸怀像大地一样宽广,母爱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如《苦菜花》中的仁义嫂不仅仅是娟子等亲生子女的母亲,还是所有革命战士的母亲;《麦秸垛》中的大芝娘不仅是大芝的母亲,还是杨青等苦孩子的母亲。这样的母爱就不是狭隘的人伦亲情,而闪耀着更为宽广博大的人道主义光芒。她们让我们想起神话中奉献自己造福全人类的女娲,想起浑身闪耀着神性的圣母。90年代的作家们则把圣母式的底层母亲从天上拉入凡间,拉入热气腾腾、泥沙俱下的日常生活中。《你是一条河》中,辣辣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的突然去世,对于这样一个子女众多的贫穷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在短暂的悲痛过后,辣辣及时调整了情绪,调动了自己的所有智慧和力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存。但是比起《苦菜花》中的仁义嫂和《麦秸垛》中的大芝娘,辣辣身上有着太多的缺点,她粗俗、泼辣、对孩子照顾不周,孩子头上长虱子了她不管,和女儿吵架时脏话连篇。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也有着众多子女,这个生活在农村底层的女性深受男权文化迫害,其实《苦菜花》中的仁义嫂也是封建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只是那个时代的性别压迫被政治伦理和此消彼长的阶级斗争掩盖了过去,而上官鲁氏的苦难却主要与男权文化和性别压迫相关,虽然《丰乳肥臀》的跨度长达百年,期间发生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苦菜花》中的仁义嫂一心为公,深明大义,为了革命事业甘愿牺牲子女,并把母爱扩散到所有革命战士身上,上官鲁氏却是自私的,她只爱自己的子女,要是有来自外来的威胁,无论对错,她首先想到的是像母兽一样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无论借种、偷粮还是打死婆婆,都是为了让孩子好好活下去。由此可见,在90年代小说中,同为坚韧顽强任劳任怨的底层母亲,她们身上却失去了以往底层母亲身上的神性光环。如果说,以前小说中的底层母亲像圣母一样无私、博爱,她们则像森林中的母兽,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和本能去保护和养育着自己的孩子,比起圣母,她们不够完美,但这样的母亲显得更加有血有肉,贴近现实。它也“展示了‘母亲的神话’或关于母亲的话语本身便是一种男性社会的虚构与压抑性力量”。(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3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二、“女儿型”母亲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还有一类母亲是以往文学中较为少见的,她们既不像代行父权的母亲那样专制,又不像“圣母”那样富有牺牲精神,也并不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面貌出现,她们在子女的眼中,像朋友,有时更像一个需要被人保护的女儿,她们身上的“女儿性”大大压过了“母性”。我把这类母亲称为“女儿型”母亲。这些“女儿型”母亲颠覆了人们对母亲的传统认知,她们与子女的关系也在无形中僭越了传统的家庭等级秩序,体现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
《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幼年时父母离异,她很小就随母亲搬到尼姑庵的一间小屋里生活,母亲开明大方,没有重男轻女的习气,虽是单亲家庭,但她并不像很多母亲那样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代行父权”,充当一个严厉的父亲式母亲,而是充分尊重肖濛的意见和想法,和肖濛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肖濛在小说中深情地说:“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温情最有知识的女人,也是最不幸的女人。”这不仅体现了肖濛对母亲的同情,也体现了肖濛对母亲的欣赏。这种民主平等的朋友式母女关系在顾艳的《精神病患者》中也得到了很好体现,在这篇小说中,“我”和母亲沈氏都是个性独立的女知识分子,母女关系中常见的代沟问题并不存在,作为叙事者的“我”的叙述口吻是轻松自在的,甚至有点油腔滑调的感觉,“我”对母亲说话也是没大没小的。朋友式的母女关系体现了作家的理想及伦理观念的变迁,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那种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慈母是最符合人们想象和期待的,而在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全面觉醒的90年代,这种民主平等的朋友式母子关系才是人们最渴望的状态。
比起《与往事干杯》和《精神病患者》中的“母亲”,《伴你到黎明》(张欣)中安妮的母亲身上的“女儿性”更加明显,她是个过了气的演员,一直活在过往的辉煌里,有一种不通人情世故的天真。早年时丈夫突然提出的离婚让她不知所措,还要请幼小的女儿帮忙拿主意。在女儿眼里,软弱且天真的母亲好像永远长不大,不但不能给女儿避风挡雨,反而还需要女儿的呵护。这使得安妮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有主见的姑娘,母女关系似乎颠倒了过来,安妮的母亲虽年事已高,却依然把女儿当成撒娇和依恋的对象。安妮则习惯像哄小孩那样哄着母亲。《大浴女》(铁凝)中的章妩也是一位“女儿型”母亲,她似乎天生就缺乏“母性”,女儿什么时候换牙,她不知道;女儿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的,她不关心;女儿在学校里受了欺负,她也不清楚,她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自己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想着开病假条休息,比起在家照顾女儿,她也更乐意和刚认识不久的唐医生在外面谈情说爱。母爱的过早缺席使得章妩的大女儿尹小跳早早成熟,她很早就学会打理家里的一切,并主动担起照顾妹妹尹小帆的任务,与母亲相比,妹妹小帆明显更依恋姐姐,因为姐姐比母亲更像一个母亲。《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做了母亲之后,也是“女儿性”远远大过“母性”的,她依旧爱表现自己,喜欢在聚光灯下被万人瞩目的感觉。在女儿成年需要参加社交的时候,她并不费心于帮女儿打扮,而是把重心放在如何与女儿斗艳上。薇薇的男朋友到楼下找薇薇,王琦瑶却将他邀请到楼上热烈交谈,引得薇薇嫉妒说“你和我妈倒有话说”,王琦瑶的行为和表现无非是在对他们宣布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地只需要表面尊重的丈母娘,她是一个可以交谈可以推心置腹的女性朋友,她在尽力争取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她的不甘老去,和女儿斗艳的行为,正是“女儿性”的体现。
三、爱的牢狱与“狱卒”一样的母亲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是最高统治者,当他们缺席或去世,代替他行使父权的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是与父亲同辈分的母亲。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上主下从”是排在“男尊女卑”之前的,作为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功臣,母亲拥有了统治子辈的权力,她们对子女的婚姻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对此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子,如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常见到的一个叙事模式也是母亲阻挠主人公的自由恋爱,在“情人之爱”和“母亲之爱”不能兼得的矛盾冲突中,主人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得到保障,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过渡到工业社会,很多女人从单纯的母亲角色转变为身兼母亲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责任,谌容的《人到中年》就展示了优秀医生陆文婷在做了母亲之后的种种忙碌和艰辛。但是,职业的获得也意味着经济的独立,经济的独立使得女性有了不依附他人生存的底气,这在无形中也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与现代文学中较为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不同,90年代小说中的很多夫妻都有着自己的职业,妻子不用再依靠丈夫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夫妻的关系也就更加趋向平等,妻子的话语权也就大大提高,甚至可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如《一去永不回》中,家庭的“统治者”就是母亲张怀雅,连父亲也是对她言听计从的,她自诩为知识分子家庭,认为比普通小市民要高人一等,因此她对女儿温泉管束严格,一心想把温泉培养成一个标准的文雅淑女,在她眼中,温泉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合乎规范。在家里,温泉没有任何的话语权,18岁了还“只能穿妈妈做的棉绸连衣裙,还不许戴花边海绵乳罩”。母亲对温泉的关心和监控达到了病态的地步,看到温泉神情恍惚,首先想到的就是跟踪女儿和偷偷观察女儿月经周期。牢狱一样的家和狱卒一样的母亲让温泉窒息,她想出去找份工作尽快独立起来,可母亲嫌当工人丢人,最后软硬兼施,以死相逼,终于如愿以偿提前办了退休让女儿顶了自己在医院的班。温泉就像个母亲手中的提线木偶,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识,必须按照母亲的规划来过自己的人生。对母亲的控制极度不满的温泉在默默储备好反抗的力量之后终于爆发了,她不顾母亲的强硬阻拦和反对,想尽一切办法嫁给了母亲看不上的一个男人,头也不回地从家走了出去,温泉对母亲的反抗,对这个牢狱一样的家的逃离,也是她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一去永不回”的小说名显示出了女儿对牢狱一样的家的极度厌恶和逃离母亲控制的坚定和决绝。
整体来说,温泉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狱卒一样的母亲身边逃离了出去,但是还有很多没能成功逃离的人,他们在母亲的统治和监管下逐渐麻木,徐小斌的《若木》中的母女关系就是如此,玄溟本是个精明能干的富家小姐,在嫁人之后依旧不改她强势的脾性,和丈夫吵架一定要占上风,对女儿的控制就更别说了。在母亲的威严和强势作风之下,若木从小就习惯了沉默,在青春期和邻居男孩的恋情被母亲撞破之后,面对歇斯底里的母亲和被关进黑屋面壁思过的惩罚,她唯一能想到的对抗方式就是不吃不喝,以惩罚自己达到惩罚母亲的目的,可这一切并没换来玄溟对自己的反思。丈夫早已厌倦她的强势宁愿成天在外和温柔体贴的戏子混在一起,若木就成了玄溟最重要的控制对象,玄溟严禁女儿与异性朋友交往,这使得女儿29岁还待字闺中。若木走出家门外出上学也没能逃脱母亲寸步不离的监视,因为玄溟会每天跟着若木来教室上课。若木的婚姻,也是玄溟通过种种手段促成的。女儿在母亲的一路操纵下已变得麻木,如果说《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还一直拥有着独立的人格和反抗的力量,为了外面自由的新鲜空气不惜竭尽全力冲破牢笼,若木却早已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和力量,她的灵魂逐渐枯萎麻木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她的一生。她对子女也是非常地淡漠:“无论女儿结婚还是离婚,若木都一概不管。陆尘早已辞世,外孙女倒是一大堆,但一律激不起若木的任何热情,若木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叫不全。”弗洛姆在谈到“自恋的女人,专横跋扈的女人,只想占有的女人”这几种类型的母亲时说,她们在孩子已经到了需要脱离开对母亲的依赖而走出婴幼儿期的分离阶段,没有起到自己的责任,而继续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的手段。(2)〔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43页,刘福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这些母亲可能以为她们对子女狱卒一样的监视和控制是爱的表现,殊不知这只是她们用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代替子女的认识,她们根本没有把子女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完全忽视了子女在走向成熟时所应该建立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建立必须是由子女们自己来完成的。在她们的意识里,子女对自己的服从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母亲天然的权力,她们享受着控制子女带来的权力感,在这样的母亲管教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迫使子女失去“自我”的同时她们自己是否也失去了“自我”呢?小说家们对此进行了反思,质疑了只强调单方面“上主下从”的“孝”文化观念。
陈染的《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也把“帝王般森严”的母爱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中黛二的母亲面容姣好,优雅高贵,是一名“出色的寡妇”,她和女儿一起居住,并时刻像侦探一样监视着女儿。她会从家里啤酒瓶子空掉的数量推测出女儿今天又领男友上门,从烟蒂上的口红印推断出家里又来了抽烟的女友,她反对女儿和外界接触,把女儿当成自己的私有物品。叙述者将母女居住的房子比喻成一个城堡:“这城堡被我和母亲日积月累的相依为命,一笔一笔涂染成晃眼的黄色,像运动场上裁判员的黄牌警告,贴近城堡走近我的犯规者,必定要罚出‘场外’。”如果说,《一去永不回》和《若木》等作品着重凸显了母亲对子女的控制欲和统治欲的话,《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则突出了母亲对女儿病态的占有欲,里面充斥着母亲对女儿进行偷窥和监视的场景:“岑寂中电话铃哗然而响,蹿跳的风拔地而起,耳鼓震颤,我心一惊,抓起话筒。这时,门缝外便会有轻微的脚步声贴近我的门扇,嘘嘘的气息声渗透过来,母亲的影子便浮在我封严的帘窗上。”母亲还生怕失去黛二的爱,哪怕居住在一起,她也会时不时把黛二叫到自己跟前,向黛二哭诉独自抚养孩子的不易,不断让女儿对自己负疚,表面看上去,黛二的母亲没有《若木》中的“玄溟”以及《一去永不回》中的“张怀雅”那样严厉和强势,可是这种控制子女的手段显得更加高明,因为一味说教和管制只会带来不满和反抗,而示弱和展示可怜则会激起子女心底的负疚感,负疚感让子女觉得不安,因此他们也就自觉放弃了对母亲的反抗。黛二对母亲是既爱又怨的:“她是我亲爱的母亲,是把我身体里每一根对外界充满欲望的热烈的神经割断的剪刀,是把我浑身上下每一个毛细孔所想发出的叫喊保护得无一丝裂缝的囚衣。母亲,是我永恒的负疚情结。多么害怕有一天,我的母亲用死来让我负疚而死。”戴锦华曾分析过黛二母亲对黛二病态的占有欲:“一边是血缘、性别、命运间的深刻认同,一边是因性别命运的不公欲绝望而拒绝认同的张力……制造痛苦的不光是下意识的对父子秩序的仿同:权力、控制、代沟与反抗;而且更多的,是不再‘归属’于男人的女性深刻的自疑与自危感的盲目转移。无法为自己独自生存建立合‘法’性与安全感的女人,其生命压力的出口,便可能富于侵犯性与危险的爱”。(3)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四、“恶母”书写——对“母性神话”的极端颠覆
上面提到的粗俗泼辣的母亲,冷漠型母亲,狱卒式母亲都颠覆了人们对慈母的想象和期待,她们把笼罩在母亲头上的圣母光环摘了下来,让我们看到了有着各种各样人性缺点的母亲,但要论对“母性神话”的极端颠覆,还得数“恶母”,因为“恶母”身上的邪恶和性格缺陷已超出了人们的底线,会让人们觉得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母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位恶母,她教会儿子吸大烟,让儿子染上毒瘾,并在准女婿面前说自己女儿的坏话,搅黄了女儿的婚事。“曹七巧”的邪恶来自于心灵的扭曲,作家叙述了她心灵一步步扭曲和异化的过程,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对人欲的极端压抑。由于“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控制加强,曹七巧式的“恶母”在文学中几乎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见到的除了大公无私的革命母亲,就是作为积极进步的子女的对立面和反衬对象的思想落后的母亲,带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痕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环境逐步宽松和西方思潮大量的涌入,我们才在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文学中重新发现了“恶母”的踪迹,如《种在走廊里的苹果树》(残雪)中的母亲有被害妄想症,她声称能看穿任何人的诡计,说话却颠三倒四,她先是抱怨她睡在箱子里,她的儿子踩到她的眼珠上,她为此痛苦不堪,接着她又声称整个故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在《污水上的肥皂泡》(残雪)中,母亲是个“铁一般的女人”,她不断地喊叫、自寻烦恼,抱怨儿子虐待她的“阴谋”。这些“母亲”都十分神经质,变态,疯狂,形象也十分阴森可怖的,变态程度不在曹七巧之下,但是我们会觉得曹七巧这个人物更真实一些,因为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耐心描绘了曹七巧在封建制度和男权文化的压迫下,从一个正常的小门小户姑娘变成豪门怨妇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心灵不断被异化的过程,嫁给了一个残疾人、因低贱出身被夫家鄙视以及被迫压迫自己的情欲等悲惨经历为曹七巧后来对子女的变态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这使得我们在审视曹七巧的时候多了几分同情,因为造成她心灵扭曲的原因是清晰的,而残雪小说中的这些母亲好像和现实日常隔得有些远,她们从一出场就是神经质和变态的,叙述者并未说明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这样的“恶母”,而叙述者本人也是神经质的,这就使得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虚幻且荒诞,有种寓言的意味,让人想起“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命题,难怪不少评论者用“梦魇”形容残雪的小说。
比起残雪80年代小说中那些“恶母”,90年代小说中的“恶母”更接近于“曹七巧”一些,因为这些“恶母”重新回到现实日常,作家不仅写了她们的“恶”,还写了她们是如何变“恶”,如何被扭曲的,如铁凝《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她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可是封建社会奉行的包办婚姻将她推给了一个她不爱也不爱她的男人,在夫家,司猗纹受尽了丈夫的虐待,不服输的性格使她最终奋起反抗,甚至还主动走到公公的卧室挑衅公公,试图以乱伦的方式来报复夫家,比起曹七巧,她似乎更加充满生命力和斗志,她对权力充满着渴望,不但在家里要做说一不二的统治者,还一直野心勃勃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各种政治运动袭来的时候,她都积极配合,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亲妹妹,她的强势使得自己的儿子软弱无能。面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儿媳竹西,她则使出种种卑劣的手段想方设法地惩治,其中包括唆使年纪幼小不谙世事的外孙女苏眉去捉奸。司猗纹对苏眉的监控也是非常严苛的,随着苏眉和自己越长越像,司猗纹拼命想把她打造成另一个自己,致使苏眉后来对生育产生厌恶和恐惧,想通过绝育来希冀这样一种虚妄历史的终结。《你一直对温柔妥协》(虹影)中小小的母亲也是一个心灵扭曲的母亲,她不顾儿子的学业和前途,利用丈夫去世儿子回来奔丧的机会,故意卧床不起,整日使唤和折磨着儿子。小小的母亲的变态是有缘由的,她本是一个读过一些书的文静淑女,和丈夫也是因为爱情才走到一起,可是丈夫的出轨让她从淑女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泼妇,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弄得家里鸡犬不宁,小小母亲的性格是刚烈且偏执的,她始终不肯原谅丈夫的错误,宁愿自慰也不愿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她对小小的折磨带着美狄亚复仇的意味,因为小小长相酷似父亲,折磨小小也意味着对丈夫的继续折磨。《天籁》(张欣)中的母亲更叫人难以置信,她本有个长相甜美,嗓音若天籁的女儿,她自己以前也是个有名的歌唱家,因为意外倒了嗓子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的生活本是宁静温馨的,可女儿的天籁嗓音带来的知名度和巨大利益激发出了她的贪欲,她一方面希望女儿替自己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一方面试图利用女儿的天籁嗓音攫取更大利益,在女儿一次因好奇和贪玩错过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后,她竟然狠心把女儿眼睛弄瞎,以让她能心无旁骛地唱歌。女儿对于她来说,仿佛只是一件工具,如此残忍的母亲让人不寒而栗。
在父权社会中,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因为父权社会中的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传宗接代和照顾家庭的工具,女人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女性作为人女、人妻、人母,虽则拥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然则那种依傍于父亲或丈夫的名姓,隐匿在一个庞大家谱当中的角落里,看似有名,实则处于‘无名’状态,其实是一部男权的文明史使然。在一个强大的阳刚菲勒斯审美机制的垄断之中,母性的历史无从展现。在母亲形象的书写中,除了一个源自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地母’原型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余者多是统一于男人视阈之下、两性关系中作为男人之对象化关系而存在的女性。”(4)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第21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随着女性主义的传播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些女作家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建构母系家族谱系,建构属于女性的历史,我们常常会在其中发现“恶母”的踪影。如徐小斌的《羽蛇》以百余年的时间跨度演绎了母系谱系中几代女人的故事,其中重点凸显的是若木和女儿陆羽的关系。若木就是一个不像“母亲”的“恶母”。陆羽是若木的第三个女儿,若木从陆羽出生起就不喜欢她,因为若木虽上过大学,却深受封建思想影响,觉得生个男孩人生才完美,这个无辜的三女儿成了她迁怒的对象。陆羽是个有着很高天分的敏感女孩,她从小就敏锐感知到母亲并不喜欢她,为此她做出种种努力,可她始终得不到母亲的认可和喜爱。在陆羽的弟弟出生后,若木在欣喜的同时对陆羽更加厌恶了,认为这个晦气的古怪女儿会伤害自己的宝贝儿子,孤独沉默的陆羽身上的恶终于被母亲持久的冷漠和憎恶激发了出来,她掐死了自己的弟弟,从此走上了和母亲势不两立的不归路,缺失的母爱和杀死弟弟的负疚感影响了陆羽的一生,使得陆羽一生都没有真正地快乐过。跟《若木》中的“若木”相比,陆羽无疑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五四小说中也有很多富有反抗精神的逆子和逆女,但是他们对长辈的反叛多指向了长辈指涉的陈旧落后的伦理文化,而陆羽的反叛完全是出于对母亲厌恶自己的报复,她对于母亲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使得她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作者在这里也给我们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那就是母亲不一定爱自己的子女的,所谓女人天生就具有母爱,天生就热爱自己的孩子不过是男权社会为了巩固男性的统治地位编织出的“母性神话”。罗素在《婚姻革命》里就曾说:“母性的情感长期以来一直为男人所控制,因为男人下意识地感到对母性情感的控制是他们统治女人的手段”。(5)〔英〕罗素:《婚姻革命》,第141页,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曾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6)〔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第574页,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学领域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报告,说明人们的确有憎恶子女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母亲”书写较之以往,显得更加丰富和多元,20世纪以来的“理想之母”书写传统得到了接续,不像“母亲”的“恶母”书写在中断多年后也在90年代小说中得到了承续和发展,此外,我们还能在很多90年代小说中看到很多狱卒式母亲,褪去圣母光环、有着种种缺点的平凡母亲,女儿型母亲,她们都是以往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这体现了伦理观念的变迁以及作家对母亲角色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母爱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中是个颇有疑问的词。当我们对男权文化进行深入清算后,发现男权文化仅仅把女性当作传宗接代和泄欲的工具,总是强调母性天职来压抑女性自我多方面的生命欲求。在男权文化背景中,女性内心中过强的母性情结,往往使得女性成为自我母性的异化物。它可能反过来否定女性生命,使女性重新沦为男权文化中的女奴”。(7)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第1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0世纪90年代作家笔下这些各式各样的不甚完美的母亲形象,质疑了传统的母性角色规范,颠覆了一直存在于男权文化中的“母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