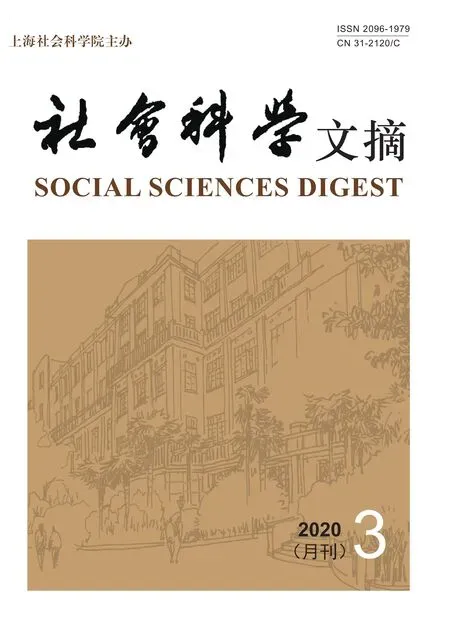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2020-11-17
晚清时期,推行来自西方的阳历成为政治改革的诉求之一,但未及改历,清王朝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宣布使用阳历。在民国初期阳历的宣传与推行过程中,面对民众习于旧历的社会心态与风俗习惯,趋新人士及政府一方面通过具体措施来扩大阳历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改换历法名称,以彰显新历法“革新”的意义,由此使得历法名称发生了巨大变化。
夷洋转换:从“西洋历”到“太阳历”
中国传统历法是兼顾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的阴阳合历,而自明末以后传入中国的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都是参考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的阳历。明末清初之际,以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迎合历法改革的需求,将当时西方天文学最新的成果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历法发展做出了贡献。1645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进呈,得到清廷重用,并以顺治帝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刊行天下,此后钦天监依此编订的历书封面都题有“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字样。不过,由于传教士制作的“西洋新历”带有西方背景和宗教目的,引发了维护儒学地位者的强烈反对,强化了时人对中西历法的区分意识。其中,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更是将中西历法置于对立的境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在夷夏之辨的思想背景之下,时人对世界的认识框架仍是以华夏为核心,遵循了文化从内向外、由高到低的层级秩序。所以当西方历算某些方面超越了中国历法时,夷夏之辨所形成的层级秩序就受到了挑战。而通过“西学中源”的论说,认定西洋历法不过是华夏世界“礼失于野”的结果,就解决了“夏不如夷”的理论困境。晚清时人则将道器分离,提出即便技艺不如西洋,但西洋先进的观测技艺却说明了“圣人之道”的正确。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历法在宣示正朔、构建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加之夷夏之辨的思想氛围,时人试图将“西洋历”的作用限于技艺层面,以维护华夏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也反映了人们不得不用而又心存排斥的复杂心态。
鸦片战争之后,“夷夏之辨”的世界认知框架逐渐走向崩溃,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趋新崇洋成为社会思潮,这就使得时人对西洋历法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趋新之士,已经能较为准确地看待中西历法的差异,对西洋历的优点亦能肯定。在这一转变中,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随着对西洋历法的了解日深,晚清时人开始从历法使用“普遍性”的角度来述论使用西洋历法的积极意义,也促使带有西方背景的“西洋历”逐渐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太阳历”转变。梳理晚清“西洋历”(西历)蜕变为“太阳历”(阳历)的过程,其背后的思想原因十分值得分析:一是“太阳历”比“西洋历”的名称更符合历法本身的特点,且从晚清时人的述论来看,现代人的社会活动与太阳的关系更为密切,加之太阳历不隔年置闰月,反利于财政、教育、农事等的安排,从实用角度更有利于社会时间秩序的构建;二是“太阳历”或“阳历”的名称已经超越了“西洋”的地理局限,开始成为世界通用的历法,其中包含了近代国人追寻公理公例、意图富国强兵的愿望;三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以“阳历”命名的格里高利历在19世纪后期已成为全球通用的时间体系,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构建都受到这一时间体系的影响。
“与世界大同”:国历与公历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阳历成为政府主导推行的历法。但由于普通民众在知识体系和日常生活中对阳历的陌生感,阳历所具有的西方背景和宗教色彩等,使得阳历在民初的推行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改换阳历的名称,重构阳历的思想因素,就成为民初推行新历的重要举措之一。
将阳历的宗教内涵和使用的普遍性进行区分,是时人重构阳历思想因素的基本路径。晚清时期,康有为、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人,都受到了基督纪年方式的影响,试图模仿它在中国建立起一以贯之的纪年体系,分别提出了“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和“西周共和元年纪年”等主张。不过,在他们的述论中,将“基督纪年”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因素视为“公理”“公例”,用以述论各自纪年主张的合理性。因而,当民初阳历推行不畅时,将宗教性因素从阳历中剥离出来,就成为时人的重要尝试。其中钱玄同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1919年11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集中地阐释了他将“基督纪年”改称“世界公历纪年”的缘由。在他看来,基督纪年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其逐渐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局限,成为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计时工具。这一主张相比于清末梁启超的《纪年公理》《太阳历法议》等文章,更加着重从时间计量符号简便易行的角度来述论使用阳历之必要性,重构了“阳历”的内容意涵,使之成为世人眼中的“公共历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逐步去掉了这一历法原来所具有的宗教性因素。
而“国历”名称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推动的国历运动。早在1922年钱玄同就已经提出了“国历”一词,指称“中华民国之历法”,用以对抗守旧的“满清遗老”。但将“国历”名称扩展到整个社会,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动的“废除旧历,普用国历”运动。这次改历运动比民国之初废除阴历运动,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尽管国历包含了沟通中西的便利性,但其塑造民国认同的指向,也彰显了“国历”名称更为强烈的政治意涵。
“公历”与“国历”实际上指同一历法,但名称的差异仍表明两者意涵指向的区别:“国历”名称意在强调该历法为中华民国使用之历法,欲强化中华民国之权威;而“公历”的名称,正是消解了阳历的西方色彩和宗教性因素,更强调了这一历法使用的普遍性。不过,1912年孙中山在宣布使用阳历的同时,也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纪年”和“国历”名称与强调世界大同的“公历”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尽管“国历”为“阳历”的别称,“公历”也是指同一历法,但“国历”还应该包括了“中华民国纪年”这一内容,其名称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公历”名称的传播。
知识重构:阴历、旧历、废历和农历
阳历名称蜕变为“国历”和“公历”,是政府及时人构建新时间秩序的努力之一。不过,阻碍新时间体系推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深厚基础及其使用的广泛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除了通过政策法令限制或废止阴历,还试图从名称上对阴历进行重构。而这种重构则是在参照阳历名称下进行的,并与阳历、新历等名称形成了一种区隔对立的关系。
就以“阴历”名称的蜕变来看,在明末清初西洋历法进入中国后,当时人们为了区分西洋历法,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中历”。进入晚清之后,随着人们对西洋历法的“阳历”特点认识深入,以“阳历”作为参照,“阴历”的名称才日渐流行。而中西新旧二元话语体系的形成,“阴历”与“阳历”名称日渐固化,反过来影响了时人对中西两种历法内涵的认识。中国传统历法兼顾地球绕日和月绕地球周期运动。但更多的人将阳历和阴历对立而论,这种名称上的区分,导致时人忽略了中国传统历法作为阴阳合历的特点,且因民国建立之后新旧历法的对立而进一步固化。这些例证至少说明,“阳历”名称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新历的代名词;而中国传统历法则被局限到与之相对的“阴历”框架之内,并且在阳历的参照之下丧失了原有的丰富内涵。此种情况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官定历书中有最直接的反映,历日编排以阳历为主导,一般放置于历书的上方,而阴历则附于阳历之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国历运动,新编订的官定历书甚至要删去以往历书中的朔望等内容,因为它们属于清代官定历书的“阴历”内容。
由于“阳历”作为塑造政治权威与革新社会的重要标志,与之相对的“阴历”就成为了新秩序构建和社会革新的障碍。在清末民初主张革新历法的人看来,阳历是西方国家富强文明的重要标志,使用阳历可以让中国耳目一新,“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而“阴历”则是中西交通和中国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国际体系在全球的扩展,格列高利历逐渐成为全球通用时间体系,中国要置身于这一国际体系自然需要遵从其时间秩序。时人已经认识到推行阳历是中弱西强的结果,预设了阳历比阴历更为现代,实际上是期望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而实现富强。因此,阴阳、新旧与中弱西强的处境产生了直接关联,两者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阳历被中华民国确立为官定历法,自然就成为当政者统一时政和塑造权威的工具,而制约阳历推行的阴历就成为新秩序构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新历”指称“阳历”所要凸显的正是这一历法对于构建新政治秩序的意义。与此对照,作为传统象征和代表的“阴历”无法满足趋新时人革新之期待,被称为“旧历”,甚至是“废历”。推行新历遇到阻碍,使得趋新之士的改历主张愈加极端,必欲废除旧历而后快。正是在这种取向之下,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观象台通过“查禁私历”和“删改旧历”,以实现“时政划一”的目标,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推行国历运动,彻底禁止阴历的使用,并将使用阴历视为落后、反动的标志,甚至宣扬“彻底革命,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历法新旧对立的二元格局。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时人将“科学性”视为阳历最突出的特点,与之相对,附着了传统信仰习俗的阴历则被视为“迷信”的代表。尽管阳历与阴历各有利弊,但在清末民初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时人并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两种历法各自的优劣。更为关键的是,在时人看来,这一历法是以现代科学作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阳历“先进”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旧历附加了太多的神煞宜忌,在时人看来,使用阴历就有助长“迷信”的消极作用。而时人也正是参照了具有“革命”“进步”和“科学”特质的阳历,对阴历名称及内涵进行了重构,形成了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阴历”从晚清时期着重反映历法特点的名称,到民国时期逐渐被趋新之士和政府当局赋予了更多负面的含义,进而蜕变为“旧历”“废历”,被塑造成了“专制”“落后”和“迷信”的面目。这一变化过程也凸显了“阳历”以及“新历”“公历”等名称的“积极”意义。
而“农历”名称的出现,既是历法新旧之争的副产品,也是历法改革者对阴历广泛使用现实的妥协。“农历”名称的重构,是在科学与权威的视角下进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废止旧历以及附着于旧历之上的迷信习俗,仅仅将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纳入到“农历”中,从而构建“科学”的历法,以便与国历保持一致。从权威的角度来看,趋新之士与政府都希望在农村推行国历,以实现时政统一,强化政府的政治权威。经过重构的“农历”,尽管其名称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但依从于原有时间体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以科学的名义试图改正民众的民俗习惯,以权威的名义推行与民众生活不相协调的时间体系,反而导致了官民之间的对立,“农历”作为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实际使用中逐渐成为“旧历”的代名词。这也是西历成为“国历”,变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公历”,相对立的“中历”、“农历”蜕变为地方性及局部性的计时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过程。
余论
清末民初之际,西洋历法从外在于中国的时间架构,变成为中国社会时间秩序的主导,并成为时人眼中的“公共历法”,其中名称的转换至关重要。“国历”“公历”等新词语的引入,也是趋新时人与政府试图通过改换历法名称,在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尝试。通过历法正名,为中国嵌入世界通用时间体系扫除了学理上的障碍,又凸显了中国在接纳这一时间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在中西二元话语体系中的新旧阴阳却具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交错的意涵指向。如“阳历”蜕为“国历”,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并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对西方“先进”历法的借鉴;而“公历”的世界主义指向虽更为明确,却是以消解了“阳历”的西方特色为前提,与已沦为地方性时间的中国传统历法相对立的。
从更深层次上看,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既消解了中国传统时间体系的独立性,又加剧了清末民初以来社会时间的纷歧,使得历法名称及其使用的统一问题得以凸显。以标准化时间为基础所构建的现代工业、学校教育、财政预算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成为推动中国在历法时间上趋同西方的重要因素。但清末民初历法改革导致的阴历与阳历并存,反倒使得原有的单一历法体系变成了阴阳并存的二元格局,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这些对阴历和阳历便利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中国被纳入到全球标准时间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讨论的预设都是以强势的阳历作为参照,进而比较两种历法的优劣,而阳历的“正名”无非是要构建其在时间秩序中的主导性地位。
正是由于时人赋予历法变革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推行阳历所具有的革新作用,也使得近代中国历法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国家危亡情感诉求的结果。因而时人论述阳历的优点时,对这一异质历法体系与中国文化传统、信仰习俗之间的冲突,并无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在趋新崇洋的背景之下,反思西历使用困境的文章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近代中国面对全球标准时间不断扩张的大势,以及国人革新社会的强烈诉求,有关中国历法的理性言论并未得到时人足够重视。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晚清民国时期历法名称改换,政府与民众在历法使用、名称改换上呈现出对立之势。一方面,民国时期政府通过推行阳历,并通过在官定历书中删除阴历,期望以这种方式实现“时政划一”的目标,但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强行改换历法名称和禁止使用旧历,又强化了阴历与阳历等名称的对立,使得人们在认识中国历法变化时,捉襟见肘:被重构的历法名称难以涵盖历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其中阴历的名称与实际之间难以完全吻合,甚至影响了后人对中国传统历法的理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历法的正名运动,并非呈现出线性的演化更替进程,时至今日,公历、阳历、阴历、农历等历法名称仍然被广泛使用,尽管已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但各自仍有较为清晰的论域范围和内容指向。这也是近代历法“正名”运动留下的遗产。